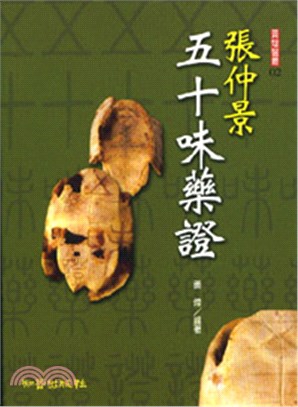商品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藥證是中醫用藥的指徵和證據,是中醫幾千年用藥經驗的結晶。藥證相應,是中醫臨床處方用藥的原則和臨床取效的前提。
張仲景是東漢著名醫學家,被歷代醫家尊為醫聖。但後世流傳的《傷寒論》《金匱要略》僅是方書,其應用單味藥物的指徵和經驗尚無專門論述。為探討張仲景對常用藥物應用的指徵和經驗,本書通過對《傷寒論》《金匱要略》有關條文的比較分析,結合作者的臨床經驗,就張仲景常用的50味藥物的臨床應用指徵進行了闡釋。
全書思路新穎,內容樸實簡潔,切合實用,可供臨床醫生、中醫院校師生、中醫藥科研人員以及中醫愛好者學習與參考。
目次
1.桂枝
2.芍藥
3.甘草
4.大棗
5.麻黃
6.附子
7.烏頭
8.乾薑
9.生薑
10.細辛
11.吳茱萸
12.柴胡
13.半夏
14.黃耆
15.白朮
16.茯苓
17.豬苓
18.澤瀉
19.滑石
20.防己
21.葛根
22.栝蔞根
23.黃連
24.黃芩
25.黃柏
26.梔子
27.大黃
28.芒硝
29.厚朴
30.枳實
31.栝蔞實
32.薤白
33.石膏
34.知母
35.龍骨
36.牡蠣
37.人參
38.麥門冬
39.阿膠
40.地黃
41.當歸
42.川芎
43.牡丹皮
44.杏仁
45.五味子
46.桔梗
47.葶藶子
48.桃仁
49.蟅蟲
50.水蛭
附錄:《傷寒論》《金匱要略》方劑一覽
2.芍藥
3.甘草
4.大棗
5.麻黃
6.附子
7.烏頭
8.乾薑
9.生薑
10.細辛
11.吳茱萸
12.柴胡
13.半夏
14.黃耆
15.白朮
16.茯苓
17.豬苓
18.澤瀉
19.滑石
20.防己
21.葛根
22.栝蔞根
23.黃連
24.黃芩
25.黃柏
26.梔子
27.大黃
28.芒硝
29.厚朴
30.枳實
31.栝蔞實
32.薤白
33.石膏
34.知母
35.龍骨
36.牡蠣
37.人參
38.麥門冬
39.阿膠
40.地黃
41.當歸
42.川芎
43.牡丹皮
44.杏仁
45.五味子
46.桔梗
47.葶藶子
48.桃仁
49.蟅蟲
50.水蛭
附錄:《傷寒論》《金匱要略》方劑一覽
書摘/試閱
前 面 的 話
一、關於藥證
藥證是中醫臨床用藥的指徵和證據,也稱藥物主治。如用麻黃的指徵和證據即為麻黃證,桂枝的主治即為桂枝證。有是證,用是藥,是中醫幾千年相傳的醫學準則。
藥證不是來自理論的推測,也不是來自動物試驗的數據,而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抵抗疾病的經驗結晶,更確切地說,是無數的先人用自己的身體嘗試藥物得出的結論。“神農嘗百草”的傳說,就是最好的佐證。
藥證是以人為背景的。如果說,西醫是治“人的病”,那麼,中醫是“治病的人”,藥證是以“病的人”為背景的。所以《傷寒雜病論》中有“其人”、“瘦人”、“中寒家”、“濕家”、“尊榮人”、“強人”、“羸人”、“冒家”、“失精家”等諸多提法。藥證將病人的體質、症狀和體徵、精神心理狀態及行為、生存質量作為其構成的部件,患者的胖與瘦、強與羸,面黃與面白,惡寒與惡熱,發熱與不發熱,出汗與不出汗,能食與不能食,嘔與不嘔,下利與便秘,出血與不出血,心下滿痛與心下痞,咳逆上氣與短氣,胸滿與腹滿,苦滿與硬滿,口渴與口不渴,小便利與小便不利,煩與不煩,眩與不眩,欲寐與不得臥,默默不語與其人如狂,氣上衝與短氣,咽喉不利與咽痛,脈浮與脈沉,脈緩與 脈促等等,均成為醫生臨床用藥的著眼點。療效判定的標準,也在於汗出與否, 脈出與否,口渴與否,血止與否,能食與否,安臥與否等等基本生命指徵。對證下藥的目的,也就是解除病人的痛苦。這個苦,就是患者的整體主觀感受。其中包括了肉體的痛苦,也包括了精神的痛苦和生活質量的下降。可以說,中醫學將解除病人痛苦和提高生存質量作為取效的最終目標和最高境界。
藥證是客觀的。它來自幾千年的臨床實踐,具有實證性。它不是哲學的 概念,也不是宗教式的感悟,而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張仲景說“觀其脈證”,就是說脈證是客觀的。藥證可以證偽,可以通過實踐進行驗證其正確與否。臨床上有是證必用是藥,用是藥必見是效。反之,有是證不用是藥,用是藥不見是證,則其結局必然是無效。其間容不得絲毫虛假與偏差。因此說藥證是實在的、是客觀的。客觀即可證偽,證偽即可存真。
藥證是具體的,也是樸素的。其內容沒有陰陽五行、元氣命門;也沒有肝陽心火、脾虛腎虛等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概念。而是老老實實從病人身上尋找用藥根據。病人體型的高矮胖瘦,皮膚的黑白潤枯,肌肉的堅緊鬆軟以及口、眼、鼻、舌、唇、喉、脈、腹、血液、分泌物、排泄物等病態表現,才是構成藥證的重要因素。藥證是構成中醫學各種概念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藥證是八綱、六經、病因、臟腑、氣血津液、衛氣營血、三焦等各種辨證方式的最具體的表現形式。不熟悉藥證,就無法理解中醫學。
藥證是綜合的。藥證既不同於現代中醫學所說的“證”,也不同於西醫學所認識的“病”,藥證是用藥經驗的概括與提煉。離開了具體的藥物,就無從談起藥證是什麼。因為有的藥證,就是現代醫學所說的某種病名,有的則是某種綜合徵,有的乾脆是某個症狀,而有的是某種體質狀態。
藥證是穩定的。人類有文明以來,疾病譜已經發生了多次變化,一些疾病被控制了,另一些新的疾病又發生了。過去沒有愛滋病,沒有埃博拉病毒,沒有O-157大腸菌,沒有SARS,但現在出現了,可見疾病種類是不斷變化的。但是,人的機體在疾病中的反應方式是幾乎不變的,發熱、咳嗽、昏迷、出血……,機體在疾病過程中的症狀和體徵,古人和今人也沒有多少區別。藥證是由症狀和體徵構成的診斷單元,所反映的是“人”的病理反應狀態,而不是“病”的病原體,所以,藥證是穩定的,幾千年來幾乎是不變的,並不會隨著疾病的變化而變化。不論在什麼時代,是什麼疾病,只要出現柴胡證、桂枝證,就可以用柴胡,就可以用桂枝,張仲景時代是這樣,我們這個時代也如此。所以,藥證是最經得起重複的。清代名醫徐靈胎說:“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變遷無定,知其一定之治,隨其病之千變萬化,而應用不爽”(《傷寒論類方》自序),就是這個道理。
藥證是嚴謹的。有是證,則用是藥;無是證,則無是藥。加藥或減藥,都以臨床見證的變化而變化,決不能想當然地隨意加減。以桂枝湯為例,證見惡風、汗出、脈浮者用之。如汗出多,惡寒關節痛者,必加附子;如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又必加人參;如氣從少腹上衝心者,則又要加桂二兩;腹中痛者,則當加芍藥;如無汗而小便不利者,則要去桂枝,加白朮、茯苓。所加所減,皆有根有據。喻嘉言說的好“有是病用是藥,病千變,藥亦千變”。 但不管是千變還是萬變,藥證依然是應變的準繩。嚴謹性決定了藥證必然是臨床化裁經方的 依據所在。
藥證是科學的。所謂科學,就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反映客觀事實和規律的知識。達爾文說:“科學就是整理事實,以便從中得出普遍的規律或結論”。所謂規律,就是客觀事實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是事物發展過程中事實之間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繫,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反覆出現的,是客觀的。藥證來源於大量臨床的事實,歷經了無數醫家的實踐檢驗,反映了藥物與疾病之間的必然的聯繫,具有極強的可重複性,有極強的科學性,是中醫學中極具魅力的東西。
藥與證本是一體的。一個蘿蔔一個坑,一味中藥一味證,藥證之間具有很強的特異性與針對性,如形影相伴時刻不離。嚴格地講,每一味經典藥都應該有與它相對應的運用指徵。用此藥必有此證,見此證必用此藥,無此證必去此藥。真正的藥物必須具備兩個特性,即嚴格的適應證和可以重複的療效。藥與證的相互對應即是藥證相應,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對證下藥”。
以藥名證的方法,源於漢代名醫張仲景。《傷寒論》中有“桂枝證”、“柴胡證”的提法,《金匱要略》中有“百合病”的名稱,這就是藥證。中醫的初學者大多認為中醫的用藥是嚴格地按照理-法-方-藥的程序進行的,但實際卻恰恰相反,在許多有經驗的臨床醫生的眼裏,面對患者,他首先看到的可能是“某某藥證”或“某某方證”,然後才上升為“某某治法”或“某某理論”。每味藥物,均有其嚴格的適應證,每張方,也有其特定的藥物組合,所以,藥證的識別極為重要,它是制方遣藥的基礎。正如鄒澍所說:“不知一病有一病之方,一方有一方之藥,一藥有一藥之效,不能審藥,何以定方?不能定方,何以治病?”
(《本經疏證 序》)
藥證是構成方證的基礎,方證是放大了的藥證。兩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所以,宋代名醫朱肱將藥證和方證是合稱的。他說:“所謂藥證者,藥方前有證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類證活人書》)。但是,單味藥證與方證是有區別的。方證不是幾味藥證的簡單疊加,而是一個複雜的組合,它們是新的整體,所以必須將方證看作是一味藥證。
二、關於藥證相應
藥證相應是中醫取效的前提。要取得療效,藥證必須相應,藥證本是一體的。《傷寒論》所謂“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317條),即用此藥必有此證,見此證必用此藥。中醫的臨床療效往往取決於藥證是否相應,也就是人們所 說的“對證下藥”。如把桂枝比作箭,桂枝證就是目標,目標對準了,命中率就高,同樣,藥證、方證相對了,療效自然會出現。換句話說,藥證相對了,這就是必效藥、特效藥;不對應,則是無效藥。這是中醫取效的關鍵。“古人一方對 一證,若嚴冬之時,果有白虎湯證,安得不用石膏?盛夏之時,果有真武湯證,安得不用附子?若老人可下,豈得不用硝、黃?壯人可溫,豈得不用薑、附?此乃合用者必須之,若是不合用者,強而用之,不問四時,皆能為害也”。(《金鏡內臺方義》)所謂的合用,就是相應。
藥證相應是天然藥物的臨床應用原則。天然藥物的成分極其複雜,藥物下嚥究竟起到何種效應?要真正解明其中奧妙,恐怕相當困難。所以,若以實驗室的動物試驗數據,加上現代醫學現階段對人體生理病理的認識,去指導對人體的天然藥物的傳統使用(煎劑、丸劑、散劑的傳統劑型),其可靠性是值得懷疑的。更何況,我們讓患者服的藥是飲片,是沒有分離過的天然藥物,幾乎所有的 藥物成分均要下嚥,所以,希望其中某種成分起作用只是良好的願望,事實如何又是另一回事了。科學的態度應當是尊重前人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經驗和久經實踐證明的事實,總結其中的規律。藥證相應的臨床應用原則是不容忽視的。
藥證相應體現了中醫學診斷與治療的一體性原則。現代醫學出現有診斷而無治療的情況是不必見怪的,而中醫雖然無法斷定是哪種疾病,但依然可以識別藥證,有藥證就有治療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藥證不是針對某種疾病病原體的,而是針對疾病中的人體。所以,與其說藥證是藥物的臨床應用指徵,倒不如說是人體在疾病狀態中的斷面和病理反應在體表的投影。應用科學的方法研究藥證,必然揭示現代醫學尚未發現的人體病理變化的新規律。
藥證識別是檢驗一個中醫臨床醫生實際工作能力的標誌。前人常以“絲絲入扣”、“辨證精細”等詞來形容名醫的用藥功夫,但由於藥證識別的準確率常與人們的臨床經驗、思想方法、即時精神狀態有關,故絕對的藥證相應僅是一種理想狀態。藥證相應是中醫臨床工作者始終追求的目標。
三、關於張仲景藥證
嚴格地講,所有被稱為“中藥”的藥物應該都有藥證,但事實不是如此。中醫學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僅僅發現了一部分天然藥物的藥證,這些已經發現的、並在臨床上起著重要指導作用的藥證,主要集中在《傷寒論》、《金匱要略》中,我們稱之為張仲景藥證。
張仲景的藥證是中醫的經典藥證。《傷寒論》、《金匱要略》非一人一 時之作,仲景既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在前,王叔和、“江南諸師”補充在後,故 仲景藥證也非仲景一人之經驗,而是總結了漢代以前的用藥經驗,而且經過後世 數千年無數醫家的臨床驗證被證實並發展,其臨床指導意義是不言自明的。所以 ,成無己說“仲景之方,最為眾方之祖。”張元素說“仲景藥為萬世法。”王好 古說“執中湯液,萬世不易之法,當以仲景為祖。”徐靈胎說的更為明白:“古 聖治病之法,其可考者,唯此兩書。”可以這麼說,張仲景藥證是構成後世臨床 醫學的基礎,離開了它,中醫學將變成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用中藥治病,若不 明仲景藥證,無疑是掩目而捕燕雀,亂摸而已。許多青年中醫使用中藥療效不明 顯,大部分是與對張仲景藥證不熟悉有關。
《傷寒論》、《金匱要略》的用藥十分嚴格,有是證,則用是藥;無是 證,則不用是藥,加藥或減藥,都以臨床見證的變化而變化,決不能想當然地隨 意加減。故惡風、汗出、脈浮用桂枝湯,如汗出多,惡寒關節痛者,必加附子, 名桂枝加附子湯。如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又必加人參,名新加湯。如無 汗而小便不利者,則要去桂枝,加白朮、茯苓,這就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治心下悸,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則為咳逆上氣。大劑量藥 與小劑量藥的主治也不相同,同樣是桂枝湯的組成,但桂枝加桂湯的桂枝5兩,其 主治為氣從少腹上衝心者;桂枝湯倍芍藥主治腹中急痛,方名也改為桂枝加芍藥 湯;再加飴糖,又名小建中湯。又雖用過某藥,但其證未去,則仍可使用某藥, 如《傷寒論》“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太 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若不上衝者,不得與之”。這種 用藥法,體現了張仲景用藥極為嚴格的經驗性。《傷寒論》、《金匱要略》是研 究藥證的最佳臨床資料。
《神農本草經》雖然是最古的本草書,其中有許多研究藥證極為重要的 內容,但畢竟不是“疾醫”所著。全書收載藥物365味,與一年天數相應。全書分 上、中、下三品,書中“輕身”、“不老”、“延年”、“通神仙”等語比比皆 是,摻雜了不少道家黃老之學。全書在如何使用這些藥物方面,論述略而不詳。 而《傷寒論》、《金匱要略》在記載病情上忠於臨床事實,表述客觀具體,完全 是臨床家的書。兩書雖為方書,但通過適當的研究,完全可以理清張仲景用藥的 規律,破譯出一本《中醫經典臨床藥物學》。
張仲景藥證的研究主要採用比較歸納的方法,通過同中求異、異中求同 ,互文參照,來分析仲景用藥的規律。以下的原則可以參照。
最大量原則:《傷寒論》、《金匱要略》中同一劑型中的最大用量方,其指 徵可視為該藥藥證。例如仲景湯方中,桂枝加桂湯中桂枝5兩,為《傷寒論》中桂 枝最大量方,主治氣從少腹上衝心者。原文“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 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則其氣從少腹上衝心是桂枝證的主要內容。
最簡方原則:配伍最簡單的處方,其指徵可視為該藥藥證。如桂枝甘草湯( 2味)主治“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則心下悸,欲得 按為桂枝證的主要內容。此外,桔梗湯證對桔梗證的研究,四逆湯證對附子證的研究,都具有特別的意義。
量證變化原則:即症狀隨藥量變化而變化者,該症狀可視為該藥藥證。如黃 耆最大量方(5兩)的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主治“黃汗之為病,身體腫,發熱汗出 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柏汁,脈自沉。”(十四)其證之一是浮腫 ,且是全身性的,因風水為“一身悉腫”。其證之二為汗出,汗出能沾衣,可見 其汗出的量較多。桂枝加黃耆湯(2兩)主治“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必身 , 即胸中痛,有從腰以上必汗出,下無汗,腰髖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痛,煩躁、小便不利,此為黃汗”;“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主之”。原文提示,患者腰以下無汗出,再加此證的治法當以汗解,其出汗的程度是較輕的,所以黃耆僅用2兩。根據以上 兩方證的比較可以發現,黃耆用於治療自汗,汗出的程度越重用量越大。又如葛 根,葛根黃芩黃連湯為葛根的最大量方(8兩),主治“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 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利遂不止,指泄瀉不止。葛 根湯類方中用於下利的有葛根湯。原文為“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自
下利,為未經攻下而大便自然溏薄者,其程度要比葛根黃芩黃連湯證的“利遂不 止”為輕,故用量僅為4兩。可見葛根用於下利,下利的程度越重,其用量也越大 。
味證變化原則:即藥物的增減變化帶來應用指徵的變化,則隨之增減的指徵 可視為該藥藥證。如《傷寒論》理中湯條下有“若臍上筑者,腎氣動也,去朮加 桂四兩”。四逆散條下有“悸者加桂枝五分”。《金匱要略》防己黃耆湯條下有 “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可見臍上筑、悸、氣上衝,均為桂枝主治。《傷寒論 》中有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原文為:“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 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可見 無衝逆證,也無自汗證。
頻率原則:應用統計方法,凡頻率越高,其屬於該藥藥證的可能性越大。如 柴胡類方中,凡大劑量柴胡與黃芩同用,其指徵都有往來寒熱,並有嘔而胸 苦 滿。如除去黃芩證,則柴胡證自明。
仲景藥證是比較成熟的藥證,需要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去搞清其所以然, 這樣可以發現一些現代醫學尚未發現的病症,也可揭示出人體生理病理上的某些 規律,還可使藥證的識別趨於客觀化,並使藥物的臨床應用範圍更清晰。通過現 代研究,有的藥物可能成為治療現代某種疾病的特效藥,有的則可能成為改善體 質的新型藥物,而有的可能還一下弄不清楚,還必須按照傳統的藥證用下去,這 都是可能的。要完全揭開藥證的實質,恐怕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所以,傳統的藥 證需要繼承,特別是仲景藥證更應繼承好,傳下去。
四、關於本書的宗旨
《傷寒論》114方,有名有藥者113方,91味藥,其中1方次36藥,2方次 以上55藥。《金匱要略》205方,有名有藥者199方,156味藥,其中1方次62藥, 2方次以上94藥。本書選擇臨床常用且仲景敘述藥證比較明確的藥物50味,分原文 考證、藥證發揮、仲景方根、常用方四部分重點論述藥物主治。雖說僅50味, 但每味藥均為常用藥,只要掌握好每藥的主治和常用配伍,則在臨床自能演化出 無數新方。
“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宋 蘇軾)。由於《傷寒論》 、《金匱要略》是臨床實踐的真實記錄,故歷代醫家都主張對仲景書要反覆研讀 ,特別在臨床上認真研究,能不斷取得新的認識。陳修園說他讀仲景書“常讀常 新”,就是這個意思。本書中的藥證發揮,為筆者的研究心得,其中肯定有許多 不當之處,隨著研究的深入,臨床經驗的增加,必然要有改進,這點必須說明。
規範化是一門學科發展的必要條件,藥證的研究就是試圖建立中醫臨床 用藥的規範。這項研究工作,歷史上中日兩國的醫家已經有了令人起敬的成績。 清代傷寒家的崛起,近代經方家的出現,日本古方派的實踐,都是為了建立一種 理論與臨床的規範,促使醫學的健康發展。代表者是清代醫家鄒澍的《本經疏證 》和日本的古方派大家吉益東洞的《藥徵》。筆者的工作,是在他們的基礎上進 行的。當前,中醫學庸俗化的趨向比較突出,青年中醫往往在不切實際的一些理 論中糾纏不清,辨證論治成為一種踏虛蹈空式的遊戲,而臨床療效的不明確,又 極大地挫傷了他們研究中醫藥的熱情。究其原因,主要應歸結為《傷寒論》、《 金匱要略》的功底不深,特別是對仲景藥證缺乏研究。如此以往,中醫學的實用 價值必將大大降低。另外,許多中醫的實驗研究,選擇的“證”大多是含糊模稜 的,往往缺乏特異性的方藥相對應,而表現在實驗動物身上的“證”更是缺乏必 要的可信度,其研究結果不能讓人十分信服,這也影響了中醫現代化的進程。有 慨於此,而作此書。希望通過筆者的工作,喚起大家對古典中醫學的重視。繼往
才能開來,根深才能葉茂,中醫學的發展離不開對古代優秀遺產的繼承,因為這 裏有中醫學的根。
黃 煌
於南京中醫藥大學 2005年1月
幾 點 說 明
一、為節省篇幅,正文中所引《傷寒論》、《金匱要略》方劑的組成、劑量、煎服法等均未注明,請查閱書後附錄的方劑一覽。
二、本書《傷寒論》原文,以明代趙開美復刻的宋本《傷寒論》為藍本(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出版),每條注明阿拉伯字文號。《金匱要略》(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年出版)則以中文注明篇號。
三、原文考證為根據《傷寒論》、《金匱要略》原文,歸納分析仲景藥物的主治。其主治盡可能採用仲景原有的術語。每味藥物的主治,均為傳統內服劑型的主治,至於外用劑型的主治則另需研究,本書沒有涉及。
四、藥證發揮為結合臨床對仲景藥證進行的闡述和解釋。為了臨床應用和記憶,筆者將一些比較客觀的用藥指徵,直接冠以某某舌、某某脈、某某腹、某某體質的名稱,諸如“桂枝舌”、“大黃舌”、“附子脈”、“黃耆肚”、“柴胡體質”等。這種提法,參照了《傷寒論》、《金匱要略》中“桂枝證”、“柴胡證”、“病形像桂枝”等說法。這本是一種略稱,並非中醫固有術語。
五、仲景方根為仲景配方的基本結構。本書通過原文作了初步的總結歸納,並附有配伍一覽表。
六、常用配方為臨床常用的經典方,其中絕大部分是《傷寒論》、《金匱要略》中的方劑,其劑量按照一兩=3克的標準進行折算,藥物之間的比例基本上遵循仲景原意。少數經方折算以後用量與現代臨床相差較大時,或無劑量可換算時,則代以筆者臨床常用量。劑量的問題一直被稱為中醫的“不傳之秘”,很難說清楚,其中有醫家個人的獨特經驗和地域性的應用習慣,目前尚不能作硬性的規定。不過,筆者提倡要以尊重經方的內部結構為原則,藥物的配伍比例需要重視
。常用配方中也有少數後世常用方,這些方久經臨床檢驗,療效肯定,已經與經典方同類。應當說明,本書非方劑全書,後世尚有許多名方不能一一收錄。劑型、煎服法是經方取效的關鍵所在,讀者可參照本書附錄的《傷寒論》、《金匱要略》方劑一覽,在實踐中認真研究。常用配方的應用指徵及其病種的確定,參照了有關臨床報導及筆者臨床經驗,僅供參考。
七、傳統中藥學對藥物的功效有獨到的解釋,現代中藥藥理研究也有豐富的成果,這些都是研究藥證的極為重要的資料,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查考這方面的教材和專著,必將加深對張仲景藥證的理解。
一、關於藥證
藥證是中醫臨床用藥的指徵和證據,也稱藥物主治。如用麻黃的指徵和證據即為麻黃證,桂枝的主治即為桂枝證。有是證,用是藥,是中醫幾千年相傳的醫學準則。
藥證不是來自理論的推測,也不是來自動物試驗的數據,而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抵抗疾病的經驗結晶,更確切地說,是無數的先人用自己的身體嘗試藥物得出的結論。“神農嘗百草”的傳說,就是最好的佐證。
藥證是以人為背景的。如果說,西醫是治“人的病”,那麼,中醫是“治病的人”,藥證是以“病的人”為背景的。所以《傷寒雜病論》中有“其人”、“瘦人”、“中寒家”、“濕家”、“尊榮人”、“強人”、“羸人”、“冒家”、“失精家”等諸多提法。藥證將病人的體質、症狀和體徵、精神心理狀態及行為、生存質量作為其構成的部件,患者的胖與瘦、強與羸,面黃與面白,惡寒與惡熱,發熱與不發熱,出汗與不出汗,能食與不能食,嘔與不嘔,下利與便秘,出血與不出血,心下滿痛與心下痞,咳逆上氣與短氣,胸滿與腹滿,苦滿與硬滿,口渴與口不渴,小便利與小便不利,煩與不煩,眩與不眩,欲寐與不得臥,默默不語與其人如狂,氣上衝與短氣,咽喉不利與咽痛,脈浮與脈沉,脈緩與 脈促等等,均成為醫生臨床用藥的著眼點。療效判定的標準,也在於汗出與否, 脈出與否,口渴與否,血止與否,能食與否,安臥與否等等基本生命指徵。對證下藥的目的,也就是解除病人的痛苦。這個苦,就是患者的整體主觀感受。其中包括了肉體的痛苦,也包括了精神的痛苦和生活質量的下降。可以說,中醫學將解除病人痛苦和提高生存質量作為取效的最終目標和最高境界。
藥證是客觀的。它來自幾千年的臨床實踐,具有實證性。它不是哲學的 概念,也不是宗教式的感悟,而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張仲景說“觀其脈證”,就是說脈證是客觀的。藥證可以證偽,可以通過實踐進行驗證其正確與否。臨床上有是證必用是藥,用是藥必見是效。反之,有是證不用是藥,用是藥不見是證,則其結局必然是無效。其間容不得絲毫虛假與偏差。因此說藥證是實在的、是客觀的。客觀即可證偽,證偽即可存真。
藥證是具體的,也是樸素的。其內容沒有陰陽五行、元氣命門;也沒有肝陽心火、脾虛腎虛等看不見摸不著的抽象概念。而是老老實實從病人身上尋找用藥根據。病人體型的高矮胖瘦,皮膚的黑白潤枯,肌肉的堅緊鬆軟以及口、眼、鼻、舌、唇、喉、脈、腹、血液、分泌物、排泄物等病態表現,才是構成藥證的重要因素。藥證是構成中醫學各種概念的最基本最重要的要素。藥證是八綱、六經、病因、臟腑、氣血津液、衛氣營血、三焦等各種辨證方式的最具體的表現形式。不熟悉藥證,就無法理解中醫學。
藥證是綜合的。藥證既不同於現代中醫學所說的“證”,也不同於西醫學所認識的“病”,藥證是用藥經驗的概括與提煉。離開了具體的藥物,就無從談起藥證是什麼。因為有的藥證,就是現代醫學所說的某種病名,有的則是某種綜合徵,有的乾脆是某個症狀,而有的是某種體質狀態。
藥證是穩定的。人類有文明以來,疾病譜已經發生了多次變化,一些疾病被控制了,另一些新的疾病又發生了。過去沒有愛滋病,沒有埃博拉病毒,沒有O-157大腸菌,沒有SARS,但現在出現了,可見疾病種類是不斷變化的。但是,人的機體在疾病中的反應方式是幾乎不變的,發熱、咳嗽、昏迷、出血……,機體在疾病過程中的症狀和體徵,古人和今人也沒有多少區別。藥證是由症狀和體徵構成的診斷單元,所反映的是“人”的病理反應狀態,而不是“病”的病原體,所以,藥證是穩定的,幾千年來幾乎是不變的,並不會隨著疾病的變化而變化。不論在什麼時代,是什麼疾病,只要出現柴胡證、桂枝證,就可以用柴胡,就可以用桂枝,張仲景時代是這樣,我們這個時代也如此。所以,藥證是最經得起重複的。清代名醫徐靈胎說:“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變遷無定,知其一定之治,隨其病之千變萬化,而應用不爽”(《傷寒論類方》自序),就是這個道理。
藥證是嚴謹的。有是證,則用是藥;無是證,則無是藥。加藥或減藥,都以臨床見證的變化而變化,決不能想當然地隨意加減。以桂枝湯為例,證見惡風、汗出、脈浮者用之。如汗出多,惡寒關節痛者,必加附子;如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又必加人參;如氣從少腹上衝心者,則又要加桂二兩;腹中痛者,則當加芍藥;如無汗而小便不利者,則要去桂枝,加白朮、茯苓。所加所減,皆有根有據。喻嘉言說的好“有是病用是藥,病千變,藥亦千變”。 但不管是千變還是萬變,藥證依然是應變的準繩。嚴謹性決定了藥證必然是臨床化裁經方的 依據所在。
藥證是科學的。所謂科學,就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是反映客觀事實和規律的知識。達爾文說:“科學就是整理事實,以便從中得出普遍的規律或結論”。所謂規律,就是客觀事實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是事物發展過程中事實之間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聯繫,是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反覆出現的,是客觀的。藥證來源於大量臨床的事實,歷經了無數醫家的實踐檢驗,反映了藥物與疾病之間的必然的聯繫,具有極強的可重複性,有極強的科學性,是中醫學中極具魅力的東西。
藥與證本是一體的。一個蘿蔔一個坑,一味中藥一味證,藥證之間具有很強的特異性與針對性,如形影相伴時刻不離。嚴格地講,每一味經典藥都應該有與它相對應的運用指徵。用此藥必有此證,見此證必用此藥,無此證必去此藥。真正的藥物必須具備兩個特性,即嚴格的適應證和可以重複的療效。藥與證的相互對應即是藥證相應,也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對證下藥”。
以藥名證的方法,源於漢代名醫張仲景。《傷寒論》中有“桂枝證”、“柴胡證”的提法,《金匱要略》中有“百合病”的名稱,這就是藥證。中醫的初學者大多認為中醫的用藥是嚴格地按照理-法-方-藥的程序進行的,但實際卻恰恰相反,在許多有經驗的臨床醫生的眼裏,面對患者,他首先看到的可能是“某某藥證”或“某某方證”,然後才上升為“某某治法”或“某某理論”。每味藥物,均有其嚴格的適應證,每張方,也有其特定的藥物組合,所以,藥證的識別極為重要,它是制方遣藥的基礎。正如鄒澍所說:“不知一病有一病之方,一方有一方之藥,一藥有一藥之效,不能審藥,何以定方?不能定方,何以治病?”
(《本經疏證 序》)
藥證是構成方證的基礎,方證是放大了的藥證。兩者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所以,宋代名醫朱肱將藥證和方證是合稱的。他說:“所謂藥證者,藥方前有證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類證活人書》)。但是,單味藥證與方證是有區別的。方證不是幾味藥證的簡單疊加,而是一個複雜的組合,它們是新的整體,所以必須將方證看作是一味藥證。
二、關於藥證相應
藥證相應是中醫取效的前提。要取得療效,藥證必須相應,藥證本是一體的。《傷寒論》所謂“病皆與方相應者,乃服之”(317條),即用此藥必有此證,見此證必用此藥。中醫的臨床療效往往取決於藥證是否相應,也就是人們所 說的“對證下藥”。如把桂枝比作箭,桂枝證就是目標,目標對準了,命中率就高,同樣,藥證、方證相對了,療效自然會出現。換句話說,藥證相對了,這就是必效藥、特效藥;不對應,則是無效藥。這是中醫取效的關鍵。“古人一方對 一證,若嚴冬之時,果有白虎湯證,安得不用石膏?盛夏之時,果有真武湯證,安得不用附子?若老人可下,豈得不用硝、黃?壯人可溫,豈得不用薑、附?此乃合用者必須之,若是不合用者,強而用之,不問四時,皆能為害也”。(《金鏡內臺方義》)所謂的合用,就是相應。
藥證相應是天然藥物的臨床應用原則。天然藥物的成分極其複雜,藥物下嚥究竟起到何種效應?要真正解明其中奧妙,恐怕相當困難。所以,若以實驗室的動物試驗數據,加上現代醫學現階段對人體生理病理的認識,去指導對人體的天然藥物的傳統使用(煎劑、丸劑、散劑的傳統劑型),其可靠性是值得懷疑的。更何況,我們讓患者服的藥是飲片,是沒有分離過的天然藥物,幾乎所有的 藥物成分均要下嚥,所以,希望其中某種成分起作用只是良好的願望,事實如何又是另一回事了。科學的態度應當是尊重前人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行之有效的經驗和久經實踐證明的事實,總結其中的規律。藥證相應的臨床應用原則是不容忽視的。
藥證相應體現了中醫學診斷與治療的一體性原則。現代醫學出現有診斷而無治療的情況是不必見怪的,而中醫雖然無法斷定是哪種疾病,但依然可以識別藥證,有藥證就有治療也是合情合理的。因為藥證不是針對某種疾病病原體的,而是針對疾病中的人體。所以,與其說藥證是藥物的臨床應用指徵,倒不如說是人體在疾病狀態中的斷面和病理反應在體表的投影。應用科學的方法研究藥證,必然揭示現代醫學尚未發現的人體病理變化的新規律。
藥證識別是檢驗一個中醫臨床醫生實際工作能力的標誌。前人常以“絲絲入扣”、“辨證精細”等詞來形容名醫的用藥功夫,但由於藥證識別的準確率常與人們的臨床經驗、思想方法、即時精神狀態有關,故絕對的藥證相應僅是一種理想狀態。藥證相應是中醫臨床工作者始終追求的目標。
三、關於張仲景藥證
嚴格地講,所有被稱為“中藥”的藥物應該都有藥證,但事實不是如此。中醫學在長期的臨床實踐中僅僅發現了一部分天然藥物的藥證,這些已經發現的、並在臨床上起著重要指導作用的藥證,主要集中在《傷寒論》、《金匱要略》中,我們稱之為張仲景藥證。
張仲景的藥證是中醫的經典藥證。《傷寒論》、《金匱要略》非一人一 時之作,仲景既勤求古訓,博采眾方在前,王叔和、“江南諸師”補充在後,故 仲景藥證也非仲景一人之經驗,而是總結了漢代以前的用藥經驗,而且經過後世 數千年無數醫家的臨床驗證被證實並發展,其臨床指導意義是不言自明的。所以 ,成無己說“仲景之方,最為眾方之祖。”張元素說“仲景藥為萬世法。”王好 古說“執中湯液,萬世不易之法,當以仲景為祖。”徐靈胎說的更為明白:“古 聖治病之法,其可考者,唯此兩書。”可以這麼說,張仲景藥證是構成後世臨床 醫學的基礎,離開了它,中醫學將變成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用中藥治病,若不 明仲景藥證,無疑是掩目而捕燕雀,亂摸而已。許多青年中醫使用中藥療效不明 顯,大部分是與對張仲景藥證不熟悉有關。
《傷寒論》、《金匱要略》的用藥十分嚴格,有是證,則用是藥;無是 證,則不用是藥,加藥或減藥,都以臨床見證的變化而變化,決不能想當然地隨 意加減。故惡風、汗出、脈浮用桂枝湯,如汗出多,惡寒關節痛者,必加附子, 名桂枝加附子湯。如發汗後,身疼痛,脈沉遲者,又必加人參,名新加湯。如無 汗而小便不利者,則要去桂枝,加白朮、茯苓,這就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治心下悸,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則為咳逆上氣。大劑量藥 與小劑量藥的主治也不相同,同樣是桂枝湯的組成,但桂枝加桂湯的桂枝5兩,其 主治為氣從少腹上衝心者;桂枝湯倍芍藥主治腹中急痛,方名也改為桂枝加芍藥 湯;再加飴糖,又名小建中湯。又雖用過某藥,但其證未去,則仍可使用某藥, 如《傷寒論》“柴胡湯病證而下之,若柴胡證不罷者,復與柴胡湯……”;“太 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可與桂枝湯,……若不上衝者,不得與之”。這種 用藥法,體現了張仲景用藥極為嚴格的經驗性。《傷寒論》、《金匱要略》是研 究藥證的最佳臨床資料。
《神農本草經》雖然是最古的本草書,其中有許多研究藥證極為重要的 內容,但畢竟不是“疾醫”所著。全書收載藥物365味,與一年天數相應。全書分 上、中、下三品,書中“輕身”、“不老”、“延年”、“通神仙”等語比比皆 是,摻雜了不少道家黃老之學。全書在如何使用這些藥物方面,論述略而不詳。 而《傷寒論》、《金匱要略》在記載病情上忠於臨床事實,表述客觀具體,完全 是臨床家的書。兩書雖為方書,但通過適當的研究,完全可以理清張仲景用藥的 規律,破譯出一本《中醫經典臨床藥物學》。
張仲景藥證的研究主要採用比較歸納的方法,通過同中求異、異中求同 ,互文參照,來分析仲景用藥的規律。以下的原則可以參照。
最大量原則:《傷寒論》、《金匱要略》中同一劑型中的最大用量方,其指 徵可視為該藥藥證。例如仲景湯方中,桂枝加桂湯中桂枝5兩,為《傷寒論》中桂 枝最大量方,主治氣從少腹上衝心者。原文“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 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則其氣從少腹上衝心是桂枝證的主要內容。
最簡方原則:配伍最簡單的處方,其指徵可視為該藥藥證。如桂枝甘草湯( 2味)主治“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則心下悸,欲得 按為桂枝證的主要內容。此外,桔梗湯證對桔梗證的研究,四逆湯證對附子證的研究,都具有特別的意義。
量證變化原則:即症狀隨藥量變化而變化者,該症狀可視為該藥藥證。如黃 耆最大量方(5兩)的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主治“黃汗之為病,身體腫,發熱汗出 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柏汁,脈自沉。”(十四)其證之一是浮腫 ,且是全身性的,因風水為“一身悉腫”。其證之二為汗出,汗出能沾衣,可見 其汗出的量較多。桂枝加黃耆湯(2兩)主治“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必身 , 即胸中痛,有從腰以上必汗出,下無汗,腰髖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痛,煩躁、小便不利,此為黃汗”;“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主之”。原文提示,患者腰以下無汗出,再加此證的治法當以汗解,其出汗的程度是較輕的,所以黃耆僅用2兩。根據以上 兩方證的比較可以發現,黃耆用於治療自汗,汗出的程度越重用量越大。又如葛 根,葛根黃芩黃連湯為葛根的最大量方(8兩),主治“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 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利遂不止,指泄瀉不止。葛 根湯類方中用於下利的有葛根湯。原文為“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自
下利,為未經攻下而大便自然溏薄者,其程度要比葛根黃芩黃連湯證的“利遂不 止”為輕,故用量僅為4兩。可見葛根用於下利,下利的程度越重,其用量也越大 。
味證變化原則:即藥物的增減變化帶來應用指徵的變化,則隨之增減的指徵 可視為該藥藥證。如《傷寒論》理中湯條下有“若臍上筑者,腎氣動也,去朮加 桂四兩”。四逆散條下有“悸者加桂枝五分”。《金匱要略》防己黃耆湯條下有 “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可見臍上筑、悸、氣上衝,均為桂枝主治。《傷寒論 》中有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原文為:“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 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可見 無衝逆證,也無自汗證。
頻率原則:應用統計方法,凡頻率越高,其屬於該藥藥證的可能性越大。如 柴胡類方中,凡大劑量柴胡與黃芩同用,其指徵都有往來寒熱,並有嘔而胸 苦 滿。如除去黃芩證,則柴胡證自明。
仲景藥證是比較成熟的藥證,需要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去搞清其所以然, 這樣可以發現一些現代醫學尚未發現的病症,也可揭示出人體生理病理上的某些 規律,還可使藥證的識別趨於客觀化,並使藥物的臨床應用範圍更清晰。通過現 代研究,有的藥物可能成為治療現代某種疾病的特效藥,有的則可能成為改善體 質的新型藥物,而有的可能還一下弄不清楚,還必須按照傳統的藥證用下去,這 都是可能的。要完全揭開藥證的實質,恐怕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所以,傳統的藥 證需要繼承,特別是仲景藥證更應繼承好,傳下去。
四、關於本書的宗旨
《傷寒論》114方,有名有藥者113方,91味藥,其中1方次36藥,2方次 以上55藥。《金匱要略》205方,有名有藥者199方,156味藥,其中1方次62藥, 2方次以上94藥。本書選擇臨床常用且仲景敘述藥證比較明確的藥物50味,分原文 考證、藥證發揮、仲景方根、常用方四部分重點論述藥物主治。雖說僅50味, 但每味藥均為常用藥,只要掌握好每藥的主治和常用配伍,則在臨床自能演化出 無數新方。
“舊書不厭百回讀,熟讀深思子自知”(宋 蘇軾)。由於《傷寒論》 、《金匱要略》是臨床實踐的真實記錄,故歷代醫家都主張對仲景書要反覆研讀 ,特別在臨床上認真研究,能不斷取得新的認識。陳修園說他讀仲景書“常讀常 新”,就是這個意思。本書中的藥證發揮,為筆者的研究心得,其中肯定有許多 不當之處,隨著研究的深入,臨床經驗的增加,必然要有改進,這點必須說明。
規範化是一門學科發展的必要條件,藥證的研究就是試圖建立中醫臨床 用藥的規範。這項研究工作,歷史上中日兩國的醫家已經有了令人起敬的成績。 清代傷寒家的崛起,近代經方家的出現,日本古方派的實踐,都是為了建立一種 理論與臨床的規範,促使醫學的健康發展。代表者是清代醫家鄒澍的《本經疏證 》和日本的古方派大家吉益東洞的《藥徵》。筆者的工作,是在他們的基礎上進 行的。當前,中醫學庸俗化的趨向比較突出,青年中醫往往在不切實際的一些理 論中糾纏不清,辨證論治成為一種踏虛蹈空式的遊戲,而臨床療效的不明確,又 極大地挫傷了他們研究中醫藥的熱情。究其原因,主要應歸結為《傷寒論》、《 金匱要略》的功底不深,特別是對仲景藥證缺乏研究。如此以往,中醫學的實用 價值必將大大降低。另外,許多中醫的實驗研究,選擇的“證”大多是含糊模稜 的,往往缺乏特異性的方藥相對應,而表現在實驗動物身上的“證”更是缺乏必 要的可信度,其研究結果不能讓人十分信服,這也影響了中醫現代化的進程。有 慨於此,而作此書。希望通過筆者的工作,喚起大家對古典中醫學的重視。繼往
才能開來,根深才能葉茂,中醫學的發展離不開對古代優秀遺產的繼承,因為這 裏有中醫學的根。
黃 煌
於南京中醫藥大學 2005年1月
幾 點 說 明
一、為節省篇幅,正文中所引《傷寒論》、《金匱要略》方劑的組成、劑量、煎服法等均未注明,請查閱書後附錄的方劑一覽。
二、本書《傷寒論》原文,以明代趙開美復刻的宋本《傷寒論》為藍本(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年出版),每條注明阿拉伯字文號。《金匱要略》(人民衛生出版社1963年出版)則以中文注明篇號。
三、原文考證為根據《傷寒論》、《金匱要略》原文,歸納分析仲景藥物的主治。其主治盡可能採用仲景原有的術語。每味藥物的主治,均為傳統內服劑型的主治,至於外用劑型的主治則另需研究,本書沒有涉及。
四、藥證發揮為結合臨床對仲景藥證進行的闡述和解釋。為了臨床應用和記憶,筆者將一些比較客觀的用藥指徵,直接冠以某某舌、某某脈、某某腹、某某體質的名稱,諸如“桂枝舌”、“大黃舌”、“附子脈”、“黃耆肚”、“柴胡體質”等。這種提法,參照了《傷寒論》、《金匱要略》中“桂枝證”、“柴胡證”、“病形像桂枝”等說法。這本是一種略稱,並非中醫固有術語。
五、仲景方根為仲景配方的基本結構。本書通過原文作了初步的總結歸納,並附有配伍一覽表。
六、常用配方為臨床常用的經典方,其中絕大部分是《傷寒論》、《金匱要略》中的方劑,其劑量按照一兩=3克的標準進行折算,藥物之間的比例基本上遵循仲景原意。少數經方折算以後用量與現代臨床相差較大時,或無劑量可換算時,則代以筆者臨床常用量。劑量的問題一直被稱為中醫的“不傳之秘”,很難說清楚,其中有醫家個人的獨特經驗和地域性的應用習慣,目前尚不能作硬性的規定。不過,筆者提倡要以尊重經方的內部結構為原則,藥物的配伍比例需要重視
。常用配方中也有少數後世常用方,這些方久經臨床檢驗,療效肯定,已經與經典方同類。應當說明,本書非方劑全書,後世尚有許多名方不能一一收錄。劑型、煎服法是經方取效的關鍵所在,讀者可參照本書附錄的《傷寒論》、《金匱要略》方劑一覽,在實踐中認真研究。常用配方的應用指徵及其病種的確定,參照了有關臨床報導及筆者臨床經驗,僅供參考。
七、傳統中藥學對藥物的功效有獨到的解釋,現代中藥藥理研究也有豐富的成果,這些都是研究藥證的極為重要的資料,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查考這方面的教材和專著,必將加深對張仲景藥證的理解。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