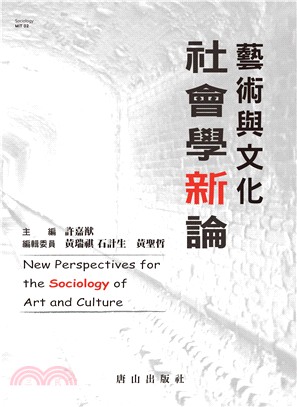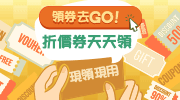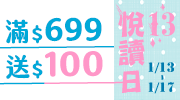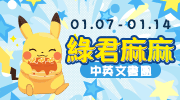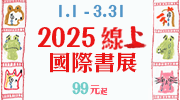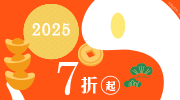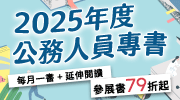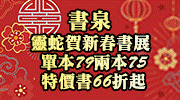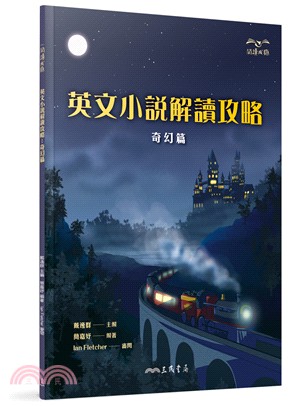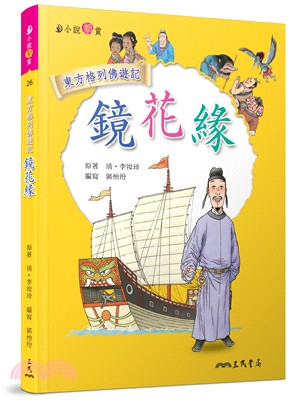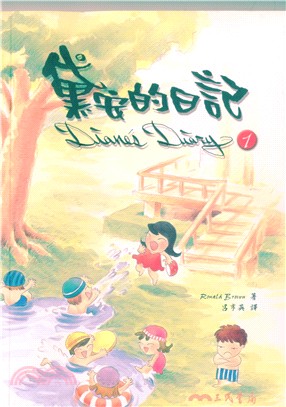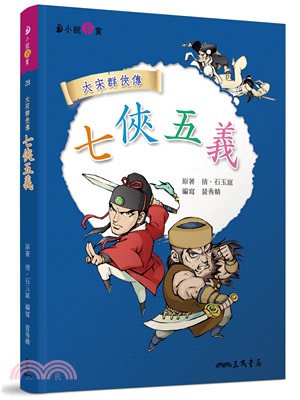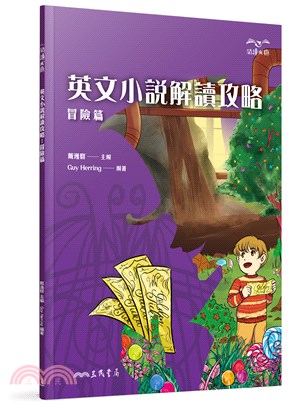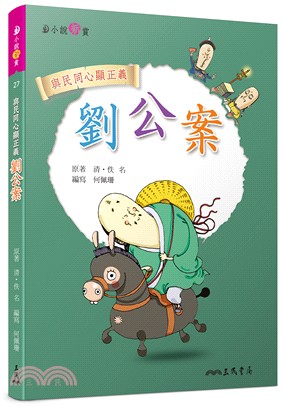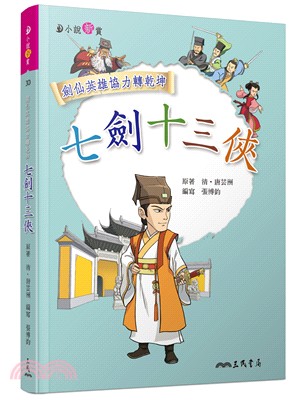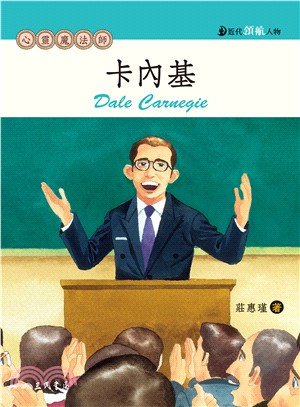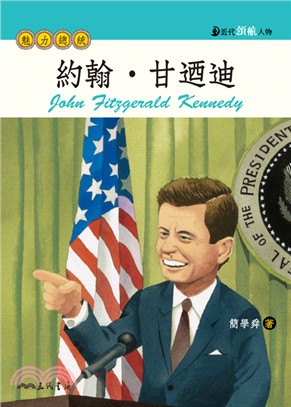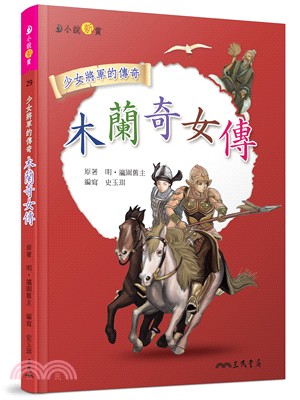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我們既要反思藝術與文化研究在社會學中的重要性,以及再發現和重新重視社會學大師涂爾幹所開啟,對宗教、藝術與文化的本質及基本形式之古典研究後,其間一度曾為社會學界所淡忘的藝術與文化研究,仍應是社會學界的核心研究議題。
作者簡介
許嘉猷 主編
學歷:Indiana University 社會學博士、Kansas State University 社會學碩士、臺灣大學社會學學士。經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社經組主任、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專業研究:藝術社會學、文化研究、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
黃瑞祺 編輯委員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博士,主要從事歐美社會政治理論、全球化、生態等研究。著有《批判社會學》、《社會理論與社會世界》、《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科學方法論集》、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Karl Marx’s Social Theory等;主編《當代社會學》、《溝通、批判和實踐──哈伯馬斯八十論集》、《再見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等。
石計生 編輯委員
臺灣高雄人、祖籍安徽宿松。美國芝加哥伊利諾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領域為藝術社會學、都市社會學、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地理資訊系統。主要著作有《社會學理論——從古典到當代之後》(三民)、《閱讀魅影:尋找後班雅明精神》(南京大學),與《時代盛行曲:紀露霞與臺灣歌謠年代》(唐山) 等。另有專書論文〈歌謡、歌謡曲集と雑誌の流通:中野忠晴、「日本歌謡学院」の戦後初期台日に対する文化を越えた影響〉即將由日本三元社以『台湾のなかの日本記憶』書名出版等。
黃聖哲 編輯委員
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博士,師承Ulrich Oevermann的客觀詮釋學學派。曾任教於東吳大學、輔仁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等校。現職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專任教授。
學歷:Indiana University 社會學博士、Kansas State University 社會學碩士、臺灣大學社會學學士。經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兼社經組主任、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專業研究:藝術社會學、文化研究、社會階層化與社會流動。
黃瑞祺 編輯委員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劍橋大學國王學院博士,主要從事歐美社會政治理論、全球化、生態等研究。著有《批判社會學》、《社會理論與社會世界》、《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科學方法論集》、Recent Interpretations of Karl Marx’s Social Theory等;主編《當代社會學》、《溝通、批判和實踐──哈伯馬斯八十論集》、《再見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等。
石計生 編輯委員
臺灣高雄人、祖籍安徽宿松。美國芝加哥伊利諾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研究領域為藝術社會學、都市社會學、社會學理論與社會地理資訊系統。主要著作有《社會學理論——從古典到當代之後》(三民)、《閱讀魅影:尋找後班雅明精神》(南京大學),與《時代盛行曲:紀露霞與臺灣歌謠年代》(唐山) 等。另有專書論文〈歌謡、歌謡曲集と雑誌の流通:中野忠晴、「日本歌謡学院」の戦後初期台日に対する文化を越えた影響〉即將由日本三元社以『台湾のなかの日本記憶』書名出版等。
黃聖哲 編輯委員
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學博士,師承Ulrich Oevermann的客觀詮釋學學派。曾任教於東吳大學、輔仁大學、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等校。現職為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專任教授。
目次
主編序 許嘉猷
PART 1 文化篇
第一章 綿延、記憶、歷史:論集體記憶 胡正光
第二章 在文化與行政之間 黃聖哲
第三章 宗教理性的意義與實踐:哈伯馬斯論後世俗社會的宗教問題 黃瑞祺、黃金盛
第四章 論戰後歌仔本與臺灣歌謠的日本連結:張邱冬松、中野忠晴及郭一男的貢獻 石計生
第五章 夢幻與罪惡:巴黎做為現代性城市原型的兩面性 高榮禧
第六章 公共社會學與理論策展做為知識分子行動 賴嘉玲
第七章 數位科技也可以是好生意:時尚文創與科技藝術融匯的初探性研究 邱誌勇
PART 2 藝術篇
第一章 藝術作品的社會性如何可能?一個Georg Simmel觀點的審視 鄭志成
第二章 以創作的社會過程解析藝術作品:啟發與限制 洪儀真
第三章 藝術的社會學啟蒙:以身體技藝為建構基礎的社會美學 齊偉先
第四章 藝術作品的文本與脈絡:文明化過程理論視角裡的莫札特、委拉茲蓋茲、華鐸 張義東
第五章 臺灣寫實主義風景畫之中的文人精神傾向及其轉化 陳泓易
第六章 當代華人文物藝術拍賣市場之形成 李玉瑛
第七章 時間之意象:江詩丹頓「藝術大成」手錶系列之藝術和文化表現模式及其一些社會文化意涵 許嘉猷
附錄一 樂生療養院:見證臺灣認同之建構 Sylvie Ragueneau、詹文
附錄二 編者與作者簡介
PART 1 文化篇
第一章 綿延、記憶、歷史:論集體記憶 胡正光
第二章 在文化與行政之間 黃聖哲
第三章 宗教理性的意義與實踐:哈伯馬斯論後世俗社會的宗教問題 黃瑞祺、黃金盛
第四章 論戰後歌仔本與臺灣歌謠的日本連結:張邱冬松、中野忠晴及郭一男的貢獻 石計生
第五章 夢幻與罪惡:巴黎做為現代性城市原型的兩面性 高榮禧
第六章 公共社會學與理論策展做為知識分子行動 賴嘉玲
第七章 數位科技也可以是好生意:時尚文創與科技藝術融匯的初探性研究 邱誌勇
PART 2 藝術篇
第一章 藝術作品的社會性如何可能?一個Georg Simmel觀點的審視 鄭志成
第二章 以創作的社會過程解析藝術作品:啟發與限制 洪儀真
第三章 藝術的社會學啟蒙:以身體技藝為建構基礎的社會美學 齊偉先
第四章 藝術作品的文本與脈絡:文明化過程理論視角裡的莫札特、委拉茲蓋茲、華鐸 張義東
第五章 臺灣寫實主義風景畫之中的文人精神傾向及其轉化 陳泓易
第六章 當代華人文物藝術拍賣市場之形成 李玉瑛
第七章 時間之意象:江詩丹頓「藝術大成」手錶系列之藝術和文化表現模式及其一些社會文化意涵 許嘉猷
附錄一 樂生療養院:見證臺灣認同之建構 Sylvie Ragueneau、詹文
附錄二 編者與作者簡介
書摘/試閱
節錄自〈第一章 綿延、記憶、歷史:論集體記憶/胡正光〉
什麼是「集體記憶」?現在的社會學研究在這方面如何將「記憶」與過去的經驗區分?我們從「集體記憶」一詞的創造者阿布瓦西(Maurice Halbwachs)的作品中,發現他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他的老師柏格森的記憶理論,以致於對「集體記憶」本質的爭論也常可以說是對柏格森「記憶」理論的爭辯。
例如,「集體記憶」的建構性質較強,抑或一個社會的「集體記憶」應當更傾向連續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文回到柏格森的哲學,從「記憶」的本質、「記憶」的使用等命題開始,由原初的柏格森理論中去尋找答案。
透過兩種對「集體記憶」本質的相對看法,我們進一步解釋了「記憶」與「歷史」的差異,並希望藉著概念的釐清,為「集體記憶」研究尋找適當的方法。
一、前言
在目前種種「集體認同」(如族群認同、國家認同、地域認同)的研究中,「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可說是一個不陌生的詞彙。 的確,個人若沒有「記憶」,就連「自我」也將無法建構(Squire & Kandel,1999:ix)。不過,「記憶」一詞,卻是令人捉摸不定的字眼。或許因為這是個沿用已久,已深入日常生活的詞彙,每個人都有一種約定俗成的印象,含意廣泛,甚至到了無意義的地步,連傳統心理學對於「記憶」的研究,也和實際生活中的記憶運作沒什麼關聯(Goldberg,2001:72)。
那麼,社會學方面對「集體記憶」一詞的定義又如何?什麼樣的記憶,可以稱為「集體的」?「集體記憶」的概念有沒有學術上的嚴謹性?從目前一些論文的使用方式,可見得模糊不清的狀態並沒有解決。例如在一篇名為〈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的文章中,作者聲稱交替使用「記憶」、「歷史」、「傳統」等詞,不加區分,因為「它們都指涉人們所記憶的過去」(蕭阿勤,1997:251)。又如一本名為《霧社事件:臺灣人的集體記憶》(許世楷、施正鋒,2001)的研討會論文集,書中的記憶呈現是請事件的目擊者來「回憶」當時的情景。霧社事件固然可說存在於每個人的記憶中,但諸多細節,有多少屬於共同的記憶?由此可見,「集體記憶」的含意相當空泛, 使得冠上「集體記憶」的研究有時變得焦點模糊。到底社會學中的集體記憶研究宗旨為何?集體記憶研究的本體論基礎又是什麼?
這些疑問,就是本文的出發點──追溯「集體記憶」這個概念最原初的理論思想。而這個研究動機,使我們連上了最早研究「集體記憶」的法國社會學家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Halbwachs目前歸類於涂爾幹學派的學者,不過在他接觸社會學之前,曾經一度想以哲學為業(Coser,1992:3)。而深深影響Halbwachs的哲學啟蒙老師,就是在20世紀初期西方哲學的領航人之一,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雖然這一段淵源並非鮮為人知,但在提到Halbwachs的集體記憶研究時,卻少有人提到柏格森哲學與他的關聯。 本文則對這對師徒的學術關係深感興趣,因為人們對於Halbwachs的「集體記憶」向來缺少哲學基礎的研究,使得今天對於該如何看待這個概念產生了相互對立的傾向。本文希望從柏格森哲學的角度,試圖解釋這組對立的觀點其實源自於柏格森哲學的不同面向,而且或許這是因為柏格森強調的「直觀」(intuition)與科學方法不能相容之故。 但是從這個哲學脈絡來看,對立的觀點卻都沒有違反柏格森哲學的原則,反而或多或少是一種誤解。
基於上述,本研究的目的因此是:第一、說明柏格森與Halbwachs二人在哲學思想上的傳承關係;第二、說明兩種研究取向對立的原因並提出建議。為了這兩個目的,本文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闡釋柏格森最重要的「綿延」與「記憶」觀念;其次、剖析Halbwachs的重要著作:《記憶的社會框架》(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與《福音書中聖地的傳奇地形學》(The Legendary Topography of the Gospels in the Holy Land,二者都收錄於Halbwachs,1992),找出分析的架構;第三、解釋兩種對立的「集體記憶」觀點,解釋對立因何產生,柏格森如何處理(或避開)這個問題;最後並做一結論。
什麼是「集體記憶」?現在的社會學研究在這方面如何將「記憶」與過去的經驗區分?我們從「集體記憶」一詞的創造者阿布瓦西(Maurice Halbwachs)的作品中,發現他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他的老師柏格森的記憶理論,以致於對「集體記憶」本質的爭論也常可以說是對柏格森「記憶」理論的爭辯。
例如,「集體記憶」的建構性質較強,抑或一個社會的「集體記憶」應當更傾向連續性?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文回到柏格森的哲學,從「記憶」的本質、「記憶」的使用等命題開始,由原初的柏格森理論中去尋找答案。
透過兩種對「集體記憶」本質的相對看法,我們進一步解釋了「記憶」與「歷史」的差異,並希望藉著概念的釐清,為「集體記憶」研究尋找適當的方法。
一、前言
在目前種種「集體認同」(如族群認同、國家認同、地域認同)的研究中,「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可說是一個不陌生的詞彙。 的確,個人若沒有「記憶」,就連「自我」也將無法建構(Squire & Kandel,1999:ix)。不過,「記憶」一詞,卻是令人捉摸不定的字眼。或許因為這是個沿用已久,已深入日常生活的詞彙,每個人都有一種約定俗成的印象,含意廣泛,甚至到了無意義的地步,連傳統心理學對於「記憶」的研究,也和實際生活中的記憶運作沒什麼關聯(Goldberg,2001:72)。
那麼,社會學方面對「集體記憶」一詞的定義又如何?什麼樣的記憶,可以稱為「集體的」?「集體記憶」的概念有沒有學術上的嚴謹性?從目前一些論文的使用方式,可見得模糊不清的狀態並沒有解決。例如在一篇名為〈集體記憶理論的檢討〉的文章中,作者聲稱交替使用「記憶」、「歷史」、「傳統」等詞,不加區分,因為「它們都指涉人們所記憶的過去」(蕭阿勤,1997:251)。又如一本名為《霧社事件:臺灣人的集體記憶》(許世楷、施正鋒,2001)的研討會論文集,書中的記憶呈現是請事件的目擊者來「回憶」當時的情景。霧社事件固然可說存在於每個人的記憶中,但諸多細節,有多少屬於共同的記憶?由此可見,「集體記憶」的含意相當空泛, 使得冠上「集體記憶」的研究有時變得焦點模糊。到底社會學中的集體記憶研究宗旨為何?集體記憶研究的本體論基礎又是什麼?
這些疑問,就是本文的出發點──追溯「集體記憶」這個概念最原初的理論思想。而這個研究動機,使我們連上了最早研究「集體記憶」的法國社會學家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Halbwachs目前歸類於涂爾幹學派的學者,不過在他接觸社會學之前,曾經一度想以哲學為業(Coser,1992:3)。而深深影響Halbwachs的哲學啟蒙老師,就是在20世紀初期西方哲學的領航人之一,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雖然這一段淵源並非鮮為人知,但在提到Halbwachs的集體記憶研究時,卻少有人提到柏格森哲學與他的關聯。 本文則對這對師徒的學術關係深感興趣,因為人們對於Halbwachs的「集體記憶」向來缺少哲學基礎的研究,使得今天對於該如何看待這個概念產生了相互對立的傾向。本文希望從柏格森哲學的角度,試圖解釋這組對立的觀點其實源自於柏格森哲學的不同面向,而且或許這是因為柏格森強調的「直觀」(intuition)與科學方法不能相容之故。 但是從這個哲學脈絡來看,對立的觀點卻都沒有違反柏格森哲學的原則,反而或多或少是一種誤解。
基於上述,本研究的目的因此是:第一、說明柏格森與Halbwachs二人在哲學思想上的傳承關係;第二、說明兩種研究取向對立的原因並提出建議。為了這兩個目的,本文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闡釋柏格森最重要的「綿延」與「記憶」觀念;其次、剖析Halbwachs的重要著作:《記憶的社會框架》(The Social Frameworks of Memory)與《福音書中聖地的傳奇地形學》(The Legendary Topography of the Gospels in the Holy Land,二者都收錄於Halbwachs,1992),找出分析的架構;第三、解釋兩種對立的「集體記憶」觀點,解釋對立因何產生,柏格森如何處理(或避開)這個問題;最後並做一結論。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