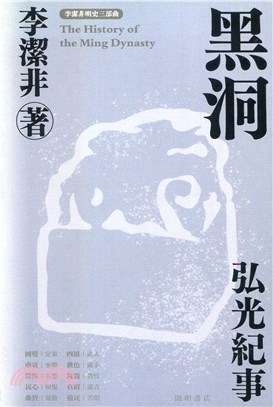商品簡介
本書將僅存一年的南明弘光朝作為對象,從軍事、經濟、政治、文化、人事諸方面展開深入論述,作者秉承史傳寫作中“史傳敘事其表,思悟認知其裡”的宗旨,在描述史事時大開大闔,奇崛跌宕,令人盪氣迴腸;又以有力的思想認識方式,清晰地梳理出歷史表像後面的深刻內涵。
作者簡介
作者
李潔非,生於安徽合肥。畢業於復旦大學中文系,先後在新華社、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供職。
序
序
大概而言,本書為一史傳敍事作品,但筆者私衷卻是史傳敍事其表,思悟認知其裏。蓋所謂史傳者,大開大闔,奇崛跌宕,人易以故事視之,猶如讀小說、聽說書,目眩神迷,不覺而將其文藝化。其實,史傳乃是極有力的思想認識方式和工具。許多以讀書為業、自命足以勝任思考的人,往往將思想等同於理論,甚而只知從理論上求之。這種誤區,尤當思想、學術嚴重格式化,讀書和著述僅為博取功名之器藝的時代,益滋其彰。其表現,我們不必到遠處去找,眼下就很典型。歲歲年年,從學術考核制度,從學位、晉職競爭中生產的論文汗牛充棟,而內容空疏、言不及義者累累。當下知識者中每可見兩種情形:一、與現實有繭疥之隔,搔不到癢處、揭不了瘡疤,論來論去,思想只在一些似是而非的術語中打轉,和科舉制藝如出一轍,此謂「無補於世」;二、對歷史,不光觀念混亂、錯誤而不自知,又陶醉於某些徒具其表的義理,從理念到理念,從空想到空想,據之對歷史東拼西湊、強以就我,甚而不惜昧實而論,此謂「學不成器」。黃宗羲說:「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三十多年前(「文革」結束時)國人精神世界絀於「讀書不多」,而今,病根卻在「不求於心」— 讀書不少,心思仍舊昏憒。何以如此?有的是被應試教育所害,讀書不為求知,目的盡在出身、文憑。有的則是根鬚扎錯了地方。黃宗羲說:「拘執經術,不適於用,欲免迂儒,必兼讀史。」古人是拘執經術,今人是拘執義理,而實質總歸一條,即頭腦已被格式化,雖然也思考,也貌似產生思想,但根鬚卻扎於先入為主的理念,不是扎在客觀事實的土壤中。這就是「迂儒」,他們有些人的表現,往往比「迂」嚴重得多,其對義理的癡迷、對客觀的排拒,可能達於偏執的地步。為了不至於此,或已然如此而願意有所改益,有效辦法是接受黃宗羲的建議「必兼讀史」。讀史,首先是樁令人愉快的事,有着如對小說一般甚至超過它的樂趣,但這是極次要的。它真正的好處是使人離真相更近從而明辨是非,搜讀益多益廣,這功效益發明顯、確鑿,世間最不容易蒙蔽之人,便是飽於讀史之士;其次,讀史能夠大大彌補空頭理論的各種不足,甚至回過頭反思理論,重估它塞到我們腦中的那些觀念。言及此,想起梁啟超的評論:「大抵清代經學之祖推炎武,其史學之祖當推宗羲。」我從這句話所得,不只是兩大師治學各有所重,進而更在於,黃宗羲何以要將最大氣力用於史學?這很值得深思。以他學問之廣之深,這一定是出於鄭重、特別的選擇。我以為,那是對自己時代現實審視、判斷的結果。明亡之後,痛定思痛,一代碩學依各自認識展開反思和總結;而在黃宗羲看來,明代近三百年人文的弊端,主要在於空談許多義理,對歷史卻認知力嚴重不足。所以他的批判,不特別致力於理論,而集中在史學層面,通過摸索歷史,得到和浮現真知。體會、揣摩這一思路,我覺得對於當代有極大參考意義。回看半個多世紀以來,根本問題也是義理過剩而史學不足。陳雲曾講「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這是從國家政治層面對歷史教訓的總結,倘從精神思想層面看,相通的問題其實便是在義理與史學之間更應依憑和尊重什麼。考諸現實,令人意外的是我們在國家政治層面基本已能採取「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態度,反倒是精神思想層面義理過剩而史學不足的情形沒有多少改變。在「從百家爭鳴到兩家爭鳴」、「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不必說義理壓倒一切,史學則完全沒有空間抑或是被義理「掛帥」的史學。「文革」終結,改革開放,思想學術似乎漸至多元,但深入觀察,尚好主義的風氣依然獨大,基於事實的討論迄無多少餘地,某些慷慨激昂之士,盛氣凌人、泰山壓頂,以至詈以粗口而有恃無恐,其所恃者何?無非是義理握於其手。但義理在手為何就如此強勢?將根由追索到最底層,我以為是歷史檢討不足。因為歷史檢討不足,許多事實沒有釐清,或雖已釐清卻沒有進入公共知識領域、向社會普及,致一般人的歷史認識仍處於某些義理覆蓋之下而非來自歷史事實本身。既有此「知識背景」為雄厚社會基礎,就難怪有些人出言強悍,氣吞山河,總有「朕曰」口吻,動輒置人罪不容誅。當下中國精神思想如欲走出這種氛圍,別無辦法,非得像黃宗羲那樣,扎實地做史學功夫,辨偽訂訛、澄清史實,同時帶動社會有讀史的意識,逐漸建立不論什麼義理都要附麗於史、接受歷史檢驗,否則就是空頭說辭的認識。
中國能否更智慧、更清明,頗待乎一個全民讀史的浪潮。極而言之,詩歌、小說、哲學、道德…… 將這些暫時放下不讀,都不要緊,但一定要讀史。眼下我們不急於理想,甚至也不急於情感,所急者首先是事實。基本事實都不甚清楚,卻憧憬理想、抒發情感,又如何靠得住?讀史,就是尋找並確定事實的過程。有些人的談吐和舉動,一眼可見起於對歷史了解不夠。關於「文革」就是這樣,我們在身邊屢能發現有人心中至今為「文革」義理留一塊領地,乃至還以此為批判現實的武器。這固然可悲,但我想其中相當的一部分(特別是年輕人)未必真的了解「文革」,使他們有如上思想感情的根因,其實是「文革」史學的不足,令那種義理仍能有所附麗。
總之,史學確是當代思想一個關鍵方面。幾十年來,義理對史學深度注入,形成許多定式,令人們以為自己在接觸歷史,實際不過是接受義理。這遠非在當代史中如此,現代史、古代史甚至史前史,都存在從某種義理而來的固定格式。舉個很明顯的例子,歷史教科書一直把到1840 年為止的中國定義為「封建社會」,把相應歷史稱為「封建史」。其實,自嬴政這位「始皇帝」起,中國就廢止了封建制,漢代初年略有反覆,不久也徹底取消實封,以後歷代封王建國都僅為虛封,亦即受封之王有爵號有封地,但並非政治經濟上的獨立國。1973 年8 月5 日,毛澤東有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說得很清楚,秦以後中國已經沒有封建制,「百代」所行,都是嬴政始創的中央集權或大一統君權專制。那麼,為什麼教科書會無視這一點,而將二千年來中國冠以「封建社會」「封建時代」之名?原因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建立了一個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共產主義社會五大階段的的社會發展史模型。本來,這一番總結,所依據的主要是歐洲史;在歐洲,直到近代資本主義之前,確實處於完整的封建形態。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曾系統研究過中國歷史,並不了解從帝制中國的集權形態,他們的理論無從考慮和吸收中國的歷史經驗,這本來沒什麼,問題是,當馬克思主義作為政治意識形態,上述社會發展史模型被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必由之路」,只能遵守,不能旁生枝節。因此,便讓中國歷史削足適履,將明明不屬於封建形態的中國帝制史硬套為「封建社會」。其實,以中國歷史實際,不單「封建社會」之說是穿鑿附會,連「奴隸社會」的存在,也並不能從史料上落實。顧名思義,「奴隸社會」即應以奴隸制為社會基本關係,但至今不論文字上還是器物上,我們都不能完全地證明,中國曾經有一個奴隸制階段。否則,其始於何時、崩於何時,歷史上會有確切的標誌和概念,可是並無任何歷史學家對我們能夠以此相告。郭沫若曾將一些論文編在一起,取名《奴隸制時代》,但裏面的論述多不令人信服。我們見到的常常是一些字形字義的詮釋,某字像是奴隸情形的表現,某字有受人奴役的含義等。他唯一肯定的結論是:「殷代是奴隸制」,但即使在殷代,連他自己都說:「『當作牲畜來買賣』的例子雖然還找不到,但『當作牲畜來屠殺』的例子是多到不可勝數了。」我們知道,奴隸是奴隸主的財富,是奴隸主的生產工具,奴隸主擁有奴隸絕不是為了用來殺掉的,如果連買賣奴隸的跡象都找不到,卻以「當作牲畜來屠殺」為奴隸制存在的證據,那麼中國及世界上的奴隸制不知要延續到何年何月了—希特勒集中營裏的猶太人不也是「當作牲畜來屠殺」的嗎?其實在很長時間中,確切講,整個世界來到「現代」階段以前,奴隸或奴僕的社會身份都不曾消除,但這與整個的「奴隸制」或「奴隸社會」究竟是兩碼事。難道我們可以因為直至明清仍能見着太監這種奴隸式現象,而稱那時中國為「奴隸社會」麼?或者,把林肯以前的美國稱為「奴隸社會」?總之,過去教科書所劃分的中國史,除了原始社會,都未必合於實際。像奴隸社會的問題,本身史料不足,尚可存疑,以俟進一步的文獻發現或考古發現。但「封建社會」之子虛鳥有,卻確確實實、一目了然。連偉大領袖都教導我們,秦始皇之後「百代」再無封建制,封建制在中國是遠在周文王時代的事情,可見1840 年之前中國是「封建史」之論,何其睜眼說瞎話。這正是我們史學中一個為遷就義理而強扭事實的充分例子。這錯誤好像至今仍在延續,和筆者當年一樣,一代代學生仍然從課堂接受對一種並不存在的歷史的認識。如非後來在教科書外多讀多想,我亦無從知道所學知識裏包含如此嚴重的不實,一旦意識到,我即自誡日後凡涉及中國帝制以來歷史,堅決不用「封建」一詞—藉此機會,同樣提醒讀者諸君。從中我還反思,它不光給了我們錯誤的知識,更阻隔或關閉了對中國歷史真境況和真問題的探究。大家都去談論並不存在的「中國封建社會」,而置二千多年的集權專制、大一統君權這一真正的「中國實際」於不論。我們身處中國卻跟在歐洲歷史後頭研究「封建社會」,本身讓人啼笑皆非,更不幸的是,我們因而不去認識自己的歷史,不清楚它究竟是怎樣形態、存在什麼問題。至今,我們的歷史批判所以不深不透,恐怕與此有很大關係。
可惜,情況到現在也還沒有顯出多大的改良。中國史學界,不乏刻苦用功的人,也不乏學問滿腹、鑽研精深的專家,但似乎始終缺乏當代黃宗羲,缺乏那種能將史學提升為一種思想認識管道的人物。在局部的一件事、一個問題,或一個歷史人物的研究上,我們每每能見精詳豐瞻的成果,但從全局高度提出切合中國史實際的方向性、規律性的命題與論證,則難得一遇。我所能找出的原因,主要在於學者不能擺脫義理,直接用歷史材料說明歷史。由此造成的疑惑、浮辭、偽說實在太多,不僅包括剛才所說的中國歷史形態這樣宏大的方面,即在具體的朝代史方面,我們的認識和解說也總是鑽籠入套。比如由明入清,或所謂「明清鼎革」這一段,以我所見,真正從當時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無拘無束、直面歷史本相的研究,基本沒有。所以這樣,是因這段歷史與兩個很大的義理有關,而大家都不能夠從中走出。一是農民起義問題,一是民族衝突問題。這兩個問題,在當下歷史語境及國家意識形態中舉足輕重,有很嚴格的界限。絕大多數史家,囿於其中,小心翼翼,瞻前顧後。我曾將共和國成立後明清史研究與孟森那時加以比較,發現史家敢於創見的精神流散甚大。孟森先生《明清史講義》、《心史叢刊》一二三集、《清朝前紀》、《明元清系通紀》諸著,只要考之有據、言有所本,所論無不明快,一則一, 二則二,不諱、不隱、不忌,學術自由心態立然。他的書和文章,我每讀必有獲益,因為都是直面事實、不抱成見、不戴帽子而來。反觀共和國成立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中期起到「文革」結束那段時間,不用說盡屬以「理」入史、以「理」入學問,即便後來,束縛之痕仍歷歷可見,思想窒礙難行。遲至九十年代晚期,有一本新出版的南明史,坊間反映良好,雖然以相關研究的寂寥,它已來之不易,可惜眼光、見解仍未克服「主流」的掣肘、薰染與羈絆,令我們對脫略義理以外、一空依傍的真知灼見之盼,頗感受挫。
比如農民起義問題。自秦末陳勝吳廣起,在中國帝制史上,農民起義與蠻族入侵一道,並為王朝周期性變更兩大主因,幾乎所有王朝,要麼為農民起義所推翻,要麼由蠻族入侵而瓦解。換言之,農民起義是帝制以來中國歷史變化的主要動力之一。農民起義爆發,是王朝政治、經濟現實極度黑暗所致,此毋庸置疑。起義,作為人民之反抗和暴政之暴露,也毋庸置疑。在此意義上,它完全擁有正義性、正當性以及必然性,這都毋庸置疑。根據歷來的義理,農民起義被視為推動中國歷史進步的力量與表現。「在中國封建社會裏,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這個論斷,衡以階級鬥爭學說很好理解,但衡以歷史實際,卻未必能落到實處。以我們的觀察,經過農民起義推翻舊的統治,雖然促成王朝更迭,但中國歷史和社會不要說大的積極變化,甚至毫無變化,所謂一元復始不過是周期循環、同義反覆。如果有什麼變化,恐怕也是社會益壞、積弊愈重。農民生存境狀,二千年來趨勢是每況愈下,賦稅負擔不降反升,一朝甚於一朝。「漢初十五而稅一」,稅負不到百分之七,而晚明,「一畝之賦,自三斗起科至於七斗…… 一歲之獲,不過一石」,高至百分之三十到七十。在政治方面,幾次成功的農民起義,最終都導致皇權體系的延續、鞏固和加強。尤其朱明王朝,可謂完全由農民起義立國,而其制度醜陋性較前有過之無不及。所以如此,首先在於社會現實和歷史結構本身都還沒有發生新格局,一切只能周而復始;其次,農民起義作為反抗黑暗的現象,固然起於「正義」無疑,但受制於文化和精神能力低下,他們對自己行為的「正義」含義不能做思想的認識,更談不上從理論高度對「正義」理念給以單獨的觀照、反思,實際上,這種「正義」既是盲目的,也僅限於特殊階段,一旦邁過「反抗」期,從造反者變成當權者,農民起義領袖就不可避免以當初的反抗對象為師,成為舊權力的抄襲者—這一規律,似乎從來沒有例外。
以明末為例,最成功的兩支農民起義軍李自成和張獻忠,後者精神上太過簡陋,暴露了太多的黯昧本能,即置諸農民起義史範圍內亦不足論;李自成軍則好很多,其文化上的努力和自我匡束,已接近農民起義在這方面的最高境界。李自成大力吸收知識分子進入農民軍,從他們那裏借取政治策略,對農民軍面貌和理想加以修正,克制子女玉帛、打家劫舍的原始衝動,着力塑造正義之師形象。正因有這些調整和提升,李軍所向披靡,終至奪取明都。李自成險些成功,如歷來所論,他「被勝利衝昏頭腦」,功虧一簣。很多人因這一點,為他扼腕。其實更需要詢問的是這樣的問題:即便李自成未「被勝利衝昏頭腦」,又將如何?李自成能夠為中國開闢新的歷史,還是僅能複製一下朱元璋的成功?這是關鍵所在,也是關於明末這段歷史我們真正應該考察的方面。從道義上說,李自成起義完全正當,明王朝覆滅則令人有「時日曷喪?吾與汝偕亡」的痛快,這些都沒問題。出於同情,我們對反抗者有所偏愛,儘量予以肯定或維護,比如說「大順軍推翻明王朝接管整個黃河流域幾乎對社會生產沒有造成什麼破壞」,也不難以理解。但我們對歷史的着眼處,終歸不是情感,而在理性。李自成起義喚起我們何種情感共鳴是一碼事,起義體現了何種內容,在歷史、文化層面達到什麼高度,是另一碼事。功虧一簣說明,即便在農民起義範圍內大順政權也未臻善美。它的表現肯定比張獻忠好,卻明顯比不了二百七十八年前緣同一路徑而來的朱元璋。就算李自成不「被勝利衝昏頭腦」,取得與朱元璋比肩的成就,對歷史又有什麼新意可言?我們不僅沒從李自成那裏看見創造歷史的跡象,甚至也沒有發現這種能力。
我們不會吝惜對農民起義的同情支持,但我們要將這種態度與對歷史正確方向的判斷區分開來。大順政權以其實踐表明,在最好情形下,它對歷史的貢獻將僅僅是王朝的周期性更迭。那是一個老套的故事,以對奴役者的反抗始,而以更換新的奴役者終。這樣的結局,感傷者目為悲劇,而理性地看,當歷史仍處於舊格局、按照老的軌跡運行時,完全是意料之中、萬變不離其宗的事情。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興與亡,不過是同質權力的易手、交割。只要權力終點仍是「龍牀」,坐於其上的姓朱姓李、姓王姓張,於歷史又有什麼分別?就此言,李自成「成」也好「敗」也罷,我們都不宜自作多情,輕易為之欣悅或喟歎,除非我們確實從歷史整體明了其成敗的意義。
歷史是複雜的,它的道理,沒法簡單到「一部階級鬥爭史」那樣,只須做二元判斷。以明末來論,雖然大規模農民起義確是激烈社會矛盾的反映,但當時中國歷史的主腦、主線是否就在這裏,卻需要給以整體的考量。我們對問題分量的估衡,不能以動靜大、表現方式火爆為標誌。依我們所知,明末農民大起義李自成也罷、張獻忠也罷,從結果看並沒有提出、形成新的問題,從起因看也主要出於飢餓、災荒、重賦等。這些內容與訴求不容漠視,揭示了社會的極大不公與黑暗;但放到歷史整體中看,畢竟是已知歷史的重複,不獨明末農民起義來自於此,過去千百年農民起義也都來自於此。所以我們一面將寄予巨大同情,另一面,從理性角度不得不說,既然一件事所觸及的只是舊問題,那麼它形成的結果也自然越不出以往的層面。說得更加透徹些,如果中國歷史已經面臨什麼新課題,以明末農民起義的客觀水準看,是不能指望由它去負載、處理和解決的。實際上,明末的現實恰恰如此。雖然從李自成、張獻忠那裏我們找不到新的歷史軌跡,但這樣的軌跡在中國的確已經出現。證據有三:一、晚明經濟因素和生產方式有新的突出變化;二、以鄉紳力量的成長為背景,出現了社會再組織情形和新的社區政治萌芽,隱約有使君主集權耗散的趨勢,甚至在局地事態中與之頡頏;三、精神思想和文化上,明確提出了君權批判,要求權力、利益重新分配,並嘗試構想和描述新的社會圖景和正確的倫理。縱覽帝制以來中國史,不難鑒辨這三條都是帶革命性的新的歷史元素,它們應該寓示着中國的歷史可能會有大的轉折和突破。
明末所以出現這樣的轉折和突破,得益於兩點,一是社會歷史本身的水到渠成,二是精神思想和文化達到了相應高度。
關於前者,我們可通過唐宋以來中國技術文明的進化、商品的發展、城市的數量增長和形態變化去了解,更可注意明朝工商繁盛、出現僱傭勞動、大規模海外貿易、金融貨幣影響加重、資本開始集中,以及在資本和技術支撐下生產益趨專業化競爭,以至初步有行業壟斷苗頭等現象。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引《歙縣風土志》說,嘉靖、隆慶間,長江中下游已現「末富居多,本富益少」之狀。古時,農為本、工商為末;「本富」是以農而富,「末富」則屬於因工商致富。這種財富來源或經濟成分的變化,當然楬櫫着中國的一種質變。而各地區緣其資源、技術優勢,開始形成專業化分工與佈局,例如布疋生產,通常在松江紡織,再運到蕪湖染色,原因是兩地在不同生產環節和技術方面各擅所長、優勢明顯。說到行業壟斷苗頭,可舉徽州為例;當時,徽州的生產者無疑已執了中國文化產業之牛耳,從文化用品(筆墨紙硯)到圖書出版,絕無他處能攖其鋒,《桃花扇》寫到的蔡益所,大概便是這樣一位;他登臺時,誇耀自己的書肆:「你看十三經、廿一史、九流三教、諸子百家、腐爛時文、新奇小說,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連樓。」我們熟知的《千字文》、《百家姓》並「三言」、「二拍」這樣一些最風行的古代出版物,都是徽州出版家的產品,由他們編纂、刻印而推出問世。此外,由著名的「白銀現象」,可知資本元素在明代之突兀。按照弗蘭克的研究,當時全球的白銀泰半湧入中國,中國乃是「世界白銀生產的終極『祕窖』」。世界史上昔日的白銀時代,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經濟的存在與支撐,正如以後美元時代與美國經濟之間的關係。中國商品經濟之發達,其又一證據是它所擁有的幾座超大城市,「南京達到100 萬人口,北京超過60 萬人口」,而廣州與鄰近的佛山有150 萬居民,這「幾乎相當於整個歐洲城市人口的總和」。城市規模取決於城市內容,在以軍事、政治為主導的古典型城市那裏,既不需要在空間和人口上有大的擴展,事實上也難以負擔這種擴展,只有在商品經濟發達的條件下,超大規模的城市才有其必要。
明代經濟和社會具轉型意義的變化及表現甚多,學界也有充分的專業性討論,茲難盡述。總之,我們從中得到這樣的印象:到了明末,中國歷史已至新舊交替的關口。它一面為舊矛盾所困(即農民起義所反映的),一面湧出全新的問題和現象。而從前瞻角度看,後者更重要、更具時代特色。代表歷史深遠去向、直指今天的,不是農民起義軍,不是李自成、張獻忠,而是社會經濟、技術、生產方式的演進所提出來的歷史變革要求。這才是真正有延展性的方向,尤當我們幸運地站在五百年後,更是一目了然看見它穿越時空而來。反觀在四川以屠戮為樂的張獻忠,抑或進入北京後終不能克制對於「子女玉帛」興趣的大順軍,我們無疑找不到這樣的線索和指向。
說來說去,還是歷史高度問題。農民起義作為社會現實釀出的苦果,有其不可避免性,也完全值得理解,然而它確實並不處在時代、歷史的高度上。在明代末年,是誰體現了這種高度?對此,只要尊重事實、直面歷史,都不難於回答:是新興經濟和文化所催生的士紳、知識分子群體。意識到並進而承認這一點,首先需要跳出「階級鬥爭為綱」思維,將目光落實和聚焦於先進生產力這一歷史大局。反之可見,這麼多年由於義理之蔽,我們對自己一段重要歷史,怎樣認識不夠、偏頗乃至嚴重誤讀。走出這遮蔽,明末歷史不單自己要浮現煥然一新的面目,很可能將使中國的古代史、古代文化被重新看過。我們看見,在社會和歷史的質變的刺激下,明末有了立足於自我、個體的強烈的私有觀念,而以此為引導,進而有「平權」的意識,又從「平權」意識中發展出對君權、獨夫的批判。將這種思想脈絡連結起來,最終它將指向何方,對已置身現代文明的我們來說,答案不言自明、相當簡單。這裏先要分辨一點:「私有」的現象、現實的存在,不等於有明確、完全的私有觀念或私有主張,後者必以個人獨立權利的認識與訴求為前提。在中國,私產的事實從春秋時代公田變私田起即已發生,但二千多年來,私產存在的事實與私有觀念或私有主張的形成並不同步,原因是對私產的承認沒有與個人獨立或對個人權利的尊重掛鈎。在大一統君權倫理中,君猶父,民猶子,這種以家庭比喻國家抑或將國家縮微於家庭的解釋,旨在限制社會的真正獨立性,百姓萬民不過是一個龐大家族的眾多支系,在生活層面有自己的單元、空間,在倫理或法理上卻仍歸家長(君父)所有。因此,中國雖容納了私產的事實,卻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所謂「神聖不可侵犯」的私有制;如果有,亦僅是皇帝一人所享有之私有制,國家為其私有,萬民為其私有,官員薪酬取之賦稅卻認為自己乃是「食君祿」…… 但這歷來的認識,在明末切切實實面臨突破。黃宗羲提出新的社會政治倫理:「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正當的國家,是讓所有人「各得其私」「各得其利」、「敢自私」「敢自利」的國家;應該根據這樣的邏輯和原則,重新立法,以「天下之法」代「一家之法」。面此表述,我們該認其為中國真正發生私有觀念之始;它與歐洲啟蒙思想家們所鼓吹的私有觀念,比如蒲伯所談「社會的正義靠自私來維繫」c 那樣的意思,既在同一方向,也在同一高度。
這樣推崇私有觀念,是破天荒的事情。一旦有這種觀念,過往一切價值都將紛然披解,倫理基石將被更換,個人或個體將就此崛起。在私有觀念的拱衞下,每一位個體都有天然的平等地位。從本質上說,私有觀念是一種人權觀,而非財產觀;它所肯定和欲加保護的,遠不僅只是「財產」和「有錢人」,而是每個人依天賦人權理當擁有的一切:他的身體、他的精神、他的自由、他的尊嚴…… 只有愚民主義,才將私有觀念曲解成唯獨富人受益之物。事實上,私有觀念與每個人悉悉相關。不論他們是貧是富,是平凡是顯赫。它讓社會真正回到對個人的尊重,真正摧毀了基於權力的人身依附。極而言之,私有觀念下即便流浪的孤兒、身無分文的丐民,也比專制制度下腰纏萬貫的富人更富有,至少他們作為人的基本權利不得踐踏,而後者卻隨時可能被不受約束的權力剝奪一切。
私有觀念不立,則平等思想無所由,平權意識無所出。黃宗羲說,君權之下,「不過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應於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時免於寒餓,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復計其禮之備與不備,躋之僕妾之間而以為當然。」君之視臣如僕,臣之視己為妾,維持着一種卑怯苟且的關係,與「禮之備與不備」全無牽涉(這裏,「禮」不妨換為「理」)。於是,他提出自己心中合理的君臣關係:「治天下猶曳大木然」,「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第一,沒有坐享其成者,大家都應該是勞動者;第二,只有分工不同,沒有主僕之分,大家只是共事者。彼此關係,是互相依存、合作,不能一方發號施令、一方匍匐服從…… 假如我們對自古以來的君臣倫理略知一二,大概都不能不震驚於他的「肆無忌憚」、「犯上作亂」。過去,我們只知有李自成那樣的「造反者」,現在才知道,跟黃宗羲相比那些「造反者」算不了什麼。黃巢、朱元璋、李自成是將舊皇帝反下臺、自己去做新皇帝。黃宗羲不然,他直接否定了君權,把它從獨大、獨夫位子拉下馬。這不是造反,這是發動一場革命。
總之,中國歷來的只反貪官、不反皇帝,乃至人人心頭暗揣的皇帝夢,到明末,終於有人起來將它徹底擊碎了。皇帝字眼,在黃宗羲那裏已徹底是負面的存在:「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而類似批判,並不僅見於黃宗羲,實際是明末清初一批知識分子的共同心聲。例如雍正間呂留良案,案主曾靜在其《所知錄》中,將過往皇帝一語概括為「光棍」,提出對皇帝「成分」加以徹底改造:「皇帝合該是吾學中儒者做」。此話的重點,與其說鼓吹儒者當皇帝,毋如說鼓吹「知書」方配得上治國。因為「知書」才能「達理」,「達理」才會講道理、不胡來。善意、理性的政治,只能是講道理、不胡來的政治。對此,他們有原則,甚至也有初步的制度構想。原則方面,黃宗羲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權力不代表真理,權力與真理不構成等式,這與我們今人「反獨裁」是同樣的意思。接着他提出了一個扼止獨裁的辦法,就是「公其非是於學校」,「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這裏的「學校」,與現在純粹的教育機構有些不同,或可解釋為國家政治人材儲備地。裏面的人,既是學生身份也是未來的從政者;他們「知書」、有知識理性,當前又置身「朝堂」之外,與烏七八糟的利益無關,大致相當於有獨立見解的專家型政治評議人。所以,「公其是非於學校」、「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這樣的環節即便一時談不上政治決策過程民主化,但對君權發生一定約束、制衡作用,顯然是可期待的。其實更重要一點在於,這是新的政治思路和方向的打開、開啟,沿此探索下去,誰能說中國人斷然提不出類似代議制那樣的設想呢?
所以說,明末的精神思想高度,明顯表現在新興社會實踐及其代言者那裏,而非表現於別的事情。但何其不幸,這進程卻迭遭兩次隔礙。明末的農民戰爭和滿清入侵,各有其必然,又各有其偶然。其必然,在於明王朝近三百年作孽多端、積重難返、窳敗不堪、千瘡百孔,早就如坐火山頂上,內憂與外患,都是一觸即發;最終而言,明朝無論亡於李自成還是亡於滿清,都應該說合情合理、咎由自取。其偶然,則是從歷史大方向來看,內亂和外侵同樣擾亂了中國的腳步;彼時中國,黃宗羲以「天崩地解」稱之,大懷疑和大批判的精神磊然而起,相對於即將到來的變革,「虜」「寇」之亂非但不處於同一方向,反倒令之鎩羽折翅、魚池水乾,恰似黎明前本來極黑暗之際,地平線一縷曙光微微露出卻倏忽消失,轉而又沉入更深的黑暗。正因此,當我偶然見到「黑洞」一詞的解釋—黑洞是一種引力極強的天體,就連光也不能逃逸—當即想到,這簡直就是明末的中國。
中國就此與可能的重大變革失諸交臂,令人悵惘。不過,此亦為歷史所常有。對於歷史,有人完全取理性主義,有人待以不可知論,恐怕各有偏至。總的來說,筆者不懷疑歷史有其大方向,但就具體一時一地之事看,歷史恐怕確實並不像理性主義者講的那樣富於規則、有規律可循,相反,種種的偶然、難以捉摸的情形屢見不鮮。明末這段歷史,便屬於後者。我們曾聽說「資本主義」—不用這個指向性過強的術語,代以「現代文明」一詞也許較好—不可能從東方的歷史和文化自發產生;它另一種意思是,中國通往現代,只能依靠西風東漸、由外鑠我的途徑,甚至引出自由、民主等理念天然不合中國之論。諸如此類,非破不可;一因它們有礙我們對更好社會的探索追求,二來也全非歷史事實。對這種論調,如果細緻考察過中晚明的社會及文化,都很難不表質疑。當時中國明顯自發地進入了「轉型」通道,這結論應謂毋庸置疑。只是這一前景,被突發事態攔腰截斷,繼而由於滿清的統治,民族矛盾取代和壓制了中國原有的歷史文化苦悶。換言之,中國所以未能延續「轉型」過程,純屬意外。歷史上,這種意外不在少數。遠的不說,近現代兩次中日戰爭,都不同程度改變了中國歷史軌跡。故爾,歷史一面有其必然,一面也隨時發生偶然;雖然總的來說,必然力量千迴百折終歸要實現,但因偶然而起的挫折、延誤與遲緩,也實實在在令一個國家和民族在「運氣」層面接受考驗。我個人認為,從「古典」向「現代」轉化中,中國的「運氣」明顯不如歐洲。當然,「運氣」也有在我們一邊的時候,例如公元之初前後,較之於別處(小亞細亞至歐羅巴大陸一帶),我們的局面相對簡單,麻煩較少,而能建起比較充分、穩固的農業社會農業文明,享其成果一千多年。
有時,歷史興廢不由人意,我們只有仰而受之,這是沒辦法的事。但我們不可以不知其來歷,不可以泯其真相,尤不可以錯過它的教益。中國人說,往時難諫、來日可追;又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知往鑒今,是歷史對我們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歷史包含各種人力難及的啟迪,許多問題,我們窮以一生、苦思冥想或許仍不能破解,到歷史中卻能輕鬆找到答案。這就是歷史的寶貴,是它值得我們熱誠相待的理由。在精神上和知識上,人類有諸多學習的途徑,或者說,有許多師法的對象;在我看來,自然和歷史是其中最好的兩位老師,因為它們從不說謊,也幾乎不會用虛離矯偽的義理誤導你。
目次
序一
序二
序三
國變.定策
四鎮.武人
虜寇.坐斃
桃色.黨爭
降附.名節
錢穀.貪忮
民心.頭髮
真假.謠言
曲終.筵散
遺民.苦悶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