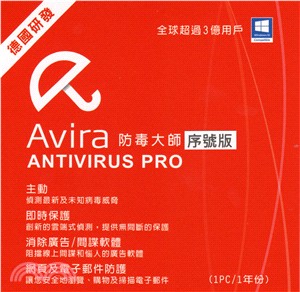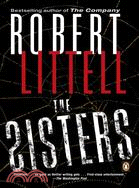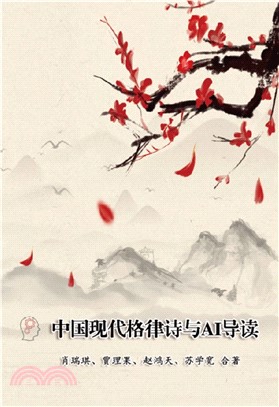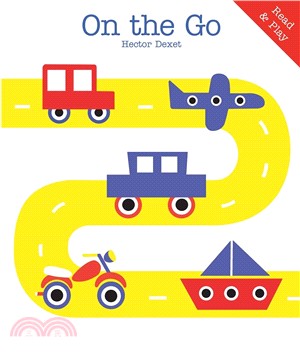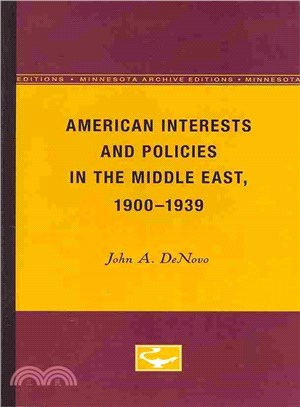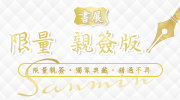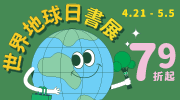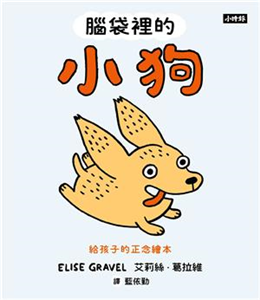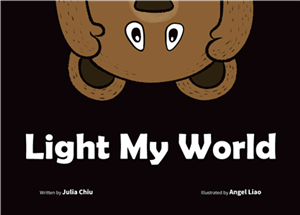帥旦(簡體書)
商品資訊
系列名:身份共同體·70後作家大系
ISBN13:9787532944828
出版社:山東文藝出版社
作者:計文君
出版日:2014/06/01
裝訂/頁數:精裝/329頁
規格:23.5cm*16.8cm (高/寬)
版次:一版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為計文君的最新中短篇小說集,主要收錄了《開片》、《白頭吟》、《剔紅》、《天河》、《無家別》、《你我》等7篇,集中展示了計文君作為70后作家代表人物的創作實績。
作者簡介
計文君,河南許昌人。2000年開始小說創作。文學博士,研究方向為“《紅樓夢》小說藝術現當代繼承”,現供職于中國現代文學館。
名人/編輯推薦
70后作家,他們形成了一個代際的“身份共同體”。這個共同體并不具有天然性,而是在文學實踐過程中逐漸“建構”起來的。
“50后”、“60后”可以看作是一個“歷史共同體”。他們有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大體相似的對于歷史的認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大體相似的歷史經歷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80后”是一個以話語方式與關注對象形成的“情感共同體”,特殊的情感認同是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征。
身份共同體 70后作家大系
匯聚70后作家 展示一個時代的文學實績
“50后”、“60后”可以看作是一個“歷史共同體”。他們有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大體相似的對于歷史的認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大體相似的歷史經歷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80后”是一個以話語方式與關注對象形成的“情感共同體”,特殊的情感認同是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征。
身份共同體 70后作家大系
匯聚70后作家 展示一個時代的文學實績
序
“70後”的身份之“迷”與文學處境孟繁華張清華當我們決心要把一群“70後”作家裝入一個籠子的時候,發現這是一件難事。因為這些人的創作確乎很難從總體上做出涵蓋與評價。除了年齡相近,他們在文學上幾乎再沒有更多共同之處。
這恐怕與這代人的歷史與文化記憶有關。總體上,比較而言,“60後”與“50後”作家之間沒有太明顯的界線或差異,因為他們都有著接近的歷史經驗與公共記憶。至於“80後”作家,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麼“集體記憶”,他們出生時社會已經開始劇變,走向差異與破碎了。而“70後”這一代,剛好處在歷史的夾縫之間——對於歷史,他們的印象是若隱若無似是而非;同時上世紀80年代以來急風暴雨式的文學革命與他們也幾乎沒有什麼關係。當他們登上文壇的時候,80年代的文學革命已經落幕了;面對現實,“80後”又橫空出世,遭遇網絡文學大行其道,沒有歷史負擔的這代人幾乎可以為所欲為無所不能。“70後”就夾在這兩代人之間,他們只能另闢蹊徑展現他們的文學才能。因此,這一代的小說可以說一直遊移於歷史與現實之間,遊移於個體的敘事與公共的記憶之間。
當然,這樣的分析或許只是一孔之見。事實上,“70後”作家們用他們的方式仍然創作了許多新鮮而獨特的各式小說。當總體性潰敗之後,用“代際”概念來表達創作的差異性也許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但文學批評就是這樣,雖然是臨時性的概念,但要試圖對之進行有效闡釋時又不得不用之,而它的通約性也為我們提供了討論問題的方便和可能。
或許這樣表達不同代際作家的文化記憶或類型是合適的:“50後”、“60後”可以看作是一個“歷史共同體”。他們有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大體相似的對於歷史的認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大體相似的歷史經歷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80後”是一個以話語方式與關注物件形成的“情感共同體”,特殊的情感認同是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徵。“70後”如前所述,他們隱約或模糊的歷史記憶難以形成明確的歷史共同體,同時又不像“80後”那樣沒有任何歷史負擔。因此,他們只形成了一個代際的“身份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並不具有天然性,而是在文學實踐過程中逐漸“建構”起來的。“70後”作家曹寇說:“在早已成名的‘60後’和‘80後’作家之間,確實存在一個灰色的寫作群體,說白了,他們就是‘70後’。雖然寫作者大多討厭將自己納入某個代際或某個類別中去,但‘70後’作為‘60後’和‘80後’之間的那一代亦為客觀事實。而且考慮到每代作家的成長環境、知識結構對他們寫作的影響,剔除清高和矯情而接受中間代這一說法也未為不可。此外,‘70後’與上下兩代人的差異也是有目共睹的。迄今沒有一位‘70後’能像‘60後’作家那樣獲得廣泛的文學認可,在‘60後’已被譽為經典之際,‘70後’仍然被視為沒有讓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①更重要的問題是,無論是“50後”、“60後”的“歷史共同體”,“70後”的“身份共同體”還是“80後”的“情感共同體”,他們都是“被想像”的共同體。一方面,這一劃分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這個合理性並沒有被充分證實。王安憶曾經說:“我們這一代的人都有人進了天國,可是還沒有來得及建立一個傳統,所以,千萬不要再說‘讀你們的書長大’的話,我們的書並不足以使你們長大,再有二十、三十年過去,回頭看,我們和你們其實是一代人。文學的時間和現實的時間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據思想的濃度,思想的濃度也許又根據歷史的劇烈程度。總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還要依憑於價值。我們還沒有向時間攫取更高的價值來提供你們繼承,所以,還是和我們共同努力,共同進步,讓二十年三十年以後的青年能真正讀我們的書長大。”①如果是這樣的話,“70後”的身份之“迷”完全是被杜撰出來的,現在的代際劃分過二三十年後也將淪為子虛烏有。那時回頭看現在,原來是一場毫無意義的白忙活。
然而另一方面,“70後”作家個體的獨立或分散狀態,也就是今日中國文學狀態的縮影和寫照。文學革命終結之後,統一的文學方向已不復存在。但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還要特殊一些,這就是他們很難找到自己的歷史定位。2009年諾獎獲獎者赫塔·米勒說,她的寫作是為了“拒絕遺忘”。類似的話還有許多作家說過,但是,這樣正確的話對中國“70後”作家來說或許並不適用。普遍的看法也認為,“70後”是一個沒有集體記憶的一代,是一個試圖反叛但又沒有反叛物件的一代。事實的確如此,當這一代人進入社會的時候,社會的大變動——急風暴雨式的社會與文學變革都已經成為過去。“文革”的終結、啟蒙主義年代的終結,使中國社會生活以另一種方式展開,經濟生活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體。日常生活合法性的確立,使每個人都拋卻了意義又深陷“關於意義的困惑”之中;同時,自80年代開始的“反叛”又日甚一日地遍及了所有的角落,90年代後,“反叛”的神話在疲憊和焦慮中無處告別,自行落幕。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不論“反叛”的執行者是誰,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切都與70年代無關或關係不大。這的確是一種宿命。於是,70年代便成了“夾縫”中生長的一代。這種尷尬的代際位置為他們的創作造成了困難,或者說,沒有精神與歷史依傍的創作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例外。在我們看來,雖然很難對這代作家做出整體性的概括,但他們也確乎沒有形成一代人文學的“同質化”傾向。換言之,他們生成了另一種難得的豐富性——他們之間是如此不同,除了一個“身份共同體”以外幾乎很難找到他們之間任何兩個人的相似性。正是這種不同,使他們在歷史縫隙中的突圍成為了可能。於是,我們在世紀之交或者新世紀以來,便看到了由魏微、戴來、朱文穎、金仁順、喬葉、李師江、徐則臣、魯敏、盛可以、計文君、付秀瑩、馮唐、瓦當、路內、曹寇、慕容雪村、梁鴻、李修文、安妮寶貝、哲貴、阿乙、張楚、李浩、石一楓、李雲雷、東君、黃詠梅、娜或、朱山坡……這樣一群人構成的“70後”小說家的主力群體。
關於“70後”作家的特徵,宗仁發、施戰軍、李敬澤三位很早即發表過對話《被遮蔽的“70年代人”》。十幾年前他們就發現了這一代人“被遮蔽”的現象,比如他們完全在“商業炒作”的視野之外,還有部分作家所負載的“白領”意識形態對大眾的鼓惑誘導等等。但現在看來,之所以會有這些看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50後”這代作家形成的“隱形意識形態”對他們的壓抑和遮蔽。“‘70年代人’中的一些女作家對現代都市中帶有病態特徵的生活的書寫,不能不說具有真實的依託。問題不在於她們寫的真實程度如何,而在於她們所持的態度。應該說1998年前後她們的作品是有精神指向的,並不是簡單的認同和沉迷,或者說是有某種批判立場的。”這些看法確乎是有遠見的,上一代作家在文壇建構起的統治地位和主流形象,作為一隻“看不見的手”持續壓抑和遮蔽了後來者,他們被早已形成的經典化秩序規定了自己的身份與姿態——“你是一個年輕的、生於70年代的作家,你就是‘新新人類’,否則你就什麼都不是。”這一描述道出了“70後”的身份之“迷”和精神的困窘。
但是,許多年過去之後,“70後”仍然以他們的創作實績,顯示了他們令人不可忽略的文學地位。假如要讓我們舉出例證,那麼例證是不勝枚舉的。
魏微——她的中、短篇小說,因其所能達到的思想深度和藝術的獨異性,已經成為這個時代中國高端藝術創作的一部分。魏微取得的成就與她的小說天分有關,更與她藝術的自覺有關——她很少重複自己的寫作,對自己藝術的變化總是懷有高遠的期待。盛可以,她一出現就顯示了不同凡響的語言姿態,她語言的鋒芒和奇崛,如列兵臨陣刀戈畢現,她的長篇小說如《火宅》、《北妹》、《水乳》以及短篇小說《手術》等,都不是以觸目驚心的故事見長,甚至也沒有跌宕起伏刻意設置的情節或懸念,可以說,其最大的魅力就在於她銳利如刀削般的語言。在她那裡,“怎麼寫”永遠大於“寫什麼”。李師江,他幾乎糾正了現代小說建立的“大敘事”的傳統,個人生活、私密生活和文人趣味等被他重新鑲嵌於小說之中。李師江似乎也不關心小說的“西化”或“本土化”的問題,但當他信筆由韁揮灑自如的時候,他確實獲得了一種自由的快感。於是,他的小說與現代生活和精神處境密切相關,他的小說也是傳統的,那裡流淌著一種中國式的文人氣息。魯敏,她的小說既寫過去也寫現在,既有虛構也有寫實,關於“東壩”的敘述,已經成為她小說創作的重要部分。這個虛構的所在,在今天已是只能想像而無從經驗的了——就像當年的魯鎮、烏鎮或其他類似的地方。現代化的進程決絕地剿滅了這些力不從心或沒有抵抗能力的脆弱區域,那些渺小而令人心痛的生命。中國的小鎮是一個奇異的存在,它在城鄉交界處,是城鄉的紐帶,是過去中國的“市民社會”與鄉紳文化存在的特殊空間。在那裡,我們總會看到一些奇異的人物或故事,這些人物或故事是帶著與都市和鄉村的某些差異來到我們面前的。張楚,他的小說的魅力,就在於難以一眼望穿的模糊。這是一個有巨大野心的小說家,他的作品難以用譜系的方式找到來路,他的小說有諸多元素:深受西方十八九世紀文學、現代派文學和後現代文學的影響,也受到中國現代小說的影響,甚至受到《水滸傳》以及其他明清白話小說的影響。經過雜糅吸收和重新鋪排,誕生了這個奇異的張楚。看來他是真的理解了小說,他的每篇作品,在生活的層面幾乎都無可挑剔,生活的質感、細節和真實性幾乎達到了“非虛構”的程度,但是整體來看,其虛構性甚至詩性又都一目了然。
在亦真亦幻、真假難辨之間,張楚的小說像幽靈一般在我們眼前飄過。哲貴,這個擅長集中書寫富人的存在與精神狀況的作家也是一個特例。他所描寫的這個階層在中國是如此特殊——他們是一個“成功者”的階層,是一個被普通人羨慕乃至仰望的成功人群,但這個人群無所歸依、空虛空洞的內心世界,在哲貴的講述中可謂令人有難以言喻的震驚。東君的小說寫的似乎都是與當下沒有多大關係的故事,或者說是無關宏旨漫不經心的故事。但是,就在這些看似不經意的、曖昧模糊的故事中,他表達了對世俗世界無邊欲望的批判。他的批判不是審判,而是在不急不躁的講述中,將人物外部面相和內心世界逐一托出,在對比中表達了清濁與善惡。計文君,她的小說仿佛出自深宅大院:它典雅、端莊,舉手投足儀態萬方。因此她是一位帶有中國古典文化氣息和氣質的作家。另一方面,它詭異、繁複、俏麗,修辭敘事雲卷雲舒。她的小說有西方20世紀以來小說的諸多技法和元素,但是計文君卻又既不是傳統的也不是西方的,她是現代的。
付秀瑩,作為一位後來居上的新秀,起初很長一段時間,她只以孫犁式簡約而又清麗的筆觸書寫她記憶中的鄉村,鄉村的錦繡年華風花雪月曾讓她迷戀不已。
近年來,她的創作視野也逐漸轉移到了城市,但她仍然寫得溫婉而跳脫、節制而耐心。娜或的小說創作,在某種程度上接續了80年代現代主義的文學傳統,接受了存在主義哲學的精神饋贈。作為潮流的現代主義雖然已成為了過去,但是,現代主義文學曾經揭示和呈現的關於人的惶惑、迷惘甚至反抗的精神狀態和內心要求不僅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比80年代更加普遍和激烈。娜或顯然發現或感受到了這一精神現象的存在,因此,以極端化的方式表達這一精神現象,顯然是娜或刻意為之的。
就在我們梳理“70後”創作成績的時候,另外一種批評的聲音也如期而至。青年批評家張莉認為“70後”小說家的創作,是“在逃脫處落網”。她認為:“70後作家創作遇到的困境,也是新時期文學三十年發展的一個瓶頸:從先鋒寫作、新歷史主義到新寫實主義、晚生代/新生代寫作,中國文學已經被剝除文學的‘社會功能’和‘思想特質’,它逐漸面臨淪為‘自己的園地’的危險。70後作家參與建構了中國當代文學近十年來的創作景觀——如果我們瞭解,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一直在強調‘祛魅’,即解除文化的神聖感、莊嚴感,使之世俗化、現實化、個人化,那麼70後作家整體創作傾向於日常生活的描摹、人性的美好禮贊以及越來越喜歡討論個人書寫趣味則應該被視作一個文學時代到來的必然結果。”①這一提醒並非惘然。整體看“70後”作家的創作,歷史全面隱退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雖然切合了這代人的身份,但也從另一個方面暴露了他們難以與歷史建構關係的真實困境。
顯然,如果從一般性的常識來看,“70後”作家的多樣性是一個非常大的優點,問題就在於他們迄今“經典化”程度的嚴重不盡如人意。到了應該“挑大樑”的年代,到了應該登堂入室的年紀,到了應該有普遍代表性的時候,一切卻幾乎還在鏡子裡,是一個“願景”。中國文學中佔據主要地位的仍然是“50後”和“60後”的一幫中年作家。究其原因,在我們看來,當然有各種難以言喻的外在因素,但如果從內部講,恐怕就是因為個人經驗書寫與共同經驗與集體記憶的接洽問題。在現階段,否認個人經驗或者經驗的個人性當然都是幼稚的,但一代作家要想成為一代人的代言者,一代人的生命的記錄者,如果不自覺地將個體記憶與一個時代的整體性的歷史氛圍與邏輯,與這些東西有內在的呼應與“神合”,恐怕是很難得到廣泛的認可的。
或許這與作家的“抱負”有關,也許他們會說,去你們的狗屁“抱負”吧,只不過是一些歷史的幻想狂或自大狂的假像,我們就是要寫局部、碎片、個人情境。那誰也沒辦法,但是我們想提及的一點就是,任何人想進入歷史都得有代價,這個代價就是如同當代法國的社會學家莫裡斯·哈布瓦赫所說的,個人記憶是必須要有“社會框架”的,否則就會產生奇怪的失憶症。或許這代人過於無序的經驗書寫,也是某種社會與歷史失憶症的表現吧。
另一方面,90年代以後的中國文學,帶著西方文學的影響和記憶開始了整體性的“後退”,這個“後退”就是向傳統文學和文化尋找資源,開始了又一輪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探索是在總體性瓦解之後的探索,因此它有更多的個人性。這也是“70後”作家整體風貌的一部分。“70後”隱約的歷史記憶,使他們不得不更多地面對個人的心理現實——因為他們無家可歸。但是,他們在矛盾、迷蒙和猶疑不決之間,卻無意間形成了關於“70後”的文學與心路的軌跡。無論如何,這代作家的成就和問題,都是我們當下中國最典型的文學經驗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在注視這代人文學實踐的時候,事實上也就是在關注當下的中國文學。
2014年2月25日於北京
這恐怕與這代人的歷史與文化記憶有關。總體上,比較而言,“60後”與“50後”作家之間沒有太明顯的界線或差異,因為他們都有著接近的歷史經驗與公共記憶。至於“80後”作家,幾乎可以說沒有什麼“集體記憶”,他們出生時社會已經開始劇變,走向差異與破碎了。而“70後”這一代,剛好處在歷史的夾縫之間——對於歷史,他們的印象是若隱若無似是而非;同時上世紀80年代以來急風暴雨式的文學革命與他們也幾乎沒有什麼關係。當他們登上文壇的時候,80年代的文學革命已經落幕了;面對現實,“80後”又橫空出世,遭遇網絡文學大行其道,沒有歷史負擔的這代人幾乎可以為所欲為無所不能。“70後”就夾在這兩代人之間,他們只能另闢蹊徑展現他們的文學才能。因此,這一代的小說可以說一直遊移於歷史與現實之間,遊移於個體的敘事與公共的記憶之間。
當然,這樣的分析或許只是一孔之見。事實上,“70後”作家們用他們的方式仍然創作了許多新鮮而獨特的各式小說。當總體性潰敗之後,用“代際”概念來表達創作的差異性也許本身就是一個錯誤,但文學批評就是這樣,雖然是臨時性的概念,但要試圖對之進行有效闡釋時又不得不用之,而它的通約性也為我們提供了討論問題的方便和可能。
或許這樣表達不同代際作家的文化記憶或類型是合適的:“50後”、“60後”可以看作是一個“歷史共同體”。他們有共同的歷史記憶,以及大體相似的對於歷史的認知方式和情感方式,在大體相似的歷史經歷中,完成了一代人的文化塑形。“80後”是一個以話語方式與關注物件形成的“情感共同體”,特殊的情感認同是這一代人近似的文化性格特徵。“70後”如前所述,他們隱約或模糊的歷史記憶難以形成明確的歷史共同體,同時又不像“80後”那樣沒有任何歷史負擔。因此,他們只形成了一個代際的“身份共同體”。這個共同體並不具有天然性,而是在文學實踐過程中逐漸“建構”起來的。“70後”作家曹寇說:“在早已成名的‘60後’和‘80後’作家之間,確實存在一個灰色的寫作群體,說白了,他們就是‘70後’。雖然寫作者大多討厭將自己納入某個代際或某個類別中去,但‘70後’作為‘60後’和‘80後’之間的那一代亦為客觀事實。而且考慮到每代作家的成長環境、知識結構對他們寫作的影響,剔除清高和矯情而接受中間代這一說法也未為不可。此外,‘70後’與上下兩代人的差異也是有目共睹的。迄今沒有一位‘70後’能像‘60後’作家那樣獲得廣泛的文學認可,在‘60後’已被譽為經典之際,‘70後’仍然被視為沒有讓人信服的‘力作’的一群。”①更重要的問題是,無論是“50後”、“60後”的“歷史共同體”,“70後”的“身份共同體”還是“80後”的“情感共同體”,他們都是“被想像”的共同體。一方面,這一劃分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這個合理性並沒有被充分證實。王安憶曾經說:“我們這一代的人都有人進了天國,可是還沒有來得及建立一個傳統,所以,千萬不要再說‘讀你們的書長大’的話,我們的書並不足以使你們長大,再有二十、三十年過去,回頭看,我們和你們其實是一代人。文學的時間和現實的時間不同,它的容量是根據思想的濃度,思想的濃度也許又根據歷史的劇烈程度。總之,它除去自然的流逝,還要依憑於價值。我們還沒有向時間攫取更高的價值來提供你們繼承,所以,還是和我們共同努力,共同進步,讓二十年三十年以後的青年能真正讀我們的書長大。”①如果是這樣的話,“70後”的身份之“迷”完全是被杜撰出來的,現在的代際劃分過二三十年後也將淪為子虛烏有。那時回頭看現在,原來是一場毫無意義的白忙活。
然而另一方面,“70後”作家個體的獨立或分散狀態,也就是今日中國文學狀態的縮影和寫照。文學革命終結之後,統一的文學方向已不復存在。但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還要特殊一些,這就是他們很難找到自己的歷史定位。2009年諾獎獲獎者赫塔·米勒說,她的寫作是為了“拒絕遺忘”。類似的話還有許多作家說過,但是,這樣正確的話對中國“70後”作家來說或許並不適用。普遍的看法也認為,“70後”是一個沒有集體記憶的一代,是一個試圖反叛但又沒有反叛物件的一代。事實的確如此,當這一代人進入社會的時候,社會的大變動——急風暴雨式的社會與文學變革都已經成為過去。“文革”的終結、啟蒙主義年代的終結,使中國社會生活以另一種方式展開,經濟生活成為社會生活的主體。日常生活合法性的確立,使每個人都拋卻了意義又深陷“關於意義的困惑”之中;同時,自80年代開始的“反叛”又日甚一日地遍及了所有的角落,90年代後,“反叛”的神話在疲憊和焦慮中無處告別,自行落幕。不知道是幸還是不幸,不論“反叛”的執行者是誰,可以肯定的是,這一切都與70年代無關或關係不大。這的確是一種宿命。於是,70年代便成了“夾縫”中生長的一代。這種尷尬的代際位置為他們的創作造成了困難,或者說,沒有精神與歷史依傍的創作是非常困難的。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例外。在我們看來,雖然很難對這代作家做出整體性的概括,但他們也確乎沒有形成一代人文學的“同質化”傾向。換言之,他們生成了另一種難得的豐富性——他們之間是如此不同,除了一個“身份共同體”以外幾乎很難找到他們之間任何兩個人的相似性。正是這種不同,使他們在歷史縫隙中的突圍成為了可能。於是,我們在世紀之交或者新世紀以來,便看到了由魏微、戴來、朱文穎、金仁順、喬葉、李師江、徐則臣、魯敏、盛可以、計文君、付秀瑩、馮唐、瓦當、路內、曹寇、慕容雪村、梁鴻、李修文、安妮寶貝、哲貴、阿乙、張楚、李浩、石一楓、李雲雷、東君、黃詠梅、娜或、朱山坡……這樣一群人構成的“70後”小說家的主力群體。
關於“70後”作家的特徵,宗仁發、施戰軍、李敬澤三位很早即發表過對話《被遮蔽的“70年代人”》。十幾年前他們就發現了這一代人“被遮蔽”的現象,比如他們完全在“商業炒作”的視野之外,還有部分作家所負載的“白領”意識形態對大眾的鼓惑誘導等等。但現在看來,之所以會有這些看法,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50後”這代作家形成的“隱形意識形態”對他們的壓抑和遮蔽。“‘70年代人’中的一些女作家對現代都市中帶有病態特徵的生活的書寫,不能不說具有真實的依託。問題不在於她們寫的真實程度如何,而在於她們所持的態度。應該說1998年前後她們的作品是有精神指向的,並不是簡單的認同和沉迷,或者說是有某種批判立場的。”這些看法確乎是有遠見的,上一代作家在文壇建構起的統治地位和主流形象,作為一隻“看不見的手”持續壓抑和遮蔽了後來者,他們被早已形成的經典化秩序規定了自己的身份與姿態——“你是一個年輕的、生於70年代的作家,你就是‘新新人類’,否則你就什麼都不是。”這一描述道出了“70後”的身份之“迷”和精神的困窘。
但是,許多年過去之後,“70後”仍然以他們的創作實績,顯示了他們令人不可忽略的文學地位。假如要讓我們舉出例證,那麼例證是不勝枚舉的。
魏微——她的中、短篇小說,因其所能達到的思想深度和藝術的獨異性,已經成為這個時代中國高端藝術創作的一部分。魏微取得的成就與她的小說天分有關,更與她藝術的自覺有關——她很少重複自己的寫作,對自己藝術的變化總是懷有高遠的期待。盛可以,她一出現就顯示了不同凡響的語言姿態,她語言的鋒芒和奇崛,如列兵臨陣刀戈畢現,她的長篇小說如《火宅》、《北妹》、《水乳》以及短篇小說《手術》等,都不是以觸目驚心的故事見長,甚至也沒有跌宕起伏刻意設置的情節或懸念,可以說,其最大的魅力就在於她銳利如刀削般的語言。在她那裡,“怎麼寫”永遠大於“寫什麼”。李師江,他幾乎糾正了現代小說建立的“大敘事”的傳統,個人生活、私密生活和文人趣味等被他重新鑲嵌於小說之中。李師江似乎也不關心小說的“西化”或“本土化”的問題,但當他信筆由韁揮灑自如的時候,他確實獲得了一種自由的快感。於是,他的小說與現代生活和精神處境密切相關,他的小說也是傳統的,那裡流淌著一種中國式的文人氣息。魯敏,她的小說既寫過去也寫現在,既有虛構也有寫實,關於“東壩”的敘述,已經成為她小說創作的重要部分。這個虛構的所在,在今天已是只能想像而無從經驗的了——就像當年的魯鎮、烏鎮或其他類似的地方。現代化的進程決絕地剿滅了這些力不從心或沒有抵抗能力的脆弱區域,那些渺小而令人心痛的生命。中國的小鎮是一個奇異的存在,它在城鄉交界處,是城鄉的紐帶,是過去中國的“市民社會”與鄉紳文化存在的特殊空間。在那裡,我們總會看到一些奇異的人物或故事,這些人物或故事是帶著與都市和鄉村的某些差異來到我們面前的。張楚,他的小說的魅力,就在於難以一眼望穿的模糊。這是一個有巨大野心的小說家,他的作品難以用譜系的方式找到來路,他的小說有諸多元素:深受西方十八九世紀文學、現代派文學和後現代文學的影響,也受到中國現代小說的影響,甚至受到《水滸傳》以及其他明清白話小說的影響。經過雜糅吸收和重新鋪排,誕生了這個奇異的張楚。看來他是真的理解了小說,他的每篇作品,在生活的層面幾乎都無可挑剔,生活的質感、細節和真實性幾乎達到了“非虛構”的程度,但是整體來看,其虛構性甚至詩性又都一目了然。
在亦真亦幻、真假難辨之間,張楚的小說像幽靈一般在我們眼前飄過。哲貴,這個擅長集中書寫富人的存在與精神狀況的作家也是一個特例。他所描寫的這個階層在中國是如此特殊——他們是一個“成功者”的階層,是一個被普通人羨慕乃至仰望的成功人群,但這個人群無所歸依、空虛空洞的內心世界,在哲貴的講述中可謂令人有難以言喻的震驚。東君的小說寫的似乎都是與當下沒有多大關係的故事,或者說是無關宏旨漫不經心的故事。但是,就在這些看似不經意的、曖昧模糊的故事中,他表達了對世俗世界無邊欲望的批判。他的批判不是審判,而是在不急不躁的講述中,將人物外部面相和內心世界逐一托出,在對比中表達了清濁與善惡。計文君,她的小說仿佛出自深宅大院:它典雅、端莊,舉手投足儀態萬方。因此她是一位帶有中國古典文化氣息和氣質的作家。另一方面,它詭異、繁複、俏麗,修辭敘事雲卷雲舒。她的小說有西方20世紀以來小說的諸多技法和元素,但是計文君卻又既不是傳統的也不是西方的,她是現代的。
付秀瑩,作為一位後來居上的新秀,起初很長一段時間,她只以孫犁式簡約而又清麗的筆觸書寫她記憶中的鄉村,鄉村的錦繡年華風花雪月曾讓她迷戀不已。
近年來,她的創作視野也逐漸轉移到了城市,但她仍然寫得溫婉而跳脫、節制而耐心。娜或的小說創作,在某種程度上接續了80年代現代主義的文學傳統,接受了存在主義哲學的精神饋贈。作為潮流的現代主義雖然已成為了過去,但是,現代主義文學曾經揭示和呈現的關於人的惶惑、迷惘甚至反抗的精神狀態和內心要求不僅依然存在,甚至在某些方面比80年代更加普遍和激烈。娜或顯然發現或感受到了這一精神現象的存在,因此,以極端化的方式表達這一精神現象,顯然是娜或刻意為之的。
就在我們梳理“70後”創作成績的時候,另外一種批評的聲音也如期而至。青年批評家張莉認為“70後”小說家的創作,是“在逃脫處落網”。她認為:“70後作家創作遇到的困境,也是新時期文學三十年發展的一個瓶頸:從先鋒寫作、新歷史主義到新寫實主義、晚生代/新生代寫作,中國文學已經被剝除文學的‘社會功能’和‘思想特質’,它逐漸面臨淪為‘自己的園地’的危險。70後作家參與建構了中國當代文學近十年來的創作景觀——如果我們瞭解,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文學一直在強調‘祛魅’,即解除文化的神聖感、莊嚴感,使之世俗化、現實化、個人化,那麼70後作家整體創作傾向於日常生活的描摹、人性的美好禮贊以及越來越喜歡討論個人書寫趣味則應該被視作一個文學時代到來的必然結果。”①這一提醒並非惘然。整體看“70後”作家的創作,歷史全面隱退已經是不爭的事實。這雖然切合了這代人的身份,但也從另一個方面暴露了他們難以與歷史建構關係的真實困境。
顯然,如果從一般性的常識來看,“70後”作家的多樣性是一個非常大的優點,問題就在於他們迄今“經典化”程度的嚴重不盡如人意。到了應該“挑大樑”的年代,到了應該登堂入室的年紀,到了應該有普遍代表性的時候,一切卻幾乎還在鏡子裡,是一個“願景”。中國文學中佔據主要地位的仍然是“50後”和“60後”的一幫中年作家。究其原因,在我們看來,當然有各種難以言喻的外在因素,但如果從內部講,恐怕就是因為個人經驗書寫與共同經驗與集體記憶的接洽問題。在現階段,否認個人經驗或者經驗的個人性當然都是幼稚的,但一代作家要想成為一代人的代言者,一代人的生命的記錄者,如果不自覺地將個體記憶與一個時代的整體性的歷史氛圍與邏輯,與這些東西有內在的呼應與“神合”,恐怕是很難得到廣泛的認可的。
或許這與作家的“抱負”有關,也許他們會說,去你們的狗屁“抱負”吧,只不過是一些歷史的幻想狂或自大狂的假像,我們就是要寫局部、碎片、個人情境。那誰也沒辦法,但是我們想提及的一點就是,任何人想進入歷史都得有代價,這個代價就是如同當代法國的社會學家莫裡斯·哈布瓦赫所說的,個人記憶是必須要有“社會框架”的,否則就會產生奇怪的失憶症。或許這代人過於無序的經驗書寫,也是某種社會與歷史失憶症的表現吧。
另一方面,90年代以後的中國文學,帶著西方文學的影響和記憶開始了整體性的“後退”,這個“後退”就是向傳統文學和文化尋找資源,開始了又一輪的探索。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探索是在總體性瓦解之後的探索,因此它有更多的個人性。這也是“70後”作家整體風貌的一部分。“70後”隱約的歷史記憶,使他們不得不更多地面對個人的心理現實——因為他們無家可歸。但是,他們在矛盾、迷蒙和猶疑不決之間,卻無意間形成了關於“70後”的文學與心路的軌跡。無論如何,這代作家的成就和問題,都是我們當下中國最典型的文學經驗的一部分。因此,我們在注視這代人文學實踐的時候,事實上也就是在關注當下的中國文學。
2014年2月25日於北京
目次
開片
白頭吟
剔 紅
天 河
無 家 別
你 我
帥 旦
白頭吟
剔 紅
天 河
無 家 別
你 我
帥 旦
書摘/試閱
開 片
一
母親離開時,鈞鎮變成了鈞州市,不到三歲的我,對這些變化還毫無概念。我上小學了,忽然發現新城區剛蓋好的樓房,外墻上都貼滿了雪白的窄瓷片,房檐則貼著深紅的瓷片,我們學校也是這樣。放學了,從包著一層鮮亮刺眼瓷片的新城區出來,穿過北關城門,就是灰撲撲的老城區了。
老城十字街口連著東西南北四條大街,僅剩的北關那點兒城墻和帶甕城的城門已經用鐵柵欄保護了起來,但門洞可以過車,城墻還可以爬。從寫著“北拱神京”的城門上往城里看,能看見北關大街上一片青灰色的磚瓦院落。
姥姥嫁進來時,那些院落還都是秦家的。秦家有七房,分過家的,各方各院地過日子。當時秦家各房的人大多還住在北大街上,幾十年,越來越多的外人混雜著住了進來,但我們的鄰居中,老親戚還很多。
姥姥曾經是六房的少奶奶,老親舊眷一直還叫她六奶奶。六房那院,大門上的漆剝盡了,黑黃的木頭還在壯心不已地炫耀著優良的材質,只有開關時才略帶悲涼地于門軸處瑟瑟地落下一些木屑。仰頭能看到門斗上生動依舊的雕花,流云百蝠,鹿嘴含花,桃之夭夭,喜鵲登枝……秦家各房的門頭都有這樣的木雕,明八仙刻的是人物,暗八仙刻的是法器,大朵的牡丹開在云頭笏板上是富貴如意……真能說得清這些名堂的人并不多,但姥姥說我還不會走路,在她懷里抱著,就能指著說得一清二楚。
大門里面,其實已經成了逼仄的巷子,早辨不出幾重幾進了,很多戶人家雜亂地擠在一起。我記事兒的時候,已經落實了房產政策,前院的房客都搬走了,姥姥只出租后院,且在通后院的過廳屋那兒壘起了一道墻,姥姥帶著我,這才又過起了獨門獨院的日子。
院里有三間正房,兩邊是廂房,還有廚房和放蜂窩煤和雜物的小屋,角上是廁所,定期會有拉糞的在我們院墻外,掀開水泥蓋板,清理糞坑。我很喜歡拉糞車的那頭栗色騾子,聽到它脖下的鈴鐺聲,我就會溜出門,靠著青灰的磚墻看它清亮的大眼睛,那大眼睛里有個穿水紅兜兜衫的小妞妞,無聲地跟它說著話。
正房的門一年四季掛著簾子,冬天是沉重的棉簾,簾腳兒墜著壓風的木板;春秋天是布簾子,我最喜歡那條湖藍色的布簾子,上面有雨絲一樣的線條;夏天是青竹簾子,竹篾子碧青,編竹篾子的線隔幾年要換,剛換那年掛上去,雪白的線一點一點在竹篾間露出來,像嵌著兩串珠子。
姥姥的日子過得講究,講究得無微不至,又不落痕跡。講究倒未必奢侈,一樣的黑疙瘩大頭菜,跟后院那些人從一個咸菜攤子上買回來的,姥姥切得細如發絲,點了香醋麻油,搭白米粥吃。絕不像他們,把黑疙瘩切成黑檁條,夾在饅頭里滿大街跑著大嚼。
講究的人必然是巧的,姥姥就是巧的。可惜我笨,姥姥恨起來,拿著尺子敲著我的手背,“白長了一雙水蔥似的手,捏根針跟拿根通條似的,笨死算了。”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同齡人這樣度過童年。長大后才知道,我大概能歸入計劃生育成為國策后的第一代獨生子女,曾被報紙稱為“小公主”、“小皇帝”的一群人,我這個“公主”當得有點兒慘。不過倒是被姥姥的尺子敲打得學了些特殊的本事,比如說我會鎖扣眼,會縫被子,會把蝴蝶牽牛花、小貓釣魚這樣簡單的圖案描在的確良布上,用各色絲線繡成門簾或搭布。
我有記憶之后,生活里只有姥姥。母親的美麗,是北關大街上余韻悠長的傳說,特別是女人們,打量著我,嘴里說著記憶中母親的眉眼,沒來由會曖昧地笑,夸張地嘆氣,我覺得莫名其妙,卻又無緣無故地滿心羞惱。
小學二年級的暑假,一個陌生的阿姨,忽然到了姥姥家,說是帶我去見我母親。姥姥給我收拾了幾件衣服,煮了幾個雞蛋,放在我的書包里,我背著書包跟那阿姨上了火車。我在母親那兒一直呆到快開學,被另外一個陌生的阿姨領著,坐火車又回了鈞鎮。
北京,是個存在于新聞和故事里的地方,母親在那兒做什么?
我從北京回來后就被人堵著問,大人小孩兒都問。我就是抿嘴不說。女人們撥拉著我蓬蓬的粉色紗裙,再扯一扯襪口翻過來的奶油色蕾絲花邊,我被她們擺弄得兩腮發燙。
東院那個夏天總光著脊梁、總也找不下媳婦的牛兒,壞笑著氣我:“你媽傍上‘大款’了,不要你了!”
我噙了淚,咬牙說:“沒有!”
“那你媽怎么又把你打發回來了?你說呀!”牛兒在院門口堵著我問,很快會招來一群人,對我母親好奇的人實在不少。
我忍住了,什么也沒說,捎帶著把淚也給忍回去了。
出了趟遠門,我忽然長大了,心底能存住事兒了。
我在北京一直住在大姨家。很久之后,我才理清了大姨與我們之間曲里拐彎的親戚關系。這位大姨的母親,跟我姥姥是遠房表姊妹。母親最初就是去北京幫大姨的女兒帶孩子,帶得能上幼兒園了,又去別人家帶孩子做飯。北京似乎有很多人家需要保姆,母親總是能找到活兒。
我去了,母親也不能天天陪我,只有禮拜天才回來,帶我出去玩。我大多數日子呆在大姨家,那院子很深,擠擠扛扛住了很多人家,大姨大姨夫都退休了,院子里還有不少跟大姨一樣的老太太,大腔大嗓、熱火朝天地過著日子,我倒覺得比跟著姥姥有趣。大姨夫一直在練各種各樣的氣功,不練功的時候很和氣,笑瞇瞇領著我看回廊下的紅漆柱子,還有他養在石榴樹下的那缸墨色龍井。
我不肯說母親是保姆,并非以此為恥,我那時候很小,還不懂革命工作有高低貴賤之分,我不說只是因為我聽話,母親不讓說,姥姥也不讓說,我就不說。
有時候,被人逼著問急了,我就想給他們編故事。我隨口就能用一些聽來的或是看來的不相干的東西編成有趣的故事,就像有人手指一繞就能把柳條編成漂亮的筐子。母親曾帶我在一家醫院門口停下來買了一只赤豆冰棍兒,身后有人帶著敬畏的口氣說什么友好醫院;一個女人匆匆走進那醫院,身上帶著來蘇水和夜巴黎香水兒混合的味道——我記得母親當時抽了一下鼻子,說來蘇水和夜巴黎;我記得櫥窗里纖細的皮鞋后跟以及那皮鞋的牌子;時髦女人額頭上高聳入云的留海,后面爆炸開的卷發,都用一種叫摩絲的泡沫噴得硬邦邦的……差不多夠了,我用這些就可以編個讓他們張著嘴聽的故事——總也沒有機會,我稍微在外面逗留得長一些,姥姥就會找出來,一箭雙雕地把我和堵著問我的人,都罵上一頓。
母親帶給我的真實感覺,很復雜,回頭想想,八歲的我已經領略了百感交集。從出站口出來就見到了母親,她看著我掉淚,我卻有些呆——母親跟那個帶我坐火車的阿姨一樣陌生,只是更好看。那晚母親給我洗澡,一起上床睡下,我聞著她身上和我身上一樣的爽身粉香氣,忽然哭了,母親跟著也哭了。
過了一星期,母親再來大姨家時,拿著那條粉色的紗裙,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帶我去動物園。在動物園意外地碰到了一位胖阿姨,母親曾經在她家做過保姆,她見了我歡喜得拉著不丟手,跟母親說舞蹈學院、考試什么的,還很懂行地拿手比著量了我的胳膊腿兒。我的命運就被這次偶遇決定了。
母親對我說,要好好學習,好好學跳舞,我就能永遠跟她在一起了。我記得她說話時的表情,臉紅撲撲的,老是半垂著的眼睛也睜圓了,光閃閃亮晶晶的,說了一遍又一遍,唯恐我聽不懂,記不住。
那時候,各種少兒藝術培訓班還不像后來那么遍地開花,不過也已經有了,只是不大像樣。我把母親的信交給姥姥,姥姥就帶我去找母親的一個同學。那個同學是個小學老師,姓王,我叫她王老師。她愛人也姓王,早年畢業于國家舞蹈學院,如今在群藝館工作,我也叫他王老師。男王老師就是我的舞蹈啟蒙老師。
讀研的時候,一位教“西方藝術史”的老師說,我們至今還在用訓練雜技演員的方法培養舞蹈家,著實荒謬。我不知道他說的對不對,反正從一開始我就注定不會成為舞蹈家。舞蹈對我基本就意味著踢腿下腰折磨自己的身體,但我依然很刻苦地練功,因為母親說,好好學跳舞,我們就能永遠在一起。
無論是姥姥敲打下學的女兒手藝,還是群藝館王老師的舞蹈訓練,我都不喜歡,卻也習慣了。我同樣不喜歡、卻很習慣的,是一個人的夜晚。
從記事起,我就是一個人住。姥姥跟我分住正房的兩個房間,中間隔著堂屋。所以,除非偶爾有留宿的遠來親友,我童年的夜晚都是一個人度過的。總有東西,在我睡著之前,攪擾著我,讓我忍不住要流淚。春天秋天是院子那些花草的氣味,要是下雨還有雨的聲音和氣味,冬天卻是那份靜,尤其是雪后,仿佛天地都凍得不能呼吸了,我縮在被窩里,積雪下那些干枯的樹枝發出細微的開裂聲……這種時候,我的心突然會被一種東西抓住,揪扯,困意再也不來,難受得眼淚會流出來——我還太小,不知道那種感覺叫作寂寞……
最難熬的是夏天。放學后在院子里做作業,吃晚飯,偶爾姥姥心情好,吃完飯能讓我看一會兒“七巧板”,更多的時候,姥姥吃完飯就插好院門和房門,上床睡覺了。外面還是大亮的天光,后院那些小孩成群結隊地在街上呼嘯而過,嘰嘰嘎嘎地笑著,奔跑追逐——姥姥的話,野馬一樣。
我也想像野馬一樣,可惜不能。揣著野馬一樣念頭的我,當然不可能睡著,下了床,拖張草枕席坐在堂屋的青磚地上,歪著頭,看寬厚的木門和門檻之間的縫里透進來的明亮光線,想著有什么有趣的游戲,可以像野馬一樣奔跑,卻不會弄出任何聲響……那些有魔力的光線帶著奇跡降臨,我開始給自己編故事。
我編的故事常常讓自己流淚,淚水無聲無息地滾下來。我都不記得自己是什么時候學會這樣不發出聲音地哭,我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鼻息和呼吸,即使在落淚的時候,也能讓自己的聲音一如往常,應付姥姥突然的呼喚。
姥姥最看不慣誰動不動就淌眼抹淚的樣子,她那鄙夷不屑的表情,弄得我一直到現在,偶爾多愁善感那么一會兒,還有罪惡感和羞恥感。
不管自己編的還是別人編的,不管是快樂的還是悲哀的,只要是故事,我都喜歡。電視機我做不得主,只有去書里找故事,尋到每本書,能被我嚼得連渣兒都化了。我從來沒有向姥姥要求買故事書,甚至腦子里都沒出現過這種妄念,母親跟我們的聯系是一封封的信、匯款單和一袋袋漂亮的糖果。那些糖果被姥姥控制著,酌情發放給我,我從來不吃,替每樣糖果編一個來歷非凡的故事,然后把故事和糖果放在一起去換同學手中的故事書。那時候“忽悠”這個東北方言里的語匯還沒傳遍大江南北,我不知道該怎么命名自己的江湖騙術,心虛卻是有的。但我很注意分寸,絕不會驚動老師和家長,漸漸地我倒也積攢了下了幾本書,最喜歡那一套橘色封皮的《意大利童話》。
我對故事的癮越來越大,跟著男王老師學跳舞,早把心操在了女王老師那成架的書上。三年級以后,認的字足夠我讀她那些沒有插圖的厚書了。每周上完課,還書借書成了慣例,女王老師對我很大方,我倒有些過意不去,破天荒朝姥姥要果仁巧克力,攢下來,還書時帶給女王老師,她反應很強烈,又是笑又是嘆的。
這些都要瞞著姥姥,姥姥不喜歡故事。不過對姥姥陽奉陰違的日子,終于要結束了。
一
母親離開時,鈞鎮變成了鈞州市,不到三歲的我,對這些變化還毫無概念。我上小學了,忽然發現新城區剛蓋好的樓房,外墻上都貼滿了雪白的窄瓷片,房檐則貼著深紅的瓷片,我們學校也是這樣。放學了,從包著一層鮮亮刺眼瓷片的新城區出來,穿過北關城門,就是灰撲撲的老城區了。
老城十字街口連著東西南北四條大街,僅剩的北關那點兒城墻和帶甕城的城門已經用鐵柵欄保護了起來,但門洞可以過車,城墻還可以爬。從寫著“北拱神京”的城門上往城里看,能看見北關大街上一片青灰色的磚瓦院落。
姥姥嫁進來時,那些院落還都是秦家的。秦家有七房,分過家的,各方各院地過日子。當時秦家各房的人大多還住在北大街上,幾十年,越來越多的外人混雜著住了進來,但我們的鄰居中,老親戚還很多。
姥姥曾經是六房的少奶奶,老親舊眷一直還叫她六奶奶。六房那院,大門上的漆剝盡了,黑黃的木頭還在壯心不已地炫耀著優良的材質,只有開關時才略帶悲涼地于門軸處瑟瑟地落下一些木屑。仰頭能看到門斗上生動依舊的雕花,流云百蝠,鹿嘴含花,桃之夭夭,喜鵲登枝……秦家各房的門頭都有這樣的木雕,明八仙刻的是人物,暗八仙刻的是法器,大朵的牡丹開在云頭笏板上是富貴如意……真能說得清這些名堂的人并不多,但姥姥說我還不會走路,在她懷里抱著,就能指著說得一清二楚。
大門里面,其實已經成了逼仄的巷子,早辨不出幾重幾進了,很多戶人家雜亂地擠在一起。我記事兒的時候,已經落實了房產政策,前院的房客都搬走了,姥姥只出租后院,且在通后院的過廳屋那兒壘起了一道墻,姥姥帶著我,這才又過起了獨門獨院的日子。
院里有三間正房,兩邊是廂房,還有廚房和放蜂窩煤和雜物的小屋,角上是廁所,定期會有拉糞的在我們院墻外,掀開水泥蓋板,清理糞坑。我很喜歡拉糞車的那頭栗色騾子,聽到它脖下的鈴鐺聲,我就會溜出門,靠著青灰的磚墻看它清亮的大眼睛,那大眼睛里有個穿水紅兜兜衫的小妞妞,無聲地跟它說著話。
正房的門一年四季掛著簾子,冬天是沉重的棉簾,簾腳兒墜著壓風的木板;春秋天是布簾子,我最喜歡那條湖藍色的布簾子,上面有雨絲一樣的線條;夏天是青竹簾子,竹篾子碧青,編竹篾子的線隔幾年要換,剛換那年掛上去,雪白的線一點一點在竹篾間露出來,像嵌著兩串珠子。
姥姥的日子過得講究,講究得無微不至,又不落痕跡。講究倒未必奢侈,一樣的黑疙瘩大頭菜,跟后院那些人從一個咸菜攤子上買回來的,姥姥切得細如發絲,點了香醋麻油,搭白米粥吃。絕不像他們,把黑疙瘩切成黑檁條,夾在饅頭里滿大街跑著大嚼。
講究的人必然是巧的,姥姥就是巧的。可惜我笨,姥姥恨起來,拿著尺子敲著我的手背,“白長了一雙水蔥似的手,捏根針跟拿根通條似的,笨死算了。”
我不知道還有沒有同齡人這樣度過童年。長大后才知道,我大概能歸入計劃生育成為國策后的第一代獨生子女,曾被報紙稱為“小公主”、“小皇帝”的一群人,我這個“公主”當得有點兒慘。不過倒是被姥姥的尺子敲打得學了些特殊的本事,比如說我會鎖扣眼,會縫被子,會把蝴蝶牽牛花、小貓釣魚這樣簡單的圖案描在的確良布上,用各色絲線繡成門簾或搭布。
我有記憶之后,生活里只有姥姥。母親的美麗,是北關大街上余韻悠長的傳說,特別是女人們,打量著我,嘴里說著記憶中母親的眉眼,沒來由會曖昧地笑,夸張地嘆氣,我覺得莫名其妙,卻又無緣無故地滿心羞惱。
小學二年級的暑假,一個陌生的阿姨,忽然到了姥姥家,說是帶我去見我母親。姥姥給我收拾了幾件衣服,煮了幾個雞蛋,放在我的書包里,我背著書包跟那阿姨上了火車。我在母親那兒一直呆到快開學,被另外一個陌生的阿姨領著,坐火車又回了鈞鎮。
北京,是個存在于新聞和故事里的地方,母親在那兒做什么?
我從北京回來后就被人堵著問,大人小孩兒都問。我就是抿嘴不說。女人們撥拉著我蓬蓬的粉色紗裙,再扯一扯襪口翻過來的奶油色蕾絲花邊,我被她們擺弄得兩腮發燙。
東院那個夏天總光著脊梁、總也找不下媳婦的牛兒,壞笑著氣我:“你媽傍上‘大款’了,不要你了!”
我噙了淚,咬牙說:“沒有!”
“那你媽怎么又把你打發回來了?你說呀!”牛兒在院門口堵著我問,很快會招來一群人,對我母親好奇的人實在不少。
我忍住了,什么也沒說,捎帶著把淚也給忍回去了。
出了趟遠門,我忽然長大了,心底能存住事兒了。
我在北京一直住在大姨家。很久之后,我才理清了大姨與我們之間曲里拐彎的親戚關系。這位大姨的母親,跟我姥姥是遠房表姊妹。母親最初就是去北京幫大姨的女兒帶孩子,帶得能上幼兒園了,又去別人家帶孩子做飯。北京似乎有很多人家需要保姆,母親總是能找到活兒。
我去了,母親也不能天天陪我,只有禮拜天才回來,帶我出去玩。我大多數日子呆在大姨家,那院子很深,擠擠扛扛住了很多人家,大姨大姨夫都退休了,院子里還有不少跟大姨一樣的老太太,大腔大嗓、熱火朝天地過著日子,我倒覺得比跟著姥姥有趣。大姨夫一直在練各種各樣的氣功,不練功的時候很和氣,笑瞇瞇領著我看回廊下的紅漆柱子,還有他養在石榴樹下的那缸墨色龍井。
我不肯說母親是保姆,并非以此為恥,我那時候很小,還不懂革命工作有高低貴賤之分,我不說只是因為我聽話,母親不讓說,姥姥也不讓說,我就不說。
有時候,被人逼著問急了,我就想給他們編故事。我隨口就能用一些聽來的或是看來的不相干的東西編成有趣的故事,就像有人手指一繞就能把柳條編成漂亮的筐子。母親曾帶我在一家醫院門口停下來買了一只赤豆冰棍兒,身后有人帶著敬畏的口氣說什么友好醫院;一個女人匆匆走進那醫院,身上帶著來蘇水和夜巴黎香水兒混合的味道——我記得母親當時抽了一下鼻子,說來蘇水和夜巴黎;我記得櫥窗里纖細的皮鞋后跟以及那皮鞋的牌子;時髦女人額頭上高聳入云的留海,后面爆炸開的卷發,都用一種叫摩絲的泡沫噴得硬邦邦的……差不多夠了,我用這些就可以編個讓他們張著嘴聽的故事——總也沒有機會,我稍微在外面逗留得長一些,姥姥就會找出來,一箭雙雕地把我和堵著問我的人,都罵上一頓。
母親帶給我的真實感覺,很復雜,回頭想想,八歲的我已經領略了百感交集。從出站口出來就見到了母親,她看著我掉淚,我卻有些呆——母親跟那個帶我坐火車的阿姨一樣陌生,只是更好看。那晚母親給我洗澡,一起上床睡下,我聞著她身上和我身上一樣的爽身粉香氣,忽然哭了,母親跟著也哭了。
過了一星期,母親再來大姨家時,拿著那條粉色的紗裙,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帶我去動物園。在動物園意外地碰到了一位胖阿姨,母親曾經在她家做過保姆,她見了我歡喜得拉著不丟手,跟母親說舞蹈學院、考試什么的,還很懂行地拿手比著量了我的胳膊腿兒。我的命運就被這次偶遇決定了。
母親對我說,要好好學習,好好學跳舞,我就能永遠跟她在一起了。我記得她說話時的表情,臉紅撲撲的,老是半垂著的眼睛也睜圓了,光閃閃亮晶晶的,說了一遍又一遍,唯恐我聽不懂,記不住。
那時候,各種少兒藝術培訓班還不像后來那么遍地開花,不過也已經有了,只是不大像樣。我把母親的信交給姥姥,姥姥就帶我去找母親的一個同學。那個同學是個小學老師,姓王,我叫她王老師。她愛人也姓王,早年畢業于國家舞蹈學院,如今在群藝館工作,我也叫他王老師。男王老師就是我的舞蹈啟蒙老師。
讀研的時候,一位教“西方藝術史”的老師說,我們至今還在用訓練雜技演員的方法培養舞蹈家,著實荒謬。我不知道他說的對不對,反正從一開始我就注定不會成為舞蹈家。舞蹈對我基本就意味著踢腿下腰折磨自己的身體,但我依然很刻苦地練功,因為母親說,好好學跳舞,我們就能永遠在一起。
無論是姥姥敲打下學的女兒手藝,還是群藝館王老師的舞蹈訓練,我都不喜歡,卻也習慣了。我同樣不喜歡、卻很習慣的,是一個人的夜晚。
從記事起,我就是一個人住。姥姥跟我分住正房的兩個房間,中間隔著堂屋。所以,除非偶爾有留宿的遠來親友,我童年的夜晚都是一個人度過的。總有東西,在我睡著之前,攪擾著我,讓我忍不住要流淚。春天秋天是院子那些花草的氣味,要是下雨還有雨的聲音和氣味,冬天卻是那份靜,尤其是雪后,仿佛天地都凍得不能呼吸了,我縮在被窩里,積雪下那些干枯的樹枝發出細微的開裂聲……這種時候,我的心突然會被一種東西抓住,揪扯,困意再也不來,難受得眼淚會流出來——我還太小,不知道那種感覺叫作寂寞……
最難熬的是夏天。放學后在院子里做作業,吃晚飯,偶爾姥姥心情好,吃完飯能讓我看一會兒“七巧板”,更多的時候,姥姥吃完飯就插好院門和房門,上床睡覺了。外面還是大亮的天光,后院那些小孩成群結隊地在街上呼嘯而過,嘰嘰嘎嘎地笑著,奔跑追逐——姥姥的話,野馬一樣。
我也想像野馬一樣,可惜不能。揣著野馬一樣念頭的我,當然不可能睡著,下了床,拖張草枕席坐在堂屋的青磚地上,歪著頭,看寬厚的木門和門檻之間的縫里透進來的明亮光線,想著有什么有趣的游戲,可以像野馬一樣奔跑,卻不會弄出任何聲響……那些有魔力的光線帶著奇跡降臨,我開始給自己編故事。
我編的故事常常讓自己流淚,淚水無聲無息地滾下來。我都不記得自己是什么時候學會這樣不發出聲音地哭,我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鼻息和呼吸,即使在落淚的時候,也能讓自己的聲音一如往常,應付姥姥突然的呼喚。
姥姥最看不慣誰動不動就淌眼抹淚的樣子,她那鄙夷不屑的表情,弄得我一直到現在,偶爾多愁善感那么一會兒,還有罪惡感和羞恥感。
不管自己編的還是別人編的,不管是快樂的還是悲哀的,只要是故事,我都喜歡。電視機我做不得主,只有去書里找故事,尋到每本書,能被我嚼得連渣兒都化了。我從來沒有向姥姥要求買故事書,甚至腦子里都沒出現過這種妄念,母親跟我們的聯系是一封封的信、匯款單和一袋袋漂亮的糖果。那些糖果被姥姥控制著,酌情發放給我,我從來不吃,替每樣糖果編一個來歷非凡的故事,然后把故事和糖果放在一起去換同學手中的故事書。那時候“忽悠”這個東北方言里的語匯還沒傳遍大江南北,我不知道該怎么命名自己的江湖騙術,心虛卻是有的。但我很注意分寸,絕不會驚動老師和家長,漸漸地我倒也積攢了下了幾本書,最喜歡那一套橘色封皮的《意大利童話》。
我對故事的癮越來越大,跟著男王老師學跳舞,早把心操在了女王老師那成架的書上。三年級以后,認的字足夠我讀她那些沒有插圖的厚書了。每周上完課,還書借書成了慣例,女王老師對我很大方,我倒有些過意不去,破天荒朝姥姥要果仁巧克力,攢下來,還書時帶給女王老師,她反應很強烈,又是笑又是嘆的。
這些都要瞞著姥姥,姥姥不喜歡故事。不過對姥姥陽奉陰違的日子,終于要結束了。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