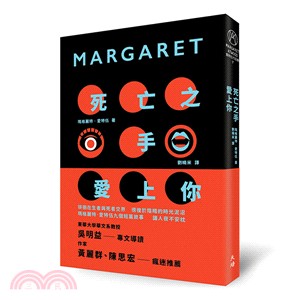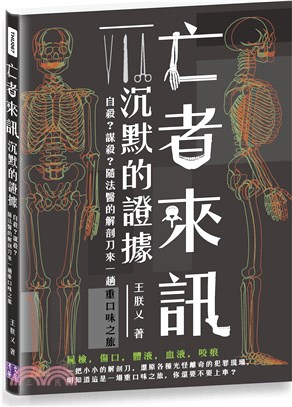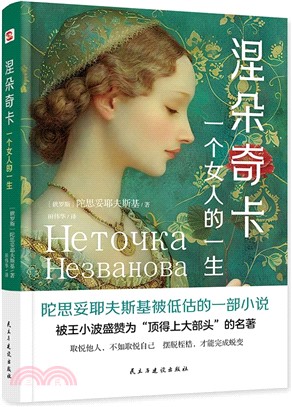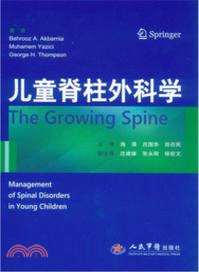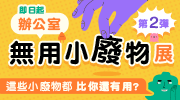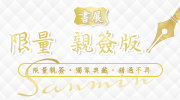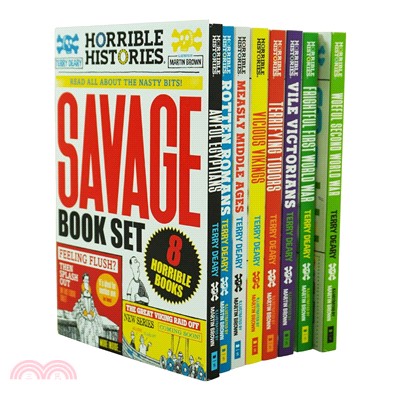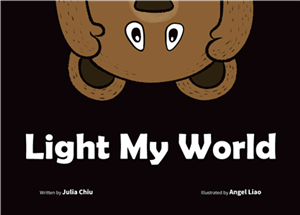死亡之手愛上你
商品資訊
系列名:愛特伍作品集
ISBN13:9789866385841
替代書名:STONE MATTRESS: NINE TALES
出版社:天培文化
作者:瑪格麗特.愛特伍
譯者:劉曉米
出版日:2016/04/01
裝訂/頁數:平裝/336頁
規格:21cm*14.8cm*1.5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前三篇<艾芬蘭>、<歸人>、<黑髮女士>可以視為連作,講述年老的奇幻女作家如何面對摯愛丈夫之死,以及像幽魂一樣纏繞不休的過往;而這一切,全都封印在琥珀般的文字裡。
<造化弄人>是畸形的女孩如何在眾人的眼光與言詞形塑之下,轉變成真正的怪物;
<冷凍脫水新郎>帶有黑色幽默;
<死亡之手愛上你>這篇談的則是愛的「永恆與執著」,讓人冷汗直冒;
<我夢見秦妮雅長了鮮亮的紅牙>是續寫《強盜新娘》中三名女子的心結;
<石墊>描述人在旅途中如何殺死另一個人,卻能安然脫身,恰是謀殺犯案最佳示範;
<燒死老廢物>寫老人之家住民受到攻擊,只因為他們的年齡……
在愛特伍筆下,恐怖的氛圍又會讓黑色幽默沖淡,但卻會讓故事盤據人的心裡久久不散。
作者簡介
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
一九三九年出生於渥太華,加拿大最傑出的小說家、詩人,同時也寫短篇故事、評論、劇本以及創作兒童文學。她已發表四十多部作品,翻譯超過三十五種語言,其中小說《盲眼刺客》獲頒二○○○年布克獎,《雙面葛蕾斯》獲頒加拿大季勒文學獎,並獲義大利最負盛名的蒙德羅文學獎(Premio Mondello)。二○○五年,她獲頒愛丁堡圖書節啟蒙獎(Edinburgh Book Festival Enlightenment),得獎理由是對世界文學與思想的傑出貢獻。二○○八年,瑪格麗特‧愛特伍獲頒西班牙艾斯杜里亞斯親王文學獎(Prince of Asturias Prize for Literature)。她目前住在多倫多。最新作品是《THE HEART GOES LAST》(二○一四)。
譯者簡介 劉曉米
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畢,現專職翻譯,譯有《父與子》、《白癡》、《預謀》、《怪遊義大利》、《藝術與設計入門》、《遇見自己》、《機巧的感覺》、《菲麗妲》等書。
名人/編輯推薦
媒體讚譽:
強而有力……機智風趣而且屢屢辛辣,《死亡之手愛上你》對於在生活中,我們選擇去愛或者傷害的對象極感興趣──而且在愛特伍的世界裡,這兩種行為一直是種選擇,後果我們終將自行承受。──《紐約時報書評》
強而有力……非比尋常……寫實和荒誕,遊戲和嚴肅異常,在各方面都取得極佳平衡。──《衛報》
聰敏機智……愛特伍基本上是寫純文學小說,不著痕跡地繞著嚴肅主題打轉,卻自通俗類型小說借來樂趣,從科幻到恐怖。──《泰晤士報文學增刊》
扣人心弦……驚奇連連……愛特伍以輕巧的筆觸闡明沈重的主題,不僅對自然物事有深刻理解,並對血肉之軀的試煉與磨難提出洞見。──《觀察家週報》
充滿機智、風格和洞見的上乘之作。──《O,歐普拉雜誌》
充滿慧黠的幽默和通俗小說刺激的系列。──《每日電訊報》
本短篇故事集充滿一種可愛的厚顏,對於正義與價值概念的主觀性,擁有全知觀點……機智、詭異、嬉皮笑臉的不敬,有點冷血,卻充滿真知灼見。。──《獨立報》
不拘一格、有趣、活潑生動、驚世駭俗、美麗,而且教人打心底被逗樂。──《波士頓環球報》
純粹、簡單和令人震驚……討人喜歡、難以捉摸,才華橫溢。 ──《舊金山紀事報》
此系列故事出奇地教人心神不寧、興奮、而且立刻喧鬧地笑開懷。它成功擄獲人們的芳心:神話歷久不衰,而本書中的故事正有那同樣的質地。它們永恆、難忘,而且就是那麼有趣。──《芝加哥論壇報》
愛特伍的]特長在於製造驚奇和其光芒萬丈、才氣縱橫的語言掌控能力……《死亡之手愛上你》不僅展現了作家最精鍊的才華,也讓人得以窺見這位在幕後發聲的女人。
──《多倫多環球郵報》
在兩性的互動上,使點小壞的風趣反芻,尖酸卻精闢……藉由《死亡之手愛上你》,愛特伍巧妙融合她的文學根底,出色打造出一名可愛逗趣的人類喜劇觀察家。
──《多倫多星報》
引人入勝……令人印象深刻……《死亡之手愛上你》攪得人夜不安枕,但在這本優雅的集子裡,不安人人皆有,表現各顯不同。──《影音俱樂部》
時髦、辛辣,帶點惡意的幽默……機智、悲憫、精準,愛特伍誘使讀者陷入沈思。──《邁阿密先驅報》
(這些)故事擁有尖刻的機智和令人眩暈的偏差……伴隨著愛特伍小說對人內心深處的探究與冷眼洞察。
──《明尼亞波利斯星報》
序
如果最後你看得夠久
吳明益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系教授
2013年諾貝爾頒獎之前,在臺灣愛特伍的知名度肯定比孟若來得高。從許多方面來看,孟若和愛特伍都是不同命運與風格的作家:孟若出身藍領家庭(父親經商失敗成為工人),愛特伍則出身學者家庭(父親是昆蟲學家);孟若擅長短篇,而愛特伍以長篇奠定她的文學地位;孟若低調沉靜,愛特伍則常在媒體受訪,並且參與許多政治與文化活動,甚至有人認為她應該角逐多倫多市長;孟若的文學語言與技巧靜水流深,數十年來以類似的筆法滴水穿石,愛特伍則是不可思議的多面手,你可以想像到的文學類型她都嘗試過,既寫過童書,也出版過畫冊。
不過,要追隨這兩位作家成功的途徑都是不容易的,因為不論是鑿出藏在深山裡的礦,或扶植一片森林都極為艱難,她們為此付出了一生。
孟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愛特伍立刻表達祝賀之意,雖然不少愛特伍迷都知道,依照諾貝爾考量地區性的慣例,那意味著她很難在短時間內獲獎,甚至可能永遠錯過。
愛特伍的作品非常多元繁複,但若說詩影響她的寫作根柢,長篇小說則是創作主力,當不致有太大誤差。我們不妨把她的長篇小說作品分成兩條河道,說不定可以看出愛特伍數十年來寫作的「大意圖」。
第一條河道是從早期的《女祭司》(Lady Oracle, 1976)、《夢斷長夜》(Bodily Harm, 1981),到愛特伍開始在臺灣建立知名度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1985),以及後來的《強盜新娘》(The Robber Bride, 1993)、《雙面葛蕾斯》(Alias Grace, 1996)與《盲眼刺客》(The Blind Assassin, 2000)。這系列作品雖然寫作方式與敘事技巧各有不同,但都可以視為是以「女性為主體」發聲的作品。飽受心靈凌虐,從而創造自我身分的女性(《女祭司》)、面對共同情敵的女性(《強盜新娘》)、涉及謀殺的女性(《雙面葛蕾斯》)、收容並愛上逃亡者的女性(《盲眼刺客》)……學術圈以女性意識檢視愛特伍的作品其來有自。
二是所謂的「末世三部曲」:包括了《末世男女》(Oryx and Crake, 2003)、《洪荒年代》(The Year of the Flood, 2009)與《瘋狂亞當》(MaddAddam, 2013)。這三部曲融合獨白、詩歌、日誌、講道、對話與夾敘夾議等形式,描繪未來世界,寫出了末世的蒼涼、希望與正義,關涉了災難、基因改造、宗教等複雜議題。
我們可以把這兩條河道視為愛特伍寫作的「大河」(愛特伍詩意的文字則是構成水質的要件),可以發現它們都是由數本小說,彷彿支流般支持起來的。這些支流與支流間,又總是存在著或隱或顯的聯繫。
簡單地來說,愛特伍讓這些水流彼此呼應、聯繫,來自於幾種文學手法。最顯著的是後設書寫。比方說,《盲眼刺客》裡還有一本《盲眼刺客》,《女祭司》裡還有一本《女祭司》。這些小說裡的小說,往往也在整個故事中,成為書寫行為的隱喻。
其二是愛特伍自己的小說與小說之間的關聯。「末世三部曲」當然是最好的例子,但也有更特殊的例子。像是《女祭司》最後,寫作羅曼史的女主角瓊,決意開始寫一本科幻小說。長期讀者當會發現,那本科幻小說很可能就是後來的《使女的故事》。
最後一個特點是,愛特伍喜歡在小說裡討論書寫,討論文學的意義,羅曼史小說、科幻小說如何挑戰嚴肅小說,人如何在小說裡隱身、報復、療傷或創造一個可以遁逃的新世界。說愛特伍的小說隱有她對文學的宣示(誓),我想並不為過。
如果你讀愛特伍的短篇小說,你將也會體會到類似的閱讀樂趣。〈艾芬蘭〉、〈歸人〉、〈黑髮女士〉是同一個故事不同敘事者的詮釋,它就像過往愛特伍專擅的一樣,敘事者往往不只敘說當下,而是帶出一整個自我人生,它細緻精巧,人物的對白與心思都殘酷且銳利。
另一方面,短篇小說有時像是長篇小說的先聲,有時則是餘韻。比方〈我夢見秦妮雅長了鮮亮的紅牙〉就延續自《強盜新娘》。
愛特伍依然在這些短篇裡託付她的文學見解,〈艾芬蘭〉系列當然顯而易見,而〈死亡之手愛上你〉在我讀來並不是恐怖故事,而是喚起了老讀者對《盲眼刺客》裡那隻書寫之手的記憶。那篇曾被文藝青年伙伴鄙視的,被視為可有可無的小說,隨著時間成了「國際恐怖小說經典」,而作者在小說裡諷刺的友誼,卻也存在著諒解的可能性。
書寫是用手撫觸他人心口的工具,是以小說最後伊琳娜說傑克「很害怕」,因為怕真實人生的對象若「伸出手」,去「碰觸作者的心口」;若讀者靠得太近、太貼近作者,那麼作者的「靈性本我」或者反而可能會消失掉。
而不知道為什麼,除了旅程導致的遊戲之作〈石墊〉外(創作淵源在後記中愛特伍有自述),我隱隱覺得,〈造化弄人〉、〈冷凍脫水的新郎〉或是〈燒死老廢物〉,都有可能藏著愛特伍那不會公布的「未來書寫」其中的片段。
同樣在出版短篇小說集《死亡之手愛上你》(Stone Mattress)的這一年,來自蘇格蘭藝術家派特森(Katie Paterson)做了一個「未來圖書館計畫」,邀請一批作家創作,然後將他們交出的作品封存百年後出版,第一位邀請的作家正是愛特伍。
為了防止屆時紙本書已不存在,這個計畫甚至在圖書館旁種植了一千棵挪威雲杉,以為造紙準備,並且也保存了一台印刷機。2114年起,後繼的計畫將開始伐木造紙,出版這批封存百年的作品,除了造紙外,雲杉也將用來建造保存這批作品的保存室。
愛特伍選的作品稱為「Scribbler Moon」,她選擇不讓任何人預先讀到它。這個計畫對作家最大的考驗是:百年後這部小說能否仍熠熠生輝?能不能對彼時的時代仍有所反應?能不能打動未來的讀者?
一如我們所理解的,時間是對作品最大的考驗,許多文學作品裡提及時間,也常意謂著作家陷入「創作生命/真實生命」難分難解的掙扎。在《死亡之手愛上你》裡,角色是作家的篇章,「敘事時間」多數拉得很長,主角都經歷了從年輕造夢、彼此撕裂,直到年華老去的過程。當他們回首時往往發現自己過了多重人生──自己的,以及小說人物的。
已步入老年的愛特伍,在這本短篇小說集裡,似乎正在把她長年思考的諸多問題「老年化」。故事裡的作家已是他人眼中的「研究材料」或「老廢物」了。每天照鏡子(重讀自己作品)時看到自己(以及自己作品)的衰老,這可不是「科幻小說」。愛特伍既已書寫過「人類的末世」,復又勇敢地把末世放到眼前。作家能寫作他人的末世,怎麼寫自己的末世呢?
在那本集結於劍橋大學「燕卜蓀講座」(William Empson)成書的《與死者協商》裡,愛特伍講了許多她的寫作理念。包括她認為寫作就像是「前去死者國度,將某個已死之人帶回人世──這是一種人心深處的渴望,但也被視為極大的禁忌。但寫作可以帶來某種生命。」(2004221)我不禁想,那「死者」也包括作家自己嗎?
而另一本在加拿大「梅西公民講座」(Massey Lectures)集結成的《債與償》裡,愛特伍既談的是現代社會的經濟體系,談的也是文學。她說在耶穌所講的閃語系亞蘭文(Aramaic),「債」與「罪」為同一字,因此,可以譯為「免我們的債/罪。」甚至譯成「我們有罪的債」。(200948)在她看來,小說寫的多半就是「欠債(犯下罪)/償還」的故事。「無記憶,無債。換言之,無故事,無債。」(200982)我在課堂上,曾舉許多世界知名故事來分析,愕然的是,一部世界文學史,還真是「債與償」的大全集。
回顧半生,讀者當可知道愛特伍和孟若還有一個絕大的不同處,那就是她是一個樂於曝光、追求新事物的行動者。她常為個人的政治、宗教、性別信念發表意見、參與運動。她既是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的活躍份子,也是PEN(Poets, Essayists, Novelists)加拿大分會的會長(這個組織常協助世界各地受政治壓迫的作家),還是鳥會的資深賞鳥人。她在非虛構作品裡批判了滴流經濟理論(trickle-down economics)、階級以及第一世界對其他世界的壓迫,乃至於宗教基本教義派的悲哀。詩作裡則洋溢著對加拿大自然、對生命的愛與欣慕。
在文學的日常,她樂於使用Twitter與她廣布世界的讀者溝通,也曾嘗試在線上為讀者「遠距簽名」。
愛特伍在作品中已明示暗示自己追求的是成為一個「大寫的作者」、「稱職的挖墓人」,但她的小說始終不離通俗作家要求的趣味、感染力與可讀性(讀這本小說你當可感受到這一點)。她不像孟若忠貞、堅定,似乎(我不敢肯定)義無反顧地朝向她的小說聖殿走去,愛特伍總像是怕到死者之地後,遺漏了什麼、少帶了什麼回來。她常徘徊在生者與死者交界之地,嗯,此刻對愛特伍的年紀來說,也不再是個遙遠的隱喻了。
我希望這本短篇小說成為還不認識愛特伍的讀者的開始(已經是愛特伍讀者的,自當不會錯過),逆向去展讀她的每一部作品,回到她那還嚮往著寫作,還不清楚要寫些什麼的青春時光。你當會發現,她是一個每一本書都值得留在你書架上的作家。而如果你讀得夠久、夠深、夠專注,你將會看到一個作家如何從猶疑、憤怒、尋路、編織故事到願意與記憶和解的時間歷程:一個小寫的掘墓人,成為大寫作家的過程。
正如愛特伍所寫的一首詩〈這是一張我的照片〉的最後一段:
(照片攝於
我溺死之後第二天
我在湖裡,在照片
中央,幾乎就在湖面下
很難判斷正確
位置,或說得清
我的大小尺寸──
水
讓光線扭曲變形
但如果最後你看得夠久
最後
你一定能看到我)(陳育虹譯)
目次
目錄
艾芬蘭
歸人
黑髮女士
造化弄人
冷凍脫水的新郎
我夢見秦妮雅長了鮮亮的紅牙
死亡之手愛上你
石墊
燒死老廢物
致謝辭
書摘/試閱
內文試閱
「死亡之手愛上你」開始時只是個笑話。或者更像一個試膽遊戲。他本該更小心的,但事實上,那陣子他大麻吸太多,劣酒也喝太多,因此無法完全負責。他不應該扛起責任的,他不應該被那些天殺的條款綁死。就是那玩意兒銬住了他的腳踝:那只合約。
而且他永遠擺脫不了那合約,因為上頭沒有任何最終履行截止日。他應該加上一個有效期限條款,就像牛奶紙盒,像優格杯,像美乃滋罐,但當時他哪懂得簽合約?當時他才二十二歲。
他一直缺錢。
錢這麼少。真是筆爛交易。他被剝削了。他們三人怎能那樣佔他的便宜?雖然他們拒絕承認其中的不公平。他們只會引述那該死的合約,和上頭那些無可抵賴的簽名,包括他自己的,然後他就得打落牙和血吞,乖乖被壓榨。起先他拒絕付他們錢,直到伊琳娜搬出個律師,現在他們三人都有律師,就像狗會互染跳蚤那樣。伊琳娜應該看在他們曾經多親密的份上,對他額外施恩,但沒有,伊琳娜有顆像柏油般的黑心,而且一年比一年乾硬,一年比一年龜裂。金錢毀了她。
他的錢,多虧有他,伊琳娜和其他兩人才請得起他們的律師。也是最頂尖的律師,和他自己的一樣優秀;倒不是他想l叫囂、對罵,讓律師們互鬥。是因為委託人老淪為兇殘土狼的早餐:他們像一大群雪貂、老鼠,或者食人魚般地對你蠶食鯨吞,直到你變成一塊碎布大小,只剩一條肌腱,一片腳指甲。
因此他非掏出這筆錢不可,數十年如一日;因為,承蒙他們公正地指出,在法庭上,他是絕對站不住腳的。因為他在那只卑劣至極的合約上簽了名。他簽了名,用熾熱的鮮血。
簽合約時,四人都還是學生。倒也沒真窮到那地步,否則他們也無法接受所謂的高等教育,但他們還是跑去修補凍脹的路面,或者煎漢堡,以賺取極微薄的工資,不然就是在便宜、氣味令人想吐的小酒吧裡做援交,起碼伊琳娜會這麼做;雖然並非要靠救濟的貧民,但他們手上還是沒有太多零錢。他們靠暑期打工收入與親戚勉為其難的借貸過活,而伊琳娜則是靠一筆少得可憐的獎學金。
起初他們是在十分錢一杯啤酒的酒館裡認識的,裡頭總聚著一夥人,喜歡相互揶揄、發牢騷和吹牛—當然不是伊琳娜,她從來不做這種事。她更像幼童軍的女訓導,會在其餘的人全喝茫而不記得自己的零錢放哪兒,或者太狡猾而沒帶半毛錢時,把帳給付了,但之後她倒不曾收不回她的錢。他們四人發現彼此都需要節省住宿開銷,便合租了間房子,就在大學附近。
那是六O年代早期的事,那時候,倘若你是個學生,想在那一帶租房子,就只能能是一間狹窄,有尖屋頂、三層樓、夏熱冬涼、老舊,充滿尿騷味、剝落的壁紙、變形的地板、哐噹響的暖氣,鼠滿為患、蟑螂橫行的維多利亞式紅磚排屋。當時那些房子未經修復,還不是貴死人不償命的古蹟建築,門口也沒被蠢蛋釘上具歷史意義的匾額,那些蠢蛋除了四處溜達著替索價過高,裝潢得花稍、上流的房地產釘牌匾之外,沒其他更好的事可幹。
他自己的房子—那份有欠考慮的合約中所指涉的房子—上頭也有塊匾—驚訝吧!—寫著他本人曾經住在那兒。他知道他曾經住在那兒,根本不需提醒。他不需要唸出自己的名字,傑克‧戴斯,1963-64,彷彿他只活了那該死的一年,下頭還有小印刷字體繼續敘說著,「享譽國際的恐怖經典,死亡之手愛上你,就是在這間屋子裡寫出來的。」
我又不是智障!我當然知道這一切!他想對著那塊上了藍白搪瓷的橢圓匾額大吼。他應該忘了它,他應該盡可能地把這整件事忘得一乾二淨,但他做不到,因為它就拴在他的腿上。每回他進城來參加什麼電影節、文學節、漫畫節、怪物節或其他類似的活動,就忍不住要來窺看幾眼。一方面可以提醒他,他簽下那份合約的愚蠢;另一方面,當看到享譽國際的恐怖經典幾個字的時候,又可悲地感到身心舒爽。他對這塊匾太過著迷,畢竟那是對他一生主要成就的尊崇。雖說那成就也沒什麼了不起。
或許他的墓碑上就會這麼寫著:死亡之手愛上你,享譽國際的恐怖經典。或許會有畫著歌德眼妝的性感小不點女粉絲,帶著凋萎的玫瑰和發白的雞骨頭前來向他致敬。她們的脖子上有著像科學怪人一樣的縫線刺青,手腕上也有虛線,標示出被砍斷的地方。他甚至還沒死,她們就已經把這類的東西寄給他了。
有時候她們會在他出席活動的周遭埋伏,像是一些期望他像機器般呆板解釋「類型」的內在價值的座談會,或者由他的鉅著所繁殖出的各種電影的回顧展。她們裹在扯破的壽衣裡,臉塗成噁心的綠色,還帶著信封,裡頭裝有她們的裸體照,或是脖子上吊著黑繩、舌頭長長伸出的照片,再不就是小塑膠袋裡裝著她們的陰毛,和她們戴著吸血鬼牙齒親自上陣演出的吹簫鉅片,又或者以上齊備。那真是太前衛了,上述的事他一樣也無法接受。但他怎能抗拒其他模式的恭維,他如何能夠?
雖然那一直是種冒險,一種對他自我的挑戰。要是他在床上的表現變差了呢?或者更正確地說—因為這些女孩就像一種令人感到中度不適的刺激物—在地板上,靠在牆上,或者被繩子綁在椅子上時?要是她們說,「我以為你會不同」,同時調整她們的皮內衣,套回她們的蜘蛛網襪,並且在浴室的鏡子裡,修補她們用膠水黏上的化膿傷口?這也不是沒發生過,而且隨著歲月使他凋萎,習慣使他陳腐之後,更常發生。
「你弄壞了我的傷口」—她們甚至會說出這樣的話。更糟的是,她們都直接說,毫無奚落之興。噘嘴、非難、嗤之以鼻。所以最好還是和這類女孩保持距離,讓她們從遠方崇拜他墮落的撒旦力量就好。無論如何,這些女孩一代比一代年輕,因此每逢她們期待他說些什麼時,都很難展開對話。只要從她們嘴裡跑出的不是舌頭,泰半時間他都不懂那是什麼。她們有全新的詞彙,有些時候,他甚至覺得自己已經被埋在地底一百年。
誰能料到他會獲得此種古怪的成功?當年每個認識他的人,包括他自己,都認為他是個浪蕩子。死亡之手愛上你一定是那種靈感之作,從某個俗不可耐、滿腦淫穢的骯髒繆思取得的靈感;因為他一氣呵成地把書寫完,完全沒有平常的起頭,中止和拖延,把紙揉成一團,拋進廢紙簍裡,時而發作的瞌睡與絕望,這些通常會阻止他完成任何事情的現象全沒出現。他就只是坐下,把故事打出來,一天八九或者十頁,在一台老舊的雷明頓打字機上,他從一家當鋪裡弄來的,多奇怪,他竟還記得打字機,它們會卡住的按鍵、糾纏起來的色帶,和做備份時,弄得到處髒兮兮的複寫紙。大概只花了他三星期,至多一個月。
當然他不知道這故事會變成享譽國際的恐怖經典。他不會穿著內衣跑下兩截樓梯,在廚房裡大喊,「我剛寫了一部享譽國際的恐怖經典!」要是他這麼做,坐在佛麥卡塑膠貼皮桌前的另外三人也只會大聲笑他。他們正喝著即溶咖啡,吃著伊琳娜常替他們煮的淡撇撇的燉菜。她用了一大堆的米、麵條、洋蔥蘑菇湯罐和鮪魚罐,因為這些食材很便宜但卻有營養。伊琳娜很重視營養。把錢花在刀口上是她的專長。
他們四人會把每週的飯錢存進晚餐公基金裡頭,那是一個豬形的餅乾罐,伊琳娜可以少出點,因為她負責烹飪。烹飪、採購、支付諸如水電費等家用帳單都是伊琳娜負責,她喜歡做這些事。過去的女人確實喜歡扮演那類的角色,而男人也喜歡此種分工。不可否認地,有人在耳邊大驚小怪地叨念他應該多吃點,他自己也很樂在其中。交易是其他三人,包括他,應該負責洗碗,雖然他不能說這事有那麼常發生,至少在他的情況如此。
煮飯時伊琳娜都會穿上圍裙。圍裙上還有個派的貼布縫。他不得不承認,穿上圍裙的她很漂亮,部分是因為圍裙會在腰間繫緊,因此你可以清楚看出她有腰身。平時為了保暖,她的腰身總藏在一層層的厚毛衣或針織衣物下。那些深灰,黑色的衣服,簡直像個在俗修女。
有腰身意味著她也有明顯的屁股和胸部,因而傑克無法自制地想像她沒穿那些厚實耐穿、觸感粗糙的衣服,甚至沒穿圍裙時的模樣。而且把頭髮鬆開,她的金髮總是在腦後捲成個髻。她看起來甘美又營養,豐滿而柔順;順從地接納你,就像一只肉做的熱水瓶,包在粉紅色天鵝絨裡。她可以玩弄他於股掌,她也的確玩弄了他;他覺得她有顆柔軟的心,一顆像羽絨枕頭般的心。他把她理想化了,真是個蠢蛋。
無論如何,倘若他走進那間飄著麵和鮪魚香的廚房,說他剛寫出一部享譽國際的恐怖經典,其他三人絕對只會笑他,因為那時他們完全不把他當回事,即使現在,也沒把他當回事。
傑克住在頂樓。閣樓裡。那是最糟的地方。夏天烤死,冬天凍死。煙會竄上來:煮飯的油煙,從底下樓層飄上來的臭襪子味,還有馬桶的惡臭—全都往上飄送。對於冷熱和臭氣他無法還擊,唯一能做的只有繞著房間用力跺腳;但那只會吵到伊琳娜,她就住在他下頭,而他不想惹惱她,因為他想鑽進她的內衣裡。
這些內衣是黑色的,沒出多久,便剛好有個機會讓他發現。當時的他認為黑色內衣很性感,一種庸俗的性感,像是警察雜誌裡的風格—可以在骯髒的五毛商店裡買到。他對真實生活中的內褲顏色不太熟悉,只知道白色和粉紅色,那是他那個年代高中生常穿的顏色。雖然他一直努力窺視路邊停放車輛的車窗,但那教人洩氣的黑暗,從未讓他好生看清那些內褲。他事後才知道伊琳娜選擇黑色內衣不是為了挑逗,純粹出於實用考量:她的黑色是一種精打細算的黑,沒有蕾絲或任何十字繡花或若隱若現的躲貓貓特色,而且選黑色不是為了襯膚色,只是為了不顯髒,可以減省洗滌費用。
和伊琳娜做那襠事,就像是在和一個鬆餅烤盤模做一般,他之後總拿這話來自嘲,不過那是在後續事件歪扭了他的回溯觀點,並讓她穿上金鐘罩之後。
伊琳娜並非單獨住在二樓。傑夫瑞也住那裡,傑克為此妒火中燒:傑夫瑞那雙穿著臭羊毛襪的噁心髒腳,可以多輕鬆地滑過走廊,在有害身心的慾火焚燒下,流淌著下作的口水,來到伊琳娜門口,就在傑克在他的閣樓小洞裡睡死了的時候,神不知鬼不覺。不過傑夫瑞的房間在用焦油紙額外搭建、隔熱很差並藏污納垢的廚房那頭,那廚房直接從屋後往外延伸,因此傑夫瑞的頭上沒有天花板可供跺腳。
羅德同樣地也在踱步範圍外,而且他,也遭傑克懷疑,對伊琳娜別有所圖。他的房間在一樓,在原本應該是餐廳的地方。他們把有毛玻璃窗格的雙扇門給釘死,那道門原先通往曾是起居室的地方,如今卻變得像鴉片煙窟,雖然他們沒有任何鴉片,只有幾個霉臭的褐紫坐墊,一條顏色像狗嘔吐液體的棕色地毯,縫隙裡塞滿洋芋片和堅果碎屑;還有一張壞掉的安樂椅,散發著老水手港甜得令人作嘔的臭味,那是愛飲廉價果酒的酒鬼們的首選,譏諷的是,竟由來訪的哲學系學生所飲,因為不值幾文錢。
那個起居室是他們懶散地聚在一起殺時間和辦派對的地方,雖然這地方沒大到可以辦派對,因此來參加的人都會散落至狹窄的走廊,樓上,甚至後面的廚房裡。派對參加者會自動分成吸大麻的和喝酒的兩組—吸大麻的還算不上是嬉皮,因為嬉皮尚未誕生,但已顯露端倪,一個頹廢、自覺的類披頭族,成天和爵士演奏家們瞎混,用他們邊緣化的逾越方式逐漸崛起;而在這樣的時刻,他,傑克‧戴斯,如今已刻上匾額上的人,享譽國際的恐怖經典的作者,一位受尊敬的作家—在這樣的時刻,很高興自己的房間位在頂樓,遠離互毆的人群,與酒臭、菸臭、大麻臭,以及偶見的嘔吐物臭,因為人們不懂適可而止。
有一個他自的己房間,一個在頂樓的房間,他可以提供暫時的避難所給一些可愛、疲倦、厭世、世故、穿著黑色高領毛衣、畫著黑色眼線,可能被他引誘上樓,走進他滿地報紙的香閨、躺上他鋪著印度風格床罩的床的女孩,他讓她們滿懷期待地聽他胡吹寫作的技巧,創造過程的痛苦與掙扎,對誠實高潔品格的需要,熱賣的誘惑,和抵抗這些誘惑的自制力,諸如此類。為了避免這樣一個女孩有可能認為他太過炫耀、自大、和自以為是,在瞎蓋的同時,不忘添加些許自我嘲弄的意味。不過他的確是炫耀、自大和以為是,因為在那樣的年紀,你不這樣做,就無法在早晨爬起床,並且在接下來醒著的十二小時內,繼續相信自己那貌似真實的潛力。
然而事實上,他從未真的成功引誘到這樣一個女孩,倘若真有的話,可能也會破壞他和伊琳娜之間的機會,後者已隱約透露她或許會撞見。伊琳娜自己並不喝酒或者吸大麻,雖然她會去現場清理善後,並在心裡記下誰對誰做了什麼,然後到了早上,每件事都依然記得清清楚楚。她從來不會對這類的事情多加著墨,她為人謹慎,但你可以從中聽出她迴避了什麼。
在死亡之手愛上你出版,並獲得如此程度的讚譽之後—不,不是讚譽,因為那種書不會獲得任何你可以稱之為讚譽的東西,至少那個時候不會;要很久以後,一旦黃色書刊和類型小說建立立足之地,而寫作的正當性也搶佔灘頭堡—到書被拍成電影—這類的引誘對他才變成容易得多。一旦他享有名氣,至少成為一名商業作家,一名平裝書大賣、書封還有凸起的燙金字體的商業作家。他再也無法以藝術家的身份來泡妞;不過喜歡恐怖故事的女孩很多,或者據說很多,姑且算是補償。就連在那個年代,在哥德風潮流行之前,她們也喜歡。或許這類的故事能提醒她們內在的陰暗面。也或許她們只是希望他能幫她們混進電影圈。
哦,傑克,傑克,看著鏡中的眼袋,用手指觸摸腦後那塊已經稀疏的頭皮,用力縮肚子,雖然他沒辦法撐太久,他對自己說, 你的樣子真是糟透了,你真是個大蠢蛋,你是如此孤單。哦,傑克很靈巧,傑克很敏捷,因為你曾經可靠的燭台,和你那即席胡謅的本事(譯註:改寫自十九世紀時創作的一首童謠,Jack be nimble。原文有跳過燭台一句。跳過燭台時,若能不弄熄燭火,將是好兆頭。)
)。你曾經如此精神抖擻,你曾經如此信任他人。你曾經如此年輕。
合約這件事就是在一種令人惱怒的情況下拉開序幕的。那是近三月底的一天,草坪上堆滿不停滲水的灰色融雪,空氣濕冷,人也心浮氣躁。正是午餐時間。傑克的三名室友坐在有塑膠貼皮的廚房餐桌前—紅色的,還有淺藍灰的螺旋花紋和鉻黃的桌腳—把殘羹剩飯掃個精光,伊琳娜的典型作風,她常把前一晚的剩菜當成午餐,因為她不喜歡浪費食物。他自己則睡過頭,不足為怪:前晚又舉行了派對,卻是一個非常令人討厭又乏味的派對,整個派對的話題都繞著尼采和卡繆打轉—這都得感謝傑夫瑞,他喜歡長篇大論地聊高深莫測的外國作家,這對他,傑克‧戴斯來說,可就太不利了,因為這兩人他連一點邊都沾不上。雖然他也可以還算精彩地扯上一段卡夫卡—卡夫卡曾寫過令人捧腹的故事,描述一個變成甲蟲的傢伙,無論如何,那都是他大多數早晨清醒時所擁有的感覺。某個虐待狂在派對前一晚帶來一燒瓶實驗室裡的酒精,並把酒精倒進葡萄汁和伏特加之中,而他,傑克‧戴斯,深陷枯燥的文學競技中不可自拔,灌了太多黃湯而吐到癱。這個,再加上他抽的不知是什麼鬼,很可能是稀釋的胯下濕疹藥粉。
因此他完全沒心情參與在吃麵條和鮪魚組成的剩菜時,由伊琳娜劈頭且無情地切入的話題。
「你已經三個月沒繳房租了,」她說。甚至在他有機會喝他的即溶咖啡之前。
「老天,」他說,「看看我,我的手在發抖耶。我昨晚喝得爛醉!」她為何就不能更體貼些、鼓勵些,看在天殺的份上?就算是一句觀察力敏銳的批評也讓人好過些,例如,「你臉色糟透了。」
「別轉移話題,」伊琳娜說。「你很清楚,我們其餘的人被迫替你分攤你的房租;否則我們全都會被趕走。不過不能一直這樣下去。不是你找到某個方式付錢,就是你得搬走。我們需要把你的房間租給某個能確實繳出房租的人。」
傑克突然趴倒在桌上,「我知道,我知道,」他說。「老天。我很抱歉。我會設法補救,我只是需要多一點時間。」
「做什麼的時間?」傑夫瑞露出不信的微笑譏諷地說。「是絕對時間,或者相對時間?內在的或者可測量的?歐幾里德還是康德的?」對他來說,現在就開始玩起吹毛求疵的初階哲學文字遊戲會不會太早了點。他那個樣子還真混蛋。
「有人有阿斯匹靈嗎?」傑克說。很弱的一步棋,卻是他唯一能走的一步。他確實頭痛得厲害。伊琳娜起身去替他拿止痛藥。她就是忍不住想扮演褓姆。
「多一點的時間是多久?」羅德說,邊從他棕綠色的小筆記本裡抬起頭,他總在那本筆記本裡做他的數學演算:他是他們聯合企業的簿記員。
「你已經要求了好幾週的更多時間,」伊琳娜說。「事實上,好幾個月。」她放下兩顆阿斯匹靈和一杯水。「加了一顆我可舒適發泡錠,」她補上一句。
「我的小說,」傑克說,他以前不是沒四處張揚地用過此藉口。「我需要時間,我真的……我快寫完了。」這不是真的。事實上,他被卡在第三章。他已經把角色設定好:四個人—四個荷爾蒙溢腦的迷人學生—住在一間三層樓,有尖頂的磚造維多利亞排屋裡,就在大學附近,他們經常用一些神秘的語言談論他們的靈魂和通姦,但他卻無法繼續往下寫,因為他不知道他們還可能再做些什麼。「我會找份工作,」他有氣無力地說。
「像是什麼?」心腸如黑曜石的伊琳娜說。「有薑汁汽水,如果你想喝的話。」
「或許你可以把百科全書賣掉,」羅德說,三人大笑。任誰都知道賣百科全書會是軟弱、無能、孤注一擲的最後手段:此外,想到他,傑克‧戴斯會真的賣任何東西給任何人,就令他們覺得好笑。他們眼中的他是個連流浪狗見了都閃的蠢蛋和倒霉鬼,因為他們可以在他身上聞到失敗的味道,就像貓屎一樣酸臭。最近他們三人甚至不讓他擦拭碗盤,因為他太常讓碗盤掉到地上砸破。他是故意那麼做的,好讓他們覺得他很笨拙而少分攤些家務,現在卻自食惡果。
「你何不賣出你小說的持份?」羅德說。他是念經濟學的;他把他多餘的零錢投進股票市場,成果不賴,他就是那樣支付他自己那份該死的房租,這讓他在談到錢的話題時,總顯得不可一世和討人厭,從那時開始,他都一直如此,不曾改變。
「好吧,我跟,」傑克說。當時完全是作戲,他們三人在遷就他—給他留一點餘地,假裝承認他是有才華的,替他開闢一條財政正道,但願只是理論上的一條。那是他們事後的說法:他們串通好推他一把,誘使他相信他們對他有信心,丟給他一些憑證。然後他或許可以真的抬起屁股去做點什麼,倒不是他們真期待此事成真。此舉竟能奏效,而且成效還如此驚人並非他們的錯。
合約的內容是羅德擬定的。四個月的房租—傑克積欠的三個月,外加馬上將付的一個月,以他尚未完成的小說收益折抵,按持份均分為四,他們,包括傑克在內,一人可拿四分之一。倘若這合約對傑克本人一點好處都沒有,將無法產生積極的動力。什麼都拿不到的情況下,他可能會興味索然,無法完成作品,羅德說。他是「經濟人」的信徒。對於最後一點,他兀自竊笑,因為他壓根不認為傑克會完成它。
倘若傑克沒有宿醉得如此嚴重,他會簽下這樣一紙合約嗎?可能會。他不想被趕出去。他不想露宿街頭,或者更糟,回到他父母位在唐米爾斯的康樂室裡,被他母親不停地扭絞雙手和燉牛肉,以及父親嘖嘖聲不斷的訓斥給圍剿。因此他同意每項條款,並且簽名,然後寬心地大呼一口氣,在伊琳娜的催促下,吃掉兩叉子的麵條燉菜,因為他的胃裡最好墊點東西,再上樓,睡個午覺。但是之後,他得寫那該死的玩意兒。
那四個住在維多利亞排屋裡的學生角色沒救了。他們顯然拒絕把他們已經坐麻的屁股從廚房那幾把三手椅子上挪開,他們的肛門現在正像同一隻章魚不同觸角上的吸盤,死巴在椅子上,就算他在他們的腳底點火也沒有用。他必須試試別的東西,某種很不一樣的東西;而且得快,因為寫這小說—任何小說—已經變成一件攸關尊嚴的事。他無法容許傑夫瑞和羅德繼續奚落他;他再也無法忍受伊琳娜用那雙可愛的藍眼睛同情又不屑地看著他。
拜託拜託拜託,他對著那盛滿油煙的冰冷空氣祈禱!快來幫我!任何東西,隨便什麼都好!任何能賣的東西!
根本是和魔鬼交易的作法。
突然間,他的眼前閃現微光,就像出現了一朵會發出磷光的毒蕈,他看見手的字樣,完整浮現:他唯一需要做的只是盡量把這些字寫下來,或者後來他上談話性節目時是如此說。這故事打哪兒冒出來的?死亡之手愛上你?誰知道?出於破釜沈舟的決心。出於床舖底下。出於童年的夢魘。比較有可能出自恐怖的黑白漫畫書,他十二歲時,常從街角的藥妝店裡順手偷來看:分離、乾涸、會自己行動的身體各部位,是那些漫畫的標準特徵。
得獎作品
獲獎紀錄:
★二○一五年加拿大推理界最高榮譽亞瑟‧艾利斯獎 (Arthur Ellis Award)最佳短篇小說獎
名家好評:
鼓動著調侃的機智雙翼,遨翔於陰暗的恐怖泥沼……看看這些故事……如同八枝透心涼的砒霜冰棒,然後是以炭疽病調味的火烤冰淇淋,全以無懈可擊的風格和泰然自若奉上,好好享用!──娥蘇拉‧勒瑰恩,《金融時報》
出人意表、強而有力……我喜歡這些古怪、尖銳和瘋狂的故事。──梅格‧沃莉茲,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