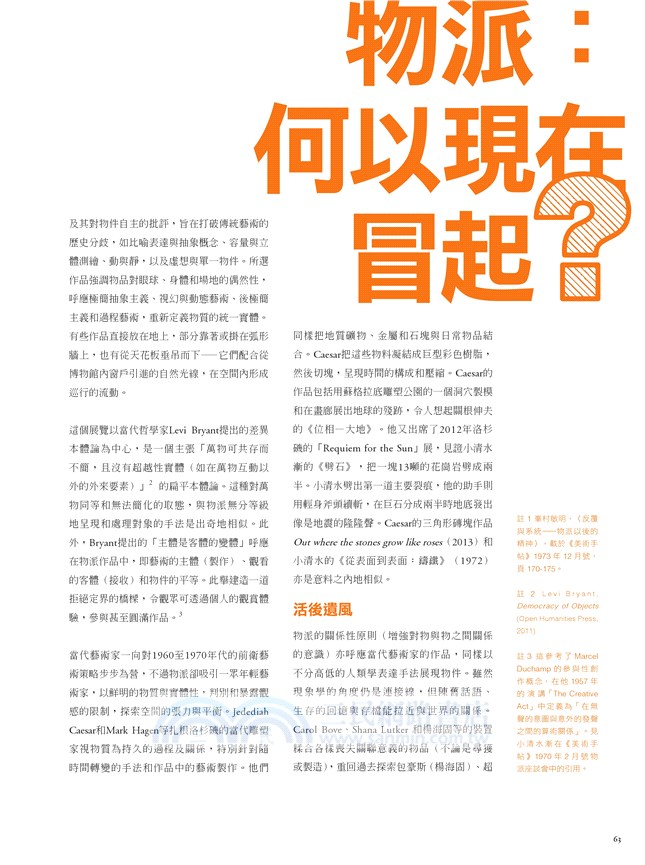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編者的話
TOPICS: Fashion/ Design
Feature 1 亞洲藝術風起時:具體派、物派、單色畫
李禹煥訪談 訪問:松井綠
單色畫
朴栖甫訪談 訪問:Taro Nettleton
河鍾賢訪談 訪問:Taro Nettleton
Artist Files
Essay:現代化的另類例子 文:Sam Bardaouil & Till Fellrath
物派
菅木志雄訪談 訪問:森啟輔
Artist Files
Essay:物派的來生——此時此代 文:吉竹美香
具體派
再解讀<跨過被封閉的圓環> 文:成相肇
Artist Files
Essay:具體派:現代主義去中心化 文:蔡宇鳴
具體派、物派、單色畫全新概覽圖
Dialogue:歷史是怎樣寫成的 奇廷泫X手塚美和子
Meet the Collectors:田口弘
鄭志剛——結合藝術及商業的文化創業家
ARTIST:Jim Shaw
ARTIST INTERVIEW:Pierre Huyghe
ARTIST FILE:Eddie Peake/ 關小/ 千葉正也/ Korakrit Arunanondchai
Feature 2 「Don’t Follow the Wind」 攝影:大森克己 文:椹木野衣
村上隆的「Superflat Collection」
MANGA:奠邊府戰歌 原作:西島大介
ART WORLD CATALYSTS:Artsy 文:Kyle Chakya
ISSUE:溫柔地,顛覆常規——紀念水木茂 文:Anselm Franke
Contributor Biographies
書摘/試閱
Interview 1
李禹煥
觸動、對話、共鳴
訪問:松井綠
「藝術,唯有考慮自我與他人之間的整體關係。」
李禹煥的創作貫穿日韓,以與他者的交會為題。在此訪談中他將呈現其作品的主導概念,令我們明白他何以成為現今物派與單色畫運動最引人注目的藝術家之一。
「相遇」的藝術與後現代化
——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期間,您為了對抗當時發生的文化危機——現代人文主義解體、物化益發嚴重、當代藝術意念具體化——而摸索著能超越這些情況的全新藝術宗旨。您在著作《尋找相遇》(2000)中構思和提出了新的藝術宗旨「相遇」(出会い),那是一個與現象世界的雙向關係的範式,人類從對外界的響應中直觀自身的獨特性;從與外界的關聯中增強他們的想像力與感官。請說說您的想法和當時的情況。
李禹煥:我從韓國搬到日本,是我能不依賴傳統智慧或認知去重新思考的最大機遇。我本在鄉郊長大,當途經首爾搬到日本時,我像是墮進人群和文明之中,身體感到各種矛盾,同時帶來強烈的迷惑和嚮往。這個人經歷變成一種靈感。「相遇」一字是來自說明當時我獨自在異國文化中掙扎時的想法。
在1960年代全共鬥(全學共鬥會議)的運動中,我發現批評和指出矛盾均不能解決問題,革命大體只是推翻前人建立的制度和累積的智慧。在遠距離觀察和考慮各種可行性時,我漸漸看見了與他人「互為彼此」(お互い様)的相處之道。理性分析無力再概括當代文明的多樣性,故我認為藝術唯有避免單方面的理解和創作,儘管自我未必能夠與他人合而為一,也應從自我與他人之間的衝突和互動中,考慮兩者所形成的整體關係。
——您用「媒介」一詞去形容藝術對「相遇」的催化作用,即「把自然而然作自然而然的挪移」是藝術的表達手法。您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李:這是最難懂的一點,亦很容易引起誤解。不過,我對「自然而然」(あるがまま)是既成概念和常識的信念,至今一直不變。若用專有名詞解釋的話,它與佛洛依德的「無意識」互相呼應。若我們把這些日常常識和習慣「存而不論」(epoché),然後用自己的方法重新整理,便會構成一種再現和藝術行為。早前與高松次郎傾談時,他認為我把「自然而然」說成是存在於某處的狀態,但我腦中的「自然而然」卻是指社會共識、常識和既成概念,而非在談論自然或一種理想。而以片假名書寫的「自然而然」(アルガママ)就是這意味著這思想可隨藝術家或個人的意思變改,以自己的方式詮釋和「重新呈現」現實。
——為了解釋「相遇」是什麼概念,您引用梅洛龐蒂(Mauric Merleau-Ponty)、海德格(Marti Heidegger)和巴舍拉Gasto Bachelar)等哲學家的思想,又提及「相遇」的個人經驗,如一向討人嫌的水窪卻能令您停下腳步,欣賞它的閃閃生光。您似是已把「相遇」的概念內化成自身感受的基本原則。
李:正是如此。個人經驗對我而言還是最關鍵的。在1960年代,我乘兼職之便拜訪過一所報館的輪轉印刷機室,所看到的畫面跟一般「機械缺乏人性」的想法大相逕庭。員工全心全意地拭抹機器,染得滿身墨黑,做成一個人與機器融為一體、「互為彼此」的狀態。那一刻我不是被工作的艱辛所震懾,反是因為人們用鼻音哼著歌拭抹機器時的手臂及身體動作,和閃閃發亮的機器相映成趣的畫面而覺得炫目。日常生活中時會出現和這種經驗相似的時刻,在再普通不過的事物中偶然有所發現,令人豁然開朗,深受感動,勾起無數回憶,非常興奮。我忽地意識到這種情感,是源自「見證」一件事時,頓悟「觀看」和「被看」的經歷能渾然成為一個和諧的整體。
——您提出了數個媒介方法,用以肯定「相遇」的一剎作為有意識的體驗。在《尋找相遇》中,您特別探討了「舉止」(仕草)和「持續的舉止」的方法。您可以闡述這些概念嗎?
李:我認為「舉止」近似是一種姿勢。這可以說是把當時流行的「事件」和其後的「演出」這些詞彙拉至更接近我的風格。在一個層面上,舉止可以是完全沒意義的肢體表達;而在一個制度中,它有時也可以是一個不祥或具威脅性的符號。因此當一個舉止是「事件」的原因而非即興動作時,它便與藝術或藝術品掛鈎。
——在1970年代初至1980年代的系列畫作《從線》和《從點》中,一線或一點也有多個方面,包括色系、痕跡、動向或過程,也看到用同一筆觸重複繪畫的契機。在這些畫作中是不是也有「舉止」的元素?
李:我想我在1970年代的作品中暗藏了演出。當時我經常看到觀眾站在我的畫作前指手劃腳,似是在追蹤線條。建構動作基礎的舉止亦藏在其中,這是我的作品予人的印象。這對我而言非常重要,因為我認為繪畫是一種與行為性密不可分的表達。
——重複同一動作的「持續舉止」對您的藝術創作重要嗎?
李:是的,重複的動作就像一種訓練或修行,其被動性尤其重要。一個有意識、有目的的舉動會包含能動性,但沒有被動性的話,只是重複同一個沒有目的的動作,行為不會有進展。套用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說法,那是「純粹持續」。例如西西佛斯反覆把巨石推到山頂,然後看著它滾下山。在這個簡單的重複中,行為性組成一種結構。同樣地,藝術家重複同一動作或製作,本身是一種勞動,而因為藝術家是人,所以他想改善事情和改良手法的意圖亦是其中一部分,結果這個重複動作的勞動本質亦自成一種表達。正正因為重複動作顯現出一種「持續」的被動性,動作的倫理和結構便因此變得明顯。最終,透過重複動作的過程理解一個意義不明的動作,而這種「領悟」亦帶有社會意義。
繪畫、雕塑、動作與餘白
——在1970年代末,當歐美唾棄平面的獨立性後,日本藝評人和藝術家接手將平面理論化。《美術手帖》舉辦了兩場座談會,即「當平面變成繪畫」(1977年4月號)和您也有份參與的「朝向繪畫的本身」(1978年2月號),該兩輪會議對當時的日本藝術界有莫大影響。意見各異的藝評人均一致認為您對發現新平面的可能性貢獻良多。您對此有何感覺?
李:藝評人嘗試基於物質和半透明狀態重塑平面的理論,但我重點強調的是繪畫這個人類行為對畫的重要性,至今仍同此理。實際上,儘管在畫畫前定好周全的計劃,但動工時總有些偏離計劃的細節或因不同情況而需要微調,如我的身體狀態或當時的氣氛。這種偏離是因為動作和存在的多樣化。
——您在著作《餘白的藝術》的其中一篇〈關於無限〉中寫道,「自我」會因與他人交流時的污染和過濾而失去,並轉化成另一種自我。您所說的偏離又是否與此有關呢?
李:對,它們是有關的。不否定在每個場合產生的巧合元素,會形成一種雙重性,讓自我在對外和跟他人的交融磨合中被過濾。
——您的「餘白」概念是否出自這種想法呢?
李:我自1970年代初已使用「餘白」一詞,但直至1990年代以後我才明白它的真正意義,並經常使用。
而且,這個「餘白」的概念與東方思考的「餘白」無關,因為後者指的是風景畫中的留白,但我的卻是源自個人經歷。在1970年代晚期,我為提升畫作的完美度,不斷從肉體上和精神上鞭策自己,結果弄垮了自己的健康,好一段時間也不能再畫,故1980年代的畫變得支離破碎。不過,在留白或刻意把事物打散的過程中,畫作的結構變得零碎,塗過與未塗過的部分互相配合,帶來不少樂趣。我的意識不斷奔馳,思索把這個組合進一步擴展的可能性。這當然是我在雕塑方面經歷過的。
——您是指「關係項」的雕塑系列嗎?
李:正是。即使你攜同一些東西到畫廊或美術館,它們也不會發揮原本的呈現。我有過數次經歷,體驗一整個空間如何能因只添加數件物品而提高密度。我也開始在繪畫時有同樣感覺。當我觸碰某處(把畫筆點在上面)時,我碰著和沒碰的地方便會展開對話。這種對話可以以不同形式呈現,如反抗、拒絕和通信,總之是一種震盪,而我稱之為「餘白現象」。當有人敲鐘時,鐘、敲鐘人和空間缺一不可。當鐘在一個空間響起時,空間透過在空中迴盪的鏗鏘聲響擴充,恍如某種力的擴張。這就是「餘白」對我的意義。
畫的超越性與無限性
——您在1978年的座談會中說:「畫不是某個物件的狀態,而是一種與繪畫行為密不可分的超越性的場面。」請問您口中的「超越性」是什麼意思?
李:其實,我在1978年真正想說的要比「行為性」更進一步。確切來說,畫畫全是關於超越性的問題。經過極簡主義藝術的階段,在形式上發展到盡頭的繪畫,因為與人的視覺體驗和思考方式扯上關係,怎樣也無法只視之為「畫的本身」。換言之,做人必然會想像。把繪畫還原為最低限度可辨認的事物,證明了這一點。若畫於未來能繼續是話題的話,我認為那是因為畫本身不能撇清的超越性。即使藝評人說幻想與氣質不再存在,人依然不能脫離這種與想像/狂想息息相關的超越性,我認為那正正是渴求畫和畫畫的理由。
——那在您近期作品中也清晰可見。《對話》用礦物顏料在空白畫布的中央一筆過地畫出單個形狀,該形狀由層層遞進的顏色組成,模糊輪廓與色彩的分界,而漸變的色調亦令人留意到各種光譜的表達,令形狀似有不同角度,或浮游在白面上,或從中冒出。當形狀的主色調是銀色時,會引人聯想起月光或鋼鐵;紅色時便是紅土、黎明或落霞,引發無限想像。
李:正是。無人能對聯想和回憶免疫。正因如此,一旦在觀看時察覺到意義,那我們便不可能只視畫為畫。當我們賞畫時,畫中最微細的超越性也能從各方面激發我們的想像。不單是畫本身有轉變,觀者對畫作的印象亦會隨燈光、觀看角度、與空間關係、當時的心理和生理狀態等因素的轉變而不斷變改。我認為畫的無限可能性源自我們回應這些轉變的能力。
物派的共性與多樣化
——您在2001年的文章〈物派:藉由內與外的相遇〉中讚揚物派,視之為「解放出與人溝通的空間」,「從觀賞的具體化和封閉意義中釋放」,「在視覺中掀起與人相遇的運動」。您認為讓海外觀眾理解這一點重要嗎?
李:每當在歐洲或美國講解這個時,我會建議去想想如何把製作與非製作連結。物派的破格是源於它提出限制製作,轉為思考用非製作去表達。貧窮藝術(Arte Povera)和「Supports/Surfaces」等其他藝術派系也有類似傾向,但物派塑造一個統一的表述空間,信手拈來身邊的東西,並「暫且」漠不經心地混合。我為我們開拓了一個全新的表達空間而感到驕傲。雖然存在各種問題,但今後仍要不斷說明物派的重要性。我認為對物派的基本評價是「製造機會去探討非製作及與其有關的表達手法」。
——物派似是以一個大的共通點為本,歡迎各種不同角度。您套用梅洛龐蒂與保羅克利(Paul Klee)對藝術的定義,認為它「並非呈現表象世界,而是為平常看不見的東西賦予實體」,「琢磨對生命的感知,從而對它有更深入的認識。」這是一個極為現象學的看法。另一方面,物派藝術家菅木志雄竭力排斥「創作」的假象,把個別物品與其他物件交疊同放,營造不自然的狀態,強調物件的獨特性。
李:你指出了菅木志雄的作品與我的不同之處。菅自1970年代起的作品是出奇地輕快,極富臨場及臨時感。我會把自己的作品發揮至無可再插手的程度,而他則沒有對作品的整理太在意。所以,即使他的作品胡亂堆放在一起,也能呈現有趣的演出。我雖談及非製作,但仍無可避免地在作品中隱約流露出自己的意願,他卻會用盡一切辦法去掩蓋。他的表達手法令事物看似自然而然。我們的作品當然有交集之處,但方向卻不盡相同。
——我們可以把這些差別歸因於物派的眾多藝術做法嗎?
李:可以。我們各自有不同的定位,但物派藝術家的共同點包括盡量減少修飾,以及臨場的、臨時的創作。
——我想這種「臨時」的感覺非常重要,而您曾用「暫且」一詞,這些特色是否與即興創作和空間的威力有關?
李:是的。每一個空間的特色都必須巧妙地利用。現代藝術是由理性主導的藝術,但物派卻採納一直被忽略的元素,如晦澀不明的事物或感覺。不論是巧合或出於情感,我們透過身體的介入,製造一個令人可以檢視曾被摒棄的事物的空間。
新開始和超越之地
——可以談談你的新畫《對話》嗎?
李:我想用已畫出來的東西作為催化劑,結合沒有畫出來的東西去吸引觀眾,製造一個統一的繪畫空間,在此引發震盪。要達到這個目的,不但需要顏色和形式,更要一股強勁的動力。這股動力不是靠猛力塗繪或加強物質性可得,而是混集各種因素,包括繪畫時的節奏和呼吸、投入其中的精力和畫布的張力等。我想創造一個呈現超越性的空間,設計出如何用最少的元素去換取最大的效果。而且,那並非一開始便灌輸某種特定意義,而是以其他形式展開,如一個會引發思考的活動。我感覺到自己現在的畫作和雕塑,終於站在我認可的全新創意的起跑線。「超越」的意思是超越藝術中的具體化。賞畫的舉動必然會有幻想同行。我所追求的表達方式,是在已畫出來的與沒畫出來的關係中,超越描繪的對象,否定藝術的具體化。這作品尚未完成,又跟展覽會場或掛畫的場所掛鈎,算是一種「未完成的完成」。總之,這畫作能促進人意識到與該地的關係,當靜靜置放在一個大房中,該空間便能活轉過來,與日本花道如出一轍。對我而言,這正是藝術的作用。
Essay 1
現代化的另類例子
文:Sam Bardaouil ﹠Till Fellrath
策展人Sam Bardaouil和Till Fellrath細說單色畫這個當代舉足輕重的藝術派系,分析造就它興起的社會和藝術發展背景,逐一解說圍繞這個1970年代韓國「極簡抽象派」的流言。
過去兩年,藝術市場對單色畫明顯興趣大增。那亦稱韓國單色畫,源自多名在1970年代冒起、鮮有連繫的韓國藝術家。在2014年2月,我們在紐約Alexander Grey Associates策辦了一個名為「Overcoming the Modern」的單色畫展覽。隨後,奇廷泫在洛杉磯的Blum & Poe策辦「From All Sides: Tansaekhwa on Abstraction」。同年10月,Tina Kim Gallery在倫敦的弗里茲藝術博覽會展出多位單色畫家的作品,行內對單色畫趨之若鶩。在2015年,Tina Kim聯同首爾的大型畫廊Kukje Gallery與布魯塞爾的伯格山基金會合作,在第56屆威尼斯雙年展舉辦以單色畫為題的平行展。同年,紐約貝浩登推出兩個重點展覽,包括5至7月的朴栖甫個人展和12月展出丁昌燮的作品。與此同時,Tina Kim Gallery也展出多幅河鍾賢的作品。各個展覽令公眾對單色畫這個韓國藝術運動有了全面認識。
五十年後的成名
單色畫獲得的注意霎時大增,卻並非毫無預兆。過去十年間也有不少博物館舉辦有關此運動的展覽,為這股熱潮鋪路。例子包括泰特利物浦美術館在1992年的「Working with Nature: Traditional Thought in Contemporary Art from Korea」和後來1998年在法國尼斯Musée des Arts Asiatiques 的「Painters of Silence」展覽。自此,數名現今被視為代表此派的藝術家便相繼冒起,當中以李禹煥為首。然而直至2012年,「單色畫」一詞才在策展人尹晉燮的文章〈心靈的風景〉中出現,載於首爾國立現代美術館「韓國單色畫」展覽的刊物中。雖然此後沒有任何主要博物館舉辦以單色畫為題的展覽,但2013年有多個介紹其他運動的重要展覽,例如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MoMA)探索日本物派的「Tokyo 1955-1970: A New Avant-Garde」展,及古根漢美術館探索日本具體派的「Gutai: Splendid Playground」展。這兩個展覽清晰說明具體派和物派何以成形,亦間接突顯單色畫未如另兩派運動的鮮明有序,缺乏明確目標和一個特定的美學定位。此分別源自一個環環相扣的過程:多名同代藝術家意識到自己與歷史衝突、地理、藝術系譜和最重要的自我忠誠糾纏不清,經過反覆的哲理、政治及藝術的洽談和討論所得。
我們早在2001年藉著李禹煥在波恩現代藝術美術館展出的作品,首次接觸到與這場運動有關的那一代藝術家。自此,透過李禹煥和超過十年到韓國的定期到訪,我們發掘了更多其他藝術家的作品,如丁昌燮、朴栖甫、李東熀、鄭相和、河鍾賢等,不勝枚舉。很明顯的,他們的畫作被誤用以滿足藝術史的分類及較近期的市場推銷和品牌期望,更甚於深究每位藝術家的獨特之處,故對他們習畫存在明顯的錯誤解讀。奇廷泫指出:「單色畫很大程度是為了滿足各種目的而存在,當中大部分極少涉及抽象主義甚至繪畫本身的抽象技術。其實,各有特色的畫家都有同一堅持,就是集中鑽研他們所熟悉的各類繪畫元素,如符號、線條、框架、表面和空間等。」
我們認為,單色畫對油畫和抽象主義的另類理解及對創作的堅持,正正是令整代藝術史家、學者和策展人著迷的原因,因為他們一直在尋找現代化的多個可能性,以挑戰或豐富現代化的歷史。大約在過去十年間,他們挑戰以歐洲角度為中心的現代主義及以其為準則的藝術創作觀念,漸漸引起藝術史家和策展人的興趣。如何令藝術史全球化?如何重整核心與邊緣的對立?如何令非西方藝術家能超越斷章取義的老掉牙比較而獲得肯定?這些問題不停打斷反思現代多樣化的討論。單色畫可算是正中要害,因為它是作為一種「另類」現代化的呈現,建基於組合和選擇,以及同時牽涉本土與國際的考慮。不論是在本地環境,還是面對其他同期理論和形式的顧慮及發展,單色畫舉足輕重,在於它反映現代主義如何在地理和概念上均能多線發展。為進一步闡述這個論點,我們必先略為瞭解單色畫的緣起和它代表的意義。
抽象藝術的抗衡
大部分在1960及1970年代冒起的單色畫家都曾見證軍事獨裁者朴正熙的鐵腕管治。他一方面推動資本主義、資助較富裕但受政治抑壓的中產階級;另一方面,他消除反對聲音,鎮壓在經濟發展操控中付出代價而不滿的窮困低下階層。這個年輕的共和國在概念框架底下進行了數個藝術運動,一再強調這些燃眉的民生和政治議題,同時這亦主宰他們採用的形式及風格,例如單色畫。韓國當時正從日本的殖民統治中復原,而與大部分後殖民國家一樣,極其重要的議題包括身份認同、真實性、歷史後遺和個人定位,當然視覺藝術亦是其一。
單色畫家就是生於這種時勢,而這個時期的政治和民生境況亦一直被用以理解和詮釋他們的作品。例如數位藝術史家認為,作品的抽象手法是故意反對被國家強行簡化成政治宣傳工具的具象風格。1967年3月,李禹煥在東京佐藤畫廊的《佐藤畫廊月報》中發表〈自相矛盾的美學〉一文,批評民族身份與文化創作的合併。文章既將李禹煥年輕時與自身民族背景的拉鋸表露無遺,亦顯示他擅於探討「韓國人與藝術家的身份對峙」的命題。李禹煥在歸屬感、民族身份和藝術革新中的掙扎亦代表很多同代人當時的憂慮。本地文化特色與西方現代化的爭論引領藝術表達手法邁向新出路,亦為後來的單色畫或韓國單色畫寫下定義。
現代主義的本土對立
除了圍繞政治關聯及目的的激烈討論,單色畫家亦面對有關其藝術根源和作者權的爭論。當中大部分藝術家曾到巴黎、紐約和東京逗留,有些更如李禹煥般永久移民。西方和本地藝術家的抽象主義在1950年代中期開始漸趨一致,而經常往返本國的藝術家更是置身其中。丁昌燮、朴栖甫、鄭相和及河鍾賢等藝術家亦充分意會到當時最得令的藝術潮流,包括1950年代的美國抽象表現主義、在巴黎地位舉足輕重的無形式藝術(art informel)、1960年代的色域繪畫(color-field painting)或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稱之為後繪畫性抽象,還有由馬丁(Agnes Martin)、曼佐尼(Piero Manzoni)和祈因(Yves Klein)代表的極簡抽象派,以及意大利的貧窮藝術。
西方現代主義思想認為藝術家會自我犧牲地抽離社會領域,並以自由藝術尋求難以觸摸的超然現實。相反,韓國在1960及1970年代的現代主義卻被多個議題糾纏,如民族主義、堅持或破舊、傳統與革新的角力等。為打破這些二元對立,藝術家在非韓國傳統的平面畫布上採用本地材料,如韓紙、傳統米紙、墨水和其他物料。「本土對完美美學的追求令理想實體化,以及重整與社會和大自然的聯繫」,而韓國單色畫家則是銳意透過形式上的選擇,模糊本地美學定位和「西方」哲學思想及實踐的界線。
對單色畫家而言,現代化絕不等同與西方藝術創作模式混為一談,亦不是信奉某種針對藝術創作不同理念和形式的獨特取態的普遍主義。綜合以上認知,近期單色畫熱潮的最基本因素大概可歸因於觀點與角度:若歐洲現代主義以「他者」的文化產物湧現(而紛亂的殖民背景始終如一)去解釋圖像及風格的復興,難道單色畫就不能和很多其他地方一樣,是一個有相似談論和合理化行為的例子嗎?換而言之,若歐洲現代主義對美學的改編和重整被譽為前衛,那為何在歐洲之外的類似討論總會被安上複製論或民族主義的框架?這個關鍵問題反映對現代主義的各路地域文化模式的日益關注,亦需留待未來在考慮如何訴說、書寫和展示單色畫和所謂的「他者」現代化的新思路或框架時繼續探討。
單色畫正處於各風格的十字路口,以及政治及社會氣氛緊張的環境,故利用抽象表現作為組合及革新的手段。他們亦因此成功塑造一門獨特的視覺語言,以形式和材料蓋過政治意圖。這些殿堂級作品超越政治和社會衝突,向觀眾展示永恒且真正普世的視覺語言。它們的美能跨過所有文化藩籬,直接觸動我們的視覺和美學感悟,這亦解釋了為何它們可流行不退。
Essay 2
物派的來生——此時此代
文:吉竹美香
物派見證有形物質的自然存在,促進實體與實體之間的互動以瓦解物質的架構,同時重整觀眾自己的感官——物派的宗旨又如何在現今當代藝術延伸呢?
自1980年代起,多個重要群展把物派帶出日本,修正主義的藝術史家和策展人為歐美傳統敍述技巧加入另類現代化元素,重新燃起對此運動的興趣。物派打破日與西、左與右等世界系統與藝評人秉持的二元思維,為觀感哲學的基調拓闊第三空間,承載傳統日本哲學和當代思想,從而重寫或摒棄具體化的二元對立。例如「Other Primary Structures」(猶太博物館,2014)和「Prima Materia」(威尼斯海關大樓博物館,2013)是近期與歐美形式不同的跨國歷史整合的展覽。前者環觀來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及東歐等世界各地的重要雕塑家,是延伸自1966年於同一博物館展出英美極簡抽象主義雕塑的歷史性展覽「Primary Structures」。
全新的關係
物派呼應當下以經驗和演出為主的創作熱潮,與1960和1970年代初期的後極簡抽象藝術遙遙相對。這股熱潮源自對藝術基礎從實體論轉型至現象學的反思。李禹煥與菅木志雄的理論建基於歐洲和東方哲學,反思我們對周邊世界的理解和感性。其中一個宗旨就是,在糅合未被加工的天然和工業物料時,能讓事物彰顯自己的結構,重點不是放在物品本身,而是在物質、感知和空間之間的關聯和觸覺。作品的說事都是建立於個別的觀賞時間和空間之上,與表演有異曲同工之妙。每個新發現或僅此一次的偶遇(一次性)均是獨一無二,造就物派作品的「此時此刻」,令人嚮往。
我在2013年時開始為美國赫什霍恩博物館二三樓的動態空間構思展覽,以「Speculative Forms」為題展出約七十件雕塑作品。展覽源自「思辨現實論」哲學(實體論對現實論和唯物主義的新詮釋),探討我們身體對物件和世界的體驗。展覽亦考慮到戰後雕塑藝術發展及其對物件自主的批評,旨在打破傳統藝術的歷史分歧,如比喻表達與抽象概念、容量與立體測繪、動與靜,以及虛想與單一物件。所選作品強調物品對眼球、身體和場地的偶然性,呼應極簡抽象主義、視幻與動態藝術、後極簡主義和過程藝術,重新定義物質的統一實體。有些作品直接放在地上,部分靠著或掛在弧形牆上,也有從天花板垂吊而下──它們配合從博物館內窗戶引進的自然光線,在空間內形成巡行的流動。
這個展覽以當代哲學家Levi Bryant提出的差異本體論為中心,是一個主張「萬物可共存而不簡,且沒有超越性實體(如在萬物互動以外的外來要素)」的扁平本體論。這種對萬物同等和無法簡化的取態,與物派無分等級地呈現和處理對象的手法是出奇地相似。此外,Bryant提出的「主體是客體的變體」呼應在物派作品中,即藝術的主體(製作)、觀看的客體(接收)和物件的平等。此舉建造一道拒絕定界的橋樑,令觀眾可透過個人的觀賞體驗,參與甚至圓滿作品。
當代藝術家一向對1960至1970年代的前衛藝術策略步步為營,不過物派卻吸引一眾年輕藝術家,以鮮明的物質與實體性,判別和暴露觀感的限制,探索空間的張力與平衡。Jedediah Caesar和Mark Hagen等扎根洛杉磯的當代雕塑家視物質為持久的過程及關係,特別針對隨時間轉變的手法和作品中的藝術製作。他們同樣把地質礦物、金屬和石塊與日常物品結合。Caesar把這些物料凝結成巨型彩色樹脂,然後切塊,呈現時間的構成和壓縮。Caesar的作品包括用蘇格拉底雕塑公園的一個洞穴製模和在畫廊展出地球的殘跡,令人想起關根伸夫的《位相—大地》。他又出席了2012年洛杉磯的「Requiem for the Sun」展,見證小清水漸的《劈石》,把一塊13噸的花崗岩劈成兩半。小清水劈出第一道主要裂痕,他的助手則用輕身斧頭續斬,在巨石分成兩半時地底發出像是地震的隆隆聲。Caesar的三角形磚塊作品Out where the stones grow like roses(2013)和小清水的《從表面到表面:鑄鐵》(1972)亦是意料之內地相似。
活後遺風
物派的關係性原則(增強對物與物之間關係的意識)亦呼應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同樣以不分高低的人類學表達手法展現物件。雖然現象學的角度仍是連接線,但陳舊話語、生存的回憶與存檔能拉近與世界的關係。Carol Bove、Shana Lutker和楊海固等的裝置糅合各樣喪失關聯意義的物品(不論是尋獲或製造),重回過去探索包豪斯(楊海固)、超現實主義(Lutker)和1960及1970年代的烏托邦意識形態(Bove)。裝置別出心裁地把物品排在平台上、從天花板垂下或靠在牆上,所營造的平衡狀態和物派如出一轍。Bove的Equinox(2014)把生鏽鐵柱、大石、銅格子、孔雀羽毛和浮木作幾何而有機的配搭。楊海固的裝置在多感官環境下重整晾碗架、電線和百葉簾等家用物品,百葉簾尤其能突出她所指的「觀感的滲透力」,與李禹煥視作品為彰顯存在的「結構」非常相似。Lutker形容自己的物品陳列為「過渡物」(transitional object),那主體與客體的交流定位,令人進一步意識到個人體驗與假定歷史的張力如何改變作品的意義和詮釋。藝術家不用改變物品,反要尋找日常生活中轉瞬即逝的干預,推翻先入為主的官能和語象,捕捉這些用語開始失去認可性的一刻。
最後,曾接受建築培訓的Oscar Tuazon和Dean Levin會更留意空間感和物品的環境,如關根的傳奇作品《位相—大地》,從地面掘出的大洞與挖出來的泥土並置,營造一個強烈的平衡狀態;還有《位相—海綿》中重與輕之間的角力,以及《空相》的鏡柱所反映的無實體倒影與壓在鏡柱上的巨石塊之間的對立。Tuazon的抽象和欠形式的結構暗藏危險,同時營造一種存在感。Levin的作品代表新一代紐約藝術家,他們的抽象作品特別重視過程,亦明顯有以往國際先例的影子。引述Levin的自述為此文作結:「當我首次在Gladstone Gallery的展覽『Requiem for the Sun: The Art of Mono-ha』中接觸李禹煥、關根伸夫和吉田克朗等物派藝術家的作品時,與美國極簡抽象主義藝術給我的印象一樣,特別是運用空間的手法,以及天然與工業物料的關係。這與我在自己工作室的創作一樣,試驗不同物品的質素,如表面、倒影和質感與空間的互動。當得知作品有如此重要的歷史背景後,我抽時間思考這種創作手法的先河:從物派到貧窮藝術、具體派、0(Zero)會和單色畫。」
Essay 3
具體派:現代主義去中心化
文:蔡宇鳴
有什麼因素令具體派運動在近年再掀熱潮呢?過去有什麼屏障一直令這一派得不到國際認同呢?
此文回答的其實不是「為何具體派會於現時風行」,而是「為何它之前會被埋沒」。換言之,為何藝術史家、藝評人、策展人和收藏家會對這運動視而不見?有什麼轉變令它能被重視呢?
具體派的作品走在時代尖端,非常高瞻遠矚和富實驗性,能突破傳統媒體的界限,更能跨越地域。那時期的藝評人卻只能搜索枯腸地應對,且時值戰後,地緣政治的權力架構令在巴黎和紐約以外的藝術創新舉步為艱。遠超時代的具體派要靜候藝術史從後追上,對運動有充足的理解。四個轉變令它漸獲接受,即藝術氛圍、藝術史背景、方法論背景和市場環境的轉變。
全球洗牌
首先,藝術氛圍的發展令藝術史家、藝評人、策展人、收藏家和觀眾能拿捏實驗作品的藝術重要性。藝評人針生一郎憶述具體派在1955年開始大膽創作:「就像是我們看到火星生物一樣。」1具體派在紐約也未能得到青睞,1958年在Martha Jackson Gallery舉行首個展覽後被評「欠缺特性和微不足道」。那些作品被包裝和理解成日本呼應抽象表現主義和無形式藝術的表現,它的破格實驗未能形成一種超越文字的藝術語言。直至最近,其他運動如偶發藝術、觀念藝術、動態藝術和關係美學興起,挑戰老式畫派的遺風,造就具體派早已發酵成熟的破格實驗終能盛放。近年,著重時間的創作令藝術史家對具體派的畫畫表現、互動作品和概念作品另眼相看,從歷史角度為它們平反。藝術史對新媒體和科技的熱衷同樣為具體派第二期(1962-1972)的定位提供合適土壤,令觀眾能瞭解具體派作品對抓緊這個瞬間萬變的世界有何重要性和關聯。
其次,全球化加速亦為藝術史背景帶來轉變。具體派藝術家早已意識到自己身處一個互相緊密聯繫的世界,為意義而創作的慣例和思維卻拖慢對國際一體化的反應。作為政治化的國家項目,博物館、博物館館藏和藝術史曾一度只顧說民族故事。另一方面,西方最能把為意義而創作藝術的思維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們所寫和所說的一直流傳至今。然而,這正慢慢改變。世界藝術史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和中東的藝術史記非常感興趣和好奇,這股風氣可追溯至1990年代的區域研究如日本藝術史分野,直至15年後隨國際雙年展盛行才成為藝術史家的焦點。同期,James Elkins致力推動各大研討會,探討全球化對藝術史的影響,而古根漢、現代藝術博物館和泰特現代藝術館等大型國際博物館亦開始把其館藏和展覽趨向全球化。
各界增強對世界藝術史的關注,亦有利於日本和海外藝術史家對戰後日本藝術進行研究。在日本國內,一小撮關西學者和策展人(包括平井章一、加藤瑞穂、河崎晃一、尾崎信一郎、山本淳夫、山脇一夫)為具體派的研究奠定基礎。而在海外,「Japanese Avant-Garde 1910-1970」(龐比度中心,1986)和Alexandra Munroe的「Japanese Art After 1945: Scream AgainsttheSky」(横濱美術館、古根漢美術館、三藩市現代藝術博物館,1994)兩個主要展覽,大大推動了法語及英語世界對戰後日本藝術的史研興趣。Munroe對戰後日本前衛藝術的獨到綜述以具體派打響頭炮,顛覆一貫主流記敍,影響深遠。「Scream AgainsttheSky」是具體派首個在北美的博物館展覽,Munroe建立戰後日本藝術的理論框架,同時兼顧國內和國際對現代主義的論述。此外,山脇一夫的「Gutai:Action andPainting」(西班牙當代藝術博物館、貝爾格萊德當代藝術博物館、兵庫縣立美術館,1985/86)、BarbaraBertozzi和Klaus Wolbert的「Gutai: Japanese Avant-Garde 1954-1965」(德霍爾藝術村,1991)和「Gutai」(巴黎國立網球場現代美術館,1999)等展覽,進一步推高海外對具體派的關注。這些展覽和書冊啟發一代學者和策展人,催生了由富井玲子和手塚美和子組織起來的戰後日本藝術學者通訊錄「PoNJA-GenKon」。這群組為戰後日本藝術史營造活躍的專業討論環境,建立現有的共同目的和學術氛圍,對戰後日本藝術的影響至為重要。
另類表達
第三是在藝術史上製造意義,發展新的方法學。新增物件或藝術家已不能再滿足不斷擴張的典型模範。對現在而言,最重要的大抵是建立質詢藝術作品之間關係的全新批論模式和結構。換言之,我們如何編寫不以歐洲為中心的藝術史?這並非易事,亦是過去十年群體辯論的焦點議題。
我的著作Gutai: Decentering Modernism(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1)對藝評和文學在貶低具體派藝術時常用的原點和派生等批判概念提出新的思維。書內蒐集證據顯示具體派作品遠超概念主義、參與式藝術、裝置、大地藝術和演出等歐美藝術發展,但仍被定形為派生或次等,從而批評編寫藝術史的手法和引起另一中心問題——派生與相似性有何分別?為何具體派被說成是衍生自JacksonPollock,但Pollock又不是衍生自WassilyKandinsky或André Masson呢?歸根究底,此書最核心的問題是我們如何書寫和剖析全球的現代歷史。
Alexandra Munroe和我在研究具體派時發展的另一個方法轉變,就是在論述如此重要的一個團體時,要淡化或轉移敍事角度。因此,我們列出具體派在關西、東京、紐約、巴黎、都靈和約翰內斯堡的通訊網絡、出版和展覽,顯示它並非被動地等待MichelTapié和Allan Kaprow發掘,而是積極地建立世界,體現早期的全球主義。在古根漢美術館的展覽中,我們根據同一理念去為具體派的陳述手法定位。一般的記載以時間編排,用具體派被Tapié和Kaprow發掘的兩個年份作分水嶺,分成初期、中期和晚期三個階段;而我們則把具體派分成第一和第二階段,以具體美術館(GutaiPinacotheca)在1962年的開幕作分界。我們亦棄用「概念主義藝術」和「關係美學」等西方藝術術語,選用「概念」和「演出」等與具體派同源的措詞,避免具體派被理解成任何派系的「日版」。
最後,市場環境亦為具體派營造最佳氣候。日本內外,同代的畫廊總監們對打造戰後日本藝術的市場極其認真,致力修復具體派作品、尋找私人收藏、出版書目和向客人介紹,為作品製造市場環境,令它們晉身成地位崇高的私人及公共收藏。只有作品成為永久收藏,具體派才能化作永恆。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