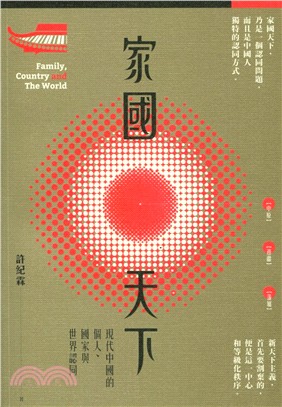商品簡介
當人們普遍地陷入精神和文化的迷惘,思考“我是誰?”“我們是誰?”“家國何在?”“天下何在?”等一系列暗含認同危機的問題時,作者敏銳地指出“家國天下,乃是一個認同問題,而且是中國人獨特的認同方式”,並且藉由精彩的論述將我們帶至那風雲激蕩的歷史轉型過程中,而對於現代中國人如何理解個人、民族、國家以及世界等困擾無數人的問題則一一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更為可貴的是,作者揚棄了“天下主義”這一中國傳統政治智慧,提出了“新天下主義”的概念,力求達至對民族國家和傳統天下主義的雙重超克。
作者簡介
目次
導 論 家國天下與自我認同 001
上 編 從古代「中國」到現代國家認同 019
第一章 多元脈絡中的「中國」 020
第二章 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 039
第三章 現代中國的天下與夷夏之變異 056
第四章 近代民族主義思潮中的國家認同 077
第五章 兩種國家認同:共和愛國主義與文化民族主義 115
中 編 現代中國的國家建構 153
第六章 民國初年的國家建構:權力還是權威? 154
第七章 「魏瑪時期」的國家建構與代表性危機 183
第八章 國家建構的基礎:富強還是文明? 225
第九章 國家富強背後的進化論 255
第十章 國家建構的正當性來源 290
第十一章 新儒家的治國方案 323
下 編 個人、地方與天下認同 353
第十二章 現代中國的個人認同 354
第十三章 國家建構中的地方認同 398
第十四章 五四:世界主義情懷的愛國運動 428
第十五章 新天下主義與中國的內外秩序 452
參考文獻 474
後 記 500
書摘/試閱
導 論 家國天下與自我認同
查爾斯.泰勒在《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一書中發現,傳統社會到近代社會的歷史轉型過程之中,發生過一場「大脫嵌」(great disembedding)的軸心革命。1 傳統社會的現實世界和意義世界,是鑲嵌在宇宙、自然、社會的系列框架之中的。在中世紀歐洲,這是一個由上帝所主宰的神意世界;在古代中國,乃是一個家國天下連續體。個人的行動和生活的意義,只有置於這樣的框架之中才能得到理解並獲得價值的正當性。然而,在17世紀歐洲的科學革命和宗教革命之後,發生了馬克斯.韋伯所說的「祛魅」,個人、法律和國家逐漸從神意的宇宙世界中游離出來,獲得了獨立的自主性,這就是「大脫嵌」。中國的「大脫嵌」發生於清末民初,自我擺脫了家國天下的共同體框架,成為獨立的個人。
中國的「大脫嵌」是一場掙脫家國天下的革命,用譚嗣同的話說,叫作「衝決網羅」。然而,脫嵌之後的中國人是因此獲得了自由,還是重新成了現代國家利維坦的奴隸,或者無所依傍的虛無主義的個人?為了重新獲得個人生活的意義,是否需要「再嵌化」,將個人重新置於新的家國天下的意義框架之中?如何建構家國天下新秩序,如何重建現代的自我認同?自我的實現與家國天下新秩序的建構,又是什麼樣的互動關係?—這些問題都是下文將一一探討的。
一、 自我為中心的家國天下連續體
家國天下,作為傳統中國意義框架的連續體,其主體和出發點是人。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2 所謂家國天下,乃是以自我為核心的社會連續體。但傳統社會的自我,並沒有現代意義上的本真性或自主性,其意義不是自明的,每一個自我都鑲嵌在從家國到天下的等級性有機關係之中,從自我出發,逐一向外擴展,從而在自我、家族、國家和天下的連續體中獲得同一性。
為什麼說家國天下是一個連續的共同體?在古羅馬的傳統之中,國與家是截然二分的兩大領域,這在羅馬的公法與私法的明確界限之中看得很清楚。然而中國的古代社會政治關係,不是用以契約為核心的法來調節,而是以倫理性的禮樂制度構成基本的社會框架。家國一體的禮樂制度,來自西周的分封制。天子封諸侯為立國,諸侯分封土地和人民給卿大夫為立家,進而形成金字塔形的封建等級制度。所謂家國天下,就是由這種宗法分封制聯為一體的卿大夫、諸侯與天子。天子代表天下(相當於現代意義上的國),諸侯代表列國(相當於現代意義上的地方),卿大夫代表采邑(相當於現代意義上的家鄉);家國天下之間,通過層層分封與效忠而形成血緣—文化—政治共同體,既是親戚,又是君臣,如同一個大家族。同時,受到分封的諸侯與卿大夫對自己的封地有絕對的自主權,不受天子的支配,因此諸侯國和采邑之間又是獨立的,相互不隸屬,各有各的特色。從士、大夫、公卿到諸侯、周天子所形成的宗法性分層網絡,有一套嚴密而複雜的周禮來維繫。
春秋戰國之際,這一西周分封制禮崩樂壞,但家國一體卻在大一統的秦漢體制中得以延續和發揚光大。到漢武帝之後,法家的郡縣制與儒家的禮樂制合流,董仲舒提出的「三綱」思想成為兩千年中華帝國的意識形態核心,宗法家族的父子、夫婦倫理與國家的君臣之道高度同構,王朝的政治關係是家族倫理關係的放大,倫理與政治高度一體化。在中國的法律與政治領域,沒有純粹的公共關係,一切都被私人化與相對化,君與臣之間、官與民之間、民與民之間,皆是相對的、情景化的私人倫理關係,而缺乏剛性的政治契約規範。於是,各種宗法家族的人情原則深刻地鑲嵌到國家的法律政治領域,以禮入法,以禮規範法,政治亦高度倫理化、私人化,形成中國特色的禮法一體和私性政治傳統,瀰漫至今,經久不衰。
在家國天下連續體當中,國是相對的,也最為曖昧。在西周,國指的是天子賜給諸侯的封地;到春秋戰國時代,國指群雄爭霸的列國;秦始皇統一天下之後,國乃是以王權為核心的王朝。歷史上的王朝,有大一統之帝國形態,如漢唐明清,也有南北對峙、中原與邊疆抗衡的多個王朝國家,如魏晉南北朝、五代十國和兩宋/遼夏金。古代中國人很難想像一個既非天下又在王朝之上的抽象的共同體。如果一定要在古代概念中尋找,「社稷」這一概念比較接近,但內涵遠遠不及近代國家那般豐富,而是帶有原始的氏族共同體意味。因此梁漱溟說:古代中國人只有王朝的觀念,沒有國家的觀念。「中國人心目中所有者,近則身家,遠則天下,此外便多半輕忽了。」3 而家國天下中的國,確切而言,乃是指具體的王朝。這一以君主為核心的王朝國家,只是家國天下連續體中的中間環節,在下受到宗法家族倫理的規範,在上有天下價值的制約。王朝國家的政治缺乏自主性。在倫理主導的禮治秩序中,公與私常常是相對的、曖昧的,王朝對於家族來說意味着公,公的一個含義就是官府、官家人。然而公還有另一個含義,乃是絕對的、超越的倫理價值,這並非官府能夠代表,而是屬於天下。因而對於天下來說,王朝又是私,明末清初的顧炎武有言,亡國只是一家一姓之王朝滅亡,而亡天下則是天下公義淪喪,人將相食。4
家國與天下,是肉身與靈魂的關係。天下代表了至真、至美、至善的最高價值,這一價值要在人間實現,必須通過宗法家族和王朝國家的制度肉身,這些制度是由將倫理與政治合為一體的名教、典章制度和風俗組成,由此,天下價值不遠人,就在人間的禮法秩序與日常生活之中。離開了家國的肉身,天道將淪為無所依傍的孤魂。另一方面,宗法秩序的正當性、國家秩序的合法性,無法自證其身,只能從超越的天下意識,從更高的天命、天道、天理中獲取。家國對於中國人來說之所以神聖,之所以具有不可撼動的現實權威性,乃是因為它是天下價值的人間體現。對家國秩序的遵守,就是對天道的尊重。反過來說,若是家長和君主的作為不符合天下之大道,違背了聖人之言,那麼作為個人就沒有盡忠盡孝的道德義務;假如出現了逆天而行的暴君,按照孟子的激進思想,便可以遵循天命,起而革命,重建王朝。
在以自我為出發點的家國天下連續體之中,家國不過是中介物,最重要的乃是自我和天下這兩極。天下在古代中國有兩個密切相關的含義:一個是普遍的宇宙價值秩序,類似於西方的上帝意志,與天命、天道、天理等同,是宇宙與自然最高之價值,也是人類社會和自我的至善所在;另一個含義是從小康到大同的禮治,是人類社會符合天道的普遍秩序。前一個天下,因為作為價值體等同於天命、天道、天理,所以不必經過家國的中介,自我便可以與其溝通,孟子有「天民」之說,此說以後為宋明理學特別是陽明心學發揚光大—個人的內心因為先天擁有良知,可以直接與天理打通,良知即天理,天理即良知,自我與天下有直接的通道,不必經過家國的轉手。後一個天下,乃是現實世界中的文化倫理秩序,個人若要與天下打通,必須經過「齊家治國」,才能達致「平天下」,因而家國成為從自我到天下不可缺少的中間環節,而與出世的佛教、嚮往天國的基督教不同,儒家的個人良知之實現,必須通過在家族與王朝的公共事務之中從事道德實踐,所謂致良知中的「致」,不僅是對天理的領悟,更是對天理的踐行。
於是,在家國天下連續體中,古代中國人的自我便具有雙重性:一重是自我無法離開家國的現實倫理秩序直接與天下溝通,個人的自我總是一定的倫理和政治秩序中的自我,離開了家國秩序,自我將不復存在;另一重是認為個人是獨立的「天民」,可以繞開家國的現實秩序,通過內心的良知,自我直接與超越的天理打通,這是從孟子到宋明心性儒家的看法。更有甚者,視家國為累贅的道家,則更是相信通過審美的自由追求,自我可以與天下至道合二為一,融入至善至美的自然秩序之中。中國文化中自我的這種雙重性,形成了中國人性格中似乎是截然對立的兩極:他們是嚴謹的家族主義者、忠君愛國的保守主義者,但同時,又是自由散漫的自然主義者。他們身上具有權威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複雜性格,常常在兩個極端當中來回動蕩,平時是遵守禮法的順民,亂世之中又會成為蔑視一切權威、無所羈絆的「天民」,甚至暴民。
總而言之,古代中國人的自我,鑲嵌在雙重的自然與社會秩序之中。其一是作為天民,自我從屬於以天道為核心的宇宙秩序,其終極價值都要在這一宇宙秩序和超越性的天道之中獲得。其二是作為家族成員和王朝臣民,自我又總是在一定的宗法和王朝秩序之中,在正式的禮法制度和民間的風俗傳統中,履行自己的道德職責,並獲得具體的身份認同,這一身份感是相對的、語境化的,但在確定的關係之中又是明晰的、絕對的。家國與天下,既是具有高度同一性的連續體,同時又有某種不可彌合的斷裂,而自我恰恰鑲嵌於這一連續與斷裂的夾縫之中。中國文化最強調天、地、人三個元素,在家國天下的序列之中,自我是人,家國是地,而天下乃為天也。在現實世界,人(自我)立足於地(家國)與天(天下)溝通,所謂的個人,總是在一定的歷史文化脈絡中,總是在家國天下的共同體中得以生存,獲得自我的認同。但在精神世界,自我因為擁有良知,又可以超越家國直接與天道接軌,他以「天民」的身份出現,直接從超越的天道中獲得神意,化為聖人的意志,而這一意志又是在現實的家國秩序之上,或者化為家國秩序本身。
正是傳統中國文化中這一微妙的兩歧趨向,到了近代演化為一場中國式的「大脫嵌」革命。
二、 近代家國天下連續體的斷裂
近代所發生的「大脫嵌」革命,指的是個人從各種宇宙、自然和社會關係網絡中抽離出來,成為本真的、獨立的個人。按照查爾斯.泰勒的分析,這一過程在歐洲大約經歷了長達五個世紀的「長征」,其間包括兩個方面:一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轉向」,人類作為整體從宇宙秩序中「脫嵌」出來,成為與自然世界相對的「人類主體」;二是「個人主義的轉向」,個人的「內在自我」被發現並被賦予獨特的價值,使個人從有機共同體中「脫嵌」出來,獲得具有個人主義取向的自我理解。個人的自我理解不再依賴任何外在的意義框架,而具有了自我的本真性,成為「分離自在的獨立個體」,這是在近代被建構出來的概念,並成為現代社會重要的社會想像。5
中國的這場「大脫嵌」革命,始於清末民初,經歷了一個世紀之久,至今依然在延續。本真性自我在中國的出現,最重要的前提乃是家國天下連續體的自我斷裂和解體。
在家國天下連續體之中,國家原來是曖昧的中介物,並不處於核心位置。但到了近代,國家昂然崛起,成為致使家國天下斷裂的中心一環。近代的國家非古代的王朝,它是一個有着政治自主性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共同體,政治正當性的來源不再是超越的天命、天道、天理,而是回歸為人的自身意志和歷史主體;另一方面,國家的法律從禮治秩序和宗法關係中剝離出來,具有了自主性的性格。因而,國家的崛起是一次重大的歷史事件,它重新塑造了個人與家國天下的關係,也顛覆了家國天下秩序本身。
首先是家與國的斷裂。近代中國的啟蒙知識分子普遍認為古代中國只知家族、不知國家,缺乏近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意識。為了建立歐洲式的國家,首先必須「去家化」,批判家族主義,將國家從宗法倫理中剝離,使其獲得獨立性。1904年,《江蘇》雜誌上有一篇《家庭革命說》,說得非常明確:「家庭革命者何也?脫家庭之羈軛而為政治上之活動是也,割家族之戀愛而求政治上快樂是也,抉家族之封蔀而開政治上之智識是也,破家族之圈限而為政治上之犧牲是也,去家族之奴隸而立政治上之法人是也,鏟家族之惡果而收政治上之榮譽是也。」6 到了五四時代,家族普遍被視為專制主義之淵藪,要建立民主共和,就必須首先打倒宗法家族,儒家的三綱思想成為首當其衝的目標。經新文化運動的衝擊,國與家脫鈎,政治的公領域與社會的私領域分化,然而,這僅僅是觀念上的,在政治實踐領域,家國一體的殘餘物依然強大,以德治國成為歷代統治者信奉的不二理念,以家想像國,儒家的人情原則依然主宰着政治領域,政治的倫理化、私性化依然是中國政治不同於法治西方的基本特徵。
其次是國與天下的斷裂。國家一旦成為自主性的實體,就脫離了超越世界中神魅價值的規約,具有了自身的價值目標。從晚清開始,因為受到亡國滅種、諸國競爭的壓力,國家的自身目標就是富國強兵,這成就了中國式的國家理性;藉助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推波助瀾,國家主義壓倒了傳統的天下價值觀,不再以德性和民生,而是以國家富強作為民族復興的中心標尺。古代的天下主義乃是一套以德性、德治為核心的文明觀,到了清末民初,文明的主體發生了變化,中國的天下主義德性文明轉變為以西方為主體的自由民主的現代文明。於是傳統的國與天下的關係,變易為富強與文明的價值衝突。國家的理性目標是民族的崛起和富國強兵,而代替天下主義的、近代世界主義的價值目標是公義、平等和自由,在富強文明之間發生了不可縫合的斷裂,晚清以還一個半世紀的民族復興過程,基本是富強壓倒文明,國家理性凌駕於普世價值。天下的式微和國家的崛起,使得家國天下連續體失去了平衡,破碎的家國不再擁有超越的天下價值,只留下世俗性的功利目標。
家國天下連續體的破裂,乃是一種個人的解放。晚清之際,最激動人心之口號,乃是譚嗣同所說的「衝決網羅」。這個「網羅」,便是儒家三綱所編織的家國共同體。最富中國特色的家族主義,成為晚清民國兩代啟蒙者鞭撻最力的萬惡之首。家族主義不僅是政治專制主義的溫床,而且是個性解放、個人自主的最大屏障。年輕一代紛紛從家鄉出走,走向自由自在的都市,家鄉之所以不值得留戀,乃是有令人窒息的宗法家族,還有與家族聯繫在一起的束縛個性的禮教家規。都市是一個高度流動的陌生人社會,脫離了各種傳統的社會文化共同體,每個人都成為獨立自在的原子化個人。
然而,近代意義上的個人,雖然從家國「網羅」中「脫嵌」而出,卻進入了另一個身份網絡,那就是與國家密切相關的國民。國民與國家是同時誕生的,當傳統的自我剝離了各種家族、地方共同體成員身份之後,其身份定位便退出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師生、朋友等各種特殊的私人領域,在日益強大的國家法權關係之中,每個人都獲得了一個平等的、同一性的身份—國民。在古代中國,個人與國家之間有家的中介,每個人都是以某個家族或地方成員的資格面對國家,但到了近代,社會中介物失卻之後,個人便直接面對國家,而以法律和政治的方式所重建的個人與國家關係不再具有原來溫情脈脈的人格化的倫理性質,而只是非個人的、非人格化的法權關係。晚清因為受到德國和日本國家主義思潮的影響,對個人與國家的關係普遍有一種「國民國家一體化」的理解,但國民與國家的蜜月期很快就結束了,到了五四時代國民與國家發生了分化和對抗,從此注重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與傾心國家權威的國家主義分道揚鑣,而以梁漱溟為代表的注重鄉村建設的社群主義,試圖走出個人與國家的二元對抗,重新在二者之間嵌入血緣與鄉緣因素,在公共的法權關係之外重建人與人之間的私人倫理。
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時代。啟蒙者們以風捲殘雲之勢破除了家國天下連續體,為的只是將從家族和君主權威下解放出的個人,與新的天下相溝通。如前節所述,傳統的天下與自我皆具有互相矛盾的雙重性,現實層面的自我與天下須經過家國的中介方得以相通,而精神層面的自我與天下這對大小宇宙卻可以繞過家國的中介獲得直接的同一性。到了五四,傳統的自我蛻變為現代具有本真性的自由個人,而原來具有天道神魅性的天下則轉型為人類中心主義的世界。新的個人與新的世界不僅在心性領域,而且在世俗領域也無須經過家國的中介,可以直接相通。傅斯年有一句名言:「我只承認大的方面有人類,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實的。『我』和人類中間的一切階級,若家族、地方、國家等等,都是偶像。我們要為人類的緣故,培成一個『真我』。」7 中介是真實的,偶像是虛幻的,在五四知識分子
看來,家族、地方、國家皆是人為製造的、需要破除的偶像,在茫茫宇宙之中,唯有人類和個人是唯一真實的,人類世界具有普世的公理與價值,而個人的價值和意義只有置於世界的普世架構和人類的歷史長河之中才能得以理解,這就是胡適所說的「小我」與「大我」:「我這個『小我』不是獨立存在的,是和無量小我有直接或間接的交互關係的;是和社會的全體和世界的全體都有互為影響的關係的;是和社會世界的過去和未來都有因果關係的。…… 我這個現在的『小我』,對於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過去,須負重大的責任;對於那永遠不朽的『大我』的無窮未來,也須負重大的責任。」8 清末民初的無政府主義和世界主義思潮曾經流行一時,影響了包括革命黨人、啟蒙派和文化保守主義在內的整個一代人,這與家國天下秩序的解紐有密切的關係。自我與天下的直接溝通,從心性層面擴展到社會實踐層面,構成了現代中國重要的歷史傳統。
----------------------------------------
1 參見[加拿大]查爾斯.泰勒:《現代性中的社會想像》,李尚遠譯,台北:商周出版,2008年,第87—112頁。
2 《孟子.離婁上》。
3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見中國文化書院學術委員會編:《梁漱溟全集》,第3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3頁。
4 [清]顧炎武:《日知錄》,第13卷,《正始》。
5 參見劉擎:《沒有幻覺的個人自主性》,載《書城》,2011年第10期。
6 家庭立憲者:《家庭革命說》,載《江蘇》,第7期,1904年1月。
7 傅斯年:《〈新潮〉之回顧與前瞻》,見歐陽哲生主編:《傅斯年全集》,第1卷,長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7頁。
8 胡適:《不朽:我的宗教》,見歐陽哲生編:《胡適文集》,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529—532頁。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