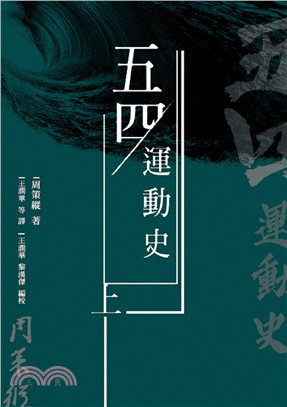定價
:NT$ 370 元優惠價
:90 折 333 元
無庫存,下單後進貨(採購期約4~10個工作天)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9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本書乃著名歷史學家周策縱先生的代表作,以豐富的文獻資料,宏大的歷史框架,客觀的敘述角度,分析民國初年影響中國近代史深遠的五四運動,詳細論述了運動發生的社會、思想條件,同時探討運動的發展過程、歷史作用及其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這三個方面的問題。
聯合推薦:
「一本材料詳實、內容豐富的卓越著作,任何一位研究現代中國的讀者不可缺少的指導性參考書……這書把歷史細節和廣闊的社會政治背景巧妙地交織起來,造成一種完美的有解釋性的關於中國的研究,實在是前所未有。」
――美國《東方學會學報》
「在這最全面而又最完整的研究中,周教授以一個其新視野和客觀態度,詳細檢視了這運動的各個方面。」
――費正清 哈佛大學教授、歷史學家
「當我讀你的書《五四運動史》時,我就立刻覺得必須寫封信,並且設法寄達你,因為我要為你這書而感謝你。如你所知,我於一九二〇年和羅素一同訪問中國,事後就和他結了婚。作為一個外國人,我當時未能知道中國正在進行的活動的詳情,這些詳情你在你書裏是那麼美妙地敘說了。」
――哲學家羅素夫人(Dora Black Russell)
聯合推薦:
「一本材料詳實、內容豐富的卓越著作,任何一位研究現代中國的讀者不可缺少的指導性參考書……這書把歷史細節和廣闊的社會政治背景巧妙地交織起來,造成一種完美的有解釋性的關於中國的研究,實在是前所未有。」
――美國《東方學會學報》
「在這最全面而又最完整的研究中,周教授以一個其新視野和客觀態度,詳細檢視了這運動的各個方面。」
――費正清 哈佛大學教授、歷史學家
「當我讀你的書《五四運動史》時,我就立刻覺得必須寫封信,並且設法寄達你,因為我要為你這書而感謝你。如你所知,我於一九二〇年和羅素一同訪問中國,事後就和他結了婚。作為一個外國人,我當時未能知道中國正在進行的活動的詳情,這些詳情你在你書裏是那麼美妙地敘說了。」
――哲學家羅素夫人(Dora Black Russell)
作者簡介
周策縱(1916-2007)
湖南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系和歷史系終身教授,為知名漢學家和歷史學家。
代表作有《五四運動史》、《中國浪漫文學探源》、《海燕》等。
一生中英文著述頗豐,計有40餘本專著和180餘篇論文出版刊行,並有多篇隨筆、散文、詩詞等作品傳世。
湖南人,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東方語言系和歷史系終身教授,為知名漢學家和歷史學家。
代表作有《五四運動史》、《中國浪漫文學探源》、《海燕》等。
一生中英文著述頗豐,計有40餘本專著和180餘篇論文出版刊行,並有多篇隨筆、散文、詩詞等作品傳世。
序
周策縱的「五四學」:
知識分子領導的「五四」與走向知識時代的「五四」
王潤華
一、離散/流亡與邊緣思考的「五四」論述:拒絕同化的多元透視力
周策縱教授(一九一六―二〇〇七) 曾寫自傳,題名〈忽值山河改:半個世紀半個「亡命者」的自白〉。他於一九四八年去國,乘輪船赴美途中,做舊詩〈去國〉(一九四八)抒懷,表明不滿混亂的時局與官場聽命的人生才出國深造,但是還未抵達彼岸,就感到「去國終成失乳兒」之苦,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於美琪輪 (General Meigs) 上:
萬亂瘡痍欲語誰,卻攜紅淚赴洋西,
辭官仍作支床石,去國終成失乳兒。
抗議從違牛李外,史心平實馬班知,
吳門傾側難懸眼,碧海青天憾豈疑。
《五四運動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第一稿是在一九五四年寫成, 一九五五年正式通過的密芝根大學政治系博士論文,根據《關於中國的博士論文》書目,原題為《五四運動及其對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影響(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upon China’s Social-Political Development)。 周策縱於一九四八到美國,擬進入芝加哥大學,但由於不喜歡芝加哥城市,轉入密芝根大學政治系,一九五〇獲碩士,一九五五年獲得博士。在前後這年些間,他感到自己四處流亡,就如他的新舊詩集《周策縱詩存》與《胡說草:周策縱新詩全集》充分反映其心態,他的新詩〈給亡命者〉(一九五七)寫的也是自己:
像受了傷的野獸舔著創傷,
你鮮紅的血只滴向荒涼的地方。
為了潔白的生命而走向漆黑的死亡,
你高大的墓碑上將只剩著兩個大字:反抗。
他經歷過典型的放逐與流亡的生活,從打工到哈佛當研究員,漂泊不定的知識分子人的邊緣思考位置,遠離政治權力,建構客觀的透視力超強的五四的新論述。
這部論述使人不禁想起薩伊德 (Edward Said, 1935-2003) 所說的放逐詩學。這是一個全球作家自我放逐與流亡的大時代,多少作家移民到陌生與遙遠的土地。這些學者作家經歷真正家園的嚴重割裂,他們企圖擁抱本土文化傳統的同時,遇上與域外文化或西方中心文化的衝擊,給今日世界文學製造了巨大的創造力。 現代西方文化主要是流亡者、移民、難民的著作所構成。美國今天的學術、知識與美學界的思想正出自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的難民與其他政權的異議分子。整個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學與文化,簡直就是ET(extraterritorial)文學與文化。 知識分子原本就位居社會邊緣,遠離政治權力,置身於正統文化之外,這樣知識分子/作家才可以誠實的捍衛與批評社會,擁有令人歎為觀止的觀察力,遠在他人發現之前,他覺察出潮流與問題。古往今來,流亡者都有跨文化與跨國族的視野。 流亡作家可分成五類:一、從殖民或鄉下地方流亡到文化中心去寫作;二、遠離自己的國土,但沒有放棄自己的語言,目前在北美與歐洲的華文作家便是這一類;三、失去國土與語言的作家,世界各國的華人英文作家越來越多;四、華人散居族群,原殖民地移民及其代華文作家,東南亞最多這類作家;五、身體與地理上沒有離開國土,但精神上他是異鄉人。 無論出於自身願意還是強逼,思想上的流亡還是真正流亡,不管是移民、華裔(離散族群)、流亡、難民、華僑,在政治或文化上,他們都是置身邊緣,拒絕被同化。在思想上流亡的學者作家,他們生存在中間地帶(median state),永遠處在漂移狀態中,他們既拒絕認同新環境,又沒有完全與舊的切斷開,尷尬的困擾在半參與半遊移狀態中。他們一方面懷舊傷感,另一方面又善於應變或成為被放逐的人。遊移於局內人與局外人之間,他們焦慮不安、孤獨,四處探索,無所置身。這種流亡與邊緣的作家,就像漂泊不定的旅人或客人,愛感受新奇的事物。當邊緣作家看世界,他以過去的與目前互相參考比較,因此他不但不把問題孤立起來看,更有一種雙重的透視力(double perspective)。每種出現在新國家的景物,都會引起故國同樣景物的思考。因此任何思想與經驗都會用另一套來平衡思考,使新與舊的都用另一種全新、難以意料的眼光來審視。
在中國近代史上,沒有任何的重要事件像「五四運動」這樣複雜與容易惹起各種爭議。關於五四運動的書寫,在五十年代,爭論性的居多,沒有一本書被學術界接受,西方人對其認識更不正確,所以周策縱老師決定寫一本書確切記錄其史實,詳細探討其演變和效應。當他在密芝根大學寫博士論文時,便決定把五四看成一件多面性的社會政治事件去描述和研究,由於這是極端複雜而多爭論性的題目,他的指導老師也反對。根據他的回憶,在一九五二年的一天,他與密西根大學指導老師討論該生的博士論文選題時,提出如此的這建議。預想不到,教授提高了嗓門:「甚麼!你說你要寫『五四』運動,不行!博士論文怎麼可以寫學生暴動?……甚麼?說這是中國的文化運動、文藝復興、思想革命?簡直胡鬧!你若是堅持寫這個題目,我們就取消你的獎學金!」這位老師還曾在中國停留多年,因此他憤然而去。
《五四運動史》,原為博士論文,在完成前,一九五四年,周老師在哈佛大學歷史系任訪問學者寫論文,畢業後,一九五六至一九六〇又回返哈佛任研究員,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任榮譽研究員。所以哈佛學術研究氛圍與教授對他的五四學之建立,帶來極大的多元的啟發。像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洪業(洪煨蓮,一八九三―一九八〇)、楊聯陞(一九一四―一九九〇)、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 -1991) 、海陶瑋 (James Hightower, 1915-2006) 、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1912-2007,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在哈佛)等人,他們這群多是流亡(洪業、楊聯陞)、,離散(史華慈猶太裔美國人)、多元文化(如費正清)。周教授原書英文版的《五四運動史》序文最後的一大段,感謝協助他完成論文撰寫、修改與出版的學者,目前所有中譯本將它刪去,非常可惜。這些精神思想導師,影響了老師的一生學術生涯。他們幾乎都是哈佛大學與美國的一流學者,很多來自中國與其他亞洲及歐洲漢學者,而且多是自我放逐、流亡的知識分子,他們位居社會邊緣,遠離政治權力,置身於正統文化之外。老師跨文化與跨國族的視野,令人歎為觀止的觀察力與他們的對話有絕對的密切關係。
二、周策縱的五四多元史觀:準確地認識過去,解釋未來
周老師回憶在哈佛大學改寫《五四運動史》時,當時哈佛的同事楊聯陞看見他不斷修改,就催他趕快出版:「我們現在著書,只求五十年內還能站的住,就了不起了。我看你這書可以達到這標凖。還擔心甚麼?」周老師回答說,由於五四是一個可以引起爭論的歷史,他要繼承中國古代史家的兩個優良傳統:「一個是臨文不諱,秉筆直書;另一個是不求得寵與當時,卻待了解於後世。」他又指出他當時寫歷史的態度,不但受了西洋歷史之父希羅多德 (Herodotus, BC 484-425) 之啟發,他的歷史觀要對過去有準確地認識,也可幫忙解釋可能發生類似的事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的多元歷史觀與分析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也影響了他對五四史實的詮釋。下面的自我回憶,可幫忙我們了解他的突破性的五四論述:
在美國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讀西洋哲學史、政治理論與制度和東西方歷史。一九五四年在哈佛大學當任訪問學者,寫完博士論文,對五四運動史化了不少時間和精力。這期間我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如何富強,如何吸收西洋的長處,推動現代化。一九五六年起再到哈佛人研究院五六年,在那裏的幾個圖書館的書,使我對中西漢學有了更多的認識,也使我的治學方向發生了又一次大轉變。
另外啟發周教授的五四史觀是《春秋公羊傳》裏的三句話:「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異辭。」這三句話使他對歷史產生兩個敏銳的觀察力。他說:「五四運動本身的複雜性,和後來個黨派的不同解釋,跟是請神參預者、所見者所聞者、所傳者,前後往往自相矛盾……我還是覺得最先的,當下的說辭較近於事實。這使我決定大量採用當時報刊的記載和個人『當下』的回憶」,對後來的說法和解釋決不得不審慎不懷疑。這也使我特別注意到「異辭」的問題。所以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認知是建構五四論述的基點。
三、超越中西文明典範的詮釋模式:文化研究典範
周策縱教授在一九四八年五月離開中國到密芝根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與博士之前,已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學有淵深精深的造詣。他的學術研究可說繼承了注重版本、目錄、注釋、考據的清代朴學的傳統,主張學問重史實依據,解讀由文字入手,以音韻通訓詁,以訓詁通義理。《周策縱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中的〈說「尤」與蚩尤〉與〈「巫」字探源〉可說是這種治學方式的代表作。
周教授出國後的學術訓練,本文上面我引用他說過的話:「在美國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讀西洋哲學史、政治理論與制度和東西方歷史。」他受益最大該是以西方漢學的精神,突破了中國傳統思考方式。西方漢學的強點,專業性很強,研究深入細緻。周教授把中國傳統的考據學與西方漢學的治學方法與精神結合成一體,這種跨國界的文化視野,就給中國的人文學術帶來全新的詮釋與世界性的意義。例如初稿於一九六七,完成於一九九九的六萬多字的論文〈扶桑為榕樹縱考〉,周老師為了考定扶桑就是榕樹,考釋古代神話、圖畫、出土文物、古文字中認定、又從歷史、文化中去觀察,舉凡文學、植物學、文字學的學識都廣泛深入的溝通,另外也前往世界各地觀察與攝影有關植物。這種跨知識領域的文化研究,是既典型又前衛。
周教授當時編輯的兩本《文林:中國人文研究》(Wen 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的學術研究, 代表當時他自己主導的歐美漢學家的跨越學科、知識整合的學術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向,所以他實際上要建構的就是目前所謂文化研究的前行者。
而美國學術界則自二次大戰以來,開發出一條與西方傳統漢學很不同的研究路向,這種研究中國的新潮流叫中國學(Chinese Studies),它與前面的漢學傳統有許多不同之處,它很強調中國研究與現實有相關,側重思想性與實用性,強調研究當代中國問題。這種學問希望達到西方了解中國,與中國了解西方的目的。 中國研究是在區域研究(Area Studies)興起的帶動下從邊緣走向主流。區域研究的興起,是因為專業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的解釋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為典範而發展出來的,對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課題涵蓋與詮釋性不夠。對中國文化研究而言,傳統的中國解釋模式因為只用中國文明為典範而演繹出來的理論模式,如性別與文學問題,那是以前任何專業都不可能單獨顧及和詮釋。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從中國研究到中國文學,甚至縮小到更專業的領域中國現代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都是在區域研究與專業研究衝激下的學術大思潮所產生的多元取向的學術思考與方法,它幫助學者把課題開拓與深化,創新理論與詮釋模式,溝通世界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上述「中國學」的這種研究中國的新潮流的發展,哈佛大學便是其中一個重要中心,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正式形成主流。周教授在這期間,也正好在哈佛擔任研究員, 他的成名作《五四運動史》,原是密芝根大學的博士論文《五四運動及其對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影響》,獲得博士學位不久後,費正清聘他到哈佛東亞問題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其中重要的研究項目就是改寫他的五四論述的論文,同時期在哈佛共事的還有洪業、楊聯陞、裘開明(一八九八至一九七七)、費正清、史華慈等,在這些中西學者的「內識」和「外識」的跨學科多元文化與思想的學術環境中,在傳統的西方漢學 (Sinology)與新起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學術思潮中,修改完成並出版他的五四論述。此類專著或論文,完全符合中國研究與現實有相關,思想性與實用性,強調研究當代中國問題以溝通東西文化的了解的傾向。另一方面,區域/文化研究思潮也使本書超越以西方文明為典範而發展出來的專業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的解釋模式,同時更突破只用中國文明為典範而演繹出來的傳統的中國解釋模式。所以《五四運動史》成為至今詮釋五四對權威的著作,成了東西方知識界認識現代新思文化運動的一本入門書,也是今天所謂文化研究的典範。
《五四運動史》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文學和歷史提出系統的觀察和論斷。奠定了作者在歐美中國研究界的大師地位。這本書使用大量原始史料,包括中、日、西方語文的原始檔案,形成窄而深的史學專 (monograph) 思想文化專題的典範著作。周教授研究《五四運動史》中所搜集到的資料本身,就提供與開拓後來的學者研究現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文學個領域的基礎。因此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也將其出版成書《五四運動研究資料》 (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另外本書所體現的不涉及道德判斷或感情偏向,就凸顯出客觀史學(現實主義史學)的特質。周教授在密芝根大學念的碩士與博士都是政治學,因此社會科學(政治、社會、經濟學等)建構了他的現實客觀的歷史觀,這正是當時西方的主流史學,這點與費正清的社會科學主導的客觀史學很相似。 而且被奉為在中國研究中,跨越知識領域研究、文化研究最早的研究典範,也是最具國際性、知識領域廣泛性的影響力的專論。
到了七十年代,文化研究領域開啟了之後,文化研究開始成為重要學術潮流,文化研究者跨越學科,結合了傳統社會學、文學、政治、與及新起的國族問題,來研究現代社會中的複雜文化現象。在《五四運動史》中,周老師已是全面執行文化研究者的思考與方法,時常關注某個現像是如何與意識形態、國族、社會階級與/或性別等議題產生關連。譬如國際民族主義權威謝佛(Boyd C. Shafer)的《民族主義的各種面貌:新現實與就神話》(Faces of Nationalism: New Realities and Old Myths),認為國際化日益重要,但國家民族仍然重要,他引用周策縱有關中國五四運動建立的國家民族主義以抵抗外國的侵略,保護領土完整作為重要證據。 文化研究的「文本」(text)不只是書寫下來的文字,還包括了口頭訪問、檔案、攝影、報紙、期刊、分析研究的文本物件包含了所有意義的文化產物。他又特別審視文化活動與權力的關係。所以他一生堅持五四是社會政治邊緣的知識分子領導的:
二十年代中葉以後,兩大勢力黨團本身也逐漸被少數領導者所控制,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利益來解釋務實運動,以便奪取政權,支持和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和威權。於是五四運動對自由、民主、科學、人權的熱烈號召,對權威壓迫的強烈抗議精神,就逐步給掩蓋抹殺了。
由於文化研究是研究的客體,同時也是政治批評與政治行動的場域,所以周教授自己最後了解到,「野心家打著五四旗號來掩飾五四,利用五四,於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就看不到五四的真正史實,於是我的《五四運動史》也就殃及魚池般在中國本土成為「禁書」大二三十年之久了。」
四、一九一七―一九二一與知識分子主導的「五四運動」
如上所述,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周教授敢以薩伊德所謂「邊緣思考」的透視力把五四定義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的知識分子領導運動,引起極大的爭議,尤其在大陸、台灣官方或具有政治傾向的學人在八十年代都難於接受。像周老師這些邊緣思考的學者與國土,自我與真正家園的嚴重割裂,企圖擁抱本土文化傳統與域外文化,又受西方中心文化的衝擊。知識分子原本就位居社會邊緣,遠離政治權力,置身於正統文化之外,擁有令人歎為觀止的觀察力,遠在他人發現之前,他已覺察出潮流與問題。古往今來,流亡者都有跨文化與跨國族的視野。在政治或文化上,他們都是置身邊緣,拒絕被同化。
周老師的英文原著書名是The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扉頁上自題中文書名是《五四運動史》。英文書名中的Intellectual Revolution 沒有標準的翻譯,可解作「思想革命」或「知識革命」,其實英文Intellectual Revolution包含兩者。他認為五四的啟蒙一切從知開始:
這「知」字自然不只指「知識」,也不限於「思想」,而是包含一切「理性」的成分。不僅如此,由於這是用來兼指這是「知識分子」所領導的運動,因此也不免包含有行動的意思。
所以五四的重要性在於青年知識分子抗議精神和對政治組織、社會制度、倫理思想和文化文學改革。在這個前提下,
對傳統重新估價以創造一種新文化,而這種工作須從思想知識上改革著手:用理智來說服,用邏輯推理來代替盲目的倫理教條,破壞偶像,解放個性,發展獨立思考,以開創合理的未來社會。
周教授把五四定義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的知識分子領導運動,他特別指出:
一九二四以後,中國兩大政黨受了蘇聯的影響,吸引知識分子參加無力革命,拋棄了「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風。我認為這是扭曲和出賣了一個性解放、人道主義、自由、民主、科學思想為主軸的「五四精神」。
他斷定五四運動時期主要為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因為一九二四年以後,中國兩大政黨受了蘇聯的影響,吸引知識分子革命,拋棄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風,他認為那是扭曲了五四精神。 他堅持的論點,至今為國際學術界所重視。但是卻被在大陸與台灣的官方與主流學術界所難於接受:五四是知識分子所主導的,是一項多面性的社會政治文化思想的啟蒙運動,大前提是對傳統重新估價以創新一種新文化,而這種工作須從思想知識上改革著手,用理智來說服,用邏輯推論來代替盲目的倫理教條,破壞偶像。解放個性,發展獨立思考,以開創合理的未來社會。五四思潮不是反傳統主義,而是革新知識,拋棄不好的傳統。因為它提倡理智和知識,現在五四精神仍然重要,因為它引導中國走向未來的知識時代。
在《五四運動史》中的時限的斷定,都非常的審慎,而且多元化。他在一九九一年的演講中,再次的解釋:
至於「五四運動」的時限,我在書中曾指出,當時的思想轉變與學生活動,主要集中於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這五年之間;不過,我同時也強調,這個運動不應限制在這五年,最低限度可以擴充為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四這十年,因而我早在哈佛出版的第二本書《五四運動研究資料史》時,索性把標題示為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四。我之所以把五四運動的下限,主要是因為是年國共正式合作,著手一物力和黨的組織推翻北洋政府,所牽涉的是隕石雨黨派鬥爭,與知識分子領導的思想運動已有所區別。這項轉變及其重要,「五四 」潮流後來所以未能順利發展,便是遭到此一阻礙。
重讀《五四運動史》,我發現老師的論述嚴謹細密,時限因應論述的課題而改變,請看下面第一章「導論」內文,很明確的鎖定五四運動為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請看下面幾章的年代:
第二章「促成「五四運動」的力量(一九一五―一九一八)
第三章 運動的萌芽階段:早期的文學和思想活動(一九一七―一九一八)
第七章 新文化運動的擴展(一九一九―一九二〇)
第九章 觀念上和政治上的分裂(一九一九―一九二一)
第十章 社會政治的演變結果(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另外書後附錄的「相關大事表(一九一四―一九二三)」,他把時限拉得更長。所以他以五四的複雜多面向的演變而考慮時限的適當性,這是當時哈佛大學費正清及其他學者所強調的客觀史學。
他堅持的論點,至今為國際學術界所重視,包括台灣大陸的學術界。無論研究社會文化、政治思想、文學藝術的著作,幾乎很少不會引用到這本具有一家之言的有關五四的權威的著作。
五、五四精神:引導中國走向知識時代
周教授在五〇年代已洞見新知識分子與新知識的重要性。單單從《五四運動史》中各章節的題目,就可見討論新知識分子與新知識的篇幅占了很多。 第三章有「新知識分子的聯合與《新潮》雜誌的創辦」、「新知識分子改革的觀點」,第七章有「新知識分子之間團結的增加」、「新知識的、新社會的、和新政治的團體」、「新知識分子所宣導的大眾教育」更重要,他全書的結論認定五四運動最終目的是獲得新思想與知識的革命。這就是所謂intellectual revolution :「五四不僅是思想知識的,同時也是政治和社會改革運動,即追求國家的獨立、個人的自由、公平的社會和的現代化中國。而本質上就是廣義的新知識思想的革命.所以說它是思想知識革命,因為思想知識的改變才能帶來現代化,它能促成思想知識的覺醒與轉型,同時這是知識分子領導的運動。」
五四至今已一百年。中國與世界,在數碼科技的推動下,已發生極大的轉型與變動。五四的精神主軸,為知識分子選擇以思想文化革新作為救國的途徑。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更理解到五四運動還有無比的感召力,因為五四提倡理智和知識,今天世界已進入知識時代,一九九五年周老師寫道:
五四提倡理智和知識,是最適合現代新潮流的趨勢。二十世紀有蒸汽文明進展到電力文明,有原子能文明到電子文明,資訊文明。在可見的將來,在可見的將來,在二十一世紀,高科技的地位越來越提高。我們對財產的觀念也初見改變和擴張了。過去計算財富的要素是土地、勞力、物資和資本,現在和將來,「知識」(knowledge)必定成為最重要的「財富」(wealth)。
經濟早已轉型,從投資經濟變成知識創新經濟,從機器生產與勞動力的社會逐漸轉型為知識社會,新知識經濟裏,整合知識、創新思考是主要資源。這種多元知識專才,在目前社會裏,會成為社會,甚至政治的主導力量。《五四運動史》在一九五五初稿就完成,周教授的詮釋力與洞察力,令人驚訝。
現在再讀《五四運動史》的第七章「新文化運動的擴展(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周老師特別不斷強調新知識分子及其領導的「新文化運動」。他引用陳獨秀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從監獄中釋放,劉半農寫一手長詩的兩句,意義非凡:「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他們都入監獄,監獄便成了研究室」。 這裏「研究室」便是知識最好的象徵。美國及西方國家,一百年來,大學的研究室,尤其實驗室通宵燈火通明,學者天天如坐牢,所以今天他們開拓了知識經濟的時代。他也引用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論文〈新文化在中國〉(New Culture in China) 中的話說,中國要富強,「沒有新思想知識運動是不能到達到的」(that is impossible without the intellectual movement) 像這樣的話語,落在過於思想意識形態教育大陸,就被簡單化的譯成「而沒有新思想運動」 ,老師一再的強調「五四不僅是學術上,同時也是政治和社會上的改革運動,及是國家的獨立、個人的自由和中國的現代化,而以學術為首」。
老師早年的學問從版本、目錄、注釋、考據的清代朴學的傳統,主張學問重史實依據,解讀由文字入手,以音韻通訓詁,以訓詁通義理。受過政治學的嚴格訓練,也就是社會學的精密分析方法,轉型到歷史,他不僅重視史實之考證,事事詳加比對求證,更要求解釋,給予史實應有的含義,因此《五四運動史》又具有史華慈的思想史學的特點,在複雜的歷史事件中,尋找沒有時間性的鑰匙與價值。中國的現代化與知識,在《五四運動史》是同義詞。如果我們細心的閱讀《五四運動史》,他的書名intellectual,雖包含思想,主要指知識 (knowledge)與知識分子(intellectual),全書「新知識分子」或「新知識」不斷重複出現在章節的標題上,如第三章的「新知識分子的聯合與《新潮》雜誌的創辦」,「新知識分子的改革觀點」。不但書名有intellectual,書後半部的總題是Analysis of Main Intellectual Currents。這些intellectual 主要是知識分子或知識。書中真正指思想的時候,用的是thought, 如十二十三章都用「新思想」 (new thought),因為這是知識分子領導的運動,這個文化運動最重要的目標就是以知識建立現代化的中國。
六、五四超越五四精神遺產
周老師的研究與論述,從政治學到史學,然後再做文學與語言文字。晚年回憶他的治學路程,如下面一九九七年為《棄園文萃》寫的〈序〉,承認撰寫五四期間用功最深:
在美國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讀西洋哲學史、政治理論與制度和東西方歷史。一九五四年在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寫完博士論文,對五四運動史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這期間我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如何富強,如何吸收西洋的長處,推動現代化。一九五六年起再到哈佛人研究院五六年,在那裏的幾個圖書館的書,使我對中西漢學有了更多的認識,也使我的治學方向發生了由一次大轉變。
他在美國的學術經驗,深深的認識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有很大的缺失。其一是認知意識不夠發達。對邏輯推理不夠精密,在實際議論時不能嚴密運用三段論法(syllogism),把是非當作道德。他在《棄園文萃》的序文裏接著上面引述的那段,指出:
由於讀了更多的外語,使我深深感到,從古代起,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免有兩個最基本的缺失:一個是邏輯推理不夠精密,尤其在實際議論時不能嚴密運用「三段論法」(syllogism)。另一個缺失看來很簡單,卻可能更基本,我們對「認知」的意識不夠發達。就是對「是」甚麼,「不是」甚麼不夠重視。從先秦起,「是非」就逐漸變成道德詞彙,不是指實之詞了。「是」、「為」、「乃」作為指實詞,用得很不普遍和明確。漢語動詞作名詞用自然太多了,可是「是」作為to be或being意義用作名詞者,恐怕古代並不多見。我只不過用這個例子來說明,我們傳統上「認知」是甚麼不是甚麼的意識,發達得可能不充分。這兩點是我去國五十年來的痛切感覺,對不對自然是另一問題,但對我後來的治學研究,關係不小。
於是我認為,對中西文明、思想和制度等,我們認知得還很不夠。甚至連中國的古代經典、文學作品,以至於古代文字和古今歷史事實,都應該切實認知一番,才能夠加以評判。
另外他又說:
歐美的文明,除宗教的思想之外,主要比較重視邏輯推理,考察自然規律,也就是客觀的知識;中國至少自秦漢以後,所發展的乃是偏重倫理道德、修齊統治的文明。
所以他的結論:「這種尚知的新作風,應該是中國文明史上綴重大的轉捩點」:
這裏所說的「知」,是指對客觀實在認知的知,是純粹邏輯推理的知。是指探索「是甚麼」、「為甚麼」、和「如何」的知,不是教人「應該如何」的道德教導。當然,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對這些並未能完全好好做到,但有許多人有這種嚮往,那就仍可說是劃時代的了。這也不是說道德不重要,只是說,五四思潮補救了傳統之偏失。
周教授一生的學術研究研究與文學創作就是建立在五四思想革新的認知上,比如研究《紅樓夢》,他就指出紅學的研究態度和方法要力求精密,就會對社會上一般思想和行動習慣:「也許還可由《紅樓夢》研究而影響其他學術思想界的風氣,甚至於中國社會政治的習慣」, 如 《紅樓夢案》前四篇論文都是強調研究曹紅學應有學術的思考精神與方法,還要建立《紅樓夢》文本解讀的文學目的,不是為考證而考證。老師認為「紅學」已是一門極時髦的「顯學」,易於普遍流傳,家喻戶曉,假如我們能在研究的態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點,也許整個學術研究,能形成一個詮釋學的典範;對社會上一般思想和行動習慣,都可能發生遠大的影響。他深痛惡絕長期以來的態度和方法:以訛傳訛,以誤證誤,使人浪費無比的精力。 比如發掘到的資料應該普遍公開。他舉胡適在一九二一年寫〈《紅樓夢》考證〉為例,考據根據的重要資料《四松堂集》,保密三十年才公開,另外他收藏的《乾隆甲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也是收藏了三十多年,不讓人利用。另外早年周汝昌主張脂硯齋就是史湘雲,並不是沒有能力看見別人反對自己的理由,而是不肯反對自己。
所以〈以五四超越五四〉(一九九一)那篇文章中,周老師反擊五四已經死忙的說法。五四運動不同於一般的歷史事件,五四是一種精神傳統,一種遺產,不會死亡。 他用可再充電的電池比喻五四精神:「所以五四有點像可以再充電的電池,即使時代變了,它還可能有它無比的感召力。」 這也就是為甚麼每年大家都紀念五四運動。
七、結論:永遠顛覆政治的霸權話語
我的老師生於一九一六,生前常說因為未趕得上親身參加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遊行,引以為憾。但少年時代在長沙就對五四感到興趣,在中學時自己成為罷課與學潮的核心人物,他的第一首新詩就是〈五四,我們對得住你了〉,寫於一九三五年:
五四,我們對得住你了
知識分子領導的「五四」與走向知識時代的「五四」
王潤華
一、離散/流亡與邊緣思考的「五四」論述:拒絕同化的多元透視力
周策縱教授(一九一六―二〇〇七) 曾寫自傳,題名〈忽值山河改:半個世紀半個「亡命者」的自白〉。他於一九四八年去國,乘輪船赴美途中,做舊詩〈去國〉(一九四八)抒懷,表明不滿混亂的時局與官場聽命的人生才出國深造,但是還未抵達彼岸,就感到「去國終成失乳兒」之苦,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日於美琪輪 (General Meigs) 上:
萬亂瘡痍欲語誰,卻攜紅淚赴洋西,
辭官仍作支床石,去國終成失乳兒。
抗議從違牛李外,史心平實馬班知,
吳門傾側難懸眼,碧海青天憾豈疑。
《五四運動史》(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第一稿是在一九五四年寫成, 一九五五年正式通過的密芝根大學政治系博士論文,根據《關於中國的博士論文》書目,原題為《五四運動及其對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影響(Th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Its Influence upon China’s Social-Political Development)。 周策縱於一九四八到美國,擬進入芝加哥大學,但由於不喜歡芝加哥城市,轉入密芝根大學政治系,一九五〇獲碩士,一九五五年獲得博士。在前後這年些間,他感到自己四處流亡,就如他的新舊詩集《周策縱詩存》與《胡說草:周策縱新詩全集》充分反映其心態,他的新詩〈給亡命者〉(一九五七)寫的也是自己:
像受了傷的野獸舔著創傷,
你鮮紅的血只滴向荒涼的地方。
為了潔白的生命而走向漆黑的死亡,
你高大的墓碑上將只剩著兩個大字:反抗。
他經歷過典型的放逐與流亡的生活,從打工到哈佛當研究員,漂泊不定的知識分子人的邊緣思考位置,遠離政治權力,建構客觀的透視力超強的五四的新論述。
這部論述使人不禁想起薩伊德 (Edward Said, 1935-2003) 所說的放逐詩學。這是一個全球作家自我放逐與流亡的大時代,多少作家移民到陌生與遙遠的土地。這些學者作家經歷真正家園的嚴重割裂,他們企圖擁抱本土文化傳統的同時,遇上與域外文化或西方中心文化的衝擊,給今日世界文學製造了巨大的創造力。 現代西方文化主要是流亡者、移民、難民的著作所構成。美國今天的學術、知識與美學界的思想正出自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的難民與其他政權的異議分子。整個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學與文化,簡直就是ET(extraterritorial)文學與文化。 知識分子原本就位居社會邊緣,遠離政治權力,置身於正統文化之外,這樣知識分子/作家才可以誠實的捍衛與批評社會,擁有令人歎為觀止的觀察力,遠在他人發現之前,他覺察出潮流與問題。古往今來,流亡者都有跨文化與跨國族的視野。 流亡作家可分成五類:一、從殖民或鄉下地方流亡到文化中心去寫作;二、遠離自己的國土,但沒有放棄自己的語言,目前在北美與歐洲的華文作家便是這一類;三、失去國土與語言的作家,世界各國的華人英文作家越來越多;四、華人散居族群,原殖民地移民及其代華文作家,東南亞最多這類作家;五、身體與地理上沒有離開國土,但精神上他是異鄉人。 無論出於自身願意還是強逼,思想上的流亡還是真正流亡,不管是移民、華裔(離散族群)、流亡、難民、華僑,在政治或文化上,他們都是置身邊緣,拒絕被同化。在思想上流亡的學者作家,他們生存在中間地帶(median state),永遠處在漂移狀態中,他們既拒絕認同新環境,又沒有完全與舊的切斷開,尷尬的困擾在半參與半遊移狀態中。他們一方面懷舊傷感,另一方面又善於應變或成為被放逐的人。遊移於局內人與局外人之間,他們焦慮不安、孤獨,四處探索,無所置身。這種流亡與邊緣的作家,就像漂泊不定的旅人或客人,愛感受新奇的事物。當邊緣作家看世界,他以過去的與目前互相參考比較,因此他不但不把問題孤立起來看,更有一種雙重的透視力(double perspective)。每種出現在新國家的景物,都會引起故國同樣景物的思考。因此任何思想與經驗都會用另一套來平衡思考,使新與舊的都用另一種全新、難以意料的眼光來審視。
在中國近代史上,沒有任何的重要事件像「五四運動」這樣複雜與容易惹起各種爭議。關於五四運動的書寫,在五十年代,爭論性的居多,沒有一本書被學術界接受,西方人對其認識更不正確,所以周策縱老師決定寫一本書確切記錄其史實,詳細探討其演變和效應。當他在密芝根大學寫博士論文時,便決定把五四看成一件多面性的社會政治事件去描述和研究,由於這是極端複雜而多爭論性的題目,他的指導老師也反對。根據他的回憶,在一九五二年的一天,他與密西根大學指導老師討論該生的博士論文選題時,提出如此的這建議。預想不到,教授提高了嗓門:「甚麼!你說你要寫『五四』運動,不行!博士論文怎麼可以寫學生暴動?……甚麼?說這是中國的文化運動、文藝復興、思想革命?簡直胡鬧!你若是堅持寫這個題目,我們就取消你的獎學金!」這位老師還曾在中國停留多年,因此他憤然而去。
《五四運動史》,原為博士論文,在完成前,一九五四年,周老師在哈佛大學歷史系任訪問學者寫論文,畢業後,一九五六至一九六〇又回返哈佛任研究員,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任榮譽研究員。所以哈佛學術研究氛圍與教授對他的五四學之建立,帶來極大的多元的啟發。像胡適(一八九一―一九六二)、洪業(洪煨蓮,一八九三―一九八〇)、楊聯陞(一九一四―一九九〇)、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 -1991) 、海陶瑋 (James Hightower, 1915-2006) 、史華慈 (Benjamin Schwartz, 1916-1999)、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1912-2007,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在哈佛)等人,他們這群多是流亡(洪業、楊聯陞)、,離散(史華慈猶太裔美國人)、多元文化(如費正清)。周教授原書英文版的《五四運動史》序文最後的一大段,感謝協助他完成論文撰寫、修改與出版的學者,目前所有中譯本將它刪去,非常可惜。這些精神思想導師,影響了老師的一生學術生涯。他們幾乎都是哈佛大學與美國的一流學者,很多來自中國與其他亞洲及歐洲漢學者,而且多是自我放逐、流亡的知識分子,他們位居社會邊緣,遠離政治權力,置身於正統文化之外。老師跨文化與跨國族的視野,令人歎為觀止的觀察力與他們的對話有絕對的密切關係。
二、周策縱的五四多元史觀:準確地認識過去,解釋未來
周老師回憶在哈佛大學改寫《五四運動史》時,當時哈佛的同事楊聯陞看見他不斷修改,就催他趕快出版:「我們現在著書,只求五十年內還能站的住,就了不起了。我看你這書可以達到這標凖。還擔心甚麼?」周老師回答說,由於五四是一個可以引起爭論的歷史,他要繼承中國古代史家的兩個優良傳統:「一個是臨文不諱,秉筆直書;另一個是不求得寵與當時,卻待了解於後世。」他又指出他當時寫歷史的態度,不但受了西洋歷史之父希羅多德 (Herodotus, BC 484-425) 之啟發,他的歷史觀要對過去有準確地認識,也可幫忙解釋可能發生類似的事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 的多元歷史觀與分析哲學(analytic philosophy)也影響了他對五四史實的詮釋。下面的自我回憶,可幫忙我們了解他的突破性的五四論述:
在美國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讀西洋哲學史、政治理論與制度和東西方歷史。一九五四年在哈佛大學當任訪問學者,寫完博士論文,對五四運動史化了不少時間和精力。這期間我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如何富強,如何吸收西洋的長處,推動現代化。一九五六年起再到哈佛人研究院五六年,在那裏的幾個圖書館的書,使我對中西漢學有了更多的認識,也使我的治學方向發生了又一次大轉變。
另外啟發周教授的五四史觀是《春秋公羊傳》裏的三句話:「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異辭。」這三句話使他對歷史產生兩個敏銳的觀察力。他說:「五四運動本身的複雜性,和後來個黨派的不同解釋,跟是請神參預者、所見者所聞者、所傳者,前後往往自相矛盾……我還是覺得最先的,當下的說辭較近於事實。這使我決定大量採用當時報刊的記載和個人『當下』的回憶」,對後來的說法和解釋決不得不審慎不懷疑。這也使我特別注意到「異辭」的問題。所以獨立思考,獨立判斷的認知是建構五四論述的基點。
三、超越中西文明典範的詮釋模式:文化研究典範
周策縱教授在一九四八年五月離開中國到密芝根大學攻讀政治學碩士與博士之前,已對中國社會、歷史、文化,包括古文字學有淵深精深的造詣。他的學術研究可說繼承了注重版本、目錄、注釋、考據的清代朴學的傳統,主張學問重史實依據,解讀由文字入手,以音韻通訓詁,以訓詁通義理。《周策縱古今語言文字考論集》中的〈說「尤」與蚩尤〉與〈「巫」字探源〉可說是這種治學方式的代表作。
周教授出國後的學術訓練,本文上面我引用他說過的話:「在美國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讀西洋哲學史、政治理論與制度和東西方歷史。」他受益最大該是以西方漢學的精神,突破了中國傳統思考方式。西方漢學的強點,專業性很強,研究深入細緻。周教授把中國傳統的考據學與西方漢學的治學方法與精神結合成一體,這種跨國界的文化視野,就給中國的人文學術帶來全新的詮釋與世界性的意義。例如初稿於一九六七,完成於一九九九的六萬多字的論文〈扶桑為榕樹縱考〉,周老師為了考定扶桑就是榕樹,考釋古代神話、圖畫、出土文物、古文字中認定、又從歷史、文化中去觀察,舉凡文學、植物學、文字學的學識都廣泛深入的溝通,另外也前往世界各地觀察與攝影有關植物。這種跨知識領域的文化研究,是既典型又前衛。
周教授當時編輯的兩本《文林:中國人文研究》(Wen Lin: Studies in the Chinese Humanities)的學術研究, 代表當時他自己主導的歐美漢學家的跨越學科、知識整合的學術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向,所以他實際上要建構的就是目前所謂文化研究的前行者。
而美國學術界則自二次大戰以來,開發出一條與西方傳統漢學很不同的研究路向,這種研究中國的新潮流叫中國學(Chinese Studies),它與前面的漢學傳統有許多不同之處,它很強調中國研究與現實有相關,側重思想性與實用性,強調研究當代中國問題。這種學問希望達到西方了解中國,與中國了解西方的目的。 中國研究是在區域研究(Area Studies)興起的帶動下從邊緣走向主流。區域研究的興起,是因為專業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的解釋模式基本上是以西方文明為典範而發展出來的,對其他文化所碰到的課題涵蓋與詮釋性不夠。對中國文化研究而言,傳統的中國解釋模式因為只用中國文明為典範而演繹出來的理論模式,如性別與文學問題,那是以前任何專業都不可能單獨顧及和詮釋。在西方,特別是美國,從中國研究到中國文學,甚至縮小到更專業的領域中國現代文學或世界華文文學,都是在區域研究與專業研究衝激下的學術大思潮所產生的多元取向的學術思考與方法,它幫助學者把課題開拓與深化,創新理論與詮釋模式,溝通世界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上述「中國學」的這種研究中國的新潮流的發展,哈佛大學便是其中一個重要中心,到了一九五〇年代,正式形成主流。周教授在這期間,也正好在哈佛擔任研究員, 他的成名作《五四運動史》,原是密芝根大學的博士論文《五四運動及其對中國社會政治發展的影響》,獲得博士學位不久後,費正清聘他到哈佛東亞問題研究中心從事研究,其中重要的研究項目就是改寫他的五四論述的論文,同時期在哈佛共事的還有洪業、楊聯陞、裘開明(一八九八至一九七七)、費正清、史華慈等,在這些中西學者的「內識」和「外識」的跨學科多元文化與思想的學術環境中,在傳統的西方漢學 (Sinology)與新起的中國研究(Chinese Studies)學術思潮中,修改完成並出版他的五四論述。此類專著或論文,完全符合中國研究與現實有相關,思想性與實用性,強調研究當代中國問題以溝通東西文化的了解的傾向。另一方面,區域/文化研究思潮也使本書超越以西方文明為典範而發展出來的專業領域如社會學、政治學、文學的解釋模式,同時更突破只用中國文明為典範而演繹出來的傳統的中國解釋模式。所以《五四運動史》成為至今詮釋五四對權威的著作,成了東西方知識界認識現代新思文化運動的一本入門書,也是今天所謂文化研究的典範。
《五四運動史》對中國社會、政治、思想、文化、文學和歷史提出系統的觀察和論斷。奠定了作者在歐美中國研究界的大師地位。這本書使用大量原始史料,包括中、日、西方語文的原始檔案,形成窄而深的史學專 (monograph) 思想文化專題的典範著作。周教授研究《五四運動史》中所搜集到的資料本身,就提供與開拓後來的學者研究現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文學個領域的基礎。因此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也將其出版成書《五四運動研究資料》 (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另外本書所體現的不涉及道德判斷或感情偏向,就凸顯出客觀史學(現實主義史學)的特質。周教授在密芝根大學念的碩士與博士都是政治學,因此社會科學(政治、社會、經濟學等)建構了他的現實客觀的歷史觀,這正是當時西方的主流史學,這點與費正清的社會科學主導的客觀史學很相似。 而且被奉為在中國研究中,跨越知識領域研究、文化研究最早的研究典範,也是最具國際性、知識領域廣泛性的影響力的專論。
到了七十年代,文化研究領域開啟了之後,文化研究開始成為重要學術潮流,文化研究者跨越學科,結合了傳統社會學、文學、政治、與及新起的國族問題,來研究現代社會中的複雜文化現象。在《五四運動史》中,周老師已是全面執行文化研究者的思考與方法,時常關注某個現像是如何與意識形態、國族、社會階級與/或性別等議題產生關連。譬如國際民族主義權威謝佛(Boyd C. Shafer)的《民族主義的各種面貌:新現實與就神話》(Faces of Nationalism: New Realities and Old Myths),認為國際化日益重要,但國家民族仍然重要,他引用周策縱有關中國五四運動建立的國家民族主義以抵抗外國的侵略,保護領土完整作為重要證據。 文化研究的「文本」(text)不只是書寫下來的文字,還包括了口頭訪問、檔案、攝影、報紙、期刊、分析研究的文本物件包含了所有意義的文化產物。他又特別審視文化活動與權力的關係。所以他一生堅持五四是社會政治邊緣的知識分子領導的:
二十年代中葉以後,兩大勢力黨團本身也逐漸被少數領導者所控制,各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利益來解釋務實運動,以便奪取政權,支持和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和威權。於是五四運動對自由、民主、科學、人權的熱烈號召,對權威壓迫的強烈抗議精神,就逐步給掩蓋抹殺了。
由於文化研究是研究的客體,同時也是政治批評與政治行動的場域,所以周教授自己最後了解到,「野心家打著五四旗號來掩飾五四,利用五四,於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就看不到五四的真正史實,於是我的《五四運動史》也就殃及魚池般在中國本土成為「禁書」大二三十年之久了。」
四、一九一七―一九二一與知識分子主導的「五四運動」
如上所述,早在一九五〇年代,周教授敢以薩伊德所謂「邊緣思考」的透視力把五四定義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的知識分子領導運動,引起極大的爭議,尤其在大陸、台灣官方或具有政治傾向的學人在八十年代都難於接受。像周老師這些邊緣思考的學者與國土,自我與真正家園的嚴重割裂,企圖擁抱本土文化傳統與域外文化,又受西方中心文化的衝擊。知識分子原本就位居社會邊緣,遠離政治權力,置身於正統文化之外,擁有令人歎為觀止的觀察力,遠在他人發現之前,他已覺察出潮流與問題。古往今來,流亡者都有跨文化與跨國族的視野。在政治或文化上,他們都是置身邊緣,拒絕被同化。
周老師的英文原著書名是The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扉頁上自題中文書名是《五四運動史》。英文書名中的Intellectual Revolution 沒有標準的翻譯,可解作「思想革命」或「知識革命」,其實英文Intellectual Revolution包含兩者。他認為五四的啟蒙一切從知開始:
這「知」字自然不只指「知識」,也不限於「思想」,而是包含一切「理性」的成分。不僅如此,由於這是用來兼指這是「知識分子」所領導的運動,因此也不免包含有行動的意思。
所以五四的重要性在於青年知識分子抗議精神和對政治組織、社會制度、倫理思想和文化文學改革。在這個前提下,
對傳統重新估價以創造一種新文化,而這種工作須從思想知識上改革著手:用理智來說服,用邏輯推理來代替盲目的倫理教條,破壞偶像,解放個性,發展獨立思考,以開創合理的未來社會。
周教授把五四定義為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年的知識分子領導運動,他特別指出:
一九二四以後,中國兩大政黨受了蘇聯的影響,吸引知識分子參加無力革命,拋棄了「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風。我認為這是扭曲和出賣了一個性解放、人道主義、自由、民主、科學思想為主軸的「五四精神」。
他斷定五四運動時期主要為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一年,因為一九二四年以後,中國兩大政黨受了蘇聯的影響,吸引知識分子革命,拋棄五四早期思想文化革新的理想和作風,他認為那是扭曲了五四精神。 他堅持的論點,至今為國際學術界所重視。但是卻被在大陸與台灣的官方與主流學術界所難於接受:五四是知識分子所主導的,是一項多面性的社會政治文化思想的啟蒙運動,大前提是對傳統重新估價以創新一種新文化,而這種工作須從思想知識上改革著手,用理智來說服,用邏輯推論來代替盲目的倫理教條,破壞偶像。解放個性,發展獨立思考,以開創合理的未來社會。五四思潮不是反傳統主義,而是革新知識,拋棄不好的傳統。因為它提倡理智和知識,現在五四精神仍然重要,因為它引導中國走向未來的知識時代。
在《五四運動史》中的時限的斷定,都非常的審慎,而且多元化。他在一九九一年的演講中,再次的解釋:
至於「五四運動」的時限,我在書中曾指出,當時的思想轉變與學生活動,主要集中於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一,這五年之間;不過,我同時也強調,這個運動不應限制在這五年,最低限度可以擴充為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四這十年,因而我早在哈佛出版的第二本書《五四運動研究資料史》時,索性把標題示為一九一五到一九二四。我之所以把五四運動的下限,主要是因為是年國共正式合作,著手一物力和黨的組織推翻北洋政府,所牽涉的是隕石雨黨派鬥爭,與知識分子領導的思想運動已有所區別。這項轉變及其重要,「五四 」潮流後來所以未能順利發展,便是遭到此一阻礙。
重讀《五四運動史》,我發現老師的論述嚴謹細密,時限因應論述的課題而改變,請看下面第一章「導論」內文,很明確的鎖定五四運動為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請看下面幾章的年代:
第二章「促成「五四運動」的力量(一九一五―一九一八)
第三章 運動的萌芽階段:早期的文學和思想活動(一九一七―一九一八)
第七章 新文化運動的擴展(一九一九―一九二〇)
第九章 觀念上和政治上的分裂(一九一九―一九二一)
第十章 社會政治的演變結果(一九一九―一九二二)
另外書後附錄的「相關大事表(一九一四―一九二三)」,他把時限拉得更長。所以他以五四的複雜多面向的演變而考慮時限的適當性,這是當時哈佛大學費正清及其他學者所強調的客觀史學。
他堅持的論點,至今為國際學術界所重視,包括台灣大陸的學術界。無論研究社會文化、政治思想、文學藝術的著作,幾乎很少不會引用到這本具有一家之言的有關五四的權威的著作。
五、五四精神:引導中國走向知識時代
周教授在五〇年代已洞見新知識分子與新知識的重要性。單單從《五四運動史》中各章節的題目,就可見討論新知識分子與新知識的篇幅占了很多。 第三章有「新知識分子的聯合與《新潮》雜誌的創辦」、「新知識分子改革的觀點」,第七章有「新知識分子之間團結的增加」、「新知識的、新社會的、和新政治的團體」、「新知識分子所宣導的大眾教育」更重要,他全書的結論認定五四運動最終目的是獲得新思想與知識的革命。這就是所謂intellectual revolution :「五四不僅是思想知識的,同時也是政治和社會改革運動,即追求國家的獨立、個人的自由、公平的社會和的現代化中國。而本質上就是廣義的新知識思想的革命.所以說它是思想知識革命,因為思想知識的改變才能帶來現代化,它能促成思想知識的覺醒與轉型,同時這是知識分子領導的運動。」
五四至今已一百年。中國與世界,在數碼科技的推動下,已發生極大的轉型與變動。五四的精神主軸,為知識分子選擇以思想文化革新作為救國的途徑。所以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更理解到五四運動還有無比的感召力,因為五四提倡理智和知識,今天世界已進入知識時代,一九九五年周老師寫道:
五四提倡理智和知識,是最適合現代新潮流的趨勢。二十世紀有蒸汽文明進展到電力文明,有原子能文明到電子文明,資訊文明。在可見的將來,在可見的將來,在二十一世紀,高科技的地位越來越提高。我們對財產的觀念也初見改變和擴張了。過去計算財富的要素是土地、勞力、物資和資本,現在和將來,「知識」(knowledge)必定成為最重要的「財富」(wealth)。
經濟早已轉型,從投資經濟變成知識創新經濟,從機器生產與勞動力的社會逐漸轉型為知識社會,新知識經濟裏,整合知識、創新思考是主要資源。這種多元知識專才,在目前社會裏,會成為社會,甚至政治的主導力量。《五四運動史》在一九五五初稿就完成,周教授的詮釋力與洞察力,令人驚訝。
現在再讀《五四運動史》的第七章「新文化運動的擴展(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周老師特別不斷強調新知識分子及其領導的「新文化運動」。他引用陳獨秀在一九一九年九月從監獄中釋放,劉半農寫一手長詩的兩句,意義非凡:「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他們都入監獄,監獄便成了研究室」。 這裏「研究室」便是知識最好的象徵。美國及西方國家,一百年來,大學的研究室,尤其實驗室通宵燈火通明,學者天天如坐牢,所以今天他們開拓了知識經濟的時代。他也引用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論文〈新文化在中國〉(New Culture in China) 中的話說,中國要富強,「沒有新思想知識運動是不能到達到的」(that is impossible without the intellectual movement) 像這樣的話語,落在過於思想意識形態教育大陸,就被簡單化的譯成「而沒有新思想運動」 ,老師一再的強調「五四不僅是學術上,同時也是政治和社會上的改革運動,及是國家的獨立、個人的自由和中國的現代化,而以學術為首」。
老師早年的學問從版本、目錄、注釋、考據的清代朴學的傳統,主張學問重史實依據,解讀由文字入手,以音韻通訓詁,以訓詁通義理。受過政治學的嚴格訓練,也就是社會學的精密分析方法,轉型到歷史,他不僅重視史實之考證,事事詳加比對求證,更要求解釋,給予史實應有的含義,因此《五四運動史》又具有史華慈的思想史學的特點,在複雜的歷史事件中,尋找沒有時間性的鑰匙與價值。中國的現代化與知識,在《五四運動史》是同義詞。如果我們細心的閱讀《五四運動史》,他的書名intellectual,雖包含思想,主要指知識 (knowledge)與知識分子(intellectual),全書「新知識分子」或「新知識」不斷重複出現在章節的標題上,如第三章的「新知識分子的聯合與《新潮》雜誌的創辦」,「新知識分子的改革觀點」。不但書名有intellectual,書後半部的總題是Analysis of Main Intellectual Currents。這些intellectual 主要是知識分子或知識。書中真正指思想的時候,用的是thought, 如十二十三章都用「新思想」 (new thought),因為這是知識分子領導的運動,這個文化運動最重要的目標就是以知識建立現代化的中國。
六、五四超越五四精神遺產
周老師的研究與論述,從政治學到史學,然後再做文學與語言文字。晚年回憶他的治學路程,如下面一九九七年為《棄園文萃》寫的〈序〉,承認撰寫五四期間用功最深:
在美國的前五年,我多半研讀西洋哲學史、政治理論與制度和東西方歷史。一九五四年在哈佛大學擔任訪問學者,寫完博士論文,對五四運動史花了不少時間和精力。這期間我最關心的問題是中國如何富強,如何吸收西洋的長處,推動現代化。一九五六年起再到哈佛人研究院五六年,在那裏的幾個圖書館的書,使我對中西漢學有了更多的認識,也使我的治學方向發生了由一次大轉變。
他在美國的學術經驗,深深的認識到中國人的思維方式有很大的缺失。其一是認知意識不夠發達。對邏輯推理不夠精密,在實際議論時不能嚴密運用三段論法(syllogism),把是非當作道德。他在《棄園文萃》的序文裏接著上面引述的那段,指出:
由於讀了更多的外語,使我深深感到,從古代起,我們中國人的思維方式不免有兩個最基本的缺失:一個是邏輯推理不夠精密,尤其在實際議論時不能嚴密運用「三段論法」(syllogism)。另一個缺失看來很簡單,卻可能更基本,我們對「認知」的意識不夠發達。就是對「是」甚麼,「不是」甚麼不夠重視。從先秦起,「是非」就逐漸變成道德詞彙,不是指實之詞了。「是」、「為」、「乃」作為指實詞,用得很不普遍和明確。漢語動詞作名詞用自然太多了,可是「是」作為to be或being意義用作名詞者,恐怕古代並不多見。我只不過用這個例子來說明,我們傳統上「認知」是甚麼不是甚麼的意識,發達得可能不充分。這兩點是我去國五十年來的痛切感覺,對不對自然是另一問題,但對我後來的治學研究,關係不小。
於是我認為,對中西文明、思想和制度等,我們認知得還很不夠。甚至連中國的古代經典、文學作品,以至於古代文字和古今歷史事實,都應該切實認知一番,才能夠加以評判。
另外他又說:
歐美的文明,除宗教的思想之外,主要比較重視邏輯推理,考察自然規律,也就是客觀的知識;中國至少自秦漢以後,所發展的乃是偏重倫理道德、修齊統治的文明。
所以他的結論:「這種尚知的新作風,應該是中國文明史上綴重大的轉捩點」:
這裏所說的「知」,是指對客觀實在認知的知,是純粹邏輯推理的知。是指探索「是甚麼」、「為甚麼」、和「如何」的知,不是教人「應該如何」的道德教導。當然,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對這些並未能完全好好做到,但有許多人有這種嚮往,那就仍可說是劃時代的了。這也不是說道德不重要,只是說,五四思潮補救了傳統之偏失。
周教授一生的學術研究研究與文學創作就是建立在五四思想革新的認知上,比如研究《紅樓夢》,他就指出紅學的研究態度和方法要力求精密,就會對社會上一般思想和行動習慣:「也許還可由《紅樓夢》研究而影響其他學術思想界的風氣,甚至於中國社會政治的習慣」, 如 《紅樓夢案》前四篇論文都是強調研究曹紅學應有學術的思考精神與方法,還要建立《紅樓夢》文本解讀的文學目的,不是為考證而考證。老師認為「紅學」已是一門極時髦的「顯學」,易於普遍流傳,家喻戶曉,假如我們能在研究的態度和方法上力求精密一點,也許整個學術研究,能形成一個詮釋學的典範;對社會上一般思想和行動習慣,都可能發生遠大的影響。他深痛惡絕長期以來的態度和方法:以訛傳訛,以誤證誤,使人浪費無比的精力。 比如發掘到的資料應該普遍公開。他舉胡適在一九二一年寫〈《紅樓夢》考證〉為例,考據根據的重要資料《四松堂集》,保密三十年才公開,另外他收藏的《乾隆甲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也是收藏了三十多年,不讓人利用。另外早年周汝昌主張脂硯齋就是史湘雲,並不是沒有能力看見別人反對自己的理由,而是不肯反對自己。
所以〈以五四超越五四〉(一九九一)那篇文章中,周老師反擊五四已經死忙的說法。五四運動不同於一般的歷史事件,五四是一種精神傳統,一種遺產,不會死亡。 他用可再充電的電池比喻五四精神:「所以五四有點像可以再充電的電池,即使時代變了,它還可能有它無比的感召力。」 這也就是為甚麼每年大家都紀念五四運動。
七、結論:永遠顛覆政治的霸權話語
我的老師生於一九一六,生前常說因為未趕得上親身參加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的遊行,引以為憾。但少年時代在長沙就對五四感到興趣,在中學時自己成為罷課與學潮的核心人物,他的第一首新詩就是〈五四,我們對得住你了〉,寫於一九三五年:
五四,我們對得住你了
目次
目錄
周策縱的「五四學」:知識分子領導的「五四」與走向知識時代的「五四」
認知.評估.再充――香港再版《五四運動史》自序
第一章 導言
第二章 促成「五四運動」的力量(一九一五―一九一八)
第三章 運動的萌芽階段:早期的文學和思想活動(一九一七――一九一九)
第四章 「五四事件」
第五章 事件的發展:學生示威與罷課
第六章 更進一步的發展:工商界及勞工界的支持
第七章 新文化運動的擴展
周策縱的「五四學」:知識分子領導的「五四」與走向知識時代的「五四」
認知.評估.再充――香港再版《五四運動史》自序
第一章 導言
第二章 促成「五四運動」的力量(一九一五―一九一八)
第三章 運動的萌芽階段:早期的文學和思想活動(一九一七――一九一九)
第四章 「五四事件」
第五章 事件的發展:學生示威與罷課
第六章 更進一步的發展:工商界及勞工界的支持
第七章 新文化運動的擴展
書摘/試閱
第一章 導言
一、「五四運動」的定義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國學生在北京遊行示威,抗議中國政府對日本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連串的罷課、罷市、罷工及其他事件,終於造成整個社會的變動和思想界的革命。沒過多久,學生們就替這新起的時代潮流起了個名字「五四運動」;後來這個名詞的內涵卻隨著時間演進比當初大大地擴充了。
本書所說的「五四運動」便是就這廣義而言。大體來說,這個運動的主要事件發生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之間;現在先把它的經過簡述如下。由於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會作出東山決議案,激起中國民眾高漲的愛國和反抗列強的情緒,中國學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領袖們得到了這種群眾情緒的支持,發起一連串的抗日活動,和一項大規模的現代化運動,希望通過思想改革、社會改革來建設一個新中國。他們最著重提倡的是西方的科學和民主觀念。而中國傳統的倫理教條、風俗習慣、文學、歷史、哲學、宗教,以及社會和政治制度,都遭受到猛烈攻擊。這些攻擊的動力多是從西洋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實用主義(pragmatism)、功利主義(utilitariansm)、無政府主義(anarchism),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socialism)思想而來。五月四日的抗議示威則是發展成這一連串活動的轉捩點。新起的商人、工業和城市工人隨即都對這次示威的目的表示同情和支持,終於逼使北京政府讓步,改變內政和外交政策。這次前所未有的大聯合獲得的勝利,為他們所鼓吹的文化、思想鋪了一條路。但是以後不久,運動逐漸捲入政治漩渦,終於使這新知識分子的聯合陣線崩潰了。那些自由主義者不是失去了熱情,就是裹足避免參加政治活動;相反地,左翼分子則採取了政治捷徑,聯合國民黨,以推翻北京的軍閥政府。西方諸國對這運動的態度從此由同情轉變為疑慮或反對,他們態度的轉變也是促使運動分裂的一個主要因素。此後,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越來越得勢,無數複雜難解的爭執紛然競起。
「五四運動」的影響很廣。它促使學生運動和勞工運動抬頭,國民黨改組,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政治、社會集團誕生。反軍閥主義和反帝國主義得到發展,新的白話文學從此建立,而群眾的普及教育也因此大為推廣,中國的出版業和民眾輿論的力量都大有進展。此外,這運動還加快了舊家庭制度的沒落和女權運動的興起。而「五四運動」的至巨影響還是:儒教的無上權威和傳統的倫理觀念遭受到基本致命的打擊,輸入的西方思想則大受推崇。
起初學生們和出版物所採用的「五四運動」一詞並不包括所有上面列舉的事件,它僅僅指五月四日北京的學生示威運動,同樣地,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及以後所發生的大拘捕則被稱為「六三運動」。隨後幾年,一般人提到「五四運動」時,固然並不一定都會有意識地採取這種狹隘的看法;但是他們也往往把整個運動和「五四事件」及其本身與後果混為一談。因此,在過去許多例子裏都可見到「五四運動」一詞和「五四事件」被交替使用。
一、「五四運動」的定義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中國學生在北京遊行示威,抗議中國政府對日本的屈辱政策。由此引起一連串的罷課、罷市、罷工及其他事件,終於造成整個社會的變動和思想界的革命。沒過多久,學生們就替這新起的時代潮流起了個名字「五四運動」;後來這個名詞的內涵卻隨著時間演進比當初大大地擴充了。
本書所說的「五四運動」便是就這廣義而言。大體來說,這個運動的主要事件發生在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二一年之間;現在先把它的經過簡述如下。由於一九一五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會作出東山決議案,激起中國民眾高漲的愛國和反抗列強的情緒,中國學生和新起的思想界領袖們得到了這種群眾情緒的支持,發起一連串的抗日活動,和一項大規模的現代化運動,希望通過思想改革、社會改革來建設一個新中國。他們最著重提倡的是西方的科學和民主觀念。而中國傳統的倫理教條、風俗習慣、文學、歷史、哲學、宗教,以及社會和政治制度,都遭受到猛烈攻擊。這些攻擊的動力多是從西洋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實用主義(pragmatism)、功利主義(utilitariansm)、無政府主義(anarchism),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主義(socialism)思想而來。五月四日的抗議示威則是發展成這一連串活動的轉捩點。新起的商人、工業和城市工人隨即都對這次示威的目的表示同情和支持,終於逼使北京政府讓步,改變內政和外交政策。這次前所未有的大聯合獲得的勝利,為他們所鼓吹的文化、思想鋪了一條路。但是以後不久,運動逐漸捲入政治漩渦,終於使這新知識分子的聯合陣線崩潰了。那些自由主義者不是失去了熱情,就是裹足避免參加政治活動;相反地,左翼分子則採取了政治捷徑,聯合國民黨,以推翻北京的軍閥政府。西方諸國對這運動的態度從此由同情轉變為疑慮或反對,他們態度的轉變也是促使運動分裂的一個主要因素。此後,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越來越得勢,無數複雜難解的爭執紛然競起。
「五四運動」的影響很廣。它促使學生運動和勞工運動抬頭,國民黨改組,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政治、社會集團誕生。反軍閥主義和反帝國主義得到發展,新的白話文學從此建立,而群眾的普及教育也因此大為推廣,中國的出版業和民眾輿論的力量都大有進展。此外,這運動還加快了舊家庭制度的沒落和女權運動的興起。而「五四運動」的至巨影響還是:儒教的無上權威和傳統的倫理觀念遭受到基本致命的打擊,輸入的西方思想則大受推崇。
起初學生們和出版物所採用的「五四運動」一詞並不包括所有上面列舉的事件,它僅僅指五月四日北京的學生示威運動,同樣地,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及以後所發生的大拘捕則被稱為「六三運動」。隨後幾年,一般人提到「五四運動」時,固然並不一定都會有意識地採取這種狹隘的看法;但是他們也往往把整個運動和「五四事件」及其本身與後果混為一談。因此,在過去許多例子裏都可見到「五四運動」一詞和「五四事件」被交替使用。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