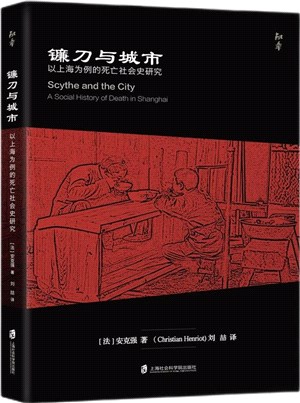鐮刀與城市:以上海為例的死亡社會史研究(簡體書)
商品資訊
ISBN13:9787552028348
出版社: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作者:(法)安克強
譯者:劉喆
出版日:2022/01/01
裝訂/頁數:平裝/402頁
規格:24cm*17cm (高/寬)
版次:一版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
艾克斯·馬賽大學亞洲研究系的歷史學教授,法國著名的漢學家,國際知名的上海史專家。先後畢業於美國斯坦福大學(歷史學碩士,1982年),索邦大學(1983年,歷史學博士學位)和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EHESS,1992年國家博士學位)。他是《歐洲東亞研究雜志》的創始人之一,也是法國裡昂大學東亞學院的創建人。他曾多次擔任美國各大學(斯坦福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俄勒岡大學)的客座教授,並曾獲得著名的斯坦福人文中心頒發的“數字人文獎學金”(2006-2007年)。還曾獲得德國“洪堡基金”等多項榮譽。
他的研究主要集中於上海史、影像史和數字歷史,目前已出版了十余本研究著述,包括《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和性》(1997年);《上海地圖集:1849年至今的空間和表象》(1999年);《新前沿:帝國主義在東亞的新社區》(2000年);《朝陽下的陰影:上海在日本占領時期)》(2004年);《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權、地方性和現代化》(2004年被譯為中文出版);《可視化中國:歷史敘事中的圖像》(2012年);《歷史中的圖像:近代中國的圖像與公共空間》(2012年);《上海人口史1865—1953年:一本資料匯編》(2018)等。
他長期從事數字歷史研究,並創建了一個國際影響頗大的視覺上海(Virtual Shanghai)網站,這是一個從19世紀中葉至今有關上海歷史的資源平臺。該平臺系統收集了有關上海的原始檔案、歷史照片、歷史地圖、原始數據等各類珍貴史料和研究性論著等文獻,方便學者、學生和廣大史學愛好者使用。該平臺還使用了功能強大的WebGIS制圖工具,用於空間分析和實時地圖繪製,這有助於從技術層面推進數字歷史的發展。
名人/編輯推薦
死亡,令人畏懼,又無法避免。作者在本書中選擇了一個司空見慣,但從未引起學界注意的物件——死亡,作為考察的物件。
死亡是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話題,卻少見嚴謹的學術分析。
當傳統的中國喪葬習俗遭遇現代化的城市管理,又產生了怎樣的火花?
在上海繁華的另一面,也許是我們從未見到的陰暗和沉重。
序
中文版序
研究死亡對歷史學家來說為什麼重要?因為死亡在歷史研究中比比皆是。除非是考察更接近現在的時期,歷史學家研究過去,主要是同那些永遠消失在歷史長河裡的社會角色打交道。說到底,歷史學家始終在同死亡打交道。歷史學著作中不時遭遇死亡——戰爭、叛亂、謀殺、刺殺、行刑、自裁、疾病、瘟疫、饑荒等諸多事件,給歷史學領域留下一地尸體。但是,這些都是死亡的具象表達,是實實在在的個體或集體的死亡。這無關死亡本身,而關乎一個社會在歷史上如何構建對死亡的感知和表征,關乎怎樣處置那些死者。
許多讀者可能會覺得死亡不是個討喜的話題。的確,死亡會喚醒對不安瞬間的記憶,譬如親近之人的離世,但最重要的是,死亡對於任何人都是不確定和無可避免的。死亡是不可知的人類存在狀態,無論科學還是宗教都改變不了這一宿命,不過兩者都以各自的方式為慰藉我們盡了份力。科學改善我們的健康,延長我們的壽命;而宗教就生死的意義提供給我們一系列關於靈魂的信念。本書並不傳達諸如此類的抽象理念,而是探索作為社會經歷的死亡,即中國城市社會如何自我組織和應對日常生活中持續存在且增長中的死亡人口。
死亡不僅事關個體。它關乎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如何界定概念、規則和習俗——如何超度亡靈的儀式,它們構成對待死者的個人信念和處置標準。根植於遙遠的過去,中國文化展現了非常豐富的殯葬習俗。這些習俗堅持一條不動底線(如土葬),同時允許跨空間(地區差異)、跨時間(從晚清至20世紀60年代早期)的不同適應性做法。譬如在上海,這座城市集中了全中國,乃至全世界的人。據1935年的記載,超過52個國家的人來到上海。因而,各種信仰匯聚於上海,也各自有一套殯葬禮儀和專用墓地。
本書試圖闡述死亡在近現代中國城市社會中的意義,以上海為考察背景,借助文獻說明一個多世紀來,死亡對個人、私人及公共機構,乃至商業的意義。盡管農村的喪葬流程和習俗勢必發生了改變,但在城市,特別是上海這樣的大都市,巨大人口帶來同樣巨大的死亡人口,對於喪葬必然需要特殊形式的組織及社會和文化上的適應性做法。充沛的史料使上海成為考察這些變化的絕佳切入點。
我數年前寫作此書時,把死亡作為歷史研究物件的中文著作尚未問世。這完全不令人驚訝,因為在我自己對上海的死亡研究中,就已發現中國社會設計了精巧的社會腳本,如姿勢儀式、規則等,與死亡保持距離,以保護生者不受影響,或更糟糕的情況——不被死亡吞沒。近現代中國城市社會對死亡有一種特殊的敏感,即便時至今日仍敬而遠之。在我寫這篇中文版序,搜尋以死亡為主題的中文參考文獻時,我逐漸意識到中國史學家尚未涉足此領域,以至於我無功而返。但我希望出版這本書的中文版能引發學界對這一話題的興趣。中國死亡史應該有它的“菲利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es)。
手稿完成時,我沒太想好起什麼書名。我猶豫的不只是什麼標題能最好地概括這本書的內容,而是展現自己想研究這個主題的學術根源。前言部分,我論述了我從研究史料中的視覺文獻轉為研究發生在上海的死亡的過程。其中既有機遇也有時機。當然,我對中日戰爭時期的研究工作讓我得以仔細審視上海這座城市面對的死亡問題。20世紀20年代晚期到20世紀30年代,戰爭多次席卷上海。1937年,日軍在上海發起了毀滅性的進攻,不僅大量士兵陣亡,也有許許多多市民喪生。但從某種角度來說,這些特殊死者和數量巨大的死亡人口多少掩蓋了更多普通人的正常死亡。然而,從過去的市政當局和城市組織(行會、慈善團體)獲取到的豐富檔案卻反映了很不一樣的情況。這可謂真正的認知覺醒。
我最初想給這本書取名“Death in Shanghai”。這個名字簡單明了,卻是我通過文獻和影像一瞥這座城市裡發生的死亡所產生的深深共鳴。當我漫步於冷酷的史料,盧基諾·維斯康蒂(Luchino Visconti)的名作《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裡的畫面閃現在了我的腦海中。電影自1971年上映以來,我看過很多遍。維斯康蒂的電影故事發生在一座深陷霍亂疫情的城市,而近現代上海也曾遭受數次嚴重的霍亂疫情。我著迷於《魂斷威尼斯》(Death in Venice)還有更深的原因。這部電影使我回想起同一時期我在讀的一部小說,加繆的《鼠疫》,至今我都對這本書印象深刻。書裡也講了一個事關可怕霍亂瘟疫的故事,故事發生在阿爾及利亞的奧蘭。小說和電影都傳達了面對疾病和瘟疫,個體改變自身命運的無力。這也是上海的大量個體所面對的殘酷命運,在危急時期特別是戰爭時期,這種殘酷達到了非人的程度。即便在和平時期,許多平民悄無聲息地逝去,他們很少有,甚至幾乎沒有資源,尤其是兒童,也不指望能有體面的下葬。
在近代上海,普通人很難掌控自己的生活。當死亡來臨,大多數人依賴於各種組織——慈善團體、公館會所——來提供雖然很基本但合乎體統的下葬。本地只有一小部分人付得起殯葬店及稍晚出現的商業公司的服務費,來組織更為複雜的葬禮,同時彰顯其精英身份。在窮人中,瘟疫或戰爭如一柄巨刃結束數以千計的生命。對於他們,死亡代表對肉體徹頭徹尾的無能為力與剝奪。他們被清掃出城市,埋葬在偏遠、無名的墳地。這幅景象,大量犧牲者靜靜地、無足輕重地死去,最終說服我回到歐洲文化中死亡的經典意象——鐮刀,既是用來收獲糧食的農具,更是死亡降臨最強烈的象徵。鐮刀在中國文化中並不能引起這樣的共鳴,但我估計讀者也能理解《欲望都市》(Sex and the City)的引喻,這啟發我最終定下了書名。
很榮幸看到這本書的中文版出版,我也希望它能吸引到中國的歷史學界、歷史學家和學生。我想感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同意出版本書的中文版。
我要特別感謝我曾經的學生——劉喆,承擔了把手稿譯成中文的艱巨任務。他出色地完成了譯稿。
最後,這些年我在研究上海的死亡社會歷史時,很幸運馬軍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他是位杰出的歷史學家;還有我的許多學生,他們熱情投入了“檔案助手”的工作,他們是: 蔣杰、劉喆、趙偉清、徐翀。
目次
中文版序
前言
第一章死神與上海: 評估死亡
第二章會館、善會和同鄉社團對死亡的管理
第三章殯葬公司和死尸處理的商業化
第四章最後的安息之所: 從墳地到現代墓地
第五章外國公墓和租界中的死亡
第六章死無人知
第七章死亡的代價與葬禮
第八章火葬: 從社會詛咒到政治規定
第九章社會主義時期的死亡管理
結論
注釋
參考文獻
書摘/試閱
前言
本書誕生並不在計劃中,或者說,它是一個意外的產物。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把注意力放在死亡研究這樣一個選題上。就像我許多同仁那樣,我可以追溯一些指引我選擇各種歷史問題進行研究並最終將其成書的潛在力量,即便這些選擇既不是有意為之也不是深思熟慮的結果。我對於戰爭的研究和我的家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下簡稱“二戰”)中的經歷背景產生了共鳴。對於妓女、難民、貧民窟居民和其他一些社會上的無名之輩的研究,則很可能和我成長在由辛勤工作的體力勞動者所組成的多文化環境有關。這本書獻給那些哺育我成人的長輩們,但和任何人的經歷無關。
起初,我涉入上海的死亡研究是和葉文心教授(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以及和一系列我在2003年起開始組織的歷史工作坊和視覺史料有關。在2004年東京召開的第二次會議上,我們將“身體”作為工作坊的主題。由於當時我的研究主題集中於二戰時的上海,士兵遺體的視覺呈現提供了一個研究的潛在路徑。我對出於宣傳需要而特制的、那些軍事行動中的士兵形象並無興趣,我的研究焦點是遭受苦難的身體、戰爭給人所帶來的痛楚和傷痕、戰鬥中的死亡以及戰爭記憶。我對檔案館的第一次“掃蕩”,除了1937年大屠殺的巨大傷亡資料之外,只找到了很少的軍事死亡資料,這讓我非常沮喪和驚奇。除了醫院所記載的傷兵名單和冷冰冰的數值記錄之外,對於犧牲的中國士兵並無其他記錄。最終,在幾年之後,我嘗試對1932年“一·二八”事變的一些傷亡材料進行了發掘。
對於檔案的探索和發掘帶來了非比尋常的收獲,打開了上海戰時死亡諸多問題的窗戶,這最終催生了那些關於上海死亡方面更大範圍的問題。死亡問題在近代上海和其他中國城市中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但在過去20年浩如煙海的歷史學研究中,這個題目幾乎是消失的。盡管城市史研究越來越犀利地聚焦於城市一系列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特定人群和文化發展領域,但死亡在研究中很少被提及。在早期的歷史研究中,死亡與政治暴力、鎮壓以及就地處決(比如1927年的“四一二”事件)相聯繫,但是這些都是集中和匿名的死亡。在死亡的另一端,尤其是在革命和戰爭時期,死神的鐮刀收割著個體生命。從1911年前的清政府官員到民國時期的宋教仁,再到史量才,政治暗殺達到了頂點,這些國民黨人、通敵者和日本特務機關裡的野蠻殺手在中日戰爭初期胡作非為。但是這仍屬於政治暴力的範疇。
我們能從中國城市或者像上海這樣一個大都會的日常死亡中得到什麼?事實上,就像本書後文會討論的那般,答案非常簡短。鑒於中國城市中死亡數據的重要性以及在公共空間中顯而易見的存在——如葬禮、棺材在街上的運輸或者露尸,我認為用大眾或者街頭文化的方式來做這個研究應該可行。即便在衛生和公共健康領域的研究中,死亡只是和(有時也不都是這樣)衛生情況、傳染病或者公共衛生政策相聯繫。
有關中國死亡的學術性研究通常屬於人類學的範疇。將死亡置於近代中國社會史之中的最嚴肅的嘗試是由華琛(James Watson)和羅友枝(Evelyn Rawski)於1985年所編寫的《晚清和近代中國的葬俗》(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然而大體上說,這本書將注意力放在了中國的鄉村社會。羅梅君(Mechthild Leutner)關於近代北京的研究提供了將死亡置於城市進行考察的驚鴻一瞥,但是由於研究的時間跨度太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原本的研究目的。在中國學術界,除了一些論文之外,死亡在歷史研究中幾乎是徹底缺失的。所有現存的相關研究——大部分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主要集中於喪葬史以及清朝以降的喪葬習俗、葬禮和墳墓。對近代以來的喪葬研究非常少,而且僅限於哲學範疇。這些研究的地理範圍覆蓋全國,其中有三個研究更關注江蘇浙江、四川和長江下遊地區。城市則從來不在死亡研究的相關範圍內。
為了理解中國的死亡,最經典的學術成果是高延(de Groot)和盧公明(Doolittle)關於19世紀福建的研究。這些非凡論著,尤其是高延的研究,極其翔實。不過他們的研究聚焦在泉州地區精英的葬禮和下葬儀式,並沒有告訴我們城市在19世紀中葉的發展之後是如何處理死亡問題的。直到顧德曼(Bryna Goodman)和羅威廉(Willian Rowe)分別對上海和漢口的同鄉會進行研究之後,如何管理城市中的死亡問題,才有了些許眉目。他們最卓越的貢獻是讓我們知道了晚清和民國時期城市中死亡的不同方面。有關上海社區網絡在管理死亡問題中所扮演的角色,日本歷史學家帆刈浩之(Hiroyuki Hokari)做過有見地的研究。這個簡短的回顧表明,對近代上海死亡問題的歷史研究幾乎無異於白手起家,歐洲史在這方面則有非常豐富多樣的研究成果。
在歐洲,死亡史是和法國歷史學家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的研究成果聯繫在一起的。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西方文化中的死亡,他的研究不僅對這個領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還形塑了這個學術領域。但是歷史學家對死亡產生興趣要比阿利埃斯的研究早了20年,自20世紀60年代始,相關成果主要以書本和論文的形式面世。這些研究成果融入了“思想史”範疇下的更宏大的歷史研究趨勢。19即便歷史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學家對死亡史有了新的發掘,但“死亡史”這種表達方式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逐漸消失。我自己的特殊興趣是都市背景下的死亡及死尸,盡管前現代階段的城市可能在我的研究中占了更多比重。21英國歷史學家們對從歷史的角度研究死亡有卓越的貢獻。總的來說,維多利亞時代吸引了絕大多數歷史研究者的目光。通過使用常規的歷史材料以及私人文件,英國歷史學家們審視了城市中死亡空間的變化(尤其是從教堂墓地到現代墓地,再到火葬的變化)、、死亡的經濟學意義(特別是死尸的商品化進程)、、通過研究私人領域的喪慟和哀悼來揭示個人的情感領域。這些成果促使了我將死亡的經驗置於中國的文化框架以及上海的都市背景之下。在這座城市裡,外國人和中國人都介入重新定義處理死者的規範和習俗的過程。
在19世紀中葉開埠之前,上海一直是長江中下遊一個次要的城市,但是對於一些重要的貨物來說,比如棉花,上海作為一個商業港口已經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自宋朝始,上海就設有海關,城市因貿易而興,吸引了來自中國各地數量眾多的旅居者。18世紀時,這些群體已經組建了同鄉組織——會館和公所,這些組織在管理同鄉群體、規範經濟活動、維系群體內部以及他們與出生地之間緊密聯繫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隨著19世紀40年代外國租界的建立,城市的社會結構和空間布局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商業的發展,然後是工業的發展,吸引了成百上千的人來上海尋找工作和商業良機,旅居者群體呈現數量膨脹並多樣化的現象,使上海成了一座龐大的移民城市。而另一些移民——西方人、日本人、印度人等——把上海變成了一座複雜的國際化大都市。對於死亡,每個群體都有自己的信仰和一整套習俗。
上海最早以老城及其沿黃浦江的商業區和港區為中心,在兩個小的外國地界——英租界和法租界——成為城市的經濟、文化和政治中心之後,上海的城市空間和行政格局便發生了轉換。到了19—20世紀之交的時候,城市發展的重心偏向於外國人政治控制的區域,即上海工部局治理的公共租界和上海公董局管轄的法租界,以及行政中心在老城並包含新城區閘北的華界(閘北坐落於蘇州河北岸並向北延展)(詳見地圖1.1,見後文)。上海的發展以三分天下的格局展開,在同一塊城市範圍內有三個自治的地域,每一個都有自己的市政機構、法律規定和行政傳統。國家的力量在這座城市中很弱。大多數市政管理的事務,三個行政區域之間幾乎沒有任何形式的合作。死亡恰恰就是一個灰色的區域,主要靠家庭成員和同鄉會來解決,僅有的數據記錄顯示,他們直到1937年中日戰事全面爆發才不再直接介入該事項的處理。
上海的獨特性能不能使其死亡社會史與其他中國城市有所不同?第一,我認為在如此多元的城市旅居者群體所構成的社會景觀之下,最強勢的是江南地區的文化,有大量旅居者從江南地區來到上海。和其他商業或者政治中心如漢口、南京和北京相比,上海的中國人群體中顯著的多樣化並無太大區別。第二,外國勢力的存在也在都市的構造上又增加了一層不同的社會、文化和宗教活動。盡管這些活動確實影響了城市的死亡管理,但推動變化的主要因素是“前進”中的現代化進程。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扮演著主要的角色,就像在其他中國城市中所發生的那樣。在死亡的領域內,法律法規、儀式呈現和殯葬習俗的發展在尊重既有價值觀以及城市化和現代化轉型力量之間砥礪前行。
在上海及中國南部的城市裡,對於死者的照顧是家庭成員以及同鄉會館或者慈善機構的責任。雖然宗教會介入儀式的操辦中,但宗教機構實際上並不在死亡管理中扮演任何角色,中國政府也如此,直到1927年國民黨政府的成立。所有中國人最關心的事情是尋求一處體面的下葬之地,一處個人專屬的、單獨的或者家族共有的安葬之所。像義冢那樣將遺體埋在一起,或者像“地上棺”那樣將遺體隨地處置的做法,會對社會規範造成挑戰,而且也被認為會對生者造成潛在的破壞性影響。不體面的葬禮不僅被認為是危險的——會有死不瞑目的遊蕩惡魂,也被認為是社會秩序缺失的信號,而這是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的。最終,旅居者對葉落歸根的最高訴求產生了一種文化。和西方不同的是,中國人將出生地視為一個神聖的地方,並定義和塑造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精心構建的系統和因殯葬所帶來的經濟活動。
整個民國時期的上海,就像一個巨大的葬禮,吞噬著成千上萬的生命,即便在和平時期亦是如此。上海和前現代的法國城市或者第一次工業革命期間的英國城市(尤其是倫敦)並無區別,它榨幹了農村的人口以維持城市的生命線。29但在20世紀之前,歐洲城市的死亡率已經急劇下降,但在上海,不斷擁入的移民不僅僅給這座城市提供了維系工業和商業發展所需的關鍵人力資源,而且還填補了因持續大量死亡所帶來的勞動力缺口。無親無故或者親屬無法接濟的窮人死在或被扔在街頭、人行道上、廣場上、市場裡、後巷中,事實上,任何地方皆有可能。露尸成為對社會秩序的一種危害和對公共衛生安全的一種隱患。在上海,照顧窮人和赤貧人群、活人和死人,成為慈善社團最主要的工作。
在研究上海死亡史的過程中,我的興趣主要在大都市背景下的死亡形式和表達,大眾與死亡有關的行為和信仰是如何經由時光演變的,以及從晚清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0年之間管理死亡的模式。盡管信仰和習俗可以慢慢變化,但不同的因素和事件會促使對新殯葬習俗的逐步適應和最終接受。戰爭就是這樣一種事物,它能創造一種環境,在這種環境下,社會會松動對約定俗成的儀式的控制。國家力量是另一股推動變革的主要力量,特別是行政機構部門和政權試圖通過介紹或者強推其政策和規定,使社會發生重要的調整和轉變。外國租界試圖推行改善公共衛生問題的法律規定,而國民黨和共產黨政權則致力於更激進地規範和轉換幾乎一整個和處理死者有關的殯葬習俗和信仰的體系。從晚清時期的放任不管,到新中國政權下的法律規定,死尸成為一個關注的焦點,也成為國家和社會間一種張力的來源。
本研究的範圍是由史料和所選擇的敘述物件而決定的。從城市開埠進行對外貿易的19世紀開始進行考察,1865年是一個標志性的時間點,租界開始進行5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作為一名歷史學家,除了社會規範、傳統慣例和法律規定之外,我也關心人口,對人口的統計將提供一個研究人口中死亡情況的必要基礎。本研究的時間下限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在上海,檔案材料開放的年限只到1965—1966年,對依靠一手材料所做的研究而言,這個時間門檻並不低,所能提供的材料很有限。此外,十年特殊時期將先前和死亡有關的殯葬習俗幾乎全部抹去,那些仍然維持這些做法的建築也被破壞。也就是在此期間,火葬最終成為處理遺體的標準做法。
這部書中有部分檔案來源是歐洲和美國的圖書館及檔案館,但是大部分資料都收集於上海檔案館。“死亡的檔案”既豐富又粗略。其中有一大部分資料是從上海的兩個租界檔案中獲得的,並不是有意為之,這反映了檔案的情況。“死亡管理”在1927年之後的民國政府心目中,直到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都不處於優先的位置,而晚清的檔案或那些善會的檔案則大部分無跡可尋。死亡檔案的殘缺也有其他原因。市政當局在基礎設施(比如墓地)的日常管理方面產生了數量可觀的檔案,但是大部分檔案和干涉或管理城市中那些與死亡有關的各式機構沒有關係。報紙是補充檔案材料的主要材料來源,給本研究注入了更具體的張力感並喚起社會關注。
最後,本研究廣泛收集和使用視覺材料,在研究中偏向於使用和戰爭有關的圖片。就像華如璧(Ruby Watson)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的流行宗教並不怎麼重視靈魂的救贖”,而這恰是基督教所重視的。從中世紀歐洲開始,豐富的視覺形象向信教者所展現的不僅僅是基督之死,而是死亡的系列呈現:“視覺文化向人們展示了他們日常生活中的死亡。”但在中國卻不是這樣,恰恰相反,死亡被認為擁有一種無處不在的負面影響,而且應該眼不見為凈。死亡僅有的視覺呈現是死者的肖像畫,後來被照片所代替。中國畫家不會畫任何類似於表現死亡或者表示死亡存在的內容,而這在歐洲畫中是常見的。即便是在20世紀,照片也不會拍攝遺體或者死者的棺材。但總的來說,照相機記錄了殯葬習俗的方方面面以及葬禮空間,這有時能幫助填補文字檔案的空白。頗為重要的是,試圖從涉及死亡、捎帶提及一個角色去世的文字文本中來辨析死亡是無法提供任何確鑿證據的。中國文化將死亡圍上了一堵厚厚的無聲之墻。
我開始這項研究時的雄心,是為了探索那些歷史中死者的心性,期望能書寫一部社會文化史,既包含和尸體有關的行為和規定,又包含和死亡、悲傷、哀悼有關的個人情感。但是私人領域的情感研究並不在我的研究範圍裡。我可以通過研究人們是如何對特定環境作出反應,尤其是當官方的規定與他們的信仰相衝突的時候,來感知人們對死亡的情感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變化。這本書試圖通過研究死亡中一些既定方面的系列小問題,來敘述19—20世紀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中的死亡社會史。大部分情況下,研究的焦點將集中在正常死亡上,意外死亡或者因戰火、謀殺以及自殺所造成的血腥死亡不在研究的範圍之列。謀殺是一個令人感興趣的研究主題,即便上海遠不是流行故事中所描述那樣的“謀殺之地”,而且有時候歷史學家也免不了去想象一些事情,但上海的確有殺人犯,在檔案中也有很多謀殺的案例,能把歷史學家帶回到謀殺現場。自殺是一個被寫過很多次的題目,尤其是女性的自殺。除了侯艷興的研究之外,還有顧德曼從另一個角度來研究的作品,但是大部分的研究都僅集中於對數據的分析,而少有對檔案館中待歷史學家發掘的眾多個人案例進行深入研究的嘗試。上海的死亡研究和死亡文化研究,以及中國其他城市的類似研究,仍大有可為。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