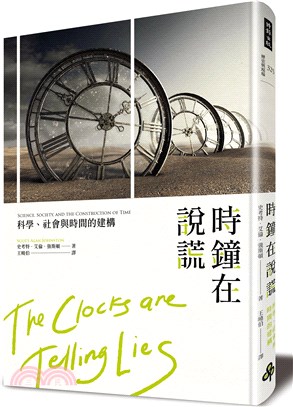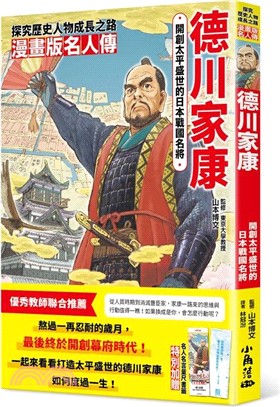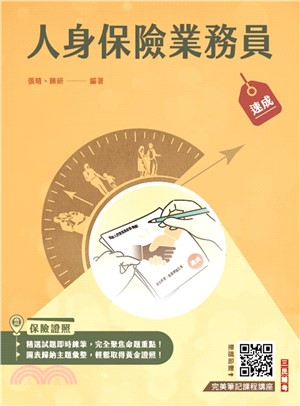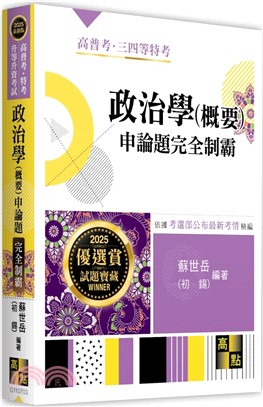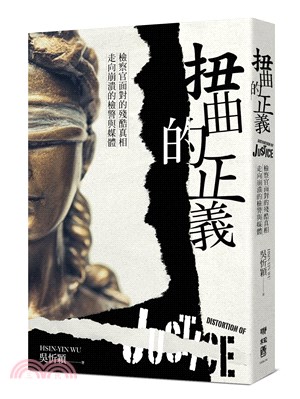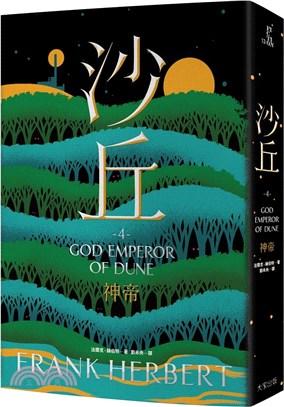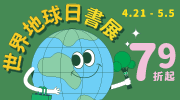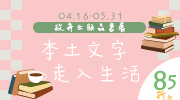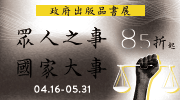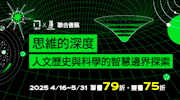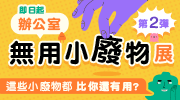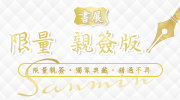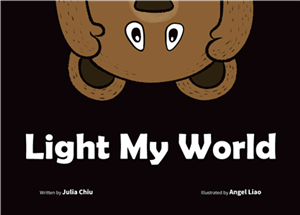時鐘在說謊:科學、社會與時間的構建
商品資訊
系列名:歷史與現場
ISBN13:9786263359147
替代書名:The Clocks Are Telling Lies: Science, Socie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ime
出版社:時報文化
作者:史考特‧艾倫‧強斯頓
譯者:王曉伯
出版日:2022/10/25
裝訂/頁數:平裝/304頁
規格:21cm*14.8cm*1.5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為什麼時鐘有12個小時?
為什麼一天是從午夜開始?
為什麼是24個時區,或根本沒有時區?
本書敘述19世紀標準化的年代
我們對時間的認知與如何編造時間的故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9世紀之前,所有的時間都是地方時間。巴黎的時鐘與莫斯科的時鐘並不需要相互校正。不論是徒步還是騎馬,來往於城鎮之間的旅行都沒有快到需要考慮距離中午或是超過中午幾分鐘,還是幾小時。在那個時候,騎馬旅行沒有所謂時差的問題。
然而,鐵路和電報的發明使得世界各地的連繫變得更加緊密,城市之間的時差也突然變得很重要,但何謂標準時間?
國際標準時間之父史丹佛‧佛萊明(Sandford Fleming)所設想的標準時間,與天文學家提出的時間甚至有衝突,雙方於 1884 年華盛頓特區舉行國際子午線會議,討論安排時間的最佳方式時卻分歧不斷,標準時間幾乎差點不存在。
時間改革所受到的影響不僅來自科學與科技,同時也包括宗教、社會、階級與文化。如果科學家與工程專家對標準時間都無法達成共識,一般人該如何遵守時間?其實我們的時間只是大家認同的一個近似值。即使是在今天,原子鐘與全球定位衛星向世人提供的時間能夠精確到十億分之一秒,也並非真正的時間。
本書透過一八七五到一九一四年發人深省的故事,探討人類對時間、空間的認識,以及對生活與時間的認知。作者認為,計時系統並沒有真正的時間,時間並不完美,世界時間仍有待我們發現。現在的時間完全是編造的,時間的建構是以人和權勢、政治與社會規範為中心,而非科技,我們需要重塑人類對標準時間的觀點。
作者簡介
史考特・艾倫・強斯頓(Scott Alan Johnston)
科學與科技史學者,現居加拿大安大略省。
譯者簡介
王曉伯
曾任職財經媒體國際新聞中心編譯與主任多年,著有《華爾街浩劫》、《葛林史班:全世界最有權力的央行總裁》(合著),譯作包括《光天化日搶錢》、《我們為什麼要上街頭?》、《海森堡的戰爭》、《小王子的寶藏》、《向領導大師學激勵》、《群策群力的領導智慧》。
目次
引言
第一章 混亂的開始
第二章 業餘人士、專家與奇人異士
第三章 國際子午線會議
第四章 傑克蓋的房子:販售時間,現代性的建構
第五章 教導時間,利用時間
結語
致謝
附錄 國際子午線會議決議案
注釋
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你是否曾盯著時鐘,納悶到底是誰來決定時間?我們知道就某種程度而言,時鐘的計時只是為了方便起見而採取的人為手段。鐘錶所報的時間,是大家都同意使用的時間,我們的社會則是依循此一時間運作,但是我們的時間其實只是大家所認同的一個近似值。即使是在今天,原子鐘與全球定位衛星向世人提供的時間能夠精確到十億分之一秒,也並非真正的時間。這些原子鐘都是政治協議下的產物,例如一秒鐘的長度或是時區的幅度,而且我們會為了配合國界來改變時間或是使用日光節約時間。因此,時間並非由物理決定,而是政治。事實上,物理學否定單一真時的概念。
根據阿爾伯特‧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相對論,現代物理學家主張時間是相對的,會根據速度與重力而改變。就一般大眾而言,相對性是在我們不知不覺中產生的效應,微小到幾乎無從衡量,但是卻足以讓衛星系統計算時間膨脹來維持穩定運作。總而言之,愛因斯坦的真知灼見意味人類無法找到一個統一的全方位計時標準。時間是由我們來決定,因此,時間就應了那句老諺語:「大家異口同聲的謊言。」計時系統並沒有「真正」的時間,時間並不完美,世界時間仍有待我們發現。現在的時間完全是編造的。
本書所敘述的就是我們如何編造時間的故事。質疑為什麼時間是現在這個樣子?尤其是計時如何成為全球標準化的系統?畢竟這是相對近期才有的現象。在十九世紀之前,所有的時間都是地方時間(local times)。巴黎的時鐘與莫斯科的時鐘並不需要相互校正。不論是徒步還是騎馬,來往於城鎮之間的旅行都沒有快到需要考慮距離中午或是超過中午幾分鐘,還是幾小時。我們可以這麼說,在那個時候,騎馬旅行沒有所謂時差的問題。
一直到了十九世紀中期才開始出現改變。鐵路與電報的發明幾乎是單槍匹馬創造了一個相互聯接的新世界。與此同時,各城市之間的時差突然變得重要。電報需要細心協調發送者與接收者之間的時間,鐵路若是沒有精確的時刻表,就會面臨生命損失的重大威脅。因此,為了避免混亂,必須有一套各方都同意的新計時系統。
這些新科技無庸置疑為時間的標準化帶來動力。不過鐵路與電報的發明並不足以說明,世人為何要以他們當初使用的方式來化解全球計時的挑戰。這些解決方式並非由科技來決定,而是透過社會與政治途徑形成,也因此更為有趣。這是一則關於互聯新世界成長煩惱的故事,(就計時而言)這樣的煩惱大約在一八七五到一九一四年達到高峰。
啟動計時革命的必要性在十九世紀逐漸浮現,尤其是在歐洲,我們或許可以把那段時期稱做存貨時代或盤點時代。當時長達幾世紀的全球探險傳奇已經結束,維多利亞時代於是全心投入測量與盤點全球的資源。這類活動可以是良性的,例如在科學界建立新的專業領域,將所有的事物標準化,包括度量衡、為蝴蝶分類以及時間。另外還有以商業利益為目的的測量、土地測繪,為作物分類與安排出口。但是這類盤點的活動也有黑暗的一面,即是形成殖民剝削。土地的測繪與測量,可以用來做為都會區佔用全球其他地區資源的工具。時間的測量可以幫助水手在汪洋大海中找到他們的經度,然而這樣的能力也促成海外殖民化。不論是好是壞(往往是壞的一面),整個世界都開始接受測量、組織、分類與標準化,所有的事物都各有其位,計時也不例外。
可想而知,這是一段混亂的過程。人類要掌控一切的野心已超過他們的技術水準。國家、專業與商業的競爭,再加上階級的不平等與殖民地的爭奪,使得這些工作難臻完美。世人永遠不缺如何組織與管理這個世界的法子,但是要讓大家都接受,不論是憑三寸不爛之舌或是脅迫的手段,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就計時而言,意味十九世紀中葉若問某人現在時間為何,可能會引出一個複雜的回答。問題並不在於缺少來源,當時鐘錶已廣為流行,市政廳與火車站的牆壁上都掛有裝飾用的大鐘,各個不同的宗教在全球許多地方都會以鐘聲來提醒信徒。同時,在緊要關頭,太陽與潮汐也可以用來粗估時間。不論是都市還是鄉村、富人與窮人、國家與殖民地,報時的工具無所不在。
問題是,儘管時間並不缺乏測量的工具,但是卻往往會造成始料未及的衝突與競爭。鐘錶相互之間並不同步,即使是最精美的鐘錶也只能維持完美的節奏幾個星期而已。這樣的情況意味每個鐘錶所報的時間都不一樣。然而使這個問題更加複雜的是,決定一座鐘錶是否準確的依據不是科技,而是權勢、政治與社會規範。雖然鐘錶互不相同只是無意之間的結果,但也可能是人為故意的,因為不同的專業、宗教、文化與國家都自有一套計時的方法(更別提日曆了,每一種都是依據不同的文化、宗教與天文學基礎而制定)。時間的不確定已成常態,於是人們開始質疑我們在二十一世紀視為當然的做法是否恰當。為什麼時鐘面有十二個小時?為什麼一天是從午夜開始?為什麼波士頓的鐘錶要與伊斯坦堡或東京的相互聯接?為什麼全球的時間要從英國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一條想像中的經線開始起算?為什麼是二十四個時區,而不是十個,或者根本就沒有時區?時間並非由天文、地理,或是任何一種「自然」力量所制定的,而是人們在特殊的情況下所決定,而且往往對於可能造成的結果毫無頭緒。如何測量時間已成為一項極具爭議的問題,引發激烈的辯論,而且難以解決。
這些激辯的中心是一八八四年在華盛頓特區舉行的國際子午線會議(International Meridian Conference, IMC)。當時,來自近三十個國家的外交官、科學家、海軍軍官與工程師齊聚一堂,討論本初子午線的創設與全球計時以及地圖繪製的未來。該會議身為現代標準時間的起源,本身就具有神話與傳奇的色彩。通俗歷史將此一會議描繪成如桑福德‧佛萊明(Sandford Fleming)與威廉‧艾倫(William Allen)等改革家為全球設立時區之類創舉的時刻。但這是過度簡化這場會議的意義了。我們如今所知道的標準時間,並非在這場於一八八四年華盛頓召開的會議中敲鑼打鼓下誕生的。確實如此,有些歷史學家還認為這場會議對於艾倫與佛萊明等推動時間改革人士而言是一大挫敗,因為儘管該會議創立了本初子午線,但是並沒有達成任何與時區與標準時間相關的協議。IMC最多也不過是邁向現代標準時間長期發展路途的踏腳石,是全球時間測量方式改變的開始,而非結束。標準時間至少要到一九四○年代才在全球通用。IMC的歷史光環還因一八八四年另一場在柏林舉行的著名會議而變得黯淡無光。在這場於德國新首都召開的會議上,歐洲列強商討如何瓜分非洲,宣告正式展開「瓜分非洲」(Scramble for Africa)的行動。就某些方面而言,這場祕密會議為二十世紀的到來奠定基礎,為列強的競爭、殖民化與去殖民化,以及自歐洲入侵以來許多前殖民地遭遇人道危機的情況埋下伏筆。相較於柏林會議,IMC似乎顯得微不足道。
然而我們也不應低估IMC所發生的事情。如果柏林會議是為二十世紀的先聲,華盛頓會議就是十九世紀的縮影──它是維多利亞時代關於專業知識、專業化的辯論,與追求對世界秩序的理解與如何組織下的產物。在這場華盛頓會議中有許多值得研究的東西。它教導謹小慎微的觀察家這個世界是如何運作的,也因為如此,它也成為一個內涵豐富的研究案例。我們很容易就會忘記當時是一八八四年,當時參與會議的人士在這個已經十分複雜的世界中做下決定,卻無從知道未來的發展會是什麼樣子。對他們而言,IMC不只是為某些輝煌的事業開啟大門,然而對其中一部分人而言,這場會議至少也不算是全然的失敗。這是維多利亞時代現代性的實驗,同時也是對當時景況的一種展示。
有鑑於此,本書的寫作完全是採用歷史研究方式,探究華盛頓會議對於與會者有何意義。在一八八四年的那個時期,世人是如何做下決定?他們又是如何理解人類的未來?什麼事會令他們擔心、興奮與受到驅使?這些問題的答案勢必會牽涉到政治與外交上的考量,同時還和與會人士身處的社會與文化環境息息相關。另外,帝國皇權與勞工階級的生活經驗也有密切關係。時間經濟學決定酒吧何時打烊;還有哪些特權階級才能接觸到準確的時間,又有哪些人能因鐘錶的商業化獲利。與此同時,科學家、工程師、外交官、商人與宗教勢力則是相互競爭國際計時的控制權。新興國家則是在努力爭取發言權,而殖民地也是極力爭取在此一議題下有一席之地。這是一個千頭萬緒的故事,或許解釋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為什麼和啟蒙時代的先輩一樣,如此執著於標準化與組織。他們試圖將時間標準化,就是要簡化這個複雜的世界。
然而遺憾的是,正如本書所顯示的,他們想將全球計時標準化的努力反而使得事情更加複雜,而不是簡化。這一結論是來自兩大論點。首先,時間是由社會建構的知識形態。科學家、工程師與外交官在IMC所做的決定並非來自亙古不變的金科玉律,也不是根據自然法則所做的邏輯推斷。他們是在政治、國家,尤其是專業利益的引導下做出決定。有鑑於此,此書不僅是分析科學與科技的歷史,同時也是社會與文化的歷史。事實上,科學家與其他領域的專家(如天文學家、鐘錶匠、外交官與工程師)不但相互競爭,同時也與其他人在爭奪時間的掌控權。在時間的改革中,個人的性格與其專業背景要比國家利益與技能要求更重要。在往後的幾年,自二十世紀中期開始,標準化的權力落入國家的勢力範圍之內。
但是一八八四年的情況並非如此。IMC並非一些所謂英國或美國的代表,於一八八四年十月坐在華盛頓悶熱的房間內進行討論,而是一批擁有不同技能的個人齊聚一堂,他們正巧來自於這些國家。會議桌上最深層的隱憂並非在於國與國之間,而是在於與會人士的專業之間,即使是來自同一國家也會相互攻擊對方的立場。在科學專業化潮流方興未艾之際,為了維護自己專業領域的利益,與會的天文學家、工程師與海軍軍官,不論是何國籍,無不激烈爭執最佳的組織時間方式。這些辯論自華盛頓的外交圈擴散至社會大眾,為了什麼才是最佳的計時方式,大家多年來一直爭論不休。
這也引導我們來到本書第二個論點:標準時間之所以確立,主要是因為眾人對時間的本質各執己見所致──時間是可以自由共享的公共財嗎?是可以出售的商品嗎?或者是只有學有專精的人才能使用的科學工具?儘管相關歷史人物很少直接承認這場辯論,但是他們的主張都已表現在他們的行動上。再次強調,這些基礎性的辯論並不僅限於IMC本身。從英國城市的貧民區、加拿大原住民地區,到美國的天文台,全球各地都在熱議時間的本質。
既然如此,為什麼這些辯論反而會使得計時問題更為複雜,而不是簡化?答案在於儘管有些改革人士希望推動計時普遍化與全球化,但是還有一批專家則是主張對其使用予以限制。如桑福德‧佛萊明與威廉‧艾倫這樣的改革派,想要一個可供世人廣為使用而且簡單的標準時間,以全球通用的計時系統來取代地方時間。但是IMC其他專家,例如天文學家,就視世界標準時間是專供天文學家、航海人員與科學家使用的科學工具。對他們而言,世界標準時間只有在地理意義上是通用的。如果你擁有適當的工具與教育水準,你可以用它來確定全球任何一個地方的時間。它並非供大家使用。
由於任何人都可以透過觀察頭頂上的太陽來使用地方時間的舊計時系統,然而全球統一的標準時間在使用上需要某種形式的專業生產與分配,使得上述全球計時的兩個觀念間的緊張關係更趨複雜。換句話說,時間的生產已從當地一般人的手中轉移到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與全球各地天文台的天文學家手中,他們會以電報來分配時間,而且有時還要付費。這也意味推動全球時間標準化的努力,反而矛盾地造成世人接觸「真時」的不平等。受限於科技水準,再加上天文學家企圖限制標準時間的使用,使得世界標準時間儘管受到專業人士與國際間的認可,仍然無法通用於社會大眾之間長達幾十年。世界標準時間普及化受阻也帶來一項副產品,即是較為通用的舊計時系統不但沒有遭到淘汰,反而還與新系統並列。地方上的計時主管單位現在必須決定是否要放棄自己的權力,並將其交給上級單位(格林威治),或者是拒絕格林威治的權威,並且與其競爭,尋求能讓他們的計時系統合法化的法子,事實上大多數都是選擇後者。因此,創造一套以格林威治為依據的新式全球標準時間,不但沒有簡化計時的工作,反而還製造出一套時間階級,而且是新舊並陳。什麼時間才是「真時」,又有哪些是在說謊,完全要視當時的觀察人員與周遭環境而定。
一則共有五個章節的故事
本書所敘述的事件大都發生在一八七五到一九一四年,這一期間也是世人經歷計時系統變革最快速與廣泛的一段歷史。雖然這些變革是全球性的,我們的故事則是主要集中在北美地區,該地區幅員廣闊,正適合推動標準時間,因為要在此一寬闊的大陸協調火車時程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情。本書也有一大部分著墨於英國,她是本初子午線的發源地,也是全球計時系統的中心,從中可以看出格林威治官方科學的標準時間,與當地民眾所使用的非官方地方時間之間的差別。
不過這是一則屬於全球的故事,其中心是一場國際會議,即是一八八四年在華盛頓特區召開的IMC,參與這場會議的人士來自二十五個國家,他們共商國際計時的操作方式。本書也會出現一些來自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士,這些在英國與北美的辯論的影響力遍及全球。
我們的故事在第一章是講述標準時間觀念的濫觴;各個階段的鼓吹與遊說,以及IMC的籌劃與組織。這些活動的關鍵人物是加拿大鐵路工程師桑福德‧佛萊明。佛萊明是IMC時間辯論的主要倡導人,但是由於他是一位鐵路人與工程師,並非科學圈內人士,而後者的建議在會議中往往會佔上風。他的職業使得他在他所發起的會議中難以佔有一席之地,他被迫只好尋求其他盟友來推動他的改革,然而這些盟友有時也會對他的主張多所懷疑。他的困境突顯了與會者的職業背景是如何形塑時間的辯論。
第二章的焦點由佛萊明轉向當時的科學圈,主要是三位在職業科學圈的外圍人士,安妮‧羅素(Annie Russell,在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工作的首批女性之一)、威廉‧帕克(時運不濟的航海家與探險家,積極為他的計時概念尋找贊助),以及查理斯‧皮亞茲‧史密斯[一位資深的天文學學家,個性乖僻,他執著於埃及吉薩金字塔(Great Pyramid of Giza)的偽科學,並將此一信念帶入其計時的主張中。]這三人突顯出維多利亞時代專業科學的界限,與在當代知識思潮下時間辯論的地位。他們三人都沒有參加IMC,但是他們與他們在計時上的主張足以代表這次會議的背景與辯論的主題。IMC的與會者肩負著本章所描述的文化包袱,例如業餘與專業間的緊張關係、宗教在科學中的地位。當時社會有一套禮儀準則來定義與規範,哪些人才能獲准在時間標準化的議題上具有話語權。現代科學變成了一種隔絕形式的追求,也形塑了科學傾向的與會者對世界時間的理解。
第三章著重於IMC本身,詳細敘述其每天的活動:誰對誰說了什麼、有哪些密室交易,以及與會者的社交活動。本章證明了第一與第二章論點:專業才是這場辯論的中心,而不是國家間的歧異,同時也是理解IMC結果的關鍵。科學界如願以償──一個只限定為專業人士使用的世界時間。佛萊明等推動標準時間普及化的人士則被打入冷宮。
第四章脫離政治與外交,探索社會大眾是如何看待這場事關時間改革的辯論。它詢問在英國有哪些人能夠接觸到真正準確的時間,哪些人又被拒絕於門外。本章並非討論計時系統的改革對英國社會造成的影響,而是描繪IMC的決定逐步滲入社會大眾生活所引發的爭議。銷售時間產業的演進,包括瑪麗亞與露絲‧貝爾維爾(Maria and Ruth Belville),這兩位挨家挨戶販售格林威治時間的女性,也是本章的重心,由此也可看出IMC是如何導致準確時間的商品化。本章也說明了有一些人認為世界時間是多此一舉,其他一些人則認為這是地位與現代化象徵,在此社會氛圍下,世界時間是如何建立其合法性與權威性。
第五章是檢視計時系統十九世紀晚期在美國與加拿大的變化。它仔細審視改革人士嘗試透過教育來重塑社會行為規範。他們企圖透過法律來實施標準時間的努力以失敗告終,(他們確實曾經試過,我們由安大略省倫敦市一椿有關酒吧打烊時間的法院案例即可看出。)於是他們轉向學校來調整行為規範。然而從知名大學、小鎮學校到原住民社區,課程與日程的安排,都會對標準時間造成破壞。結果是好壞參半,顯示自一八八三年推出之後,標準時間與社會公眾間的關係益趨複雜。
本書最後所顯示的是計時系統在IMC之後不但沒有簡化,反而更加複雜的一個世界。該次會議創造出一套時間階級制度,引發何者才是「真時」的辯論。在這個議題上,一個人的立場不僅是由其職業背景而定,同時也要看他是否認為時間是公共財、一種商品,還是特殊工具。社會大眾無法平等享有權威性的格林威治時間,加劇了這些鴻溝,並使得世界的計時系統陷入困境。此一僵局直到一九二○年代中期,無線廣播技術的發明與使用才告打破,該技術對格林威治時間的通行居功厥偉。就計時而言,這段長達四十年的時間既混亂又刺激,然而時間本身的未來卻仍是一個謎團。
摘自〈引言〉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