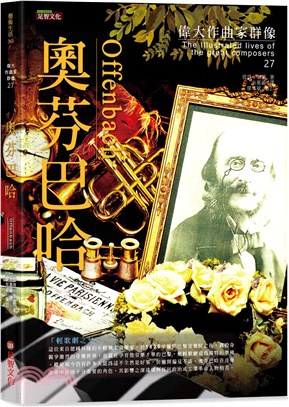偉大作曲家群像27:奧芬巴哈
商品資訊
系列名:藝術生活
ISBN13:9789865569860
替代書名:The Illustrated lives of the great composers︰Offenbach
出版社:足智文化有限公司
作者:彼得.加蒙
譯者:余慕薌
出版日:2023/01/06
裝訂/頁數:平裝/236頁
規格:24.5cm*17.5cm*1.5cm (高/寬/厚)
重量:550克
版次: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奧芬巴哈是)香榭麗舍大道上的莫札特」──羅西尼
奧芬巴哈常和優美但浮淺的音樂相提並論,不過他也是一位嚴肅的作曲家,從雷哈爾到蓋希文等作曲家都從他為音樂喜劇帶來的動力中獲益匪淺。若要將所有的榮耀都歸於一個人身上可能並不明智,但若一定要找出一位法國輕歌劇真正創始人,那就非奧芬巴哈莫屬。他的輕歌劇情節輕快幽默,曲風優美,多採用當時流行的歌曲、舞曲形式,使作品通俗易懂。這位來自德國科隆的年輕猶太音樂家,於1835年離開巴黎音樂院之後,就投身競爭激烈的音樂世界;也就在孕育他音樂才華的巴黎,使輕歌劇成為獨特的樂種。縱使現今仍有許多人認為這不全然是好事,但撇開偏見不談,奧芬巴哈在音樂改革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影響之深遠堪與任何政治或工業革命人物相若。
奧芬巴哈與孟德爾頌皆為音樂史上光芒四射的猶太作曲家,並與小約翰‧史特勞斯同享輕歌劇創始盛名,由於觀眾需要歡笑來調劑生活,喜劇因而有著它存在的必要與價值。他因而被羅西尼稱為「香榭麗舍大道上的莫札特」,他的這些輕歌劇,不僅打破傳統、挑戰尺度,且娛樂性強,為歌劇的發展開立了一個新的局面,以《天堂與地獄》和《霍夫曼的故事》等輕歌劇名作而聞名。他有多齣作品諷刺第二帝國時期在巴黎的奢靡生活,但是巴黎人還是拜倒他的音樂之下。
奧芬巴哈工作不輟,但他也過著多彩多姿的生活。這本經由彼得‧加蒙對奧芬巴哈的生平和音樂成就所著的讀物,寫來可讀性甚高,插圖豐富,文後所附奧芬巴哈的作品目錄也包括當時演出的寶貴資料。
奧芬巴哈常和優美但浮淺的音樂相提並論,不過他也是一位嚴肅的作曲家,從雷哈爾到蓋希文等作曲家都從他為音樂喜劇帶來的動力中獲益匪淺。若要將所有的榮耀都歸於一個人身上可能並不明智,但若一定要找出一位法國輕歌劇真正創始人,那就非奧芬巴哈莫屬。他的輕歌劇情節輕快幽默,曲風優美,多採用當時流行的歌曲、舞曲形式,使作品通俗易懂。這位來自德國科隆的年輕猶太音樂家,於1835年離開巴黎音樂院之後,就投身競爭激烈的音樂世界;也就在孕育他音樂才華的巴黎,使輕歌劇成為獨特的樂種。縱使現今仍有許多人認為這不全然是好事,但撇開偏見不談,奧芬巴哈在音樂改革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影響之深遠堪與任何政治或工業革命人物相若。
奧芬巴哈與孟德爾頌皆為音樂史上光芒四射的猶太作曲家,並與小約翰‧史特勞斯同享輕歌劇創始盛名,由於觀眾需要歡笑來調劑生活,喜劇因而有著它存在的必要與價值。他因而被羅西尼稱為「香榭麗舍大道上的莫札特」,他的這些輕歌劇,不僅打破傳統、挑戰尺度,且娛樂性強,為歌劇的發展開立了一個新的局面,以《天堂與地獄》和《霍夫曼的故事》等輕歌劇名作而聞名。他有多齣作品諷刺第二帝國時期在巴黎的奢靡生活,但是巴黎人還是拜倒他的音樂之下。
奧芬巴哈工作不輟,但他也過著多彩多姿的生活。這本經由彼得‧加蒙對奧芬巴哈的生平和音樂成就所著的讀物,寫來可讀性甚高,插圖豐富,文後所附奧芬巴哈的作品目錄也包括當時演出的寶貴資料。
作者簡介
彼得.加蒙(Peter Gammond)
曾任笛卡唱片公司(Decca Record Company)與唱片評鑑(Gramophone Record Review)的音樂編輯、廣擂人,並創作了數首歌曲和一齣輕歌劇。
曾任笛卡唱片公司(Decca Record Company)與唱片評鑑(Gramophone Record Review)的音樂編輯、廣擂人,並創作了數首歌曲和一齣輕歌劇。
序
總序
音樂家傳記新視野
傳記文學在整個文學及人類文化,占有相當的分量與地位。世界各民族起初以口語傳承民族、部族或原始社會英雄人物的事蹟;有了文字以後,就用筆記載偉大人物的傳記。
傳記因此被認為是歷史學的重要佐證,學界視其為歷史學的分支,極重要的史料。
傳記類書籍在我的藏書裡占了相當的分量,將近1,000本。這些傳記的範圍很廣,包括歷史人物(其實那一個不是歷史人物)、間諜、探險家、發明家、詩人、畫家、建築家等等。其中音樂家傳記就占了三分之二。
我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那就是對某個特定人物感興趣時,除了蒐集在學術上受肯定的傳記以外,凡是在書店(幾乎是在國外)看到有關他們的傳記,或從書上讀到另有附人物圖像的好傳記,就會如在田野挖地瓜般,想盡辦法蒐購。結果是,書架上有關馬勒、莫札特的書就各超過100本。馬勒的研究在這幾年成為風氣,除了米契爾(D. Mitchel)及法國人拉•朗格(La Grange)以外,也有一些新近的研究,被挖掘出來的資料越來越多。
音樂家傳記與其他領域傳記最大的不同點,可能是與一般傑出人物的生涯不同。我們從很多傳記上的記載得悉,不少人物屬大器晚成型,如發明家愛迪生兒童時期的智能發展就比較慢;但音樂家與著名數理學者一樣,很早就展現驚人的天才。
依照學者的研究,音樂家的各種特殊技藝、才能,及數理學者驚人的計算能力,最容易被發現。通常一個人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受教育及實務工作,從中自覺所長,並集中精力投注於此,才能磨練出才華及成就;但是音樂及數理方面的才華,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如上帝的恩寵,頭頂光環,因此很容易被發掘。
幾乎可以斷言,歷史上留名的大作曲家或演奏家,都有過一段神童時期。有些特異才華無法維持太久,過了幾年這種能力就消失。
在東方長幼有序、注重本分倫理的威權之下,天才很難得以發揮,沒有人栽培天才,就沒有天才生存的空間。但在西方有個特別的文化現象,即不管什麼年代都有「期待天才出現」的強烈願望,這可能與西方「等待救世主來臨」的宗教觀有關,西方各國肯定天才,對天才多方栽培的例子不勝枚舉。
有人認為天才不但要是神童,而且創作力必須維持到年邁時期甚至逝世為止;另外一個條件是作品多,而且要對當時及後世有影響才算數。
這樣的條件,令許多夭折的天才只能屈居為才子,無法封為天才。許多人認為天才都是英年早逝,但有些天才很長壽,可見天才夭折的說法,在科學昌明的廿世紀及即將來臨的廿一世紀,是近於妄斷的說法。
音樂家傳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傳;另外是由親友知已或學者所寫的傳記。十九世紀浪漫時期的特徵之一,就是對超現實的強烈慾望,或因想像所產生的幻想的現實,及由於對現實的不滿,而產生的超現實兩種不同的極端,因而產生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在這種風潮下,自傳及一般傳記中的許多史實,不是將特定人物的幻想,或對人物的期許寫得如事實般,不然就是把紀實寫成神奇的超現實世界。例如莫札特死後不久,早期的傳記往往過分美化莫札特或將他太太康絲坦彩描述為稀世惡妻;貝多芬被捧為神聖不可觸及的樂聖、李斯特是情聖、舒伯特是窮途潦倒、永遠的失戀者。更可怕的是,將邁人廿一世紀的今天,這種陳腔濫調的傳記,還是充斥市面,不少樂迷都被誤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各國對古樂器的復原工作不遺餘力,利用各種資料、圖片、博物館收藏品及新科技,而有長足的進步,得以重現這些古音。同時因副本或印刷器材的發達,原譜不必靠手抄,使古樂譜的研究有突破性的成果, 加上文獻學的發達,以及各種週邊旁述,不同年代的演奏形式、技法漸漸地被分析出來。因此目前要聽所謂純正的巴洛克時期所使用的樂器、原譜、奏法、詮釋,及重現湮沒多年的古樂,已不再是夢想。同樣地,音樂史上的作曲家如巴哈、莫札特、貝多芬的面目,已經相當準確地重現,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人員,不再只是苦心研究的學者,還包括許多業餘研究的經濟、社會、文化、醫事專業人員,從事精密的考證工作;著名音樂家的健康、遺傳病、死因、經濟收人、人際關係等,都有豐富的史料被發掘出來。因此第二次大戰後所出版的音樂家傳記,與十九世紀浪漫筆調下的描繪相距很遠。
十九世紀傳記中描述的音樂家愛情故事極端被美化,而當時極流行的書簡更是助長了這些故事。十九世紀名人所留下的書簡,有些是吐露內心的真話,有些卻是刻意寫給旁人看的,若要以之作為史料,史學者、傳記作者都要小心取捨。
優良傳記的標準是什麼?見人見智,很難有定論,但一定要忠於史實,不能私自塑造合乎自己理想的人物形象,不能偏頗或限於狹隘的觀點,要考慮時代性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廣泛的文化現象,但也要有自己的史觀。
讀了優良的傳記後,重新聆聽這些音樂家的作品,會增加多層面的體會與瞭解。雖然音樂以音響觸發聽者的想像力,有些是普遍的理念,有些是作曲者強烈主觀所訴求的情感,與作曲家的個性及所追求的目標有密切關係。因此我鼓勵真正喜歡音樂的年輕人,只要有時間,多閱讀傳記。馬勒、莫札特、巴哈的傳記或研究書籍,我各有一百多本,但我還是繼續在買,看起來雖是重複,但每一本都有他們研究的成果,即使是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獨特見解。當然,當作工具書的葛羅夫(Grove)音樂大辭典,都是由樂界的權威人士所執筆,比差勁的傳記可靠,但優良的傳記更富於情感、更有深人的見解,當作工具書也很可靠。
由於喜歡讀傳記,不知不覺中對這些音樂家最後的居所有所知悉。因此旅遊時,我都會去憑弔這些音樂家的墓地或他們曾經居住過的居所。看到這些文物器具,會讓你像突然走入「時間隧道」般,回到幾百年前的景象,與這些作曲家的心靈交流。那種感觸與感動難以言喻。
旅遊時,我除了參觀美術館、音樂博物館、上劇院、看音樂廳、拍攝大教堂及管風琴外,音樂家的史蹟或墓園都列人行程,會對這些地方產生興趣或好奇,大半是讀了傳記而引發的。
讀好的音樂家傳記,如聽好音樂,對人的一生、才華、成就,可以做烏瞰式的觀察,對同時代人造成衝擊,對後代產生影響,並可以培養人們閱讀歷史的技巧;而且有些文章如文學作品般巧妙雋永,讀來回味無窮。
這套由Omnibus出版的音樂家傳記系列,英文原版我幾乎都有,因為內容比聞名的葛羅夫音樂大辭典更深人,對每一個音樂家所處時代,有清楚的定位,應用最新研究資料,附加適宜的註解及推薦相關書籍,幾乎可以當作工具書,其中有些作者是樂界的權威人士。對音樂家及其作品想要有更深人瞭解或欣賞的有心人,這是一套良好的讀物。
資深樂評人
曹永坤
――――――――――――
講究音樂與語言一致的法國歌劇
法國的歌劇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其形成顯得較為特異。十八世紀初葉以前,法國以外其他國家的歌劇均或多或少受到義大利歌劇的影響。公元1620年前後,義大利歌劇已在德語系的各大城市上演,並於1700年的前後受到英國的青睞。而法國雖於1645年後,有上演過義大利歌劇幕間短劇的記錄,但是這些零星上演過的短劇,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就漸漸式微。以法國宮廷和義大利在血緣上密切的關係以及文化上的頻繁交流來看,法國理應相當容易接受義大利歌劇,但義大利歌劇卻沒有在法國生根。雖然法國人自十六世紀以來一直喜愛舞劇,並以舞劇為宮廷的主要娛樂,另外以神話故事為題材的音樂劇也在十七世紀盛行,但是法國的歌劇自始一直刻意擺脫義大利和德國歌劇的影響,這其間從古典主義時期一直到浪漫主義時期,歷經三百年的過程,它固然隨著潮流的變化走過來,但是「講究音樂與語言相互一致」的要求是始終如一的,也就是在歌劇中非常重視法語,而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輕歌劇的護軔與流行
輕歌劇(operetta〔義文及英文〕,Operette德文,operette〔法文〕)又稱喜歌劇,從其字意來看,是一種小型的歌劇,亦指十八世紀的一種歌劇型態。十八世紀的輕歌劇是指短的歌劇,而到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則是指輕鬆傷感的戲劇小品。輕歌劇與莊歌劇的不同處在於不使用宣敘調,也不使用大規模編制與浩大場面,並以常見的事物為主題而較少採用歷史或傳說為題材,形式簡單而通俗,其構成與內容包括口語對話、音樂、舞蹈,劇情則較偏重喜劇、諷刺、嘲弄、幽默、滑稽等。此類輕鬆歌劇發軔於法國,後來流傳到奧匈帝國、德國、英國,進而盛行於美國。一九二O年代後期,感傷的輕歌劇在美國開始轉型為現代的音樂喜劇(Musical Comedy或稱Musical Play),並風行全世界。
諷刺大師與輕歌劇
奧芬巴哈與孟德爾頌皆為音樂史上光芒四射的猶太作曲家,並與小約翰‧史特勞斯同享輕歌劇創始盛名,而被羅西尼稱為「香榭麗舍大道上的莫札特」。這位德裔法籍的輕歌劇作曲家,是以《天堂與地獄》和《霍夫曼的故事》等輕歌劇名作而聞名。奧芬巴哈在年輕時代,由於長期被拒於巴黎著名的喜歌劇院門外,而下定決心自組劇院演出自己的作品,遂於1855年藉著萬國博覽會在巴黎舉行之際,在香榭麗舍大道租了一間木造小劇院,經改裝後命名為「滑稽的巴黎人」劇院,並於同年7月5日正式開張推出節目,以配合熱鬧的萬國博覽會。奧芬巴哈製作了為數不少的輕鬆幽默、滑稽諷刺的獨幕劇,充分表現了他的才能與獨特的風格。雖然有的劇碼並不如預期叫座,但是以長時間來講應可用「屢演屢盛、造成轟動、極大成功」來形容,由於大眾熱烈的回響,使奧芬巴哈信心倍增,繼續以他慣用的華麗音樂要素配上多變化的手法加速他的創作。奧芬巴哈的旋律平易近人,緩慢時,具有牧歌的情趣;急速時,饒富活潑而且無窮的律動感,性格的表達上富有敏銳而靈巧的效果,大體而言,雖然沒有莊歌劇的莊嚴效果,但卻有大眾喜愛的通俗效果,因此能奠定輕歌劇的基石,從而獲得諷刺大師之美譽。
《霍夫曼的故事》永垂後世
奧芬巴哈在一生中寫下了大約一百餘部輕歌劇。在晚年時,生活趨於暗淡,雖然身患風濕與咳嗽,但仍傾全力譜寫鉅作《霍夫曼的故事》。
這部歌劇的題材是選自五幕劇「霍夫曼的幻想故事」,而這齣戲劇是由巴畢耶(Jules Barbier, 1822―1901)和卡瑞根據德國浪漫作家E. T. A. 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 1766―1822)的幾部小說改寫而成,而奧芬巴哈又從這部戲劇改寫成歌劇腳本,而在音樂的表達方面,奧芬巴哈除了保存原著的怪誕感之外,也充分運用一貫的輕鬆技巧,加上富於幻想情趣,將流暢旋律洋溢在整齣歌劇之中。譜寫工作完成之前,奧芬巴哈渴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此劇的上演,但由於過度勞累,以致尚未完成就告去世。過世後不久,由知己季侯(Ernst Guirand, 1837―1892)補筆完成,並於1881年2月10日在季侯的指揮下首度公演,而獲得極大的成功,使這部遺作永留後世。
奧芬巴哈在年幼時就對音樂極感興趣,但因身體孱弱無法正式學習音樂。九歲時毅然開始學習小提琴和大提琴,從此踏入音樂之途。十四歲移居巴黎之後便和歌劇結緣。爾後克盡萬難、堅持己見、打破傳統、創新局面,日以繼夜以歌劇為職志。他的創作都以觀眾的娛樂為主要目標,因此能夠掌握群眾的心理而創出輕歌劇,他的堅韌意志力和執著的創作態度相當值得後人效法,其作品永垂後世,精神永留人間。
國立台灣藝術學院教授
廖年斌
音樂家傳記新視野
傳記文學在整個文學及人類文化,占有相當的分量與地位。世界各民族起初以口語傳承民族、部族或原始社會英雄人物的事蹟;有了文字以後,就用筆記載偉大人物的傳記。
傳記因此被認為是歷史學的重要佐證,學界視其為歷史學的分支,極重要的史料。
傳記類書籍在我的藏書裡占了相當的分量,將近1,000本。這些傳記的範圍很廣,包括歷史人物(其實那一個不是歷史人物)、間諜、探險家、發明家、詩人、畫家、建築家等等。其中音樂家傳記就占了三分之二。
我有一個很大的毛病,那就是對某個特定人物感興趣時,除了蒐集在學術上受肯定的傳記以外,凡是在書店(幾乎是在國外)看到有關他們的傳記,或從書上讀到另有附人物圖像的好傳記,就會如在田野挖地瓜般,想盡辦法蒐購。結果是,書架上有關馬勒、莫札特的書就各超過100本。馬勒的研究在這幾年成為風氣,除了米契爾(D. Mitchel)及法國人拉•朗格(La Grange)以外,也有一些新近的研究,被挖掘出來的資料越來越多。
音樂家傳記與其他領域傳記最大的不同點,可能是與一般傑出人物的生涯不同。我們從很多傳記上的記載得悉,不少人物屬大器晚成型,如發明家愛迪生兒童時期的智能發展就比較慢;但音樂家與著名數理學者一樣,很早就展現驚人的天才。
依照學者的研究,音樂家的各種特殊技藝、才能,及數理學者驚人的計算能力,最容易被發現。通常一個人必須經過一段時間的學習、受教育及實務工作,從中自覺所長,並集中精力投注於此,才能磨練出才華及成就;但是音樂及數理方面的才華,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如上帝的恩寵,頭頂光環,因此很容易被發掘。
幾乎可以斷言,歷史上留名的大作曲家或演奏家,都有過一段神童時期。有些特異才華無法維持太久,過了幾年這種能力就消失。
在東方長幼有序、注重本分倫理的威權之下,天才很難得以發揮,沒有人栽培天才,就沒有天才生存的空間。但在西方有個特別的文化現象,即不管什麼年代都有「期待天才出現」的強烈願望,這可能與西方「等待救世主來臨」的宗教觀有關,西方各國肯定天才,對天才多方栽培的例子不勝枚舉。
有人認為天才不但要是神童,而且創作力必須維持到年邁時期甚至逝世為止;另外一個條件是作品多,而且要對當時及後世有影響才算數。
這樣的條件,令許多夭折的天才只能屈居為才子,無法封為天才。許多人認為天才都是英年早逝,但有些天才很長壽,可見天才夭折的說法,在科學昌明的廿世紀及即將來臨的廿一世紀,是近於妄斷的說法。
音樂家傳記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自傳;另外是由親友知已或學者所寫的傳記。十九世紀浪漫時期的特徵之一,就是對超現實的強烈慾望,或因想像所產生的幻想的現實,及由於對現實的不滿,而產生的超現實兩種不同的極端,因而產生了「為藝術而藝術」的藝術至上主義。在這種風潮下,自傳及一般傳記中的許多史實,不是將特定人物的幻想,或對人物的期許寫得如事實般,不然就是把紀實寫成神奇的超現實世界。例如莫札特死後不久,早期的傳記往往過分美化莫札特或將他太太康絲坦彩描述為稀世惡妻;貝多芬被捧為神聖不可觸及的樂聖、李斯特是情聖、舒伯特是窮途潦倒、永遠的失戀者。更可怕的是,將邁人廿一世紀的今天,這種陳腔濫調的傳記,還是充斥市面,不少樂迷都被誤導。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各國對古樂器的復原工作不遺餘力,利用各種資料、圖片、博物館收藏品及新科技,而有長足的進步,得以重現這些古音。同時因副本或印刷器材的發達,原譜不必靠手抄,使古樂譜的研究有突破性的成果, 加上文獻學的發達,以及各種週邊旁述,不同年代的演奏形式、技法漸漸地被分析出來。因此目前要聽所謂純正的巴洛克時期所使用的樂器、原譜、奏法、詮釋,及重現湮沒多年的古樂,已不再是夢想。同樣地,音樂史上的作曲家如巴哈、莫札特、貝多芬的面目,已經相當準確地重現,從事這方面的工作人員,不再只是苦心研究的學者,還包括許多業餘研究的經濟、社會、文化、醫事專業人員,從事精密的考證工作;著名音樂家的健康、遺傳病、死因、經濟收人、人際關係等,都有豐富的史料被發掘出來。因此第二次大戰後所出版的音樂家傳記,與十九世紀浪漫筆調下的描繪相距很遠。
十九世紀傳記中描述的音樂家愛情故事極端被美化,而當時極流行的書簡更是助長了這些故事。十九世紀名人所留下的書簡,有些是吐露內心的真話,有些卻是刻意寫給旁人看的,若要以之作為史料,史學者、傳記作者都要小心取捨。
優良傳記的標準是什麼?見人見智,很難有定論,但一定要忠於史實,不能私自塑造合乎自己理想的人物形象,不能偏頗或限於狹隘的觀點,要考慮時代性及政治、經濟、社會等廣泛的文化現象,但也要有自己的史觀。
讀了優良的傳記後,重新聆聽這些音樂家的作品,會增加多層面的體會與瞭解。雖然音樂以音響觸發聽者的想像力,有些是普遍的理念,有些是作曲者強烈主觀所訴求的情感,與作曲家的個性及所追求的目標有密切關係。因此我鼓勵真正喜歡音樂的年輕人,只要有時間,多閱讀傳記。馬勒、莫札特、巴哈的傳記或研究書籍,我各有一百多本,但我還是繼續在買,看起來雖是重複,但每一本都有他們研究的成果,即使是同一件事,也有不同的獨特見解。當然,當作工具書的葛羅夫(Grove)音樂大辭典,都是由樂界的權威人士所執筆,比差勁的傳記可靠,但優良的傳記更富於情感、更有深人的見解,當作工具書也很可靠。
由於喜歡讀傳記,不知不覺中對這些音樂家最後的居所有所知悉。因此旅遊時,我都會去憑弔這些音樂家的墓地或他們曾經居住過的居所。看到這些文物器具,會讓你像突然走入「時間隧道」般,回到幾百年前的景象,與這些作曲家的心靈交流。那種感觸與感動難以言喻。
旅遊時,我除了參觀美術館、音樂博物館、上劇院、看音樂廳、拍攝大教堂及管風琴外,音樂家的史蹟或墓園都列人行程,會對這些地方產生興趣或好奇,大半是讀了傳記而引發的。
讀好的音樂家傳記,如聽好音樂,對人的一生、才華、成就,可以做烏瞰式的觀察,對同時代人造成衝擊,對後代產生影響,並可以培養人們閱讀歷史的技巧;而且有些文章如文學作品般巧妙雋永,讀來回味無窮。
這套由Omnibus出版的音樂家傳記系列,英文原版我幾乎都有,因為內容比聞名的葛羅夫音樂大辭典更深人,對每一個音樂家所處時代,有清楚的定位,應用最新研究資料,附加適宜的註解及推薦相關書籍,幾乎可以當作工具書,其中有些作者是樂界的權威人士。對音樂家及其作品想要有更深人瞭解或欣賞的有心人,這是一套良好的讀物。
資深樂評人
曹永坤
――――――――――――
講究音樂與語言一致的法國歌劇
法國的歌劇與歐洲其他國家相比,其形成顯得較為特異。十八世紀初葉以前,法國以外其他國家的歌劇均或多或少受到義大利歌劇的影響。公元1620年前後,義大利歌劇已在德語系的各大城市上演,並於1700年的前後受到英國的青睞。而法國雖於1645年後,有上演過義大利歌劇幕間短劇的記錄,但是這些零星上演過的短劇,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就漸漸式微。以法國宮廷和義大利在血緣上密切的關係以及文化上的頻繁交流來看,法國理應相當容易接受義大利歌劇,但義大利歌劇卻沒有在法國生根。雖然法國人自十六世紀以來一直喜愛舞劇,並以舞劇為宮廷的主要娛樂,另外以神話故事為題材的音樂劇也在十七世紀盛行,但是法國的歌劇自始一直刻意擺脫義大利和德國歌劇的影響,這其間從古典主義時期一直到浪漫主義時期,歷經三百年的過程,它固然隨著潮流的變化走過來,但是「講究音樂與語言相互一致」的要求是始終如一的,也就是在歌劇中非常重視法語,而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輕歌劇的護軔與流行
輕歌劇(operetta〔義文及英文〕,Operette德文,operette〔法文〕)又稱喜歌劇,從其字意來看,是一種小型的歌劇,亦指十八世紀的一種歌劇型態。十八世紀的輕歌劇是指短的歌劇,而到了十九世紀與二十世紀,則是指輕鬆傷感的戲劇小品。輕歌劇與莊歌劇的不同處在於不使用宣敘調,也不使用大規模編制與浩大場面,並以常見的事物為主題而較少採用歷史或傳說為題材,形式簡單而通俗,其構成與內容包括口語對話、音樂、舞蹈,劇情則較偏重喜劇、諷刺、嘲弄、幽默、滑稽等。此類輕鬆歌劇發軔於法國,後來流傳到奧匈帝國、德國、英國,進而盛行於美國。一九二O年代後期,感傷的輕歌劇在美國開始轉型為現代的音樂喜劇(Musical Comedy或稱Musical Play),並風行全世界。
諷刺大師與輕歌劇
奧芬巴哈與孟德爾頌皆為音樂史上光芒四射的猶太作曲家,並與小約翰‧史特勞斯同享輕歌劇創始盛名,而被羅西尼稱為「香榭麗舍大道上的莫札特」。這位德裔法籍的輕歌劇作曲家,是以《天堂與地獄》和《霍夫曼的故事》等輕歌劇名作而聞名。奧芬巴哈在年輕時代,由於長期被拒於巴黎著名的喜歌劇院門外,而下定決心自組劇院演出自己的作品,遂於1855年藉著萬國博覽會在巴黎舉行之際,在香榭麗舍大道租了一間木造小劇院,經改裝後命名為「滑稽的巴黎人」劇院,並於同年7月5日正式開張推出節目,以配合熱鬧的萬國博覽會。奧芬巴哈製作了為數不少的輕鬆幽默、滑稽諷刺的獨幕劇,充分表現了他的才能與獨特的風格。雖然有的劇碼並不如預期叫座,但是以長時間來講應可用「屢演屢盛、造成轟動、極大成功」來形容,由於大眾熱烈的回響,使奧芬巴哈信心倍增,繼續以他慣用的華麗音樂要素配上多變化的手法加速他的創作。奧芬巴哈的旋律平易近人,緩慢時,具有牧歌的情趣;急速時,饒富活潑而且無窮的律動感,性格的表達上富有敏銳而靈巧的效果,大體而言,雖然沒有莊歌劇的莊嚴效果,但卻有大眾喜愛的通俗效果,因此能奠定輕歌劇的基石,從而獲得諷刺大師之美譽。
《霍夫曼的故事》永垂後世
奧芬巴哈在一生中寫下了大約一百餘部輕歌劇。在晚年時,生活趨於暗淡,雖然身患風濕與咳嗽,但仍傾全力譜寫鉅作《霍夫曼的故事》。
這部歌劇的題材是選自五幕劇「霍夫曼的幻想故事」,而這齣戲劇是由巴畢耶(Jules Barbier, 1822―1901)和卡瑞根據德國浪漫作家E. T. A. 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 1766―1822)的幾部小說改寫而成,而奧芬巴哈又從這部戲劇改寫成歌劇腳本,而在音樂的表達方面,奧芬巴哈除了保存原著的怪誕感之外,也充分運用一貫的輕鬆技巧,加上富於幻想情趣,將流暢旋律洋溢在整齣歌劇之中。譜寫工作完成之前,奧芬巴哈渴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此劇的上演,但由於過度勞累,以致尚未完成就告去世。過世後不久,由知己季侯(Ernst Guirand, 1837―1892)補筆完成,並於1881年2月10日在季侯的指揮下首度公演,而獲得極大的成功,使這部遺作永留後世。
奧芬巴哈在年幼時就對音樂極感興趣,但因身體孱弱無法正式學習音樂。九歲時毅然開始學習小提琴和大提琴,從此踏入音樂之途。十四歲移居巴黎之後便和歌劇結緣。爾後克盡萬難、堅持己見、打破傳統、創新局面,日以繼夜以歌劇為職志。他的創作都以觀眾的娛樂為主要目標,因此能夠掌握群眾的心理而創出輕歌劇,他的堅韌意志力和執著的創作態度相當值得後人效法,其作品永垂後世,精神永留人間。
國立台灣藝術學院教授
廖年斌
目次
原著致謝詞
總序 音樂家傳記新視野
導讀 講究音樂與語言一致的法國歌劇
1. 楔子
2. 科隆的奧先生
3. 擠身作曲家的行列
4. 滑稽的巴黎人劇院
5. 香榭麗舍大道上的莫札特
6. 《奧菲歐》到維也納
7. 《巴黎人的生活》
8. 月亮之旅
9. 落幕
10. 奧芬巴哈過世
尾聲
作品目錄
參考文獻
譯名對照表
總序 音樂家傳記新視野
導讀 講究音樂與語言一致的法國歌劇
1. 楔子
2. 科隆的奧先生
3. 擠身作曲家的行列
4. 滑稽的巴黎人劇院
5. 香榭麗舍大道上的莫札特
6. 《奧菲歐》到維也納
7. 《巴黎人的生活》
8. 月亮之旅
9. 落幕
10. 奧芬巴哈過世
尾聲
作品目錄
參考文獻
譯名對照表
書摘/試閱
1
楔子
我深感榮幸,幾乎所有人都對拙作《費加洛》(Figaro)中為方舞(quadrille)和華爾滋所配之音樂非常欣賞。人們口中所談的只有《費加洛》,除了《費加洛》以外,沒有其他的歌劇被演奏或演唱,沒有其他的歌劇能像《費加洛》那樣吸引觀眾的注意,只有,只有《費加洛》。對我而言,這當然是至高無上的榮幸!
1787年,沃夫岡‧阿瑪麵斯‧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從布拉格(Prague)寫了封信給他的一位年輕門生──加菲德‧馮‧賈侃(Gottfried von Jacquin)男爵,快樂之情溢於字裏行間。
莫札特的寥寥數語已深刻表達出當一位藝術家的創作為全世界所共享之後的快樂。在這個階段的歷史中,這代表了由長久束縛、激怒音樂家的禁錮中的一種解放。在沒有其他方法謀生之時,能夠有貴族和富豪的資助,他們的確該心存感激;但是這種情形也可能變成一種專橫,使得溫厚如海頓(Haydn)者也難以忍受,使莫札特心生厭煩,讓貝多芬痛恨並不惜與之為敵。公眾音樂會的需求日漸殷切雖有所助益,但主要還是劇院逐漸提供逃離這種境況的管道。敘述需時數十年的轉變過程往往有過度簡化之虞,而且情況會因國家或個人的不同而有差異,不過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已可明顯看出藝術家的地位的改變和音樂作品的逐漸商品化。
這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變遷。財富逐步由貴族階級和富有的上層中產階級商人手中釋放出來,首先是到龐大、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手中,十九世紀未才擴及勞動階層。作曲家和作家愈來愈可以依賴簡單的商業法則:提供大眾所喜歡的商品,你便能賺錢。在今天,商業或是「流行」的音樂世界完全不同於學院派或所謂「嚴肅」音樂;作曲家如艾文‧柏林(Irving Berlin)和理察‧羅傑斯(Richard Rodgers)之流若發現人們並不哼唱他們的作品,心情一定不好,因為他們擺明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創作。比起那些依賴官方贊助(如同過去依賴貴族)的「嚴肅」作曲家,他們才是真正繼承莫札特、盧利(Lully)、羅西尼(Rossini),董尼才悌(Donizetti)和奧芬巴哈的傳統。
音樂(特別是劇院音樂)應該是為「每一個人」所作,莫札特信中所寫的,正是這種觀念的表徵。「為藝術而藝術」以及「為大眾而作」的分歧在莫札特的時代僅初露端倪而已,其後至少六十年間,作曲家順應此一情勢,因為愈來愈多的人們負擔得起娛樂的花費,也因此要求能夠符合他們「非學院」品味的作品。當觀眾愈來愈多,劇院如雨後春筍般地興建,舞廳也家家客滿;而競爭日趨激烈之際,作家也不斷快速、有效率的推陳出新,以因應市場的需求。諾維洛(Novello)在英國開風氣之先,推出大量價格低廉的音樂作品,同樣刺激了家庭音樂的需求。
全球最偉大的歌劇院,如米蘭的史卡拉(La Scala)劇院,巴黎歌劇院、倫敦的柯芬園(Covent Garden)歌劇院都是於十八世紀末興建完成,後來也都紛紛重建,除了因劇院內部蠟燭、煤氣燈光設備常導致火災,被迫不得不重建之外,這些歌劇院在十九世紀初也都進行了擴建和現代化的工程。有趣的是,由於十九世紀後半葉勞動階層的觀眾對音樂的需求日益殷切,到了1868年,在倫敦就有兩百場的首演,另外散布英倫各島還有三百多場的演出。
「一般大眾」(很難界定的一群)的需求,簡而言之,即是希望舞台上能演出一篇連貫的故事(也因此逐漸以口語對白取代凌亂無序的宣敘調〔recitative〕,並使劇情流暢進行),可以哼唱的美妙曲調,另外還有舞蹈,以及琳琅滿目的壯觀場面。例如,巴黎歌劇院即長期聘僱一龐大的芭蕾舞團,不管對情節是否有助益,只要是歌劇搬上舞台,都應有芭蕾配合。著名的作曲家都會溫順地遵從這項要求。
繼《費加洛婚禮》輕快、旋律豐富的傳統之後,接著登場的是歌劇黃金時代的義大利大作曲家──羅西尼(Gioacchino Rossini. 1792―1868),他於1816年所作的《塞維里亞的理髮師》(I1 Barbiere di Siviglia)很快就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在他最後一齣鉅作《威廉泰爾》(wi11iam Tell)在巴黎歌劇院(其中包括芭蕾和壯觀場面)登場之前,還有許多作品;威爾第(Giuseppe Verdi, 1813―1901)的《弄臣》(Rigoletto, 1851)、《遊唱詩人》(I1 Trovatore, 1853)以及《荼花女》(La Traviata, 1853)盛演不衰;此外還有貝里尼(Vincenzo Be11ini, 1801―1835)和董尼才悌(1797―1848)。
以此角度來看,1840年董尼才悌首演於巴黎喜歌劇院的《聯隊之花》(La Fille du Regiment),可說是喜歌劇史上一個真正的轉捩點。這齣喜歌劇旋律豐富,配上正合時宜的故事情節以及搭配良好的合唱,幽默感十足,它為當時的僕僮、手風琴師以及波卡舞及方舞的編舞者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確實,如果我們重聽如瑪麗亞《每個人知道,每個人講》(Chacun le sait, chacun le dit)之類的抒情調,並能看出《聯隊》的優點,那麼我們才算進入輕歌劇的世界。不絕於耳的鼓聲與喇叭聲和對軍旅生涯的諷刺,幾乎也成為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輕歌劇大部分寫作題材的來源。
如果說巴黎是歌劇革命的溫床,不僅僅是因為外國作曲家發現這裏是個有利可圖的市場。法國作曲家同樣也在莫札特的影響下,在喜歌劇(opera comique)的型式下逐漸建立起自己特殊的輕歌劇,風格足以媲美義大利的諧歌劇(opera buffa)。同樣有活潑的對話,獨立的詠歎調,押韻詩和合唱曲。創作曲調通俗但出身音樂學院的作曲家,如法蘭斯華‧波伊迪厄(Francois Boieldieu, 1775―1834)、丹尼‧奧伯(Daniel Auber, 1782―1871),費迪南‧艾侯(Ferdinand Herold, 1791―1833)和阿道夫‧亞當(Ado1phe Adam, 1803―1856),他們追隨盧利、葛魯克(Christoph Wi11ibald Gluck)、葛雷特里(Andre Gretry)及梅裕爾(Etienne Nicolas Mehul)等前輩的腳步,如今他們創作的簡潔有力的序曲比歌劇本身還要為人所知。這些作曲家,加上幾位義大利和德國作曲家如奧托‧尼可萊(Otto Nicolai, 1810―1849),成為1850年代逐漸嶄露頭角的年輕作曲家所必須超越的對手。
到1850年,對任何一個能夠在複雜熱鬧的音樂環境(特別是在巴黎)認清方向的人,音樂可以分成兩條路。所需要的只是一個能踢出臨門一腳的人物,也許是一個領袖,甚或一個替罪羔羊。總的來說,若將所有的榮耀都歸於一個人身上可能並不明智,但若一定要找出一位法國輕歌劇真正創始人,那就非奧芬巴哈莫屬。這位來自德國科隆(Cologne)的年輕猶太音樂家,於1835年離開巴黎音樂院之後,就投身競爭激烈的音樂世界;也就在孕育他音樂才華的巴黎,使輕歌劇成為獨特的樂種。即使沒有奧芬巴哈,輕歌劇還是可能會產生。他是在十分不利的環境中被推上歷史地位,同時也激勵許多他國音樂家的崛起:在英國激發了吉伯特和蘇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在維也納則是約翰‧史特勞斯二世(Johann Strauss II),經過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在西班牙札瑞拉(zarzuela)中,我們不難發現奧芬巴哈的餘音?如艾維(Herve)等對手雖然也曾挑戰奧芬巴哈在輕歌劇的領導地位,但奧芬巴哈持續不斷的毅力與冒險,還是勝於其他人。這種以輕歌劇(operetta)、諧歌劇(opera-bouffe),輕歌劇(light operetta)和後來的音樂喜劇或音樂劇(musical)之名的嶄新、商業而通俗的樂種,它的興起必須要歸功(或怪罪)於奧芬巴哈。縱使現今仍有許多人認為這不全然是好事,但撇開偏見不談,奧芬巴哈在音樂改革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影響之深遠堪與任何政治或工業革命人物相若。
楔子
我深感榮幸,幾乎所有人都對拙作《費加洛》(Figaro)中為方舞(quadrille)和華爾滋所配之音樂非常欣賞。人們口中所談的只有《費加洛》,除了《費加洛》以外,沒有其他的歌劇被演奏或演唱,沒有其他的歌劇能像《費加洛》那樣吸引觀眾的注意,只有,只有《費加洛》。對我而言,這當然是至高無上的榮幸!
1787年,沃夫岡‧阿瑪麵斯‧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從布拉格(Prague)寫了封信給他的一位年輕門生──加菲德‧馮‧賈侃(Gottfried von Jacquin)男爵,快樂之情溢於字裏行間。
莫札特的寥寥數語已深刻表達出當一位藝術家的創作為全世界所共享之後的快樂。在這個階段的歷史中,這代表了由長久束縛、激怒音樂家的禁錮中的一種解放。在沒有其他方法謀生之時,能夠有貴族和富豪的資助,他們的確該心存感激;但是這種情形也可能變成一種專橫,使得溫厚如海頓(Haydn)者也難以忍受,使莫札特心生厭煩,讓貝多芬痛恨並不惜與之為敵。公眾音樂會的需求日漸殷切雖有所助益,但主要還是劇院逐漸提供逃離這種境況的管道。敘述需時數十年的轉變過程往往有過度簡化之虞,而且情況會因國家或個人的不同而有差異,不過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已可明顯看出藝術家的地位的改變和音樂作品的逐漸商品化。
這本質上是一種社會變遷。財富逐步由貴族階級和富有的上層中產階級商人手中釋放出來,首先是到龐大、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手中,十九世紀未才擴及勞動階層。作曲家和作家愈來愈可以依賴簡單的商業法則:提供大眾所喜歡的商品,你便能賺錢。在今天,商業或是「流行」的音樂世界完全不同於學院派或所謂「嚴肅」音樂;作曲家如艾文‧柏林(Irving Berlin)和理察‧羅傑斯(Richard Rodgers)之流若發現人們並不哼唱他們的作品,心情一定不好,因為他們擺明就是為了這個目的而創作。比起那些依賴官方贊助(如同過去依賴貴族)的「嚴肅」作曲家,他們才是真正繼承莫札特、盧利(Lully)、羅西尼(Rossini),董尼才悌(Donizetti)和奧芬巴哈的傳統。
音樂(特別是劇院音樂)應該是為「每一個人」所作,莫札特信中所寫的,正是這種觀念的表徵。「為藝術而藝術」以及「為大眾而作」的分歧在莫札特的時代僅初露端倪而已,其後至少六十年間,作曲家順應此一情勢,因為愈來愈多的人們負擔得起娛樂的花費,也因此要求能夠符合他們「非學院」品味的作品。當觀眾愈來愈多,劇院如雨後春筍般地興建,舞廳也家家客滿;而競爭日趨激烈之際,作家也不斷快速、有效率的推陳出新,以因應市場的需求。諾維洛(Novello)在英國開風氣之先,推出大量價格低廉的音樂作品,同樣刺激了家庭音樂的需求。
全球最偉大的歌劇院,如米蘭的史卡拉(La Scala)劇院,巴黎歌劇院、倫敦的柯芬園(Covent Garden)歌劇院都是於十八世紀末興建完成,後來也都紛紛重建,除了因劇院內部蠟燭、煤氣燈光設備常導致火災,被迫不得不重建之外,這些歌劇院在十九世紀初也都進行了擴建和現代化的工程。有趣的是,由於十九世紀後半葉勞動階層的觀眾對音樂的需求日益殷切,到了1868年,在倫敦就有兩百場的首演,另外散布英倫各島還有三百多場的演出。
「一般大眾」(很難界定的一群)的需求,簡而言之,即是希望舞台上能演出一篇連貫的故事(也因此逐漸以口語對白取代凌亂無序的宣敘調〔recitative〕,並使劇情流暢進行),可以哼唱的美妙曲調,另外還有舞蹈,以及琳琅滿目的壯觀場面。例如,巴黎歌劇院即長期聘僱一龐大的芭蕾舞團,不管對情節是否有助益,只要是歌劇搬上舞台,都應有芭蕾配合。著名的作曲家都會溫順地遵從這項要求。
繼《費加洛婚禮》輕快、旋律豐富的傳統之後,接著登場的是歌劇黃金時代的義大利大作曲家──羅西尼(Gioacchino Rossini. 1792―1868),他於1816年所作的《塞維里亞的理髮師》(I1 Barbiere di Siviglia)很快就成為當時最受歡迎的作品之一,在他最後一齣鉅作《威廉泰爾》(wi11iam Tell)在巴黎歌劇院(其中包括芭蕾和壯觀場面)登場之前,還有許多作品;威爾第(Giuseppe Verdi, 1813―1901)的《弄臣》(Rigoletto, 1851)、《遊唱詩人》(I1 Trovatore, 1853)以及《荼花女》(La Traviata, 1853)盛演不衰;此外還有貝里尼(Vincenzo Be11ini, 1801―1835)和董尼才悌(1797―1848)。
以此角度來看,1840年董尼才悌首演於巴黎喜歌劇院的《聯隊之花》(La Fille du Regiment),可說是喜歌劇史上一個真正的轉捩點。這齣喜歌劇旋律豐富,配上正合時宜的故事情節以及搭配良好的合唱,幽默感十足,它為當時的僕僮、手風琴師以及波卡舞及方舞的編舞者提供了豐富的素材。確實,如果我們重聽如瑪麗亞《每個人知道,每個人講》(Chacun le sait, chacun le dit)之類的抒情調,並能看出《聯隊》的優點,那麼我們才算進入輕歌劇的世界。不絕於耳的鼓聲與喇叭聲和對軍旅生涯的諷刺,幾乎也成為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輕歌劇大部分寫作題材的來源。
如果說巴黎是歌劇革命的溫床,不僅僅是因為外國作曲家發現這裏是個有利可圖的市場。法國作曲家同樣也在莫札特的影響下,在喜歌劇(opera comique)的型式下逐漸建立起自己特殊的輕歌劇,風格足以媲美義大利的諧歌劇(opera buffa)。同樣有活潑的對話,獨立的詠歎調,押韻詩和合唱曲。創作曲調通俗但出身音樂學院的作曲家,如法蘭斯華‧波伊迪厄(Francois Boieldieu, 1775―1834)、丹尼‧奧伯(Daniel Auber, 1782―1871),費迪南‧艾侯(Ferdinand Herold, 1791―1833)和阿道夫‧亞當(Ado1phe Adam, 1803―1856),他們追隨盧利、葛魯克(Christoph Wi11ibald Gluck)、葛雷特里(Andre Gretry)及梅裕爾(Etienne Nicolas Mehul)等前輩的腳步,如今他們創作的簡潔有力的序曲比歌劇本身還要為人所知。這些作曲家,加上幾位義大利和德國作曲家如奧托‧尼可萊(Otto Nicolai, 1810―1849),成為1850年代逐漸嶄露頭角的年輕作曲家所必須超越的對手。
到1850年,對任何一個能夠在複雜熱鬧的音樂環境(特別是在巴黎)認清方向的人,音樂可以分成兩條路。所需要的只是一個能踢出臨門一腳的人物,也許是一個領袖,甚或一個替罪羔羊。總的來說,若將所有的榮耀都歸於一個人身上可能並不明智,但若一定要找出一位法國輕歌劇真正創始人,那就非奧芬巴哈莫屬。這位來自德國科隆(Cologne)的年輕猶太音樂家,於1835年離開巴黎音樂院之後,就投身競爭激烈的音樂世界;也就在孕育他音樂才華的巴黎,使輕歌劇成為獨特的樂種。即使沒有奧芬巴哈,輕歌劇還是可能會產生。他是在十分不利的環境中被推上歷史地位,同時也激勵許多他國音樂家的崛起:在英國激發了吉伯特和蘇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在維也納則是約翰‧史特勞斯二世(Johann Strauss II),經過一連串的連鎖反應,在西班牙札瑞拉(zarzuela)中,我們不難發現奧芬巴哈的餘音?如艾維(Herve)等對手雖然也曾挑戰奧芬巴哈在輕歌劇的領導地位,但奧芬巴哈持續不斷的毅力與冒險,還是勝於其他人。這種以輕歌劇(operetta)、諧歌劇(opera-bouffe),輕歌劇(light operetta)和後來的音樂喜劇或音樂劇(musical)之名的嶄新、商業而通俗的樂種,它的興起必須要歸功(或怪罪)於奧芬巴哈。縱使現今仍有許多人認為這不全然是好事,但撇開偏見不談,奧芬巴哈在音樂改革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其影響之深遠堪與任何政治或工業革命人物相若。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