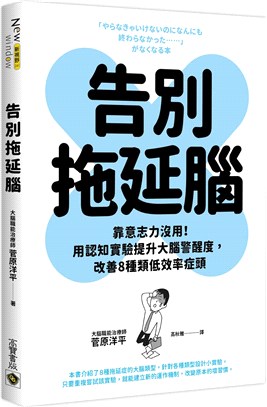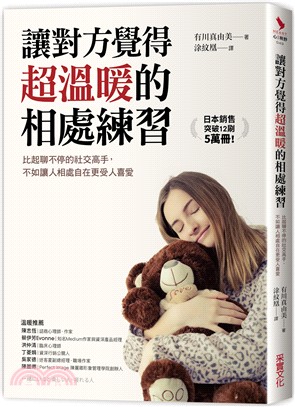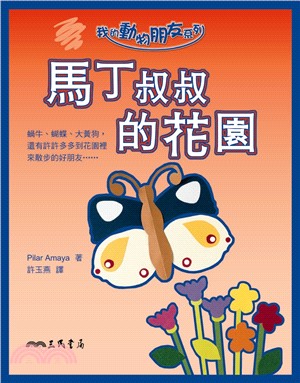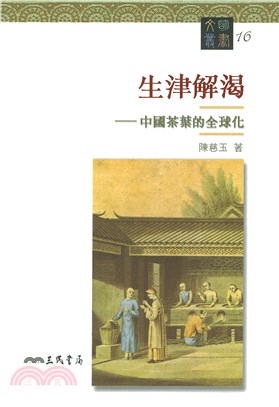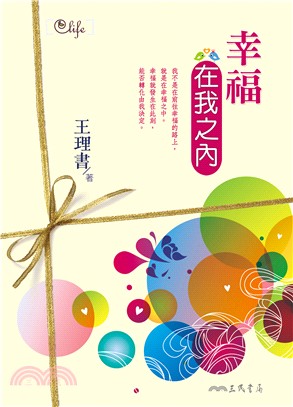我的痛苦有名字嗎?:瘋狂而古怪,傲慢又聰明的女子們--不被理解的痛楚,女性憂鬱症
商品資訊
系列名:MARK系列
ISBN13:9786267206775
替代書名:미쳐있고 괴상하며 오만하고 똑똑한 여자들
出版社:大塊文化
作者:河美娜
譯者:徐小為
出版日:2023/03/07
裝訂/頁數:平裝/336頁
規格:21cm*15cm*2.3cm (高/寬/厚)
版次:1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為什麼20、30歲的女性容易得憂鬱症?
會得憂鬱症不是因為「本來就有病」
讓她們以自己的語言述說
擺脫醫學疾病與社會汙名的定義
替女性書寫全新的受苦簡史
--推薦--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王雅涵 諮商心理師
胡展誥 諮商心理師
陳志恆 諮商心理師、暢銷作家
蘇益賢 臨床心理師
「這本書點出了值得被看見與探討的觀點。」――陳志恆 諮商心理師、暢銷作家
「本書以女性為視角,搭配調查、醫學歷史與個案經驗,補足了相關領域更多延伸的讀本,相信能對許多讀者有助益。」――蘇益賢 臨床心理師
從2003至2020年,南韓屢次成為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自殺率最高的國家,而「憂鬱症」被指出是自殺率居高不下的罪魁禍首,一直以來都被視為造成社會問題的成因。近年來,有越來越多20、30歲的女性被診斷出患有心理疾病,而20歲女性的自殺率也節節升高,2020年,南韓20-29歲的女性自殺人數比去年多出了40%。年輕女性的自殺問題如此嚴重,南韓當局已將20、30多歲的女性列為官方自殺危險群。
求助精神科醫師的人越來越多,也開始接連出現分享自身罹病經驗的著述。不過,作者認為,雖然這些疾病經驗的敘事十分重要,但如果只以「個人經驗」的形式來省思憂鬱症,就難以從社會及歷史脈絡的角度來檢視這個被稱為憂鬱症的疾病,而我們對憂鬱症成因的解釋,也會因此只限縮在探討患者身處的環境與個性。
為什麼2、30歲的女性會得憂鬱症?本書作者自己也是躁鬱症患者,並察覺了心理疾病並非單純是個人問題。她在書中訪談了三十一名2、30歲女性憂鬱症患者,並結合了自身的精神醫學知識、親身面對醫療不公的經驗,耗費兩年的時間寫成了此書。
本書採取了全新的觀點,使用患者自身的語言,重新定義了名為「憂鬱症」的痛苦,打造了一個面向大眾的公共溝通平台,讓眾人能互相討論共有的受苦經驗,並提出更平等面對憂鬱症的看法。
正如同美國作家兼詩人安妮.波爾所說:「疾病的歷史並非醫學的歷史,而是世界的歷史」。本書作者擺脫了醫學疾病與社會汙名的定義,替女性書寫了一部全新的受苦簡史,而這是讓一個文化理解痛苦的方式開始產生改變的起始點。作者讓罹患憂鬱相關疾病的女性們用自己的語言說話,不再讓醫生和諮商師奪走詮釋她們的主導權,而是成為自己人生的作者,採訪對象包含韓國及海外的韓國女性,學歷橫跨高中畢業至研究所畢業。
會得憂鬱症不是因為「本來就有病」
讓她們以自己的語言述說
擺脫醫學疾病與社會汙名的定義
替女性書寫全新的受苦簡史
--推薦--
(依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王雅涵 諮商心理師
胡展誥 諮商心理師
陳志恆 諮商心理師、暢銷作家
蘇益賢 臨床心理師
「這本書點出了值得被看見與探討的觀點。」――陳志恆 諮商心理師、暢銷作家
「本書以女性為視角,搭配調查、醫學歷史與個案經驗,補足了相關領域更多延伸的讀本,相信能對許多讀者有助益。」――蘇益賢 臨床心理師
從2003至2020年,南韓屢次成為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中自殺率最高的國家,而「憂鬱症」被指出是自殺率居高不下的罪魁禍首,一直以來都被視為造成社會問題的成因。近年來,有越來越多20、30歲的女性被診斷出患有心理疾病,而20歲女性的自殺率也節節升高,2020年,南韓20-29歲的女性自殺人數比去年多出了40%。年輕女性的自殺問題如此嚴重,南韓當局已將20、30多歲的女性列為官方自殺危險群。
求助精神科醫師的人越來越多,也開始接連出現分享自身罹病經驗的著述。不過,作者認為,雖然這些疾病經驗的敘事十分重要,但如果只以「個人經驗」的形式來省思憂鬱症,就難以從社會及歷史脈絡的角度來檢視這個被稱為憂鬱症的疾病,而我們對憂鬱症成因的解釋,也會因此只限縮在探討患者身處的環境與個性。
為什麼2、30歲的女性會得憂鬱症?本書作者自己也是躁鬱症患者,並察覺了心理疾病並非單純是個人問題。她在書中訪談了三十一名2、30歲女性憂鬱症患者,並結合了自身的精神醫學知識、親身面對醫療不公的經驗,耗費兩年的時間寫成了此書。
本書採取了全新的觀點,使用患者自身的語言,重新定義了名為「憂鬱症」的痛苦,打造了一個面向大眾的公共溝通平台,讓眾人能互相討論共有的受苦經驗,並提出更平等面對憂鬱症的看法。
正如同美國作家兼詩人安妮.波爾所說:「疾病的歷史並非醫學的歷史,而是世界的歷史」。本書作者擺脫了醫學疾病與社會汙名的定義,替女性書寫了一部全新的受苦簡史,而這是讓一個文化理解痛苦的方式開始產生改變的起始點。作者讓罹患憂鬱相關疾病的女性們用自己的語言說話,不再讓醫生和諮商師奪走詮釋她們的主導權,而是成為自己人生的作者,採訪對象包含韓國及海外的韓國女性,學歷橫跨高中畢業至研究所畢業。
作者簡介
河美娜(하미나)
1991年生,紀實作家。
為了學習科學哲學,大學同時主修了地球環境學系及哲學系。進入科學史及科學哲學聯合研究所後,稍微拐了個彎開始學習科學史。同時並參與2016年「江南站女性目標殺人事件」後正式營運的女性運動組織「Femidangdang」。此時也為日漸嚴重的憂鬱症所苦,便以此作為碩士學位論文主題,終於得以脫離研究所。
為了生計曾經歷過專欄作家、科學記者、寫作教師等各種職業,最後決心成為一名作家,目前為《時事IN》、《韓民族21》、《韓國日報》等韓國各大媒體撰寫短文。《我的痛苦有名字嗎》則是她將至今的研究、與人們的相遇和自身煩惱集結而成的第一本書。
譯者簡介
徐小為
政治大學韓語系畢業。愛好閱讀,樂於生活,喜歡把看懂的什麼說給人聽,便開始翻譯的日子。
序
【自序】
作者序
一些關於憂鬱症故事的事
憂鬱症這個主題實在過於龐大而複雜,讓人無法簡單俐落地建構出一個恰如其分的故事。想要理出頭緒,將它的結構整理得一目了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決定以重複出現的主題為主,採取將故事們綁在一起的方式進行。就像一起手牽著手探索名為憂鬱症的迷宮,走過各種不同的路,一一試著打開路上每個房間的大門一樣。有些房間待得久一點,有些房間則只有短暫停留;有些房間擠滿了人,有些房間則空空如也;有個房間都是學者,但有些房間則充滿了當事人。希望像這樣一起走過一些路之後,各位可以用和從前稍微不太一樣的角度去看待憂鬱症。
這本書的內容集結了我大學時主修科學史,並同時進行憂鬱症研究時學到的東西,以及三十位二、三十歲女性的專訪,還有躁鬱症當事人─我的個人經驗。就像世上所有對話一樣,訪問也是一種政治,所以受訪者回應的內容常常是採訪者提問時意圖得到的答案。問了受害的事情,就只以受害者的角度回答,問了生病的事,則只給出病人為主的答案。
然而憂鬱並非簡單的問題,人類也不是如此單純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麼我會進行至少超過一年的採訪,和受訪者在各種不同的場所相聚,透過面對面採訪及書寫等各種方式交換彼此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總會率先對她們吐露自己的病史。因為訪問也是患者之間的一種聚會。
之後我將包含受訪者個人故事的稿件全都給當事人看過,並向她們得到了出版的許可。願意公開的受訪者使用本名,不願意公開的人則使用自己想用的假名。受訪者們大部分來自首爾或南韓首都圈,但也有出身大邱、釜山、春川、海外的人。而她們全都了解憂鬱症相關的醫學資訊,更重要的是她們有辦法用自己的語言訴說自身故事,能用自己的話講述自己的人生,這的確是一種特權。
儘管身處傷痛之中,這些受訪者們也在反芻自己經驗數千次,再經過重新剖析後獲得了成長。雖然她們是家庭暴力、性暴力的受害者,但同時也是親自控訴被害事實,想盡辦法讓改變發生的倖存者。她們自我感知不對勁,靠著自己的雙腳走向醫院。雖然需要照顧,但她們自己其實也是長久以來提供照顧的人。她們不願意一直只停留在接受幫助的位置。她們全然使用自己的語言發聲,不被醫生、諮商師或其他任何人奪走說明的主導權。這些故事之中存在著矛盾與混亂,因為她們並非浮在真空中的受害者,而是真正的人類。
雖然開啟這個故事的人是我,但為故事作結的並不是。我不想替和我相遇的這些女子貼上憂鬱症、焦慮症、邊緣性人格障礙的標籤並加以區分。我更想成為一個擁護者,去捍衛她們述說的這些故事。書寫自己人生的女人,某種程度上都是瘋子。
作者序
一些關於憂鬱症故事的事
憂鬱症這個主題實在過於龐大而複雜,讓人無法簡單俐落地建構出一個恰如其分的故事。想要理出頭緒,將它的結構整理得一目了然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決定以重複出現的主題為主,採取將故事們綁在一起的方式進行。就像一起手牽著手探索名為憂鬱症的迷宮,走過各種不同的路,一一試著打開路上每個房間的大門一樣。有些房間待得久一點,有些房間則只有短暫停留;有些房間擠滿了人,有些房間則空空如也;有個房間都是學者,但有些房間則充滿了當事人。希望像這樣一起走過一些路之後,各位可以用和從前稍微不太一樣的角度去看待憂鬱症。
這本書的內容集結了我大學時主修科學史,並同時進行憂鬱症研究時學到的東西,以及三十位二、三十歲女性的專訪,還有躁鬱症當事人─我的個人經驗。就像世上所有對話一樣,訪問也是一種政治,所以受訪者回應的內容常常是採訪者提問時意圖得到的答案。問了受害的事情,就只以受害者的角度回答,問了生病的事,則只給出病人為主的答案。
然而憂鬱並非簡單的問題,人類也不是如此單純的存在。這就是為什麼我會進行至少超過一年的採訪,和受訪者在各種不同的場所相聚,透過面對面採訪及書寫等各種方式交換彼此的故事。更重要的是,我總會率先對她們吐露自己的病史。因為訪問也是患者之間的一種聚會。
之後我將包含受訪者個人故事的稿件全都給當事人看過,並向她們得到了出版的許可。願意公開的受訪者使用本名,不願意公開的人則使用自己想用的假名。受訪者們大部分來自首爾或南韓首都圈,但也有出身大邱、釜山、春川、海外的人。而她們全都了解憂鬱症相關的醫學資訊,更重要的是她們有辦法用自己的語言訴說自身故事,能用自己的話講述自己的人生,這的確是一種特權。
儘管身處傷痛之中,這些受訪者們也在反芻自己經驗數千次,再經過重新剖析後獲得了成長。雖然她們是家庭暴力、性暴力的受害者,但同時也是親自控訴被害事實,想盡辦法讓改變發生的倖存者。她們自我感知不對勁,靠著自己的雙腳走向醫院。雖然需要照顧,但她們自己其實也是長久以來提供照顧的人。她們不願意一直只停留在接受幫助的位置。她們全然使用自己的語言發聲,不被醫生、諮商師或其他任何人奪走說明的主導權。這些故事之中存在著矛盾與混亂,因為她們並非浮在真空中的受害者,而是真正的人類。
雖然開啟這個故事的人是我,但為故事作結的並不是。我不想替和我相遇的這些女子貼上憂鬱症、焦慮症、邊緣性人格障礙的標籤並加以區分。我更想成為一個擁護者,去捍衛她們述說的這些故事。書寫自己人生的女人,某種程度上都是瘋子。
目次
推薦文
作者序 一些關於憂鬱症故事的事
第1部 我的痛苦也有名字嗎
第1章 裝病
患者多為女性的顳顎關節疾病
歸根究柢都是女性荷爾蒙的錯
是生病?還是心病?
瘋女人的歷史
歇斯底里,女性貶抑的歷史
沒有人相信的痛苦
第2章 診斷
依理解方式不同而不一樣的世界
各式各樣的文化症候群
極其美式的病,憂鬱症
憂鬱症自我檢測:超過21分就是憂鬱症?
一項診斷,裝不完全部的情緒
病名的力量很大
醫療化?藥療化?哪個都好,只要它可以證明我的痛苦
解放與壓抑,我們的診斷故事
第3章 治療
擲地有聲的藥物史
「販售憂鬱症」
精神醫學的兩大派:精神動力學和生物精神醫學
精神醫學是由誰定義為病理學的呢?
「書寫」可以成為治療
以自己身體的專家之姿參與治療的女子們
良好的存在
第2部 可以死去,或活得不憂鬱嗎
第4章 家人
從沒有記憶的小時候開始:憂鬱是一種生存策略
當一個懂事的好女兒
我恨媽媽,卻又懂她
世上存在不留下傷痕的母愛嗎
在這個家證明我的用處
有愛的家人很稀有
第5章 戀愛
在我眼裡,他們都是救命繩
這還算是爸爸嗎?
需要被照顧的女人們
結果擔任保護人的人是我啊
愛可以是一種救贖嗎
第6章 社會
想要的人生之於社會所期盼的人生
9點到6點之間,不能生病的那些人
害怕跟爸媽要錢
貧窮的我夠格嗎
太多女生因為窮在性方面處於弱勢
就像呼吸般頻繁的性騷擾
是我太敏感嗎
貧窮使人害怕互惠
從我、戀愛、家人還有社會向前一步
第3部 可以改變故事結局的話
第7章 自殺
提起自殺的難堪之處
所謂「因憂鬱症而自殺」是一種陷阱
自殺的各式型態
什麼叫好死不如賴活
作為社會性他殺的自殺
所以我們能做什麼
然後那些被留下來的人們
第8章 照護
患者是照護的主角
理好病歷記敘後,病仍未清
多彬和宇容的故事
保護人或監視人
管控可以不變成支配嗎
照護他人之重
照護共同體─femidangdang
第9章 康復
走向康復之路
改變故事結局的女子們
傷痕可以化為自負嗎
結語:我們的故事現在才剛開始
注釋
作者序 一些關於憂鬱症故事的事
第1部 我的痛苦也有名字嗎
第1章 裝病
患者多為女性的顳顎關節疾病
歸根究柢都是女性荷爾蒙的錯
是生病?還是心病?
瘋女人的歷史
歇斯底里,女性貶抑的歷史
沒有人相信的痛苦
第2章 診斷
依理解方式不同而不一樣的世界
各式各樣的文化症候群
極其美式的病,憂鬱症
憂鬱症自我檢測:超過21分就是憂鬱症?
一項診斷,裝不完全部的情緒
病名的力量很大
醫療化?藥療化?哪個都好,只要它可以證明我的痛苦
解放與壓抑,我們的診斷故事
第3章 治療
擲地有聲的藥物史
「販售憂鬱症」
精神醫學的兩大派:精神動力學和生物精神醫學
精神醫學是由誰定義為病理學的呢?
「書寫」可以成為治療
以自己身體的專家之姿參與治療的女子們
良好的存在
第2部 可以死去,或活得不憂鬱嗎
第4章 家人
從沒有記憶的小時候開始:憂鬱是一種生存策略
當一個懂事的好女兒
我恨媽媽,卻又懂她
世上存在不留下傷痕的母愛嗎
在這個家證明我的用處
有愛的家人很稀有
第5章 戀愛
在我眼裡,他們都是救命繩
這還算是爸爸嗎?
需要被照顧的女人們
結果擔任保護人的人是我啊
愛可以是一種救贖嗎
第6章 社會
想要的人生之於社會所期盼的人生
9點到6點之間,不能生病的那些人
害怕跟爸媽要錢
貧窮的我夠格嗎
太多女生因為窮在性方面處於弱勢
就像呼吸般頻繁的性騷擾
是我太敏感嗎
貧窮使人害怕互惠
從我、戀愛、家人還有社會向前一步
第3部 可以改變故事結局的話
第7章 自殺
提起自殺的難堪之處
所謂「因憂鬱症而自殺」是一種陷阱
自殺的各式型態
什麼叫好死不如賴活
作為社會性他殺的自殺
所以我們能做什麼
然後那些被留下來的人們
第8章 照護
患者是照護的主角
理好病歷記敘後,病仍未清
多彬和宇容的故事
保護人或監視人
管控可以不變成支配嗎
照護他人之重
照護共同體─femidangdang
第9章 康復
走向康復之路
改變故事結局的女子們
傷痕可以化為自負嗎
結語:我們的故事現在才剛開始
注釋
書摘/試閱
【內文試閱】
第2章 診斷
好像被憂鬱症這個單字吞噬了
我第一次造訪精神科是在2016年12月。2020年研究所畢業後,因為轉院需要而有機會拿到診療紀錄,那是我第一次透過文件看到醫師的診斷。上面寫著:
Impression: biopolar II disorder, current depressed
(推定診斷為:第二型雙極性疾患,現為憂鬱狀態)
雙極性疾患是常被稱為躁鬱症的情緒障礙疾病,依躁症期與憂鬱症狀的狀況不同而有不同分類。第一型雙極性疾患是出現躁症及嚴重憂鬱的類型,而我被推定診斷(醫師以患者陳述之症狀為基礎所推定的診斷)出的第二型雙極性疾患,則是出現輕躁症及嚴重憂鬱的類型。我並沒有出現足以被診斷為躁症發作的嚴重躁症症狀。
對於醫生推定診斷我是躁鬱症這件事,其實我並沒有太驚訝。雖然過去就診的時候沒有得到確切的診斷,但從醫生開給我的處方藥種類,就可以大概了解我的狀態。包含我在內的許多病人,都是像這樣靠著搜尋藥名進行自我推定診斷的。醫師開給我的是最具代表性的躁鬱症治療藥物─鋰鹽和具有強烈安眠效果的佐沛眠(Zolpidem)。
比起診斷病名,更烙印在我心中的是下面這條紀錄。
情緒不符。相較於內在的憂鬱,表情過於開朗並保持過度的社會性微笑。
我想起來了。我在幾個月以前飽受持續失眠、憂鬱和焦慮所苦,抱著疲憊的心情造訪了精神科診療室,那時候也本能地把笑容擠在臉上。因為怕我的情緒狀態在陌生人面前會讓對方感到不適,感到焦躁不已。而這樣的不一致居然病態到足以被寫在診療紀錄上,這個事實讓我既震驚又感到莫名羞恥。
不知道該不該說是多虧了「過度的社會性微笑」,在我狀態最糟的時候,也很少被人發現。我只在家人和戀人面前無法徹底隱瞞日常生活,所以唯有他們才看出了我不正常的亢奮和消沉。但情緒的起伏究竟要到什麼程度才算是「不正常」呢?人類畢竟只能經驗各自的情緒才對吧。
人憂鬱的時候,連周圍環境都是憂鬱的。青少年自殺事件頻仍的原因,大多是家庭出了問題。我第一次前往醫院就診,是在首爾江南站10號出口發生女性目標殺人事件後,我開始參與女性運動組織「femidangdang」的時候。那年冬天,在現在廣為人知的「me too運動」之前,以推特為中心展開了「○○_我_性暴力」的hashtag運動。各領域接二連三地出現遭受性暴力事件的女性站出來發聲。每天晚上讀著發到社群軟體的性暴力控訴文,讓我無法成眠。想到那些遭受性暴力的經歷就很難過,而就在離我這麼近的地方,我竟然不知道我的朋友或同事正在受苦,更令人難受。我感覺自己是一個旁觀者。而且……竟然有這麼多女子在人生中經歷了同樣的痛苦?
失眠持續了幾個月,而我變得難以在日常生活裡維持神智清醒。越來越常因為離不開床,一天就這樣虛度光陰。後來我開始具體想像自殺的情景,為了以防萬一,我便把房裡所有尖銳的東西通通清掉。有一天我翻開一本書,卻沒辦法閱讀。不停反覆看著同一句話,卻完全看不懂。居然沒辦法看書了嗎?那意味著我已經不再是我了。於是我第一次去了醫院。
從第一次造訪醫院的2021年8月到現在,我每天都會吃藥。早上吃抗憂鬱劑威克倦(Wellbutrin)150mg,晚上吃抗躁症藥物碳酸鋰300mg,一吃就是4年。最近(尤其是開始寫這本書以後)我的狀況變得比較好,所以正在停吃抗憂鬱劑中。
我在醫院的經驗並不算太好,以下是我聽過的一些話。
「(在我說完和戀愛有關的煩惱之後)焦慮症患者也很容易離婚喔。」
「到目前為止的人生感覺就像坐雲霄飛車一樣對吧?如果不吃藥的話以後也會那樣喔。」
不過因為一個病名就被總結了至今的人生。對方用覺得可憐的目光看著我的樣子也令人厭煩。我換了好幾個醫生,經歷了許多試誤後才找到了現在的這位醫生。
病名具有很大的力量,且非常有說服力。躁鬱症這個病名大大影響了我對自己的理解。從前以為是自然的情緒流動,但看完醫生之後開始會和躁鬱症的症狀作對照了。狀況好的時候,我還會煩惱這究竟是「正常的」情緒,還是藥物製造出來的「人為的」情緒。老是會去查一些「躁鬱症發展成思覺失調症」、「用自殺結束生命」、「治癒後復發」等躁鬱症相關的案例,拿統計數據為自己的未來算命。我真的瘋了嗎?
痛苦的來龍去脈在診療室裡被刪除了。在那裡重要的不是憂鬱的原因,而是憂鬱的症狀。治療的目標不在於找出痛苦的根源後嘗試解除,而是緩和症狀。然而只要根源不解除,憂鬱就很難完全消失。光靠診斷和治療是不夠的。
也就是說……雖然我需要治療,但我不想把解釋人生的權利讓給任何人。不管是在精神科聽到的,還是在心理諮商時聽到的,我都希望把那些話語留在判斷的層面就好。我難道只能當一個憂鬱的瘋子嗎。我不想為了同理別人的痛苦、為了跟他們站在一起,而把生病的事當成我脆弱的證據。更重要的是我並沒有拚命努力與其戰鬥。總之不就這樣子活下來了嗎。
在那之後,我大概有5年都在埋頭研究憂鬱症,以及更進一步的精神疾病相關主題。我改了碩士論文的題目,研究定義並測定憂鬱症的知識如何形成,也和數十位跟我一樣的人見面進行訪談。這些文字就是因為完全無法滿足於「躁鬱症」這個診斷病名,而由我自己重新寫下的故事,是我努力不讓自己的權利被搶走所留下的痕跡。
依理解方式不同而不一樣的世界
雖然我是在2016年,二十六歲時得到了躁鬱症的診斷結果,但憂鬱則從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與我同行了。只是我的症狀被賦予「憂鬱症」之名的時間點是2016年而已。女性受訪者們大部分都會說這種話,而我也是,記憶中我的第一個瞬間也非常憂鬱。
我小時候經歷過的不只是憂鬱。還有自殺的念頭、焦慮、恐慌、輕躁症,甚至出現過幻覺,只不過每個時期為其命名的方式不一樣罷了。回過頭來看,小時候的我並沒有辦法明確區分身體和心靈,或分辨感受和思考到的東西有何差別。無法區分現實和想像的差異,懵懵懂懂的。我也有好幾次任憑思緒發展為實際的感覺,而不只是停留在思考的層面。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時我腦海中認知的世界所製造出來的,那陌生而恐怖的感覺。
小時候我常常看到鬼。六歲左右的時候,只要是打雷閃電下大雨的日子,我就會看見一群敲著玄關門,喊人開門的陰間使者。他們的樣子看起來跟〈傳說的故鄉〉裡出現的陰間使者一模一樣。如果告訴媽媽陰間使者一直在敲我們家的門,媽媽就會跟我說那只是風雨使得大門震動而已。在我看來明明就是陰間使者。這到底算是真的,還是假的經驗呢?
我長久以來一直以為兒童時期看見鬼的記憶是假的,不久前問了媽媽相關的事,媽媽也說她記得。她還說那時我常常黏著姨婆,所以總是說一些奇怪的話。姨婆是小時候照顧我和哥哥的人,對我更是特別寵愛。而姨婆是韓國的傳統女巫(巫堂)。因為我老是說我看到鬼,媽媽就把姨婆和我拆散了。因為她擔心姨婆的「神氣」會傳到我身上。
我不是要主張世上真的存在鬼魂,或者薩滿信仰值得信仰。我對世上有沒有鬼、我的幻聽是真是假、甚至去區分精神疾病是不是真正的疾病都沒有興趣。我只關心人們面對痛苦、恐怖,以及混亂的時候,該用怎樣的方式去排解而已。我想要細細端詳人們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以及實際上以不同方式存在(而非再現)的世界之間有怎樣的關係。
過去的日常生活中,有時會有突如其來感到瘋狂焦慮的時候。明明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卻覺得非常恐懼。感覺呼吸困難,好像快要死了。這樣的恐懼周而復始地襲來。我當時年紀太小,並不知道那恐懼意味著什麼。所以就把小孩子能想到的理由都配了上去。
「貼在桌上的貼紙好像要掉下來了……」
「昨天學的除法好可怕,都除不完,數字一直重複……」
這種恐怖的感覺實在過於強烈,讓我久久無法忘懷那時的記憶。但我對於恐懼的解釋,則是每個人生時期都不太一樣。在我認真上教會的那段時間,我得到的結論是過去想的都是錯的。那些體驗都來自撒旦。我跟教會的人講這些事,他們便為我說明恐懼的意義,而我接受了。再長大一點之後,比起教會,我更信賴的是書本裡的內容。上大學後,我開始對精神醫學感興趣,看了許多書之後,把自己的症狀貼上了「恐慌發作」的標籤。
那種恐懼究竟是什麼?珍惜貼紙的心意嗎?或是無理數給人一種對無限的恐懼呢?還是罕見的兒童期恐慌症呢?這之中哪個才能被稱為真正的經驗呢?不,這種區分真的有意義嗎?
經歷一連串事件後,我感受到的正是如此。解釋痛苦的方式,會根據一個人擁有的文化、知識資源而有所不同。而最終如何表現痛苦,同樣也會受家人、學校、媒體等日常生活中我們所接收到的各種概念影響。我六歲時的恐懼與焦慮,是受到〈傳說的故鄉〉這個節目的影響,以鬼魂或陰間使者的模樣出現。而媽媽用她對巫教信仰的知識為基礎分析我的經驗。教會的人則用從聖經出發的基督教世界觀接納我的經驗。人們會不知不覺以自己內在的世界觀為基礎,對經驗做出自我分析。這種世界觀不只停留在認知的層面,還會延伸成實際的感覺。看見鬼魂、看見撒旦、聽見主的聲音等等。這些經驗比一切事物都更生動而真實地存在著。這世界不只以人們各自不同的理解方式被認知,實際上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著。
為了理解自己感受到的不安和恐懼,一直以來我不斷尋找各種資源,並以它們為基礎重新解釋我的經驗。而我的世界每每因此崩毀,又再重新被建立。這些經驗告訴我,無論面對多麼強大的價值觀(世界觀),總是會有可以重新檢視的餘地。被一個人篤信如命的信念,在另外一個世界也可能一文不值。儘管我在精神科就診,拿了處方藥,而且做了這麼多相關研究,自己也深受幫助,但我之所以沒有全盤接受這些說明方式,可以保持一點距離觀望的原因,正是多虧了以往渾沌的時光。儘管把原本堅固的世界摧毀這件事,每次都還是非常令人害怕就是了。
各式各樣的文化症候群
區分不了幻想與現實,精神恍惚的人應該不只我一個。世上隨處可見人們無法區分身體與心靈,真實世界和想像中的世界相互交流,在精神及身體上同時出現症狀的情況。
常見於東南亞與中國南部地區的恐縮症(Koro),指的是男性擔心生殖器會逐漸縮小、縮入腹部,最後完全消失的一種極度恐懼與焦慮的狀態。患有恐縮症的病人,即使在親眼見證自己的生殖器官仍完好無缺後,仍會持續焦慮並向外哭訴。據說1984~1985年間,中國的16個城市裡甚至有3000多人集體發病的情況。「Dhat症候群(dhat syndrome)」則常見於印度及尼泊爾的南亞印度教文化圈,指的是認為自己的精液混入尿液流出而產生的焦慮狀態。甚至會因此導致無力、疲倦、陽痿、早洩等症狀。印度教文化圈認為精液是生命之液,因此精液隨時會漏出的想法為當事人帶來極度的恐懼與不安。
日本的「社交恐懼症(對人恐怖症,taijin kyofusho)」也是類似的例子。這種症狀經常出現在極度害怕造成他人困擾或不便的人身上。症狀有心跳加快、呼吸不順、身體發抖,進而致使恐慌發作。這種症候群的患者之中,還有許多人會害怕自己的身體散發令人不快的臭味。
韓國的火病也是,光看它的名稱「화병」(Hwabyeong),就知道它是只在韓國出現的特定疾病。火病又被稱為鬱火病,正如其名是因怒火被壓抑而生,並伴隨著失眠、疲勞、呼吸困難、胸痛等身體症狀。火病的特徵是越鄉下的地區、學歷越低的族群,以及女性,便越容易出現相關症候群。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症候群並非出自於一、兩人的錯覺,而是集體且有固定形式地出現。而且它們只在特定社會或文化圈中被認知,在其他文化圈中則不被認為是病症。目前全世界大多使用標準化的疾病分類方式,例如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以下稱ICD)。出現異常症狀時,不管在世界的哪個地方都能在這分類下診斷出同樣的疾病。至少在有制度的醫療體系下大致上是這樣。
精神疾病同樣也經歷了標準化的過程。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DSM便是歷經標準化後最具代表性的疾病分類體制。DSM在1952年第一次出版後,到現在發行的第5版之間經歷了多次改版,過程中也增添或刪減了各種疾病。DSM被廣泛使用於診斷精神疾病,可說是全世界最具權威性的診斷標準。
收錄在DSM中的精神疾病,例如我們熟知的憂鬱症、躁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症等,被認為普遍在全世界都會發生。但前面介紹的恐縮症、Dhat症候群、社交恐懼症、火病等則不符合這樣的分類標準。所以DSM第4版將只出現在特定社會或文化圈的「文化結合症候群(culture-bound syndrome)」單獨做了分類與定義。而在2013年重新修訂的DSM第5版中,雖然有介紹一些文化症候群的例子,但跟韓國火病相關的內容則被刪除了。
極其美式的病,憂鬱症
每個文化用來解釋憂鬱症等精神痛苦的「解釋模型」都不盡相同,加拿大蒙特婁麥基爾大學社會與跨文化精神醫學系教授羅倫斯.J.克梅爾(Laurence J. Kirmayer),是一位對此特別關注的學者。克梅爾表示特定文化圈的信仰與故事會將個人的關注帶向特定的情緒與症狀,同時遠離其他的感覺與症狀。例如在某個文化圈裡會把疾病相關的事情和腸胃不適或肌肉疼痛做連結,而相對在另一個文化圈則將疾病連結至其他類型的症狀,那麼該症狀就會被認為是合理的。因為這種解釋模型能創造出該文化圈中預期得到的疾病經驗,克梅爾主張對於憂鬱症等疾病的病因、症候及病程的堅信,具有自證預言的傾向。
現在的DSM裡,文化症候群就像微不足道的附錄般好不容易才擠了進去;比起火病,現在韓國年輕一輩的女性們也通常是藉由憂鬱症─這個美國製造的精神醫學解釋模型─去理解自己的疾病。然而正如世上存在所謂的文化症候群,去思考每個文化用來解釋人們痛苦的模型都不盡相同這件事,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們訴說的症狀本身有時候正好藏著線索,能幫助找出心理痛苦的原因。恐縮症和Dhat症候群,為什麼剛好是與男性生殖器和精液有關的焦慮症呢?火病或社交恐懼症等與人際關係相關的疾病,為何經常出現在女性身上呢?
人們在特定社會中控訴的痛苦,和該社會強制要求的正常性有關。去分析人們表達與解釋痛苦的方式,就可以探究人們的心理痛苦起因於何種脈絡。
克梅爾認為所謂「憂鬱症」的診斷,也是很美式、很獨特的一種型態。他指出把痛苦的情緒與感覺欣然公布在陌生人面前,傾向把心靈的痛苦當成醫療問題,只有美國人才會這樣。在其他文化中,大部分人對於內在的痛苦會想尋求道德上、社會上的意義,所以會去找群體內的長輩或精神指導者,而不會向群體外的醫師尋求幫助。韓國也一樣,有憂鬱症狀的女性中,年齡層越高的一輩就越容易去尋求朝鮮巫教信仰的幫助。尤其是認為去精神科求醫很困難,或者就算去了也因症狀沒有好轉而失望的人,便會更傾向仰賴巫教信仰。
來自美國的DSM改變了原本分類症狀的方式,在正常的行動與狀態,和被認為是病態的部分之間重新劃下了分界線。顯示精神疾病─甚至是個人對於自我理解的信念─的確是可以從一個文化輸出至另一個文化的。我們經常認為疾病與人們的認知無關,獨立存在於世上,但如同前面探討過的,疾病的形成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社會化的。就算症狀相同,在不同文化圈、不同時代,甚至講得具體一點,在醫學上科別的不同,都可能出現不一樣的診斷。而診斷內容不同,自然會導致出現不同的治療方式。
跟歇斯底里症或火病比起來,我的受訪者們,包括我自己反而都對憂鬱症、焦慮症等名詞更加熟悉。像這樣從美國傳來的大眾精神疾病的各種名字,到底能多精準地詮釋韓國女性們的痛苦呢?我們正在錯過的是什麼?
很多女性會把憂鬱和憤怒一起講出來,她們不說自己憂鬱,而是控訴自己的憤怒。憂鬱症的診斷標準中並沒有與憤怒相關的症狀。而又被稱為鬱火病的火病,則開始就是一種憂鬱同時包含著憤怒的疾病概念。透過火病去了解憂鬱症時,我們是否可以發現藏在憂鬱症之名底下,以前未曾察覺的部分呢?
在過去憂鬱與憤怒被當成火病的時候,當時的診斷體制或治療法其實似乎沒有辦法完整理解女性的人生,並提供解決問題的線索。反而只是利用火病這樣的診斷,使陷入愁苦的女性們病理化而已。但我在此想指出的是,「憂鬱症」這個病名,並無法充分涵蓋韓國女性的情緒與症狀,以及她們所面臨的社會情況。以治療層面來說也一樣,比起獨自去尋求位於群體之外的陌生專家幫忙,人們更傾向在群體內部傾訴問題並解決。我們必須動員被賦予的各種資源,去分析痛苦、與彼此分享,充分學到更多東西。
第2章 診斷
好像被憂鬱症這個單字吞噬了
我第一次造訪精神科是在2016年12月。2020年研究所畢業後,因為轉院需要而有機會拿到診療紀錄,那是我第一次透過文件看到醫師的診斷。上面寫著:
Impression: biopolar II disorder, current depressed
(推定診斷為:第二型雙極性疾患,現為憂鬱狀態)
雙極性疾患是常被稱為躁鬱症的情緒障礙疾病,依躁症期與憂鬱症狀的狀況不同而有不同分類。第一型雙極性疾患是出現躁症及嚴重憂鬱的類型,而我被推定診斷(醫師以患者陳述之症狀為基礎所推定的診斷)出的第二型雙極性疾患,則是出現輕躁症及嚴重憂鬱的類型。我並沒有出現足以被診斷為躁症發作的嚴重躁症症狀。
對於醫生推定診斷我是躁鬱症這件事,其實我並沒有太驚訝。雖然過去就診的時候沒有得到確切的診斷,但從醫生開給我的處方藥種類,就可以大概了解我的狀態。包含我在內的許多病人,都是像這樣靠著搜尋藥名進行自我推定診斷的。醫師開給我的是最具代表性的躁鬱症治療藥物─鋰鹽和具有強烈安眠效果的佐沛眠(Zolpidem)。
比起診斷病名,更烙印在我心中的是下面這條紀錄。
情緒不符。相較於內在的憂鬱,表情過於開朗並保持過度的社會性微笑。
我想起來了。我在幾個月以前飽受持續失眠、憂鬱和焦慮所苦,抱著疲憊的心情造訪了精神科診療室,那時候也本能地把笑容擠在臉上。因為怕我的情緒狀態在陌生人面前會讓對方感到不適,感到焦躁不已。而這樣的不一致居然病態到足以被寫在診療紀錄上,這個事實讓我既震驚又感到莫名羞恥。
不知道該不該說是多虧了「過度的社會性微笑」,在我狀態最糟的時候,也很少被人發現。我只在家人和戀人面前無法徹底隱瞞日常生活,所以唯有他們才看出了我不正常的亢奮和消沉。但情緒的起伏究竟要到什麼程度才算是「不正常」呢?人類畢竟只能經驗各自的情緒才對吧。
人憂鬱的時候,連周圍環境都是憂鬱的。青少年自殺事件頻仍的原因,大多是家庭出了問題。我第一次前往醫院就診,是在首爾江南站10號出口發生女性目標殺人事件後,我開始參與女性運動組織「femidangdang」的時候。那年冬天,在現在廣為人知的「me too運動」之前,以推特為中心展開了「○○_我_性暴力」的hashtag運動。各領域接二連三地出現遭受性暴力事件的女性站出來發聲。每天晚上讀著發到社群軟體的性暴力控訴文,讓我無法成眠。想到那些遭受性暴力的經歷就很難過,而就在離我這麼近的地方,我竟然不知道我的朋友或同事正在受苦,更令人難受。我感覺自己是一個旁觀者。而且……竟然有這麼多女子在人生中經歷了同樣的痛苦?
失眠持續了幾個月,而我變得難以在日常生活裡維持神智清醒。越來越常因為離不開床,一天就這樣虛度光陰。後來我開始具體想像自殺的情景,為了以防萬一,我便把房裡所有尖銳的東西通通清掉。有一天我翻開一本書,卻沒辦法閱讀。不停反覆看著同一句話,卻完全看不懂。居然沒辦法看書了嗎?那意味著我已經不再是我了。於是我第一次去了醫院。
從第一次造訪醫院的2021年8月到現在,我每天都會吃藥。早上吃抗憂鬱劑威克倦(Wellbutrin)150mg,晚上吃抗躁症藥物碳酸鋰300mg,一吃就是4年。最近(尤其是開始寫這本書以後)我的狀況變得比較好,所以正在停吃抗憂鬱劑中。
我在醫院的經驗並不算太好,以下是我聽過的一些話。
「(在我說完和戀愛有關的煩惱之後)焦慮症患者也很容易離婚喔。」
「到目前為止的人生感覺就像坐雲霄飛車一樣對吧?如果不吃藥的話以後也會那樣喔。」
不過因為一個病名就被總結了至今的人生。對方用覺得可憐的目光看著我的樣子也令人厭煩。我換了好幾個醫生,經歷了許多試誤後才找到了現在的這位醫生。
病名具有很大的力量,且非常有說服力。躁鬱症這個病名大大影響了我對自己的理解。從前以為是自然的情緒流動,但看完醫生之後開始會和躁鬱症的症狀作對照了。狀況好的時候,我還會煩惱這究竟是「正常的」情緒,還是藥物製造出來的「人為的」情緒。老是會去查一些「躁鬱症發展成思覺失調症」、「用自殺結束生命」、「治癒後復發」等躁鬱症相關的案例,拿統計數據為自己的未來算命。我真的瘋了嗎?
痛苦的來龍去脈在診療室裡被刪除了。在那裡重要的不是憂鬱的原因,而是憂鬱的症狀。治療的目標不在於找出痛苦的根源後嘗試解除,而是緩和症狀。然而只要根源不解除,憂鬱就很難完全消失。光靠診斷和治療是不夠的。
也就是說……雖然我需要治療,但我不想把解釋人生的權利讓給任何人。不管是在精神科聽到的,還是在心理諮商時聽到的,我都希望把那些話語留在判斷的層面就好。我難道只能當一個憂鬱的瘋子嗎。我不想為了同理別人的痛苦、為了跟他們站在一起,而把生病的事當成我脆弱的證據。更重要的是我並沒有拚命努力與其戰鬥。總之不就這樣子活下來了嗎。
在那之後,我大概有5年都在埋頭研究憂鬱症,以及更進一步的精神疾病相關主題。我改了碩士論文的題目,研究定義並測定憂鬱症的知識如何形成,也和數十位跟我一樣的人見面進行訪談。這些文字就是因為完全無法滿足於「躁鬱症」這個診斷病名,而由我自己重新寫下的故事,是我努力不讓自己的權利被搶走所留下的痕跡。
依理解方式不同而不一樣的世界
雖然我是在2016年,二十六歲時得到了躁鬱症的診斷結果,但憂鬱則從我很小的時候就開始與我同行了。只是我的症狀被賦予「憂鬱症」之名的時間點是2016年而已。女性受訪者們大部分都會說這種話,而我也是,記憶中我的第一個瞬間也非常憂鬱。
我小時候經歷過的不只是憂鬱。還有自殺的念頭、焦慮、恐慌、輕躁症,甚至出現過幻覺,只不過每個時期為其命名的方式不一樣罷了。回過頭來看,小時候的我並沒有辦法明確區分身體和心靈,或分辨感受和思考到的東西有何差別。無法區分現實和想像的差異,懵懵懂懂的。我也有好幾次任憑思緒發展為實際的感覺,而不只是停留在思考的層面。我到現在都還記得那時我腦海中認知的世界所製造出來的,那陌生而恐怖的感覺。
小時候我常常看到鬼。六歲左右的時候,只要是打雷閃電下大雨的日子,我就會看見一群敲著玄關門,喊人開門的陰間使者。他們的樣子看起來跟〈傳說的故鄉〉裡出現的陰間使者一模一樣。如果告訴媽媽陰間使者一直在敲我們家的門,媽媽就會跟我說那只是風雨使得大門震動而已。在我看來明明就是陰間使者。這到底算是真的,還是假的經驗呢?
我長久以來一直以為兒童時期看見鬼的記憶是假的,不久前問了媽媽相關的事,媽媽也說她記得。她還說那時我常常黏著姨婆,所以總是說一些奇怪的話。姨婆是小時候照顧我和哥哥的人,對我更是特別寵愛。而姨婆是韓國的傳統女巫(巫堂)。因為我老是說我看到鬼,媽媽就把姨婆和我拆散了。因為她擔心姨婆的「神氣」會傳到我身上。
我不是要主張世上真的存在鬼魂,或者薩滿信仰值得信仰。我對世上有沒有鬼、我的幻聽是真是假、甚至去區分精神疾病是不是真正的疾病都沒有興趣。我只關心人們面對痛苦、恐怖,以及混亂的時候,該用怎樣的方式去排解而已。我想要細細端詳人們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以及實際上以不同方式存在(而非再現)的世界之間有怎樣的關係。
過去的日常生活中,有時會有突如其來感到瘋狂焦慮的時候。明明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卻覺得非常恐懼。感覺呼吸困難,好像快要死了。這樣的恐懼周而復始地襲來。我當時年紀太小,並不知道那恐懼意味著什麼。所以就把小孩子能想到的理由都配了上去。
「貼在桌上的貼紙好像要掉下來了……」
「昨天學的除法好可怕,都除不完,數字一直重複……」
這種恐怖的感覺實在過於強烈,讓我久久無法忘懷那時的記憶。但我對於恐懼的解釋,則是每個人生時期都不太一樣。在我認真上教會的那段時間,我得到的結論是過去想的都是錯的。那些體驗都來自撒旦。我跟教會的人講這些事,他們便為我說明恐懼的意義,而我接受了。再長大一點之後,比起教會,我更信賴的是書本裡的內容。上大學後,我開始對精神醫學感興趣,看了許多書之後,把自己的症狀貼上了「恐慌發作」的標籤。
那種恐懼究竟是什麼?珍惜貼紙的心意嗎?或是無理數給人一種對無限的恐懼呢?還是罕見的兒童期恐慌症呢?這之中哪個才能被稱為真正的經驗呢?不,這種區分真的有意義嗎?
經歷一連串事件後,我感受到的正是如此。解釋痛苦的方式,會根據一個人擁有的文化、知識資源而有所不同。而最終如何表現痛苦,同樣也會受家人、學校、媒體等日常生活中我們所接收到的各種概念影響。我六歲時的恐懼與焦慮,是受到〈傳說的故鄉〉這個節目的影響,以鬼魂或陰間使者的模樣出現。而媽媽用她對巫教信仰的知識為基礎分析我的經驗。教會的人則用從聖經出發的基督教世界觀接納我的經驗。人們會不知不覺以自己內在的世界觀為基礎,對經驗做出自我分析。這種世界觀不只停留在認知的層面,還會延伸成實際的感覺。看見鬼魂、看見撒旦、聽見主的聲音等等。這些經驗比一切事物都更生動而真實地存在著。這世界不只以人們各自不同的理解方式被認知,實際上也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著。
為了理解自己感受到的不安和恐懼,一直以來我不斷尋找各種資源,並以它們為基礎重新解釋我的經驗。而我的世界每每因此崩毀,又再重新被建立。這些經驗告訴我,無論面對多麼強大的價值觀(世界觀),總是會有可以重新檢視的餘地。被一個人篤信如命的信念,在另外一個世界也可能一文不值。儘管我在精神科就診,拿了處方藥,而且做了這麼多相關研究,自己也深受幫助,但我之所以沒有全盤接受這些說明方式,可以保持一點距離觀望的原因,正是多虧了以往渾沌的時光。儘管把原本堅固的世界摧毀這件事,每次都還是非常令人害怕就是了。
各式各樣的文化症候群
區分不了幻想與現實,精神恍惚的人應該不只我一個。世上隨處可見人們無法區分身體與心靈,真實世界和想像中的世界相互交流,在精神及身體上同時出現症狀的情況。
常見於東南亞與中國南部地區的恐縮症(Koro),指的是男性擔心生殖器會逐漸縮小、縮入腹部,最後完全消失的一種極度恐懼與焦慮的狀態。患有恐縮症的病人,即使在親眼見證自己的生殖器官仍完好無缺後,仍會持續焦慮並向外哭訴。據說1984~1985年間,中國的16個城市裡甚至有3000多人集體發病的情況。「Dhat症候群(dhat syndrome)」則常見於印度及尼泊爾的南亞印度教文化圈,指的是認為自己的精液混入尿液流出而產生的焦慮狀態。甚至會因此導致無力、疲倦、陽痿、早洩等症狀。印度教文化圈認為精液是生命之液,因此精液隨時會漏出的想法為當事人帶來極度的恐懼與不安。
日本的「社交恐懼症(對人恐怖症,taijin kyofusho)」也是類似的例子。這種症狀經常出現在極度害怕造成他人困擾或不便的人身上。症狀有心跳加快、呼吸不順、身體發抖,進而致使恐慌發作。這種症候群的患者之中,還有許多人會害怕自己的身體散發令人不快的臭味。
韓國的火病也是,光看它的名稱「화병」(Hwabyeong),就知道它是只在韓國出現的特定疾病。火病又被稱為鬱火病,正如其名是因怒火被壓抑而生,並伴隨著失眠、疲勞、呼吸困難、胸痛等身體症狀。火病的特徵是越鄉下的地區、學歷越低的族群,以及女性,便越容易出現相關症候群。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症候群並非出自於一、兩人的錯覺,而是集體且有固定形式地出現。而且它們只在特定社會或文化圈中被認知,在其他文化圈中則不被認為是病症。目前全世界大多使用標準化的疾病分類方式,例如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問題統計分類(the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and related health problems,以下稱ICD)。出現異常症狀時,不管在世界的哪個地方都能在這分類下診斷出同樣的疾病。至少在有制度的醫療體系下大致上是這樣。
精神疾病同樣也經歷了標準化的過程。美國精神醫學學會的DSM便是歷經標準化後最具代表性的疾病分類體制。DSM在1952年第一次出版後,到現在發行的第5版之間經歷了多次改版,過程中也增添或刪減了各種疾病。DSM被廣泛使用於診斷精神疾病,可說是全世界最具權威性的診斷標準。
收錄在DSM中的精神疾病,例如我們熟知的憂鬱症、躁鬱症、焦慮症、思覺失調症等,被認為普遍在全世界都會發生。但前面介紹的恐縮症、Dhat症候群、社交恐懼症、火病等則不符合這樣的分類標準。所以DSM第4版將只出現在特定社會或文化圈的「文化結合症候群(culture-bound syndrome)」單獨做了分類與定義。而在2013年重新修訂的DSM第5版中,雖然有介紹一些文化症候群的例子,但跟韓國火病相關的內容則被刪除了。
極其美式的病,憂鬱症
每個文化用來解釋憂鬱症等精神痛苦的「解釋模型」都不盡相同,加拿大蒙特婁麥基爾大學社會與跨文化精神醫學系教授羅倫斯.J.克梅爾(Laurence J. Kirmayer),是一位對此特別關注的學者。克梅爾表示特定文化圈的信仰與故事會將個人的關注帶向特定的情緒與症狀,同時遠離其他的感覺與症狀。例如在某個文化圈裡會把疾病相關的事情和腸胃不適或肌肉疼痛做連結,而相對在另一個文化圈則將疾病連結至其他類型的症狀,那麼該症狀就會被認為是合理的。因為這種解釋模型能創造出該文化圈中預期得到的疾病經驗,克梅爾主張對於憂鬱症等疾病的病因、症候及病程的堅信,具有自證預言的傾向。
現在的DSM裡,文化症候群就像微不足道的附錄般好不容易才擠了進去;比起火病,現在韓國年輕一輩的女性們也通常是藉由憂鬱症─這個美國製造的精神醫學解釋模型─去理解自己的疾病。然而正如世上存在所謂的文化症候群,去思考每個文化用來解釋人們痛苦的模型都不盡相同這件事,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為人們訴說的症狀本身有時候正好藏著線索,能幫助找出心理痛苦的原因。恐縮症和Dhat症候群,為什麼剛好是與男性生殖器和精液有關的焦慮症呢?火病或社交恐懼症等與人際關係相關的疾病,為何經常出現在女性身上呢?
人們在特定社會中控訴的痛苦,和該社會強制要求的正常性有關。去分析人們表達與解釋痛苦的方式,就可以探究人們的心理痛苦起因於何種脈絡。
克梅爾認為所謂「憂鬱症」的診斷,也是很美式、很獨特的一種型態。他指出把痛苦的情緒與感覺欣然公布在陌生人面前,傾向把心靈的痛苦當成醫療問題,只有美國人才會這樣。在其他文化中,大部分人對於內在的痛苦會想尋求道德上、社會上的意義,所以會去找群體內的長輩或精神指導者,而不會向群體外的醫師尋求幫助。韓國也一樣,有憂鬱症狀的女性中,年齡層越高的一輩就越容易去尋求朝鮮巫教信仰的幫助。尤其是認為去精神科求醫很困難,或者就算去了也因症狀沒有好轉而失望的人,便會更傾向仰賴巫教信仰。
來自美國的DSM改變了原本分類症狀的方式,在正常的行動與狀態,和被認為是病態的部分之間重新劃下了分界線。顯示精神疾病─甚至是個人對於自我理解的信念─的確是可以從一個文化輸出至另一個文化的。我們經常認為疾病與人們的認知無關,獨立存在於世上,但如同前面探討過的,疾病的形成某種程度上來說是社會化的。就算症狀相同,在不同文化圈、不同時代,甚至講得具體一點,在醫學上科別的不同,都可能出現不一樣的診斷。而診斷內容不同,自然會導致出現不同的治療方式。
跟歇斯底里症或火病比起來,我的受訪者們,包括我自己反而都對憂鬱症、焦慮症等名詞更加熟悉。像這樣從美國傳來的大眾精神疾病的各種名字,到底能多精準地詮釋韓國女性們的痛苦呢?我們正在錯過的是什麼?
很多女性會把憂鬱和憤怒一起講出來,她們不說自己憂鬱,而是控訴自己的憤怒。憂鬱症的診斷標準中並沒有與憤怒相關的症狀。而又被稱為鬱火病的火病,則開始就是一種憂鬱同時包含著憤怒的疾病概念。透過火病去了解憂鬱症時,我們是否可以發現藏在憂鬱症之名底下,以前未曾察覺的部分呢?
在過去憂鬱與憤怒被當成火病的時候,當時的診斷體制或治療法其實似乎沒有辦法完整理解女性的人生,並提供解決問題的線索。反而只是利用火病這樣的診斷,使陷入愁苦的女性們病理化而已。但我在此想指出的是,「憂鬱症」這個病名,並無法充分涵蓋韓國女性的情緒與症狀,以及她們所面臨的社會情況。以治療層面來說也一樣,比起獨自去尋求位於群體之外的陌生專家幫忙,人們更傾向在群體內部傾訴問題並解決。我們必須動員被賦予的各種資源,去分析痛苦、與彼此分享,充分學到更多東西。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本週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