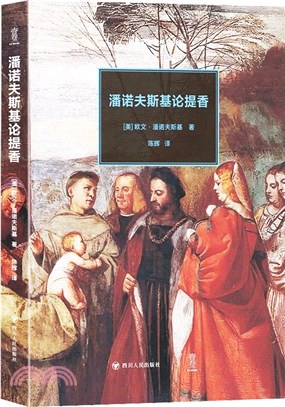潘諾夫斯基論提香(簡體書)
商品資訊
系列名:文藝復興經典書系
ISBN13:9787220129704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作者:(美)歐文‧潘諾夫斯基
出版日:2023/02/16
裝訂/頁數:平裝/238頁
規格:24cm*17cm (高/寬)
版次:一版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歐文·潘諾夫斯基,美國著名藝術史家,在圖像學領域有突出貢獻,對二戰以後西方藝術史研究有巨大影響,著有《視覺藝術的含義》等。譯者陳輝,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圖像理論、現象學。
名人/編輯推薦
本書是潘諾夫斯基晚期藝術史研究的代表作,也是其講座風格的研究方法的典型體現,通過這部著作,我們可以從各個方面來重建潘諾夫斯基的具體研究方法。
目次
【目錄】
第1章 導論······································································································· 001
第2章 聖經和聖徒傳的一些問題·································································· ·026
第3章 對位:偽裝的中世紀程式和古典程式················································057
第4章 對時間的反思························································································086·
第5章 對愛與美的反思····················································································106
第6章 提香和奧維德························································································136
附錄······················································································································170
附錄1:關於文獻目錄的一些注釋································································170
附錄2:提香出生日期的問題········································································175
附錄3:卡多雷之戰························································································178
附錄4:提香與塞森格····················································································181
附錄5:伊莎貝拉皇后的肖像········································································183
附錄6:宗教的寓言························································································185
附錄7:羅浮宮的“帕爾多維納斯” ··························································189
索引······················································································································193
圖式[31]之中。
書摘/試閱
【內容節選】
第6章 提香和奧維德
在迄今為止討論的世俗作品中,神話元素——如果有的話——被限定在人物和靜態境況,還沒有拓展到戲劇性事件。在《維納斯的盛宴》和《安德裡亞人的酒神》中,在《神聖與世俗之愛》和《瓦斯托侯爵的寓言》中,在《丘比特的教育》和各種版本的《維納斯與音樂家》中——在所有這些繪畫中,古典男神和女神即使不是同時代人所假扮的,但仍顯現為一個普遍觀念或原則的化身,而不是某個個體敘事的男主角或女主角。我們被期待著去理解他們是什麼或者代表什麼,而不是去共享他們的所作所為或者所遭受的東西。[1]
當提香想要講述一個真正的寓言時(除了永遠具有吸引力的盧克尼西亞\[Lucretia\]主題[2],他似乎對非神話人物的古典主題沒什麼興趣),他通常會在奧維德那裡找到他的文本靈感。[3]鑒於奧維德從大約1100年到我們今天的西方人文主義中的作用——沒有另外一位古典作家處理過如此廣泛的神話題材,並且被如此勤勉地閱讀、翻譯、釋義、評注和圖示——這一事實既不令人驚訝,也不是非同尋常的;奧維德《變形記》的很多印行版本以及它們的釋義都帶有諸如“詩人的聖經”(“Bible des poètes”)、“畫家的聖經”(“Malerbibel”)或“畫家聖經”(“Schildersbijbel”)這樣的副標題,這並非沒有道理。[4]
然而,提香與這位“兩個世界之間的詩人”——正如其被稱呼的那樣——的關係是相當特別的。他一定在這樣一位作家身上感覺到一種內在的親和力,這位作家既深刻,又風趣,既感性,又意識到人類對命運的悲劇性服從。而且,正是這種內在的親和力,使得提香對奧維德文本的解釋能夠既是確切的又是自由的,既詳盡地關注細節,又具有不拘一格的創新精神。在對神話敘事感興趣的重要藝術家中,沒有另外一位如此強烈地依賴奧維德,並且從文本的某一單個短語中得出如此重要的視覺結論。然而,在受惠於奧維德的重要藝術家中,也沒有另外一位如此毫不猶豫地用其他資源來補充文本,並且甚至——至少在一種情況下——改變其本質性的意義。難怪作為奧維德的解釋者,提香不受拘束地使用各種各樣的視覺模式,無論是古代的還是現代的,但與此同時,他在總體上仍然獨立於這樣一種獨特的傳統,這種傳統在《變形記》無數的插圖版、翻譯和釋義中,無處不在地蓬勃發展。[5]
提香早的奧維德敘事畫——這幅畫是關於文本資源和視覺資源的多重推導的一個主要案例——是他為裝飾阿方索·德·埃斯特位於費拉拉城堡的書房而創作的後一幅作品:現藏於倫敦國家美術館的《巴庫斯和阿裡阿德涅》,我們記得,這位公爵到1523年春季或初夏才等到這幅畫。[6]
這幅畫的主題在古典藝術中如此不同尋常[7],更不用說在後古典藝術中了,以至於安尼巴萊·龍卡利(Annibale Roncagli)——這位紳士記錄了1598年從費拉拉非法轉移走的繪畫——都不能正確地識別出它:他將這幅畫描述為,“一幅方形版式的繪畫,出自提香之手,畫中描繪了拉奧孔”。這個陳述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右側前景中被蛇所環繞的那個人物同從側面看到的梵蒂岡群雕具有一種可能不僅僅是偶然的相似,提香在1520年左右必定已經可以接觸到這件群雕的石膏模型。[8]提香之所以將這個被蛇所環繞的人物包括進來,完全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正如洛馬佐\[Lomazzo\]和裡多爾菲已經注意到的那樣)他是以卡圖盧斯對一件虛構掛毯的描述為基礎來描繪巴庫斯的隊伍,這件虛構的掛毯顯示,巴庫斯及其扈從們在尋找阿裡阿德涅(Carmina, LXIV, 257-265)——卡圖盧斯的這個描述不僅列舉了這樣一些標準主題,例如揮舞酒神杖、敲擊鈸和手鼓以及拋擲被肢解的小母牛的四肢等,而且還包含對特定信徒——這些信徒“用盤繞的蛇環繞著他們自己”(pars sese tortis serpentibus incingebant)——的警示性提及。
然而,就提香的繪畫而言,卡圖盧斯的這段話僅僅說明了巴庫斯追隨者們的裝備和行為。實際的主題是受到了奧維德的啟發——並且典型地受到兩個完全不同的段落的啟發,這兩個段落都沒有在《變形記》中被找到。這兩個段落中的其中一個——在這方面,我認同埃德加·溫德(Edgar Wind)——是奧維德在《歲時記》(Fasti, III, 459-516)中對阿裡阿德涅與巴庫斯第二次也是後一次相遇的熱情重現。阿裡阿德涅已經被忒修斯(Theseus)遺棄在納克索斯島上,她被巴庫斯救起,後者發現她在岸邊睡著了。接著,他也拋棄了她去征服印度。她絕望地走在水邊,譴責她兩位愛人的不忠,並且想要尋死。但是,巴庫斯已經凱旋,並且“從後面”跟著她(a tergo forte secutus\[碰巧跟在後面\]),他第二次出現在她面前。他“用親吻擦幹了她的眼淚”,而她則死在了他懷裡,以分享他的不朽:“這位神說道,‘讓我們一起登上天堂的’”(Et, pariter coeli summa petamus, ait)。她王冠上的寶石變成了被稱為北冕座(Corona; the “Cnossian Crown”\])的星座,這個星座在提香繪畫的左上角清晰可見。只有通過a tergo forte secutus(碰巧跟在後面)這個短語,我們才能夠解釋阿裡阿德涅轉向的姿勢。[9]
但是,為了解釋巴庫斯自己的行為——在這方面,我必須認同GH湯普森(GHThompson)——我們必須假定奧維德《愛的藝術》(Ars amatoria, I, 525-564)的附加影響。在這裡(同樣也在《變形記》\[Metamorphoses, VIII, 174-18\]的更為簡要的提及中),巴庫斯與阿裡阿德涅的次和第二次相遇之間的差異被故意掩蓋了。巴庫斯已經將阿裡阿德涅稱作他的“妻子”,他承諾讓她不朽,並且宣布北冕座將會一直為海上“迷茫的船只”指引方向;她仍然為忒修斯嘆息和哭泣,就好像後者剛剛離開,而她以前則從未遇到過巴庫斯一樣。[10]但是,正是《愛的藝術》,並且也只有《愛的藝術》,才為提香這幅令人難忘的繪畫中的那個令人難忘的主題提供了文本基礎:正如濟慈所說,“巴庫斯從戰車上迅速跳下來”。“這就是說,這位神從戰車上跳下來,以免她被他的老虎們嚇到……”(“Dixit et e curru, ne tigres ilia timeret,/Desilit…”)。
我們曾順便提到,提香從一件古典俄瑞斯忒斯石棺那裡借鑒了巴庫斯的姿勢(我們記得,這個姿勢在兩幅《聖瑪格麗特》得到恢復)[11];面對表達至高情感的任務,他轉向古典藝術,將其視為被瓦爾堡恰如其分地稱為激情樣式(Pathosformein,“patterns of passionate emotion”)的東西的寶庫。但是,這裡和其他地方一樣,提香改進了這種指導。為了統一並加強其古典模式的節奏,他降低了右臂,將頭部降低到低於左肩的水平,並且可以說,通過添加一件深紅色斗篷——這件斗篷以壯麗的揮舞向後翻涌——他為人物提供了翅膀。然而,“跳下”(“leap”)的觀念卻是受奧維德的Desilit(跳下)一詞的啟發。
有一個微小但重要的變化——這個變化見證了對文本的尊重與精神的自由之間的結合,這種結合體現了提香對奧維德的態度的特徵——即巴庫斯的“老虎”(它們轉而被詩人以更為常見的黑豹所取代)被更小的貓科動物所替代,這些貓科動物帶有斑點,而不是條紋,專家們已經將其鑒定為獵豹或印度豹。[12]正如其印度名字所暗示的,印度豹是一種印度物種;並且,用它們來替換奧維德的老虎,似乎是出於兩個考慮。首先,畫家希望滿足其贊助人對稀有、奇異動物的興趣——這個興趣體現了大多數文藝復興時期貴族的特徵,但在阿方索·德·埃斯特這裡是如此明顯,以至於在1520年,他要求提香去描繪一只飼養在科爾納羅宮(Palazzo Cornaro)的瞪羚(提香盡職盡責地去了那裡,才知道這只動物已經死了;但他提出,通過創作一幅由喬凡尼·貝裡尼曾創作出來的繪畫的放大摹本,來滿足公爵的願望)。[13]其次,並且更為重要的是,提香想要完全清楚地表明,巴庫斯是從印度歸來。盡管並不明顯,但印度豹的存在證實了這樣一個假設,即提香繪畫的主題是巴庫斯與阿裡阿德涅的第二次也是後一次相遇:在將這位神同化為俄瑞斯忒斯的過程中,提香將一個殺死其所恨之物的人變成了一個神,這個神將其所愛之物不朽化,但也由此摧毀了其所愛之物。
在經歷了二十多年的時間間隔,並且在環境的一種獨特交織的情況下,才產生出提香的下一幅神話敘事:現藏於那不勒斯的《達那厄》。[14]這幅畫是在羅馬為奧塔維奧·法爾內塞(Ottavio Farnese,我們記得,他是教皇保羅三世的孫子)繪製的[15],它服務於三重目的:旨在以對愛欲主題的描繪來取悅一位年輕的王子;旨在恰當地處理一個古典神話,在文藝復興時期,關於這個神話的古典表征並不為人所知;以及旨在挑戰米開朗琪羅。
在奧維德那裡,達那厄的故事——阿爾戈斯國王阿克裡西俄斯(Acrisius)的美麗女兒,她的父親將她囚禁在一座青銅塔中,以避免她同男人進行任何交往,但是她被偽裝成一陣黃金雨的朱庇特所接近,並成為珀爾修斯(Perseus)的母親——經常被提及,但沒有詳盡地被講述過。[16]並且,除了後期的一個例外[17],它並未被包含在眾多微縮圖、木版畫或銅版畫——這些微縮圖或版畫構成了奧維德《變形記》及其釋義的手抄本或印刷本的插圖——的系列之內。
因此,中世紀根據語境以很多不同的方式來表現和解釋達那厄:要麼將其表現和解釋為一位同時代的公主,這位公主周圍環繞著一群年輕的侍女,而不是古典資料中所謂的一個“女仆”(nurse)或“老婦人”,朱庇特則是偽裝成一個珠寶推銷員來接近她;要麼表現和解釋為端莊的化身,她受到銅塔的保護,這個銅塔由此而成為貞潔的象徵(《隱喻化的孚爾革恩提烏斯》\[Fulgentius metaforalis\]);要麼甚至表現和解釋為聖母馬利亞的預表:我們的老朋友弗朗西斯·德·雷察(Franciscus de Retza)問道,“如果達那厄是通過一陣黃金雨而從朱庇特那裡受孕,那麼為什麼聖母不能受孕於聖靈而生育呢”?(“Si Danaё auri pluvia praegnans a Jove claret,/Cur Spiritu Sancto gravida Virgo non generaret”?)
讓·戈薩特(Jan Gossart)可以從中世紀的“端莊樣式”中發展一個充滿魅力的、孩子般的達那厄。然而,義大利文藝復興卻是從零開始;而且,除了這樣一些迷人的罕見案例,例如巴爾達薩雷·佩魯齊位於法爾內西納別墅(Villa Farnesina)的小型雕飾帶和柯勒喬現藏於博爾蓋塞美術館的奢華杰作,16世紀和17世紀義大利文藝的描繪分為兩個類別。在其中一個類別中——該類別包含之前藏於布裡奇沃特故居的安尼巴萊·卡拉奇(Annibale Carracci)的《達那厄》(Danaё)[18]和現藏於冬宮的倫勃朗的著名畫作[19]——,女主人公的形象被同化於斜倚維納斯的威尼斯樣式,由此期待取代了實現。在另一個類別中,她被同化於米開朗琪羅的《麗達》(Leda),在後者那裡,我們見證了歌德所謂的“所有場景中可愛的場景”的高潮時刻。
這種“麗達樣式”被普裡馬蒂喬(Primaticcio)在其位於楓丹白露弗朗索瓦一世畫廊的壁畫(該壁畫畫於1540年之後的某個時刻,但遺失了,所以是通過一幅由萊昂納多·蒂裡\[Léonard Thiry\]創作的銅版畫以及一件現藏於維也納博物館的掛毯而傳播開來)中所採用,同時也被提香在其那不勒斯畫作中所採用。提香很可能通過萊昂納多·蒂裡的銅版畫或者通過一幅素描而了解普裡馬蒂喬的作品(他幾乎不可能親眼見過普裡馬蒂喬,因為後者在1540年至1542年間前往羅馬時,僅僅是為了為弗朗索瓦一世購買藝術品,並且不太可能在威尼斯停留)。但可以確定的是,普裡馬蒂喬和提香都是從米開朗琪羅1530年的《麗達》中發展出他們的作品,我們知道,他們兩個都很熟悉後者的那件作品。普裡馬蒂喬可能在法國(很有可能就是在楓丹白露那裡)看到過原作——以及羅索(Rosso)對其的摹本[20];提香可能看到過瓦薩裡的摹本,後者於1541年將這件摹本帶到威尼斯,並且將其連同一件仿米開朗琪羅《維納斯》的摹本一起賣給提香的朋友和客戶唐·迭戈·烏爾塔多·德·門多薩(Don Diego Hurtado de Mendoza)。[21]
我毫不懷疑,提香英雄般的《達那厄》意在同米開朗琪羅的《麗達》一較高下,後者在參訪提香的羅馬工作室時,就像人們在畫家在場的情況下所做的那樣,高度贊揚了這幅畫(在私底下,他將這種贊揚限定在“色彩和技巧”上,同時對威尼斯的畫家們從未學習過美的素描的原則而感到遺憾)。但是,不用說,有多少相似之處,就有多少差異。正如查爾斯·德·托爾奈(Charles de Tolnay)正確強調的那樣,米開朗琪羅的《麗達》低下她的頭,並閉上其眼睛,就像在夢中一樣;提香的《達那厄》則有意識地、紅著臉地、快樂地放任自己;而且她的姿勢——那只抬著腿的腳牢固地支撐在長榻上,而不是(像在《麗達》中那樣)懸在半空中——給人一種既狂喜又放鬆的印象。此外,提香作品的結構中似乎還有兩三條其他線索。他自己一定看過似乎構成米開朗琪羅《麗達》的古典來源的東西,即一件羅馬浮雕,該浮雕通過一幅16世紀的素描而傳播開來[22],它不僅在支撐手臂的位置和動作方面(這個手臂在米開朗琪羅的《麗達》和普裡馬蒂喬的《達那厄》中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放置和使用),而且在右側存在的丘比特方面——這個人物形象也許並不真正地屬於這件羅馬浮雕,但在16世紀卻被明確地與其關聯在一起——都預示了那不勒斯畫作。而且,在將這個丘比特的姿勢戲劇化為一種強烈的、令人驚嘆的對立式平衡——即頭部的運動是對立於而不是遵從軀幹和雙腿的運動——時,提香不僅模仿了現藏於卡比多裡諾博物館(Museo Capitolino)的利西普斯的(Lysippian)《厄洛斯在彎弓》(Eros Bending His Bow),而且也模仿了——也許更是如此——米開朗琪羅雕像中他喜歡的雕像:現藏於神廟遺址聖母堂的“《復活的基督》”。[23]
在米開朗琪羅和古代藝術的共同影響的強化之下,一種英雄氣概的精神也滲透到一個由四幅繪畫組成的神話敘事系列中,這些畫是由查理五世的妹妹,即當時的荷蘭攝政匈牙利的瑪麗(Mary of Hungary)在提香逗留奧格斯堡期間——也就是說,在1548年——委托給提香的。[24]它們於1549年裝飾了她位於班什(Binche)的宮殿的上層大廳,但是,1554年在法軍逼近時卻不得不被轉移走。兩年之後,它們被運往西班牙,並在馬德裡的王宮中找到了其位置,在那裡,它們成為1734年那場臭名昭著的大火的犧牲品。其中兩幅嚴重受損(正如一份西班牙語資料所說的那樣,被虐待了\[maltratado\]),但可以修復,並幸存於普拉多博物館[25];另外兩幅則完全被毀了,盡管其中一幅至少通過一幅由朱利奧·薩努托(Giulio Sanuto)創作的銅版畫而為我們所知。
這一四重組合的主題來自於奧維德的《變形記》(Metamorphoses, IV, 455-461)。[26]在被奧維德稱為“惡人居所”(sedes scelerata)的冥界的一個特殊角落裡——這也許可以解釋這樣一個事實,即提香的畫作被安置於其中的王宮的那個房間要麼被稱為“復仇女神之屋”(“Room of the Furies”;Pieza de las Furias),要麼被稱為“被詛咒者之屋”(“Room of the Damned”;Pieza de los Condenados)——,朱諾觀察到了以如下順序和方式對四大罪人進行的懲罰:提提俄斯(Tityus),作為拉托那(Latona)的侵犯者,他的肝臟(情愛激情的位置)永遠被一只禿鷹啄食;坦塔羅斯(Tantalus),作為奧林匹斯秘密的泄密者,永遠徒勞地伸手去拿食物和飲品;西西弗斯(Sisyphus),作為聰明、言而無信的人,永遠將一塊沉重的石頭推上山,並且看著它滾下去;以及伊克西翁(Ixion),作為朱諾本人的潛在誘惑者,永遠在其輪子上旋轉。
提香似乎有意以這樣一種方式來建立奧維德式的順序,即他將四幅繪畫的系列分成兩對,這兩對在對面墻上面對著彼此:《提提俄斯》(幸存於普拉多博物館的兩幅繪畫之一,並且早在16世紀就被誤釋成“《普羅米修斯》”\[“Prometheus”\])[27]面對著房間另一邊的《坦塔羅斯》,後者通過薩努托的銅版畫而傳播開來;《西西弗斯》(這個系列中另一個幸存的成員)同樣地面對著《伊克西翁》。從一幅素描中可以推斷出,至少在班什時,《提提俄斯》和《西西弗斯》是在同一面墻上。[28]
《提提俄斯》可能受到了米開朗琪羅在其一幅卡瓦列裡(Cavalieri)素描中對同一主題的描繪的影響,也可能沒有[29];但可以肯定的是,《坦塔羅斯》的姿勢——斜倚在被水環繞的岩石上——源自於已經提到過兩次的《墜落的高盧人》[30];而且,對一個古典主題的這種大膽的非古典改變使得提香能夠——首次並且也許是獨一無二地——展示這位處在由荷馬和奧維德所描述的困境中的不幸英雄:“無法獲得水,同時懸垂的果樹也逃離他的掌控”(Metamorphoses, IV, 458f: tibi, Tantale, nullae/Deprenduntur aquae, quaeque imminet effugit arbor)。此外,坦塔羅斯的姿勢與《墜落的高盧人》的姿勢的同化使得他成為《提提俄斯》的一個值得欽佩的對應物:兩個人物都被展示為斜臥著,而不是站立著,並且產生了一種精美的交錯樣式,提提俄斯的身體處在高處,但向下傾斜,他的右臂下垂著;坦塔羅斯的身體處在低處,但向上傾斜,他的右臂上舉著。
我們記得,《伊克西翁》沒有留下任何痕跡。至於《西西弗斯》,我們只能說,這個宏大的人物負重到崩潰的地步——但從未被允許崩潰——,並在壯麗的地獄背景下出發,他代表著另一種嘗試,即將米開朗琪羅的可怖性注入一種古典的運動圖式[31]之中。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