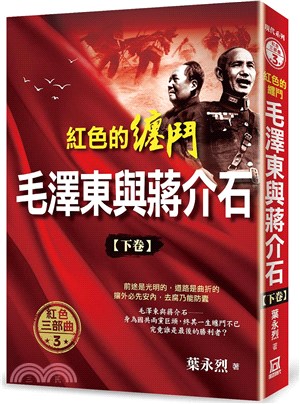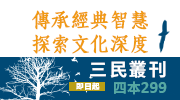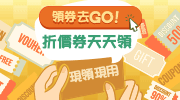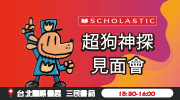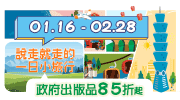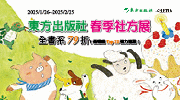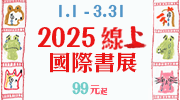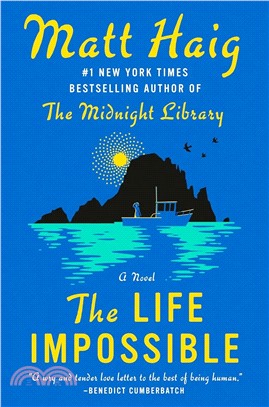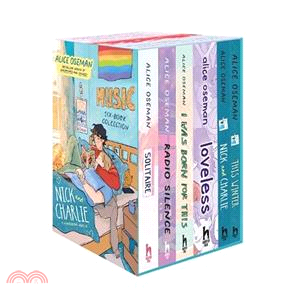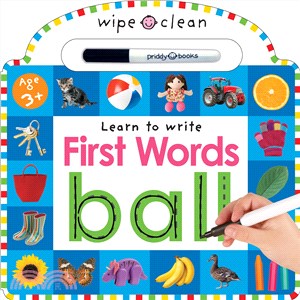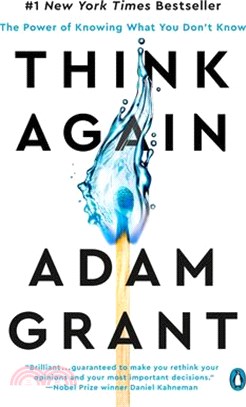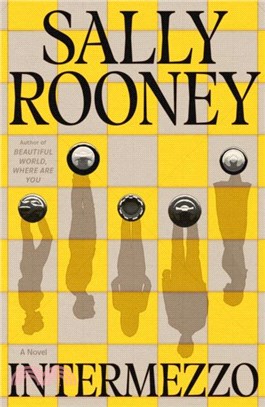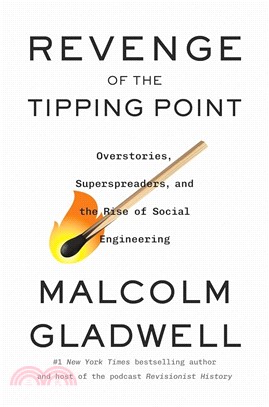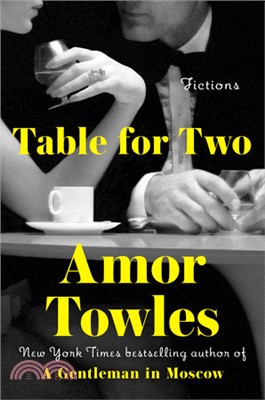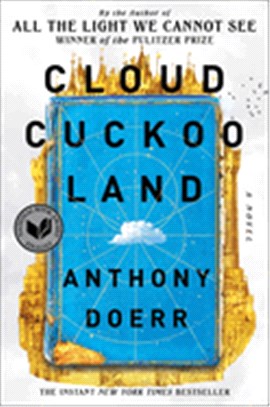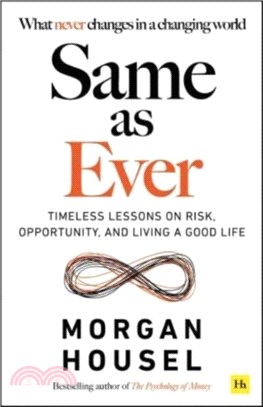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中共成立百年全秘辛大揭露,大陸一級作家葉永烈當世之作!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紅色三部曲三部曲之三《紅色的纏鬥:毛澤東與蔣介石(下)》搞懂國共鬥爭與毛蔣升沉的世紀真相!
※內含16頁精彩圖片。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攘外必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毛澤東與蔣介石身為國共兩黨巨頭,終其一生纏鬥不已,究竟誰是最後的勝利者?
※毛澤東為何笑稱蔣介石是「紙老虎」?他又是用什麼戰略對付蔣介石?
※國共最後決戰時,美國政府既「拋蔣」又「棄台」是怎麼回事?
※「文革」狂潮中的毛澤東和蔣介石各是什麼心情?
※「你辦事,我放心」是毛澤東寫給誰的評語?
※尼克森眼中的毛澤東與蔣介石是什麼樣子?
※萬炮齊轟金門震驚世界,金門為何竟成毛、蔣爭鬥的焦點?
揭密毛蔣之爭的內幕及秘辛
世界歷史兩大巨頭世紀之爭
在國共內鬥的角力時,他們誰輸誰贏?
在中美關係的盤算下,他們誰走誰留?
在腥風血雨的權謀中,他們誰是誰非?
在往左往右的路線上,他們誰對誰錯?
在危機四伏的考驗中,他們誰悲誰喜?
──蔣介石──
曾是世界「四巨頭」之一,亦被視為中華民族的救星,
──毛澤東──
創造了中國第一個紅色政權,建立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
在詭譎複雜的政權爭奪戰中,他們棋逢敵手,難分高下。
毛澤東與蔣介石終將展開一生永不休止的纏鬥……
書中透過國共兩黨的領袖,即毛澤東和周恩來與蔣介石的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邊談邊打、邊打邊談,談判桌上的明爭暗鬥,高潮起伏不斷;談判桌下的爾虞我詐,更是波濤洶湧。
作者首次運用「比較政治學」的手法,將兩人的思想、策略、品格、功過,一一做出最完整詳實的呈現。令人看得欲罷不能。
※內含16頁精彩圖片。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攘外必先安內,去腐乃能防蠹。毛澤東與蔣介石身為國共兩黨巨頭,終其一生纏鬥不已,究竟誰是最後的勝利者?
※毛澤東為何笑稱蔣介石是「紙老虎」?他又是用什麼戰略對付蔣介石?
※國共最後決戰時,美國政府既「拋蔣」又「棄台」是怎麼回事?
※「文革」狂潮中的毛澤東和蔣介石各是什麼心情?
※「你辦事,我放心」是毛澤東寫給誰的評語?
※尼克森眼中的毛澤東與蔣介石是什麼樣子?
※萬炮齊轟金門震驚世界,金門為何竟成毛、蔣爭鬥的焦點?
揭密毛蔣之爭的內幕及秘辛
世界歷史兩大巨頭世紀之爭
在國共內鬥的角力時,他們誰輸誰贏?
在中美關係的盤算下,他們誰走誰留?
在腥風血雨的權謀中,他們誰是誰非?
在往左往右的路線上,他們誰對誰錯?
在危機四伏的考驗中,他們誰悲誰喜?
──蔣介石──
曾是世界「四巨頭」之一,亦被視為中華民族的救星,
──毛澤東──
創造了中國第一個紅色政權,建立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
在詭譎複雜的政權爭奪戰中,他們棋逢敵手,難分高下。
毛澤東與蔣介石終將展開一生永不休止的纏鬥……
書中透過國共兩黨的領袖,即毛澤東和周恩來與蔣介石的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邊談邊打、邊打邊談,談判桌上的明爭暗鬥,高潮起伏不斷;談判桌下的爾虞我詐,更是波濤洶湧。
作者首次運用「比較政治學」的手法,將兩人的思想、策略、品格、功過,一一做出最完整詳實的呈現。令人看得欲罷不能。
作者簡介
葉永烈(1940-2020),為中國大陸的一級作家,生於1940年,自11歲起即發表詩作,現已出版130多部著作,作品曾獲獎六十餘次,電影《紅綠燈下》(擔任導演)獲中國第三屆電影「百花獎」。葉永烈作品曾在美國、法國,英國、日本,韓國、瑞典、西德、捷克等地出版或發表,1989年被收入美國《世界名人錄》,並被美國傳記研究所聘請為顧問,被台灣《幻象雜誌》聘請為顧問。1992年擔任大陸和台灣聯合攝製的百集系列片《中華五千年》總主筆。著有《十萬個為什麼》、《歷史選擇了毛澤東》、紅色三部曲:《紅色的起點:中國共產黨原形》、《紅色的掙扎:毛澤東與共產黨》、《紅色的纏鬥:毛澤東與蔣介石上/下》、《四人幫興亡》、《歷史在這裡沉思》及《他影響了中國:陳雲全傳》等多部暢銷書。
目次
◎第七章 風雲多變
國共關係陷入僵局
蔣介石想找台階下台
毛澤東在參政會得了大面子
蔣介石夫婦笑宴周恩來夫婦
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
毛澤東以「感冒」為由第四次拒晤蔣介石
蔣介石、林彪重慶談判
共產國際的解散如同「新聞原子彈」爆炸
毛澤東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共最高領袖
毛澤東抓住張滌非,來了個「質問國民黨」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引起一番風波
蔣介石出席開羅「三巨頭」會議
赫爾利邀毛澤東去重慶會晤蔣介石
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
對台戲:中共「七大」和國民黨「六全」大會
◎第八章 重廈談判
毛澤東說「蔣介石在磨刀」
妙棋乎?刁棋乎?
各方關注延安棗園的動向
毛澤東決策親赴重慶
毛澤東的八角帽換成了巴拿馬盔式帽
棗園、桂園、林園
國共兩巨頭歷史性的握手
初次會談風波驟起
國共談判在山城艱難地進行著
各方關注桂園「何先生」的行蹤
「毛詩」引起的「《沁園春》」熱
毛澤東臨別前山城突然響起槍聲
周恩來冷靜平息「謀殺」風波
毛澤東握別蔣介石
◎第九章 國共決戰
《雙十協定》只是「紙上的東西」
迷航的飛機洩露了蔣介石的天機
大規模內戰正「不宣而戰」
馬歇爾充當了「調解人」的角色
緊張時刻發生緊張事件
毛澤東笑稱蔣介石是「紙老虎」
毛澤東用林沖戰略對付蔣介石
蔣介石為「光復中共赤都」興高采烈
毛澤東笑謂胡宗南「騎虎難下」
蔣介石下令「通緝」毛澤東
毛澤東稱蔣介石為「匪」
蔣介石步上中華民國總統寶座
大決戰前夕雙方摩拳擦掌
東北之敗使蔣介石氣得吐血
五十五萬蔣軍受殲淮海
古都北平在沒有硝煙中交接
◎第十章 風捲殘雲
毛澤東和蔣介石新年對話
毛澤東斥責蔣介石求和是虛偽的
蔣介石忍痛宣告「引退」
李宗仁「代行總統職務」
毛澤東論蔣介石、李宗仁優劣
國民黨代表團在北平受到冷遇
「百萬雄師過大江」
毛澤東通向李宗仁的「暗線」
蔣介石在上海差一點被活捉
國共之戰已進入「殘局」
別了,司徒雷登!
毛澤東在北京主持開國大典
蔣介石對中國大陸的最後一瞥
◎第十一章 隔著海峽
蔣介石只能實行第三方案
蔣介石對退往「美麗島」作了周密部署
蔣介石迫使李宗仁讓位
蔣介石反思失敗的原因
美國政府既「拋蔣」又「棄台」
朝鮮的槍聲使蔣介石喘了一口氣
毛澤東的解放台灣和蔣介石的反攻大陸
「克什米爾公主號」的迷霧
周恩來在萬隆首次提出解決台灣問題
章士釗和程思遠各負特殊使命
曹聚仁為北京和蔣經國牽線
蔣介石派出宋宜山密訪北京
◎第十二章 未完的棋
萬炮齊轟金門震驚了世界
金門成了毛澤東和蔣介石爭鬥的焦點
葉飛透露出炮打金門的內情
曹聚仁在緊張時刻出現在北京
戲劇性的炮擊金門
毛澤東的經濟失誤使蔣介石幸災樂禍
毛澤東笑謂李宗仁歸來「誤上賊船」
曹聚仁穿梭於北京―香港―台北
「文革」狂潮中的毛澤東和蔣介石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著手安排身後事
季辛格密訪北京如同爆炸了原子彈
台灣被逐出聯合國成了太平洋中的孤舟
尼克森眼中的毛澤東和蔣介石
毛澤東派章士釗赴港「重操舊業」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垂垂老矣
蔣介石自知不起口授遺囑
病危的毛澤東給華國鋒寫了「你辦事,我放心」
鄧小平和蔣經國繼續著那盤沒完的棋
後記
國共關係陷入僵局
蔣介石想找台階下台
毛澤東在參政會得了大面子
蔣介石夫婦笑宴周恩來夫婦
蔣介石出任中國戰區盟軍最高統帥
毛澤東以「感冒」為由第四次拒晤蔣介石
蔣介石、林彪重慶談判
共產國際的解散如同「新聞原子彈」爆炸
毛澤東成為名符其實的中共最高領袖
毛澤東抓住張滌非,來了個「質問國民黨」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引起一番風波
蔣介石出席開羅「三巨頭」會議
赫爾利邀毛澤東去重慶會晤蔣介石
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
對台戲:中共「七大」和國民黨「六全」大會
◎第八章 重廈談判
毛澤東說「蔣介石在磨刀」
妙棋乎?刁棋乎?
各方關注延安棗園的動向
毛澤東決策親赴重慶
毛澤東的八角帽換成了巴拿馬盔式帽
棗園、桂園、林園
國共兩巨頭歷史性的握手
初次會談風波驟起
國共談判在山城艱難地進行著
各方關注桂園「何先生」的行蹤
「毛詩」引起的「《沁園春》」熱
毛澤東臨別前山城突然響起槍聲
周恩來冷靜平息「謀殺」風波
毛澤東握別蔣介石
◎第九章 國共決戰
《雙十協定》只是「紙上的東西」
迷航的飛機洩露了蔣介石的天機
大規模內戰正「不宣而戰」
馬歇爾充當了「調解人」的角色
緊張時刻發生緊張事件
毛澤東笑稱蔣介石是「紙老虎」
毛澤東用林沖戰略對付蔣介石
蔣介石為「光復中共赤都」興高采烈
毛澤東笑謂胡宗南「騎虎難下」
蔣介石下令「通緝」毛澤東
毛澤東稱蔣介石為「匪」
蔣介石步上中華民國總統寶座
大決戰前夕雙方摩拳擦掌
東北之敗使蔣介石氣得吐血
五十五萬蔣軍受殲淮海
古都北平在沒有硝煙中交接
◎第十章 風捲殘雲
毛澤東和蔣介石新年對話
毛澤東斥責蔣介石求和是虛偽的
蔣介石忍痛宣告「引退」
李宗仁「代行總統職務」
毛澤東論蔣介石、李宗仁優劣
國民黨代表團在北平受到冷遇
「百萬雄師過大江」
毛澤東通向李宗仁的「暗線」
蔣介石在上海差一點被活捉
國共之戰已進入「殘局」
別了,司徒雷登!
毛澤東在北京主持開國大典
蔣介石對中國大陸的最後一瞥
◎第十一章 隔著海峽
蔣介石只能實行第三方案
蔣介石對退往「美麗島」作了周密部署
蔣介石迫使李宗仁讓位
蔣介石反思失敗的原因
美國政府既「拋蔣」又「棄台」
朝鮮的槍聲使蔣介石喘了一口氣
毛澤東的解放台灣和蔣介石的反攻大陸
「克什米爾公主號」的迷霧
周恩來在萬隆首次提出解決台灣問題
章士釗和程思遠各負特殊使命
曹聚仁為北京和蔣經國牽線
蔣介石派出宋宜山密訪北京
◎第十二章 未完的棋
萬炮齊轟金門震驚了世界
金門成了毛澤東和蔣介石爭鬥的焦點
葉飛透露出炮打金門的內情
曹聚仁在緊張時刻出現在北京
戲劇性的炮擊金門
毛澤東的經濟失誤使蔣介石幸災樂禍
毛澤東笑謂李宗仁歸來「誤上賊船」
曹聚仁穿梭於北京―香港―台北
「文革」狂潮中的毛澤東和蔣介石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著手安排身後事
季辛格密訪北京如同爆炸了原子彈
台灣被逐出聯合國成了太平洋中的孤舟
尼克森眼中的毛澤東和蔣介石
毛澤東派章士釗赴港「重操舊業」
毛澤東和蔣介石都垂垂老矣
蔣介石自知不起口授遺囑
病危的毛澤東給華國鋒寫了「你辦事,我放心」
鄧小平和蔣經國繼續著那盤沒完的棋
後記
書摘/試閱
第七章 風雲多變
國共關係陷入僵局
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中國各報差不多都在頭版以醒目的大字標題,報導了觸目驚心的皖南事變。
不過,那時的中國報紙,大都控制在蔣介石手中。各報紛載的,除了消息之外,所登都是清一色的蔣氏文告,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關於解散新四軍的通電》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言人談話》。
中共掌握的報紙,大體限於延安,很難進入國民黨統治區,在那裏產生影響。唯一突破「防線」的中共報紙,是在重慶印行的《新華日報》。不過,《新華日報》也要受國民黨的新聞檢查,稿件只有經過審查同意才能刊登。
這天,《新華日報》有關皖南事變的新聞稿,全被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官扣押,只得臨時採用巧妙的調包的手法,在第二版刊出周恩來的題詞:
「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
另外,在第三版,還醒目地刊載周恩來一首詩的手跡: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後來,毛澤東在看到這份不平常的報紙之後,曾致電周恩來:「報紙題字亦看到,為之神往。」
各國駐華記者也紛紛發出急電,報告中國政局的重大變化。
來自各國的反應,隨著各國的立場不同,而對皖南事變作出不同的評價。
美國的反應出人意料。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社論指出,皖南事變是「極大的不幸」,認為國民黨稱中共為「心腹大患」、日本為「癬疥之疾」,是極其錯誤的。
美國駐華使節詹森拜見蔣介石,表達了這樣的態度:「我一向認為,共產黨問題不應導致大規模的互相殘殺,美國人民及其政府對中國維持獨立生存的能力極為關切。」
美國對皖南事變不悅,是因為美日關係已極度緊張。美國不希望中國內戰削弱了抗日力量。
英國的立場和美國一致。英國政府通過駐華大使卡爾把意見告訴蔣介石:「內戰只會加強日本的攻擊。」
蘇聯的反應則在意料之中。蘇聯支持中共,理所當然反對皖南事變。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崔可夫明確表示:「對於所發生的事件,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
一月二十五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會見蔣介石,指出:「對於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滅亡。」
美、英、蘇三國採取反對立場,使蔣介石由「三喜臨門」轉為「三不歡迎」。
日本當然歡迎中國內戰。早在皖南事變發生之前的一個多月,日軍駐滬軍部參謀長櫻井便已赴南京,與駐華日軍司令西尾壽造制訂了計劃,其中有一條:
「對散駐京滬杭地區之新四軍,決迫其向皖南退卻,並設法使其與中央部隊自相火並。」
最妙的反應來自汪精衛。他說了一句「名言」:
「數年來蔣介石未作一件好事,惟此次尚屬一個好人。」
國內也一片嘩然。叫好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國民黨左派人士發出一片反對聲。其中,最為激烈的是宋慶齡、何香凝,尖銳地抨擊了蔣介石。
美國華僑領袖司徒美堂的一句批評蔣介石的話,最為概括:
「自毀長城,自促國亡。」
態度最強硬的,自然是中共。毛澤東在公開發表《命令》和《談話》中,明確指出:
「中國共產黨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樣容易受人欺騙和容易受人摧毀。中國共產黨已是一個屹然獨立的大政黨了。」
毛澤東還接連對中共內部作出指示:
「蔣介石已將我們推到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一切已無話可說。」(一月二十日致周恩來電)
「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是全面投降與全面破裂的開始。」(一月二十三日致劉少奇電)
「人家已宣布我們叛變,我們決不能再取遊移態度,我們決不能再容忍,我們決不能怕破裂,否則我就要犯嚴重錯誤……我們是只有和他對立一途,因為我沒有別的路。」(一月二十五日致周恩來電)
「蔣一月十七日命令及談話,對我們甚為有利,因為他把我們推到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因為破裂是他發動的,我們應該捉住一月十七日命令堅決反攻,跟蹤追擊,絕不游移,絕不妥協。」(同上,另一電)
面對著只有日本、汪精衛和國民黨右翼發出的稀稀落落的掌聲,面對著來自國內外的一片譴責聲,面對著毛澤東的強硬態度,蔣介石不能不收斂了一些。
一月二十七日,蔣介石在重慶中央紀念週發表講話,那姿態處於守勢。雖說他仍堅持十天前「一‧一七」文告的立場,但他的講話調子明顯變軟了。蔣介石說:
「這次新四軍因為違抗命令,襲擊友軍,甚至稱兵作亂,破壞抗戰,因而受到軍法制裁,這純然是為了整飭軍紀。除此以外,並無其他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派的性質夾雜其中,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
蔣介石的意思是這回皖南事變,只侷限於新四軍,他並不準備與中共決裂。
蔣介石還擺出「家長」的架勢說道:
「新四軍乃是國民革命軍之一部,而本席乃是國民革命軍的統帥。我常說我們國民革命軍是一個大家庭,所以我平時看待自己的部下,猶之於家長之看待子弟,子弟良好,固然是家長的榮幸,如果子弟不良,亦就是家長的恥辱。……」
蔣介石的講話中居然還談起了聖經──他和宋美齡結婚之後,已成了基督教徒。蔣介石以虔誠的基督教徒的口氣說道:
「大家看過聖經新約的,都知道基督的教條,訓勉一般人,對於罪人,須要饒恕他七十個七次的罪過,而現在新四軍的罪過,早已超過了七十個七次以上。我們就以耶穌的寬大為懷,對於這種怙惡不悛,執迷不悟的軍隊,也決不能再隱忍,再饒恕,否則就是我們自己的犯罪,就是我們貽害國家,要成為千古罪人。
蔣介石的講話,缺少幽默感,倒也不乏「生動」!
毛澤東當即讀了蔣介石的講話,他在三天後――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在致周恩來的電報中,作出反應:
「蔣二十七日演講已轉入辯護(防禦)態度,可見各方不滿,他已賊膽心虛……」
皖南事變使國共關係陷入了僵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月二十九日作出《關於目前時局的決定》,對皖南事變作出了這樣結論性的正式評價:
「蔣介石發動的皖南事變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軍叛變的命令,是全國性突然事變與全面破裂的開始,是西安事變以來中國政治上的巨大變化,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由合作到破裂的轉折點。」
蔣介石想找台階下台
不過,即使國共關係近於冰點的時候,蔣介石和毛澤東都還保持著克制:蔣介石沒有借皖南事變繼續大打;毛澤東沒有借皖南事變大鬧。
國共雙方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外敵――日本。蔣介石要顧忌各方的批評,毛澤東要考慮大敵當前。國共大打,「漁翁」日本得利。這樣,國共雙方都下不了大分裂的決心。
毛澤東的反擊,只是在政治上,在輿論上,大造聲勢。如毛澤東所言,「政治上取攻勢,軍事上暫時仍取守勢。」
蔣介石呢?也只侷限於新四軍,只侷限於說新四軍「違抗軍令」,這把火沒有燒到八路軍,沒有燒到整個中共。
毛澤東在一月二十五日致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的電報中,便作出這樣「有節」的策略規定:
「蔣現尚未提及八路與中共,故我們亦不提及整個國民黨及中央軍,八路及中共人員亦不公開出面,看蔣怎樣來,我們便怎樣去,在這點上我們仍是防禦的。」
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黨內指示文件中,又提醒給蔣介石留點「面子」。毛澤東寫道:
「惟在蔣沒有宣布全部破裂時(宣布八路及中共叛變),我們暫時不公開提出反蔣口號,而以當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蔣介石的名字……」
正是由於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在互相指責中保持了克制,使國共瀕於大破裂的局面,終於得以挽回。
最使蔣介石尷尬的是,就在他的「一‧一七」命令發佈之後,日軍居然便在二十四日把蔣介石的湯恩伯部隊十五萬人包圍於平漢鐵路以東!這表明,蔣介石一旦與毛澤東大決裂,日本便會大舉進攻!
日本陸相東條英機在三十日發表講話,聲稱:
「蔣政權內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戰,但日本決不能依賴國共糾紛,而是要依賴自己的力量來解決中國事件。」
日本的態度,也使蔣介石不能不考慮和中共重新和好。
不過,國共關係從冰點漸漸昇溫,要有一個過程。最初,雙方都彆彆扭扭,冷冷淡淡,圓睜怒眼,板著面孔。
周恩來在這陰晦寒冷的時刻,機警地指出:蔣介石一下子下不了台,正在尋找台階……
毛澤東也很清楚時局的轉變。他在二月十四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作出判斷:
「蔣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我亦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國內外)。」
「目前形勢是有了變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進攻的,我是防禦的;十七日以後反過來了,他已處於防禦地位,我之最大勝利在此。」
「反共不會變,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
「目前國共是僵局(如陳布雷所說),但時間不會久,敵大舉進攻之日,即僵局變化之時……」
真是尷尬人偏遇尷尬事。蔣介石正在找台階下台之際,碰上了棘手的難題:
早在皖南事變前十來天,公佈了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名單。其中,中共參政員依然是毛澤東等七人。同時還公佈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將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開幕。眼下,三月一日逐漸臨近,而中共卻表示如果蔣介石不接受「十二條」,他們就不出席會議。蔣介石本來是以國民參政會來裝潢民主的,中共不出席會議,理所當然使蔣介石尷尬不堪。
中共的「十二條」,早在一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中,就明明白白地開列了:
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
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並宣布自己是完全錯了;
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三人;
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新四軍軍長;
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
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
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
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
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
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
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
十二,逮捕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顯而易見,毛澤東所開列的這十二條,是蔣介石所萬萬不能接受的。
其實,毛澤東心裏也很明白,蔣介石是不可能接受這十二條的。毛澤東在二月二十四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說了一句頗為微妙的話:
「用蔣介石的手破了一條缺口的國共關係,只有用我們的手才能縫好,我們的手即政治攻勢,即十二條,除此再無別的妙法。」
「我們目的,不在蔣承認十二條或十二條之一部份,他是不會承認的(當然對黨內外群眾都不如此說,仍是要求蔣承認),而在於以攻勢打退攻勢。」
「對於一個強力進攻者把他打到防禦地位,使他不再進攻了,國共好轉的可能性就有了。」
這就是說,在毛澤東看來,他的十二條,乃是一種「政治攻勢」。
毛澤東索性把這「政治攻勢」鬧大:讓周恩來以中共七參政員的名義,把這十二條乾脆送交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杰,要求國民參政會加以討論!
周恩來還說明,在這十二條未得裁奪之前,中共參政員礙難出席!
在這一「政治攻勢」面前,蔣介石顯得被動。雖說蔣介石想約周恩來一談,但聖誕節的那次談話猶在耳邊……
於是,只好請國共談判的元老張沖出馬。
國共關係陷入僵局
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八日,中國各報差不多都在頭版以醒目的大字標題,報導了觸目驚心的皖南事變。
不過,那時的中國報紙,大都控制在蔣介石手中。各報紛載的,除了消息之外,所登都是清一色的蔣氏文告,即《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關於解散新四軍的通電》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發言人談話》。
中共掌握的報紙,大體限於延安,很難進入國民黨統治區,在那裏產生影響。唯一突破「防線」的中共報紙,是在重慶印行的《新華日報》。不過,《新華日報》也要受國民黨的新聞檢查,稿件只有經過審查同意才能刊登。
這天,《新華日報》有關皖南事變的新聞稿,全被國民黨的新聞檢查官扣押,只得臨時採用巧妙的調包的手法,在第二版刊出周恩來的題詞:
「為江南死國難者致哀」。
另外,在第三版,還醒目地刊載周恩來一首詩的手跡:
「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後來,毛澤東在看到這份不平常的報紙之後,曾致電周恩來:「報紙題字亦看到,為之神往。」
各國駐華記者也紛紛發出急電,報告中國政局的重大變化。
來自各國的反應,隨著各國的立場不同,而對皖南事變作出不同的評價。
美國的反應出人意料。紐約《先驅論壇報》的社論指出,皖南事變是「極大的不幸」,認為國民黨稱中共為「心腹大患」、日本為「癬疥之疾」,是極其錯誤的。
美國駐華使節詹森拜見蔣介石,表達了這樣的態度:「我一向認為,共產黨問題不應導致大規模的互相殘殺,美國人民及其政府對中國維持獨立生存的能力極為關切。」
美國對皖南事變不悅,是因為美日關係已極度緊張。美國不希望中國內戰削弱了抗日力量。
英國的立場和美國一致。英國政府通過駐華大使卡爾把意見告訴蔣介石:「內戰只會加強日本的攻擊。」
蘇聯的反應則在意料之中。蘇聯支持中共,理所當然反對皖南事變。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崔可夫明確表示:「對於所發生的事件,我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
一月二十五日,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會見蔣介石,指出:「對於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著滅亡。」
美、英、蘇三國採取反對立場,使蔣介石由「三喜臨門」轉為「三不歡迎」。
日本當然歡迎中國內戰。早在皖南事變發生之前的一個多月,日軍駐滬軍部參謀長櫻井便已赴南京,與駐華日軍司令西尾壽造制訂了計劃,其中有一條:
「對散駐京滬杭地區之新四軍,決迫其向皖南退卻,並設法使其與中央部隊自相火並。」
最妙的反應來自汪精衛。他說了一句「名言」:
「數年來蔣介石未作一件好事,惟此次尚屬一個好人。」
國內也一片嘩然。叫好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國民黨左派人士發出一片反對聲。其中,最為激烈的是宋慶齡、何香凝,尖銳地抨擊了蔣介石。
美國華僑領袖司徒美堂的一句批評蔣介石的話,最為概括:
「自毀長城,自促國亡。」
態度最強硬的,自然是中共。毛澤東在公開發表《命令》和《談話》中,明確指出:
「中國共產黨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樣容易受人欺騙和容易受人摧毀。中國共產黨已是一個屹然獨立的大政黨了。」
毛澤東還接連對中共內部作出指示:
「蔣介石已將我們推到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一切已無話可說。」(一月二十日致周恩來電)
「蔣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是全國性突然事變的開始,是全面投降與全面破裂的開始。」(一月二十三日致劉少奇電)
「人家已宣布我們叛變,我們決不能再取遊移態度,我們決不能再容忍,我們決不能怕破裂,否則我就要犯嚴重錯誤……我們是只有和他對立一途,因為我沒有別的路。」(一月二十五日致周恩來電)
「蔣一月十七日命令及談話,對我們甚為有利,因為他把我們推到同他完全對立的地位,因為破裂是他發動的,我們應該捉住一月十七日命令堅決反攻,跟蹤追擊,絕不游移,絕不妥協。」(同上,另一電)
面對著只有日本、汪精衛和國民黨右翼發出的稀稀落落的掌聲,面對著來自國內外的一片譴責聲,面對著毛澤東的強硬態度,蔣介石不能不收斂了一些。
一月二十七日,蔣介石在重慶中央紀念週發表講話,那姿態處於守勢。雖說他仍堅持十天前「一‧一七」文告的立場,但他的講話調子明顯變軟了。蔣介石說:
「這次新四軍因為違抗命令,襲擊友軍,甚至稱兵作亂,破壞抗戰,因而受到軍法制裁,這純然是為了整飭軍紀。除此以外,並無其他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派的性質夾雜其中,這是大家都能明白的……」
蔣介石的意思是這回皖南事變,只侷限於新四軍,他並不準備與中共決裂。
蔣介石還擺出「家長」的架勢說道:
「新四軍乃是國民革命軍之一部,而本席乃是國民革命軍的統帥。我常說我們國民革命軍是一個大家庭,所以我平時看待自己的部下,猶之於家長之看待子弟,子弟良好,固然是家長的榮幸,如果子弟不良,亦就是家長的恥辱。……」
蔣介石的講話中居然還談起了聖經──他和宋美齡結婚之後,已成了基督教徒。蔣介石以虔誠的基督教徒的口氣說道:
「大家看過聖經新約的,都知道基督的教條,訓勉一般人,對於罪人,須要饒恕他七十個七次的罪過,而現在新四軍的罪過,早已超過了七十個七次以上。我們就以耶穌的寬大為懷,對於這種怙惡不悛,執迷不悟的軍隊,也決不能再隱忍,再饒恕,否則就是我們自己的犯罪,就是我們貽害國家,要成為千古罪人。
蔣介石的講話,缺少幽默感,倒也不乏「生動」!
毛澤東當即讀了蔣介石的講話,他在三天後――一月三十日,毛澤東在致周恩來的電報中,作出反應:
「蔣二十七日演講已轉入辯護(防禦)態度,可見各方不滿,他已賊膽心虛……」
皖南事變使國共關係陷入了僵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一月二十九日作出《關於目前時局的決定》,對皖南事變作出了這樣結論性的正式評價:
「蔣介石發動的皖南事變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軍叛變的命令,是全國性突然事變與全面破裂的開始,是西安事變以來中國政治上的巨大變化,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由合作到破裂的轉折點。」
蔣介石想找台階下台
不過,即使國共關係近於冰點的時候,蔣介石和毛澤東都還保持著克制:蔣介石沒有借皖南事變繼續大打;毛澤東沒有借皖南事變大鬧。
國共雙方都面臨著一個共同的外敵――日本。蔣介石要顧忌各方的批評,毛澤東要考慮大敵當前。國共大打,「漁翁」日本得利。這樣,國共雙方都下不了大分裂的決心。
毛澤東的反擊,只是在政治上,在輿論上,大造聲勢。如毛澤東所言,「政治上取攻勢,軍事上暫時仍取守勢。」
蔣介石呢?也只侷限於新四軍,只侷限於說新四軍「違抗軍令」,這把火沒有燒到八路軍,沒有燒到整個中共。
毛澤東在一月二十五日致周恩來、劉少奇、彭德懷的電報中,便作出這樣「有節」的策略規定:
「蔣現尚未提及八路與中共,故我們亦不提及整個國民黨及中央軍,八路及中共人員亦不公開出面,看蔣怎樣來,我們便怎樣去,在這點上我們仍是防禦的。」
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黨內指示文件中,又提醒給蔣介石留點「面子」。毛澤東寫道:
「惟在蔣沒有宣布全部破裂時(宣布八路及中共叛變),我們暫時不公開提出反蔣口號,而以當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蔣介石的名字……」
正是由於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在互相指責中保持了克制,使國共瀕於大破裂的局面,終於得以挽回。
最使蔣介石尷尬的是,就在他的「一‧一七」命令發佈之後,日軍居然便在二十四日把蔣介石的湯恩伯部隊十五萬人包圍於平漢鐵路以東!這表明,蔣介石一旦與毛澤東大決裂,日本便會大舉進攻!
日本陸相東條英機在三十日發表講話,聲稱:
「蔣政權內部打架,固然不能抗戰,但日本決不能依賴國共糾紛,而是要依賴自己的力量來解決中國事件。」
日本的態度,也使蔣介石不能不考慮和中共重新和好。
不過,國共關係從冰點漸漸昇溫,要有一個過程。最初,雙方都彆彆扭扭,冷冷淡淡,圓睜怒眼,板著面孔。
周恩來在這陰晦寒冷的時刻,機警地指出:蔣介石一下子下不了台,正在尋找台階……
毛澤東也很清楚時局的轉變。他在二月十四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作出判斷:
「蔣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我亦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國內外)。」
「目前形勢是有了變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進攻的,我是防禦的;十七日以後反過來了,他已處於防禦地位,我之最大勝利在此。」
「反共不會變,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止。」
「目前國共是僵局(如陳布雷所說),但時間不會久,敵大舉進攻之日,即僵局變化之時……」
真是尷尬人偏遇尷尬事。蔣介石正在找台階下台之際,碰上了棘手的難題:
早在皖南事變前十來天,公佈了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名單。其中,中共參政員依然是毛澤東等七人。同時還公佈第二屆國民參政會第一次會議將在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開幕。眼下,三月一日逐漸臨近,而中共卻表示如果蔣介石不接受「十二條」,他們就不出席會議。蔣介石本來是以國民參政會來裝潢民主的,中共不出席會議,理所當然使蔣介石尷尬不堪。
中共的「十二條」,早在一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中,就明明白白地開列了:
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
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並宣布自己是完全錯了;
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三人;
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新四軍軍長;
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
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
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
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
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
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
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
十二,逮捕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顯而易見,毛澤東所開列的這十二條,是蔣介石所萬萬不能接受的。
其實,毛澤東心裏也很明白,蔣介石是不可能接受這十二條的。毛澤東在二月二十四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說了一句頗為微妙的話:
「用蔣介石的手破了一條缺口的國共關係,只有用我們的手才能縫好,我們的手即政治攻勢,即十二條,除此再無別的妙法。」
「我們目的,不在蔣承認十二條或十二條之一部份,他是不會承認的(當然對黨內外群眾都不如此說,仍是要求蔣承認),而在於以攻勢打退攻勢。」
「對於一個強力進攻者把他打到防禦地位,使他不再進攻了,國共好轉的可能性就有了。」
這就是說,在毛澤東看來,他的十二條,乃是一種「政治攻勢」。
毛澤東索性把這「政治攻勢」鬧大:讓周恩來以中共七參政員的名義,把這十二條乾脆送交國民參政會秘書長王世杰,要求國民參政會加以討論!
周恩來還說明,在這十二條未得裁奪之前,中共參政員礙難出席!
在這一「政治攻勢」面前,蔣介石顯得被動。雖說蔣介石想約周恩來一談,但聖誕節的那次談話猶在耳邊……
於是,只好請國共談判的元老張沖出馬。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