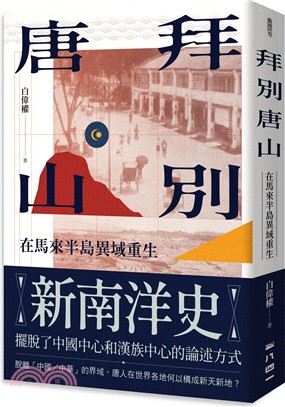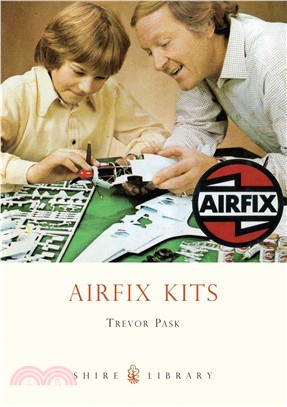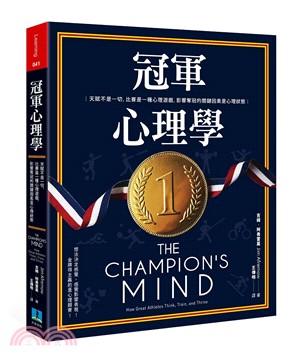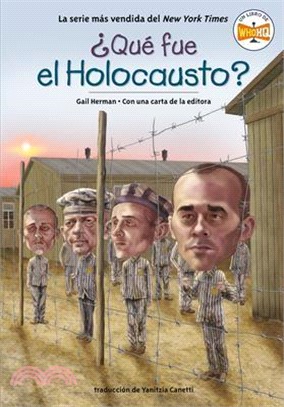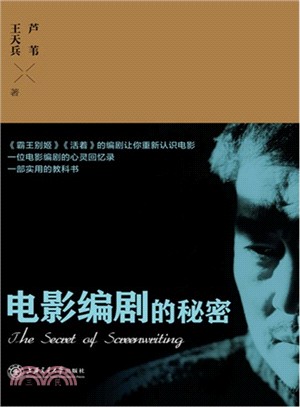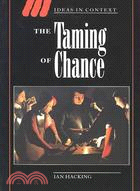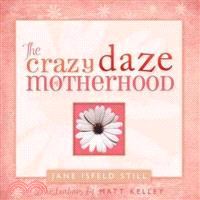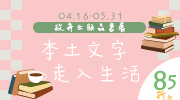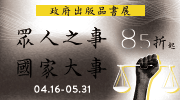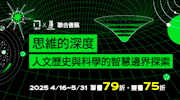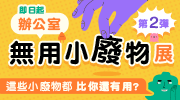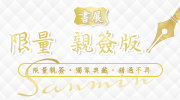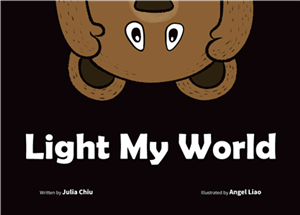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商品簡介
誰的歷史?誰能想像?誰可書寫?
地廣人稀、物產豐富,爭相移居之地
為我們揭開海外華人在南洋的真實面目
歐洲人稱之為東印度,中國人稱之為 「南洋」,當地南島民族稱之為Nusantara
無論是南洋、東印度,都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命名,充滿他者的想像以及主導意識
二戰之前的歷史長河,這塊區域的名字都非憑空產生,而是反映某種歷史現實
南洋是中國人出洋的最大目的地,是一片處處充滿通商機會的大型貿易場
旅居於此的西方殖民者、傳教士,阿拉伯、印度、歐美等地的商人和移民
族群雜處,眾聲喧嘩,為冒險者提供了無限的可能
相對原鄉中國單一的社會,南洋則如同一個縮小版的世界
同一條街上有觀音廟、象頭神神龕、甲必丹吉靈回教堂、聖公會教堂
「南洋華人」在日常生活中吸納其他文化,而有別於「原鄉華人」
《拜別唐山:在馬來半島異域重生》,呈現南洋的華人生活
回到歷史現場,聚焦於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的拿律
以該時空拿律的人、事、物為核心往外延伸,開展引人入勝的小故事
體現了華人族群之間、其他民族之間、國家之間、經濟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
他們都是拜別唐山離鄉背井在馬來半島這片異域上重生的華人
地廣人稀、物產豐富,爭相移居之地
為我們揭開海外華人在南洋的真實面目
歐洲人稱之為東印度,中國人稱之為 「南洋」,當地南島民族稱之為Nusantara
無論是南洋、東印度,都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命名,充滿他者的想像以及主導意識
二戰之前的歷史長河,這塊區域的名字都非憑空產生,而是反映某種歷史現實
南洋是中國人出洋的最大目的地,是一片處處充滿通商機會的大型貿易場
旅居於此的西方殖民者、傳教士,阿拉伯、印度、歐美等地的商人和移民
族群雜處,眾聲喧嘩,為冒險者提供了無限的可能
相對原鄉中國單一的社會,南洋則如同一個縮小版的世界
同一條街上有觀音廟、象頭神神龕、甲必丹吉靈回教堂、聖公會教堂
「南洋華人」在日常生活中吸納其他文化,而有別於「原鄉華人」
《拜別唐山:在馬來半島異域重生》,呈現南洋的華人生活
回到歷史現場,聚焦於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的拿律
以該時空拿律的人、事、物為核心往外延伸,開展引人入勝的小故事
體現了華人族群之間、其他民族之間、國家之間、經濟環境之間的互動關係
他們都是拜別唐山離鄉背井在馬來半島這片異域上重生的華人
作者簡介
白偉權
出生於新加坡,馬來西亞華裔,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在台期間曾任中國地理學會秘書、國家教育研究院學術名詞審譯委員會編輯委員、東吳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現為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兼東南亞學系主任、馬來西亞董教總統一課程委員會地理科學科顧問、《當今大馬》專欄作者。研究旨趣包括馬來西亞區域地理、歷史地理、華人研究、地名學。
著有《柔佛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1855-1942》(2015)、《赤道線的南洋密碼:台灣@馬來半島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誌》(2022),主編《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年刊》(2018-2021)。 《拜別唐山:在馬來半島異域重生》。
出生於新加坡,馬來西亞華裔,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在台期間曾任中國地理學會秘書、國家教育研究院學術名詞審譯委員會編輯委員、東吳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國立中央大學客家學院博士後研究員。
現為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助理教授兼東南亞學系主任、馬來西亞董教總統一課程委員會地理科學科顧問、《當今大馬》專欄作者。研究旨趣包括馬來西亞區域地理、歷史地理、華人研究、地名學。
著有《柔佛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1855-1942》(2015)、《赤道線的南洋密碼:台灣@馬來半島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誌》(2022),主編《新山華族歷史文物館年刊》(2018-2021)。 《拜別唐山:在馬來半島異域重生》。
序
推薦序/陳國川
東南亞區域的名稱多元,提醒我們反思:「誰的歷史?誰寫的歷史?」的問題。白偉權教授,我們都暱稱他小白,十餘年來孜孜矻矻於田野,皓首窮經於文獻史料,從不間斷。經由田野調查及檔案、古地圖蒐集史料,採跨域的觀點,以拿律為核心的北馬舞台,書寫近二百年來的庶民歷史,並釐清華人在這塊土地歷史中扮演的角色。
本書由三個主題單元組成,首先「這才是華人社會日常」,以華人先輩在熱帶叢林中爭奪、採集不可更新資源為軸線,描述華人社會底層庶民,離鄉背井來此謀生時的勞動條件、飲食內容、地方疾病及社會網絡等,他們大多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成就的不只是今日華族生活家園的奠基者,也是北馬歷史的共同書寫者。第二部分「異域重生:拿律演義」,描繪來自不同原鄉的華人族群,在採集資源過程中,彼此之間,以及和在地邦國、和英國殖民勢力之間的互動,相當程度重建了十九世紀拿律地區人―地交互作用、人―人交互作用與地―地交互作用的歷史圖像。最後,「拜別唐山的華人們」單元,則以錫米產業鏈各級礦務主及商賈為主角,以錫礦開採、加工、物流等的操作為經,以操作過程刻畫的遺跡與地景為緯,書寫各階層華人先輩在實踐「日久他鄉變故鄉」過程裡,所付出的努力與代價。
本書的最大貢獻是,以宏觀的區域視角,回到小地域或地點的歷史現場。從荒野中的墓碑、廟宇裡的牌匾、對聯及碑記,以及行政、治安單位留下的檔案與古地圖等庶民史料,以簡潔精確的描述,訴說先輩篳路藍縷的過程。在各篇的敘述中,小白以苦力、頭家、會黨、地景、礦主及其產業鏈中的商賈為對象,解析他們在歷史現場所面對的環境挑戰與時代難題,在多面向的歷史發展中,講述這些發展如何引導他們在歷史長河中就地演出的位置。當然,這些挑戰、難題或歷史定位,未必成為科學性的知識問題,但卻是自身生命意義的創造與展現。我們現在享受他們奠基的家園之餘,不只要緬懷,更要關切他們櫛風沐雨的過程。
在博士論文完成後,小白不斷多方嘗試研究的切入角度,從未間斷過其學術旅程,本書是他彙集近年研究成果的第二本專著。研究過程中,小白深入各地義山拍攝墓碑資料、造訪各地廟宇記錄碑記牌匾、親臨大小圖書館蒐集各式檔案、探問在地耆老蒐羅口述資訊,經由這些過程克服華族先輩留下史料較為欠缺的困境。本書匯集的各篇專文,都是他一步一腳印的錐心之作。我肯定小白對學術的執著,對家鄉的熱情,更佩服他有取之不盡的動能。能夠先睹本書的內容,是我的光榮。
陳國川
序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推薦序 /黃賢強
首次與偉權相遇可追溯至二○二○年。當時,我應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陳國川教授之邀,擔任其門生葉韻翠博士論文答辯的口試委員之一。那時的偉權是一位出席旁聽答辯的碩士生。在閑談中,驚喜地發現我們同是馬來西亞新山寬柔中學的校友,盡管我比他早很多年畢業。更引起我關注的是,他正在研究的碩士論文課題是《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1855-1942)》,準備有系統地梳理和論析新山開埠後到二戰前近百年的文化地景發展和演變。偉權於二○一一年完成碩士論文並順利取得碩士學位後,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並以馬來西亞的另外一個地域作為研究個案,深入探討國家與地方,產業與社會的錯綜複雜關係。
二○一六年,我再度有幸受到陳國川教授的邀請,成為偉權博士論文《國家、產業與地方社會的形構:馬來亞拿律地域華人社會的形成與變遷 (1848-1911)》的口試委員。這部博士論文有豐富史料,立論有據,學術視野廣闊。偉權的博士論文不僅順利通過了答辯,也成為研究拿律地區,甚至是研究整個馬來亞地區華人社會的重要學術著作。
如果說偉權的博士論文是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是與學界同行對話的作品,那麽,這本《拜別唐山:在馬來半島異域重生》則是面向普羅大眾的讀物,內容精煉,卻不失學術養分。換句話說,它具備學術內涵,卻以通俗易懂的文筆將故事講清楚說明白。
本書至少有三個值得關注的特點:首先,書中所收錄的文章並非一般無據可查的野史或耆老的回憶,而是有充分的史料支撐,有註明資料來源,並經過考證的史地故事。每篇文章末尾均列有「延伸閱讀」,提供相關參考文獻乃至原始資料,為有興趣深入探究的讀者提供了指引。其次,書中的一些故事或許看似熟悉,但並非老生常談,而是帶有新的觀點和論述。偉權喜歡與讀者一同探討問題,逐層揭示問題的真相。例如,他引領讀者思考東南亞華人是否都是苦力豬仔的後代?最後,全書各章適當地配置相關插圖,有些來自檔案,更多是作者在田野考察中拍攝的照片或繪制的地圖,圖文並茂,增加閲讀的樂趣。
總而言之,偉權博士之所以能夠將學術議題巧妙地以通俗易懂的文筆呈現,或者說將史地故事提升至具有學術內涵的短篇文章,得益於他長期的田野考察,並勤於查閱檔案文獻的雙重努力成果。近年來,馬來西亞湧現了各類地方史出版物,成果參差不齊。偉權的作品可作為範本,在傳播本土史地知識的同時,保持了立論有據的學術原則。高興看到偉權能夠遊走於學術殿堂與大眾教育之間,為馬來西亞華人知識體系的建構添上濃彩重墨的一筆,是為序。
推薦序/李永球
讀歷史,寫歷史,歷史能夠帶來什麼?有說歷史是一面鏡子,能夠鑑古知今,了解過去,知道當今,預知未來。既然是一面鏡鑑,又是怎樣的鏡鑑呢?那就眾說紛紜,各有不同的看法。總覺得那是一面照妖鏡,在歷史的鏡鑑下,妖魔無法遁形,正義永遠是真理。
「董狐之筆」此話是形容撰史依照事實,公正不偏。撰寫歷史須有此精神,依照資料,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切忌添油加醋,胡編瞎造,撰史者必須具備此種「歷史道德」,對得起天地良心。歷史是勝利或當權者撰寫的,我們華族的歷史就得靠我們自己來撰寫,由外族或外國人來撰寫,往往只寫到皮而寫不到骨頭裡的精髓。
照妖鏡之下,被抹黑消滅的歷史,展現鳳凰重生;被篡改捏造的歷史,顯出醜態百出;被排斥邊緣的歷史,終於重見天日;被詆毀誹謗的歷史,獲得伸張正義。
白偉權博士即將出版一本有關太平的史書,邀我為之寫序,受寵若驚之下,不敢怠慢,唯有遵命提筆。
細讀白博士的文章,發現研究成果比很多人都來得好,紮實穩重,大量引用文獻及田野資料,這方面我深感慚愧,亦感到望塵莫及。由於白博士致力於收集及閱讀文獻資料,在此方面勤下苦功,收穫的果實豐碩。因此不僅欽佩,更覺得應該虛心向他學習。
撰寫歷史文章,除了文獻資料,田野調查也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由當地人收集資料並撰寫是最好的。若是外地人,就得長期居留一段時間,付出事倍功半的努力,才會有好的成績。
在田野資料方面,白博士是有缺陷,不僅不夠完整,也不夠深入,畢竟他不是太平本地人。他來過太平幾次,急匆匆收集資料就走,這方面就有欠缺了。但是,批評人家之際,或者說否定人家之後,本人也得自我檢討,切忌倚老賣老,以專家學者自居,目中無人。雖然我在田野調查方面做得好,不過在文獻方面就不夠完整也不夠全面了,畢竟我天生比較懶,文化水平也不夠,閱讀資料就困難重重。
我非常堅持由本地人撰寫本地史。雖說外來的師傅會唸經,這得住上多年熟悉當地後,才會有滾瓜爛熟之效,否則就出現荒腔走板的窘況。如果白博士做的是他本身家鄉的歷史,那就得心應手,事半功倍矣!
地方史最適合當地人來做,蓋因外地人對地方不是很熟悉,對當地語言、環境、地理、人文、歷史更是生疏,做起來就障礙重重,無法深入。閱讀過他的一些文章,發現就有這些缺點,講了這麼多,不舉個例子彷彿在貶低人家,抬高家己。曾經拜讀過他的文章,記得他寫太平的「福建義山」,這是不正確的名稱,真正是「福建公塚」。不過瑕不掩瑜,其文章依然擲地有聲,值得讚揚並推薦。畢竟多一個人來撰寫,好過少一個人寫,還是贊成並感謝他對於太平歷史的撰寫並交出極佳的果實。
而一些文獻派的學者,則不注重田野調查資料,完全抄自書籍及文獻,如此一來,書中有誤則跟著誤矣。或許有人認為書籍文獻或官方檔案、報章資料不會錯,其實還是有一些錯誤或不實的,所謂外行人看熱鬧,內行人看門道,照妖鏡之下,如何遁形呢?
導論:東南亞之前的南洋世界
東南亞是現今人們熟知的地理名詞,然而對很多老一輩的人而言,這是一個新的詞彙。在二戰之前的歷史長河中,這塊區域有很多的名字,歐洲人稱之為東印度(East Indies),中國人則稱之為 「南洋」,當地南島民族則稱之為Nusantara。除了Nusantara之外,無論是南洋,還是東印度,這些名字都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命名,充滿了他者的想像以及主導意識。這種現象並非憑空產生,多少也貼地的反映了某種歷史現實。
對過去的世界而言,這裡物產豐富,有著世界市場所需的商品,因此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在爭相佔地的同時,這裡地廣人稀,無法支援生產過程中所需的勞力,在此情況下,這片區域成為周邊的人口大國人們移出的目的地。中國人便是這個過程當中的最大參與者,也開啟了海外華僑、海外華人在南洋的序章。
事實上,無論是回到歷史現場,或是放在今天的情境,離開自己熟悉的地方,前往一個文化、政治等客觀環境上不屬於自己的地方,絕對不是必然的,而是經歷過無限選擇與掙扎,以及各種推力、拉力的結果。若是以清朝中末葉這個華人大舉出洋的時代來檢視當時中國的話,中國無疑是個相當深的窪地。地方治安不靖、械鬥、人口暴漲、天災、西方國家的入侵、割地賠款、官府壓迫等問題層出不窮,這種從下而上的困境形成一股極強的推力,將人們推向出洋之途。
南洋是中國人出洋的最大目的地,這裡是由多個大小邦國所組成,在殖民經濟的作用下,這裡是一片處處充滿通商機會的大型貿易場,為冒險者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南洋在族群構成上以南島民族為主體,其他也包含旅居於此的西方殖民者、傳教士,以及來自阿拉伯、印度、歐美等地的商人和移民,可謂族群雜處,眾聲喧嘩。這樣的異域是中國正統觀念下的「蠻夷之邦」,按照正常邏輯,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這邊不會有中國元素,但隨著週邊各個國家的移民相繼前來定居之後,這片土地開始變得精彩,精彩的地方在於有許多無法預測的創新元素。
中國人進入南洋的多元世界可謂是一種新的嘗試,因為原鄉中國是一個無論在語言或是文化上都相當單一的社會。南洋的環境則如同一個縮小版的世界,一個福建人隔壁可以是廣府人,像是在檳城的椰腳街(Jalan Masjid Kapitan Keling ),同一條街上不到四百公尺的距離內就可以出現華人的觀音廟、印度人的象頭神神龕、印裔穆斯林的甲必丹吉靈回教堂,以及英國人的聖公會教堂。中國人在這片多元世界定居後,也開始吸納其他文化而成為有別於原鄉華人的「南洋華人」。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存在於新加坡、檳城、馬六甲這些貿易港市的峇峇社群。一般南洋華人即使不像峇峇社群擁有這麼多的「番夷」元素,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語言或是飲食習慣上,或多或少也會受到「番夷」的影響。
在社會上,除了與原鄉所不同的多元之外,這裡也收納了許多原鄉所謂的「暴徒」。中國長期以來充滿了民變、海盜、土匪劫鄉事件,例如在大明實施海禁政策後流亡海外的走私客和海盜,以及在明末清初,那些不服從清朝統治而轉往海外以發展「國際戰線」的叛亂分子。在此後的整個清代當中,不時也有人高舉反清的旗幟來抵抗清政權,在生存空間日益限縮的情況下,每個時間點都有人轉往海外,懸居南洋,南洋由此成為天地會「暴徒」的大本營。
據殖民官員的報告,十九世紀中葉這裡的華人有超過百分之六十有會黨身份,會黨儼然成為華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這些天地會組織在南洋諸土著王國是合法團體,早期的南洋開發基本都離不開天地會的勢力,而居中團結他們的精神標語更是「反清復明」,南洋儼然成為反清勢力的人才庫。無論是一八五〇年的廈門小刀會起事還是清末的革命運動,都能見到南洋華人的身影。當時的清帝國流傳著這麼一段話,指說「臺地之難,難於孤懸海外,非內地輔車相依可比。諺云: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豈真氣數使然耶?」,此句描繪了臺灣山高皇帝遠的社會現狀。我們只能說,幸好南洋不在中華帝國的版圖之中,若是這樣的話,充滿「亂黨」的南洋必然更勝臺灣,成為皇帝黑名單中的第一名。
從多元的文化、會黨林立的角度看來,南洋與原鄉確實有著一百八十度的不同,這樣的差異也構成南洋特殊的主體性,成為形塑南洋華人認同的要素。上述所列舉的南洋特色,其實在東南亞各地的發展軸線幾乎一致。無論是在馬來亞、印尼、越南、緬甸、暹羅、菲律賓等等,華人的在地發展軸線或是所面對的挑戰幾乎是一致的,不外乎是華人沒有國家(中國)在背後保護,他們對於國家也抱持矛盾的態度,既希望有國家,但是又卻步於自己的國家。而東南亞華人也共同經歷殖民統治轉變為獨立國家後的挑戰。在這種歷史共性的作用下,「南洋」已成為東南亞華人的集體認同。那麼,在這個垂直歷史上多變,橫向軸線也很多元的南洋,華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南洋論述的建構及悲情轉向
南洋如何被人所理解,離不開文本的建構,早在清代之前,基本上就已經開始出現文人對南洋的書寫,這也是「南洋」論述建構的一種過程。明、清時期的南洋書寫多數是以遊記的方式出現,像是馬歡的《瀛涯勝覽》(一四五一),陳倫炯的《海國見聞錄》(一七三〇),謝清高的《海錄》(一八二〇),力鈞的《檳榔嶼志略》,李鍾鈺的《新嘉坡風土記》(一八八七),王錫祺的《小方壺齋輿地叢抄》(一八九一)等等。這時候的南洋書寫者大多並非移民或是寓居者(sojourn),而是以一個天朝文人、旅行者的身份來書寫南洋番邦,對他們而言,印象深刻會被記錄的事物無疑是當地居民的服飾、風俗民情、土王、物產等等,充滿了薩伊德(Edward Waefie Said)那種東方主義的調調。
隨著南洋地區歷經多年的城鎮化,加上晚清至民國初年的紛亂,開始有越來越多的移民定居南洋。這時也開始出現一些前來避難的中國南來文人,他們也成為接下來南洋意象的建構者。較知名的有張禮千、姚楠以及許雲樵對馬來亞各地和東南亞的書寫。他們是活躍於二十世紀初至戰後初期的民國文人,被稱為南洋研究三傑。他們在中國戰亂時期以僑民身份寓居南洋,因此在這裡並沒有國籍,但長久的居住也已經令他們對這片土地有所認同,他們的出現也正是南洋研究的濫觴。
他們的書寫有幾個特色,主要是把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視為是華南閩粵社會的延伸,在這個社會中,方言群、幫群林立,華人以會館、廟宇、行業組織等的機構集結。這或許是因為廣大閩粵地區的人們聚集在這小小的聚落中所呈現出的特殊景觀,因此成為不得不提的元素。有趣的是,他們的視野並不侷限於華人社區,更關注區域歷史的發展,馬來半島、暹羅、緬甸等南洋地區都是其關注的重點。此外,他們常針對一些南洋文化進行考釋,亦大量翻譯其他語言的研究成果,充分體現其為這片土地建立論述的企圖心。
在他們之前,南洋研究其實主要是由學院派殖民學者所主導,他們產量豐富,早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便已有自己的發表平台,像是一八四七年發刊的《印度群島與東亞學報》(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一八七八至一九二二年發刊的《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學報》(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SBRAS),以及一九二三年接續至一九四一年的《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MBRAS) ,激發了他們對南洋知識的追求,於是集結了其他志趣相投的學人,才有了一九四〇年中國南洋學會和《南洋學報》的出現。自南洋研究的學群成型之後,後來的學者也開始繼續投入,已經形成一套南洋華人的研究體系。
戰後,大部分的華人開始面對人生的重大抉擇,究竟要放棄中國國籍,入籍僑居地?還是放棄在僑居地辛苦打拼的成果,舉家遷回動蕩的內地?在長久以來國家與民族身份重疊的情況下,選擇脫離中國籍當一名外國人,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抉擇,也是他們無法想象事,畢竟「加入番邦者,還能算是唐人嗎?」。
但從後來的歷史結果看來,成為新的華人是絕大部分人的選擇。在這些新興國家生活的華人,入籍之後並不代表王子和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真正的挑戰才正要開始。華人在東南亞這些土著所掌權的新興國家當中面臨了許多的挑戰,這些挑戰也影響了華人內部既有的幫群認同,使華人轉向一體化,以面對族群政治的挑戰。在新時代中,「悲情」成為華人社會論述的主旋律。
在此背景下,這時期的南洋研究不免也會呈現出一種悲情性格,這種悲情並不見得只是表現在賣豬仔的慘痛經過,同時也會呈現出一種華人貢獻的歷史論述,內容類似傳統中國史的治、亂、興、衰一樣,有著固定方程式:即「從華人賣豬仔南來,最後在自己的努力、克勤克儉等中華傳統美德的作用下,終於成功排除萬難在本地開拓一番事業,即使國家再如何打壓,也不畏懼,國家有今天的發展,也不應該忘記華人的貢獻」。
類似的故事情節在許多民間論述中不斷出現。然而藉由史料的考證,真正的歷史事實是殘酷的,因為真正的豬仔大多在開發時期就已經死亡,並未留下後代,華人底層勞工所面對的剝削者,也不見得是殖民者,更多的是來自華人的上層階級。目前許多的華人,其祖先多是二十世紀初南來的自由移民,而那些在本地超過四代或五代的,其祖先大多是當時的佼佼者,並非底層人士。當然,這樣的歷史論述有其時代背景,那麼,南洋史是否就只能停留在「有貢獻的華人」以及「悲情」之上?若不是的話,未來的南洋史應該如何書寫呢?
我們要怎樣的南洋史?
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同樣回顧當前的大環境,以馬來西亞而言,目前許多的第三、第四代華人對於祖籍國是陌生的,許多年輕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籍貫,也無法掌握華人方言,加之現今華人政治處境已不如二十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那樣的嚴峻,華人議題逐漸不是爭議性話題。此外,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大家更關注的是如何繼續保有在地的特色及身份認同。在此新的環境前提底下,告別華人研究,告別悲情,回到二十世紀中葉南洋學會一樣,重新將華人與其他族群放在一個平等客觀的平台之上,或許是南洋研究可以提供的貢獻。
那麼,接下來要看的是,為甚麼要告別「有貢獻的華人」和「悲情」?如何告別?華人與會黨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很長的時間裡頭,華人對於先輩存在秘密會社(天地會組織)、包娼包賭的過去,總是充滿著矛盾與尷尬,導致在論述這段歷史時,經常會用一種避重就輕,甚至花很多文字去加以修飾或掩飾他們所認為的「惡行」。若是站在價值二元對立的角度,只是關注好―壞、道德―不道德、仁―不仁等等,歷史研究便成為一種民族主義道德光環的保衛戰,為特定族群服務了。
也因為如此,馬來西亞的華人與馬來人才會陷入「華人是黑社會」的無謂罵戰之中。因此需要站在歷史現場的角度,跳脫二元的價值判斷,承認過去的客觀事實,不是去避而不談,才是應該具備的觀點態度。就像是回到中學歷史課堂中,老師告訴學生學歷史是為了以古鑒今的那份簡單又單純的初心。那麼,我們要如何轉移視線呢?
其實這個問題不難解答,且也已經有人解答。在二〇二〇年時,安煥然教授便集合從事新山研究的青年學者,編輯出版了一本名為《新史料.新視角:青年學者論新山》的論文集。這本書的創新之處誠如主編安煥然開宗明義所說的,在於新的史料和新的視角,如此一來才能夠形成不同的論述。
在史料的應用上,用一些過去南洋研究不常用的檔案及語言資料,像是用一些過去歐洲人、馬來人對華人同一件事情的書寫,往往會從他人視角中看到自己,例如當現今華人認為自己衛生條件較好,較為乾淨時,從政府記錄當中卻看到在歐洲人的書寫中,馬來人是較注重衛生的民族,而政府費了很多的努力在維護華人聚落的維生。當然,解讀這些史料需要費一番心力去尋找,並且解讀不同的文字,例如爪夷文、荷蘭文等等。在當今許多的史料公開、數位化、線上翻譯軟體日漸普及的條件之下,已為新史料的發掘和解讀,提供了新的契機。
在新的視角方面,回顧過去,奠定南洋史基本格局的書寫者多為中國南來文人,到了戰後,新的研究者也多承襲他們的治學方法來敘寫南洋史,成果卓著,必須肯定,但就歸納過去研究的角度而言,南洋史的方法論也呈現了十分單一的面貌。然而,隨著近年來新一代研究者背景的多元性逐漸增加,我們可以看到來自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地理學、經濟學、公共衛生等領域的研究者,使南洋史的書寫重新迎來多元發展的契機。
在新的視野下,舊有的史料可以有不同的解讀,像是在看到十九世紀的娼妓時,就不一定只有悲情的解讀,而是女性主義、產業發展、國家政策等的討論。此外,在議題式的研究主題下,南洋史的書寫就不至於服務於個別族群或是就地方而地方,在研究某個族群或主題時,也可以出現跨域的論述。這種打破政治界線,將區域視為是一個體系的視角來自歷史學者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和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分析概念,也就是在思考地方的時候,需要跳脫一種展示櫥窗那種一格一格,彼此毫無連結的「孤獨地方」,因為地方是相互影響的,如此一來,南洋研究才能避免陷入孤獨地方的限制。
黃賢強二〇〇八年在其《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便已經做出此一嘗試。跨域,顧名思義就是強調地理空間上跨域行為,特別是政治和文化上的疆界。對此,黃氏以中國及包含南洋在內的海外華人為對象,藉由跨區域的共同事件(如美國、澳洲、馬新地區華人的愛國運動),以及人物的跨域行為(如康有為、孫中山在各地的移動及意思傳播)來展現他的跨域史學。另一方面,黃賢強的跨域也帶有研究方法上的跨領域視野,從中可以看到地方史、性別史及歷史人類學的互動嘗試。此外,黃賢強二〇二三年撰寫的《伍連德新論:南洋知識分子與近現代中國醫衛》亦是其跨域史學之作。
類似的新史料和新視角並非南洋史所獨有,早在一九九〇年代,一些學者在參照了滿語、蒙語等少數民族史料之後, 便開始對清史有了不同的解讀,即從一個內亞區域史的角度來去反思由「漢化」和「朝貢體系」對於清朝歷史的理解。縱使新清史同時也引來不少中外學者間的論戰,但站在學術角度,能引起討論的議題總好過寫完出版之後就置諸高閣。因此期待在南洋史有新的視角進來之後,能跳脫單一族群,而有更多議題式的地方關懷,然後就特定主題展開南洋不同地區之間的比較。如此一來,南洋史才能跳脫獨立的國別,而重新有對話及整合的機會,回去對應到最初應該要有的「南洋」圖像。綜合上述對於南洋歷史書寫的期許,本書又能夠如何將新的史料和視角來理解馬來半島的華人社會呢?華人社會又有甚麼值得操作的點?
北馬區域視角下的拿律
東南亞近代大歷史當中的人與事,很大程度上始於歐洲在本區域的殖民經濟,馬來半島作為東南亞的一環,其殖民經濟的內容主要來自礦業以及種植業,這兩種經濟形態對馬來半島社會影響深遠,可說是決定後續區域及歷史發展的DNA。本書的內容主要聚焦於礦業經濟的馬來半島,從十九世紀拿律(Larut)的經驗出發,觀察華人拜別唐山之後的南洋重生記。
拿律(今天的太平一带)位在馬來半島北部的馬來王國―霹靂(Perak),自十九世紀中葉發現錫礦開始,它便由一個平凡的馬來封地一躍成為馬來半島北部最大,人口最多的錫礦產區,因而也成為霹靂王國最為富裕的封地。也因為錫礦這一利源,使得中國人蜂擁而至,希望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
在拿律這個馬來封地,華人的數量已經大到能夠自成體系,因此可以見到具有規模的錫礦場、勞工宿舍、商業市街、娛樂場所、廟宇、義山(墳山)等,可謂國中之國。這裡的華人也分為兩大義興和海山兩大集團,兩者都是具有天地會性質的商業拓墾組織。拿律兩大集團的存在建立於錫礦這一不可更新資源之上,資源的日益減少伴隨著人口增加,也對拿律的社會穩定埋下了定時炸彈,最終在一八六一年開始爆發大規模的衝突。
拿律的衝突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十餘年,在此過程中,除了械鬥帶來的生命財產損失,我們可以看到華人集團之間的跨地域動員,馬來統治者和英殖民者的回應,以及拿律對於檳城、新加坡等周邊地區的影響。到了一八七四年,在英殖民政府的積極干預下,衝突終於結束,拿律所在的霹靂王國也由完全自主的馬來王國變成英國的保護邦,成為英國殖民馬來半島的開端。
除了上述人事設定之外,拿律的空間架構也是值得我們留意的。拿律雖作為當時馬來半島的重要錫都,但它的價值卻取決於附近的檳城。當一八四八年拿律發現錫礦時,馬來封地主第一個前往的便是檳城,到當地去募集資金以及招攬開發的投資者。除了資金和人員之外,拿律生活所需的米糧、鴉片、酒等生活物資也都全由檳城供應,拿律所產出的錫礦也銷往檳城。對檳城這個國際貿易港市而言,拿律只是其眾多腹地之一,檳城可說是這個錫都的造王者。
拿律因為檳城而重要,並不意味著拿律就只是完全任由檳城影響的附屬,拿律的地位仍然舉足輕重,它的興衰對檳城的社會經濟也有直接的影響。當拿律礦業興盛,錫價高漲時,檳城也迎來美好的經濟榮景,當拿律因為華人衝突而生產停擺時,檳城的社會和經濟也會有所感,效果立竿見影。在一八六七年所發生的檳城大暴動便是最好的例子,那是拿律戰爭的延伸。另一方面,拿律的身份也是多重的,在奠定錫都地位之後,拿律也成為北馬腹地們的中心,夾帶著其所累積的資本及礦業知識,拿律礦家往周邊地區擴散,像是拿律南部近打河谷(Kinta Valley)的怡保(Ipoh)、務邊(Gopeng)、甲板(Papan)、拿乞(Lahat)、端洛(Tronoh)等地,這裡多少都能夠看到拿律的影子。像拿律這樣有著特定產業內容,即是核心也是邊區這樣多重地理身份的地方,在東南亞其實相當常見,拿律可說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綜合拿律的人、事和空間架構可以得知,拿律在馬來半島歷史中舉足輕重,而撐起這個壯闊大歷史的,則是底下微觀的小故事。本書分為「這才是華人的社會日常」、「異域重生:拿律演義」以及「拜別唐山的華人們」三大部分,每個部分由六個篇章所組成,這些文章主要修改自筆者在《當今大馬》的專欄。其中兩篇曾收錄於筆者二〇二二年由麥田出版的《赤道線的南洋密碼:臺灣@馬來半島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誌》,因敘述脈絡及內容完整性所需,故再次納入,經麥田同意重新收錄本書,特此申謝。
1. 這才是華人的社會日常
第一部分「這才是華人的社會日常」特別挑選了華人身份、會黨組織、飲食、娛樂等南洋華人研究常見的大議題為主軸,以期從日常生活的角度打破現有主流論述所存在的迷思。特別是當代馬新華人,無論是老百姓或是政治領袖,總是喜歡將「我們是苦力豬仔的後代」這樣的悲情論述掛在嘴邊,因為這個低微的身份能夠和華人後來的成功構成完美的對照,便可說好華人故事。然而回看過去人口的死亡率、性別比,再輔以周邊朋友的家族經驗之後,我們是不是豬仔苦力的後代,答案呼之欲出,因此本書以〈我們的故事:我們是苦力豬仔的後代嗎?〉為開端,叩問華人自我的身份。
在那個真正有華人賣豬仔南來,華人足以在馬來土地上構成國中之國的時代,天地會組織―會黨是華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或許是受到電視劇影響,現代人對於過去的會黨有一定的刻板印象,認為會黨成員都是忠肝義膽,義氣為先,但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他們真是如此嗎?以前的人憑甚麼跟現在的人不一樣?〈因為忠義所以賣命?被過度想像的會黨歷史〉便期望能彰顯出一直被過度想像的誤區。
看了會黨之後,我們回到當時的基層華人本身。一般認為,基層的苦力地位低微,並無甚麼影響力可言,因此在各種討論上,他們都不會是被聚焦的對象。然而,勞工因為人口基數大,使得他們合起來之後,便會被帶來顯著的影響。接下來這三篇〈拿律礦工一頓飯所連結出的地理關係〉、〈拿律礦工吞雲吐霧間所促成的邊區開發〉、〈疫情即生活:十九世紀的華人、礦工、腳氣病〉便是分別從拿律礦工的飲食、鴉片吸食,以及疾病這些日常的微觀行為來突顯他們的集體性對於區域地理環境及社會所帶來的影響。
本單元最後一篇文章〈十九世紀遊走於中國及馬來海域的雙國籍華人〉則轉而觀照處於上層階級的華人。十九世紀有能力在馬來半島開枝散葉的人,多半有著中國人和英籍民的雙重身份,他們比起一九五七年馬來亞獨立時期的華人更早面臨身份選擇的問題。從經驗上看來,當時的華人比較不像現今的主流論述,每個都熱愛祖國以及傳承中華文化,而是務實地因應不同情境來調整自己的身份。總體而言,第一單元主要是從一些人們熟悉的議題來反思華人社會裡頭常見的主流論述,先從宏觀的角度建立貼近歷史事實的史觀,接著再進入第二部分。
2. 異域重生:拿律演義
第二部分以「異域重生:拿律演義」為題,共有六篇文章所組成,這部分主要聚焦於拿律戰爭這個大歷史背景之下的小故事。這裡首先以〈還原消失的拿律舊礦區〉為開端,先對這個華人生活的礦區有基本的空間概念,從資源、生產方式,以及兩大陣營華人所處的位置來看地理環境如何為華人社會埋下衝突因子。長達十餘年的拿律戰爭是殘酷的,每一次的衝突都造成數以萬計的人命傷亡,對於這些衝突,人們所關注的往往都是男性,像是苦力、礦主以及那些居住在檳城的大資本家。然除了男性之外,女性也是拿律戰爭的重要角色。在那個非自由移民的時期,拿律的女性絕大部分以娼妓的身份出現在拿律,少部分則是當地上層人士的妻兒。女性雖然不參與戰爭,但她們卻是戰爭下的犧牲品,就像古代戰事一樣,戰勝的一方除了奪取戰敗方的財物之外,女性也是被奪取的對象。〈看得見的拿律女性:米字旗升起前夕的一場婦女營救行動 〉便是希望女性能夠被看見,看女性如何成為拿律戰爭的戰利品,而基於人道主義精神的英國人如何四處奔走營救女性。
除了女性應該被看見之外,華人研究一直都有另一個問題,也就是研究論述中,永遠都只有華人,似乎華人孤立存在於族群多元的異族世界之中。其實不然,〈威震南幫:拿律戰爭與本地錫克人的紮根〉便是講述第三次拿律戰爭陷入膠著,就連馬來統治者也無法控制局面時,檳城警官史必迪(Speedy)便接受拿來統治者的委託,辭職前往印度旁遮普去募集錫克傭兵,最終藉著他們的力量成功平定拿律戰爭。錫克人就此成為英政府管理殖民地的中堅力量,其軍警的形象至今仍深入民心,錫克人也就此在馬來半島落地生根,成為馬來西亞其中一大族群。拿律戰爭便是這一社會面貌的關鍵推手。
在拿律戰爭結束後,為了長久平息拿律各造的衝擊,英國與霹靂統治者們簽訂了《邦咯條約》,也標誌著霹靂乃至馬來半島其他邦國進入英殖民時期的開端。該條約對馬來西亞意義非凡,不僅考試會考,連國家檔案館也會在大廳展示條約照片。但實際上,國家歷史所不會提的是英國人和拿律華人因應日後經濟生產管理權責的《邦咯副約》。因此〈被遺忘的邦咯副約〉便是講述這個被遺忘的條約,同時也探討英國如何確保條約對華人的約束力。
《邦咯條約》簽訂之後,英國派駐參政司接管霹靂。同樣地,戰事平定之後,馬來統治者並不見得理所當然的會遵守合約精神,他們仍無法放棄其固有的徵稅權。〈怡保大鐘樓與拿督沙谷廣場的超時空咒怨〉便是講述英國參政司和馬來統治者之間的權力拉扯。這個衝突有趣的地方在於,故事並沒有在參政司遭到地方馬來領袖暗殺,英國出兵平定叛亂後終止。在此之後,雙方的角力繼續展現在以參政司伯治(Birch)為名的紀念鐘樓之上,歷經英殖民全盛時期、馬來亞獨立初期、種族主義高漲的後殖民時期,怡保大鐘樓都有不同的命運,從中可以看出當代馬來政府對於殖民歷史論述的態度。
繼霹靂之後,英殖民勢力陸續以同樣的方式接管了其他幾個同樣是產錫且動亂不堪的馬來邦國,像是雪蘭莪和森美蘭。進入英治時期之後,原有馬來邦國之間的界線被打破,無形中也加強了人員和資本的流動,馬來半島歷經另一波的區域化過程。〈陳秀連的跨域事蹟與拿律在歷史上的地理意義〉便是講述拿律海山礦家陳秀連在英治時期如何離開拿律前往中部的雪蘭莪開發,最終扎根雪蘭莪。至今,陳秀連已經是雪蘭莪和吉隆坡地區人們所熟知的名字,從輕鐵陳秀連站、陳秀連路,甚至是變奏的陳秀「蓮」蒸魚頭,陳秀連已經和雪隆地區緊密鑲嵌了,唯一被人們所遺忘的是,他是一位出自拿律的礦家。
3. 拜別唐山的華人們
第三部分「拜別唐山的華人們」顧名思義,談的就是人物。在拿律演義當中,人物關係並非表面上看到的義興―海山、廣府―客家這些簡化的二元概念。事實上,他們擁有不同的角色,像是礦工、財副、工頭、礦主、熔錫廠主、繳主(投資人)、餉碼商(稅收承包人)、糧食商、會黨領袖、馬來封地主、英國總督等等,他們構成了拿律複雜的人物關係網。幸運的是,這些人物並沒有完全隨著時間而消逝,反而是因為一些事件或過程以不同形式保留下來,像是義山的墓碑、廟宇的碑記、街道上的路牌,以及會館的肖像和機構裡頭的銅像等,使它們成為可以近距離接觸的歷史人物。
拿律開發雖早,但馬來王國時期的華人史跡卻少之又少,〈前殖民時期的拿律礦主:從嶺南廟塚的同治古墓談起〉便是旨在敘寫和考證碩果僅存的拿律礦主的墓碑,以期從微觀尺度了解這些礦主的家族資訊。在拿律,礦主們雖然都是以廣、客籍為主,這也是馬來半島乃至東南亞礦區普遍的現象。然而,若將錫礦放在上下游的生產鏈來看的話,便會浮現其他華人族群的圖像,福建商人便是隱藏在錫礦產銷鏈背後,最具影響力的群體。〈隱藏在拿律錫礦產業鏈中的檳城福建商人〉便是整理出影響拿律錫礦產業和社會的幾個檳城福建大家族,了解他們的角色以及影響,讓人物關係的拼圖更加具體。
〈鳳山寺碑記:石頭上的社會關係圖〉及〈檳城大伯公街福德祠裡的拿律大佬〉則是更進一步了解這些人物的社會網絡,從這些碑文中的名單當中,我們能夠見到的,更多是一些居住在外地(特別是檳城)的著名商人。他們在各種資料上都未呈現出與拿律的關係,但在碑文中,同一群人卻重複出現在檳城和拿律等地,完整呈現了核心和腹地之間密不可分的社會關係。當然,拿律的地域身份是雙重的,對檳城而言,它是邊區,是腹地,但對霹靂其他地方而言,拿律是重要的核心。
拿律歷經長年的發展,已經累積出深厚的資本和礦業知識,因此進入英治時期以後,許多拿律礦家夾帶著資本和技術,擴散至霹靂其他地方,成為地方開發的主力。當然,拿律錫礦也有被開挖殆盡的一天,到了一九三〇年代,霹靂首都的地位便拱手交接給近打河谷的另一個錫都―怡保。怡保是現今馬來西亞人熟知的礦區,拿律的地位早已為當代人所遺忘,〈怡保街路牌上的華人礦家溯源〉便是從日常生活可見的人名路牌著手,回顧這些人物的歷史,從中可以發現不少鑲嵌於怡保的華人礦家,都像雪隆的陳秀連一樣,具有拿律背景,足見拿律雖然因為礦產資源的下滑而逐漸淡出歷史舞台,但對周邊地區的影響仍是深遠的。
拿律的關係當然不僅限於檳城和怡保,透過人與人的連結,其所帶出的地―地關係可以無遠弗屆,充滿無限的可能,本書最後一章〈拿律海山大哥與港大中文學院主任〉便是講述馬來半島礦業邊區和香港之間的關係,從中可以見到增城籍的海山大哥鄭景貴與同鄉―朝廷太史賴際熙之間的往來。清朝覆亡之後,賴際熙來到香港,憑藉著先前在南洋所累積的網絡關係,最終開創了港大的中文學院,也建立了對馬新地區客家意識有深遠影響的崇正總會。
對現在的人而言,拿律或許毫不起眼,也無法和一些大國歷史相提並論,但它的故事絕對是同一時期整個南洋華人歷史的典型。南洋華人的歷史有著諸多面向,而華人大城市的經驗並不足以涵蓋它們,只有藉由不同的區域和族群視野,輔以不同的材料,才能構建出貼地的拿律經驗,同時破除被想象的歷史,進而跳出「有貢獻的華人」以及「悲情」的誤區。
延伸閱讀及參考資料
王賡武(1994),《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臺灣商務。
安煥然編(2020),《新史料∙新視角:青年學者論新山》,新山:南方大學出版社。
黃賢強(2008),《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黃賢強(2023),《伍連德新論:南洋知識分子與近現代中國醫衛》,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廖文輝(2017),《馬新史學80年︰從「南洋研究」到「華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三聯書店。
薛莉清(2015),《晚清明初南洋華人社群的文化建構:一種文化空間的發現》,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東南亞區域的名稱多元,提醒我們反思:「誰的歷史?誰寫的歷史?」的問題。白偉權教授,我們都暱稱他小白,十餘年來孜孜矻矻於田野,皓首窮經於文獻史料,從不間斷。經由田野調查及檔案、古地圖蒐集史料,採跨域的觀點,以拿律為核心的北馬舞台,書寫近二百年來的庶民歷史,並釐清華人在這塊土地歷史中扮演的角色。
本書由三個主題單元組成,首先「這才是華人社會日常」,以華人先輩在熱帶叢林中爭奪、採集不可更新資源為軸線,描述華人社會底層庶民,離鄉背井來此謀生時的勞動條件、飲食內容、地方疾病及社會網絡等,他們大多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價,成就的不只是今日華族生活家園的奠基者,也是北馬歷史的共同書寫者。第二部分「異域重生:拿律演義」,描繪來自不同原鄉的華人族群,在採集資源過程中,彼此之間,以及和在地邦國、和英國殖民勢力之間的互動,相當程度重建了十九世紀拿律地區人―地交互作用、人―人交互作用與地―地交互作用的歷史圖像。最後,「拜別唐山的華人們」單元,則以錫米產業鏈各級礦務主及商賈為主角,以錫礦開採、加工、物流等的操作為經,以操作過程刻畫的遺跡與地景為緯,書寫各階層華人先輩在實踐「日久他鄉變故鄉」過程裡,所付出的努力與代價。
本書的最大貢獻是,以宏觀的區域視角,回到小地域或地點的歷史現場。從荒野中的墓碑、廟宇裡的牌匾、對聯及碑記,以及行政、治安單位留下的檔案與古地圖等庶民史料,以簡潔精確的描述,訴說先輩篳路藍縷的過程。在各篇的敘述中,小白以苦力、頭家、會黨、地景、礦主及其產業鏈中的商賈為對象,解析他們在歷史現場所面對的環境挑戰與時代難題,在多面向的歷史發展中,講述這些發展如何引導他們在歷史長河中就地演出的位置。當然,這些挑戰、難題或歷史定位,未必成為科學性的知識問題,但卻是自身生命意義的創造與展現。我們現在享受他們奠基的家園之餘,不只要緬懷,更要關切他們櫛風沐雨的過程。
在博士論文完成後,小白不斷多方嘗試研究的切入角度,從未間斷過其學術旅程,本書是他彙集近年研究成果的第二本專著。研究過程中,小白深入各地義山拍攝墓碑資料、造訪各地廟宇記錄碑記牌匾、親臨大小圖書館蒐集各式檔案、探問在地耆老蒐羅口述資訊,經由這些過程克服華族先輩留下史料較為欠缺的困境。本書匯集的各篇專文,都是他一步一腳印的錐心之作。我肯定小白對學術的執著,對家鄉的熱情,更佩服他有取之不盡的動能。能夠先睹本書的內容,是我的光榮。
陳國川
序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推薦序 /黃賢強
首次與偉權相遇可追溯至二○二○年。當時,我應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陳國川教授之邀,擔任其門生葉韻翠博士論文答辯的口試委員之一。那時的偉權是一位出席旁聽答辯的碩士生。在閑談中,驚喜地發現我們同是馬來西亞新山寬柔中學的校友,盡管我比他早很多年畢業。更引起我關注的是,他正在研究的碩士論文課題是《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1855-1942)》,準備有系統地梳理和論析新山開埠後到二戰前近百年的文化地景發展和演變。偉權於二○一一年完成碩士論文並順利取得碩士學位後,繼續攻讀博士學位,並以馬來西亞的另外一個地域作為研究個案,深入探討國家與地方,產業與社會的錯綜複雜關係。
二○一六年,我再度有幸受到陳國川教授的邀請,成為偉權博士論文《國家、產業與地方社會的形構:馬來亞拿律地域華人社會的形成與變遷 (1848-1911)》的口試委員。這部博士論文有豐富史料,立論有據,學術視野廣闊。偉權的博士論文不僅順利通過了答辯,也成為研究拿律地區,甚至是研究整個馬來亞地區華人社會的重要學術著作。
如果說偉權的博士論文是一部嚴肅的學術著作,是與學界同行對話的作品,那麽,這本《拜別唐山:在馬來半島異域重生》則是面向普羅大眾的讀物,內容精煉,卻不失學術養分。換句話說,它具備學術內涵,卻以通俗易懂的文筆將故事講清楚說明白。
本書至少有三個值得關注的特點:首先,書中所收錄的文章並非一般無據可查的野史或耆老的回憶,而是有充分的史料支撐,有註明資料來源,並經過考證的史地故事。每篇文章末尾均列有「延伸閱讀」,提供相關參考文獻乃至原始資料,為有興趣深入探究的讀者提供了指引。其次,書中的一些故事或許看似熟悉,但並非老生常談,而是帶有新的觀點和論述。偉權喜歡與讀者一同探討問題,逐層揭示問題的真相。例如,他引領讀者思考東南亞華人是否都是苦力豬仔的後代?最後,全書各章適當地配置相關插圖,有些來自檔案,更多是作者在田野考察中拍攝的照片或繪制的地圖,圖文並茂,增加閲讀的樂趣。
總而言之,偉權博士之所以能夠將學術議題巧妙地以通俗易懂的文筆呈現,或者說將史地故事提升至具有學術內涵的短篇文章,得益於他長期的田野考察,並勤於查閱檔案文獻的雙重努力成果。近年來,馬來西亞湧現了各類地方史出版物,成果參差不齊。偉權的作品可作為範本,在傳播本土史地知識的同時,保持了立論有據的學術原則。高興看到偉權能夠遊走於學術殿堂與大眾教育之間,為馬來西亞華人知識體系的建構添上濃彩重墨的一筆,是為序。
推薦序/李永球
讀歷史,寫歷史,歷史能夠帶來什麼?有說歷史是一面鏡子,能夠鑑古知今,了解過去,知道當今,預知未來。既然是一面鏡鑑,又是怎樣的鏡鑑呢?那就眾說紛紜,各有不同的看法。總覺得那是一面照妖鏡,在歷史的鏡鑑下,妖魔無法遁形,正義永遠是真理。
「董狐之筆」此話是形容撰史依照事實,公正不偏。撰寫歷史須有此精神,依照資料,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切忌添油加醋,胡編瞎造,撰史者必須具備此種「歷史道德」,對得起天地良心。歷史是勝利或當權者撰寫的,我們華族的歷史就得靠我們自己來撰寫,由外族或外國人來撰寫,往往只寫到皮而寫不到骨頭裡的精髓。
照妖鏡之下,被抹黑消滅的歷史,展現鳳凰重生;被篡改捏造的歷史,顯出醜態百出;被排斥邊緣的歷史,終於重見天日;被詆毀誹謗的歷史,獲得伸張正義。
白偉權博士即將出版一本有關太平的史書,邀我為之寫序,受寵若驚之下,不敢怠慢,唯有遵命提筆。
細讀白博士的文章,發現研究成果比很多人都來得好,紮實穩重,大量引用文獻及田野資料,這方面我深感慚愧,亦感到望塵莫及。由於白博士致力於收集及閱讀文獻資料,在此方面勤下苦功,收穫的果實豐碩。因此不僅欽佩,更覺得應該虛心向他學習。
撰寫歷史文章,除了文獻資料,田野調查也是一項很重要的工作。由當地人收集資料並撰寫是最好的。若是外地人,就得長期居留一段時間,付出事倍功半的努力,才會有好的成績。
在田野資料方面,白博士是有缺陷,不僅不夠完整,也不夠深入,畢竟他不是太平本地人。他來過太平幾次,急匆匆收集資料就走,這方面就有欠缺了。但是,批評人家之際,或者說否定人家之後,本人也得自我檢討,切忌倚老賣老,以專家學者自居,目中無人。雖然我在田野調查方面做得好,不過在文獻方面就不夠完整也不夠全面了,畢竟我天生比較懶,文化水平也不夠,閱讀資料就困難重重。
我非常堅持由本地人撰寫本地史。雖說外來的師傅會唸經,這得住上多年熟悉當地後,才會有滾瓜爛熟之效,否則就出現荒腔走板的窘況。如果白博士做的是他本身家鄉的歷史,那就得心應手,事半功倍矣!
地方史最適合當地人來做,蓋因外地人對地方不是很熟悉,對當地語言、環境、地理、人文、歷史更是生疏,做起來就障礙重重,無法深入。閱讀過他的一些文章,發現就有這些缺點,講了這麼多,不舉個例子彷彿在貶低人家,抬高家己。曾經拜讀過他的文章,記得他寫太平的「福建義山」,這是不正確的名稱,真正是「福建公塚」。不過瑕不掩瑜,其文章依然擲地有聲,值得讚揚並推薦。畢竟多一個人來撰寫,好過少一個人寫,還是贊成並感謝他對於太平歷史的撰寫並交出極佳的果實。
而一些文獻派的學者,則不注重田野調查資料,完全抄自書籍及文獻,如此一來,書中有誤則跟著誤矣。或許有人認為書籍文獻或官方檔案、報章資料不會錯,其實還是有一些錯誤或不實的,所謂外行人看熱鬧,內行人看門道,照妖鏡之下,如何遁形呢?
導論:東南亞之前的南洋世界
東南亞是現今人們熟知的地理名詞,然而對很多老一輩的人而言,這是一個新的詞彙。在二戰之前的歷史長河中,這塊區域有很多的名字,歐洲人稱之為東印度(East Indies),中國人則稱之為 「南洋」,當地南島民族則稱之為Nusantara。除了Nusantara之外,無論是南洋,還是東印度,這些名字都是站在他者的角度命名,充滿了他者的想像以及主導意識。這種現象並非憑空產生,多少也貼地的反映了某種歷史現實。
對過去的世界而言,這裡物產豐富,有著世界市場所需的商品,因此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在爭相佔地的同時,這裡地廣人稀,無法支援生產過程中所需的勞力,在此情況下,這片區域成為周邊的人口大國人們移出的目的地。中國人便是這個過程當中的最大參與者,也開啟了海外華僑、海外華人在南洋的序章。
事實上,無論是回到歷史現場,或是放在今天的情境,離開自己熟悉的地方,前往一個文化、政治等客觀環境上不屬於自己的地方,絕對不是必然的,而是經歷過無限選擇與掙扎,以及各種推力、拉力的結果。若是以清朝中末葉這個華人大舉出洋的時代來檢視當時中國的話,中國無疑是個相當深的窪地。地方治安不靖、械鬥、人口暴漲、天災、西方國家的入侵、割地賠款、官府壓迫等問題層出不窮,這種從下而上的困境形成一股極強的推力,將人們推向出洋之途。
南洋是中國人出洋的最大目的地,這裡是由多個大小邦國所組成,在殖民經濟的作用下,這裡是一片處處充滿通商機會的大型貿易場,為冒險者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南洋在族群構成上以南島民族為主體,其他也包含旅居於此的西方殖民者、傳教士,以及來自阿拉伯、印度、歐美等地的商人和移民,可謂族群雜處,眾聲喧嘩。這樣的異域是中國正統觀念下的「蠻夷之邦」,按照正常邏輯,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這邊不會有中國元素,但隨著週邊各個國家的移民相繼前來定居之後,這片土地開始變得精彩,精彩的地方在於有許多無法預測的創新元素。
中國人進入南洋的多元世界可謂是一種新的嘗試,因為原鄉中國是一個無論在語言或是文化上都相當單一的社會。南洋的環境則如同一個縮小版的世界,一個福建人隔壁可以是廣府人,像是在檳城的椰腳街(Jalan Masjid Kapitan Keling ),同一條街上不到四百公尺的距離內就可以出現華人的觀音廟、印度人的象頭神神龕、印裔穆斯林的甲必丹吉靈回教堂,以及英國人的聖公會教堂。中國人在這片多元世界定居後,也開始吸納其他文化而成為有別於原鄉華人的「南洋華人」。其中最顯著的例子就是存在於新加坡、檳城、馬六甲這些貿易港市的峇峇社群。一般南洋華人即使不像峇峇社群擁有這麼多的「番夷」元素,在日常生活中,無論是語言或是飲食習慣上,或多或少也會受到「番夷」的影響。
在社會上,除了與原鄉所不同的多元之外,這裡也收納了許多原鄉所謂的「暴徒」。中國長期以來充滿了民變、海盜、土匪劫鄉事件,例如在大明實施海禁政策後流亡海外的走私客和海盜,以及在明末清初,那些不服從清朝統治而轉往海外以發展「國際戰線」的叛亂分子。在此後的整個清代當中,不時也有人高舉反清的旗幟來抵抗清政權,在生存空間日益限縮的情況下,每個時間點都有人轉往海外,懸居南洋,南洋由此成為天地會「暴徒」的大本營。
據殖民官員的報告,十九世紀中葉這裡的華人有超過百分之六十有會黨身份,會黨儼然成為華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這些天地會組織在南洋諸土著王國是合法團體,早期的南洋開發基本都離不開天地會的勢力,而居中團結他們的精神標語更是「反清復明」,南洋儼然成為反清勢力的人才庫。無論是一八五〇年的廈門小刀會起事還是清末的革命運動,都能見到南洋華人的身影。當時的清帝國流傳著這麼一段話,指說「臺地之難,難於孤懸海外,非內地輔車相依可比。諺云: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豈真氣數使然耶?」,此句描繪了臺灣山高皇帝遠的社會現狀。我們只能說,幸好南洋不在中華帝國的版圖之中,若是這樣的話,充滿「亂黨」的南洋必然更勝臺灣,成為皇帝黑名單中的第一名。
從多元的文化、會黨林立的角度看來,南洋與原鄉確實有著一百八十度的不同,這樣的差異也構成南洋特殊的主體性,成為形塑南洋華人認同的要素。上述所列舉的南洋特色,其實在東南亞各地的發展軸線幾乎一致。無論是在馬來亞、印尼、越南、緬甸、暹羅、菲律賓等等,華人的在地發展軸線或是所面對的挑戰幾乎是一致的,不外乎是華人沒有國家(中國)在背後保護,他們對於國家也抱持矛盾的態度,既希望有國家,但是又卻步於自己的國家。而東南亞華人也共同經歷殖民統治轉變為獨立國家後的挑戰。在這種歷史共性的作用下,「南洋」已成為東南亞華人的集體認同。那麼,在這個垂直歷史上多變,橫向軸線也很多元的南洋,華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南洋論述的建構及悲情轉向
南洋如何被人所理解,離不開文本的建構,早在清代之前,基本上就已經開始出現文人對南洋的書寫,這也是「南洋」論述建構的一種過程。明、清時期的南洋書寫多數是以遊記的方式出現,像是馬歡的《瀛涯勝覽》(一四五一),陳倫炯的《海國見聞錄》(一七三〇),謝清高的《海錄》(一八二〇),力鈞的《檳榔嶼志略》,李鍾鈺的《新嘉坡風土記》(一八八七),王錫祺的《小方壺齋輿地叢抄》(一八九一)等等。這時候的南洋書寫者大多並非移民或是寓居者(sojourn),而是以一個天朝文人、旅行者的身份來書寫南洋番邦,對他們而言,印象深刻會被記錄的事物無疑是當地居民的服飾、風俗民情、土王、物產等等,充滿了薩伊德(Edward Waefie Said)那種東方主義的調調。
隨著南洋地區歷經多年的城鎮化,加上晚清至民國初年的紛亂,開始有越來越多的移民定居南洋。這時也開始出現一些前來避難的中國南來文人,他們也成為接下來南洋意象的建構者。較知名的有張禮千、姚楠以及許雲樵對馬來亞各地和東南亞的書寫。他們是活躍於二十世紀初至戰後初期的民國文人,被稱為南洋研究三傑。他們在中國戰亂時期以僑民身份寓居南洋,因此在這裡並沒有國籍,但長久的居住也已經令他們對這片土地有所認同,他們的出現也正是南洋研究的濫觴。
他們的書寫有幾個特色,主要是把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視為是華南閩粵社會的延伸,在這個社會中,方言群、幫群林立,華人以會館、廟宇、行業組織等的機構集結。這或許是因為廣大閩粵地區的人們聚集在這小小的聚落中所呈現出的特殊景觀,因此成為不得不提的元素。有趣的是,他們的視野並不侷限於華人社區,更關注區域歷史的發展,馬來半島、暹羅、緬甸等南洋地區都是其關注的重點。此外,他們常針對一些南洋文化進行考釋,亦大量翻譯其他語言的研究成果,充分體現其為這片土地建立論述的企圖心。
在他們之前,南洋研究其實主要是由學院派殖民學者所主導,他們產量豐富,早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便已有自己的發表平台,像是一八四七年發刊的《印度群島與東亞學報》(Journal of the Indian Archipelago and Eastern Asia)、一八七八至一九二二年發刊的《皇家亞洲學會海峽分會學報》(Journal of the Straits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SBRAS),以及一九二三年接續至一九四一年的《皇家亞洲學會馬來亞分會學報》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JMBRAS) ,激發了他們對南洋知識的追求,於是集結了其他志趣相投的學人,才有了一九四〇年中國南洋學會和《南洋學報》的出現。自南洋研究的學群成型之後,後來的學者也開始繼續投入,已經形成一套南洋華人的研究體系。
戰後,大部分的華人開始面對人生的重大抉擇,究竟要放棄中國國籍,入籍僑居地?還是放棄在僑居地辛苦打拼的成果,舉家遷回動蕩的內地?在長久以來國家與民族身份重疊的情況下,選擇脫離中國籍當一名外國人,這是一個相當困難的抉擇,也是他們無法想象事,畢竟「加入番邦者,還能算是唐人嗎?」。
但從後來的歷史結果看來,成為新的華人是絕大部分人的選擇。在這些新興國家生活的華人,入籍之後並不代表王子和公主從此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真正的挑戰才正要開始。華人在東南亞這些土著所掌權的新興國家當中面臨了許多的挑戰,這些挑戰也影響了華人內部既有的幫群認同,使華人轉向一體化,以面對族群政治的挑戰。在新時代中,「悲情」成為華人社會論述的主旋律。
在此背景下,這時期的南洋研究不免也會呈現出一種悲情性格,這種悲情並不見得只是表現在賣豬仔的慘痛經過,同時也會呈現出一種華人貢獻的歷史論述,內容類似傳統中國史的治、亂、興、衰一樣,有著固定方程式:即「從華人賣豬仔南來,最後在自己的努力、克勤克儉等中華傳統美德的作用下,終於成功排除萬難在本地開拓一番事業,即使國家再如何打壓,也不畏懼,國家有今天的發展,也不應該忘記華人的貢獻」。
類似的故事情節在許多民間論述中不斷出現。然而藉由史料的考證,真正的歷史事實是殘酷的,因為真正的豬仔大多在開發時期就已經死亡,並未留下後代,華人底層勞工所面對的剝削者,也不見得是殖民者,更多的是來自華人的上層階級。目前許多的華人,其祖先多是二十世紀初南來的自由移民,而那些在本地超過四代或五代的,其祖先大多是當時的佼佼者,並非底層人士。當然,這樣的歷史論述有其時代背景,那麼,南洋史是否就只能停留在「有貢獻的華人」以及「悲情」之上?若不是的話,未來的南洋史應該如何書寫呢?
我們要怎樣的南洋史?
在解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同樣回顧當前的大環境,以馬來西亞而言,目前許多的第三、第四代華人對於祖籍國是陌生的,許多年輕人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籍貫,也無法掌握華人方言,加之現今華人政治處境已不如二十世紀七十至八十年代那樣的嚴峻,華人議題逐漸不是爭議性話題。此外,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大家更關注的是如何繼續保有在地的特色及身份認同。在此新的環境前提底下,告別華人研究,告別悲情,回到二十世紀中葉南洋學會一樣,重新將華人與其他族群放在一個平等客觀的平台之上,或許是南洋研究可以提供的貢獻。
那麼,接下來要看的是,為甚麼要告別「有貢獻的華人」和「悲情」?如何告別?華人與會黨是一個很好的案例,很長的時間裡頭,華人對於先輩存在秘密會社(天地會組織)、包娼包賭的過去,總是充滿著矛盾與尷尬,導致在論述這段歷史時,經常會用一種避重就輕,甚至花很多文字去加以修飾或掩飾他們所認為的「惡行」。若是站在價值二元對立的角度,只是關注好―壞、道德―不道德、仁―不仁等等,歷史研究便成為一種民族主義道德光環的保衛戰,為特定族群服務了。
也因為如此,馬來西亞的華人與馬來人才會陷入「華人是黑社會」的無謂罵戰之中。因此需要站在歷史現場的角度,跳脫二元的價值判斷,承認過去的客觀事實,不是去避而不談,才是應該具備的觀點態度。就像是回到中學歷史課堂中,老師告訴學生學歷史是為了以古鑒今的那份簡單又單純的初心。那麼,我們要如何轉移視線呢?
其實這個問題不難解答,且也已經有人解答。在二〇二〇年時,安煥然教授便集合從事新山研究的青年學者,編輯出版了一本名為《新史料.新視角:青年學者論新山》的論文集。這本書的創新之處誠如主編安煥然開宗明義所說的,在於新的史料和新的視角,如此一來才能夠形成不同的論述。
在史料的應用上,用一些過去南洋研究不常用的檔案及語言資料,像是用一些過去歐洲人、馬來人對華人同一件事情的書寫,往往會從他人視角中看到自己,例如當現今華人認為自己衛生條件較好,較為乾淨時,從政府記錄當中卻看到在歐洲人的書寫中,馬來人是較注重衛生的民族,而政府費了很多的努力在維護華人聚落的維生。當然,解讀這些史料需要費一番心力去尋找,並且解讀不同的文字,例如爪夷文、荷蘭文等等。在當今許多的史料公開、數位化、線上翻譯軟體日漸普及的條件之下,已為新史料的發掘和解讀,提供了新的契機。
在新的視角方面,回顧過去,奠定南洋史基本格局的書寫者多為中國南來文人,到了戰後,新的研究者也多承襲他們的治學方法來敘寫南洋史,成果卓著,必須肯定,但就歸納過去研究的角度而言,南洋史的方法論也呈現了十分單一的面貌。然而,隨著近年來新一代研究者背景的多元性逐漸增加,我們可以看到來自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地理學、經濟學、公共衛生等領域的研究者,使南洋史的書寫重新迎來多元發展的契機。
在新的視野下,舊有的史料可以有不同的解讀,像是在看到十九世紀的娼妓時,就不一定只有悲情的解讀,而是女性主義、產業發展、國家政策等的討論。此外,在議題式的研究主題下,南洋史的書寫就不至於服務於個別族群或是就地方而地方,在研究某個族群或主題時,也可以出現跨域的論述。這種打破政治界線,將區域視為是一個體系的視角來自歷史學者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和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分析概念,也就是在思考地方的時候,需要跳脫一種展示櫥窗那種一格一格,彼此毫無連結的「孤獨地方」,因為地方是相互影響的,如此一來,南洋研究才能避免陷入孤獨地方的限制。
黃賢強二〇〇八年在其《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便已經做出此一嘗試。跨域,顧名思義就是強調地理空間上跨域行為,特別是政治和文化上的疆界。對此,黃氏以中國及包含南洋在內的海外華人為對象,藉由跨區域的共同事件(如美國、澳洲、馬新地區華人的愛國運動),以及人物的跨域行為(如康有為、孫中山在各地的移動及意思傳播)來展現他的跨域史學。另一方面,黃賢強的跨域也帶有研究方法上的跨領域視野,從中可以看到地方史、性別史及歷史人類學的互動嘗試。此外,黃賢強二〇二三年撰寫的《伍連德新論:南洋知識分子與近現代中國醫衛》亦是其跨域史學之作。
類似的新史料和新視角並非南洋史所獨有,早在一九九〇年代,一些學者在參照了滿語、蒙語等少數民族史料之後, 便開始對清史有了不同的解讀,即從一個內亞區域史的角度來去反思由「漢化」和「朝貢體系」對於清朝歷史的理解。縱使新清史同時也引來不少中外學者間的論戰,但站在學術角度,能引起討論的議題總好過寫完出版之後就置諸高閣。因此期待在南洋史有新的視角進來之後,能跳脫單一族群,而有更多議題式的地方關懷,然後就特定主題展開南洋不同地區之間的比較。如此一來,南洋史才能跳脫獨立的國別,而重新有對話及整合的機會,回去對應到最初應該要有的「南洋」圖像。綜合上述對於南洋歷史書寫的期許,本書又能夠如何將新的史料和視角來理解馬來半島的華人社會呢?華人社會又有甚麼值得操作的點?
北馬區域視角下的拿律
東南亞近代大歷史當中的人與事,很大程度上始於歐洲在本區域的殖民經濟,馬來半島作為東南亞的一環,其殖民經濟的內容主要來自礦業以及種植業,這兩種經濟形態對馬來半島社會影響深遠,可說是決定後續區域及歷史發展的DNA。本書的內容主要聚焦於礦業經濟的馬來半島,從十九世紀拿律(Larut)的經驗出發,觀察華人拜別唐山之後的南洋重生記。
拿律(今天的太平一带)位在馬來半島北部的馬來王國―霹靂(Perak),自十九世紀中葉發現錫礦開始,它便由一個平凡的馬來封地一躍成為馬來半島北部最大,人口最多的錫礦產區,因而也成為霹靂王國最為富裕的封地。也因為錫礦這一利源,使得中國人蜂擁而至,希望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
在拿律這個馬來封地,華人的數量已經大到能夠自成體系,因此可以見到具有規模的錫礦場、勞工宿舍、商業市街、娛樂場所、廟宇、義山(墳山)等,可謂國中之國。這裡的華人也分為兩大義興和海山兩大集團,兩者都是具有天地會性質的商業拓墾組織。拿律兩大集團的存在建立於錫礦這一不可更新資源之上,資源的日益減少伴隨著人口增加,也對拿律的社會穩定埋下了定時炸彈,最終在一八六一年開始爆發大規模的衝突。
拿律的衝突斷斷續續地持續了十餘年,在此過程中,除了械鬥帶來的生命財產損失,我們可以看到華人集團之間的跨地域動員,馬來統治者和英殖民者的回應,以及拿律對於檳城、新加坡等周邊地區的影響。到了一八七四年,在英殖民政府的積極干預下,衝突終於結束,拿律所在的霹靂王國也由完全自主的馬來王國變成英國的保護邦,成為英國殖民馬來半島的開端。
除了上述人事設定之外,拿律的空間架構也是值得我們留意的。拿律雖作為當時馬來半島的重要錫都,但它的價值卻取決於附近的檳城。當一八四八年拿律發現錫礦時,馬來封地主第一個前往的便是檳城,到當地去募集資金以及招攬開發的投資者。除了資金和人員之外,拿律生活所需的米糧、鴉片、酒等生活物資也都全由檳城供應,拿律所產出的錫礦也銷往檳城。對檳城這個國際貿易港市而言,拿律只是其眾多腹地之一,檳城可說是這個錫都的造王者。
拿律因為檳城而重要,並不意味著拿律就只是完全任由檳城影響的附屬,拿律的地位仍然舉足輕重,它的興衰對檳城的社會經濟也有直接的影響。當拿律礦業興盛,錫價高漲時,檳城也迎來美好的經濟榮景,當拿律因為華人衝突而生產停擺時,檳城的社會和經濟也會有所感,效果立竿見影。在一八六七年所發生的檳城大暴動便是最好的例子,那是拿律戰爭的延伸。另一方面,拿律的身份也是多重的,在奠定錫都地位之後,拿律也成為北馬腹地們的中心,夾帶著其所累積的資本及礦業知識,拿律礦家往周邊地區擴散,像是拿律南部近打河谷(Kinta Valley)的怡保(Ipoh)、務邊(Gopeng)、甲板(Papan)、拿乞(Lahat)、端洛(Tronoh)等地,這裡多少都能夠看到拿律的影子。像拿律這樣有著特定產業內容,即是核心也是邊區這樣多重地理身份的地方,在東南亞其實相當常見,拿律可說是一個典型的代表。
綜合拿律的人、事和空間架構可以得知,拿律在馬來半島歷史中舉足輕重,而撐起這個壯闊大歷史的,則是底下微觀的小故事。本書分為「這才是華人的社會日常」、「異域重生:拿律演義」以及「拜別唐山的華人們」三大部分,每個部分由六個篇章所組成,這些文章主要修改自筆者在《當今大馬》的專欄。其中兩篇曾收錄於筆者二〇二二年由麥田出版的《赤道線的南洋密碼:臺灣@馬來半島的跨域文化田野踏查誌》,因敘述脈絡及內容完整性所需,故再次納入,經麥田同意重新收錄本書,特此申謝。
1. 這才是華人的社會日常
第一部分「這才是華人的社會日常」特別挑選了華人身份、會黨組織、飲食、娛樂等南洋華人研究常見的大議題為主軸,以期從日常生活的角度打破現有主流論述所存在的迷思。特別是當代馬新華人,無論是老百姓或是政治領袖,總是喜歡將「我們是苦力豬仔的後代」這樣的悲情論述掛在嘴邊,因為這個低微的身份能夠和華人後來的成功構成完美的對照,便可說好華人故事。然而回看過去人口的死亡率、性別比,再輔以周邊朋友的家族經驗之後,我們是不是豬仔苦力的後代,答案呼之欲出,因此本書以〈我們的故事:我們是苦力豬仔的後代嗎?〉為開端,叩問華人自我的身份。
在那個真正有華人賣豬仔南來,華人足以在馬來土地上構成國中之國的時代,天地會組織―會黨是華人社會生活的一部分。或許是受到電視劇影響,現代人對於過去的會黨有一定的刻板印象,認為會黨成員都是忠肝義膽,義氣為先,但我們更應該思考的是,他們真是如此嗎?以前的人憑甚麼跟現在的人不一樣?〈因為忠義所以賣命?被過度想像的會黨歷史〉便期望能彰顯出一直被過度想像的誤區。
看了會黨之後,我們回到當時的基層華人本身。一般認為,基層的苦力地位低微,並無甚麼影響力可言,因此在各種討論上,他們都不會是被聚焦的對象。然而,勞工因為人口基數大,使得他們合起來之後,便會被帶來顯著的影響。接下來這三篇〈拿律礦工一頓飯所連結出的地理關係〉、〈拿律礦工吞雲吐霧間所促成的邊區開發〉、〈疫情即生活:十九世紀的華人、礦工、腳氣病〉便是分別從拿律礦工的飲食、鴉片吸食,以及疾病這些日常的微觀行為來突顯他們的集體性對於區域地理環境及社會所帶來的影響。
本單元最後一篇文章〈十九世紀遊走於中國及馬來海域的雙國籍華人〉則轉而觀照處於上層階級的華人。十九世紀有能力在馬來半島開枝散葉的人,多半有著中國人和英籍民的雙重身份,他們比起一九五七年馬來亞獨立時期的華人更早面臨身份選擇的問題。從經驗上看來,當時的華人比較不像現今的主流論述,每個都熱愛祖國以及傳承中華文化,而是務實地因應不同情境來調整自己的身份。總體而言,第一單元主要是從一些人們熟悉的議題來反思華人社會裡頭常見的主流論述,先從宏觀的角度建立貼近歷史事實的史觀,接著再進入第二部分。
2. 異域重生:拿律演義
第二部分以「異域重生:拿律演義」為題,共有六篇文章所組成,這部分主要聚焦於拿律戰爭這個大歷史背景之下的小故事。這裡首先以〈還原消失的拿律舊礦區〉為開端,先對這個華人生活的礦區有基本的空間概念,從資源、生產方式,以及兩大陣營華人所處的位置來看地理環境如何為華人社會埋下衝突因子。長達十餘年的拿律戰爭是殘酷的,每一次的衝突都造成數以萬計的人命傷亡,對於這些衝突,人們所關注的往往都是男性,像是苦力、礦主以及那些居住在檳城的大資本家。然除了男性之外,女性也是拿律戰爭的重要角色。在那個非自由移民的時期,拿律的女性絕大部分以娼妓的身份出現在拿律,少部分則是當地上層人士的妻兒。女性雖然不參與戰爭,但她們卻是戰爭下的犧牲品,就像古代戰事一樣,戰勝的一方除了奪取戰敗方的財物之外,女性也是被奪取的對象。〈看得見的拿律女性:米字旗升起前夕的一場婦女營救行動 〉便是希望女性能夠被看見,看女性如何成為拿律戰爭的戰利品,而基於人道主義精神的英國人如何四處奔走營救女性。
除了女性應該被看見之外,華人研究一直都有另一個問題,也就是研究論述中,永遠都只有華人,似乎華人孤立存在於族群多元的異族世界之中。其實不然,〈威震南幫:拿律戰爭與本地錫克人的紮根〉便是講述第三次拿律戰爭陷入膠著,就連馬來統治者也無法控制局面時,檳城警官史必迪(Speedy)便接受拿來統治者的委託,辭職前往印度旁遮普去募集錫克傭兵,最終藉著他們的力量成功平定拿律戰爭。錫克人就此成為英政府管理殖民地的中堅力量,其軍警的形象至今仍深入民心,錫克人也就此在馬來半島落地生根,成為馬來西亞其中一大族群。拿律戰爭便是這一社會面貌的關鍵推手。
在拿律戰爭結束後,為了長久平息拿律各造的衝擊,英國與霹靂統治者們簽訂了《邦咯條約》,也標誌著霹靂乃至馬來半島其他邦國進入英殖民時期的開端。該條約對馬來西亞意義非凡,不僅考試會考,連國家檔案館也會在大廳展示條約照片。但實際上,國家歷史所不會提的是英國人和拿律華人因應日後經濟生產管理權責的《邦咯副約》。因此〈被遺忘的邦咯副約〉便是講述這個被遺忘的條約,同時也探討英國如何確保條約對華人的約束力。
《邦咯條約》簽訂之後,英國派駐參政司接管霹靂。同樣地,戰事平定之後,馬來統治者並不見得理所當然的會遵守合約精神,他們仍無法放棄其固有的徵稅權。〈怡保大鐘樓與拿督沙谷廣場的超時空咒怨〉便是講述英國參政司和馬來統治者之間的權力拉扯。這個衝突有趣的地方在於,故事並沒有在參政司遭到地方馬來領袖暗殺,英國出兵平定叛亂後終止。在此之後,雙方的角力繼續展現在以參政司伯治(Birch)為名的紀念鐘樓之上,歷經英殖民全盛時期、馬來亞獨立初期、種族主義高漲的後殖民時期,怡保大鐘樓都有不同的命運,從中可以看出當代馬來政府對於殖民歷史論述的態度。
繼霹靂之後,英殖民勢力陸續以同樣的方式接管了其他幾個同樣是產錫且動亂不堪的馬來邦國,像是雪蘭莪和森美蘭。進入英治時期之後,原有馬來邦國之間的界線被打破,無形中也加強了人員和資本的流動,馬來半島歷經另一波的區域化過程。〈陳秀連的跨域事蹟與拿律在歷史上的地理意義〉便是講述拿律海山礦家陳秀連在英治時期如何離開拿律前往中部的雪蘭莪開發,最終扎根雪蘭莪。至今,陳秀連已經是雪蘭莪和吉隆坡地區人們所熟知的名字,從輕鐵陳秀連站、陳秀連路,甚至是變奏的陳秀「蓮」蒸魚頭,陳秀連已經和雪隆地區緊密鑲嵌了,唯一被人們所遺忘的是,他是一位出自拿律的礦家。
3. 拜別唐山的華人們
第三部分「拜別唐山的華人們」顧名思義,談的就是人物。在拿律演義當中,人物關係並非表面上看到的義興―海山、廣府―客家這些簡化的二元概念。事實上,他們擁有不同的角色,像是礦工、財副、工頭、礦主、熔錫廠主、繳主(投資人)、餉碼商(稅收承包人)、糧食商、會黨領袖、馬來封地主、英國總督等等,他們構成了拿律複雜的人物關係網。幸運的是,這些人物並沒有完全隨著時間而消逝,反而是因為一些事件或過程以不同形式保留下來,像是義山的墓碑、廟宇的碑記、街道上的路牌,以及會館的肖像和機構裡頭的銅像等,使它們成為可以近距離接觸的歷史人物。
拿律開發雖早,但馬來王國時期的華人史跡卻少之又少,〈前殖民時期的拿律礦主:從嶺南廟塚的同治古墓談起〉便是旨在敘寫和考證碩果僅存的拿律礦主的墓碑,以期從微觀尺度了解這些礦主的家族資訊。在拿律,礦主們雖然都是以廣、客籍為主,這也是馬來半島乃至東南亞礦區普遍的現象。然而,若將錫礦放在上下游的生產鏈來看的話,便會浮現其他華人族群的圖像,福建商人便是隱藏在錫礦產銷鏈背後,最具影響力的群體。〈隱藏在拿律錫礦產業鏈中的檳城福建商人〉便是整理出影響拿律錫礦產業和社會的幾個檳城福建大家族,了解他們的角色以及影響,讓人物關係的拼圖更加具體。
〈鳳山寺碑記:石頭上的社會關係圖〉及〈檳城大伯公街福德祠裡的拿律大佬〉則是更進一步了解這些人物的社會網絡,從這些碑文中的名單當中,我們能夠見到的,更多是一些居住在外地(特別是檳城)的著名商人。他們在各種資料上都未呈現出與拿律的關係,但在碑文中,同一群人卻重複出現在檳城和拿律等地,完整呈現了核心和腹地之間密不可分的社會關係。當然,拿律的地域身份是雙重的,對檳城而言,它是邊區,是腹地,但對霹靂其他地方而言,拿律是重要的核心。
拿律歷經長年的發展,已經累積出深厚的資本和礦業知識,因此進入英治時期以後,許多拿律礦家夾帶著資本和技術,擴散至霹靂其他地方,成為地方開發的主力。當然,拿律錫礦也有被開挖殆盡的一天,到了一九三〇年代,霹靂首都的地位便拱手交接給近打河谷的另一個錫都―怡保。怡保是現今馬來西亞人熟知的礦區,拿律的地位早已為當代人所遺忘,〈怡保街路牌上的華人礦家溯源〉便是從日常生活可見的人名路牌著手,回顧這些人物的歷史,從中可以發現不少鑲嵌於怡保的華人礦家,都像雪隆的陳秀連一樣,具有拿律背景,足見拿律雖然因為礦產資源的下滑而逐漸淡出歷史舞台,但對周邊地區的影響仍是深遠的。
拿律的關係當然不僅限於檳城和怡保,透過人與人的連結,其所帶出的地―地關係可以無遠弗屆,充滿無限的可能,本書最後一章〈拿律海山大哥與港大中文學院主任〉便是講述馬來半島礦業邊區和香港之間的關係,從中可以見到增城籍的海山大哥鄭景貴與同鄉―朝廷太史賴際熙之間的往來。清朝覆亡之後,賴際熙來到香港,憑藉著先前在南洋所累積的網絡關係,最終開創了港大的中文學院,也建立了對馬新地區客家意識有深遠影響的崇正總會。
對現在的人而言,拿律或許毫不起眼,也無法和一些大國歷史相提並論,但它的故事絕對是同一時期整個南洋華人歷史的典型。南洋華人的歷史有著諸多面向,而華人大城市的經驗並不足以涵蓋它們,只有藉由不同的區域和族群視野,輔以不同的材料,才能構建出貼地的拿律經驗,同時破除被想象的歷史,進而跳出「有貢獻的華人」以及「悲情」的誤區。
延伸閱讀及參考資料
王賡武(1994),《中國與海外華人》,臺北:臺灣商務。
安煥然編(2020),《新史料∙新視角:青年學者論新山》,新山:南方大學出版社。
黃賢強(2008),《跨域史學:近代中國與南洋華人研究的新視野》,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黃賢強(2023),《伍連德新論:南洋知識分子與近現代中國醫衛》,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廖文輝(2017),《馬新史學80年︰從「南洋研究」到「華人研究」(1930―2009)》,上海:三聯書店。
薛莉清(2015),《晚清明初南洋華人社群的文化建構:一種文化空間的發現》,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目次
目錄
「新南洋史」系列出版說明
推薦序/陳國川
推薦序/黃賢強
推薦序/李永球
導論:東南亞之前的南洋世界
第一部:這才是華人社會日常
(一) 我們的故事──我們是苦力豬仔的後代嗎
(二) 因為忠義所以賣命?被過度想像的會黨歷史
(三) 拿律礦工一頓飯所連結出的地理關係
(四) 拿律礦工吞雲吐霧間所促成的邊區開發
(五) 疫情即生活:十九世紀的華人、礦工、腳氣病
(六) 十九世紀遊走於中國及馬來海域的雙國籍華人
第二部:異域重生:拿律演義
(七) 尋找消失的拿律舊礦區
(八) 看得見的拿律女性:米字旗升起前夕的一場婦女營救行動
(九) 威震南邦:拿律戰爭與本地錫克人的紮根
(十) 被遺忘的邦咯副約
(十一) 怡保大鐘樓與拿督沙谷廣場的超時空咒怨
(十二) 陳秀連的跨域事蹟與拿律在歷史上的地理意義
第三部:拜別唐山的華人們
(十三) 前殖民時期的拿律礦主:從嶺南廟塚的同治古墓談起
(十四) 隱藏在拿律錫礦產業鏈中的檳城福建商人
(十五) 鳳山寺碑記:石頭上的社會關係圖
(十六) 檳城大伯公街福德祠裡的拿律大佬
(十七) 怡保街路牌上的華人礦家溯源
(十八) 拿律海山大哥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
「新南洋史」系列出版說明
推薦序/陳國川
推薦序/黃賢強
推薦序/李永球
導論:東南亞之前的南洋世界
第一部:這才是華人社會日常
(一) 我們的故事──我們是苦力豬仔的後代嗎
(二) 因為忠義所以賣命?被過度想像的會黨歷史
(三) 拿律礦工一頓飯所連結出的地理關係
(四) 拿律礦工吞雲吐霧間所促成的邊區開發
(五) 疫情即生活:十九世紀的華人、礦工、腳氣病
(六) 十九世紀遊走於中國及馬來海域的雙國籍華人
第二部:異域重生:拿律演義
(七) 尋找消失的拿律舊礦區
(八) 看得見的拿律女性:米字旗升起前夕的一場婦女營救行動
(九) 威震南邦:拿律戰爭與本地錫克人的紮根
(十) 被遺忘的邦咯副約
(十一) 怡保大鐘樓與拿督沙谷廣場的超時空咒怨
(十二) 陳秀連的跨域事蹟與拿律在歷史上的地理意義
第三部:拜別唐山的華人們
(十三) 前殖民時期的拿律礦主:從嶺南廟塚的同治古墓談起
(十四) 隱藏在拿律錫礦產業鏈中的檳城福建商人
(十五) 鳳山寺碑記:石頭上的社會關係圖
(十六) 檳城大伯公街福德祠裡的拿律大佬
(十七) 怡保街路牌上的華人礦家溯源
(十八) 拿律海山大哥與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