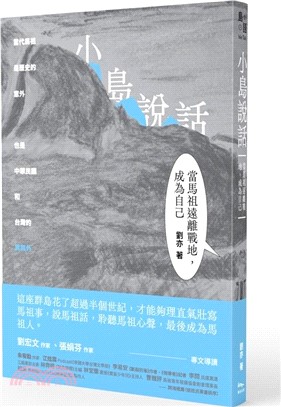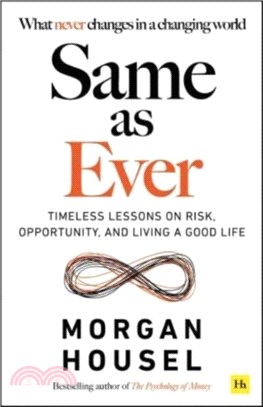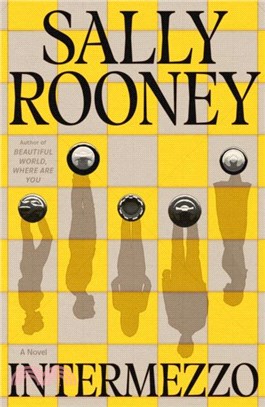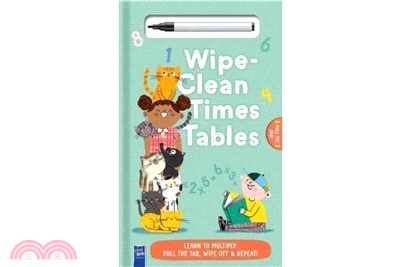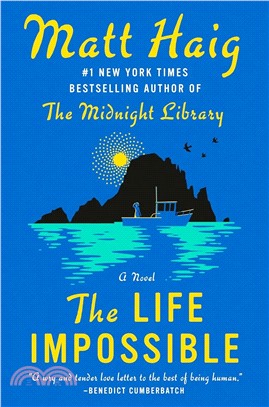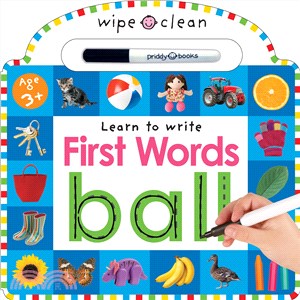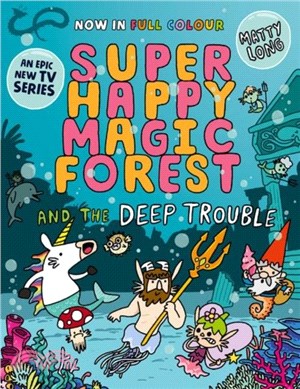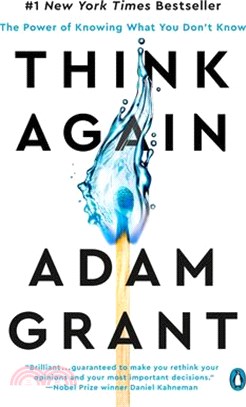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當代馬祖,是歷史的意外,也是中華民國和台灣的異與外。
★而這座群島花了超過半個世紀,才能夠理直氣壯寫馬祖事,說馬祖話,聆聽馬祖心聲,最後成為馬祖人。
★理解馬祖文學,就是理解馬祖人如何在歷史與地理夾縫中生存。
海洋封鎖、戰地管制、軍法審判⋯⋯馬祖上空曾籠罩漫長的永夜。戰後的「台灣群島」有一群寫作者,他們或者因冷戰而與馬祖交會,逡巡於東亞窄小的海域;或者降生於馬祖,受困於島的禁錮。他們的創作見證了馬祖如何在歷史上承受傷害,並在文學的深深水底等待天光。而這些「異」且「外」於中華民國/台灣的馬祖敘事與觀點,也為當代「新台灣人」的想像,提供更多元的可能。
一九四九年後,馬祖從原本的「化外之地」,正式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邊疆小島被迫成為戰地前線。本書爬梳一九四九後至當代的馬祖文學發展,並佐以馬祖相關的歷史、政治、地理、社會文化知識乃至時事評論,試圖闡述半世紀以來,馬祖是如何尋回自己的聲音,建構起與「中華民國台灣」若即若離、「合」而不同的主體。
從過去舒暢等老兵「等待戰爭」,渴望以一場戰爭解除「枕戈待旦」、僵固在冷戰的冷極的現狀;到如今面對棘手的「中華民國vs台灣」史觀與意識形態對決,以及身陷其中的馬祖之兩面不是人。當前的狀況似乎又回到某種「等待戰爭」的局面,「期盼」一場戰事來分娩出「新台灣(群島)人」,來打造出真正放下內部歧見的「新共同體」。
無論如何,這個新的共同體,都得先理解馬祖曾經擁有的深沉經歷,並且深刻認知到馬祖如何在歷史上承受傷害,而後才有機會逐步走向永夜後的破曉天光。就如同作家張娟芬在本書推薦序中寫到的:「在某一個臨界點,基於身心安頓之需,智慧也許會說:我知道我們個個不同,不過,我就把共同體的界線畫在這裡,我回家了。」
★而這座群島花了超過半個世紀,才能夠理直氣壯寫馬祖事,說馬祖話,聆聽馬祖心聲,最後成為馬祖人。
★理解馬祖文學,就是理解馬祖人如何在歷史與地理夾縫中生存。
海洋封鎖、戰地管制、軍法審判⋯⋯馬祖上空曾籠罩漫長的永夜。戰後的「台灣群島」有一群寫作者,他們或者因冷戰而與馬祖交會,逡巡於東亞窄小的海域;或者降生於馬祖,受困於島的禁錮。他們的創作見證了馬祖如何在歷史上承受傷害,並在文學的深深水底等待天光。而這些「異」且「外」於中華民國/台灣的馬祖敘事與觀點,也為當代「新台灣人」的想像,提供更多元的可能。
一九四九年後,馬祖從原本的「化外之地」,正式成為「中華民國」的一部分,邊疆小島被迫成為戰地前線。本書爬梳一九四九後至當代的馬祖文學發展,並佐以馬祖相關的歷史、政治、地理、社會文化知識乃至時事評論,試圖闡述半世紀以來,馬祖是如何尋回自己的聲音,建構起與「中華民國台灣」若即若離、「合」而不同的主體。
從過去舒暢等老兵「等待戰爭」,渴望以一場戰爭解除「枕戈待旦」、僵固在冷戰的冷極的現狀;到如今面對棘手的「中華民國vs台灣」史觀與意識形態對決,以及身陷其中的馬祖之兩面不是人。當前的狀況似乎又回到某種「等待戰爭」的局面,「期盼」一場戰事來分娩出「新台灣(群島)人」,來打造出真正放下內部歧見的「新共同體」。
無論如何,這個新的共同體,都得先理解馬祖曾經擁有的深沉經歷,並且深刻認知到馬祖如何在歷史上承受傷害,而後才有機會逐步走向永夜後的破曉天光。就如同作家張娟芬在本書推薦序中寫到的:「在某一個臨界點,基於身心安頓之需,智慧也許會說:我知道我們個個不同,不過,我就把共同體的界線畫在這裡,我回家了。」
作者簡介
劉亦
馬祖台灣混血,生於中壢。師大附中、台大社會系、台大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在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交換留學,沿鴨川散步一整年。曾獲馬祖文學獎、台大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評論見於鳴人堂、轉角國際、端傳媒等。
馬祖台灣混血,生於中壢。師大附中、台大社會系、台大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曾在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交換留學,沿鴨川散步一整年。曾獲馬祖文學獎、台大文學獎、林榮三文學獎等。評論見於鳴人堂、轉角國際、端傳媒等。
名人/編輯推薦
★專文導讀
劉宏文(作家)
張娟芬(作家、學者、社會運動者)
★好評推薦
朱宥勳(作家)
江炫霖(Podcast《帝國大學台灣文學部》)
李易安(《斷裂的海》作者、《報導者》記者)
李問(民進黨連江縣黨部主委)
林齊晧(《轉角國際》主編)
林宜蘭(廣播《寶島少年兄》主持人)
曹雅評(馬祖青年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
掐米(馬祖話YouTube《掐米亜店》製作人)
劉宏文(作家)
張娟芬(作家、學者、社會運動者)
★好評推薦
朱宥勳(作家)
江炫霖(Podcast《帝國大學台灣文學部》)
李易安(《斷裂的海》作者、《報導者》記者)
李問(民進黨連江縣黨部主委)
林齊晧(《轉角國際》主編)
林宜蘭(廣播《寶島少年兄》主持人)
曹雅評(馬祖青年發展協會創會理事長)
掐米(馬祖話YouTube《掐米亜店》製作人)
序
〈推薦序〉
◎寫給馬祖的情書
初識劉亦是在2016年,我那時正忙於撰寫《桃園市馬祖移民史》。臉書上偶然看到〈劉金姊姊的馬祖話教室〉紛絲專頁,劉亦跟妹妹繞著外婆學講馬祖話的短片,非常活潑有趣;特別是他們戲稱外婆為姊姊,這在馬祖家庭極為罕見。我立即被祖孫間的親密互動給吸引,承他引介,認識了劉金依姆。長居台灣近五十年,依姆的馬祖話夾帶許多華語、台語,我們共度了非常愉快的下午。
1970年代,馬祖仍在軍管戒嚴,駐軍人數約是島民三、四倍,大大改變傳統以農以漁的生息,但也因此開啟一面認識台灣的窗口。原來海峽另一邊賺錢這麼容易,大人小孩進工廠,省吃儉用,一年即可掙得一戶平房。於是,從1970年至1990年解嚴前夕,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島民,前呼後擁,橫渡台海,在大小工廠上班加班。從此不再搏命捕魚,不再覓水沃菜,徹底告別民防隊身分,再也不用在防空洞裡躲避懾人心魂的恐怖砲擊。
劉金依姆即是在這波移居潮中,領著那時還在讀國中的劉亦媽媽、舅舅、阿姨,投入他們原本稱為「兩個聲」的台灣社會,重新適應「不見大海」的生活。像多數適婚的馬祖女生一樣,近水樓台,她們與台灣男生戀愛、結婚,而有了如劉亦所說,他成了意外家庭之下的「意外受精卵」。
某次,我到龍岡跟依姆攀講,她正在蒸粽子,那種甜筒狀、僅有花生佐料的馬祖鹼粽。依姆說:「是給依命食的,伊愛食!」我聽錯了嗎?「依命」一般是馬祖人對幼兒的暱稱,像命一般疼愛;劉亦都已成年,在依姆心中仍是當年拿竹條追打的戇孫。
因為血脈之情的召喚,劉亦不斷回到小島,回到外婆與媽媽的出生地㇐白犬島田澳村,村裡只剩幾戶人家。他邀集友人在那裏辦夏日市集,海廢藝品、二手衣物,居然還有剪頭髮的攤位,島上的人都來關心,那可能是田澳村近年來擺暝以外最熱鬧的時光。我想,在沒有任何政府經費支援下,自發回到幾乎被人遺忘的小村,擺幾個注定無利可圖的小攤,在村人疑惑的眼中,他一心回望的,應該是外婆當年在這裡開撞球店、洗軍服的場景吧!
不僅如此,他甚至以一年時間留在馬祖擔任國小教師,教學以外,親手親腳探查這個他所謂「艱澀、深邃」的故鄉,以及被過多浪漫之霧遮蔽的島嶼。2019年5月,同婚專法上路後,有議員在質詢時詢問地方政府是否有「配套措施」,表示「馬祖是個純淨、純樸的地方,男男接吻、女女接吻,『比野狗還恐怖!』」因這番言論,他與幾位夥伴以「彩虹海風小郊遊」為名,連續三年手持彩虹旗,在南竿與北竿繞島,表達對多元性別的支持。如同他在本書所寫:「我曾經寫過乘著班機離開馬祖,回頭鳥瞰島嶼,它像胎兒倒懸在溫柔的羊水之中——如果我們像聽診器靠近島的胎動,會聽見馬祖怎樣的心內音?」他聽見的島嶼胎動,轉換成散文與詩,後來變成一篇一篇馬祖文學獎的得獎作品,以及疫情最熾期間,線上辦理「島嶼大學」的熱情。
甫離世的文壇大師王文興老師,祖籍福州,跟馬祖人講同樣語言。他寫的《家變》與《背海的人》已是現代文學的經典,雖然許多人不習慣書中的句法與詞彙,可馬祖人咀之嚼之,卻有「說到心坎裡」的感覺。在一篇談〈讀與寫〉的文章裏,王老師說:「慢讀而後,可知文體氣定神閑,從容不迫者為美,反是乃劣。」
我讀劉亦的文章,就有這種感覺。他的「氣定神閒」與「從容不迫」除了來自文字節奏、韻律,來自他優美的文體之外,主要還是他的知識與學養。他幾乎遍覽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當代所有與馬祖相關的資料與文獻,消化整理,而有了一己之見,娓娓道來,處處可見機鋒;以致這本改寫自學位論文、近九萬字的書寫,我讀來如平原走馬,一閃一閃亮晶晶(劉亦語),絲毫不覺學院文章的艱澀與阻滯。
劉亦出身台大社會系,或因如此,他總是從更廣泛的社會建構的角度,將作品置於外在環境的某個定點(書寫年代、冷戰氣氛、兩岸情勢、地緣關係、民主運動等),融合內在體驗(成長背景、島嶼觀察、遊學經歷等),大致依照台灣文學史的概念,從「軍中文學」、「懷鄉文學」、「地方文學」到「島嶼文學」,有條不紊的探討了幾位曾在馬祖服役、或與馬祖有某種淵源的作家,包括:1970年代的公孫嬿、張拓蕪,1990年代的舒暢、桑品載,以及2000年以後的何致和與龍應台的作品,最後聚攏到島嶼自己的聲音。他以精確而富有詩意的筆觸,抵抗一切宣言式的粉飾與簡化,一步一步為馬祖文學堆磚疊石,填補歷史的縫隙。
劉亦在文中曾寫道:「不諱言,本書試著努力朝向一門「馬祖學」,建構外婆背後的世界。論文的關鍵字也許需要格式工整,正襟危坐,但我心裡的關鍵字無疑是:回家……。然而回家豈有如此容易?這一路注定是一趟永恆的飛行:我和外婆的老樹濃蔭——雖然戰地馬祖很難有老樹濃蔭——那真正的「家」只能無限逼近,永遠不可能真正觸及。」
他在2018年「 馬祖文學獎」的得獎詩作〈遲來〉,寫他摯愛的外婆,最末一段:
有那一夜她降生在小小的白犬島
有包圍著島的海,包圍著海的雨
搖搖晃晃
密密麻麻
織成這封,注定失效的情書
是八十年後臺灣外孫遲遲趕到
用許多字想贖回妳的一生
我以為,《小島說話:當馬祖遠離戰地、成為自己》即是劉亦寫給外婆的情書;對馬祖而言,收信人不只是外婆,它沒有失效,也沒有遲來。
歡迎回家,劉亦。
(文:劉宏文/作家)
◎寫給馬祖的情書
初識劉亦是在2016年,我那時正忙於撰寫《桃園市馬祖移民史》。臉書上偶然看到〈劉金姊姊的馬祖話教室〉紛絲專頁,劉亦跟妹妹繞著外婆學講馬祖話的短片,非常活潑有趣;特別是他們戲稱外婆為姊姊,這在馬祖家庭極為罕見。我立即被祖孫間的親密互動給吸引,承他引介,認識了劉金依姆。長居台灣近五十年,依姆的馬祖話夾帶許多華語、台語,我們共度了非常愉快的下午。
1970年代,馬祖仍在軍管戒嚴,駐軍人數約是島民三、四倍,大大改變傳統以農以漁的生息,但也因此開啟一面認識台灣的窗口。原來海峽另一邊賺錢這麼容易,大人小孩進工廠,省吃儉用,一年即可掙得一戶平房。於是,從1970年至1990年解嚴前夕,大約有三分之二的島民,前呼後擁,橫渡台海,在大小工廠上班加班。從此不再搏命捕魚,不再覓水沃菜,徹底告別民防隊身分,再也不用在防空洞裡躲避懾人心魂的恐怖砲擊。
劉金依姆即是在這波移居潮中,領著那時還在讀國中的劉亦媽媽、舅舅、阿姨,投入他們原本稱為「兩個聲」的台灣社會,重新適應「不見大海」的生活。像多數適婚的馬祖女生一樣,近水樓台,她們與台灣男生戀愛、結婚,而有了如劉亦所說,他成了意外家庭之下的「意外受精卵」。
某次,我到龍岡跟依姆攀講,她正在蒸粽子,那種甜筒狀、僅有花生佐料的馬祖鹼粽。依姆說:「是給依命食的,伊愛食!」我聽錯了嗎?「依命」一般是馬祖人對幼兒的暱稱,像命一般疼愛;劉亦都已成年,在依姆心中仍是當年拿竹條追打的戇孫。
因為血脈之情的召喚,劉亦不斷回到小島,回到外婆與媽媽的出生地㇐白犬島田澳村,村裡只剩幾戶人家。他邀集友人在那裏辦夏日市集,海廢藝品、二手衣物,居然還有剪頭髮的攤位,島上的人都來關心,那可能是田澳村近年來擺暝以外最熱鬧的時光。我想,在沒有任何政府經費支援下,自發回到幾乎被人遺忘的小村,擺幾個注定無利可圖的小攤,在村人疑惑的眼中,他一心回望的,應該是外婆當年在這裡開撞球店、洗軍服的場景吧!
不僅如此,他甚至以一年時間留在馬祖擔任國小教師,教學以外,親手親腳探查這個他所謂「艱澀、深邃」的故鄉,以及被過多浪漫之霧遮蔽的島嶼。2019年5月,同婚專法上路後,有議員在質詢時詢問地方政府是否有「配套措施」,表示「馬祖是個純淨、純樸的地方,男男接吻、女女接吻,『比野狗還恐怖!』」因這番言論,他與幾位夥伴以「彩虹海風小郊遊」為名,連續三年手持彩虹旗,在南竿與北竿繞島,表達對多元性別的支持。如同他在本書所寫:「我曾經寫過乘著班機離開馬祖,回頭鳥瞰島嶼,它像胎兒倒懸在溫柔的羊水之中——如果我們像聽診器靠近島的胎動,會聽見馬祖怎樣的心內音?」他聽見的島嶼胎動,轉換成散文與詩,後來變成一篇一篇馬祖文學獎的得獎作品,以及疫情最熾期間,線上辦理「島嶼大學」的熱情。
甫離世的文壇大師王文興老師,祖籍福州,跟馬祖人講同樣語言。他寫的《家變》與《背海的人》已是現代文學的經典,雖然許多人不習慣書中的句法與詞彙,可馬祖人咀之嚼之,卻有「說到心坎裡」的感覺。在一篇談〈讀與寫〉的文章裏,王老師說:「慢讀而後,可知文體氣定神閑,從容不迫者為美,反是乃劣。」
我讀劉亦的文章,就有這種感覺。他的「氣定神閒」與「從容不迫」除了來自文字節奏、韻律,來自他優美的文體之外,主要還是他的知識與學養。他幾乎遍覽包括文學作品在內、當代所有與馬祖相關的資料與文獻,消化整理,而有了一己之見,娓娓道來,處處可見機鋒;以致這本改寫自學位論文、近九萬字的書寫,我讀來如平原走馬,一閃一閃亮晶晶(劉亦語),絲毫不覺學院文章的艱澀與阻滯。
劉亦出身台大社會系,或因如此,他總是從更廣泛的社會建構的角度,將作品置於外在環境的某個定點(書寫年代、冷戰氣氛、兩岸情勢、地緣關係、民主運動等),融合內在體驗(成長背景、島嶼觀察、遊學經歷等),大致依照台灣文學史的概念,從「軍中文學」、「懷鄉文學」、「地方文學」到「島嶼文學」,有條不紊的探討了幾位曾在馬祖服役、或與馬祖有某種淵源的作家,包括:1970年代的公孫嬿、張拓蕪,1990年代的舒暢、桑品載,以及2000年以後的何致和與龍應台的作品,最後聚攏到島嶼自己的聲音。他以精確而富有詩意的筆觸,抵抗一切宣言式的粉飾與簡化,一步一步為馬祖文學堆磚疊石,填補歷史的縫隙。
劉亦在文中曾寫道:「不諱言,本書試著努力朝向一門「馬祖學」,建構外婆背後的世界。論文的關鍵字也許需要格式工整,正襟危坐,但我心裡的關鍵字無疑是:回家……。然而回家豈有如此容易?這一路注定是一趟永恆的飛行:我和外婆的老樹濃蔭——雖然戰地馬祖很難有老樹濃蔭——那真正的「家」只能無限逼近,永遠不可能真正觸及。」
他在2018年「 馬祖文學獎」的得獎詩作〈遲來〉,寫他摯愛的外婆,最末一段:
有那一夜她降生在小小的白犬島
有包圍著島的海,包圍著海的雨
搖搖晃晃
密密麻麻
織成這封,注定失效的情書
是八十年後臺灣外孫遲遲趕到
用許多字想贖回妳的一生
我以為,《小島說話:當馬祖遠離戰地、成為自己》即是劉亦寫給外婆的情書;對馬祖而言,收信人不只是外婆,它沒有失效,也沒有遲來。
歡迎回家,劉亦。
(文:劉宏文/作家)
目次
【推薦序】
◎寫給馬祖的情書(文:劉宏文/作家)
◎劉亦舞劍(文:張娟芬/作家、學者、社會運動者)
【第一章】
開往家鄉的慢船
【第二章】
前線島嶼:「等待戰爭」的戰地
第一節 戰地政「霧」:公孫嬿的馬祖「新文藝」
一、國家要你扛筆當槍
二、指揮官難以洞視的島
第二節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舒暢的小兵書寫
一、限婚令與特約茶室
二、「國仇」與「家恨」
第三節 島際的時差:何致和的「外島書」
一、東引更在重洋外
二、「後冷戰」的「不願役」
【第三章】
中繼島嶼:流動的懷鄉文學
第一節 馬祖的卓别林:張拓蕪的大兵手記
一、從詩人沈甸到「代馬輸卒」張拓蕪
二、像「島群」一樣活著
第二節 陸地拋棄你,島嶼收容你:桑品載的回憶錄
一、從娃娃兵到總編輯
二、「嶼」生俱來的身世
第三節 民國代言人:龍應台的一九四九敘事
一、從批評家到述史者
二、「恕」史者?兩代「民國女子」
【第四章】
新生島嶼:後戰地馬祖
第一節 寫馬祖事:馬祖文學獎
一、「名家書寫」
二、藍色,是馬祖的眼淚
第二節 聽馬祖聲:「自由的」馬祖資訊網
一、馬祖人的首頁
二、天真又殘酷的戰地童年
第三節 說馬祖話:在地作家的閩東話書寫
一、尋聲:《鄉音馬祖》
二、失聲:白色恐怖和「國」語的反思
【第五章】
永恆的向家飛行
【謝辭】
◎寫給馬祖的情書(文:劉宏文/作家)
◎劉亦舞劍(文:張娟芬/作家、學者、社會運動者)
【第一章】
開往家鄉的慢船
【第二章】
前線島嶼:「等待戰爭」的戰地
第一節 戰地政「霧」:公孫嬿的馬祖「新文藝」
一、國家要你扛筆當槍
二、指揮官難以洞視的島
第二節 沒有女人的男人們:舒暢的小兵書寫
一、限婚令與特約茶室
二、「國仇」與「家恨」
第三節 島際的時差:何致和的「外島書」
一、東引更在重洋外
二、「後冷戰」的「不願役」
【第三章】
中繼島嶼:流動的懷鄉文學
第一節 馬祖的卓别林:張拓蕪的大兵手記
一、從詩人沈甸到「代馬輸卒」張拓蕪
二、像「島群」一樣活著
第二節 陸地拋棄你,島嶼收容你:桑品載的回憶錄
一、從娃娃兵到總編輯
二、「嶼」生俱來的身世
第三節 民國代言人:龍應台的一九四九敘事
一、從批評家到述史者
二、「恕」史者?兩代「民國女子」
【第四章】
新生島嶼:後戰地馬祖
第一節 寫馬祖事:馬祖文學獎
一、「名家書寫」
二、藍色,是馬祖的眼淚
第二節 聽馬祖聲:「自由的」馬祖資訊網
一、馬祖人的首頁
二、天真又殘酷的戰地童年
第三節 說馬祖話:在地作家的閩東話書寫
一、尋聲:《鄉音馬祖》
二、失聲:白色恐怖和「國」語的反思
【第五章】
永恆的向家飛行
【謝辭】
書摘/試閱
〈台灣,是群島的國度〉
一九九二年,金門、馬祖解嚴,揮別戰地政務時代,台灣文學界大佬葉石濤在金門作家黃克全的小說座談會上說:「金門不屬於臺灣的一部分。將來當臺灣人走向自決之路時,金門應該不包括在內。縱然,金門全體人民願意與臺灣站在一起,但是其地理位置太靠近大陸了,其未來命運將是如何?」葉石濤一語道破金門和金門文學的尷尬處境:就算金門人願意和台灣站在一起,但因它靠近大陸/中國,仍然難逃其地緣位置帶來的強大引力。「金門應該不包括在內」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台灣人對金馬的態度:不爭取亦不承認金門(與馬祖)是當下的共同體,以及未來以「台灣為主體的新國家」的一部分。
然而果真如此嗎?或者還能有其它想像?三十年後,台灣文學界終於回過頭來探問「離島問題」,二〇二一年台灣文學學會年度研討會以「台灣大文學史的建構與想像」為題,直言在討論台灣文學時多半集中台灣本島,我們是否能夠更宏觀的想像一部擴及金門、澎湖、馬祖乃至其他離島的「台灣大文學史」?學界開始出現「更新文學史」的呼聲 。
我將在這本書裡展示:隔著海峽,從過去素未謀面、到現在也因了解不深而難免猜忌的台灣和馬祖,其實在文學上的交織早已絡繹於途。馬祖的書寫過去不曾被系統性的指認出來,如今我們發現它早就坐落在台灣文學的星系之中。雖然它體積不大,引力卻不小,讓台灣文學裡的幾個重要概念:「軍中文學」、「懷鄉文學」與「地方文學」,都被牽引著稍稍偏離了本來的航道,發生了一點點斗轉星移。「一九四九」後大遷徙的寫作者們在東亞這一片小小的海域畫下複雜的軌跡,有的雄心壯志,有的萬般無奈。但連綴起來,就幾乎可以伸手去指:那是過去半世紀,台灣、馬祖、甚至中國的交相作用下,作家以生命歷程繪製出的群島圖。
如果不是一九四九,馬祖不會跟著中華民國的統治,匯入「中華民國台灣」,和中華民國政權、和台灣「本島」綁定。如果不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對峙,邊疆小島不會成為戰地前線,得到黨國銳意經營、大力挹注。所以對馬祖而言,它的現代化和國家化是同時開始的。雖然馬祖常和金門並稱,有近乎難兄難弟的命運,但它們真的天南地北,毫不相同。
金門說的是閩南語,和台灣腔調有別,但大致能通;馬祖說的是閩東語,台灣朋友說乍聽像客家話,但完全不互通。金門的開發史遠早於台灣,當然更早於馬祖,所以有悠久的宗族組織,金門人注重功名、科舉,出了一堆儒家知識份子;馬祖不是,馬祖相較沒有長期、穩固的歷史,和儒家核心的士大夫相較,馬祖更以海盜的歷史自豪。雖然經過黨國的恐海教育,現在馬祖血液析出的體脂肪可能比海水鹽分更高了。
前現代的馬祖被哈佛學者宋怡明(Michael Szonyi)稱為「沒有社會的社會」,因為它在歷史上一直是座隨季風遷徙的臨時漁場和貿易小島,少有定居住民。直到國軍登陸,開始封鎖海洋。因此宋怡明稱:「馬祖本身是脫胎自軍事化時期的產物。」或謂「軍事現代性」。討論日治時期台灣史時,「殖民現代性」是一個關鍵詞,它表達一種難以評斷的曖昧:雖然日本統治帶入了醫療衛生、現代教育、標準時間制等「現代」產物,應該給予正評,但實際上這些「現代」事物並不是為了台灣人生活舒適,而是方便殖民統治。因此「現代」的好和「殖民」的惡,是糾結在一起的。
馬祖也是如此。軍方的統治固然帶給馬祖教育、醫療、經濟等發展,但其初衷並非帶給馬祖福祉,而是便於實施軍事統治。然而中華民國統治馬祖並不算殖民,因此「軍事現代性」不只言簡意賅說明了馬祖有別於台灣的獨特性,也表達了馬祖對戰地時代統治者的難以評價。
鳥瞰台灣周邊島嶼,雖然各擁脈絡,但仍有共相可尋。例如不只綠島,蘭嶼也在戒嚴時期被當成重刑犯、政治犯的監獄,台灣的海洋「兩岸」——台灣海峽與太平洋,因各自的地緣位置,受到戰後中華民國分派了不同的國家任務。金門、馬祖靠近「匪區」而被指派為「前線」;太平洋側的綠島、蘭嶼則成為國家的「垃圾桶」,丟棄衍生物、副產品——從社會的副產品罪犯,到能源的副產品核廢料。邏輯一以貫之,形成一個環繞著中華民國/台灣本島的「犧牲的體系」,為了本島的安全和繁榮服務。巧合的是,日本學者高橋哲哉曾在《犧牲的體系》中指出,服務於戰後東京之繁榮的福島、沖繩,正好是被轉嫁了能源與國家安全責任之處,可見現代國家的責任轉嫁是有共相的:「地方」為中央服務,服務項目是能源與軍事的負擔。無獨有偶,身為島嶼,馬祖、金門也曾經是核廢料的貯存候選地。
金馬的複雜還不只如此。一般談到「戰後」,盤桓在「中華民國台灣」上空的戰爭時間有兩股。其一是台灣史觀的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台灣改受中華民國統治;其二是中華民國史觀的一九四九年,國共戰敗,政府遷台。然而金馬其實存有第三股「戰後」時間,即解除戰地政務的一九九二年。至此之前,法律上金馬是戰地,受各種禁制。實際上的砲戰也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才歇。論及台灣四大、乃至五大族群(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近年加上新住民),金馬人卡在各分類的中間,無處落座——金馬確實是「外省」(福建省),但和一九四九前後渡海來台那波外省人的脈絡大相逕庭。明明稱「台澎金馬」彷彿占了國土的二分之一,但其實是通天入地的「被缺席」。
對於馬祖而言,台灣和中華民國雖然未必全等,但兩者幾乎同步被馬祖認識——馬祖認識的「台灣」,已經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台灣。對馬祖人而言,無論中華民國和台灣都是外來或外在於馬祖的,兩者不一定有台灣人認知的這麼大不同。可能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台灣本島才被以新興的政治力量——「台獨」之名,被馬祖重新認識,使馬祖意識到台馬有別。更令人五味雜陳的是,這個「新台灣」往往是來「切割」馬祖的。正如馬祖尷尬的地緣位置,它既陷落在中國與台灣「兩岸」,又同時受到中華民國和台灣兩股史觀的沖激,置身多重的夾縫中。
我曾經有一個版本的論文計畫,是將琉球(沖繩)和馬祖並置。二戰時死傷慘重的沖繩戰,可以比擬台澎金馬唯一發生過登陸戰的金門古寧頭;而二戰後迅速進入冷戰,沖繩為日本本土扛起基地化的任務,也如同金馬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所承受的命運。不過礙於語言的次元之壁與沖繩學的汗牛充棟,我自認不足而放棄。不過沖繩經驗與省思仍值得對話,我甚至認為不具軍事化、基地化經驗,反而身為金馬軍事化之受益者的台灣,相較之下,是很難理解沖繩的。
進入現代以來,島嶼不可免俗被納編進以大陸國家為延長的政權之中,有學者語重心長:「現代國家權力粗暴地基於進步主義,將所有地方性的東西加以扼殺。」十九世紀的廢藩置縣、琉球處分之於沖繩如此,二十世紀的「一九四九」、戰地政務之於馬祖也莫不如此。
出身琉球西表島的作家崎山多美在一次來台演講就提到,對她而言沖繩(本島)和巴黎都像是異國。島嶼的成長經驗,讓她對「國家」的認知相當不同——「國界線」、「國籍」是有如殖民地的概念;對於日語則有「違和的身體感」。她認為也許正是在西表島生活、長大的身體,自然地抗拒「我是哪國人」,所以形成了傾軋、扞格的感受。在本書中,我們也能見到馬祖列島作為地方,面對現代國家強行刺入的張皇失措。
大江健三郎(一九三五-二〇二三)遊歷沖繩後,認為「日本屬於沖繩」(日本は沖縄に属する)。學者吳叡人在《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中對此的詮釋是:日本的自立建立在沖繩的犧牲之上。也就是說,沖繩為日本承擔苦難、付出代價,日本在道德上對沖繩有所虧欠(morally indebted)。從沖繩和日本的案例,除了能認識到「加害/被害」關係的重層性——以廣島核爆為代表,日本擁有「受害」經驗,但面對沖繩時,日本則是無庸置疑的加害者。延續著這樣的說法,台灣同樣可能屬於馬祖——不只在文化的互為涵融,更是政治道德的層次上。在大江健三郎的意義上。
日本小說家島尾敏雄(一九一七-一九八六)用拉丁語自創語彙「日本尼西亞」,也就是「日本-群島」。同一個構詞原則的「台灣群島」則是來自吳音寧在臉書粉絲專頁的說法:「我說的台灣島嶼,包括了澎湖、金門、馬祖、小琉球、綠島、蘭嶼等地。我們的台灣,是群島的國度。」「日本尼西亞」朝海洋與島群開放,「台灣群島」也擴張台灣,解除「本土」的狹隘性。所謂「本土」其實是多元,主體並立,秩序繽紛,就如同法律史學家王泰升所言:「台灣共同體內部是複雜的,只有看到複雜性,才能夠相互尊重。」
(本文摘自:第一章「開往家鄉的慢船」)
一九九二年,金門、馬祖解嚴,揮別戰地政務時代,台灣文學界大佬葉石濤在金門作家黃克全的小說座談會上說:「金門不屬於臺灣的一部分。將來當臺灣人走向自決之路時,金門應該不包括在內。縱然,金門全體人民願意與臺灣站在一起,但是其地理位置太靠近大陸了,其未來命運將是如何?」葉石濤一語道破金門和金門文學的尷尬處境:就算金門人願意和台灣站在一起,但因它靠近大陸/中國,仍然難逃其地緣位置帶來的強大引力。「金門應該不包括在內」一定程度上也代表台灣人對金馬的態度:不爭取亦不承認金門(與馬祖)是當下的共同體,以及未來以「台灣為主體的新國家」的一部分。
然而果真如此嗎?或者還能有其它想像?三十年後,台灣文學界終於回過頭來探問「離島問題」,二〇二一年台灣文學學會年度研討會以「台灣大文學史的建構與想像」為題,直言在討論台灣文學時多半集中台灣本島,我們是否能夠更宏觀的想像一部擴及金門、澎湖、馬祖乃至其他離島的「台灣大文學史」?學界開始出現「更新文學史」的呼聲 。
我將在這本書裡展示:隔著海峽,從過去素未謀面、到現在也因了解不深而難免猜忌的台灣和馬祖,其實在文學上的交織早已絡繹於途。馬祖的書寫過去不曾被系統性的指認出來,如今我們發現它早就坐落在台灣文學的星系之中。雖然它體積不大,引力卻不小,讓台灣文學裡的幾個重要概念:「軍中文學」、「懷鄉文學」與「地方文學」,都被牽引著稍稍偏離了本來的航道,發生了一點點斗轉星移。「一九四九」後大遷徙的寫作者們在東亞這一片小小的海域畫下複雜的軌跡,有的雄心壯志,有的萬般無奈。但連綴起來,就幾乎可以伸手去指:那是過去半世紀,台灣、馬祖、甚至中國的交相作用下,作家以生命歷程繪製出的群島圖。
如果不是一九四九,馬祖不會跟著中華民國的統治,匯入「中華民國台灣」,和中華民國政權、和台灣「本島」綁定。如果不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對峙,邊疆小島不會成為戰地前線,得到黨國銳意經營、大力挹注。所以對馬祖而言,它的現代化和國家化是同時開始的。雖然馬祖常和金門並稱,有近乎難兄難弟的命運,但它們真的天南地北,毫不相同。
金門說的是閩南語,和台灣腔調有別,但大致能通;馬祖說的是閩東語,台灣朋友說乍聽像客家話,但完全不互通。金門的開發史遠早於台灣,當然更早於馬祖,所以有悠久的宗族組織,金門人注重功名、科舉,出了一堆儒家知識份子;馬祖不是,馬祖相較沒有長期、穩固的歷史,和儒家核心的士大夫相較,馬祖更以海盜的歷史自豪。雖然經過黨國的恐海教育,現在馬祖血液析出的體脂肪可能比海水鹽分更高了。
前現代的馬祖被哈佛學者宋怡明(Michael Szonyi)稱為「沒有社會的社會」,因為它在歷史上一直是座隨季風遷徙的臨時漁場和貿易小島,少有定居住民。直到國軍登陸,開始封鎖海洋。因此宋怡明稱:「馬祖本身是脫胎自軍事化時期的產物。」或謂「軍事現代性」。討論日治時期台灣史時,「殖民現代性」是一個關鍵詞,它表達一種難以評斷的曖昧:雖然日本統治帶入了醫療衛生、現代教育、標準時間制等「現代」產物,應該給予正評,但實際上這些「現代」事物並不是為了台灣人生活舒適,而是方便殖民統治。因此「現代」的好和「殖民」的惡,是糾結在一起的。
馬祖也是如此。軍方的統治固然帶給馬祖教育、醫療、經濟等發展,但其初衷並非帶給馬祖福祉,而是便於實施軍事統治。然而中華民國統治馬祖並不算殖民,因此「軍事現代性」不只言簡意賅說明了馬祖有別於台灣的獨特性,也表達了馬祖對戰地時代統治者的難以評價。
鳥瞰台灣周邊島嶼,雖然各擁脈絡,但仍有共相可尋。例如不只綠島,蘭嶼也在戒嚴時期被當成重刑犯、政治犯的監獄,台灣的海洋「兩岸」——台灣海峽與太平洋,因各自的地緣位置,受到戰後中華民國分派了不同的國家任務。金門、馬祖靠近「匪區」而被指派為「前線」;太平洋側的綠島、蘭嶼則成為國家的「垃圾桶」,丟棄衍生物、副產品——從社會的副產品罪犯,到能源的副產品核廢料。邏輯一以貫之,形成一個環繞著中華民國/台灣本島的「犧牲的體系」,為了本島的安全和繁榮服務。巧合的是,日本學者高橋哲哉曾在《犧牲的體系》中指出,服務於戰後東京之繁榮的福島、沖繩,正好是被轉嫁了能源與國家安全責任之處,可見現代國家的責任轉嫁是有共相的:「地方」為中央服務,服務項目是能源與軍事的負擔。無獨有偶,身為島嶼,馬祖、金門也曾經是核廢料的貯存候選地。
金馬的複雜還不只如此。一般談到「戰後」,盤桓在「中華民國台灣」上空的戰爭時間有兩股。其一是台灣史觀的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台灣改受中華民國統治;其二是中華民國史觀的一九四九年,國共戰敗,政府遷台。然而金馬其實存有第三股「戰後」時間,即解除戰地政務的一九九二年。至此之前,法律上金馬是戰地,受各種禁制。實際上的砲戰也直到一九七八年底才歇。論及台灣四大、乃至五大族群(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近年加上新住民),金馬人卡在各分類的中間,無處落座——金馬確實是「外省」(福建省),但和一九四九前後渡海來台那波外省人的脈絡大相逕庭。明明稱「台澎金馬」彷彿占了國土的二分之一,但其實是通天入地的「被缺席」。
對於馬祖而言,台灣和中華民國雖然未必全等,但兩者幾乎同步被馬祖認識——馬祖認識的「台灣」,已經是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台灣。對馬祖人而言,無論中華民國和台灣都是外來或外在於馬祖的,兩者不一定有台灣人認知的這麼大不同。可能直到一九九〇年代,台灣本島才被以新興的政治力量——「台獨」之名,被馬祖重新認識,使馬祖意識到台馬有別。更令人五味雜陳的是,這個「新台灣」往往是來「切割」馬祖的。正如馬祖尷尬的地緣位置,它既陷落在中國與台灣「兩岸」,又同時受到中華民國和台灣兩股史觀的沖激,置身多重的夾縫中。
我曾經有一個版本的論文計畫,是將琉球(沖繩)和馬祖並置。二戰時死傷慘重的沖繩戰,可以比擬台澎金馬唯一發生過登陸戰的金門古寧頭;而二戰後迅速進入冷戰,沖繩為日本本土扛起基地化的任務,也如同金馬為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所承受的命運。不過礙於語言的次元之壁與沖繩學的汗牛充棟,我自認不足而放棄。不過沖繩經驗與省思仍值得對話,我甚至認為不具軍事化、基地化經驗,反而身為金馬軍事化之受益者的台灣,相較之下,是很難理解沖繩的。
進入現代以來,島嶼不可免俗被納編進以大陸國家為延長的政權之中,有學者語重心長:「現代國家權力粗暴地基於進步主義,將所有地方性的東西加以扼殺。」十九世紀的廢藩置縣、琉球處分之於沖繩如此,二十世紀的「一九四九」、戰地政務之於馬祖也莫不如此。
出身琉球西表島的作家崎山多美在一次來台演講就提到,對她而言沖繩(本島)和巴黎都像是異國。島嶼的成長經驗,讓她對「國家」的認知相當不同——「國界線」、「國籍」是有如殖民地的概念;對於日語則有「違和的身體感」。她認為也許正是在西表島生活、長大的身體,自然地抗拒「我是哪國人」,所以形成了傾軋、扞格的感受。在本書中,我們也能見到馬祖列島作為地方,面對現代國家強行刺入的張皇失措。
大江健三郎(一九三五-二〇二三)遊歷沖繩後,認為「日本屬於沖繩」(日本は沖縄に属する)。學者吳叡人在《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中對此的詮釋是:日本的自立建立在沖繩的犧牲之上。也就是說,沖繩為日本承擔苦難、付出代價,日本在道德上對沖繩有所虧欠(morally indebted)。從沖繩和日本的案例,除了能認識到「加害/被害」關係的重層性——以廣島核爆為代表,日本擁有「受害」經驗,但面對沖繩時,日本則是無庸置疑的加害者。延續著這樣的說法,台灣同樣可能屬於馬祖——不只在文化的互為涵融,更是政治道德的層次上。在大江健三郎的意義上。
日本小說家島尾敏雄(一九一七-一九八六)用拉丁語自創語彙「日本尼西亞」,也就是「日本-群島」。同一個構詞原則的「台灣群島」則是來自吳音寧在臉書粉絲專頁的說法:「我說的台灣島嶼,包括了澎湖、金門、馬祖、小琉球、綠島、蘭嶼等地。我們的台灣,是群島的國度。」「日本尼西亞」朝海洋與島群開放,「台灣群島」也擴張台灣,解除「本土」的狹隘性。所謂「本土」其實是多元,主體並立,秩序繽紛,就如同法律史學家王泰升所言:「台灣共同體內部是複雜的,只有看到複雜性,才能夠相互尊重。」
(本文摘自:第一章「開往家鄉的慢船」)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