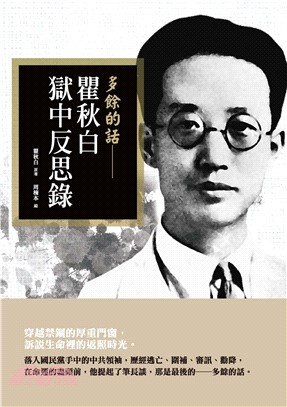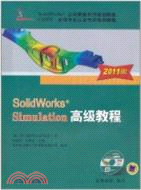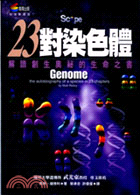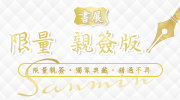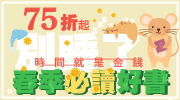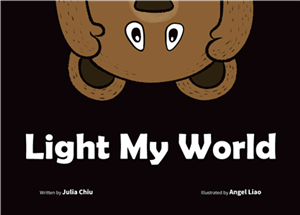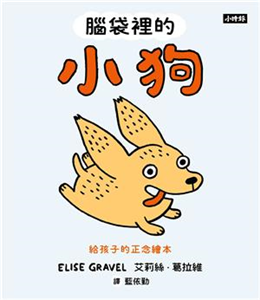多餘的話:瞿秋白獄中反思錄(電子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也是繼陳獨秀之後第二個被共產國際打倒的中共領袖人物。《多餘的話》是他於一九三五年被國民黨軍隊俘虜後在獄中寫下的反思錄。這篇反思錄不過是對其棄文從政給自己所帶來的惡果感到痛惜,在「文化大革命」中他的這一作品卻被當作變節書,即宣佈其為叛徒,其妻子也慘遭逮捕、迫害致死。雖然後來瞿秋白得到了平反昭雪,但是他的這篇遺作仍然成為了他的一個軟肋,不能為人正視面對,至少不可能如另一紅軍將領方志敏的獄中遺作那樣廣為傳誦。
本書收入了目前能見到的瞿氏在獄中的全部遺稿,還編入了當年記者獲准對囚禁中的他進行採訪的記錄,國民黨軍圍捕他時所發電報,當局對他進行審訊、勸降等檔案材料,以及諸多見證者的回憶文章等等。本書是《多餘的話》最完善的版本,也是瞿案最為詳實的原始資料集。
本書特色
1.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物,瞿秋白的遺作,敘說民國初期共產黨成型期的經歷。
2.收錄大量相關資料,包括瞿秋白的創作詩詞、訪談紀錄、審問資料、相關人員的回憶錄等。
3.文本與注釋資料詳實,同時佐有圖片,具有保存重要史料的價值。
作者簡介
瞿秋白 原著
散文作家,文學評論家,俄語翻譯家。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與締造者。1935年在福建長汀被南京國民政府逮捕並槍決。
周楠本 編
1951年出生於湖南常德,北京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中國魯迅研究學會理事。曾為湖南人民出版社文史編輯、《魯迅研究月刊》常務副主編。著作有《我注魯迅》、《魯迅回想錄》(編注)等。近年注重於中國近代史研究,瞿秋白的遺作《多餘的話》即為其中之一。此外發表有《孫中山〈倫敦蒙難記〉探析》、《管學大臣與大學校長》、《京師大學堂史料研究》、《〈湘報〉與南學會的創辦及結束》等史實考證文章。
序
話既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已經是走到了生命的盡期,餘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甚至3不能按星期來算了。就是有話,也可說可不說的了。
但是,不幸我捲入了「歷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為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為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著政治工作②──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裡做著這個,心裡想著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布林塞維克所討厭的小布爾喬亞智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不能夠不發作了。
雖然我明知道這裡所寫的,未必能夠到得讀者手裡,也未必有出版的價值,但是,我還是寫一寫罷。人往往喜歡談天,有時候不管聽的人是誰,能夠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況我是在絕滅的前夜,這是我最後「談天」的機會呢?
瞿秋白
一九三五‧五‧一七 於汀州獄中。
目次
編者前言
一、獄中遺稿
多餘的話
記憶中的日期
未成稿目錄
致郭沫若
獄 中 詩 詞
供 詞(摘錄)
二、獄中談話錄
瞿秋白訪問記
勸降問答錄
三、被俘審訊資料
陶峙岳致蔣鼎文電
鍾紹葵致李默庵呈文
鍾紹葵致宋希濂密電
鍾紹葵致李默庵密電
鍾紹葵呈汪精衛、蔣介石邀功請賞電
審訊記
蔣介石處決電令
宋希濂呈李默庵行刑電
宋希濂呈蔣鼎文執刑電
畢命前之一剎那
瞿秋白畢命紀
瞿秋白伏法記
瞿秋白絕筆詩
四、參考文獻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
中央緊急通告(中央通告第九十六號)
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的發言(一九三一年一月)
致共產國際執委和中共中央的信(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
聲明書(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八日)
我對於錯誤的認識(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七日)
五、回憶資料
我和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突圍、被俘的前前後後
瞿秋白被害經過
關於瞿秋白的手稿
回憶瞿秋白獄中寄出的信
回憶秋白烈士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同志
一個深晚
秋白同志印象斷片
《多餘的話》
未曾忘卻的往事
瞿秋白獄中側記
為獄中瞿秋白看病的兩個陳軍醫
我所知道的瞿秋白烈士就義前後
六、附 錄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關於瞿秋白同志被捕問題的複查報告
書摘/試閱
一
他出身於一個破落的士紳家庭。十六歲時因貧輟學,中學未畢業即到社會上去謀職。十七歲時他的母親因不堪承受家庭重負,服毒棄世;父親飄泊異鄉自尋生路,弟妹離散。瞿秋白則投奔其在北洋政府任職的堂兄瞿純白,隨其堂兄從武漢來到北京,並進了「一個既不要學費又有『出身』的外交部立俄文專修館」去學習,當時他不過當做將來與其堂兄一樣,能有一技之長,可以學到謀一碗飯吃的本事而已。
魯迅說:「孺子弱也,而失母則強」。瞿秋白正因為過早的失去了父母親的保護,倒使一個生來文弱而多愁善感的人,剛一進入京城就捲入到社會潮流之中,走向了反抗社會的叛逆道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爆發,他是俄文專修館學生代表、北京學聯成員,是學生運動的一名活躍分子。後來他還與俄文專修館的同學及文學研究會的幾個朋友創辦《新社會》雜誌(一九一九‧十一月);不久他參加了北京大學教授們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一九二○年初),成為中國最早一批共產主義信徒(實際上不過是俄國革命追隨者)。由於熱愛俄國文學,嚮往俄國革命,不甘於將來僅僅只有「謀一碗飯吃的本事」去做一名政府機關公務人員,最終他沒有依從在外交部任職的堂兄的意願,在結業前夕,竟然放棄了學業和文憑,於一九二○年十月應聘為《晨報》特派記者赴俄國做通訊員。應該說「歷史的誤會」由此就開始了,因為他不僅沒有遵循堂兄給他安排的道路,而且也不得不捨棄了他理想的語言文學事業,接受了命運對他的安排,做了一個職業政治活動家。所以多年後他在獄中的遺作裡,帶著悔恨的心情寫道:「從一九二○到一九三○,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我所願意幹的俄國文學研究──到這時候才回來,不但田園荒蕪,而且自己的氣力也已經衰憊了。」所謂「到這時候才回來,不但田園荒蕪,而且自己的氣力也已經衰憊了」,是說的一九三一年初被王明集團打倒拋棄之後,他遇到了中共週邊組織左翼作家聯盟的朋友們,得到他們的接納歡迎,隱居在上海重新開始自己喜愛的文學工作。他認為他過去對人生道路的選擇是「離開了『自己的家』」,現在回歸已經為時已晚;他完全承認這是一個錯誤的選擇,是「歷史的誤會」。但這只是針對「棄文從政」這一職業道路的選擇,並非否定其政治理念本身,更談不到叛變革命。
一九二○年,這一年他僅僅二十一歲;而到俄國僅僅過了半年時間,一九二一年五月他就成為了共產國際屬下的黨員。此時國內的共產黨活動剛開始萌芽。
在蘇聯受了兩年第三國際理論薰染之後他於一九二三年初被派回國,六月作為蘇聯歸國代表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並受命撰寫了中共黨綱,這是中共黨史上的第一個黨的綱領。緊接著參加國共合作工作,並受委派參加國民黨一大宣言起草。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上被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
這一個時期可以說是他政治生涯中最為嶄露頭角、陽光燦爛的時期。在個人私生活上也是極不平凡的一年,這一年他有過兩次婚姻。他的第一位妻子王劍虹,是他在上海大學做教授時的學生,在他工作最為緊張之時不幸病故;他的第二個妻子楊之華,是他黨內的同志,與他共同度過了以後的十年顛沛流離的生活,而且許多年後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浩劫中,由她代替承擔早已死於國民黨刑場上的丈夫臨刑前在獄中留下的遺墨《多餘的話》的政治責任,竟被「紅衛兵」活活整死(被關進秦城監獄,於一九七三年病亡)。
瞿秋白一生中最為風光的國共合作蜜月期只不過短短三年光景就很快結束了。一九二七年七月國共徹底決裂,陳獨秀作為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運動中的第一個替罪羊遭到清除;幾個月前在中共五大上已經鋒芒畢露的瞿秋白被共產國際選中,在「八七會議」上他不僅接替了陳獨秀在中共的領導位置,同時也接替了他未來做犧牲的資格。一九二八年六月、七月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上瞿秋白承擔了一九二七年武裝起義失敗的責任,以「盲動主義」之罪名遭到猛烈批判,被調離中共領導崗位,留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在他任駐蘇聯中共首席代表期間,蘇聯大清洗的苗頭已經出現,中共代表團尤其是作為首席代表是不可能置身於世外桃源的。在莫斯科的這兩年裡,他與王明集團交惡,尤其是深深的觸犯了兩年之後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去收拾黨內反對派的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王明集團的主子米夫。當時米夫任莫斯科中山大學(後改名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校長,在對待學潮問題上中共代表團多次與他發生衝突。一九二八年秋,中共代表團與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共監察委員會聯合組成審查委員會,調查審理中國勞動大學(原莫斯科中山大學)學潮事件,糾正了王明集團製造的「江浙同鄉會」冤案;瞿秋白以中共代表團長名義向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庫西寧提出撤銷東方部副部長兼勞動大學校長米夫職務的建議。從此瞿秋白即成為米夫、王明集團重點打擊的對象。一九二九年秋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就因為捲入莫斯科勞動大學反對米夫的學潮遭到暗害。一九三○年六月,共產國際通過了《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因中國勞動大學派別鬥爭關於中共代表團行動問題決議案》,撤銷了瞿秋白中共代表的職務。如果此時他在政治上一直往下滑坡,對他也許是個極大的幸運,可是他自己並沒有料到,對於第三國際他還有一次極其重要的使用價值。正當要遣返他回國之際,他卻意外的接受了一項重任,奉命回國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目的是制服當時掌握中共中央實權的李立三,制止其冒險主義鬥爭路線。根據共產國際的部署,瞿秋白在三中全會上組成了以他為首的中央政治局。可是當李立三就範之後僅僅三個月,而立三路線並未真正糾正,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就在上海緊急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宣佈三中全會所執行的是比立三路線更陰險的反對共產國際的機會主義路線,而所謂瞿秋白的「盲動主義」以及對「立三路線」的「調和主義」是中國革命遭受失敗的禍根。就這樣瞿秋白被開除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並且作為戴罪之人,隨時聽命中央的鞭撻批判。
瞿秋白與陳獨秀當年所犯「罪錯」的區別是:陳犯的是「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即在共產國際實行全力援助國民黨之時,由他承擔國共合作失敗的責任;而瞿犯的是「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即在共產國際被迫轉向,指令中共武裝反抗已經壯大起來的國民黨政權之時,由他承當盲動主義的失敗責任。無論是「左」的還是「右」的機會主義都必然的為更「左」或更「右」的機會主義提供了取而代之的「理論」口實。為時僅僅一天的四中全會達到了其預期目的,就是將比李立三冒險主義路線更為冒險,比瞿秋白「盲動主義」更為「盲動」的,更加荒謬無理性的王明路線定為了真正的馬列主義路線。也正是這個王明集團所統治的中共中央加速了江西蘇區紅軍的大潰敗。
離開中共領導機關,在左翼文藝界朋友的幫助下,瞿秋白潛伏在上海賣文為生。儘管他自覺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經結束,上海的媒體(如《社會新聞》)謠傳他已病死鄉間,但國民黨當局仍然將其視為赤匪首領懸賞二萬元通緝捉拿。國民黨的通緝並不足懼,使他痛苦不堪的是被逐出「教廷」的事實。他內心深處的這個痛苦,他在獄中最後的反省裡才開始坦然流露:「我第二次回國是一九三○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這期間只有半年不到的時間。可是這半年對於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像完全用盡了似的,我告了長假休息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臺。」「我自由不自由,同樣是不能夠繼續鬥爭的了。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結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雖然他不能像在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裡遭祕密屠殺的「二十幾名黨的重要幹部」那樣,毫不畏懼被宣佈為叛徒、特務、反黨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堅持反對四中全會的立場,勇敢的面對並接受嚴重的制裁;但是他明白,在黨的決議上,他也已經被宣佈為「整個階級敵人在黨內的應聲蟲」(見《中央關於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錯誤的決定》,一九三三‧九‧二二),實際上他早就被定性為反革命(「叛徒的一種」)了。他是帶著這一極度矛盾和絕望的心情向人世告別的:「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著,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讀者如果明瞭他是戴著階級敵人的帽子而赴死的,就會明白他何以苦痛、何以心憂了。
他只能表達到這一地步,他只有把自己肉體的消滅作為思想解脫的唯一辦法了。這種苦痛消沉的思想情緒表達,近於以死抗爭,也可視為一種絕望的反抗吧。
雖然作者將他的這篇遺言題作「多餘的話」──對他本人來說,到生命即將結束之時才說出這些以前沒有說的話,似乎已經沒什麼意義了──但是他又意識到這是他結束生命以前向人們傾訴他內心的痛苦、鬱悶的唯一機會了;他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留給未來的人們去做經驗總結,歷史功罪自有後人評說。由於他身陷囹圄的處境,更由於其思想的局限混沌,他只能以一種自責的方式,在無情的解剖自己思想靈魂的同時,極其曲折隱晦的向後人,向今後研究這一段中國歷史以及國際共運歷史的人們,提供一個思想的線索,留下一點個人的痕跡。儘管他極其頹唐,但並不是一個思想已經枯竭了的人,他在獄中還作了續寫《多餘的話》的計畫,已經擬就了提綱《未成稿目錄》。這篇「目錄」中的最後一篇題作《得其放心矣》(《汀州》),儘管作者在《多餘的話》中並沒有真正做到所謂「得其放心矣」,沒有能夠真正突破自己思想的禁區,更加直白的說出自己內心深處的話,但是就作者寫作此文的本意來說,它已經達到目的,起到了「多餘」的話應有的社會效應了,它將促使人們去重新評判作者以及他的這篇遺著,更促使人們審視反思這一段歷史。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