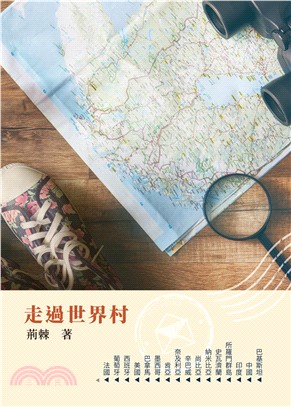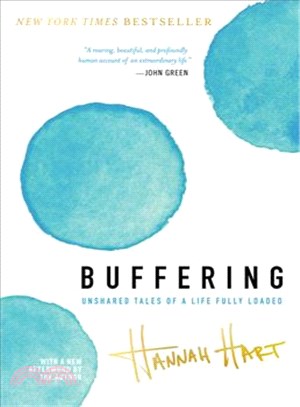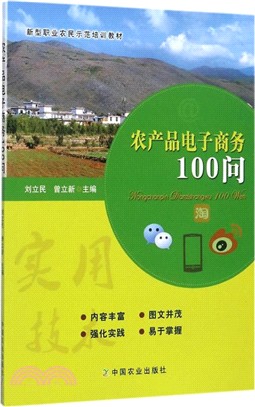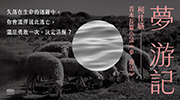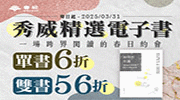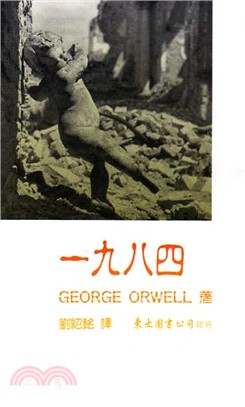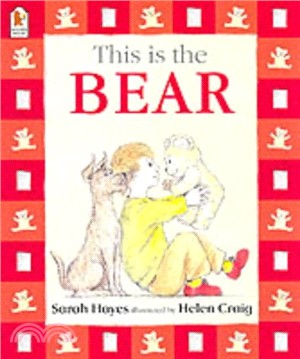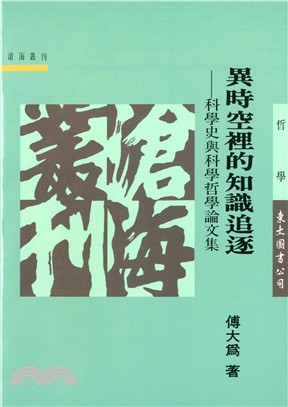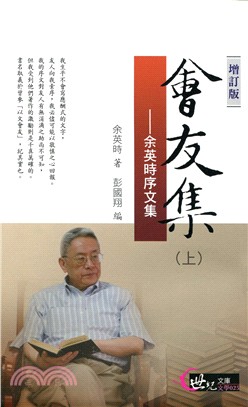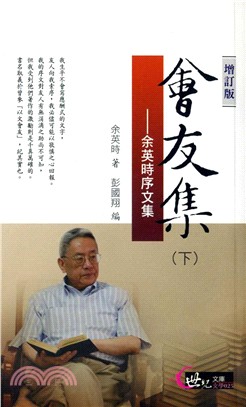自序
處處無家處處家
家是什麼呢?是不是祖母講故事時你蜷曲依偎的搖籃?是不是父母引頸盼你早歸時依靠的斜牆?是不是孩子們過年過節的遊戲和嬉笑?是不是熊熊火爐前親朋好友暢談通宵的時光?是不是夫婦長年忙於油鹽柴米中的恩愛和溫柔?還有那菜餚飄香撲鼻的廚房?
或者,家是魂牽夢繞的歸宿,是失去了的樂園,是那被渴念塗染得美麗溫馨的景象?
對我來說,家,輕得使我無以承受。我曾經四海飄蕩到處尋求,卻已不知家鄉何在。
我出生在戰火緊逼的湖北臨時省會恩施,那地方和我空白的記憶一起已經淹沒在新建的三峽大壩之下。父親的老家在黃岡鄉下的旗杆村,我從未去過,兩年前我去找的時候,鄉人都說沒聽過這個名字,好像旗杆村已經改了名字劃分到黃石縣去了。我們一家曾經住過的黃岡縣政府宿舍,已成了新蓋七層大樓底下的瓦礫,哥哥表姊和我曾坐在屋後的赤壁樓圍牆上看滾滾長江,數腳下翻轉的白色江豚。我還鄉尋根的時候,江水早已退縮到幾十里以後,江豚瀕臨絕跡,在渾濁的河水中看不到了;稀疏蒼茫的叢林之後,風聲呼嘯之中,倒是隱約可聽到蘇東坡和黃庭堅吟詩對談,山坡的小路畔也彷彿留有歷史上過客流放的足跡。
我在台北成長,從國民小學到大學畢業一直住在松江路。白先勇家兄弟眾多是我的鄰居,三毛在中正小學低我一年級,她從小引人注目也住在附近,我卻因羞澀自慚而沒有和他們說過一句話。至今,松江路仍然常年在我解不開的夢境中,繼續與我的成長時代糾纏不休。我當年騎著腳踏車到處跑,台北的大街小巷都像是我的後院,甚至騎車上下陽明山也不是問題。當然那時台北的交通不擁擠,松江路附近還是僻靜的田野,現在這一區商業極其繁盛,我家的房子早已改建成高聳的銀行大樓,要不是掛著同樣的125門牌,我無法認辨。父母早已過世,家人也已凋零無幾,記憶再沒有支架可棲。臨街的店面正在賣豪華汽車,旁邊有個咖啡店。我坐下來品味咖啡的苦澀,車水馬龍在身邊馳騁,呼嘯一如戰事般激烈,難以想像睡了十五年的臥房是在哪個角落。
多麼羨慕詩人席慕蓉;在遼闊的蒙古長空之下,在綿延到地平線的草原上,有這麼一棵她從沒有見過的大樹,固執地一再出現在她的夢境。她聽到一聲又一聲的呼喚,她一遍又一遍地塗畫它。居然有一天,她在蒙古的草原看到它,真真實實地存在,一如她夢中見到的形象,像是千秋萬世都孤立在那裡,等候她歸來家鄉。
我已無家鄉,沒有可以歸去的地方。家成了一個抽象的意念,一份凝固了的渴望。像是瘂弦詩中的紅玉米,和北方的天空一起長久懸掛在屋簷下;像是結凍的冰川,看起來堅挺穩固如山,其實河底的石礪掙扎剝落,溶冰滴滴,隱然深藏。
我走過世界,不時停足試著在各地建立我的家。就像沙漠裡的滾動草,被長年呼號的狂風催促,止不住腳步地滾動不息,卻一路撒播著它細小的種子,渴望在任何一個角落生根成長。
在貝里斯的珊瑚礁海濱,我夢想作個熱帶島嶼的魯賓遜,我們買了一千英尺面臨珊瑚的沙灘,恨不得在此棕櫚拂面的潔白沙灘,以簡單純樸的生活方式度我們的餘生。在熱得透不過氣的巴基斯坦,我們用當地色彩濃烈的飾物來布置我們的小家,研習這土地上曾經繁盛的文明,在文化和宗教的嚴厲衝擊之下試著去尋找幾分幽默和趣味,也一再為這個社會壓制下的女性痛心疾首。
在西南非的納米比亞和南非的史瓦濟蘭,我們和當地人生活在一起,為村莊的野火、鼓擊和舞蹈迷惑,被紅土上千萬隻奔騰的野生動物震撼,聽到散布空中的原始野性呼喚。我到所羅門群島去找當地女子手製的貝殼錢,到中南美去探索瑪雅人遺留下來的金字塔遺跡,去印加深山拜望馬丘比丘。我們在南非的辛巴威露營,看到手工鈎織的桌布大片地掛在樹梢,鋪天蓋地地垂下,在夕陽西下燦爛一如金色的蜘蛛網。蜘蛛網絲絲入扣線線相接,沒有哪一根細線單獨掛在空中。我這才而意識到人與人之間的相牽相連,我與周圍膚色深黑的婦女沒有不同,只不過是命運的手指偶爾地抖了那麼一下,她成了我,我變了她;我其實很可能出生在她的土族村落,住在她的圓型茅舍泥屋,她也原可住在我的水泥台北城,我們之間本來親密無間,都是這個世界村的鄰居。
我在北密西根州的寒鄉遇到海諾,結為伴侶,兩人動手把一棟百年老木屋重新修建成可禦寒冬的溫馨小家。房子雖然簡單樸實,可是圍著小屋是一個夏季都開不完的繽紛野花,美麗一如錦綉的地毯。沒多久我們就搬到美國新墨西哥州的浩瀚沙漠,那裡的天空寬濶得沒有邊際,碧藍深沉好似純淨的海洋,從地平面的這一邊伸展到地平面的那一面,時光靜止在沙礫裡沉寂而永恒。沿著維爾格蘭地大河,我們擁有一片二十七畝的沼澤和農場,在教書的餘暇,我們耕耘我們的田園,種了核桃、瓜果和辣椒。我們全家人動手一磚一石地砌造我們的阿土壁土屋,千辛萬苦地用手把它從沙漠裡雕塑出來。雖然它是我們一手建造的,這阿土壁卻像是具有獨立的生命,存活在它自己的另一個世界中。我們叫它「沙堡」,像孩童一樣在海潮後退的沙灘遊戲,嬉笑著堆砌出來一座幻想中的堡壘,卻是聚精會神地把這當作世界上最重要的事來做,在一鏟沙一杯土之中,要為永恆畫像,明知海潮不久就會湧來把這一切摧毀淹沒。
果然,我們最後還是離開了這住了四分之一個世紀、 一生住得最長久的、花了最多心血建造的、我們以為永不會離開的「沙堡」。這才知道人生就是不斷地去建造、去收集,也是不斷地捨棄。而永恆,不也就是每一個消失的瞬間的總和?
我們離開了新墨西哥州,搬到繁榮擁擠的南加州,我們這些偏愛農村的鄉下人居然也住進了高聳的摩天大樓,遠離了田園和土地,過起嘈雜的城市生活來。我的日曆密密記下的是歌劇和交響樂團的節目,我跑的是圖書館、博物館和動物園,我喜歡散步的是沿海的沙灘。然而去年,老伴海諾搬進了養老院,我們被詩人瘂弦命名為「望海閣」的公寓,也立刻被人搶手買過去了
於是我真的沒有家了。人生如寄,我成了空中飄蕩沒人牽線的風箏。然而,再一轉念,世界不就是我的家鄉?人類不就是我的親友?而愛,不也就是存在我的胸懷?
俄國大音樂家柴可夫斯基一生憂鬱,因他的同性性向而受到慘痛的迫害。他為了順應社會壓力而結婚,婚姻卻完完全全地失敗,婚後三個月他就逃往義大利,卻在那兒過了一生中最快樂最自在的一年。在那裡他寫下《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在這首極為羅曼蒂克的協奏曲裡,柴考夫斯基懷念他的家鄉,採用了很多俄羅斯民謠。但是如果靜心聆聽,可以聽到他別的曲子所沒有過的——義大利燦爛明亮的陽光。
正如義大利的陽光能滲透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協奏曲,我們居住的每一個地方都影響我們,它們的色彩塗染我們的思想,它們的食物和香料進入我們的血液,它們的音樂溶入我們的夢境,它們的文化擴大我們的視野。所有我們愛過、思想過、建立過、生活過的,都成了我們的一部分,促使我們成長。
作家張翎在《疼痛是生命和寫作的起源》一文中提到,在海外居留多年以後,家的意識已變得淡泊模糊,自己像是存在於本土和異地之外的第三個國度。詩人洛夫也在《在北美的天空下丟了魂》一文中表示,他的定位已經變得如此地噯昧而虛浮。看來,我們這些海外過客的共同點,就是沒有家鄉,沒有稜角明顯的定位,沒有一所注定的歸宿。
然而,沒有家的世界過客,是不是更能把處處都當作是家?在我們不停的漂泊之中,每一個暫時駐足的角落,是不是都存在愛和情?都有給我們去思想去領悟的空間?讓我們去建立和放棄?
我常常想起我在世界各地曾經建立和放棄的家,當地獨特的景致和文化傳統,也有如天方夜譚般光怪陸離的奇遇。在那些地方我留下了我的一部分,也帶走當地的一部分。當我把這些寫下來時,我好像進入另一個時空,重新活在那些故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