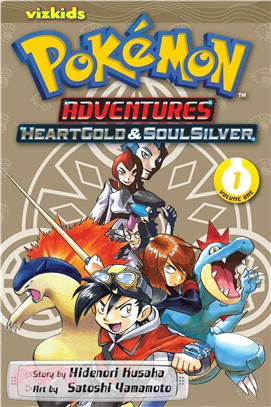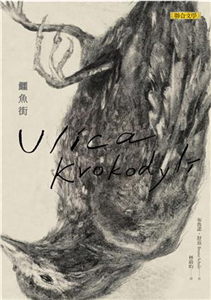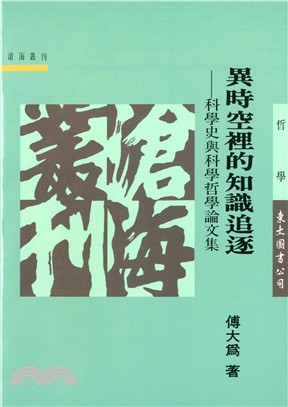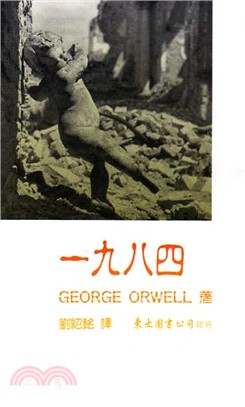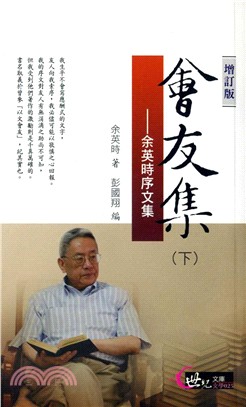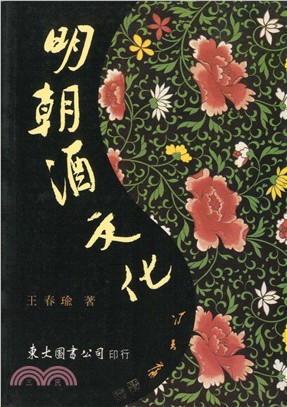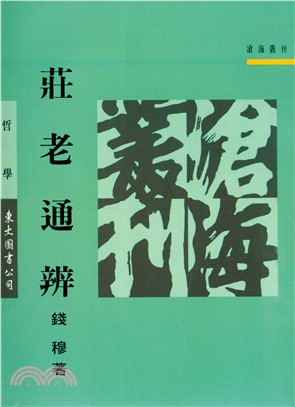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電子書)
商品資訊
ISBN:9789869987073
EISBN:9789869987080
出版社:健行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作者:沙力浪
出版日:2021/05/01
裝訂:電子書
商品碼:2222221393336
商品簡介
★ 藉由新增的後記,再度思索對於山林政策、國有地、原保地、傳統領域的平衡與傳承。
★ 主動探究族群文化,並以文字深刻記錄走過的路線、部落名、河流,以及山中的故事。
★ 關注原住民族議題,以民族學科田野調查、歷史敘事,記錄族群文化以及祖先的歷史。
★ 記錄布農族人——拉庫拉庫溪流域的人文歷史。
孫大川 政治大學臺文所專任副教授、李根政 地球公民基金會執行長、瓦歷斯˙諾幹 作家、乜寇.索克魯曼 作家 真誠推薦
看著祖先走過的路,他們用背簍、背架,在這個空間活出自己的生活。
用頭帶背著歷史,傳承,也背著夢想……,回到自己的家,說出自己的故事。
二○○○年,作者第一次被帶到山林祖居地時,祖居地對他來說還是一個模糊的名詞,既不認得山的名字,也不知道有哪些部落,更是第一次聽到巡山員、高山嚮導等名稱。斷斷續續進入山林二十幾年的協作生活中,慢慢發現有一群在山上的族人們,用腳走出自己的路,用頭帶背出自己的生命經驗,說出祖先的歷史與故事。而他的參與其中,讓他的生命有了不一樣的體現。開始了解到山對自身的意義,不單是一個空間,還有族群的歷史。
在山林工作的高山嚮導、背工、巡山員等族人,雖然職位名稱不同,相同的是他們用自己的力量在祖居地工作。族人們的實際工作情況又是如何呢?人們對這份工作的想像又是什麼呢?這些問題在二○一三年前往祖居地馬西桑的行程與一群旅人的對話中,產生了小小的疑問。與山林為伍的工作,真的如此浪漫嗎?讓他興起撰寫有關於族人在傳統領域的山林中,真實的工作環境。
這群唱著歌、穿著獵裝的族人,在山林中長期累積的經驗,是生態保育與研究幕後的大功臣,也是很多登山朋友們登山築夢、完夢的推手。
作者期許自己能像布農族作家田雅各一樣「以筆代替獵槍」,來為自己的族群發聲,將族群獨特文化記載下來。藉由寫出臺灣這一塊土地,不一樣的人、事、物,讓更多人看見高山協作、高山嚮導、巡山員等高山相關職業故事,了解到有一群人在山林中,努力的工作著、努力的生活著。
作者簡介
花蓮縣卓溪鄉中平Nakahila部落布農族詩人與文學家,書寫部落的情感與哀愁。曾經因為念書的關係,離開部落。到桃園念元智中文系,再回到花蓮念東華大學民族發展所。這樣的經歷,開始以書寫來記錄自己的部落、土地乃至於族群的關懷。目前部落成立「一串小米族語獨立出版工作室」,企圖出版以族語為主要語言之書籍,並記錄部落中耆老的智慧,一點一滴地存繫正在消逝中的布農族文化。除了在部落成立工作室,也在傳統領域做山屋管理員、高山嚮導、高山協作的工作,努力的在部落、在山林中生活,並書寫。
文學創作曾獲得原住民文學獎、花蓮縣文學獎、後山文學獎、教育部族語文學獎、臺灣文學獎,著有《笛娜的話》、《部落的燈火》《祖居地‧部落‧人》。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序
用文學背起山的記憶 孫 大 川 Paelabang danapan
對於原住民來說,最困難的不是法政經濟權益的爭取,也不是學術發言權的奪回,而是歷史主體的重建。這不能由別人來替代,也無法依賴某個個人的努力;它必須是整個群體的共識與覺悟,是一連串長期點滴積累的志業。這一個志業,不單是一種知識的堆砌或建構(就像考古學家、人類學家或歷史學家一樣),而應該同時是一種民族情感和認同的召喚,是一種血肉和靈魂的賦予。它不完全是理性的,它帶動情緒,引發哀痛;但也開啟盼望,讓我們有新的嚮往……
沙力浪的《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正是這樣一種覺悟的實踐,它不是向外的宣示,而是向內的充填,讓我們有機會擺脫「空心人」的虛無和偽裝。沙力浪實踐的腳步,依循著三個方向前進。第一篇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引導我們回溯近百年來,族人的山林智慧與生活世界,如何變成別人探索、丈量、規畫的對象?而我們一代又一代的先祖,又如何從獵人、守護者變成任人指使僱用的工具,在自己的土地上流離,淪為「無名」的存在?更令人傷感的是,沙力浪第二篇的文字,帶領我們瀏覽一塊又一塊的碑文,每一塊碑文背後都是族人的血淚故事。日本殖民帝國的力量往高山森林延伸,道路開鑿到哪裡,隘勇線就到哪裡,駐在所、學校和大砲也跟著深入。勞役的剝削和生存空間的壓縮,引發一次又一次的衝突、戰鬥,碑石雖然是為紀念入侵的「英靈」,卻同時也見證了他們的罪行。
佐久間左馬太(總督任期:一九○六–一九一五)武力掃蕩為主的五年理蕃計畫,全面掌控了中央山脈原住民各個族群及其部落。拉庫拉庫溪沿線的布農族聚落,面臨結構性的變化。隨後的集團移住政策,終於成功誘使布農族人從原居地往山下移住,卓溪、卓清、太平、清水、古風等村落即是族人遷徙的結果。舊聚落荒廢了,也成了「國有地」;族人的血脈系譜,被新的戶籍制度摧毀了。這是背工、巡山員和百年碑石共同指向的命運和結局。沙力浪將它稱為「淚之路」(第三篇),應該不是出於浪漫的想像。有趣的是,沙力浪的「淚之路」,是從尋找、重建佳心(kashin)Istasipal家族的Banitul之一座小小的石板屋開始的。與前兩篇的筆調和氛圍完全不同,沙力浪敘述重建Banitul石板家屋的過程,雖面對內外總總不同的困難和壓力,卻充滿虔敬、耐力和信心。原來這一段「淚」之路,已經不再是對過去族人命運的悲嘆,而是將背工、開路、隘勇線、駐在所、戰爭、集團移住、碑石、荒廢的遺址和記憶,藉一塊一塊石板的堆疊,細細縫合、重建起來。這才是真正歷史主體性的確立,最困難卻是我們未來必須全力以赴的工作。
寫序的這段時間中,剛好是「山海」承辦第十屆原住民族文學營,四天三夜的活動選在沙力浪的家鄉卓溪舉辦。其中一天是回到佳心石板屋的行程,來到沙力浪這本書的文學現場。沙力浪說,希望我的序能有真實的臨場感。
部落的參訪,沙力浪動員了不同家族,就像是重現石板屋修復工程,不是一個人可以完成。來到沙力浪的工作室、中平林道,接送的司機都是參與石板屋重建的工一班。當天來回佳心石板屋之行,有Tamapima的Sauli陪同,在〈淚之路〉那篇文章中,沙力浪提到他在佳心報戰功的情形,這次他則負責帶領我們回佳心。另一個嚮導是Istasipal石板家族的成員張緯忠。一路上,兩位族人將自己回到祖居地的心路歷程與我們分享,引導大家深入中平林道以及佳心舊部落空間以外豐美的歷史追尋之路,直接探觸到族人重建Banitul舊家屋的渴望、矛盾、虔敬、辛勞、堅忍與最後的喜悅。
來到石板屋前,張緯忠先進到家屋內,將三石灶bangin起火。張緯忠說這是為了讓升起的火煙燻屋內的樑柱,避免蛀蟲的侵襲,也讓祖靈知道,孩子們回來了。Sauli帶領大家向祖靈祭告、獻酒、禱祝。回到祖居地,不單單是石板屋的修復,與祖靈和解、對話,重新聯結,更是族人最深的盼望。
站在石板屋前,看著族人一塊又一塊背上來的石板,壘堆起來,疊成了一座石板屋;而沙力浪的文學敍述,也像一個接一個的記憶堆叠,藉文字的縫合,編織成可以感受得到、觸摸得到的活的歷史意識。
序
作者序
高山協作的背架
先用一首詩,寫給在深山中工作的人,寫給書中的高山協作、高山嚮導、巡山員,這些人的背架裡到底裝了什麼,是裝了文化、經濟、生命經驗?透過這首詩來呈現高山工作者的心情,詩名為〈高山協作的背架〉:
裝進奶粉罐
一步一步地踏進
祖先的路
將嬰兒祭的項錬
放在東谷沙飛
背著背架
一路上採集
玉山薊、麥門冬、射干
金線蓮、七葉一枝花、梅花、菊花
帝雉的羽毛
登上玉山
背架裡
裝進逝去的棒球夢
梅花鹿般的跳躍
穿過竹林
攀上大霸尖山
背架裡
裝著
細心呵護的
櫻花鉤吻鮭
走向南湖大山
背架裡
裝進一座獎臺
連續登上
三六○三公尺、三二七九公尺
三五六四公尺、三六三○公尺
放在第一百座的山頂上
請授獎人站在榮耀的頂端
高山協作的背架
很高
高到可裝進
三○○○公尺的百岳大山
從清朝的背伕、日治的背工、隘勇,當代的高山協作們,會在山上工作的族人,大部分還是以生存為主要訴求,這樣才能夠溫飽家人,才能講求更深一層的心理、文化層面。在高山工作是一份很辛苦的職業,但是對族人來說,它是一份少有可以留在部落,又可以在傳統領域行走的一份工作。透過這份工作看到自己祖先走過的路,族群的歷史感自然而然的就加注在自己的身上。或許對在山上工作的人來說,不會把深奧的族群文化、族群認同,輕易說出口。但是這群在山上的族人們,用腳走出自己的路,用頭帶背出自己的生命經驗,說出祖先的歷史。
兩千年我第一次被林淵源(Nas Qaisul)大哥帶去山上,那時候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進山林。只知道我要回到祖居地,祖居地對來我說是一個很模糊的名詞。其他的事情我一概都不知道。進入山林,也不認得山的名字,祖居地有哪些部落,哪些部落名。
後來,只要大哥在玉山國家公園內的工作,有任務進入山林,都會問我有沒有空一起進人山林。就這樣斷斷續續的進入祖居地,接近二十年了。開始了解到山對我的意義,它不單單是一個空間,還有我族群的歷史在裡面。
斷斷續續的進入山林二十幾年,我進入了協作的生活中,慢慢的發現,有一群族人,要靠山林生活,要靠山養活全家,這是一份艱苦的工作。我從拉庫拉庫溪流域空間的書寫,慢慢用筆記錄高山協作的生活。有時自己也背負重物,擔任起高山協作的工作。幸好大哥們,知道我一路上要拍攝、記錄,不會分配很重的東西。也因為這樣,可以很專心的寫下一路上的事物。
走進山中,靠著大哥們的協助,讓我完成了第一篇〈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是寫給曾經在這群山中工作的族人,日治的阿美族、平埔族隘勇、布農族背工,當代的高山協作、高山嚮導、巡山員。這群人讓山增添了許多故事,而我也參與其中,讓我的生命有了不一樣的體現。
由於學業關係,開始鑽研自己拉庫拉庫溪流域的歷史,對這個空間有一些書寫。有些人就會請我當高山嚮導,讓我介紹拉庫拉庫溪流域的人文歷史。但是,我看到的書籍,都是以日本的觀點為主。尤其往瓦拉米、大分的路上,都是日本建立的紀念碑。
幸好在進入山林的過程中,我一直拿著攝影機做記錄。我把這些影像,重新整理化為文字。我看著自己跟著林
淵源大哥站在歷史現象的影像,他站在紀念碑前,說著老人家傳給他的口述歷史,每一個歷史都呈現別於文本的內
容。回到山下再找一些耆老,如黃泰山耆老,一句一句的把喀西帕南述說出來。這些文本與口述的交錯,形成了第二篇文章〈百年碑情〉,記錄著布農族人與日本人的百年悲情。
最初跟著林淵源大哥上山,我一直抱著很單純的想法,就是把他走過的路線、部落的地名、河流的名字,山中
的故事,一一的記錄下來。有時候,走在古道,走在稜線上,心中會默默的想,當我們這一代族人不走這條路,下一代族人應該沒有人會想要來這裡,布農族人對這裡的空間知識,都可能化為文本。
退伍之後進入職場,較少去山上,但是只要林淵源大哥問,要不要回祖居地,一定會排除萬難跟著上山,尤其是看到大哥逐漸年邁的身軀,想要抓住每一次的機會,希望留住大哥山林知識的隻字片語。二○一六年,林淵源大哥走進布農族的mai-asang,布農族美好的國度。我從Qaisul大哥,改叫他為Nas Qaisul。布農語人名加Nas是為亡者。大哥的離去,讓我以為山中的一切都即將回歸大自然,沒有人會再回到祖居地。之後,我發現曾經被大哥帶過的協作,開始帶自己家族回到祖居地,有人循著大哥的口述,找到自己的家屋,人慢慢的走回去。
二○一七年,開始接觸到家屋修復的工作,讓我重新跟高山協作一起工作,一起重建家屋,一起作夢。在傳統領域內家屋的修復,是我進入山林中從來沒有想過的,尤其這個地方早己被國家畫為國家公園和林務局。修復家屋的花蓮文化局陳孟莉,影響她想要進行這件工程的觸因是看了兩本書,一本是林一宏的拉庫拉庫溪布農族家屋的調查,另外一本就是我寫的碩士論文,探討拉庫拉庫溪地名的轉變研究。兩千年的第一次入山,就是跟著林一宏進入山林,那一次就是林淵源大哥帶路,我的碩士論文也是大哥帶領我。原來每個人都是另一個人的啟發點。一個人啟發另一個人的想法,又推動另一個人的想法,眾人的互相影響下,家屋就這樣被修復起來。我把這一段修復家屋的過程,寫成本書的第三篇文章〈淚之路〉。
進入山林的這段時間,我曾經這樣的認為:怎麼可能在傳統領域修復家屋。現在,石板屋的修復,讓我想像的界線更為寬廣,我希望傳統領域能重建幾棟家屋,連到西部布農族聚居地南投東埔部落。這樣可以像其他國家一樣,進入八通關越嶺道路的山友,可以住進族人所蓋的石板屋。山友拜訪的同時,就好像走進村落的生活一般。
我無法想像,這一本書,可以影響多少人,改變多少事。但是我寫出了臺灣這一塊土地,不一樣的人、事、物。讓更多人看見高山協作、高山嚮導、巡山員等高山相關職業故事,了解到有一群人在山林中,努力的工作著、努力的生活著。
感謝山海文化雜誌社每年持續舉辦臺灣原住民文學獎,如果沒有文學獎的激勵,幾乎沒時間把手邊的田野資料,整理成這三篇文章。這三篇都是因為參與了山海舉辦的文學獎,才能讓這些文章得以呈現。
■〈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嚮導背工與巡山員的故事〉,得到二○一三年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報導文學。
■〈百年碑情〉,得到二○一五年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報導文學。
■〈淚之路〉,得到二○一八臺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報導文學。
最後將本書獻給在佳心工寮,因病身故的工班班長陳中正大哥(Nas Bade)、教我編頭帶的黃泰山耆老(Nas Bisazu Naqaisulan)、帶領我回到祖居地Mai-asang的林淵源大哥(Nas Qaisul Istasipal),還有卓溪鄉高山協作資歷最早的林啟南阿公(Nas Laung Istasipal),也在這本書成書前,離開人世。雖然你們回到天上的Mai-asang,但是你們的故事,豐富了這一本書。
附件3內文試閱
從頭帶開始說起
我們布農族的祖先,運送物品都是以人力搬運,所以製作很多器具來做背負的工作。像是背架(patakan),一種用木頭製作的背負支架,側面看起來是L型的背架,類似後來由登山用品社引入的大鋁架背包的構造;還有背簍(palangan)、密封背簍(palangan qaibi)、網袋(davaz)、女用網袋(sivazu),這些都是布農族人重要的背負工具,大都是採用斜紋編法或六角編法編製而成的。
這些背負工具,不能缺少兩個附屬物件──肩背帶(vaki)和頭帶(tinaqis)。利用這兩個藤編物品的附屬物件,就會形成兩種不同的搬運方式,雙肩背負及頭額頂法。雙肩背負是將物品裝置在搬運工具,將一對背帶套在雙肩,靠在背上搬運;頭額頂載法則是將一條頭帶頂載於前額,以頭部力量撐住,將背簍等背負工具靠額頭搬運。
所以用肩背帶的時機,是我們背負的物品,重量沒有那麼重時,就可以使用肩背帶。我們稱雙肩背負這個動作為vakilun。背負的東西比較重時,就用頭帶,我們稱用額頭頂重物這個動作為patinbunguan。
肩背帶通常是背負較短的行程,例如從家園附近的耕地,背一些農作物。頭帶則是東西較重,背負的行程也比較遠,例如從獵場背負獵物,頭帶可以讓族人在背負重物時走得比較久。我們就從頭帶開始寫起,因為我們討論的高山協作,都是背負重物,並且要走較長程的登山路線。
二○○○年的日治八通關越嶺道路調查之行,從東埔走到南安部落。在離開大分的那一刻,〈背負重物傳訊歌〉(matin lumaq)的音律,緩緩地由領路人林淵源的腹中升開、凝聚,流洩至脣齒,振顫、共鳴、回響,清澈的歌聲,一聲聲迴盪在大分的山谷間。
頭上包著毛巾,額頭戴著頭帶,腳穿塑膠雨鞋、肩上背著「鐵架配米袋」搭湊的登山背包。在這一身的裝扮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頭帶,以前的族人就用頭帶背負重物,現在很多背工則使用L型大鋁架搭配頭帶,來減少肩膀的負擔。早期頭帶使用的是黃藤皮編織,隨著時代的進步與材料的取得方便性,已經漸漸改採用打包帶來作編織,頭帶的編織方式雖然各族有所不同,但是編法主要以斜紋編法,戴在頭頂上,也很像頭上的裝飾品,煞是好看。
我頭上也頂著頭帶,這是從笛娜的背籃拿下來,我把它裝在大鋁架上,讓我可以行走在山林裡。部落大部分的頭帶,都是黃泰山長老製作出來的,部落只剩下他一個人用藤製作頭帶,所以部落的族人,大部分都是使用Bisazu製作的頭帶。現在的編織物有打包帶和大自然的黃藤(quaz)兩個原料,這兩個素材他都可以製作出來,編織出一個又一個傳統且實用的編織品。
頭帶是我目前最常使用的物品,每次上山都要跟笛娜借,深怕哪一天被我弄丟,於是抽空跟黃泰山學習製作頭帶,一個月的學習中,讓我擁有專屬的頭帶。出生在拉庫拉庫溪太魯那斯的Tina Umav,已經九十多歲,曾經跟我說過,以前藤編只有Isbabanal這一個氏族才可以編,其他家族都要向他們以物易物,來換編織物,她如此說:
naitun maqansia matas-I balangan、tuban、sivazu、davaz、at talangqas、
kaupakaupa tindun qai Isbabanaz a tindun, maqa ata qai mabaliv ata,
只有他們可以製作背簍、籐籩、網袋、talangqas,只有isbabanaz氏族才可以做這些,其他氏族就向他們買。
這個專屬Isbabanaz的編織技術,其他氏族編織是禁忌(samu)。在時代的變遷,氏族互為交流下,技術廣為其他氏族學習,就像Bisazu他是屬於istasipaz氏族。現在的年輕人卻越來越少人學習這項傳統技藝,未來不知道這個美麗的編織物,還能不能在山上看得到。
頭帶是原住民嚮導和高山協作上山一定會攜帶的物品之一,這個編織物可以讓我們從眾多的山友中,猜出這群戴著頭帶的人,具有原住民的身分。但是,現在也越來越多的平地人,開始學習使用背帶。使用頭帶需要經過練習,否則會造成頸椎的傷害。頭帶使用的位置其實不在前額處,而是在頭頂前三分之一靠近前額處,使用時頸椎一定要呈一直線,不可以抬頭仰望,所以視角要看著地面。頭帶平時可以綁在肩帶固定帶上,在背負比較重的時候、或長時間行走時,來減少肩膀的負擔。
隊伍當中有人因為受傷、疾病無法行走,排除頸椎、脊椎損傷的患者,也可以透過頭帶跟登山杖來搬運傷患。靠著兩支登山杖,一個頭帶,一條布繩,能背動一百公斤的人,無論再遠的路,再重的傷患,都可以用頭帶把人帶到安全的地方。
頭頂著頭帶的林淵源,把我帶入布農族的傳統領域中,也是第一次聽到巡山員這個工作職位名稱,才知道有一群布農族人在自己的祖居地,為外來旅客、學術團體做嚮導背工的工作。在這十幾年中,我因為林淵源大哥的關係,有機會持續地進入山林,讓我認識也是頭頂著頭帶的一群族人,他們各自有不同的身分,高山嚮導、背工、巡山員等,雖然不同的職位名稱,相同的是他們用自己的力量在祖居地工作。
那族人們的實際工作情況又是如何呢?人們對這份工作的想像又是什麼呢?這些問題是我在二○一三年前往祖居地馬西桑的行程與一群旅人的對話中,產生的小小的疑問。那是行程的第二天早晨,當天的晨曦很美,金黃的光暈輕輕淡淡,灑在林淵源及高忠義(Tiang Tanaouna)等巡山員的身上。當我們在瓦拉米山屋前整理背包時,一位旅人看著我們說:「你們要去哪裡啊?」林淵源回答:「我們要進去大分。」旅人說:「你們要去幾天?要做什麼啊?」林淵源笑著說:「大約還要走十幾天,我們是國家公園的巡山員,要巡山。」
旅人興奮地說:「那麼好,可以邊工作邊看風景,還可以與青山綠水為伴。」一般遊客只能走到瓦拉米山屋,再往裡面走就是國家公園生態保護區,要經過國家公園管理處的許可才行。所以聽到我們可以輕鬆自在地在大自然中工作,生起羨慕之心。
與山林為伍的工作,真的如此浪漫嗎?這種對山林工作的浪漫之心,不只當代才有這樣的感覺。日治時期,鹿野忠雄的《山、雲與蕃人》書中,寫到當他聽到布農族的歌聲時,「歌聲響徹森林,引起一陣不可思議的迴響。從原始人口中流洩出的原始韻律……穿透我的靈魂。」跟著布農族上山工作的時候是他最得意,而且最有活力的時候。他認為布農族的高山嚮導具備古武士般高雅的氣宇與重視情義、負責到底的作風。族人出現在文學作品中,呈現了一股浪漫的想像。
這讓我興起寫有關於布農族族人,在傳統領域的山林中,真實的工作環境。本篇利用兩次進入玉山國家公園的行程,第一次為二○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九日的清朝八通關古道調查,簡稱為清古道行程。另一次行程為二○一三年四月十九日至四月三十日的日治八通關越嶺道路,祖居地馬西桑之行。接下來的幾篇文章以清古道為主,日治八通關越嶺道路為輔,將兩次的行程,以巡山員和背工為主題,搭配一些歷史事件及族人在山中工作的狀況。
我將從頭帶開始說起,說出山林工作的這群人,如何背出自己的山。頭帶雖然是背簍、網袋、背架的附屬器物,但在背負物品,用頭帶頂於前額時,卻可以固定貨物,不至於行走時滑落,並使行走時承受重力較為輕鬆。讓頭頂背起重物的族人,用背簍、網袋、背架,一步一步地寫出山林的故事。將〈背負重物傳訊歌〉的音律,傳唱給更多人。
穿著制服的原住民巡山員
二○一三年四月,馬西桑祖居地的行程中,參與的有高忠義、林淵源、蘇印惠,他們三位都是巡山員,而我則是跟隨著林大哥上山。雖然常有人送林大哥最新的登山裝備,他仍然喜歡用改良的鋁架背包,他特別用組合式泡棉地板當作背部的襯墊,減輕堅硬鋁架直接壓迫背部,來增加接觸面的舒適性。
這些巡山員,延續著前輩的腳步,將布農族人在深山中行動、穿梭的特殊技能,傳承下來,持續地在山林活動。從日本時代一直到戰後,布農族人就像是玉山的守護者,不透過布農族人的嚮導,外來世界的人難以親近玉山。而近幾十年來,全臺灣的高山幾乎都可以看到布農族擔任背工、嚮導的蹤跡。國家公園成立後,巡山員的工作就從原住民尋找。
泰雅族青年高旻陽曾經在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任職,他整理玉山國家公園巡山員的演變。他說:「玉山國家公園其前身必須溯及日治時期規畫的新高山國家公園」。國民政府遷臺後,設立了第一座高山型的玉山國家公園。成立時,國家公園看到東埔部落的布農族人,早在日本時代就從事背工與嚮導的工作,很多山友,也都是請布農族來當「波達」(porter),這個詞就是從日語轉音而來,可以知道族人做這個工作,從日本時代就開始。所以國家公園想要借重族人的經驗,在自己熟悉的地方工作。
在招募第一批巡山員時,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與部落的窗口是一位東埔部落的年輕人伍榮富,他的父親伍勝美,就是將于右任銅像背至玉山主峰的其中一人。伍盛美因為參與背負于右任的銅像,有了一些名氣。
二○○○年,我第一次跟隨林淵源大哥做玉山國家公園園區巡視,從東埔到玉里,第一次進入布農族的傳統領域,途中順道爬上玉山,想著布農族人參與于右任銅像的建造過程這一段歷史。族人只是做著自己本分的工作,族人不會想要了解銅像背後的意涵,于右任日記所寫的意思,日記本中《思鄉歌》:「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
玉山國家公園成立之後,也在卓溪鄉的南安部落,成立了玉山國家公園南安管理站。第一梯的巡山員,開始找卓溪鄉當地的布農族人。像是林淵源大哥,高忠義大哥。在還沒有進入國家公園,做過遠洋,去臺中梨山採過水果。林淵源先接到家裡的消息,於是就跟高忠義說:「他要回卓溪,有一份工作可以在自己的山上工作。」林淵源大哥比高忠義大哥提早加入國家公園巡山員的行列。所以八十一年玉山東部園區設南安管理站,林淵源是第一批進去的巡山員,並且持續擔任國家公園巡山員長達二十五年。
國家公園巡山的路徑,大部分都是查看古道或是一般的登山路線有無崩壞。部落的傳統聯絡道路,對國家公園來說沒有觀光和歷史價值,因而被忽視。林淵源一直想要回到他爸爸的獵場,開會時一直建議走祖居地的部落聯絡道路,尤其是馬西桑,因為這個地方,是他跟他爸爸曾經的獵場。
我們的祖居地在apulan狩獵的地方在馬西桑那邊,小時候不喜歡念書,跟著爸爸去山上,有時候在山上一待就三個月,我就來來回回,那時候還沒有結婚,有時候一個月一直待在馬西桑。(林淵源口述)
他想帶著他的大兒子一同前往,讓他以後能認路。雖然清古道行程他的兒子走完了,但林大哥最想要他的兒子,走回馬西桑獵場。他的兒子在出發前卻因身體不適,不能同行。前幾天的路程都可以感受到他失落的心情。林大哥本來也要帶高塋山來,希望他能一同上山,跟著他學習山林的知識。但是這一趟是國家公園例行性工作,沒有多餘的錢請背工,而高塋山有另外一份有薪水的背工任務,他需要這份薪水養活一家人。不可能像我一樣,只為了再次踏上祖居地,什麼後顧之憂都沒有。
二○一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大分與林大哥做祖靈祭拜的儀式,我跟林大哥吃著供品邊聊天。林大哥對於自己的兒子和想要培養的背工都不能前來,感到無奈。他說他是玉山國家公園第一代的巡山員,工作到現在也有一段時間了,也開始肩負起傳承的重任。五十三歲的他,除了擔心體力日衰,也擔心自己如何將山林的知識傳承下去。
在淚之路,用石板屋來說故事
美國將當年印地安人被迫遷徙的路徑列為國家歷史步道,稱為「淚之路」,國家公園管理局也以「不正義的旅程」(A Journey of Injustice)來定義這段歷史。(中時電子報,二○一六年四月二十三日)
回到Banitul被逼迫搬遷佳心的那一天。進入了日本昭和年代,Banitul看著拉庫拉庫溪流上方Idaza,大分、喀西帕南、大分的族人,舉家搬遷,背著衣物往山下走。Banitul覺得已經無法抵抗日本警察的勸說,在半威脅恐嚇、半勸誘的情況之下,他開始叫自己家族的男丁,背起一片一片的石板往山下走。
族人們把屋頂的石板,一片一片的放在背架,順路把石板背下去,背到卓樂附近。族人們,眼光泛淚的看著這曾經一手蓋起來的家屋,咬著牙,背起裝滿食物和衣物的背簍,默默的跟隨Banitul的腳步,走在日本人蓋好的八通關越嶺道,這條道路就像一把插入中央山脈心臟的尖刀,掐著族人們的喉嚨,逼著族人往山下遷移。
八通關越嶺道,把Banitul家族及整個拉庫拉庫溪的布農族人,從這條路上,遷移到現在卓溪鄉,山中的家就這麼逐漸湮沒於山林。
民國之後,林務局與國家公園先後接管,如今這片山區被稱為「玉山國家公園」,在古道口掛了步道解說牌,一路往深山走,沿途可見許多巒大杉與柳杉的造林地。
現在這塊土地,已經是國家公園和林務局管理,要重新蓋出石板屋,還是會處處受到限制。沿著古道進入祖先的土地,看到日本遺留下的遺址、國家公園的保育解說牌、林務局的柳杉,卻看不到布農族人自己的遺址,而過去的布農家屋就躺在遊人不曾停駐的步道之外,沒有人知道轉個彎,就可以了解布農族的歷史。
重建家屋是要讓更多人看到我們的故事。
在修復房子的過程中,充滿辛苦,與團隊一起工作的部落青年、耆老,基本上都是以務農、工地為主,族人們沒有經過正式的專業訓練。只受過一個月的石板屋傳習班訓練,這些受過訓的學員,成為石板屋工班的成員。
來到佳心後,疊石牆都是工班一塊一塊石頭疊出來。一片一片的石板,都是族人們用鑿刀一片一片自己鑿出來的,木柱的開槽,也都是工班雕出來的。辛苦的工作,是為了在祖先的土地上,蓋出布農族的房子。
這裡無法用大型機具,所有的工作都是人力才能施工。這些對雜牌軍,對非專業的族人來說,都是困難的事,但這些都在工班的努力下,一一的解決,並完成了這棟房子。工班在這件工程,增加了自信心,一件消失百年的石板建屋知識,慢慢重新接回,也重新在祖先使用過的三石灶,點燃火苗。
期待還有同樣的機會,用手建造祖先的石板屋。
族人希望能在這條路上,說出這棟家屋的故事,讓外地遊客、族人,讓後代了解到布農族人的歷史、故事。
以前講拉庫拉庫溪流域的歷史時,大部分都是講大分事件,但二十幾個重工班成員修復這棟房子,每個人都成為故事,用自己親身參與蓋房子,把自己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我們現在做的都是全新的開始。
在一些文獻中曾經提到,布農族人似乎將家屋視為一個孕育生命的子宮,它的出口,一個在屋頂的天窗,是對天的,一個出口,在正面牆的門,這是人日常出入的。「Bunun」這個字的意思是「人」,也指「未出殼之雛雞」、「未離巢的蜂」。那麼人相對於家屋,有如蜂相對於巢,孵化中的雛雞相對於蛋殼。我們都像是「未出殼之雛雞」、「未離巢的蜂」慢慢回到孕育生命的子宮,回到自己的家,說出自己的故事。
在mai lumah舊家屋、mai-asang舊家園,即使很多家屋都查不出是誰家的了。但那裡是我們布農族人的信仰與歸屬,如何保住以前老人家山上住過的地方,對於布農族人的自我認同是很重要的事。
我們一同與Istasipal家屋修復的族人,在淚之路上,讓回家的一步一步往前行,在祖靈的呵謢和叮嚀中,逐步踏實的前進。這些工作是為了重新連結卓溪鄉布農族人與祖居地的牽繫,追尋歷史記憶。
透過蓋石板屋,重現百年前布農族人山居生活地景,傳承先人與環境互相適應創造實踐的生存智慧。
目次
推薦序
作者序
第一篇 用頭帶背起一座座的山
從頭帶開始說起
頂著頭帶的領路人
背著網袋的勇士
背著鋁架的高山背工
穿著制服的原住民巡山員
用頭帶背負夢想
第二篇 百年碑情
重回百年前的山林
喀西帕南殉職者之碑
大分事件—殉職者之碑
戰死地之碑
唱出歌聲,回到石板屋
碑從中來
會說話的碑文
第三篇 淚之路
尋找Banitul的家園
撿拾祖先的石板痕跡
畫出石板屋的藍圖
背起一片片的石板
修復石板屋
淚之路上的報戰功
重新點燃火苗
在淚之路,用石板屋來說故事
後記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