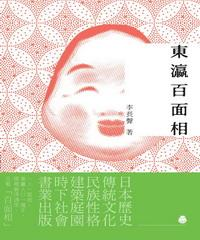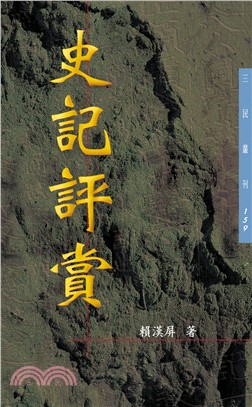東瀛百面相(電子書)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李長聲與知日 止庵
談起李長聲的文章,一般總要提到「知日」。但怎麼才算知日呢,他不以此自我標榜,筆下向來不大涉及;論家卻也很少為我們解釋清楚。最近讀了李長聲的五卷選集,覺得知日的確可以概括其特色,雖然確切地説那是「李長聲式的知日」。不管怎樣先得搞明白知日一詞的含義,否則只貼個標籤既沒意思,也沒用處。
知日常常與「仇日」、「哈日」相提並論,好像只是程度或火候的問題,是在兩個極端之間執中似的。讀了李長聲的書就知道,知日與仇日並不在同一層次,甚至不在同一領域;知日與哈日同樣不在一個層次。仇日根本不知日;哈日則是局部或膚淺地知日,這樣的知約莫等於不知。好有一比是盲人摸象,摸着腿的就説大象只是條腿,沒摸着腿的便不知道大象有腿。
相對於仇日、哈日,知日要困難得多,麻煩得多。仇日是泛泛的,一概的;哈日不全面,不深入,不客觀冷靜;而知日總是具體的,從細微處入手,卻不淺嘗輒止,以偏概全。知日有賴於積少成多,將一個個具體題目彙總起來,由質而量,再由量而質。這裡又有個因果關係:他不是為了顯示知日而寫那些文章,而是因為那些文章我們才説他知日。所以知日這名目並不能隨便派送。
知日首先是工夫問題,其次是態度問題,最後是理念問題,三者缺一不可。知日總是一手的。哈日雖然也是一手的,但未免隻手遮天;仇日則二手就行,抑或連二手也不需要。有時知與略知或不知的差別就在些微之間,但這起始一步須落到實處,往後的路才走得穩當。且從李長聲的書裡找個例子:「阿城在《常識與通識》中談到吃,説『若到日本,不妨找間餐館(坐下之前切記估計好付款能力),裡面治河豚的廚師一定是要有「上崗證」的。我建議你第一次點的時候,點帶微毒,吃的時候極鮮,吃後身體的感覺有些麻麻的。我再建議你此時趕快作詩,可能你此前沒有作過詩,而且許多著名詩人都還健在,但是,你現在可以作詩了。』如果讓我來建議,那麼,你最好在進店之前估計好付款能力,此事很容易,非常大眾化的『虎河豚亭』門口就擺着菜樣,惟妙惟肖,明碼實價是日本人經商的一大特色。坐下之後再起身走人,不大合乎常識或通識,雖然是老外。」我因想起孔子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末了那個「知」説的正是知日的「知」。
知日需要知道得多,但知道得多並不一定知日。知日先得去成見。仇日的成見往往來自別人,哈日的成見則來自一己。知日卻是不預設立場,也不一定有總的結論,至少不匆匆忙忙地下結論。這裡另外舉個例子。前幾天我看報上摘錄某本書的片斷,寫到下關有云:「在日本,很少看到中文標識和説明書,『日清講和紀念館』特别使用中文,可以理解為對中國參觀者的關照,也可以理解為某種剌激。因為這個紀念館,對於中國人有着不同的意義。」我就想李長聲肯定不寫類似的話,他見識得多,所以不至於想多了。知日是止於詮釋,而不過度詮釋。李長聲曾自謙地説:「我已活過周作人撰寫《日本之再認識》(1942)的年齡,在日本生活的年頭也比他長得多,猶不能忝列他所説的少數人,即『中國人原有一種自大心,不很適宜於研究外國的文化,少數的人能夠把它抑制住,略為平心靜氣的觀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傷的時候,也就不能再冷靜了』。」不同的人自尊心的閾值有所不同,閾值過低,自尊心就成了自大心,隨處可能把自己傷了。
李長聲説:「這種寫作大概客觀上也算是一種文化交流。或許有助於了解,但關係的好壞未必取决於了解或理解。兄弟鬩於牆,彼此很了解;理解萬歲,並非萬能。文化交流在歷史上也帶來過戰爭,最典型的例子不就是日本與中國麼?」知日如果説有什麼目的,那麼就在獲得了區別於包括仇日、哈日之類不知的知,亦正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相合。
然而要説李長聲寫文章純係無為而為,倒也未必。譬如他在書中曾提到我所説的「李長聲寫日本有一種俯視的態度」。我與他相識多年,每每口無遮攔,我的本意是仇日很容易,表示蔑視更是習慣成自然,舉我身邊朋友的例子,有好幾位愛讀書也愛出門旅遊,卻一律略過了日本。正為如此,即便這蔑視是對的,也不如緘口不言,以免隨了大流。現在讀了李長聲的五卷書,打算對自己所説略作訂正。知日與仇日風牛馬不相及,所以他寫文章,於仇日了無牽涉,倒有針對哈日予以匡正之意。曾有記者在採訪李長聲之後寫道:「他把自己定位在哈日與學者之間,也並不總寫ABC。……他表示,哈日族如果想提升一下,由哈進入知,知道日本、了解日本的話,不妨看看他的小文章。」他自己則説:「我行文有一個毛病,那就是通篇好話,得便總提醒一下,事情還有另一面,況且寫的是人們常説具有二重性的日本,點到為止,卻常被讀成了譏諷。」李長聲不贊同本尼迪克特將二重性説成日本人的特性,更不贊同照搬當初本尼迪克特的説法來看當今的日本人,在他看來無論哪個民族都有二重性,但這裡卻是擔心哈日的人輕率地把日本看成一重的。是以我所謂「俯視」,實乃「不仰視」。至於何以能做到不仰視,他自己歸結為兩點:一是「得益於讀書」,「日本人寫的書,寫他們自己,能夠為我們的觀察提供個高度」;二是「把事物置於歷史之中看」。
李長聲很推崇周作人的日本論,有云:「周作人寫的是隨筆,長也不過萬把字,那一條條真見,若到了西洋人手裡,可以洋洋灑灑成一本又一本論著,雖然多是填充料,卻能譲中日兩國人歎為觀止。」李長聲走的也是這個路子。雖然周作人説他的四篇《日本管窺》是「關於日本的比較正式的論文」,其實還是隨筆寫法,而李長聲所作多接近於周氏《日本的小詩》、《談混堂》、《緣日》和《關於日本畫家》那一類題目更具體的文章。李長聲説,自己「只是對日本文化有一些觀感罷了」;還説:「我寫的是隨筆。……又自我規定為知識性與趣味性,也就是有益而有趣。有益而無趣,難以讀下去;有趣而無益,不讀也罷。還需要點淡泊,對於熱血的讀者來説卻近乎潑冷水。」他寫文章不作高大正統的議論,因為別人説得多了;不簡單傳播無見解、無感受的信息,因為網上可以查到,此其獨出心裁處,亦其生命長久處。
李長聲一九九○年起在《讀書》上發表文章,迄今不過四分之一世紀,其間卻已跨越兩個不同的時代,雖然他的寫作是「吾道一以貫之」。如今在互聯網上,信息的更新較之過去迅速得多,信息的查詢也便利得多。對於一位作者來説,寫作到底因此變得容易了,還是困難了;應該多寫,還是少寫;有些內容需要寫,還是不必再寫,都是無法迴避的問題。「信息爆炸」之際,只有真正屬於個人的聲音才有可能不被淘汰。那種僅僅倚仗語言優勢的「編譯」,同樣很容易被替代。
李長聲説:「所寫內容局限於文化,因而逝者如斯,讀來似乎也並無過時之嫌。」歸根到底,信息不是文化,或者説,文化高於信息。也只有在這個層次才可以談知日。
李長聲曾記錄他與作家水上勉的談話:「我問,日本文學為什麼那麼簡素呢?
目次
序 李長聲與知日(止庵)
優雅的牛車
009 假設……就會有別樣日本
013 優雅的牛車
017 鹹蘿蔔的禪味
021 文章讀本八十年
027 二千年友誼的畫皮
034 小和尚從哪裡來
044 古典四大戲
053 江戶文化東京人
057 恩仇何曾一笑泯
075 日本人與英語
080 日本猶須中國化
084 踏繪與火眼金睛
089 老二們
092 話說平清盛
096 也讀《倭人傳》
沒跟你說我懂日本
103 作家與酒
108 粹
112 蛛絲能承受之重
116 心醉橫山成大觀
120 行腳與旅行
128 浮世繪的糾結
132 桃太郎
138 活吃龍蝦
143 頭頭皆是道
153 橫排與直排及日本人的二重性
156 莫須有的日本論
160 沒跟你説我懂日本
167 關於《菊與刀》的隨感
170 知書不答禮
173 酒館
177 晚酌
極樂的庭園
183 緣廊的妙趣
187 一書在手遊奈良
191 枯水枯山費苦心
196 稻草繩文化
200 極樂的庭園
204 看園
208 天皇家的祖墳
212 東京城裡墓地多
216 一柱摩天樹信心
220 櫻花
下流的幸福生活
225 少女癖
230 AV女優
234 警察的兩難
238 女孩兒叫啥名
244 年輕人不好當
247 讀書的寂寞
249 松下幸之助的「經營教」
253 下流的幸福生活
258 熟年離婚
262 讀書術
改變了生活的編輯家
269 漱石和嫂子
273 學譯談藝
281 惜櫟莊
285 舊書的標價
290 大江健三郎的私小説
297 飲食男女村上龍
303 書有金腰帶
309 巧騙讀者的推理小説
315 關於多崎作的作
319 書評……書為誰評
323 村上春樹與雷克薩斯
327 城巿中的推理‧推理中的城市
332 曖昧的川端康成
337 舊書店血案
342 改變了生活的編輯家
347 暢銷書是怎麼回事
350 日本的武士小説
書摘/試閱
優雅的牛車
假設……就會有別樣日本
十五世紀歐洲諸小國競相發展,猶如中國春秋無義戰,鏗鏗鏘鏘,一片片海洋都被他們佔了去。假設……假設中國少一點皇恩浩蕩的念頭,不到處買好,汲汲於利,鄭和之後繼續下西洋,稱霸海上,或許不至於如今才有了一艘航母,卻招人説三道四。
歷史沒有假設,人死不能復活。但分析歷史,總結歷史的經驗或教訓,其實就是在假設,雖然常難免事後諸葛亮之嫌。保阪正康著《假設的昭和史》,「考察在某個史實的某個斷面、某個局面若另有選擇,史實會變成什麼樣呢」。上下兩卷,截取一九二○年代至一九四○年代的日本歷史提出了四十九個假設,其中只要有幾個當年不是假設的話,興許就會有一個別樣的日本。如:假設日本不退出國際聯盟,假設共產黨幹部不在獄中變節,假設二‧二六造反部隊佔領了皇宫,假設德國駐華大使為日中斡旋成功,假設日本研製出原子彈,假設日本被美蘇分割佔領,假設日語改用羅馬字……
一九二六年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一九二八年張作霖從北京乘火車退回奉天(瀋陽),車將抵達,發生爆炸,這位東北王傷重不治,而跟隨他乘車的日本人顧問,叫町野武馬,卻已在天津下車而去。町野説,他在天津下車,是前一天張作霖命令他協助張宗昌抵抗北伐軍。一九六一年町野曾經對作家山本有三口述歷史,但三十年過後開封,並沒有多大的史料價值。炸死張作霖,這一事件始作俑昭和年代的軍事主導體制,「在哪裡提出假設才能看出史實的背面呢」?保阪正康認為,町野在爆炸之前下車,對於歷史具有頗大意義。假設他知情,車到天津就逃之夭夭,説明炸死張作霖是陸軍當局的意思;假設他不知情,冥冥之中躲過一劫,那就是關東軍的瘋狂,為掃除有礙於製造滿洲國的張作霖,賠上老前輩(町野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與事件當時的關東軍參謀長齊藤恆同期)也在所不惜。
對往事如煙的歷史作出假設,需要有學識、史觀、良知。假設往往就是編故事,或許更屬於歷史小說家的擅場。例如台灣小說家高陽在歷史小說《玉壘浮雲》中替張學良假設;與張作霖同歲的町野武馬,雖有軍籍,但跟日本陸軍的關係不深,自從三任共九年任期滿後,改充張作霖的私人顧問,每年
又有個俄國小説家,叫德米特里‧普羅霍洛夫,二○○○年與人合著《GRU帝國》,假設皇姑屯事件乃蘇聯情報機關的所為。二○○五年英國作家張戎和丈夫聯手出版了一本《毛》,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炸死張作霖事件一般認為是日軍幹的,但是據蘇聯情報機關的資料,最近清楚了,實際是按照斯大林的命令,Naum Etingon(此人後來參與暗殺托洛茨基)策劃的,偽裝成日軍的勾當。(據日譯本轉譯,但不知日譯準確與否)所謂據蘇聯情報機關的資料,恐怕不過是取自普羅霍洛夫的假設。二○○六年《毛》日文版上市,這段話引起日本媒體注意。不過,普羅霍洛夫始終未拿出史料證據,而且日本沒有一個史學家對此説感興趣,鬧閧的都是些論客。
説來有些歷史就是當時的假設造成的。日本投降後,蘇聯、英聯邦等都要把天皇列為頭號戰犯,但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假設:處刑天皇可能會引發遊擊戰,因而不可傷及他一根毫毛。經麥克阿瑟同意,一九四六年昭和天皇巡行各地,到處都受到狂熱的歡迎,麥克阿瑟不由地擔心出現反佔領軍傾向,又命令天皇好好呆在皇宮裡。天皇有退位之意,麥克阿瑟耳聞,悄悄傳話:那是不可能的。保阪正康假設昭和天皇真的退了位,就可以明示天皇對那場戰爭心懷多麼強烈的自省之念,日本戰敗後社會就不只是單純表面上比戰前有所改變,而且包括太平洋戰爭在內的昭和這一時代的歷史意義也大有變化。
一個史實的形成有前因,還有當時的環境,回頭再來一次,假設未必能變成現實,未必就做得更好。保阪正康的假設大都不是從時代所具備的現實條件提出來的,一廂情願,希望那麼一來就避免了戰爭,歷史的進程會一路和平。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向中國出兵七十餘萬,其中也有人退伍回鄕,講述侵華故事,使陸軍部擔憂會暴露「皇軍」所作所為的真相,於是草擬了一紙關於指導、取締還鄕軍人言行的通令,其中列舉不當的誇誇其談,如戰鬥的時候最高興的是掠奪,參加戰爭的軍人挨個是殺人搶劫強姦的犯人,戰場上長官下令卻沒人冒着彈雨往前衝。保阪正康寫道:士兵們誇張、虚偽、隱瞞事實的證言也延續到戰後社會。被虛偽證言洗腦的國民當中,至今還有人不相信日軍的野蠻行徑,公然説那場戰爭敗給了美國但戰勝了中國什麼的。假設陸軍部、媒體當時公佈了這樣的內部文件,有勇氣糾正軍紀……讓老百姓知道戰爭另一面,打下去的能量就會一下子變小。這樣的假設,完全忽略了軍國主義的本質,甚至要覺得作者過於天真,甚而有點膚淺了。
保阪正康是紀實作家,專攻日本近現代史,著述頗豐。自二○○六年在週刊雜誌上連載《昭和史溯往》,歷史五年餘,結集第十二、十三卷即《假設的昭和史》。
優雅的牛車
近幾年每當晚秋去一趟深圳,參加讀書月活動,以致對於我來説,深圳就是讀書。今年除了讀書,還參觀了十月剛剛開館的望野博物館,不消説,精彩輝煌。聽説是個人收藏,更不禁想像值多少錢。最吸引我的,是一輛陶牛車,北齊年間的。那頭牛塑造得碩壯敦實,四條腿短得只是個意思,很有點當代藝術的趣味。悠悠牛車,惟穩惟緩,坐上去一定很安逸,不思再變革什麼。
四十多年前下鄉在延邊,常看見牛車,木輪鐵箍,車架子簡陋,老黃牛不畏鞭策,那樣子好像永遠也走不到目的地。離開延邊後再沒遇見過牛車,來在日本居然又得見。譬如京都三大祭之一的葵祭,年年五月裡舉行,招搖的首先是牛車。黑牛披紅掛綵,車篷垂掛紫藤花,兩個穿一身紅的女孩兒左右牽長韁,牛車兩側有幾個渾身縞素的男人挾持。總計五百多人遊行,説是像一幅王朝畫卷,如實再現了王朝貴族的優雅。王朝指平安時代(794-1185,京城在平安京,即京都),葵祭是潔齋三日的國家祭典。《源氏物語》描寫光源氏參與這種修禊行列,皇太子遺孀六條御息所是他的戀人,偷偷去觀看,而光源氏結髮之妻葵上懷孕在身,也出來散心,車填牛隘,已無停車位。家僕們仗勢,硬是把六條妃子的兩輛車擠了出去,並且折損了上下車的木凳。現今有的地方搞什麼祭,也有車遊行,卻是人推拉,其實本應是牛車,但近年來日本只有肉牛奶牛了,找一頭能駕車的牛已經是難事。
日本飛鳥時代(592-710)以前受六朝影響,奈良時代(710-784,京城在奈良,即平城京)以後受唐影響。即為受影響,就不會是同步,日本乘用工具的發展進程跟中國差不多,但時間上錯位,好像往昔男女走在街上,不是並肩而行,女人要落後一步。八世紀後半編成的《萬葉集》裡出現車:「戀如野草積七車,車車出自我心窩」。這車是人力車,九世紀初駕上牛牽引,起先是貴族女性的專車。走起來四平八穩,男人們艷羨,也競相享用。八九四年朝廷發出告示,「男女有別,禮敬殊著」,禁止不分貴賤地乘坐牛車。《延喜式》一書記載九世紀末禮儀風俗,對女性乘坐的牛車樣式、服飾等規定甚詳。九九九年朝廷又對於六位以下的卑位凡庶者嚴加禁止,坐牛車成為五位以上的特權。器物因人而異,車形按位階與俸祿而不同,各種各樣的牛車成為車主身份的視覺指標。牛車相遇,根據身份差異,或者停車讓路,或者卸牛下車,蹲踞或平伏。平安時代的繪畫、文學描寫牛車很多見,譬如後白河天皇敕繪的《年中行事繪卷》、清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前半的小説《平家物語》寫平家惡行之始:攝政藤原基房的車隊與平資盛相遇,資盛不下馬行禮,被基房的家僕拽下馬。資盛的爺爺平清盛得知,派三百騎襲擊基房,把幾個隨從拽下馬,剪掉髮髻,並撕毀牛車簾子。
北齊陶牛車的車廂後面有出入口,而日本牛車從後面上,前面下。下車時牛童先把牛卸下,軛觸地,人踏木凳下來,然後將軛架在木凳上。女性乘車,把裳裾從車簾下露出來,讓路人知道是女性乘車,也藉以炫耀或誘惑。《源氏物語》中,六條御息所深坐在車裡,只略微露出袖口、裳裾、汗衫等,顏色搭配很得當,且明顯有微行之意。
天皇在位時不乘牛車,坐沒有輪子的輿,由眾人肩扛,前呼後擁。退位的太上皇乘坐有輪子的人力輦車或者牛車。美在細節,坐牛車才可以細緻入微地觀賞世界,平安貴族的雅文化乘着牛車來。但牛車在路上吱嘎作響,庶民聽來是噪音。平安時代後期創作的裝飾性圖案有車形紋、源氏車紋。車形紋是整個車,以《源氏物語》為題材的源氏繪的車紋只表現車輪。東京國立博物館珍藏一個十二世紀的泥金螺鈿盒,是國寶,上面畫了許多半浸在流水中的車輪。這叫半輪車,非常圖案化,卻源於生活,木製車輪需要浸在河水中保養。所以,旅遊日本,若看見酒館外面擺設一個車輪子,莫聯想田園風光,那車輪象徵平安時代,是一種優雅。京都市的市徽就是一個車輪子。車輪圖案在和服、日常用品上很常見,買紀念品可不要以為車輪子圖案很土氣喲。
乘坐工具發展史:奈良時代用的是輿,平安時代乘牛車,鐮倉時代(1185前後-1333,執掌國柄的幕府在鐮倉)、室町時代(1338-1573,幕府在平安京的室町;自一四六七年的後期亦稱戰國時代)騎馬,江戶時代(1603-1867)坐駕籠,明治時代(1868-1912)出現人力車等。牛車是乘坐工具發達的頂點,式微後興起的不是馬車,更不是汽車,而是駕籠,類似於中國的轎子,歷史開了倒車。
中國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紀就利用馬車了,但日本人好像直到一八六○年出使美國才見識馬車似的,引進來不久又讓位給自動車。為什麼從中國拿來牛車,不拿來馬車呢?許是車文化經朝鮮半島傳入,而那裡始終未發展馬車。看見延邊朝鮮族趕牛車,優哉游哉,對馬車不感興趣,聽憑大鞭子一甩嘎嘎響,我也曾驚奇。
鹹蘿蔔的禪味
説到中日關係,兩國都津津樂道遣唐使。唐太宗貞觀四年,即六三○年,舒明天皇向唐朝派出使節以及留學生、留學僧,從此二百多年間,有成行的,也有未能成行的,總計遣唐二十回,恨不能把我大唐的文物制度統統搬回去。到了唐昭宗乾寧元年,菅原道真被任命為大使,本該率領船隊第二十回赴唐,卻奏請宇多天皇緩行。理由有二:一是唐朝已衰敗,名存實亡,無須再學了;二是航路阻遏,九死一生,不值得冒險。大概頭一條理由很有效,所以第十九回遣唐的副使小野篁望海生畏,稱病不行,被處以流放,而這次准奏。時當八九四年,學生學歷史,為記住這個年代,諧音為白紙,意思是取消、撤回。九○七年唐朝滅亡,遣唐也真就廢止了。
大海茫茫,出航確實極危險。留學僧圓載在唐朝鑽研四十年,八七七年攜萬卷經典歸國,不幸船破,葬身於波濤。不過,海上船帆從不曾減少,而是越來越多,商人和僧侶冒死往來。圓載滯留唐朝時,日本朝廷曾兩度給他送金子,應該是這些人捎帶的罷。商船不絕於途,國家也就用不着遣使,那是要傾其國庫的,耗資巨大。清末黃遵憲在《日本國志‧鄰交志》中寫道:「有宋一代,聘使雖罕,而緇流估客往來日密。」緇流是取經或傳經的緇衣僧侶,估客是唯利是圖的商人,他們取代了國家行為。南宋被蒙古鐵騎征服,有更多僧侶亡命東渡,不僅帶來了清規戒律,也帶來日常生活。誠如周作人所言:「日本舊文化的背景前半是唐代式的,後半是宋代式的。」貴族、寺院等階層崇尚從中國舶來的文物,卻叫作「唐物」,可能也讓人誤以為這唐就是唐代,不知有宋。
正是禪宗興盛之時,入宋或渡日大多是禪僧。南宋傳來水墨畫,禪寺將其立體化,在地上創作出沙盤也似的日式園林枯山水。飲茶始於中國,宋代茶及酒鹽專賣,並輸出海外。日本茶道用抹茶,這種茶就是宋代定型的。八一五年出使過唐朝的僧永忠向嵯峨天皇獻過茶,是為日本正史上關於飲茶的第一條記錄,但真正讓日本人吃起茶來的是榮西。他兩度到南宋學禪,一一九一年歸國後開山日本臨濟宗。還帶回茶種,在雲仙寺(在今佐賀縣)附近種植,寺院由此愛種茶。榮西撰寫了日本第一本茶書《吃茶養生記》。中國文化主要由僧侶引進日本,寺院堪為最先進的學問機構。禪寺有「茶禮」。武士、貴族、文化人出入,看見和尚們裝飾了華麗的中國文物,在禪房裡飲茶,一定覺得酷。照葫蘆晝瓢,在家裡擺設中國的書畫陶瓷學喝茶。也曾坐在椅子上吃茶,到底坐不來,逐漸按日本生活方式設計了茶禮。飲茶在中國是日常的,世俗的,日本把茶和禪一起拿了來,日常化、世俗化之前,先加以精神化,這或許是拿來外國文化的一個手法。茶從禪寺傳出來,被誇大解釋,演變為世間的茶道。非同尋常的事物就容易成「道」,日本人給茶附加了太多的精神性、宗教性感覺。由於戰亂,王朝的建築及收集的唐物焚燬殆盡,厭世空氣籠罩,吃茶的道具也只好採用日本製造了,茶就枯寂起來。僧珠光是枯寂茶的先驅,傳説他隨一休參禪,領悟了茶禪一味的境界。珠光的弟子宗珠曾題畫:「料知茶味與禪味同」。珠光的徒孫武野紹鷗及其弟子利休都曾在大德寺參禪,禪的思想被充作茶道的理論支柱。明治時代否定江戶時代的價值觀,吃穿住等生活環境急劇西方化,茶道衰微。為求活路,基本上變成禮儀修行,並普及大眾。戰敗後,茶道更搞成表演藝術,還有點神秘兮兮。尤為女性所好,會做點茶道、花道,顯得有女人味,看着就賢惠。
和尚吃什麼,人們自古就好奇,而禪宗尤其講究吃。平常人家喝的「建長汁」,是用蘿蔔、豆腐、魔芋之類做的湯。傳説七百五十年前,南宋禪僧蘭溪道隆在鐮倉開山建長寺,某日,小和尚把豆腐掉在了地上,不知所措,蘭溪禪師就用這碎豆腐,再加上蘿蔔絲什麼的做成湯。
日本菜餚幾乎離不開蘿蔔,魚生用蘿蔔絲墊底,烤魚用蘿蔔泥調味。醃鹹菜基本是蘿蔔,各種各樣的鹹蘿蔔在市場裡擺了一架。這種鹹蘿蔔叫「澤庵漬」,可用來下酒,但有人討厭它的味道。澤庵者,江戶時代臨濟宗和尚澤庵宗彭也,創建東海寺。第二代將軍德川家光來訪,拿出鹹蘿蔔招待,將軍為之命名。十八世紀從江戶傳到京都、九州,遍及日本,自不免「鹹吃蘿蔔禪操心」。
江戶時代初葉的一六五四年,禪僧隱元隆琦從福建來到日本,建萬福寺,開山黃檗宗,他帶來扁豆、孟宗竹、西瓜、蓮藕等。黃檗宗寺院的素菜也傳到市井人家。素菜卻要做出肉味來,只怕心思仍然是葷的。中國烹飪好用澱粉和油,而日本人學會炒與炸,「料理」至今少油水。好些東西如豆腐、納豆都是由禪僧帶入日本,先普及寺院,再傳入民間,不免染上了禪味,或附加了禪味傳説,所以我們常覺得日本有禪味兒。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