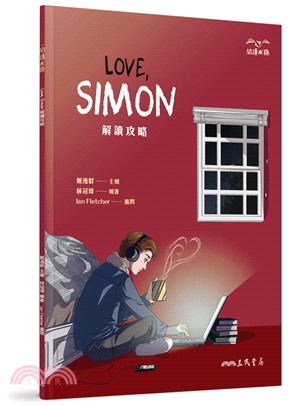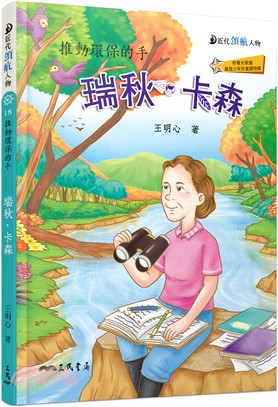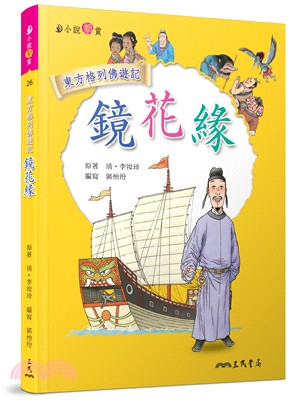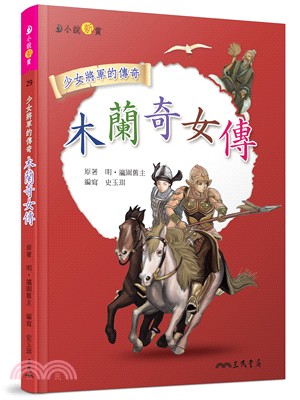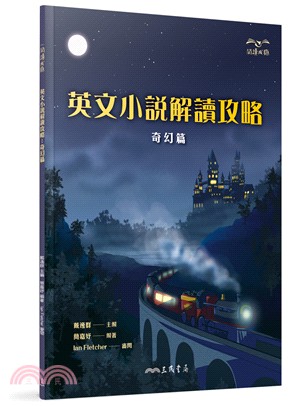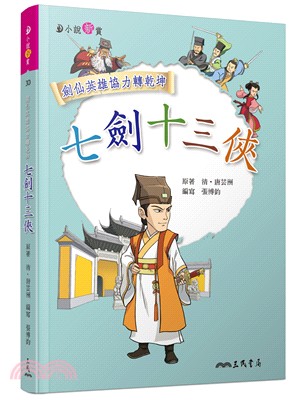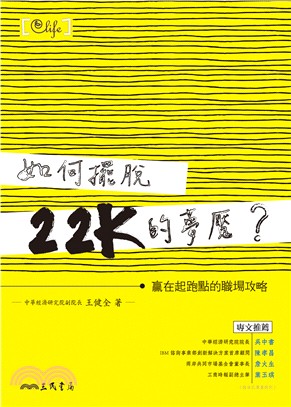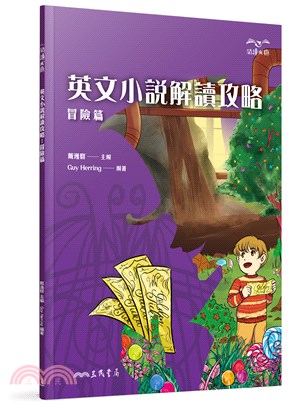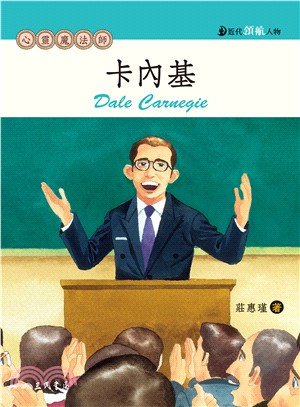藝術怪獸:女性主義藝術中那些張狂不羈的身體
商品資訊
系列名:Passion系列
ISBN13:9786267063798
替代書名:ART MONSTERS: Unruly Bodies in Feminist Art
出版社:網路與書
作者:蘿倫・艾爾金
譯者:黃懿翎
出版日:2024/11/01
裝訂/頁數:平裝/456頁
規格:20cm*14cm*2.6cm (高/寬/厚)
庫存:2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20 點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純潔與猥褻、壓抑與挑釁
女性主義藝術的叛逆之美
《漫遊女子》作者最新力作
「女人必須變成怪獸,才能成為藝術家。」——杜若西雅.譚凝,畫家、雕塑家
數百年來,女性藝術家面臨各種困境。除了受父權和厭女社會的壓迫,還須抵抗身旁與心中的「家中天使」,這種端莊賢淑、渺小安靜的女性典範要求她們溫柔奉承、成就丈夫,即使犧牲自己的創作也在所不惜。
成為蕙心蘭質的母親,或驚世駭俗的藝術怪獸——女性藝術家須在兩者間做出決擇。
作者展現了文化評論家的實力,巧妙地串連不同領域的作品:從維吉尼亞.吳爾芙的小說到車學敬的《聽寫》、從凡妮莎.貝爾的肖像畫到伊娃.海瑟的繩索雕塑。她們冒著被視為怪獸的風險,用身體與想像力挑戰社會中的嚴格界線,探索、創造她們的美、溢踰、理想、情感。
在作者蒐集、拼貼、混搭、編織而成的敘事中,女性主義藝術的發展或許充滿挑戰,但也催生了豐富多彩的藝術新語彙。
國際好評:
蘿倫・艾爾金改變了你看待周圍世界的方式⋯⋯這是一場感官的藝術史驚奇之旅。——《時尚》
博學、挑釁且兼容並蓄。——《紐約客》
充滿好奇,總是在探索的路上⋯⋯一位敏捷的作家⋯⋯細緻入微,生動鮮明。——《紐約時報書評》
激進⋯⋯深思熟慮且細緻入微⋯⋯《藝術怪獸》結合了關於怪獸與藝術的廣泛討論。——《衛報》
探討了歷代藝術家豐富的傳統,艾爾金審視了女權主義者如何面對講述自身經歷和表達身體語言的問題。《藝術怪獸》以其豐富的歷史研究和評論,向蘇珊.桑塔格和瑪姬.尼爾森等作家致敬。——《芝加哥書評》
生動⋯⋯在艾爾金氣場之中隨行令人陶醉。——《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介紹視覺藝術的領域中,女性主義趨勢的完整指南,使許多曇花一現的事件又充滿活力地重現⋯⋯極具啟發性。——《電訊報》
《藝術怪獸》提供迷人的洞見,展示女性如何打破歷史重負,以她們獨特的聲音構建了一種新語言。——《沒有男人的藝術故事》作者凱蒂.赫塞爾
國內推薦:
李根芳(師大翻譯所教授)
陳紫吟(女性主義者)
盧郁佳(作家)
盧省言(台師大歷史系助理教授)
謝佩霓(藝評人、策展人)
女性主義藝術的叛逆之美
《漫遊女子》作者最新力作
「女人必須變成怪獸,才能成為藝術家。」——杜若西雅.譚凝,畫家、雕塑家
數百年來,女性藝術家面臨各種困境。除了受父權和厭女社會的壓迫,還須抵抗身旁與心中的「家中天使」,這種端莊賢淑、渺小安靜的女性典範要求她們溫柔奉承、成就丈夫,即使犧牲自己的創作也在所不惜。
成為蕙心蘭質的母親,或驚世駭俗的藝術怪獸——女性藝術家須在兩者間做出決擇。
作者展現了文化評論家的實力,巧妙地串連不同領域的作品:從維吉尼亞.吳爾芙的小說到車學敬的《聽寫》、從凡妮莎.貝爾的肖像畫到伊娃.海瑟的繩索雕塑。她們冒著被視為怪獸的風險,用身體與想像力挑戰社會中的嚴格界線,探索、創造她們的美、溢踰、理想、情感。
在作者蒐集、拼貼、混搭、編織而成的敘事中,女性主義藝術的發展或許充滿挑戰,但也催生了豐富多彩的藝術新語彙。
國際好評:
蘿倫・艾爾金改變了你看待周圍世界的方式⋯⋯這是一場感官的藝術史驚奇之旅。——《時尚》
博學、挑釁且兼容並蓄。——《紐約客》
充滿好奇,總是在探索的路上⋯⋯一位敏捷的作家⋯⋯細緻入微,生動鮮明。——《紐約時報書評》
激進⋯⋯深思熟慮且細緻入微⋯⋯《藝術怪獸》結合了關於怪獸與藝術的廣泛討論。——《衛報》
探討了歷代藝術家豐富的傳統,艾爾金審視了女權主義者如何面對講述自身經歷和表達身體語言的問題。《藝術怪獸》以其豐富的歷史研究和評論,向蘇珊.桑塔格和瑪姬.尼爾森等作家致敬。——《芝加哥書評》
生動⋯⋯在艾爾金氣場之中隨行令人陶醉。——《泰晤士報文學副刊》
介紹視覺藝術的領域中,女性主義趨勢的完整指南,使許多曇花一現的事件又充滿活力地重現⋯⋯極具啟發性。——《電訊報》
《藝術怪獸》提供迷人的洞見,展示女性如何打破歷史重負,以她們獨特的聲音構建了一種新語言。——《沒有男人的藝術故事》作者凱蒂.赫塞爾
國內推薦:
李根芳(師大翻譯所教授)
陳紫吟(女性主義者)
盧郁佳(作家)
盧省言(台師大歷史系助理教授)
謝佩霓(藝評人、策展人)
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
蘿倫・艾爾金LaurenElkin
《漫遊女子》作者,該著作為二〇一七年《紐約時報》百大注目好書,二〇一六年《衛報》、《觀察家報》、《金融時報》年度好書,並入圍美國筆會藝術評論獎。她探討藝術、文學、文化的文章常見於《倫敦書刊評論》、《紐約時報》、《格蘭塔》、《哈潑》、《世界報》、《搖滾至尊雜誌》、《弗列茲》等刊物。她也是傑出的翻譯工作者,最新譯作為西蒙.波娃未出版的小說《形影不離》。旅居巴黎二十年後,現居倫敦。
譯者簡介
黃懿翎
中興外文與靜宜生態所畢,譯有《像山一樣思考》、《女性主義與基督教要點指南》、《黃金的傳奇史》、《在候診室遇見佛陀》、《為衝突立界線:有效溝通,創造改變》、《神聖生態學》,現為專職翻譯。
蘿倫・艾爾金LaurenElkin
《漫遊女子》作者,該著作為二〇一七年《紐約時報》百大注目好書,二〇一六年《衛報》、《觀察家報》、《金融時報》年度好書,並入圍美國筆會藝術評論獎。她探討藝術、文學、文化的文章常見於《倫敦書刊評論》、《紐約時報》、《格蘭塔》、《哈潑》、《世界報》、《搖滾至尊雜誌》、《弗列茲》等刊物。她也是傑出的翻譯工作者,最新譯作為西蒙.波娃未出版的小說《形影不離》。旅居巴黎二十年後,現居倫敦。
譯者簡介
黃懿翎
中興外文與靜宜生態所畢,譯有《像山一樣思考》、《女性主義與基督教要點指南》、《黃金的傳奇史》、《在候診室遇見佛陀》、《為衝突立界線:有效溝通,創造改變》、《神聖生態學》,現為專職翻譯。
目次
斜線
第一部 怪獸理論
天使與怪獸
承受那份重量
手摸的觸感
粗俗之物
斜線/美學
論感覺
論闡述
第二部 女性的職業
畫中天使
西比爾與割畫者
極端世代就需要極端女英雄
很難對話的議題
迦梨,亮出你的牛排刀吧
燒吧!
第三部 作品的身體
身體這隻怪獸
身體意識
融合
她的身體是個問題
虛空畫
令人厭惡
火的本性
凱西.艾克是我的賤斥
肉
為創作而毀壞
那之後
致謝
圖目錄
參考書目
註解
索引
第一部 怪獸理論
天使與怪獸
承受那份重量
手摸的觸感
粗俗之物
斜線/美學
論感覺
論闡述
第二部 女性的職業
畫中天使
西比爾與割畫者
極端世代就需要極端女英雄
很難對話的議題
迦梨,亮出你的牛排刀吧
燒吧!
第三部 作品的身體
身體這隻怪獸
身體意識
融合
她的身體是個問題
虛空畫
令人厭惡
火的本性
凱西.艾克是我的賤斥
肉
為創作而毀壞
那之後
致謝
圖目錄
參考書目
註解
索引
書摘/試閱
天使與怪獸
一九三一年時,吳爾芙在浴缸中突然頓悟了一些事情。
我在沐浴時失神,因此構思了一整本新書——這應該是繼《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的續集——談女性的性生活,要命名為〈女性的職業〉(Professions for Women),老天!太令人興奮了!這些內容就從我星期三要在皮帕學會讀的文章 裡蹦了出來。
上述提到的這篇文章,是她在倫敦國家婦女服務協會的演說講稿。在那十二年前的一九一九年〈排除性別無資格法〉(Sex Disqualification(Removal)Act),使女性開始加入白 領行列,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硬將她們與家庭綁在一起,如今終於可以輕鬆拋諸腦後。李修齊(Hermione Lee)認為,吳爾芙寫《自己的房間》時,是在「回顧女性在歷史中被噤聲與排擠 的情形」,這本新書則是急切地開始思考那些職業女性可能迎來的前景。她知道縱然當時已經 立法,女性本身仍在成為職業婦女方面,面對了嚴峻的挑戰。 她於〈女性的職業〉中開宗明 義表示,女性的身體與工作生活直接相關:這份直覺會啟發他接下來那數十年的人生中,不斷思考性別與權力的議題。
吳爾芙在演說中提到,她成為作家後感受到一種阻力,這股力量不全然來自「另一個性別」,反而透過她所謂家喻戶曉、與自己相同性別的「家中天使」而來。 她自我犧牲、端莊有禮,無欲無求,隨侍在側、「極具同理心」、「非常有魅力」並且 「全然無私」,但也非常危險,把關於奉承、欺騙和純潔的想法悄悄地灌輸給那個天真但野心 勃勃的年輕作家。「你把自己的立場變得非常古怪,」她會說,「你所寫的文章是屬男人所有、是男人編輯的——主要資助人也是男人,甚至你所評論的書也是男人寫的⋯⋯。因此,無 論你說什麼,都應該讓男人高興。要有同理心、要溫柔、要奉承⋯⋯。絕對不要讓他們知道你 有自己的想法,造成他們的困擾,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純潔。」 天使深知年輕女性在這產業 的所有條件,對她而言是相當不利的。要在這世界中順利生存,就必須討好人、避免冒犯人。 天使也暗示說,如果必須從事藝術創作,就要創作出他們會認可的藝術。
吳爾芙一九二七年的小說《燈塔行》(To the Lighthouse)可以證明,她早在數年前就已思 考過這種矛盾。畫家莉莉.布里斯柯(Lily Briscoe)在小說到尾聲時,回到十年前造訪過的蘇 格蘭島,當時雷姆塞太太在內的家族中成員大多已經過世。莉莉腦海中第一個想到的是桌布圖 案,她最後一次造訪時,幾乎都在想某一幅畫的事情,想著前景、樹該畫在哪個位置,到最後也沒能完成。 她把畫架立起來,試圖畫出她當時想不起來的事情,但在雷姆塞先生旁邊完全 無法工作,他咆哮抱怨這地方、一臉不爽、很難相處、喪妻,就跟吳爾芙自己的父親一樣。 「每次他接近——他正在臺階上走來走去——毀滅就接近,混亂就接近。她無法畫」,他只 要在場,就會影響她看到的景象:「她無法看到顏色,她無法看到線,即使他是背對著她,她只能想;但是他等一會兒就會逼近我,要求我——要求某種她覺得她無法給他的東西。」她自年輕時就記得他要的是什麼:他要她像雷姆塞太太那種女人一樣,在臉上表現出「屈 從」,「在類似這樣的場合他們展現出熱情,⋯⋯他們展現同情的欣喜,高興他們所獲得的報 酬,這種狂喜(雖然她已記不起原因)顯然賦予了他們人性所能賦予的最崇高的福佑。」
莉莉拒絕投降,吳爾芙也是。她聽到天使命令她對人和善時,拿起墨水瓶都擲向天使。這 畢竟是生死攸關之事:「我若不殺死她,她就會殺死我,她可能會把我寫作中的靈魂抽走。」
「要殺死她死不容易。」吳爾芙這麼告訴我們。
/
但真是如此嗎?
/
二〇一四年時,我看到一個令我震驚的詞,雖然有注意到,卻不知其 意,才讀了珍妮.奧菲爾短篇小說《臆測部門》(Dept. of Speculation) 其中幾頁,就感受到電光火石。
我打算永遠不要結婚,我要變成 藝術怪獸(art monster)。
藝術怪獸
我去網路上搜尋這個詞。
毫無結果,毫無任何原始出處。法文中有這個詞: monstre del l’art,意指不講理的 重要大人物,而且明顯是男性,是有魅力的自大狂,但在英文裡卻完全不是這麼回 事。克麗絲.克勞斯的《我愛迪克》(I Love Dick)中有一句「而我告訴華倫:我也 要變成女怪獸」,或安潔拉.卡特(Angela Carter)的《薩德式女人》(The Sadeian Woman)中的「自由自在的女人生活在不自由社會裡,會成為一隻怪獸」,都有些有 些半呼應的例子。超現實主義派畫家與雕塑家杜若西雅.譚凝(Dorothea Tanning) 則說「女人必須變成怪獸,才能成為藝術家。」 我找到許多描寫野獸般女性特質的 著作;然而,我唯一找到女人與獸性(monstrosity)之間的關連,只有:女性獸性、女性詭態(grotesque)。
《臆測部門》採取更實際的策略,這本小說中充斥著瑣碎的家庭生活日常,淹沒了敘事者的自我意識(sense of self)。奧菲爾書裡的旁白表明「藝術怪獸只關心藝術,對於世俗事物總 是不屑一顧」,把女人與藝術怪獸分成兩邊,怪獸不會是女人,或極少是女人,或即便是女 人,也是聲明放棄世俗事物——家事、兒女、行政事務——的女人:「納博科夫沒有把自己的 雨傘收起來,維菈替他黏好郵票」。 只能是母親或藝術家,不可能兩者皆是。你看到髒亂、沒有小孩的屋子,就會知道她是藝術怪獸,母親要成為藝術怪獸,就必須拋棄子女、自殺或虐 待子女,藉此來離開或傷害他們,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西爾維亞.柏拉絲(Sylvia Plath)、安妮.賽克絲頓(Anne Sexton)都是。
這段話在奧菲爾小說問世之後隨處可見,經常出現於年輕女性仔細思量是否應生兒育女的個人文章中,因為身兼母親/妻子/藝術家/怪獸既是一種挑戰,更可能是完全不可能之事。 藝術怪獸很快變得與家中天使一樣,是流行的女性主義用語。
但這對我而言,似乎不僅是當藝術家或擁有家室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已。我本身是育有一名 幼子的母親,每天都在緊張的生活之中全神貫注,但藝術怪獸的問題,早在我兒子出世之前, 就已經不斷對我造成困擾,不過這與我從小到大接受的教導較為有關,這社會要求二十世紀末 美國白人女性必須打扮合宜、矜持、友善、慷慨助人,儘量讓自己看起來漂亮、渺小,卻無法在這世界多佔一席之地,因此而感到憤慨。 我也耳聞一些隱約明白的事情:若你一直以來都用女人的身分與人來往,就很難允許自己變成怪獸,但其實也極其容易——稍不經意就能辦到。
/
我剛開始寫這本書時,覺得這本書應該會談怪獸與創意,談女性藝術家要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至少這是我告訴出版社這本書所要談的內容。但我重新從奧菲爾的脈絡來閱讀〈女性 的職業〉,這次讀過倫納德(Leonard Woolf) 於吳爾芙逝世後出版的修訂版之後,明白自己忽 視了文中非常重要、實際上可謂文中高潮的一段話,吳爾芙比喻創作過程如同「女性漁人」那 樣,將她的文字拋到想像力的深海裡,任其在「我們無意識深處的每塊石頭和裂縫中遨游」,隨著文字漂泊、想法流動,出現了吳爾芙認為「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更常遇到」的某些東西:
發生了碰撞與爆炸,浪花翻騰、出現錯亂。想像力撞到了某種堅硬的東西。⋯⋯她想 到某件事,與身體有關的事,想到她身為女人,並不適合表達這種激情。⋯⋯她寫不 下去了,發呆時間結束了。
上述那段崩潰的過程變成自我審查的寓言——阻斷女性藝術創作的力量,不是外在的小孩或先生,而是內化的警告聲音:注意!注意!我們已踏入水深危險之處!吳爾芙在文章最後, 回到一開始演說中談的議題:女人的工作與性生活,並視之為她作家生涯中的兩大關鍵挑戰。 「首先——殺死『家中天使』——我認為自己已完成這任務,她已經死了。但其次——以我自 己作為主體,說出自己感受到的經驗——這我應該尚未辦到,也不相信有任何女人已成功做到」。
就是這個:這或許就是藝術怪獸試圖要做的事情。雖然她已殺死天使,但仍有東西在阻礙著她。她想說一些事,卻受到社會制約而說不出口。截至目前為止,藝術怪獸相關的論述大多 在談女性藝術家的生活,但瞭解他們的作品也很重要,看看她們一心想做的事情為何,為何為 此甘冒被稱作怪獸的風險。
/
吳爾芙認為,我們後續該做的,是鼓起勇氣重塑社會灌輸的文化傳統,並以體化經驗 (embodied experience)作為主要媒介。吳爾芙在《自己的房間》裡勸勉女性作家,若要創作 出真正屬於自己、不受天使干預的作品,就必須打破「句子」,接著打破「順序」。 我們必須從中理解到的是,此處談的不僅是女人,而是每個在文法規範之外的人:此即怪獸的另一個 定義。吳爾芙追求的,與《燈塔行》的小說接近結局之處的描述很像,莉莉努力透過她的畫傳 達的是:「美麗的圖像。美麗的語句,但是她想捕獲的是那神經上的顫動,那還沒有被變成任何東西的東西。」 演說版的〈女性的職業〉以較為原始、急迫的方式呈現這些概念,吳爾芙在這版本中,明確地將想像力人格化,其實就是賦予想像力一個身體,使其能夠衝刺、躍入「天知道在哪裡 的」深處,但她卻必須「氣呼呼又失望地」被拉回來。「『親愛的,總而言之你做得太過分 囉。』女性漁人告訴她。 她試圖安撫不滿的想像力,她保證『情況絕對不會如此』。總有一 天,男人聽到女人『真實談論她的身體』時,不會感到那麼『震驚』。 只要等五十五年左右,五十五年之後,我就可以運用你可以給我的那些古怪知識。但現在不能。」 「很好,」想像力如此說,穿回她的襯裙和裙子,「我們會等。我們會再等五十五年,但我覺得這樣似乎太可惜了。」
/
一九七五年,距離吳爾芙的演說還不到五十五年,藝術家卡洛琳.史尼曼爬上紐約東漢普 頓一間美術館的桌子,既未穿襯裙,也沒穿裙子。事實上,她身上除了一件漂亮的小圍裙之 外,幾乎衣不蔽體,而且很快就把圍裙脫了。她把深色顏料塗在身上,打開一本自己寫的獨立 刊物開始朗讀,擺出各種模特兒的姿勢。接著把書放下,兩腿張得更開,從陰道拉出一個捲軸,有點像臍帶,是厚厚的螺旋狀,開始大聲念:
我遇見一個開心的男人 一位結構主義電影製作人⋯⋯
他說我們很喜歡你
你很有魅力
但別叫我們
看你的電影
沒辦法
有某些片
我們無法看
像是雜亂的個人式作品
像是堅持談感受的
像是有手摸觸感的
像是放縱的心情日記
像是混亂的畫風
像是難懂的格式塔(gestalt)
像是原始的技巧
有人認為史尼曼說這段話的對象,應該是她當時的伴侶安東尼.馬柯爾(Anthony McCall),他的確也是結構主義電影製作人,但她一九八八年告訴電影史學家史考特.麥克唐 納(Scott MacDonald),那段獨白的對象其實是《藝術論壇》(Artforum)的評論家兼編輯安妮 特.米切爾森(Annette Michelson),一位「沒辦法看她的電影」,在紐約大學上電影課時也 未將其納入教學,並將她的作品排除於女性主義經典之外的人。這當中有許多米切爾森談到史尼曼時告訴學生的話,如「像是混亂的畫風」、「像是有手摸觸感的」、「像是放縱的心情日 記」。 這幾句話建構的女性主義藝術家宣言在字裡行間顯然地,恰好是吳爾芙的天使禁止她 寫下的內容。女性主義者用盡心力要使自己的身體獲得解放,〈內在捲軸〉(Interior Scroll) 將那一刻具體表現出來,創作出向前後左右延伸,聚集了所有的美與溢踰(excess),閃耀出光芒的藝術。
史尼曼說:「我原本不想從陰道拉出捲軸當眾朗讀」,但她嘗試「公開」這文化想要「壓抑」的內容時,人們卻大為驚駭,使她認為有必要如此做。 史尼曼想透過〈內在捲軸〉, 「以有形的方式,將無形的、被邊緣化與嚴重受到壓抑的外陰歷史表現出來。外陰十分強大, 能帶來欲仙欲死的快感,使人能夠分娩、帶來轉變、產生月經,也能使人成為母親,藉此來證 明那不是死的、看不見的地方。」 史尼曼使女性身體能夠吐露以前沒有管道可說出口的話,〈內在捲軸〉使「外陰空間」變得清晰與可見,使其除了擁有潛在的生育能力之外,也極具創造力。 史尼曼二〇一九年過世時,我將她的照片發布於社群媒體 Instagram 紀念她,卻被該平台下架。
史尼曼本應別無所求,自她開啟藝術家生涯以來,作品就經常因為敢於描繪某些內容而遭到審查與抨擊,她就讀大學時找不到裸體模特兒,所以找裸體熟睡中的男朋友下手,畫他鬆 軟的陰莖,也畫自己沒有穿衣服的樣子,因此遭到退學;展館總監薩賓.布萊茲維澤(Sabine Breitwieser)表示:「但她為同為畫家的男同學擔任裸體模特兒時,卻未曾遭到任何人反 對。」 她一九六三年的攝影集《審視身體》(Eye Body)中收錄陰蒂的照片時,藝術界對此相當反感。「為何要在藝術界做這件事,不去『色情』界做呢?」 他們說這是淫穢的、是春宮 圖,也說這與藝術毫無關連。
「淫穢」一詞的英文是 obscene,詞源是 ob-(意指:前面)與 -caenum(意指:污穢)。淫穢使我們置身於應該要被洗掉或隔離起的污穢面前,按瑪利.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潔淨與不潔的定義,就是「不合宜之物」,女性私密的身體部位在藝術界即屬於不合宜之物。
一九九一年時,史尼曼發表了一篇極具真知灼見的文章〈淫穢的身體/政治〉(The Obscene Body/Politic),談的是身體、淫穢、以及專業水準與性別歧視。她寫道,若女性早在 數十年前就闖入了藝術界,必然是出於她們過去數千年來當藝術家時遭到排擠的憤怒:藝術界 不使用稱呼她們的代名詞,「而是以男性的他稱呼」,並以性化、「戀物」角度看待她們,同 時又將她們真正的身體視為「污穢、糟糕、毒害人的」。史尼曼在一九九〇年代一部談女性藝 術家的紀錄片中,於〈維納斯對鏡梳妝〉(Rokeby Venus)這幅畫出現於螢幕上時以聲音說道:
自古至今我都只能出現在畫布上,事實上,就像被埋葬成為一幅圖畫,在一個除了他 這個代名詞(無論是指藝術家還是學生)之外,沒有任何其他代名詞擁有權威的文化 中,我真的不知如何理解「自己既是真實能夠做畫的人,但身體又成為描繪對象」 。
身兼藝術家與藝術的史尼曼說道:「女人只要作風夠像男人,創作時明顯走在男人開闢的傳統與道路上,就能挑戰並威脅到允許她們加入男子藝術俱樂部(the Art Stud Club)一脈相承 的精神領域權力。」 史尼曼如同其他七〇年代許多女性主義藝術家,希望能夠受到重視, 但她更認真從自己的性別與身體角度來提出挑戰。她在行為藝術〈赤裸行動演說〉(Naked Action Lecture, 1968)中一邊脫衣服,一邊用幻燈片進行藝術史的演說。
在我看來,藝術怪獸就穿梭在 MoMA PS 1 美術館 二〇一七年底舉辦的大型史尼曼回顧展之中。如果奧 菲爾用的詞語在近年來引發如此強烈的共鳴,我想某 部分可歸因於,該詞指出文化如何懲罰了不願當個渺小、安靜存在的女人。我們的界線是受到管制的,越 界就會被稱作噁心。我認為自己在藝術怪獸一詞中看 到的,與怪獸如何認可女人反對那些我們——及我們 的藝術——該有哪些特質、樣貌與做法方面的既定觀念有關。然而,我為了寫這本書而進行調查的過程 中,看到像吳爾芙與史尼曼那樣的作家與藝術家作品 時,就不再花費那麼大的心思,立法規定誰才是藝術 怪獸了。我知道怪獸也能當作動詞使用:藝術能夠「怪獸」(monsters)某些事物。我們透過舊詞新意 可以瞭解,藝術的作用在於將熟悉之物變為陌生,提 醒我們跳脫習慣,並使我們想像其他不同的存在方式,讓身體與想像力跳脫社會、父權以及內化的厭女觀念設下的嚴格界線之外,進行陳述與想 像。無論我們是把藝術怪獸理解為名詞或動詞,這概念都是大膽推翻加諸於我們身上的限制,並創造出我們自己對於美的定義的挑戰。
一九三一年時,吳爾芙在浴缸中突然頓悟了一些事情。
我在沐浴時失神,因此構思了一整本新書——這應該是繼《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的續集——談女性的性生活,要命名為〈女性的職業〉(Professions for Women),老天!太令人興奮了!這些內容就從我星期三要在皮帕學會讀的文章 裡蹦了出來。
上述提到的這篇文章,是她在倫敦國家婦女服務協會的演說講稿。在那十二年前的一九一九年〈排除性別無資格法〉(Sex Disqualification(Removal)Act),使女性開始加入白 領行列,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硬將她們與家庭綁在一起,如今終於可以輕鬆拋諸腦後。李修齊(Hermione Lee)認為,吳爾芙寫《自己的房間》時,是在「回顧女性在歷史中被噤聲與排擠 的情形」,這本新書則是急切地開始思考那些職業女性可能迎來的前景。她知道縱然當時已經 立法,女性本身仍在成為職業婦女方面,面對了嚴峻的挑戰。 她於〈女性的職業〉中開宗明 義表示,女性的身體與工作生活直接相關:這份直覺會啟發他接下來那數十年的人生中,不斷思考性別與權力的議題。
吳爾芙在演說中提到,她成為作家後感受到一種阻力,這股力量不全然來自「另一個性別」,反而透過她所謂家喻戶曉、與自己相同性別的「家中天使」而來。 她自我犧牲、端莊有禮,無欲無求,隨侍在側、「極具同理心」、「非常有魅力」並且 「全然無私」,但也非常危險,把關於奉承、欺騙和純潔的想法悄悄地灌輸給那個天真但野心 勃勃的年輕作家。「你把自己的立場變得非常古怪,」她會說,「你所寫的文章是屬男人所有、是男人編輯的——主要資助人也是男人,甚至你所評論的書也是男人寫的⋯⋯。因此,無 論你說什麼,都應該讓男人高興。要有同理心、要溫柔、要奉承⋯⋯。絕對不要讓他們知道你 有自己的想法,造成他們的困擾,最重要的是,要保持純潔。」 天使深知年輕女性在這產業 的所有條件,對她而言是相當不利的。要在這世界中順利生存,就必須討好人、避免冒犯人。 天使也暗示說,如果必須從事藝術創作,就要創作出他們會認可的藝術。
吳爾芙一九二七年的小說《燈塔行》(To the Lighthouse)可以證明,她早在數年前就已思 考過這種矛盾。畫家莉莉.布里斯柯(Lily Briscoe)在小說到尾聲時,回到十年前造訪過的蘇 格蘭島,當時雷姆塞太太在內的家族中成員大多已經過世。莉莉腦海中第一個想到的是桌布圖 案,她最後一次造訪時,幾乎都在想某一幅畫的事情,想著前景、樹該畫在哪個位置,到最後也沒能完成。 她把畫架立起來,試圖畫出她當時想不起來的事情,但在雷姆塞先生旁邊完全 無法工作,他咆哮抱怨這地方、一臉不爽、很難相處、喪妻,就跟吳爾芙自己的父親一樣。 「每次他接近——他正在臺階上走來走去——毀滅就接近,混亂就接近。她無法畫」,他只 要在場,就會影響她看到的景象:「她無法看到顏色,她無法看到線,即使他是背對著她,她只能想;但是他等一會兒就會逼近我,要求我——要求某種她覺得她無法給他的東西。」她自年輕時就記得他要的是什麼:他要她像雷姆塞太太那種女人一樣,在臉上表現出「屈 從」,「在類似這樣的場合他們展現出熱情,⋯⋯他們展現同情的欣喜,高興他們所獲得的報 酬,這種狂喜(雖然她已記不起原因)顯然賦予了他們人性所能賦予的最崇高的福佑。」
莉莉拒絕投降,吳爾芙也是。她聽到天使命令她對人和善時,拿起墨水瓶都擲向天使。這 畢竟是生死攸關之事:「我若不殺死她,她就會殺死我,她可能會把我寫作中的靈魂抽走。」
「要殺死她死不容易。」吳爾芙這麼告訴我們。
/
但真是如此嗎?
/
二〇一四年時,我看到一個令我震驚的詞,雖然有注意到,卻不知其 意,才讀了珍妮.奧菲爾短篇小說《臆測部門》(Dept. of Speculation) 其中幾頁,就感受到電光火石。
我打算永遠不要結婚,我要變成 藝術怪獸(art monster)。
藝術怪獸
我去網路上搜尋這個詞。
毫無結果,毫無任何原始出處。法文中有這個詞: monstre del l’art,意指不講理的 重要大人物,而且明顯是男性,是有魅力的自大狂,但在英文裡卻完全不是這麼回 事。克麗絲.克勞斯的《我愛迪克》(I Love Dick)中有一句「而我告訴華倫:我也 要變成女怪獸」,或安潔拉.卡特(Angela Carter)的《薩德式女人》(The Sadeian Woman)中的「自由自在的女人生活在不自由社會裡,會成為一隻怪獸」,都有些有 些半呼應的例子。超現實主義派畫家與雕塑家杜若西雅.譚凝(Dorothea Tanning) 則說「女人必須變成怪獸,才能成為藝術家。」 我找到許多描寫野獸般女性特質的 著作;然而,我唯一找到女人與獸性(monstrosity)之間的關連,只有:女性獸性、女性詭態(grotesque)。
《臆測部門》採取更實際的策略,這本小說中充斥著瑣碎的家庭生活日常,淹沒了敘事者的自我意識(sense of self)。奧菲爾書裡的旁白表明「藝術怪獸只關心藝術,對於世俗事物總 是不屑一顧」,把女人與藝術怪獸分成兩邊,怪獸不會是女人,或極少是女人,或即便是女 人,也是聲明放棄世俗事物——家事、兒女、行政事務——的女人:「納博科夫沒有把自己的 雨傘收起來,維菈替他黏好郵票」。 只能是母親或藝術家,不可能兩者皆是。你看到髒亂、沒有小孩的屋子,就會知道她是藝術怪獸,母親要成為藝術怪獸,就必須拋棄子女、自殺或虐 待子女,藉此來離開或傷害他們,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西爾維亞.柏拉絲(Sylvia Plath)、安妮.賽克絲頓(Anne Sexton)都是。
這段話在奧菲爾小說問世之後隨處可見,經常出現於年輕女性仔細思量是否應生兒育女的個人文章中,因為身兼母親/妻子/藝術家/怪獸既是一種挑戰,更可能是完全不可能之事。 藝術怪獸很快變得與家中天使一樣,是流行的女性主義用語。
但這對我而言,似乎不僅是當藝術家或擁有家室之間的緊張關係而已。我本身是育有一名 幼子的母親,每天都在緊張的生活之中全神貫注,但藝術怪獸的問題,早在我兒子出世之前, 就已經不斷對我造成困擾,不過這與我從小到大接受的教導較為有關,這社會要求二十世紀末 美國白人女性必須打扮合宜、矜持、友善、慷慨助人,儘量讓自己看起來漂亮、渺小,卻無法在這世界多佔一席之地,因此而感到憤慨。 我也耳聞一些隱約明白的事情:若你一直以來都用女人的身分與人來往,就很難允許自己變成怪獸,但其實也極其容易——稍不經意就能辦到。
/
我剛開始寫這本書時,覺得這本書應該會談怪獸與創意,談女性藝術家要在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至少這是我告訴出版社這本書所要談的內容。但我重新從奧菲爾的脈絡來閱讀〈女性 的職業〉,這次讀過倫納德(Leonard Woolf) 於吳爾芙逝世後出版的修訂版之後,明白自己忽 視了文中非常重要、實際上可謂文中高潮的一段話,吳爾芙比喻創作過程如同「女性漁人」那 樣,將她的文字拋到想像力的深海裡,任其在「我們無意識深處的每塊石頭和裂縫中遨游」,隨著文字漂泊、想法流動,出現了吳爾芙認為「女性作家比男性作家更常遇到」的某些東西:
發生了碰撞與爆炸,浪花翻騰、出現錯亂。想像力撞到了某種堅硬的東西。⋯⋯她想 到某件事,與身體有關的事,想到她身為女人,並不適合表達這種激情。⋯⋯她寫不 下去了,發呆時間結束了。
上述那段崩潰的過程變成自我審查的寓言——阻斷女性藝術創作的力量,不是外在的小孩或先生,而是內化的警告聲音:注意!注意!我們已踏入水深危險之處!吳爾芙在文章最後, 回到一開始演說中談的議題:女人的工作與性生活,並視之為她作家生涯中的兩大關鍵挑戰。 「首先——殺死『家中天使』——我認為自己已完成這任務,她已經死了。但其次——以我自 己作為主體,說出自己感受到的經驗——這我應該尚未辦到,也不相信有任何女人已成功做到」。
就是這個:這或許就是藝術怪獸試圖要做的事情。雖然她已殺死天使,但仍有東西在阻礙著她。她想說一些事,卻受到社會制約而說不出口。截至目前為止,藝術怪獸相關的論述大多 在談女性藝術家的生活,但瞭解他們的作品也很重要,看看她們一心想做的事情為何,為何為 此甘冒被稱作怪獸的風險。
/
吳爾芙認為,我們後續該做的,是鼓起勇氣重塑社會灌輸的文化傳統,並以體化經驗 (embodied experience)作為主要媒介。吳爾芙在《自己的房間》裡勸勉女性作家,若要創作 出真正屬於自己、不受天使干預的作品,就必須打破「句子」,接著打破「順序」。 我們必須從中理解到的是,此處談的不僅是女人,而是每個在文法規範之外的人:此即怪獸的另一個 定義。吳爾芙追求的,與《燈塔行》的小說接近結局之處的描述很像,莉莉努力透過她的畫傳 達的是:「美麗的圖像。美麗的語句,但是她想捕獲的是那神經上的顫動,那還沒有被變成任何東西的東西。」 演說版的〈女性的職業〉以較為原始、急迫的方式呈現這些概念,吳爾芙在這版本中,明確地將想像力人格化,其實就是賦予想像力一個身體,使其能夠衝刺、躍入「天知道在哪裡 的」深處,但她卻必須「氣呼呼又失望地」被拉回來。「『親愛的,總而言之你做得太過分 囉。』女性漁人告訴她。 她試圖安撫不滿的想像力,她保證『情況絕對不會如此』。總有一 天,男人聽到女人『真實談論她的身體』時,不會感到那麼『震驚』。 只要等五十五年左右,五十五年之後,我就可以運用你可以給我的那些古怪知識。但現在不能。」 「很好,」想像力如此說,穿回她的襯裙和裙子,「我們會等。我們會再等五十五年,但我覺得這樣似乎太可惜了。」
/
一九七五年,距離吳爾芙的演說還不到五十五年,藝術家卡洛琳.史尼曼爬上紐約東漢普 頓一間美術館的桌子,既未穿襯裙,也沒穿裙子。事實上,她身上除了一件漂亮的小圍裙之 外,幾乎衣不蔽體,而且很快就把圍裙脫了。她把深色顏料塗在身上,打開一本自己寫的獨立 刊物開始朗讀,擺出各種模特兒的姿勢。接著把書放下,兩腿張得更開,從陰道拉出一個捲軸,有點像臍帶,是厚厚的螺旋狀,開始大聲念:
我遇見一個開心的男人 一位結構主義電影製作人⋯⋯
他說我們很喜歡你
你很有魅力
但別叫我們
看你的電影
沒辦法
有某些片
我們無法看
像是雜亂的個人式作品
像是堅持談感受的
像是有手摸觸感的
像是放縱的心情日記
像是混亂的畫風
像是難懂的格式塔(gestalt)
像是原始的技巧
有人認為史尼曼說這段話的對象,應該是她當時的伴侶安東尼.馬柯爾(Anthony McCall),他的確也是結構主義電影製作人,但她一九八八年告訴電影史學家史考特.麥克唐 納(Scott MacDonald),那段獨白的對象其實是《藝術論壇》(Artforum)的評論家兼編輯安妮 特.米切爾森(Annette Michelson),一位「沒辦法看她的電影」,在紐約大學上電影課時也 未將其納入教學,並將她的作品排除於女性主義經典之外的人。這當中有許多米切爾森談到史尼曼時告訴學生的話,如「像是混亂的畫風」、「像是有手摸觸感的」、「像是放縱的心情日 記」。 這幾句話建構的女性主義藝術家宣言在字裡行間顯然地,恰好是吳爾芙的天使禁止她 寫下的內容。女性主義者用盡心力要使自己的身體獲得解放,〈內在捲軸〉(Interior Scroll) 將那一刻具體表現出來,創作出向前後左右延伸,聚集了所有的美與溢踰(excess),閃耀出光芒的藝術。
史尼曼說:「我原本不想從陰道拉出捲軸當眾朗讀」,但她嘗試「公開」這文化想要「壓抑」的內容時,人們卻大為驚駭,使她認為有必要如此做。 史尼曼想透過〈內在捲軸〉, 「以有形的方式,將無形的、被邊緣化與嚴重受到壓抑的外陰歷史表現出來。外陰十分強大, 能帶來欲仙欲死的快感,使人能夠分娩、帶來轉變、產生月經,也能使人成為母親,藉此來證 明那不是死的、看不見的地方。」 史尼曼使女性身體能夠吐露以前沒有管道可說出口的話,〈內在捲軸〉使「外陰空間」變得清晰與可見,使其除了擁有潛在的生育能力之外,也極具創造力。 史尼曼二〇一九年過世時,我將她的照片發布於社群媒體 Instagram 紀念她,卻被該平台下架。
史尼曼本應別無所求,自她開啟藝術家生涯以來,作品就經常因為敢於描繪某些內容而遭到審查與抨擊,她就讀大學時找不到裸體模特兒,所以找裸體熟睡中的男朋友下手,畫他鬆 軟的陰莖,也畫自己沒有穿衣服的樣子,因此遭到退學;展館總監薩賓.布萊茲維澤(Sabine Breitwieser)表示:「但她為同為畫家的男同學擔任裸體模特兒時,卻未曾遭到任何人反 對。」 她一九六三年的攝影集《審視身體》(Eye Body)中收錄陰蒂的照片時,藝術界對此相當反感。「為何要在藝術界做這件事,不去『色情』界做呢?」 他們說這是淫穢的、是春宮 圖,也說這與藝術毫無關連。
「淫穢」一詞的英文是 obscene,詞源是 ob-(意指:前面)與 -caenum(意指:污穢)。淫穢使我們置身於應該要被洗掉或隔離起的污穢面前,按瑪利.道格拉斯(Mary Douglas)的潔淨與不潔的定義,就是「不合宜之物」,女性私密的身體部位在藝術界即屬於不合宜之物。
一九九一年時,史尼曼發表了一篇極具真知灼見的文章〈淫穢的身體/政治〉(The Obscene Body/Politic),談的是身體、淫穢、以及專業水準與性別歧視。她寫道,若女性早在 數十年前就闖入了藝術界,必然是出於她們過去數千年來當藝術家時遭到排擠的憤怒:藝術界 不使用稱呼她們的代名詞,「而是以男性的他稱呼」,並以性化、「戀物」角度看待她們,同 時又將她們真正的身體視為「污穢、糟糕、毒害人的」。史尼曼在一九九〇年代一部談女性藝 術家的紀錄片中,於〈維納斯對鏡梳妝〉(Rokeby Venus)這幅畫出現於螢幕上時以聲音說道:
自古至今我都只能出現在畫布上,事實上,就像被埋葬成為一幅圖畫,在一個除了他 這個代名詞(無論是指藝術家還是學生)之外,沒有任何其他代名詞擁有權威的文化 中,我真的不知如何理解「自己既是真實能夠做畫的人,但身體又成為描繪對象」 。
身兼藝術家與藝術的史尼曼說道:「女人只要作風夠像男人,創作時明顯走在男人開闢的傳統與道路上,就能挑戰並威脅到允許她們加入男子藝術俱樂部(the Art Stud Club)一脈相承 的精神領域權力。」 史尼曼如同其他七〇年代許多女性主義藝術家,希望能夠受到重視, 但她更認真從自己的性別與身體角度來提出挑戰。她在行為藝術〈赤裸行動演說〉(Naked Action Lecture, 1968)中一邊脫衣服,一邊用幻燈片進行藝術史的演說。
在我看來,藝術怪獸就穿梭在 MoMA PS 1 美術館 二〇一七年底舉辦的大型史尼曼回顧展之中。如果奧 菲爾用的詞語在近年來引發如此強烈的共鳴,我想某 部分可歸因於,該詞指出文化如何懲罰了不願當個渺小、安靜存在的女人。我們的界線是受到管制的,越 界就會被稱作噁心。我認為自己在藝術怪獸一詞中看 到的,與怪獸如何認可女人反對那些我們——及我們 的藝術——該有哪些特質、樣貌與做法方面的既定觀念有關。然而,我為了寫這本書而進行調查的過程 中,看到像吳爾芙與史尼曼那樣的作家與藝術家作品 時,就不再花費那麼大的心思,立法規定誰才是藝術 怪獸了。我知道怪獸也能當作動詞使用:藝術能夠「怪獸」(monsters)某些事物。我們透過舊詞新意 可以瞭解,藝術的作用在於將熟悉之物變為陌生,提 醒我們跳脫習慣,並使我們想像其他不同的存在方式,讓身體與想像力跳脫社會、父權以及內化的厭女觀念設下的嚴格界線之外,進行陳述與想 像。無論我們是把藝術怪獸理解為名詞或動詞,這概念都是大膽推翻加諸於我們身上的限制,並創造出我們自己對於美的定義的挑戰。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