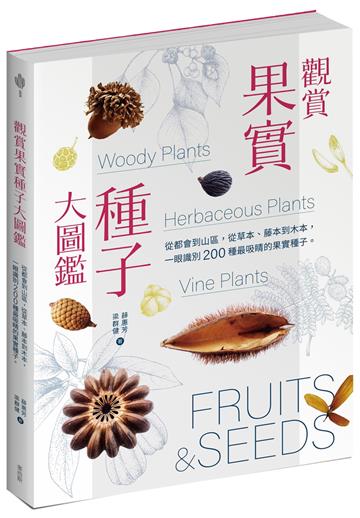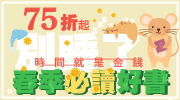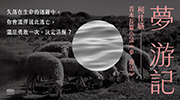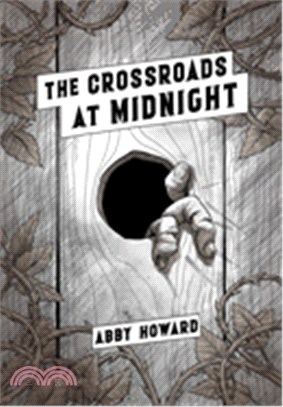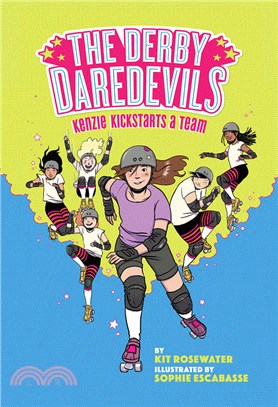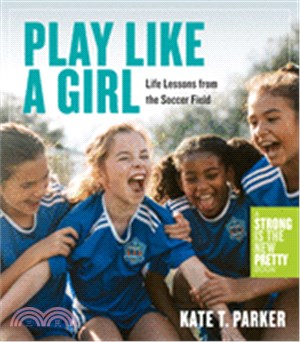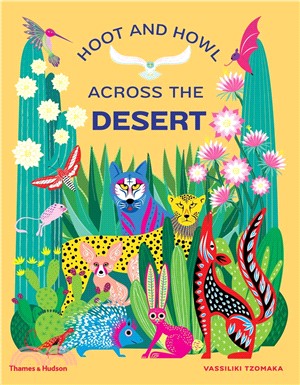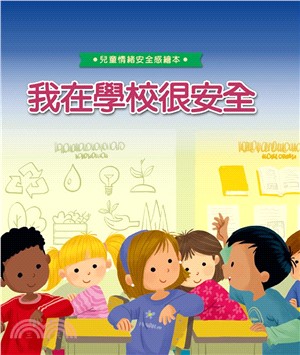噤聲之界:北臺灣客庄與原民的百年纏結和對話(電子書)
商品資訊
ISBN:9786269716463
EISBN:9786269716470
出版社:游擊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梁廷毓
出版日:2024/04/17
裝訂:電子書
檔案格式:EPUB
商品碼:2222221512683
商品簡介
★本書由國藝會臺灣書寫專案補助
★2024年臺灣文學獎金典獎
★2024年臺灣文學獎蓓蕾獎
★2024桃園閱讀節「最佳族群共榮指南」推薦
塵封的族譜,喚起原客數百年來互動的血色記憶;
無頭魂與魍神,依舊遊蕩在北臺灣的山林,鬼影幢幢。
「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作為國家強力推動的文化政策,透過發掘/發明客家文化與美學符號,企圖重新活絡沿線客庄產業與觀光,藉由夏雪紛飛的桐花詩意印象,讓遊人可在每年的桐花祭體驗浪漫的山林氛圍。
然而,臺三線的前身,不管是清朝時期的土牛溝,抑或是日本時期的隘勇線,代表的卻是由國家或民間以暴力手段劃設下的原/漢分界。既然有了「界」,不同人群的文化觀、宇宙觀、土地倫理,甚至「靈」的力量,就在此發生競逐與衝突。為了捍衛家園、守護獵場,部落族人面對來犯的侵墾者,遵循祖律,以出草獵首論斷是非曲直,執行正義;為了爭得田地、落土安居,漢庄客民以「食番肉」,宣洩開山打林的父兄親人,失去頭顱、橫死山林,所帶來的仇恨與哀傷。這段長達數百年的過去,並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成為遙遠的歷史。眾多的伯公祠、有應廟、大墓公塚,以及飄盪無依的無頭鬼,見證了屍味與血色,依舊籠罩在臺三線所在的北臺灣淺山地帶,魑魅魍魎,鬼氣森森。
一本塵封的族譜,留下了家族長輩被獵首的記述。梁家先人於十八世紀渡海來到臺灣,深入到今日新竹新埔、關西一帶拓墾。在開創新家園的過程中,他們面對的是甚麼樣的環境?又經歷了甚麼樣的遭遇?為甚麼新版的族譜要將獵首的紀錄刪除?種種的不解與疑問,驅使作者走入北臺灣淺山地帶,訪廟、找墓、問神、尋鬼。透過文獻資料的爬梳與走訪部落與客庄的耆老,採集口述,一部有別於官方所建構出來的——以客家為主體、用浪漫作包裝的——臺三線沿線山林,重新被詮釋出來。
作者筆下的這處山林,包含了客家人、道卡斯族、凱達格蘭族與泰雅族人,以及諸神與野鬼們為了生存,累世累代的互動與折衝,這些故事存在於民間記憶與口述傳說,視角多元、眾聲喧嘩。然而,這並不是一本單純講述北臺灣山林的鄉野傳奇之書,也不是要重新扒開過往人群接觸所造成的傷與痛。當國家元首代表政府與國家,向原住民族道歉之後,唯有重新回到人群交界地帶,透過客庄與部落耆老口中的娓娓道來,不管是客家人念茲在茲的無頭祖公婆,或是泰雅與平埔族人被佔據開發的傳統領域,存在於不同人群的記憶,以及存在於記憶之中,深邃而難以拋下的悲痛與埋怨,才得以被說出、被看見。唯有被說出、被看見,才有機會進行人群間多向的溝通、對話與理解,也才能達到真正的和解,讓因歷史與時代造成的傷口,得以結痂癒合。
共同推薦
王振武(新竹縣立富光國中教師、中華大學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諮詢委員)
陳金萬(紀錄片導演、藝術評論人、自由撰稿人、凱達格蘭族巴賽語復振計畫推動者)
廖志軒(新竹縣道卡斯族文化協會理事長)
羅烈師(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專文推薦
百年前的臺灣,現代文明尚未進駐,族群之間為爭奪土地,引發武裝械鬥,甚而以獵首、食人肉、走私交易……等私刑手段,或者通婚抱養的折衝方式,達到土地侵墾的目的。梁廷毓在本書中,融會客庄與原民部落的耆老記憶,運用民族誌、藝術及跨學科的地方研究方法,進行「在場的書寫」。他從高空視角,俯瞰大嵙崁群、馬武督群、麥樹仁群的原住民族,如何在百年前遷徙、建立部落,再進入丘陵、河谷地區,從大溪、平鎮、龍潭、關西、橫山、竹東地區,與客家拓墾者相遇的種種細節,重現當前「浪漫臺三線」產業觀光背後被遺忘的歷史,這是相當可貴的書寫。——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林淇瀁(向陽)
作者簡介
梁廷毓
藝術創作者與研究者,近年的「斷頭河計畫」(2017年至今)聚焦於計畫型藝術及匯合跨學科的地方研究,關注晚近歷史轉型正義、非人轉向趨勢中的超自然鬼魅與漢人、原住民互動之歷史和記憶。寫作曾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臺灣書寫專案」獎助(2020),並參與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逆寫北臺灣客家開發史計畫」(2021-2022);相關研究曾獲「世安美學論文獎」(2022),學術發表散見於《臺灣文獻》、《臺灣風物》、《史物論壇:歷史博物館學報》、《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臺灣原住民族研究論叢》與《臺灣文學研究學報》等。
目前「斷頭河計畫」的相關展演包括《斷頭鬼之夢》(2023)、《食人之界》(2023)、《墳.屍骨.紅壤層》(2019)、《山.殺人.斷頭河》(2018)、《番肉考》(2018)。創作亦受邀於札那巴札爾美術館(烏蘭巴托,2023)、國立臺灣美術館(臺中,2022)、湯普森藝術中心(曼谷,2022)、國家攝影文化中心(臺北,2021)、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臺北,2021)、臺北當代藝術館(臺北,2020、2019)等地展出或放映。近幾年致力於開發複合型的展示介面,以展覽、研討會、工作坊、調研隊、文論等社會展演方式,進行相關計畫的實踐。
序
作者序 傾聽由「眾靈」所牽動的記憶
每每要下筆時,總感覺身後有許多的眼睛在凝望著我,靜默地望著我要如何「下手」;無論是在紙上起草,或敲擊鍵盤時,也一直覺得有許多雙手在同我「共筆」。這並不是瞎扯一種怪力亂神的寫法,而是當我開始意識到不同視域的存在時,以一種分裂之眼,嘗試握住「他」和「她」,以及「祂」的手勢,敦促自己在不同的角度上進行情感、思緒和紙筆之間的觀點協商,使我重新回訪那一處不可能復現,且溢滿靈性與人性的歷史劇場。因此,對我而言,這是一本被眾靈、族人、家人和眾多老者們推著寫的書,也是一項思索如何探尋與追述記憶的寫作,而不是考證歷史檔案和文獻的學術論著。本書觸及了既有檔案與文獻之外的大量民間記憶與物質現場,如果有某些研究是從檔案中尋找線索,挖掘出提供我們看待過去與整體社會環境的視角,那麼這本書則是從民間流散的記憶,逐步描繪出當下的人群是如何地認知過去,以及如何轉化被留在世代生命、經驗傳承之中的過往痕跡。
接下來的故事,便是從這樣的起心動念開始的。村落歷史不會因學術研究的翻案和揭示,就直接影響當地人民的認知。相反地,當地人民的歷史記憶、生存經驗與家族境遇卻緊緊地綑綁在一起,往往呈現與歷史正義和歷史反思相左的主觀認知。當意識到這件事情時,記憶形塑過程就必須被反思。也許有人認為,民間所述說的歷史總是一部訛傳的歷史。確實,民間記憶或許不是史實,也往往差異於官方檔案文件的記述。但是,無論文史工作者和歷史學者的學術專書和研究論文,如何從歷史檔案中考證與修正這些偏誤,民間社會還是存在一股持續傳述的強大動力,短時間內無法被阻斷、扭轉或消解。它仍然可以在特定時空的情境和語境中影響人的認知與價值,甚至做出或正或反的行動,進而構築出人們與現實的關係。
記憶與口傳不一定是史實,但卻是民間社會中認定及相信的「真實」,隨時會反過來構成一個人與人群之間、人群與其他人群之間的關係。特別是在族群的記憶上,又進一步構造出某種彼此的現實語境與敘事方式,甚至很難因為歷史教科書的客觀性,而改動人們對於歷史認識的主觀情感,因為很多是關乎親人與家族的事。記憶儲存之處,有些是在國家力量的控制與影響之內,有些則在國家控制之外,這也是為甚麼歷史敘事當中,終究存在一處得以反抗與逆讀的縫隙。另一方面,多數人會忘記不斷隨著時代交替的政府與官員,在記憶中化作一個抽象而遙遠的統治者,將結構性的事物置於無意識的背景之中,卻仍然記得曾經朝夕相逢的異族,處在你爭我奪的交纏關係裡的各種細節。或許可以說,國家的控制是一種讓人身於其中、無法覺察的統治技術,但是從民間記憶裡面——特別是對族群互動的記述,則呈現了國家統治技術的漏洞,甚至凸顯國家勢力的界限與盡頭——十八至十九世紀的漢人與泰雅族人逐漸有較多接觸後,泰雅人的力量反而滲入到沿山地區漢人社會的記憶中有多麼地深層。換言之,原住民在人口逐漸趨於劣勢的過程中,仍採取一定程度反抗,同時不斷地讓漢人對土地與資源的利用作重新的確認。族人的行動也在與漢人一來一往、一攻一守的互動下,間接決定了漢人村莊位置與防禦系統,甚至仍遺留到現在,存在於村莊的發展結構中。疊架式的歷史,每個時期的影響必然會疊加至今。
從社會結構變遷與移墾歷史的角度來看,總會令人有種漢人因為侵墾原住民的土地而產生虧欠及希冀補償的心態,部落的耆老也會講述和反思過往傳統習俗中對待漢人的方式,只是因為現實條件的限制下也無力補償甚麼。談論人們如何去記述一個地方,除了能洞見記憶是一種彼此疊加、混沌的感覺團塊,還能看見記憶的運作如何影響人群實踐的方式,所以本書並不是將民間傳聞或口碑故事,當作一個和現在無涉且過去式的事物,也不是要以此質疑歷史研究和檔案記載的事實性。因為記憶是不斷建構與重構的流變之物,即使從未看過歷史檔案上寫著甚麼,也沒有看過學術報告的研究成果,它仍然存在一套理解歷史的邏輯與論辯方式。
因此,本書力圖在描述一處地點時,不以歷史檔案的官方話語,來蓋過地方現存者的聲音。畢竟,如果一件事情沒發生,或是沒有在檔案中出現,但人們卻記憶為有發生,或是一件事情在檔案文獻中有記載,但今人卻認為沒發生或不知道,這些居住當地的人們,所下的歷史判斷和選擇,往往是接下來影響地方歷史走向具體文化實踐的關鍵力量。我甚至時常思慮,地方生活者如何去想像歷史的過程,應該比判斷其正確與否更為重要。是故,如果不是做一位歷史的後設分析者,而是要投身未來歷史走向的文化運動,認識當地人是如何認知與傳述在地觀點,會遠遠比理解檔案更不可或缺。
這並非說既有檔案文獻都不重要,現存大量關於清代的檔案、方志與日治初期、戰後修編的資料,都是我在寫作過程中幫助理解歷史的基礎材料。諸多師長學者的研究和論點,也都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資源和資料,在在令我深受啟發。但我相信,甚至很多書寫者也曾經歷過——當你面對的是一位住在一地五十年以上,也從小生長在該處的人,你跟他講一個這個地方在檔案上記錄的事情,如果他在這個地方所認識的人身上都沒聽過,他根本很難相信一個外來研究者所說的話。即使將資訊分享給他,基於對檔案可能造假、認為政府常欺騙人民的不信任心理,他還是認為沒有這回事。可是如果有一位居住附近的人知道檔案上所記載關於這個地方的事情,然後講出來,被他聽到,基於人際交往的信任感,他可能就相信了,這就會影響未來的行動。我在原漢人群彼此很接近的地帶,便時常深深陷進這一問題的深淵裡,不斷尋求雙方可以契合的記憶,從彼此的記憶去傳達與對話,而不是從檔案上去告訴他們說「以前如何地互動」。
但從民間觀點出發,與官方檔案所呈現的想法和記述,兩者確實存在不同之處。我的老家在新竹的關西鎮,家族先輩在清朝嘉慶至光緒年間,活動於龍潭、關西、橫山、尖石一帶淺山與山谷河埔地。因為家族中流傳著有幾位長輩被原住民獵首的記憶,並記載在族譜上,這件事情驅使我在二○一七年起,開始藉由調查、耆老訪問、歷史研究的方式,瞭解這個區域的人群歷史關係。我從耆老口中得知了許多泰雅族原住民出草的記憶,也從泰雅部落耆老得知他們祖先曾經打獵生活的地方現在被客家人的聚落佔據。
如果人的記憶與生活空間是建構在這個區域的政治經濟條件下,不斷互動的結果,那麼藉由人群間長時間的互動與記憶的反芻,「定居型殖民者」(settler)的敘事能否察覺得以鬆動「定居殖民結構」的縫隙?農耕社會與移墾社會為主體視角的論述——漢人內山開發史下的歷史敘事,都將因此需重新打上一個問號。究竟是誰的「內山」?如果不只是使用「開墾」、「拓墾」、「防番」等詞彙,我們還能用甚麼方式書寫「臺三線」的歷史?為了回答這個一直壓在我心頭的疑問,這本書會以桃園、新竹一帶的原客互動歷史為主軸,從原住民在近山地區建立部落的時間點開始,從大嵙崁群、馬武督群、麥樹仁群泰雅人等淺山地帶的部落,逐漸進入到桃園新竹的丘陵、河谷地區的過程,從不同人群間的遭逢、相遇、面臨拓墾者逐漸逼近、建立防禦性村落的過程,返回至當代客家山村和部落。
我注意到目前涉及到北臺灣淺山地區的相關文史寫作中,鮮少思考到「定居型殖民者」如何存在於區域歷史和人群記憶當中之問題。我並非是這些議題的專業研究者,也不是歷史學背景出身,但卻對這段漢人侵逼、移居與融入土地的歷史和記憶深感興趣。事實上,客庄與原住民之間的百年纏結和情仇,並不是一項容易化解的事。我們必須探問:在原住民族人這端,是否會因為漢人社會及定居殖民型態的延續,而不願輕易「和解」?相對地,要達成客家人這端的「講和」,做法又會是甚麼?其實彼此都不容易,甚至在一些地方家族的認知裡,可能也沒有任何的意願。回到基本的課題,今日我們為何不斷地思考,甚麼是泰雅族原住民的Sbalay(因「真相」而來的和解)?甚麼又是客家人的「講和」(協調爭端,結束爭執)?面對總是交錯蔓生及層層堆疊的歷史,若從考古學(archaeology)與考現學(modernology)的角度,照片、地圖、族譜、古文書等檔案,以及墓塚、建物、山景、靈異傳聞,某種程度都構成了回答上述問題的潛在部分。
我並不諱言,因種種歷史際遇而形成的地方靈異傳聞,以及居民之間口耳相傳的超自然經驗,對本書的寫作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一部分。相信大多數的研究者,在面對歷史時,都會承認歷史檔案有其先天的遺漏、缺陷和碎片性,並在開始思考史料背後的權力和運作機制,分析出契約文書背後隱含較為真實的樣貌之後,才會進行縝密的書寫布局。正是因為歷史是一部巨大的「遺忘機制」,不斷進行「空缺」的生產,才使得記憶及歷史的書寫,能夠擁有無限想望、潛能及擴延的空間。但是,檔案在本質上,已經是一種使死者「噤聲」的物質證據;也正是在建構一套歷史的敘事時,對於檔案的依賴,時常令人深陷一種想要為死者「代言」的狀態。進而言之,我認為在調度檔案的書寫,促成的「幽靈」復返作用仍然有限,此種「歷史幽靈」通常是文化及隱喻性的存在。唯有置身於在地行動者們共同築構的宇宙論(cosmology)及泛靈論(animism)之中,深刻感覺到各種人群與真實鬼魅交錯橫生的世界,才能更為生態性地實踐一種傾聽「眾靈」聲音的寫作。
必須承認,我作為客家人,以中文寫作本書,儘管有一定程度的反省,仍已經繼承漢人社會與原住民族之間的不平等結構。經由歷史累積而成結構性因素,早已強加於我身上,並且先於我而存在。但是,當我知道家族長輩曾經和道卡斯族的三姓族人通婚,自己身上流著道卡斯族人的血脈,也使我產生一個巨大的疑問:究竟是在甚麼社會結構和歷史因素底下,家族長輩逐漸避談或遺忘了這件事情?除了進行自我批判與反思,目前只能以一種高度自我裂變、從漢人視角內部裂解的思維,反覆推辨這項問題。另一方面,作為一位藝術創作者,這本書也是我近年執行「斷頭河計畫」的一部分,寫作與我的創作總是交繞雙生的關係,甚至是同一件、無法分離的工作;雖然自二○一七年開始至今,我已經在《臺灣文獻》、《臺灣風物》、《歷史臺灣: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刊》、《臺灣原住民族研究論叢》、《桃園文獻》與《qmul rhzyal Tayal?開山打林?逆寫北臺灣客庄形成史》等學術專書和研究期刊上,發表數篇探討漢人開發史與原漢族群互動記憶的田野調查報告和論文。但這本書所寫的,幾乎都是在論文化的寫作過程裡,難以清楚寫成論述、無法輕易消化的故事,甚至是各種仍待化解的情緒。因此,面對如此糾結且複雜的地方紋理和歷史,確實也疏漏不少。若在本書中有使用史料和解讀上的偏誤,再請專家、學者不吝給予我批評,也請耆老們、族人們不吝給予我指正和建議。
這本書之所以能完成,要感謝非常多人。謝謝我的父母黃月美與梁有燈、大伯梁有龍、伯母范鳳英、三伯梁有輝,以及龍潭姑姑及姑丈梁桂宜、劉興隆與關西的范振雲舅舅,還有曾經關心這項計畫的所有親戚朋友。走訪過程則要感謝臺三線沿路曾帶領及協助過我的地方里長、在地耆老與社區居民,也要謝謝近年來參與研討會時,在會中給予方向建議及指教的師長,以及眾多無法一一列於此處的同儕友人。對自已而言,這是一本嘗試和各種「界線」上的歷史鬼魂對話的書,也是一本關於「浪漫臺三線」兩側的客庄與部落的書。試圖讓自己理解在假日時充滿觀光客、饕客、登山客、露營客、單車族、重機族的「臺三線」周圍,那一道界線至今仍在的影響。也許,現在述說這段歷史,某種程度上是幸運的,在整體社會環境氛圍有所轉變之際,似乎更有契機去開啟理解和諒解之路。最後,要特別感謝羅烈師教授、王振武老師、廖志軒理事長與陳金萬前委員,分別從客家、泰雅、道卡斯與凱達格蘭族人、後裔及研究者的角度,為本書撰寫精彩的序文。也要謝謝游擊文化出版社的許家旗先生,在書籍校對和編排上給予協助與寶貴建議,讓本書能以更完整的面貌呈現給讀者。
目次
出版緣起 重啟對話:解構北臺灣客庄與原民的歷史噤聲/林淇瀁(向陽)
推薦序 未完成的土地保衛戰/王振武
推薦序 寂靜之後,秋蟬開始唱歌/陳金萬
推薦序 家族歷史的追尋/廖志軒
推薦序 臺灣山林,豈止剩下浪漫?/羅烈師
作者序 傾聽由「眾靈」所牽動的記憶
本書的用詞及考量
前言 往返交界帶
族譜:回到鬼鄉/內山:浪漫臺三線?/衝突:定居者與原住者/界線:跨界流動的諸民與眾魂/部落與客庄:村里化的歷史/記憶:歷史的視差
第一章 獵場.豐饒之地
Mgaga:獵首的起源傳說/眾泰雅人的到來/從Tranan到Mutu/Hkuy Bilus:甘蔗之灣/閩客人群的到來/平原:沿海的行徑/山嶺:高地的視線/番社諸公廟/之巴社與青山番/土地是何人?/土牛溝:異族的地界/隘口寮伯公祠
第二章 異族.遭逢之地
隘寮頂與生番立葬/老莿桐與七姓公/竹塹埔:異族之亂/叛民、流民與奸民/家譜中的三氏婆/鹿場的劃界/吧哩嘓與殺人窩/名登堂與向天公/魂歸飛鳳丘陵/上三墩的國王宮/十四股窩:神靈佔地/逃往山野的道卡斯
第三章 頭顱.襲奪之河
河西的番仔寮/大嵙崁溪/內柵與大姑陷隘/三層埔的城仔/頭寮城:tatak tunux/溪州城仔:退移之地/越山入墾之徑/水流東:交易之地/阿姆坪:十四命公/Mgaga:獵首儀式/泰雅的戰刀
第四章 屍身.斷頭之河
被趕到山邊的人,被趕到山上的人/菱潭現地行動展/龍潭大池/刣人崎與三坑仔/霄裡社與大銅鑼圈隘/泰雅耆老的記憶/大坪:武裝聚落/石門峽與銃櫃崠/Marlin:馬麟埔/粗坑:坭銃櫃/義民烈士祠/客庄的平埔族人/血染的山林
第五章 殺戮.食人之地
橫越牛欄河/移動的隘線,獵場的復往/山村中的傷亡者/「番割」家族/牛鬥口:死亡的界線/湳湖:宴席的陰謀/一顆頭顱換一畝田/獵首生態學/出草山與山神/殺番賞/食其肉,剔其骨/番寮溝:血流之溝/亡魂何處去?
第六章 血壤.祖遺之地
泰雅女子/大嵙崁撫墾局與蔡家的發跡/馬武督社的休戰或和解?/紛擾的淺山:帝國官員的見聞/和與戰:山貢金與番頭崠/金廣成墾號/交界考:走踏活動/退與進:童山濯濯與焚廟驅神/大嵙崁市街的番肉販/神與鬼:靈力的漲與退/風水、骨骸與祖塔/馬武督大山圖
第七章 烈戰.鉅變之地
重返前沿的山村/柑仔樹下:交易之所/大坪庄獵首事件/八股、十股、湳湖:結仇之地/湖肚庄出草與食蕃肉事件/石門:鄰近之界/溪州山、十寮、馬福:迫近之界/夾境中的山村人/彩和山、檔耙山與赤柯山:佔境之界/臭臊坑:血淌的溝谷/南援北戰的馬武督人/泰雅化的漢人/戈尤浪:最後之戰/瓦旦.馬瀨/大庭頂:迴盪的炮仔聲/瘟疫之地/土地的悲歌/巴度.巴燕
第八章 尋靈.眾魂之域
死者的群落/問伯公神/迴繞的雞鳴聲/殺人窩與㓾人店/Utux:泰雅之靈/衛王爺與衛平星之墓/福任公之墓與番仔塚/無頭之鬼/飛頭之鬼/祖父的噩夢/沒有頭顱的父親/義勇與忠魂
第九章 幽谷.著魔之地
石門大壩/閻王崎:山峽與谷口/山河交殺:落山的出草路/客家文化傳承與發展研討會/顱骨與食人記憶/老茶樹與大石爺/是進到山裡,不是退到山裡/受咒詛之地/惡靈與日本兵鬼/客庄與部落的墓地/「番」與「人」/仙島之行
第十章 記憶.越渡之地
無頭祖公婆/不義之物:碑記與方志/淺山地帶的哀愁/部落裡的異鄉人/馬武督部落的傳統領域/傳統領域之外:一瓶米酒換一塊土地/客家庄裡的泰雅部落/逆寫北臺灣客家開發史/轉換視角:山地前沿的部落史/臺三線:觸動記憶的流轉之地
後記 歷史的熱度
附錄 問魂、尋屍的旅途:給「斷頭河」的一封信
書摘/試閱
第九章 幽谷.著魔之地
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能夠留下幾張攝影的淺山部落與聚落,不是外地攝影師、人類學家的調查或行旅之地,便是殖民政權在理蕃事業下的戰地寫真。雖然,很多淺山地帶的村落與住民,在當時沒有留下任何一張照片,要到一九三○年代之後才有一些攝影。但是,這些沒有明確影像留存之地,反而在民間留下繁茂多樣的記述——這些腦內景象,於世代繁衍的家族之間構成一種異質「潛像」——某種尚未成像、還未顯影的記憶、傳聞或鬼魅軼事,指向歷史敘事還未定型、仍在變化中的動態,維持它被講述的活力,不斷流變為各種言說版本的野史,並透過地方口碑、廟誌、墓塚等形式雜揉在一起。
漢人村落中心的廟宇、聚落四境的地名、廢棄山野的舊隘道、記憶中的人群地界,每個時期的劃界工程、建物元素與基礎設施都彼此混雜堆疊,或多或少影響今日人們的日常。對我而言,它們就如同一座網絡狀的歷史迷徑,相互交錯又曲折縱橫。往往在走入現場時,才意識到各種異樣物質與檔案堆疊出繁複的歷史,經由文字化的過程被層層抽取為簡化之物。若僅將目光停留在那寥寥幾張的白紙黑字與文書檔案上,沒有役使自己親臨現場,那麼所見的歷史,永遠是經由他人之眼揀選的結果。
置身現場,表面上所有事物看似毫無來由地堆積在一塊,實際上都有其線索與生命時間的。大嵙崁溪沿岸兩旁的「三坑仔」與「大坪」、「溪洲」和「內柵」等聚落就屬於這一種地方,尤其內柵聚落作為一處最早開發的河階地之一,昔日「內柵城」的潛型仍然存在。以庄廟為中心,左右兩處仍稱「東內柵」與「西內柵」,兩處各建一座土地神祠,銘刻著異族「侵擾」地方的歷史。聚落東邊河階坡崁長滿刺竹林,一排排地佇立於村落前線,對照日治初期的等高線圖,昔日坡崁跟今日高度差不多,村落後頭仍倚靠著大嵙崁溪。「內柵」並不是單一個案,淺山地帶有著數座防衛輪廓仍然完整的聚落,留下一道道武裝侵墾的陰影,至今不曾散去。
閻王崎:山峽與谷口
閩客人群往「番界」推移時,臨山村落必須藉由武裝隘防組織才能存續。經歷一百多年的廝殺,也讓今日漢人視角下的「內山開發史」,注定成為一部被多重魔魂、鬼魅纏繞的敘事。在斷頭河遺留地形上,這處大河的遺棄之地,坡、崁、坪、坑、坵、山、崠、崎、窩等地形彼此鑲嵌,共構一處死者的居所,溢散出鬼魅感的同時,也對我產生一種異樣魅惑。鳳山溪流經新竹新埔一帶,有條支流名為霄裡溪,源頭位於昔日龍潭霄裡社的境界。從新埔的照門聚落沿著霄裡溪右岸往下游走,會經過一處地勢極為陡峭的河岸,被當地耆老稱為「閻王崎」。
為何名為「閻王崎」?據地方志記載,「山前頗平坦,山後為崩崁,險峻陡絕」。此「山後」,從新埔照門方向來看,則為山前,其「山後」則接新埔大屏山脈,乃當年新埔往照門必經之地。曾有泰雅人或竹塹社族人多次在此伏擊路過的漢人:「早期新埔往照門無公路可行,居民多沿山邊徑通行,位於今大茅埔橋頭附近路段,坡度陡地形險惡,『生番』常埋伏在山坡下獵殺過往旅客人頭,居民因稱此地為閻王崎或閻王溜。」「閻王崎」可以視為身處帝國邊地的閩客人群,對於第一現場親身遭遇的標記。這處不見於官修史冊經傳,也沒有出現在官版地圖中的地名,僅在地方人們口頭之間流傳,具有鮮明野史性質。地名形成時間已經不可考,如同「殺人窩」、「刣人崎」或「㓾人店」的地名,這類命名不一定虛假,反而映射出民間社會的歷史記憶,指向了此地的凶死傳聞。
「閻王崎」較為不同之處在於,是將地方上「生番」殺人的事件與漢人的地獄觀念結合而生的命名,而不僅是直接描述、指認某一地方有「生番」殺人之事。有句諺語說,「閰王註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這種觀念意味著閻王判人死亡,沒有人能夠不死,反映出漢人「生死由命」與「天注定」的觀念。「閻王崎」背後的命名原由,似乎是漢人將死者前往陰間去面見閻王的原因,歸咎於被「生番」送去見閻王,或是會被原住民「帶走」性命,是被閻羅王「判死」,命定時辰已到所致。漢人對於地獄的詮釋,某種程度上與當時漢人對於「生番」的想像有關。也許是在現實環境中,面對完全陌生、恐怖及未知的他者時,漢人自身對於傳統地獄觀念的變異與修正,成為深深烙印在「崎」這種陡峭地形中極其細微而複雜的精神變異。再一次地,地形驅使著人們著魔,人們賦予為一處地獄的入口,也是閻王審判所在之處。漢人傳統地獄觀念下的鬼卒與當時「生番」在形象上產生意外的交逢,角色與功能也進一步結合,衍生成一場夜夜相纏的地獄之夢。
除此之外,在作者佚名的〈渡臺悲歌〉中,也可以看到生番形象在觀念上被與漢人地獄觀、閻王、鬼卒明顯串聯在一起,甚至從歌謠的描述裡,已經隱約將地獄鬼卒與生番「合而為一」,形成一套思維次序:「勸君切莫過臺灣,臺灣恰似鬼門關……面目一身坭鬼樣,閻王看見笑連連……遇著生番銃一響,登時死在樹林邊,走前來到頭斬去,變無頭鬼落陰間。」歌謠中提到,臺灣如同鬼門關,而掌管生死的閻王彷彿在等著每一個來到此地的人,這裡離死亡、離陰間地府非常近,而死法則大多是被射殺或斬去頭顱,最後成為無頭之鬼流落陰間。換言之,閻王與「生番」在這裡的角色,對漢人來說如同一種共謀關係,地獄觀底下的閻王與帶來死亡的「生番」,被同時放置於造成凶死因素這一端,「生番」出沒地區就像是地獄,他們如同活在世上的鬼卒,可以將漢人殺死,送其魂魄到陰間,甚至帶往地獄面見閻王。「崎」是一處死亡之地,也是著魔之地,使人們精神與觀念產生錯動。
漢人將「生番」與鬼卒身分的類比、混用、相結合,使得漢人的地獄觀、審判、受刑,在面對他者時產生了矛盾與弔詭的文化想像,但也反映了與異族接觸過程中,文化觀念的變異。這種對於原住民族人形象的形塑與再現,透過地獄想像,已經滲透進傳統漢人自身相當重視,甚至是深信不疑的生死觀、世界觀之中。透過山峽與谷口,娓娓道出一段隱微而複雜的精神變異史。
山河交殺:落山的出草路
溪河是進入「內山」的通道,寬敞的河床、河階與沖積谷地,視線良好時可以直望「內山」魅景。層層山嶺則會形成視覺阻隔,地理空間的遮蔽也造成人群活動的不安。不可見的環境被漢人與歷代外族認為是無法掌握的凶險之處,也是讓早期來到臺灣的漢人恐懼山區的原因之一。相反地,河谷則是通往山區的徑路,少了視線的屏蔽,增添了不少景深。所見之處便是雙腳可及之處,多數漢人因而沿河上溯亦沿河墾殖。峽谷橋接著上游與下游的水道,向內/外敞開,也嫁接山稜的兩端,以中斷山脈走勢來擴展地形的複雜性。清代漢人早已將「生番」與「山」的凶險連繫在一起。一如過去霄裡溪岸的「閻王崎」,今日馬武督一帶的峽谷,無疑也被漢人賦予這一種凶險意涵,總是徘徊著各種各樣的凶險記憶:
我們客家人也會殺原住民,馬武督的番仔全部就一直被趕進山裡。以前,在馬武督的外邊,不會被番仔殺,但在牛鬥口那邊,只要我們越過去就會被殺,他們出來也會被我們殺。
牛鬥口那邊有一個山谷,大竹坑這邊也有一個山谷,兩個地方都有山谷。牛鬥口最低的地方,叫三十八份;大竹坑最低的山谷,叫十四窩。以前原住民會過來到大竹坑砍人頭,但客家人也會殺原住民,把馬武督的人一直趕進山裡。牛鬥口那邊,番仔出來就被我們殺,我們進去也被番仔殺。
兩位耆老的口述,某種程度代表漢人的觀點,因為位處在山谷的一側,望著山谷景象的內與外,從自身視角傳述不同的記憶。不論是哪一處村莊,只要有山的地方,客家耆老們不用經過考證,便能展現出一種言說的自信,大方且毫不含糊地指出昔時原住民「落山出草」的方向。這幾年下來,時常聽到老者口中「番仔」前來攻擊、襲擊先人,以及前來的方向與概略位置,共有「山崁下來襲人」、「沿溪、圳而下來襲人」和「從山谷凹地處進來」等說法。雖然無法證實口述真確性,但是從耆老記憶中的隘址,以及對伯公廟建立位置的描述,人們對於空間環境的認知,顯然與兩方人群衝突歷史過程和村落周遭的地形條件,有著密切關聯。泰雅人與漢人侵墾者各自依照地形勾勒出移動行徑路線,在斷頭河遺留的地形中,河階是被用來潛伏及守望的極佳地勢,對於漢人聚落的防禦考量來說,就是某種村落的境界:
聽老人家說,以前從龍潭銅鑼圈這裡去關西的路上,時常有人被殺。他們是從番仔窩下山來殺人,番仔窩就在這裡過去沒多遠,以前那裡有住番仔。
以前番仔會沿著水圳下來到龍潭四方林這裡殺人,從山上到冬瓜山那個方向過來。
以前從大溪買東西、帶東西回來龍潭三坑仔的路上,長輩們都會怕被搶劫,因為路上有土番、土著。
以前有原住民從大溪番仔寮那邊下來出草,龍潭三坑仔這裡有幾個人,在現在開庄伯公廟後面的山坡上被殺掉。
我是聽過龍潭大坪這裡有幾個人被番仔殺掉,沒有很多人啦。以前他們會從大漢溪渡河過來殺人,就這樣而已。
番仔大部分是從大竹坑和關林排那裡,或是從湳湖越過山這樣來到關西湖肚這裡;番仔是馬武督的原住民,從馬武督和鳥嘴山那裡來。
在地方記憶裡,原漢人群衝突時常發生於聚落邊界,同時也是河階崁緣。族人的獵首行動,也反過來時時刻刻在影響閩客人群對於地域意識與村落建構的領域、地理想像。當代漢人耆老往往認為泰雅人並非居住於「這裡」,而是來自村落之外,獵首則被視為「外力侵擾」。儘管泰雅族人從此離去,昔日的影響力仍未消失,反倒被持續保留在漢人處理村落空間的細節之中。特別是伯公祠廟宇空間與村落四方界境的關係,都離不開與泰雅人互動的過程,一再強化並顯示出當時泰雅族人在漢人記憶裡的種種作為:「特常侵犯」、「打家劫舍」、「獵取人頭」。這是一處動態時空,從族人回返到此地的捍衛行動,到外來移民闢地築隘、建庄設廟的系列工程,雙方呈現一來一往的過程。儘管都是片面的再現,也無法呈現真實面貌,但卻隱隱地反映出族人似乎藉由不斷回來往返這些曾經的社域與獵場,長久擾動著當時漢人在精神層面對於空間感知的建構,以及地理感的部署。
選擇定居於此地的閩客人群,打從最初到此墾殖之時,文化和宇宙觀之間的互動、牽動與連繫,就在一系列接觸行為中合併展開了:哪裡的土地不敢使用?何處需要耗費財力、人力著手進行空間築構?山川應該如何命名?何處設置隘寮、興建伯公祠?廟宇與村莊四境位置怎樣配置?地勢風水如何與人群運勢彼此牽扯?這些林林總總潛藏在意識深處的地方感、地理感知與在地經驗,是如同伏流般隱而不顯的作用力。與其說原本生活於淺山的原住民,在閩客人群拓墾過程中被驅逐入山,使土地流失到異族後裔的手中;或是說,因為漢人已成為「定居型殖民者」,所以族人「早就拿不回過去被強佔的土地」、「被抹除在這片土地之上」、「成為歷史中無聲的一群人」等,這類聽了令人窒息、厭煩的悲劇式結語;不如說,族人反而參與了沿山地帶漢人傳統空間建構的發展,以及土地命名的過程。
在村落前方一連串橫貫南北山脈走勢的V形山谷,其實是一系列沿山地帶的峽谷群之一。我常隨著地理形勢走入山中,總會如此地望「山谷」生義,從更廣袤的角度來看,北臺灣淺山地區呈現一系列W型的河谷與山脊交錯型態。在許多地方,漢人沿著河道往上溯武裝拓墾、逼殺原住民;族人則沿著山脊地勢下山獵首、伺機反抗。在泰雅耆老口述裡,雖然部落與部落之間也會有仇恨,但因為雙方體質與身體條件,要進行獵首與襲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反而是當時人生地不熟的漢人,沿著低處溪河兩岸拓墾,泰雅族人很容易從高地上監視、伺機而動。這也讓山谷和平原接壤處,成為雙方時常爆發流血衝突之地。於是,在山河之間交相襲殺,雙邊人群往往捲入一處難以脫身的死亡境地當中。谷底的血色記憶化為一處死亡地景,流竄出各式各樣的鬼魅傳聞,而魂斷峽谷之人,往往以生命作為代價,銘刻於地形之中。
一般均質化的空間不容易產生鬼魅,反倒是破碎、曲折、角落與幽暗的所在總是鬼影幢幢。斷頭河作用留下的河階地形,也是族人疾步而來的路徑,今日坡崁大多沒有被開發,或僅有低度使用,反而成為山景與記憶纏繞之所。斷頭河的核心地塊,扇狀發散點周遭切割出的碎裂地形,在言說與地景、記憶與經驗的複雜形構中撐出一個死亡舞臺,無頭死者則彷彿透過一種極為不完整的斷片、幾句不連續的話語,無形無影地持續附著在此地人們身上。無頭屍身不是一般臨終安詳的死者,而是與所處環境緊密相關的外力死亡。散落於山河之間的屍骨、凶死位址,是一種「山川食人」的吸納結果。在這個過程裡,謠言、傳聞與祭拜場所被釋放了出來,鬼魂即在這處大地的吞吐之間持續現身。人食人、土地食人、人食土地,交錯在斷頭河地形上,迴盪在漢人「殺番食肉」與原住民「奪顱飲酒」的地理記憶之中,遍布著無數條不可見的「鬼徑」。
(本書的「番」之用詞,為地方漢人耆老慣用之文字,為貼近在地耆老的口述用語,並揭露及呈現當代記憶型塑的現實面貌,因此保留閩客耆老的口述文句。本書也對此問題進行描述和反思,在此並無歧視或不敬之意。)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