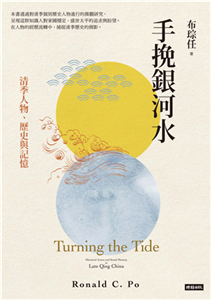手挽銀河水:清季人物、歷史與記憶(電子書)
商品資訊
定價
:NT$ 420 元優惠價
:
70 折 294 元
閱讀器:書紐電子書
下單可得紅利積點:8 點
商品簡介
商品簡介
以不同視角展讀清季歷史人物眼中的時代洪流,
在行雲流轉的文字中,
看到一個龐大揉雜的歷史空間。 本書通過對清季個別歷史人物進行的微觀研究,
彰顯他們的意志與信念,
呈現這群知識人對家國穩定、盛世太平的追求與盼望。
在人物的經歷更迭中,捕捉清季歷史的側影。 手挽銀河水,一展函夏雄圖。 自乾隆遜位、嘉慶登極以降,清帝國的內憂外患紛至沓來,衰世之象耳目昭彰。在這個日益多事的非常時代,不論是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是在華的西洋顧問,也不乏矢志力挽狂瀾、積極追尋改革蹊徑的大小人物。值得注意的是,這批文化學人在苦思維新出路、急切謀求復興富強之際,卻不約而同地遭遇各式各樣的問題與制肘,致令他們對自身的經歷、信念和傳統涵養作出探問與反思…… 【本書提要】 大家可曾想過,「曾左李」這個詞組,究竟是一個隨機生成的簡稱或表達,還是一個被建構出來的時代標籤呢?至於我們非常熟悉的「士、農、工、商」,真的是一個顛撲不破、不容倒毀的社會位階嗎?晚清學人薛福成所論及的「新四民觀」,是對舊說的一個徹底顛覆,還是一種概念的轉移?另一方面,「幕府制度」如何與清季政經格局息息相關?而在幕府之中,我們又可以找尋到歐美幕僚的身影嗎?這些主題看似瑣碎細微,卻可以幫助讀者們梳理、鉤沉與拼湊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與歐美世界的歷史圖繪。 《手挽銀河水》是作者第一部自選論文集,也可視為其研究路徑和志趣的一個階段性紀錄。集內所錄七文,雖然各自獨立成篇,但彼此之間卻存具內在紋理,或可並讀。作者通過對清季個別歷史人物進行的微觀研究,以小見大地呈現並解構一系列涉及政局更迭、歷史記憶、人才流動、文化碰撞等宏觀性課題。全書結合學術思想史、治亂興衰史和文化交流史等取徑,以期彰顯歷史人物及所處時代,乃至後世記憶之間千絲萬縷的脈絡與扣連。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