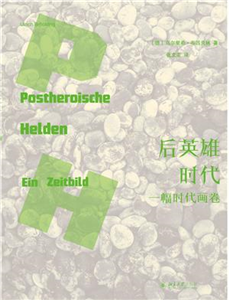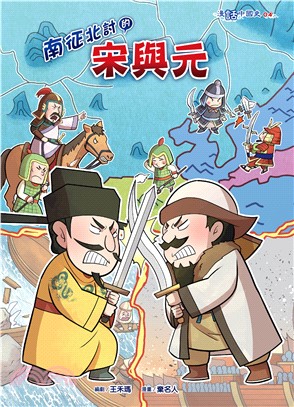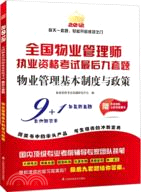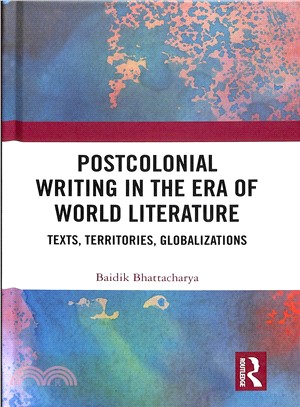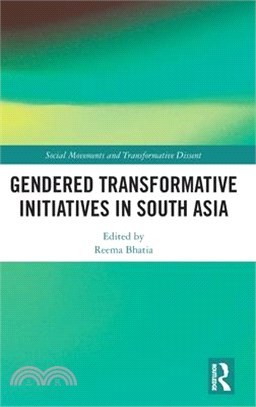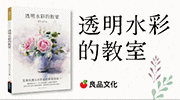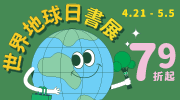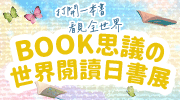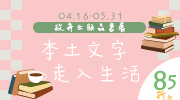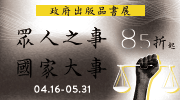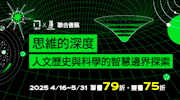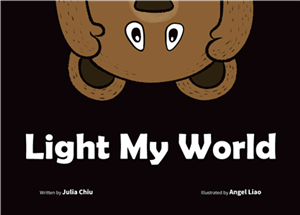后英雄时代:一幅时代画卷(電子書)
商品資訊
ISBN:9787301345863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德】乌尔里希·布吕克林(Ulrich Br?ckling)
出版日:2024/01/01
裝訂:電子書
檔案格式:EPUB
商品碼:2222221991846
商品簡介
一直以來,從文學作品中的主人公,到戲劇舞臺、電影熒幕上的主角,英雄傳奇或英雄故事深入人心。但直到今天,人們尚未就英雄主義的價值問題達成共識。
德國文化社會學教授烏爾裡希·布呂克林,從文化社會學的元視角,以巧妙的論點和優雅的筆觸,探尋英雄在當代社會文化中的地位。通過探討西方的漫威英雄、體育明星等文化現象,認為英雄崇拜是後英雄社會中的一種文化技術,具備自身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後英雄時代:一幅時代畫卷》涉及對近代英雄主義的反思、英雄故事的敘述模型、英雄化的願望和去英雄化的趨勢等前沿問題,思想性和可讀性俱佳。
作者簡介
作者:[德] 烏爾裡希·布呂克林(Ulrich Br?ckling)
文化社會學家,1959年出生,現任德國弗萊堡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文化社會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社會與自我技術的社會學,文化社會學,人類學,軍事社會學。
譯者:張文奕,女,北京大學漢語言文學學士、亞非語言文學博士。主要著作有《東方民間文學》(合編)。
名人/編輯推薦
1. 話題具有廣泛的讀者基礎。“英雄”這一話題深入普通人日常,易激起讀者興趣;
2. 討論具有前沿性和啟發性。從文化社會學的元視角,試圖對英雄主義的價值這一懸而未決的問題達成共識;
3. 素材豐富,可讀性強。從神話到史詩,從戲劇到電影,論點巧妙,筆觸優雅,凝練優美。
4. 適用於各個年齡段的讀者。既有助於令對英雄感興趣的專業學者、大眾讀者激辯思想,也可以為初高中教師、學生開拓寫作思路。
序
導言 英雄與後英雄:對立共存
一篇關於英雄,也包括後英雄之英雄的社會學文章,需要自陳其意義所在。如果這篇文章是為診療時代症候(Gegenwartsdiagnostisch)而作的,就更應如此。我們通常會把英雄與勇武好斗,甚至帶有悲劇性的人物聯繫起來,他們做出超越常人的舉動,對抗強大的敵人,抵御災難,在逆境之中砥礪突破,為了正義的事業而置自身於危難之中;他們漠視規矩和老套的繁文縟節,並因此受到尊敬和欽佩。一份包含上述內容的文獻,與其說是社會學的時代圖卷,倒不如說是浪漫故事、軍事檄文、教諭文學或大眾神話的圖卷——社會學處理起英雄化的問題來終歸不易。因為它感興趣的是小人物,而非偉人;更注意頻率分布,而非奇點;它關注社會秩序,而非那些不同尋常的事件。男英雄或女英雄是否必須存在?對此必要性的疑慮絲毫不亞於對英雄生成機制本身的質疑。社會學將英雄主義作為意識形態來懷疑,將其歸為那個前現代的、等級僵化的世界裡無可救藥的過時遺存。不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它對理解當下幫助都有限。
面對時代症候,不僅要找到正確的答案,更要提出正確的問題。毋庸置疑,為了描述當代社會,比起考察英雄形象的危機和變遷,有更好的研究路徑。就算是對英雄特質的問題化處理也不一定總能達到批判的效果:我們常常打著去魅的旗號,卻在無形中繼續著英雄所表征的那個等級世界觀。從這個意義上講,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每當‘英雄’備受推崇時,我都會問這樣的問題,誰需要英雄以及為什麼需要英雄”1 阿這一評注應一並引申至社會學研究中來。這一問題意識同樣可以被用來質問當下,即“我們生活在後英雄時代”這一命題。這一時代診斷容易助長一種錯覺,即一種令人滿意的、扁平化的後現代社會不需要英雄,也無須創造英雄。概因後英雄社會視個體之“偉大”為譫妄,要以談判溝通來解決矛盾衝突,既不願意也不能夠做出志願犧牲的行為。因此,在後英雄時代,我們同樣需要問:誰需要英雄,以及為什麼需要?
不管是英雄敘述還是其後英雄轉向都充斥著政治滲透,我們有必要對其意圖和效用質問,與此同時,也可以借此來獲得解鎖當下的力量:這些英雄和後英雄敘事可被視作範例,展現社會制度對其成員的期待,以及這一制度如何取信於人,它以哪種價值觀念、行為準則和情感機制來約束人們,它準許或褫奪什麼樣的主體性,又讓哪些想象成為可能。此外,本書還探討規範化的願景和層級制度,評估一致性和差異性、主體訴求和公共訴求、個人在高度複雜的機械化運轉社會中所處的位置、領導範式、自我犧牲精神,以及由之而來的面對死亡的態度問題,也評估性別角色或宗教紐帶的重要性。誰需要英雄人物,為什麼需要;誰又否定這種需求,為什麼否定,這些問題都涉及對危機的認識和對常規化的期許。
上述話題充滿爭議,所以截至目前,人們尚未就英雄主義的價值定位達成共識。筆者接下來的思考,其出發點來自一個充滿矛盾的觀察:一方面,自1980年代以來,“後英雄”這一定語在不同的語境中大量出現,人們宣稱其能夠被用來進行時代診療;另一方面,也是在這樣的社會中,幾乎每天都有新的男性或女性英雄被召喚出來,或者是經典的英雄劇目被再次搬上前臺。唱衰和鼓吹英雄氣概的聲音並駕齊驅。隨著傳統的“英雄陣地”逐漸褪色,此前從未出現過英雄的領域裡繁衍出了全新的英雄。英雄主義敘事的號召力可能減退了,但其娛樂價值似乎並未被動搖。那些現實中我們不忍再見的被縛的榜樣,被我們在想象的世界裡更加狂熱地追尋。
有關未來戰爭的政治和軍事科學論述首先察覺並指出了後英雄時代的來臨。據其論點,西方社會不再能夠動員大規模的犧牲,也不再能接受自己的軍隊遭受長時間的巨額損失。這促使他們利用高科技武器系統發動不對稱戰爭,然而,敵手會以殊不畏死的英雄氣概來彌補技術上的劣勢,這就使得他們更易受到傷害。與此同時,組織和管理理論家們公布了後英雄的領導範式。這些範式告別了計劃型政府的樂觀主義,也告別了理性管理的“操縱幻覺”,轉而青睞一種參與式的領導風格,這種風格旨在提升人們自我控制的潛能,或主張在自我面臨的實際選擇中,以後英雄的方式去解決問題,而不再是英雄式的。心理學研究則鑒定出了後英雄人格在當代的社會特徵,它通過不斷適應加速前進的社會變革而獲得靈活性。據說,連流行音樂都邁進了“不反文化的反文化主義”2的後英雄主義階段。還有很多其他領域中的佐證可以補充進來。即便形形色色的討論枝節在很大程度上相互脫節,彼此之間並無密切關聯,它們仍然共同凝結成了時代的畫卷。
“後英雄”幾乎只作為形容詞被使用,這一點令人震驚。後英雄可能會在所有領域被提及,但幾乎沒有任何關於後英雄者或後英雄主義的討論。與其他帶有“後”這一前綴的時代標記一樣,這一定語也無法用精確的概念來闡明。有時,它指一種精神氣質或舉止特徵;有時,它指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階段,或一種作戰形式。“後英雄”也可用來定義一種對治理藝術(Foucault)的理解,這種藝術認識到社會的複雜性,因此拋棄了技術官僚主義治國的傲慢。此外,這一定語也用於描述某些態度和情緒,它們對激情程式(Pathosformel)過敏,對犧牲的呼吁無動於衷,或者拒絕接受毫無保留的身份認同,並且在大多數情況下,對偉人及其事跡崇拜持挖苦諷刺態度。最後,與這類心態相關的物件和文化實踐(Kutuelle Praktiken)也被描述為後英雄。
正如談論後現代並不等同於告別現代一樣,標記後英雄時代的意向並不意味著英雄主義導向的終結,而是使其具有了問題性和反身性。將當下診斷為後英雄時代,意味著在語意上指涉那些英雄敘述的斷裂並與之劃分界限。但是英雄主義號召的凝聚力和動員力絕未枯竭。後英雄主義社會一方面認為英雄形象值得懷疑且已經過時,可另一方面又充分利用著從未間斷過的對英雄的饑渴。這種渴求得到了很好的滿足。漫畫和計算機遊戲的世界中滿是被重塑和被全新創作出的英雄,超級英雄大片實時打破票房紀錄,競技體育中英雄人才輩出。“9·11”事件中的消防員被稱為英雄,氣候活動家、吹哨人和政治自由斗士們同樣如此。需要注意的是,這種英雄主義不再與職責和效忠聯繫在一起,新英雄更被刻畫出反成規和拒絕順從的特徵。英雄氣概表現為勇於表達自我、剛正不阿。英雄氣概成了公民勇氣。與此同時,被指稱為英雄的物件經歷了民主化和日常化。最終,就像大衛·鮑伊(David Bowie)承諾過的那樣,每個人都可以成為英雄——“哪怕只有一天”,抑或如安迪·沃霍爾(Andy Warhol)所言,在大眾傳媒時代,每個人都能擁有哪怕只有“十五分鐘的名氣”。
然而,隨著民粹主義領袖的崛起,另一種英雄類型卷土重來:他不是一個體現法律權威的父親形象,而是反法律權威的帶頭大哥,因為對其人而言,法律不夠專斷獨行。他喚起一個暴力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只有力量最重要,只有那些缺乏同情心的人能獲得機會。他任由追隨者們宣泄情緒,而不去關注社會的繁榮穩定。他告訴追隨者們對哪些人冷酷殘暴可以不受懲處。他將真實與謊言之間的區別置之一旁,唯強調其個人的權力意志:誰對事實核查不屑一顧,誰就可以肆意捏造事實。這些“民間英雄”進行個人表演,商業巨擘、意見領袖和軍閥首腦間相互攀比,挑釁般地展示他們擁有的驚人私產,他們的外表不僅要亮麗炫目,還要表現出一種咄咄逼人的大男子主義,擺出具有男性陽剛之氣的姿態,向女性發出唯有他們掌握著生殺予奪大權,是真正的權勢人物的訊號,但又絕不僅限於此。無政府主義者也很難將他們推翻下臺。他們叫囂著,滿嘴英雄主義伴隨著暴力威脅和對弱者的鄙夷,與胸懷坦蕩、具有大無畏勇氣的平民英雄們(Alltagsheldinnen)形成了鮮明對照。
不同英雄模型之間的矛盾,尤其是在英雄與後英雄範式之間的碰撞,勾勒出當代社會的裂隙與衝突。在本篇中,我將探究這些共時的對立面 (diesen gegenstrebigen Gleichzeitigkeiten),動態考察當代英雄化與去英雄化之間的話語前沿(die diskursiven Fronten)和混合區域。我將討論英雄敘事(及相應的消費)中情感(affektiv)、道德感、合法性和號召性的面向 ,並關注對這些面向具體的相對化處理(Relativierung),批判和消解。因此,我既不附和“我們生活在後英雄社會”這一論斷,也不排斥它。相反,我對針對時代症候而作的二階診斷感興趣。二階診斷考察那些談論我們當下的言說。一方面,在許多不同領域,當下被認為具有後英雄的特徵。另一方面,英雄的生產在我們所處的當下仍然在全速運轉。在這一背景下,有哪些當代特徵被聚焦,又有哪些被邊緣化了?當代英雄主義響應哪些挑戰?“後英雄”這一定語回答的又是哪些問題呢?
風評認為,在診療時代症候的過程中,人們易將個別突出事例泛化至普遍情況,有時只依據個人道聽途說的軼事作出判斷,以致其結論戲劇化地前後矛盾,它忽視新舊事物之間的延續性,優先考慮貼標籤,而不重視分析差異。這些論斷被認為“有趣,但也有一點不可靠”4。對後英雄社會的診斷,將在這裡得到批判性的闡釋。雖然其本根植於當代診斷之中,但也只是作為一種平行的行動而存在,即這樣的診斷或多或少仍然在粗略地使用著同樣的標籤,這些標籤被用來描述迥異的當代現象,它們的效力面和解釋力都是不確定的。
為避免社會學研究容易寬泛的陷井,我在對英雄的社會形象以及英雄主義的驅動力和影響力進行分析考量時嵌入對時代症候的探求(第一章)。它並不等同於一種英雄主義理論(那將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而是一個由異質模塊匯聚構成的啟發性方法,引導我們深入英雄主義理論的核心層面。接下來的部分涉及英雄崇拜與現代社會之間的矛盾關係,是與其相關的思想史研究。我追溯了從黑格爾(Hegel)到恩岑斯貝格(Enzensberger)之間的範式,進行了反思,同時揭示了後英雄主義對“英雄主義的現代性”的摒棄。通過對闡述後英雄人格的社會心理學篇章進行話語分析(第三章),對後英雄主義管理(第四章)、後英雄主義戰爭(第五章)和對那些為後英雄主義社會所承認或是在後英雄社會中產生的男女英雄們的類型學(第六章)進行分析,這些分析將研究視野從思想史移開,並聚焦在當下。材料選擇方面,除了科學論文和新聞素材,我還利用指南類文獻(通常指成功學、心靈雞湯類書籍)和其他流行文化現象,察明英雄人物形象在當下如何以後英雄之名被進行去中心化改造。它將他們發配至不易引起他人警覺的領域,用庸碌的日常生活圈禁其非凡之處,或者將他們置於待機狀態——危機一旦發生,他們便隨時可被激活。在後英雄時代,英雄的形象充滿矛盾,其首要特徵即在於他能夠靈活地在“開機”和“關機”這兩種模式間來回切換。
英雄化的基本特徵之一,是我們無法對它無動於衷。英雄形象以情動的方式蔓延開去。我對此深感疑慮:有太多的情緒,太多的陽剛之氣,太多的道德指摘,太多的自我克制,太多的死者崇拜。在結語部分,我嘗試讓反英雄主義的情動貫穿全書,我將繼續利用它們展開一場激進的質問。在這裡,倘若我寬泛地借用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一本書名,提出要對英雄主義進行“否思”,那就最好不要抱有一種廉價期望,認為在擺脫對英雄的渴求,或者更確切地說,在擺脫“英雄相思病”這回事上可以一勞永逸。這本身就是一種英雄主義的巨大幻夢。只要政治或宗教制度仍依賴於獻身精神,只要被普世化了的競爭仍在驅動人們不斷進行自我提升,並驅使他們參與其中;只要充滿無助感的經驗仍在滋生關於偉大的幻覺,而日常規範仍煽動著人們對僭越的渴望——人們就會一直尋覓並找到英雄。英雄是一種標志,他們出現在哪裡,人們都會必然想到是那裡出了問題。他們又是一種索引,指向社會對個體的要求。即便英雄主義本身及其外在表現看起來與此截然相反,英雄仍然更多地表現為危機出現,而非危機解除的征兆。
對英雄主義的“否思”並不僅限於對其後英雄轉義的描摹。相反,它始於拒絕,拒絕將假定的所謂虛假與真實英雄氣概進行二元對立區分,而不對後者進行審問。需要討論的並非英雄行為本身,而是那些支撐英雄主義的框架:毫無疑問,那些挺身而出與強者抗衡,或者為了挽救他人生命而自願置身於險境之中的人令人尊重、值得欽佩。然而,宣稱一些人是英雄,並要求他人效仿這些榜樣,就將道德情狀變成了規範說教。任何借助英雄榜樣的力量來說服他人,要求後者做出壯舉、犧牲的人,都將英雄用作實現其自身目的的手段。反之,英雄們被推至遙不可及的位置,以致其行為似乎從源頭上就無法被復制,這鞏固了一種秩序。在這種秩序裡,一些人抬頭仰望,而另一些人被他人仰望;一些人的職責就是領導,而另一些人寄望於被領導。英雄模範超義務地承擔著履行著自己的分外職責,他們也許能起到鼓舞人心的作用,但不得不提的是,他們主要通過讓人良心不安來達到這一效果的。
從這個意義上講,對英雄主義的“否思”意味著把英雄化理解為一種號召手段,在它的影響下,人們受到誘導,抑或有意識地誘導自己做出壯舉,承認等級制度,把社會看作一場持續的斗爭,並為了實現更高目標而將自身幸福旁置。這種號召的效能也源自英雄主義敘事的魔力。正是感人至深、激動人心的傳聞故事,促動我們將男女英雄們捧上神壇,我們想要效仿他們,或者沐浴在他們的榮光之中。因此,對英雄主義的“否思”總意味著講述不同的故事,或用不同的方式講述故事。
目次
目錄
導言 英雄與後英雄:對立共存 / 001
第一章 英雄主義理論的模塊 / 013
1.獨特性 / 019
2.僭越 / 028
3.斗爭 / 031
4.男性氣概 / 035
5.行動力 / 043
6.犧牲精神 / 049
7.悲劇 / 054
8.道德感 / 058
9.審美營造 / 066
10.神話 / 069
11.教育學 / 075
12.類型學 / 078
13.歷史編纂學 / 081
第二章 英雄精神與現代性 / 087
1.黑格爾的英雄 / 088
2.社會主義英雄精神 / 098
3.英雄主義的現代性 / 106
4.英雄主義式動員的過度與崩潰 / 125
5.泥沼中的英雄 / 130
第三章 後英雄時代的輪廓I:主體 / 139
1.英雄自我 / 140
2.後英雄人格 / 149
3.英雄之旅中的自我 / 152
4.靈活變通 / 156
第四章 後英雄時代的輪廓Ⅱ:管理 / 159
1.創造性毀滅 / 160
2.後英雄管理 / 170
3.市場法庭 / 179
第五章 後英雄時代的輪廓Ⅲ:戰爭 / 183
1.後英雄領導 / 184
2.後英雄戰爭 / 188
3.後英雄社會中的英雄共同體 / 192
4.盲區 / 200
第六章 後英雄時代的英雄 / 209
1.日常英雄 / 210
2.體壇英雄 / 217
3.超級英雄 / 222
4.強悍的男人,勇敢的女人 / 230
結語 英雄主義之“否思”? / 239
致謝 / 251
注解 / 253
書摘/試閱
結語 英雄主義之“否思”?
考察後英雄時代的主體、管理和戰爭,其當代診斷清晰地表明,英雄式詢喚在多大程度上仍然存在。通過對當代男女英雄人物陳列式的描述,可以看出他們對後英雄主義問題意識的吸納度。因此,應該避免發布英雄主義的訃告或發布英雄主義永存的主張。英雄傳奇之所以存在,是因為它們滿足了一直延續至今的利益和情感需求;它們會發生變化,而當這些需求所依托的形勢與情勢發生變化時,英雄傳奇也隨即更迭。正如我在本書中所嘗試的那樣,人們可以並從考察英雄主義發生轉變的過程入手,追溯社會變革的歷程。然而,很難堅守一種“客觀中立的”遠觀者的姿態,要寫清英雄主義,必定會涉及對它的價值判斷。無論如何,隨著這裡勾勒出的時代畫卷的輪廓越來越清晰,英雄傳奇,包括那些後英雄之英雄的傳奇,在我心中激起的不安也越來越強烈。
這種不安推動我嘗試對英雄形象進行批判,我將英雄形象看作一種解釋模式、一種行動的命令和一種關係形式,簡而言之:一種個人和集體的取向模式。我從 2019 年去世的社會學家和社會歷史學家伊曼紐爾·沃勒斯坦那裡借用了“否思”(kaputtdenkens)一詞,這遵照了他本人對英文“unthinking”的翻譯建議。沃勒斯坦想從根本上質疑歷史社會科學的基本認識論概念,他所創立的世界系統分析和對英雄所指的考察幾乎沒有共同之處。但正如發展範式(Entwicklungsparadigma),英雄敘事也預設著觀點的導向和行動的導向。
有時甚至在同一個方向上:“我們需要英雄。”例如,精神分析學家克裡斯蒂安·施耐德(Christian Schneider)使用了“別開生面”這一現代基本母題,“因為他們是調節社區和社會烏托邦需求最主要的人物投影。社群總是面對兩個問題:自我保護和自我超越。英雄人物涉及後者。我們生活在熱血滾燙的文化之中,我們不斷需要新的目標,需要受到超越自我和超越日常事務的激勵。這正是英雄所提供的。他們指向超越的東西。如果你沒有這些衝動、沒有烏托邦、沒有對於未來的憧憬和追求,那麼人們在一個社會中共同生活的機制就會變得脆弱”。英雄作為代際發展的推動者——這讓人想起黑格爾對“世界歷史個人”的命名,和他一樣,施耐德知道引領進步的主角們踏過尸山血海。“但凡說到英雄,自然會提起死亡,更準確地說:謀殺。”他在同一次訪談中說道。當然,這就產生了對合法性的需求:“古典的英雄不會自私自利。他總是為群體服務。他打破殺戮禁忌,以保護群體,對外捍衛群體及其價值觀。”這種以集體利益為名的英雄式暴力只會強化與其一致的現代的歷史觀念,即將歷史看作敵對集團之間的斗爭。“我們”需要英雄,因為只有這個“我們”感受到來自其他人的威脅,並且只有在永久動員起來對抗外部威脅時,我們才能體驗自己是“我們”。——英雄的本質:一種人格化的群體利己主義行為。
英雄主義在道德上也出現兩極分化:要麼只有勝利才重要,只要目的高尚,一切手段都是合理的;要麼英雄即使在戰鬥中長期失敗,仍堅守他的原則。兩者都需要對自己和對環境冷酷無情。妥協能力並非英雄美德的一部分。 恩岑斯貝格所指的憂鬱的“回撤英雄”(Helden des Rueckzugs)是英雄行會裡的非典型代表,他們是反英雄,無人為其豎立紀念碑,也無人稱言對其崇拜。與此同時,英雄的語言受制於苛刻的語法:最主要的部分是一貫如此的!任何要成為榜樣的人都必須將其堅持到底。最好謹守笛卡爾(Descartes)的準則,“在行動上盡可能堅定果斷,一旦選定某種看法,哪怕它十分可疑,也毫不動搖地堅決遵循,就像它十分可靠一樣”。即便南轅北轍,只要你走的時間足夠長,走得足夠遠,就一定能在漫漫森林之中找到容身之所。
這番教誨肯定不適合用作道德指南。世界太複雜,本無原則可循。英雄主義將矛盾衝突化解為二元對立或戲劇化其不可解性,來緩解模棱兩可的矛盾衝突。最後,英雄戰勝邪惡勢力,悲劇性死亡,或是在戰鬥進入下一輪之前得到短暫的喘息。透過英雄的眼睛,世界呈現為黑白相間的樣子。灰色的混合區域會消失,並且不提供其他顏色——英雄的本質:一道簡化程序。
英雄榜樣保護我們免於平庸和停滯,這是所有為英雄辯護的論點中反復出現的論點。但這再也不能令人信服了。必須始終優先考慮創新、增長和消除邊界的前提是值得懷疑的。在全球變暖的時代,熱烈喧囂的社會及其英勇的火力加速器理所當然地聲名狼藉。對奧多·馬庫阿德“馬克思的第十一篇‘費爾巴哈(Feuerbach)論文’離間了歷史和哲學這對鐵哥們”這一妙語稍作調整:英雄們“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改變了世界,但重要的是不要傷害這個世界”。最不需要的就是英勇的非凡人物。有太多的利害關係,關鍵不是憑一己之力所能扭轉。英雄傳奇裡掩藏了太多人的輝芒,這樣便更能凸顯出那一個人的閃耀奪目;它們忽略了其他眾人的參與,而把最終的勝利成果歸功於一人。然而,最重要的是,英雄傳奇包含的是個人主義的謊言,即一個單獨的個體如果全力以赴去拼搏,那所有的艱難險阻、致命挑戰也都可以克服。任何接收到這個信息的人都可以沉浸在偉大的幻想中度過一段時間??,然後才不得不更加強烈地感到挫敗——英雄的本質:一種關於責任化的話術,它一面讓人有能動性,一面又同樣程度地讓人“負罪”。
約瑟夫·坎貝爾的追隨者將有關英雄進階的神話作為成功學販賣。英雄可能會猶疑並與自己斗爭,但最終他超越了自己,他出發、擊敗怪物並最終迎娶了公主。這樣做的代價至少是暫時的人格分裂,英雄主義自我意識的形成過程是一項高處不勝寒的事業。甚至崇拜者為了向英雄表達致敬,不得不將英雄旅人與其社群分離開來,以此來暗示著他是個特殊之人。一個只由英雄旅者構成的社會更可能是一個令人十分難以忍受的自大且自戀者的集合,不會是一個團結的地方。正因為英雄之旅將每個人都送上了同一條旅程,其他有志者只會阻礙自己的神化。 ——英雄的本質:一次自我之旅(Egotrip)。
然而,勇氣、決心、勝利甚至個人更願意為集體作出犧牲,這些似乎非常直接地打動了我們。誰會懷疑英雄榜樣帶來的啟示呢?那麼,不是一切都取決於正確的選擇嗎?這是那些不相信英雄的必要性的人的論點,但他們至少相信英雄的必然性,因此試圖用道德上無可挑剔的變體來置換那些令人反感的變體。但是關於勇敢的日常英雄和不屈不撓的反抗者女英雄的故事也受到個人主義偏見的影響。旨在減少無力感和鼓勵該出手時就出手的做法將注意力集中在少數人的工作上,難以從上層構築起反抗力量。“對個人責任和對個人干預的敘述維持了現狀,無論是關於社會不平等、貧困還是污染,”美國公關家和活動家麗貝卡·索爾尼特(Rebecca Solnit)寫道:“我們所面對的最大的問題不能靠英雄來解決。它們應該靠社會運動、聯盟和公民社會來解決,如果有的話。”因此,“當公民將責任推卸給英雄時,這樣的國家是不幸的”。沒有人比那些被授予這一稱號的人更清楚這一點,並且,他們盡其所能與它作斗爭。“作為個人,你可以為保護氣候做的最有效的事情就是,是停止做‘個人’,”索爾尼特引用一位生態活動家的話說。鞠躬以示崇敬,或單打獨斗以追逐桂冠當然比尋找盟友更容易,而這當然無助於事業。英雄崇拜即使在向女性反抗者道賀時也是保守的。也許英雄改變世界不是真的;也許他們的故事只是為了讓事情保持這種狀態而製造出了一點仿佛事情已有所改變的噪聲。——英雄的本質:一種去政治化的策略。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將政治作為理解為坦率的“和而不同”,英雄傳奇將個人行為與犧牲意願結合起來。不僅僅只有軍事英雄主義是以戰士英模為基礎的。英雄是那些自願(或加引號的“自願”)接受特殊剝奪,甚至冒著生命危險服務於群體或執行救援任務的人。(在殉道者的意義上)必須做出犧牲這一事實絕對不容置疑,必須使眾多英雄道路上(在受害者的意義上)的非自願犧牲消弭於無形。尸體的氣味被熏香掩蓋。英雄主義的死亡崇拜將朋友和敵人之間的區別凝固為可受哀悼的人和被剝奪了受吊念這種認可形式的人之間的區別。有些人被提升到英雄的地位,有些人被妖魔化或被完全從公眾記憶中抹去。英雄敘事將合法性強加給它們的主人公,而英雄對他人實施的行為是否合法則無人在意。為此,人們以圍繞英雄行為的情感能量為食糧。對他的勇氣感到驚訝,對他的勝利充滿熱情,對他的失敗表示同情,對他不得不忍受的事情感到憤慨,對他的命運感到恐懼。最後,對他去世的哀悼產生了一種吸引力,同時也讓受眾免於去質疑——也包括對他們自己癡迷於此的質疑。言必稱大義的英雄指令與其說是正當的,不如說它引誘和壓倒一切。通過人們的祈願,他們設置了一個識別陷阱:在欽佩和崇敬的模式下,幾乎沒有可供反思的空間距離。英雄的犧牲的出現似乎是理由充分正當的,因為它會引發感動。對此質疑就是大逆不道。——英雄的本質:企圖進行情感綁架。
對後英雄時代的診斷涉及犧牲意願的減退以及權威領導和自我領導模式的合法性的喪失,但他們仍堅持讓英雄來擔當危機解除者,或者至少承認在需要應對危機時,對英雄有明顯的渴求。如《信經》(Credo)所示,面對非同尋常的情況不僅需要非同尋常的措施,還需要具有非同尋常品格的個人來執行這些措施。例外狀況(state of exception)需要特別的格式塔。如果常規運作使人庸碌,那麼在緊急狀態下,英雄主義就會蓬勃發展。與取得官方授權、遵循程序規則或強制進行非正式的更佳論證等相比,更重要的是采取決定性的行動。集中力量對個人采取行動,從敘事上概括了統治者的自我賦權實踐。英雄傳奇也有其政治神學。在民主制度中,統治地位已經退回到了組織結構之中,利維坦(Leviathan)的化身仍然是抽象的或可被替換的。“權力的空位”出現,英雄主義的個人化政治填補了進去。行使權力的個人中心越少,由強悍的男人、偶爾也由鐵娘子出演的統治劇目的受眾就越多。如同其大眾神話樣板一樣,演出的導向遵循戲劇衝突需不斷升級的誡命,在遭遇危機時,對英雄的需求就增加了,但英雄既然輩出,不能無用武之地,這就生出了對危機的需求。英雄永遠枕戈待旦、蓄勢而發,他們需要緊急狀態,就像警察需要罪犯作案一樣。沒有來自四面八方的敵人,沒有處處潛伏著的危險,他們就沒有把自己當成救世主的機會。他們承諾驅散的恐怖正是他們權威的來源。——英雄主義:一種統治技術。
英雄主義領域裡,“否思”仍在上演。作為神話殺手的啟蒙者是一個英雄人物,他的反英雄衝動證實了即使在否定行為中,英雄主義神話仍具有其有效性。這也許就是我們為何還要更進一步,對“否思”的概念進行再“否思”的原因。無論在何種情況下,為了解毒,僅僅發現它們的毒性所在是不夠的。毫無疑問,英雄崇拜支持了逆來順受的產生——就像犧牲一樣——它們描繪了一幅滿溢著戰鬥意識的畫面。一個充斥著不可調和的對立面的世界,只有依靠更強大的人才能保證其安全。這也正是這些英雄傳奇本身的敘事吸引力所在。他們提供令人興奮的娛樂,帶你進入奇妙的世界,並邀請你與他們的主人公一起戰栗,與他們一起為最後的勝利歡呼,或哀悼他們的垮臺。簡而言之,它們刺激感官。情感無可抗拒,只能被其他情感抵消;也只有其他的故事才能顛覆英雄傳奇的力量。“去英雄化”不僅是一個敘事學主題。
美國科幻作家厄休拉·K.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在她的“虛構的提袋理論”(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中設計了一個替代無處不在的英雄傳奇的方案,同時解釋了為什麼這種替代方案尚未能夠站穩腳跟:她寫道,對於人類來說,食物的主要來源包括收集的種子、根、芽和水果,而獵物只占飲食的一小部分。然而,獵人不僅從他們的遠足中帶回了肉,還帶回一個故事。她標出了其中的不同之處。與第一個獵人如何用他的長矛猛刺猛犸象的側腹、第二個怎樣被猛犸象的獠牙刺穿、第三個憑借何種精湛的箭法射中巨象這樣高度戲劇化的描述相比,告訴你如何在這裡挖塊莖、在那裡采摘漿果,首先收集蘑菇,然後費力地將燕麥粒從外殼中取出就顯得那樣乏味,很難從中找出有吸引力的部分。獵人的故事裡不全是動作,它還有一個英雄,“英雄是強大的。在不知不覺中,野燕麥地的男男女女、他們的孩子,乃至工匠的技藝、思想家的思想、歌手的歌聲,都已經融入了英雄的故事之中。但這不是她的故事,而是他的”;這是一個“殺手故事(Killerstory)”。勒古恩從這裡劃出了一條線,直到長崎,到被投擲了凝固汽油彈的越南村莊,再到受裡根威脅的“邪惡帝國”(蘇聯),也在“科技領先神話”裡畫了線。這個故事的結構類似於矛或箭的運動軌跡:英雄敘事是線性的。它不蜿蜒曲折,而是尋求從起點到目的地的直達路線。它的核心是一場衝突,英雄自當參與其中。
勒古恩拿來與英雄敘事進行對比的故事既不是線性的,不採用對立結構,也不圍繞著一個強大的演員展開。相反,它是關於提袋的。在人類文化之初,沒有可以用來打、刺、殺的物品,而是需要用於收集和儲存的容器:卷起的葉子、蚌殼、挖空的南瓜、鍋和網。提袋的故事是完全不英雄主義的。它們收集不同種類的素材並將它們相互關聯起來。當然,其中也包括衝突。但它們似乎只“作為一個整體的必要組成部分,其本身不能被描述為衝突或和諧,因為它的目的不是最終解決問題或就此停滯不前,而是維持一個持續的過程”。很明顯,這個故事中的主人公看起來不太好。他雖然在提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但他不再是全部事物的中心,最重要的是,沒有支撐起他的基座。正如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在評論勒古恩時所寫的那樣,“磨刀霍霍,作好了戰鬥準備的行動寓言”取代了 “獵人殺死並帶回可怕獵物的男性化人造故事”,“改變”和“消逝”的故事和諧共生。
人們沒必要分享勒古恩(從伊麗莎白·費舍爾[Elizabeth Fisher]那裡借鑒來的)的人類學推測,追隨她(本身就是英雄敘事的一個特徵)的二元性別象徵說,人們可能會偶然發現她(與哈拉維共享)的整體主義,並注意到她關於箭頭運動的敘事隱喻具有誤導性(她忽略了英雄傳奇也需要“阻礙元素”的事實),但可能會被提袋理論中暗含的“溫和的極端”刺激到。她的文章只有六頁,包含了對英雄主義的基本批判,她認真對待其敘事結構,避開了反對認同反英雄主義的陷阱。勒古恩並不認為英雄是要被擊破的,她把英雄們從其基座上摘取下來,把他們和其他許多人、動物、物品等一起裝進一個大袋子裡,並在她的冒險旅程中夾帶了大量的故事,這些故事無關於戰鬥、殺戮和自我犧牲,而與采集和收集有關。
如果有人想把講述如此這般的故事的藝術、傾心於這樣的故事的態度稱為後英雄的,那麼應該說,我們距離真正成為後英雄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成為後英雄中的一員,會是個好主意。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