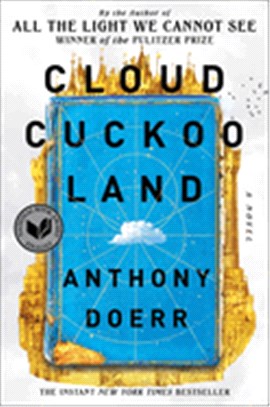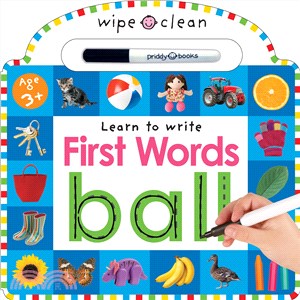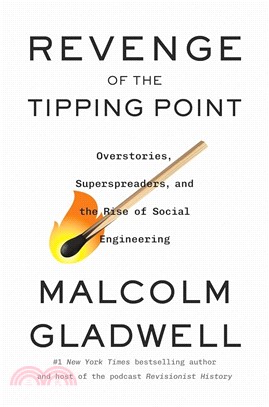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我」姐姐家所在的張莊,即將成為市高新區的組成部分,姐姐和同村人想趁著土地被征之前搶先蓋樓,以獲取更多的政府補償。為幫助姐蛆脫貧致富,「我」身不由己地成了這一重大舉措的參與者和背後軍師。樓蓋好之後,結成統一戰線的十幾家人家先後遭到上級部門的各種瓦解,一場巨大的較量拉鋸戰一樣展開。在種種現實利誘或威脅面前,統一戰線逐漸分崩離析,何去何從?怎麼選擇都令人心有不甘,結局出人意料,令人難以釋懷。《拆樓記》既有紀實作品的現場感,亦有小說的精巧架構與卓越的敘事技巧,更兼學者般的縝密與思辨力。它重在刻寫人與人之間細膩微妙的情感變遷;人心的向背與暗角,人性的脈絡與真相,令人無力逼視。
作者簡介
喬葉,漢族。河南省修武縣人。河南省文學院專業作家。《讀者》雜志簽約作家。中國作協會員。魯迅文學院高研班第三期學員。出版敦文集《坐在我的左邊》、《我們的翅膀店》、《喜歡和愛之間》、《自己的觀音》、《薄冰之舞》、《迎著灰塵跳舞》、《孤獨的紙燈籠》、《愛情底片》八部,長篇小說兩部。在《人民文藝》、《十月》、《上海文學》、《中國作家》等刊物上發表過長中短篇小說五十余萬字.多篇作品被《讀者》、《青年文摘》、《小說選刊》、《中華文學選刊》、《小說月報》、《小說精選》等刊物轉載。被評為“中國十佳青春美文作家”,獲首屆河南省文學獎及第三屆河南省文學藝術成果獎。長篇處女作《我是真的熱愛你》人選2004年度中國小說長篇排行榜。短篇小說《取暖》榮登2005年度中國小說短篇排行榜榜首。被中國青年作家批評家論壇評“2006年度青年作家”。
名人/編輯推薦
喬葉編著的《拆樓記》內容介紹:一個纖毫畢現的人性標本,一份獨特鮮活的社會檔案。作家親歷拆遷事件全過程。喬葉以毫不妥協的有力筆觸,描繪出利益之下人與人、人與世界之間真實甚至是殘酷的角力。在異常復雜棘手的現場,在層層逼仄的壓迫感之中,她所刻畫的人物看似狡黠沉著、精通世故,其實卻經歷著劇烈的內心起伏與煎熬。作品結合深邃的觀察和有力掘進的語言,使讀者從看似扭曲的種種現象中探尋真相,以及隱藏在背後的世道人心。
序
從《月牙泉》說起。這是喬葉的一個短篇小說,寫作時間應在《拆樓記》前後。
《拆樓記》的讀者,應該讀《月牙泉》。這是一篇讓我很不舒服的小說,我克制著羞恥感把它讀完。
我牢牢地記住了那對姐妹,她們住在一家豪華酒店里,妹妹是城里人了,而仍是一個農婦的姐姐被妹妹忍不住地厭棄著,妹妹知道這是不對的,妹妹和我們大家一樣,預裝了很多話語和言詞來反對這種厭棄,但妹妹忍不住啊,她甚至厭棄姐姐的身體。
——階級、階級感情,我還真想不起更好的詞。
類似的情景讓人想起“十七年”的小說,想起“十七年”的思想路徑從何時開始改變,從《陳奐生上城》?在進城的窮人身上,一種羞恥感被明確地表達出來,然後,就是逐漸發展起來的對這種羞恥感的消費,在大眾文化中、在趙本山那樣的小品中。
現在,這是社會無意識,它不能形成言詞,它不需要經過大腦。
社會在哪里?如果說一個人的本質是他的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話,那么,他的這種本質如何呈現?
在《月牙泉》中,這不是通過思想和言詞,而是通過本能、身體。
我的“不舒服”在于,《月牙泉》揭示了我們的思想和言詞著意掩蓋的事實,它把羞恥感還給了我們,撕開了我們精神上的羞處。
是的,多多少少,我們和那位妹妹是一樣的。
現在,談《拆樓記》。喬葉寫了一部不那么討人喜歡或肯定不討人喜歡的作品。
喬葉當然知道討人喜歡的作品怎么寫,別忘了她是《讀者》的老牌簽約作家。實際上,作為小說家,一直有兩個喬葉在爭辯:那個乖巧的、知道我們是多么需要安慰的小說家,和那個兇悍的、立志發現人性和生活之本相的小說家。
現在,是後一位小說家當班。
她在《拆樓記》中,力圖重建我們的生活世界:在紙上,把我們生活與意識的隱秘結構繪制出來。
對此,我們當然是不喜歡的,我們都希望,打開一本書時,發現自己在“別處”,而不是仍在“此處”,而且,“此處”如此赤裸清晰,令我們羞愧不安。凡懼怕注視自身的人,不要打開此書。凡在此處“安居”而樂不思蜀的人,不要打開此書。凡戴著言詞和公論的盔甲,永不卸下的人,不要打開此書。凡堅信世上只有黑白二事的人,不要打開此書。凡頭腦簡單者,不要打開此書,此書會把他簡單的頭腦攪亂。
“拆遷”這件事,每天出現在媒體上,我們對它有最明晰的認識。
但是,真的嗎?
圍繞這件事,聚集著當下社會一系列尖銳的沖突主題:人們捍衛“家”的自然正義,人的安全感和公平感,以及常常不能得到有效回應的訴求,由此產生的無助感和憤怒,等等。
所有這一切,形成了鮮明的戲劇效果,它幾乎就是古老戲劇的基本結構,它有力地激發了深植于民間傳統的情感力量。
社會在按照戲劇的、文學化的方式組織和表達自身的意識。
那么文學還能夠做什么?
伯林在《反潮流》一書的一個腳注中說:“我們從馬基雅維利以及他那類作家里受益良多,他們開誠布公地講述了人們在做什么,而不是應當做什么。” 無論是對于看客,還是對于演員,社會戲劇的力量在于,它強烈地訴諸“應當做什么”,而對于人們在做什么,遠不是“開誠布公”的。
社會戲劇的燈光在照亮什么的同時,必定簡省了什么,讓有些事物留在燈光之外。在《拆樓記>中,喬葉或許是在探索文學的另外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的可能:
文學必須把自己化作一種更全面的感受形式和思想形式,它必須反戲劇化,必須超越于各種概念和命題,必須盡可能忠直地回到全面的人生和經驗。
也就是,看到燈光之下和燈光之外,看到前臺和後臺,看到白天和夜晚,看到那些拆遷和被拆遷的人們,他們真實的、赤裸裸的動機、利益和情感,不是對著記者、對著麥克風所說的,而是他們正在做的。
《拆樓記》由此成為龐大社會戲劇的一個腳注,一種邊緣的思想和爭辯。
《拆樓記》本身就有很多注釋。這些注釋或許應該刪掉,因為它們增加了閱讀的難度。
但不能刪掉。因為,這種閱讀的難度和麻煩也正是思想的難度和麻煩。
人生的真正秘密,或許不在正文,而在那些被刪掉的注釋里。
社會現象的復雜結構,也正藏在被記者和專家們略去不提的漫長注釋中。
這樣的寫作一定是令人不適的,它使人從令人激憤、某種程度上也令人安心的戲劇場景中回到灰色的、模糊的人生。
它甚至令人惱怒、令人羞恥——
揭開事物的羞處,揭開人心與社會中隱秘運行的規則。
揭開指引著我們行動的那些難以形諸公共話語的情感、本能和習俗。
揭開下意識和無意識。
揭開正在博弈、心照不宣的各種“真理”,這些“真理”相互沖突和對抗,但是也在妥協和商量,秉持著各自“真理”的人們在緊張關系中達成了某種生態,這是誰也不滿意的生態、誰也不認為正確的生態,但它成了“自然”。
為此,喬葉采用了“非虛構小說”這樣的形式。
她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源頭:比如杜魯門·卡波特的《冷血》和諾曼-梅勒的《劊子手之歌》。
但其實略有不同,卡和梅,當他們使用“非虛構小說”的時候,他們某種程度上是回到混沌初開,他們在卑微的層面上模仿宏大的諸神。
而喬葉,是從宏大的戲劇中,回到經驗,回到凡人和人間。
這樣的形式同樣會令人惱怒,對于那些老實得像火腿一樣的評論家和藝術家來說,僅僅是“非虛構小說”這樣既矛又盾的概念就令他們生氣,就令他們欣喜:如此輕而易舉地就找到了空門和破綻。
但為什么不可以呢?《矛盾論》都忘了嗎?難道體裁和形式本身在它的發展過程中不就是要充分運用矛盾的張力嗎?
你看著“非虛構小說”生氣,你看“史詩”這樣的說法是否生氣呢?
“非虛構小說”是以爭辯和挑戰的姿態回到小說的史前史,把虛構與非虛構、生活與對生活的表達、“真實”的承諾與真實的相對性。把所有這些夾纏不清的問題,重新在這個網絡的、媒體的、眾聲喧嘩的時代擺在我們面前,讓我們如同小說史前史的那些人們一樣,自由而富于想象力地著手書寫模糊混沌的人類理智、情感、欲望和夢想。
在這里,這個人、這個書寫者站在這里,她拒絕宣布這一切純屬虛構,她愿意為自己的每一個字承擔責任——本故事純屬非虛構,歡迎對號入座。
但同時,她也明確地承認自身的裂痕和有限:我有我的特定身份以及相隨而來的局限和偏見。因而“小說”在這里也不是托辭。不是作者為自己爭取特權的方式,而是,這個人說,我只能在我力不能及的地方努力動用我的理解力和想象力。
喬葉在嘗試一種被無數人推崇但很少被人踐行的寫作倫理,她以自剖其心的態度,見證了她的所見和所知。
是的,所有的人,她愛他們,這是無疑的。但她同時也對他們感到失望,這也是無疑的。她深刻地知道自己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她對自己同樣失望。
《月牙泉》是如此,《拆樓記》亦是如此。
《拆樓記》的讀者,應該讀《月牙泉》。這是一篇讓我很不舒服的小說,我克制著羞恥感把它讀完。
我牢牢地記住了那對姐妹,她們住在一家豪華酒店里,妹妹是城里人了,而仍是一個農婦的姐姐被妹妹忍不住地厭棄著,妹妹知道這是不對的,妹妹和我們大家一樣,預裝了很多話語和言詞來反對這種厭棄,但妹妹忍不住啊,她甚至厭棄姐姐的身體。
——階級、階級感情,我還真想不起更好的詞。
類似的情景讓人想起“十七年”的小說,想起“十七年”的思想路徑從何時開始改變,從《陳奐生上城》?在進城的窮人身上,一種羞恥感被明確地表達出來,然後,就是逐漸發展起來的對這種羞恥感的消費,在大眾文化中、在趙本山那樣的小品中。
現在,這是社會無意識,它不能形成言詞,它不需要經過大腦。
社會在哪里?如果說一個人的本質是他的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話,那么,他的這種本質如何呈現?
在《月牙泉》中,這不是通過思想和言詞,而是通過本能、身體。
我的“不舒服”在于,《月牙泉》揭示了我們的思想和言詞著意掩蓋的事實,它把羞恥感還給了我們,撕開了我們精神上的羞處。
是的,多多少少,我們和那位妹妹是一樣的。
現在,談《拆樓記》。喬葉寫了一部不那么討人喜歡或肯定不討人喜歡的作品。
喬葉當然知道討人喜歡的作品怎么寫,別忘了她是《讀者》的老牌簽約作家。實際上,作為小說家,一直有兩個喬葉在爭辯:那個乖巧的、知道我們是多么需要安慰的小說家,和那個兇悍的、立志發現人性和生活之本相的小說家。
現在,是後一位小說家當班。
她在《拆樓記》中,力圖重建我們的生活世界:在紙上,把我們生活與意識的隱秘結構繪制出來。
對此,我們當然是不喜歡的,我們都希望,打開一本書時,發現自己在“別處”,而不是仍在“此處”,而且,“此處”如此赤裸清晰,令我們羞愧不安。凡懼怕注視自身的人,不要打開此書。凡在此處“安居”而樂不思蜀的人,不要打開此書。凡戴著言詞和公論的盔甲,永不卸下的人,不要打開此書。凡堅信世上只有黑白二事的人,不要打開此書。凡頭腦簡單者,不要打開此書,此書會把他簡單的頭腦攪亂。
“拆遷”這件事,每天出現在媒體上,我們對它有最明晰的認識。
但是,真的嗎?
圍繞這件事,聚集著當下社會一系列尖銳的沖突主題:人們捍衛“家”的自然正義,人的安全感和公平感,以及常常不能得到有效回應的訴求,由此產生的無助感和憤怒,等等。
所有這一切,形成了鮮明的戲劇效果,它幾乎就是古老戲劇的基本結構,它有力地激發了深植于民間傳統的情感力量。
社會在按照戲劇的、文學化的方式組織和表達自身的意識。
那么文學還能夠做什么?
伯林在《反潮流》一書的一個腳注中說:“我們從馬基雅維利以及他那類作家里受益良多,他們開誠布公地講述了人們在做什么,而不是應當做什么。” 無論是對于看客,還是對于演員,社會戲劇的力量在于,它強烈地訴諸“應當做什么”,而對于人們在做什么,遠不是“開誠布公”的。
社會戲劇的燈光在照亮什么的同時,必定簡省了什么,讓有些事物留在燈光之外。在《拆樓記>中,喬葉或許是在探索文學的另外一種可能,一種不可能的可能:
文學必須把自己化作一種更全面的感受形式和思想形式,它必須反戲劇化,必須超越于各種概念和命題,必須盡可能忠直地回到全面的人生和經驗。
也就是,看到燈光之下和燈光之外,看到前臺和後臺,看到白天和夜晚,看到那些拆遷和被拆遷的人們,他們真實的、赤裸裸的動機、利益和情感,不是對著記者、對著麥克風所說的,而是他們正在做的。
《拆樓記》由此成為龐大社會戲劇的一個腳注,一種邊緣的思想和爭辯。
《拆樓記》本身就有很多注釋。這些注釋或許應該刪掉,因為它們增加了閱讀的難度。
但不能刪掉。因為,這種閱讀的難度和麻煩也正是思想的難度和麻煩。
人生的真正秘密,或許不在正文,而在那些被刪掉的注釋里。
社會現象的復雜結構,也正藏在被記者和專家們略去不提的漫長注釋中。
這樣的寫作一定是令人不適的,它使人從令人激憤、某種程度上也令人安心的戲劇場景中回到灰色的、模糊的人生。
它甚至令人惱怒、令人羞恥——
揭開事物的羞處,揭開人心與社會中隱秘運行的規則。
揭開指引著我們行動的那些難以形諸公共話語的情感、本能和習俗。
揭開下意識和無意識。
揭開正在博弈、心照不宣的各種“真理”,這些“真理”相互沖突和對抗,但是也在妥協和商量,秉持著各自“真理”的人們在緊張關系中達成了某種生態,這是誰也不滿意的生態、誰也不認為正確的生態,但它成了“自然”。
為此,喬葉采用了“非虛構小說”這樣的形式。
她為自己找到了一個源頭:比如杜魯門·卡波特的《冷血》和諾曼-梅勒的《劊子手之歌》。
但其實略有不同,卡和梅,當他們使用“非虛構小說”的時候,他們某種程度上是回到混沌初開,他們在卑微的層面上模仿宏大的諸神。
而喬葉,是從宏大的戲劇中,回到經驗,回到凡人和人間。
這樣的形式同樣會令人惱怒,對于那些老實得像火腿一樣的評論家和藝術家來說,僅僅是“非虛構小說”這樣既矛又盾的概念就令他們生氣,就令他們欣喜:如此輕而易舉地就找到了空門和破綻。
但為什么不可以呢?《矛盾論》都忘了嗎?難道體裁和形式本身在它的發展過程中不就是要充分運用矛盾的張力嗎?
你看著“非虛構小說”生氣,你看“史詩”這樣的說法是否生氣呢?
“非虛構小說”是以爭辯和挑戰的姿態回到小說的史前史,把虛構與非虛構、生活與對生活的表達、“真實”的承諾與真實的相對性。把所有這些夾纏不清的問題,重新在這個網絡的、媒體的、眾聲喧嘩的時代擺在我們面前,讓我們如同小說史前史的那些人們一樣,自由而富于想象力地著手書寫模糊混沌的人類理智、情感、欲望和夢想。
在這里,這個人、這個書寫者站在這里,她拒絕宣布這一切純屬虛構,她愿意為自己的每一個字承擔責任——本故事純屬非虛構,歡迎對號入座。
但同時,她也明確地承認自身的裂痕和有限:我有我的特定身份以及相隨而來的局限和偏見。因而“小說”在這里也不是托辭。不是作者為自己爭取特權的方式,而是,這個人說,我只能在我力不能及的地方努力動用我的理解力和想象力。
喬葉在嘗試一種被無數人推崇但很少被人踐行的寫作倫理,她以自剖其心的態度,見證了她的所見和所知。
是的,所有的人,她愛他們,這是無疑的。但她同時也對他們感到失望,這也是無疑的。她深刻地知道自己就是這些人中的一個,她對自己同樣失望。
《月牙泉》是如此,《拆樓記》亦是如此。
目次
序
蓋樓記
新區
高血壓
情況
村景
籌謀
鴻門宴
田莊4·29
合作
後來
王永
心跳
拆樓記
告示
開會
首戰
首拆
道理
五米
上訪
西風烈
他們
底牌
殺手?
雜事
後記
蓋樓記
新區
高血壓
情況
村景
籌謀
鴻門宴
田莊4·29
合作
後來
王永
心跳
拆樓記
告示
開會
首戰
首拆
道理
五米
上訪
西風烈
他們
底牌
殺手?
雜事
後記
書摘/試閱
去年,姐姐的大女兒苗苗考上了鄭州輕工職業學院,這么一來,每次回老家,苗苗搭我的順風車就成了必然。我和姐姐的日常聯系也自然而然地多了起來。各自出嫁之後,在姊妹五個中間,我和姐姐見面最少。原因很簡單,我們五個里,唯有她現在還生活在鄉村。我的鄉村生活史在15年前就已經結束。曾經和其他三個兄弟在縣城生活過幾年,10年前調到鄭州之後,我每次回去的目的地基本也都是縣城,不到清明上墳或者農歷十月初一給祖宗們“送寒衣”,再或是春節走親戚,一般不會和姐姐碰面,對姐姐的情況也就所知甚少。兄弟姊妹多,哪能整天想著他們。各有各的活路,平常里,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沒時間去特別關切誰。但是,苗苗在這里,經常見面,終歸要絮些家常閑話,對姐姐的細節也就聽得越來越多。聽著聽著,我覺得姐姐似乎是越來越陌生了:姐姐學會了鹵雞腿和鹵豬蹄,姐姐從不刷牙,姐姐在繡十字繡,姐姐的小姑子因為信了邪教而住了監獄,姐姐正在給她的孩子做棉衣……
姐姐對我的感覺,應該也是一樣。一年多來,每次我碰到姐姐,我們之間親熱是親熱,客套是客套,但也橫亙著體積龐大的生疏。我會問她:“黏玉米那么貴為啥不種點兒?”“去磨坊磨面也太羅唆了吧?”她會問我:“聽說你有仨電腦,要恁多干啥?”“整天坐飛機不害怕?多費錢。”我的提問,她的回答認真;她的提問,我的回答敷衍。但我并不覺得虧欠。我很清楚:無論認真還是敷衍,這些問答對我們之間的那道溝壑而言都只是杯水車薪。無論是什么樣的語言材料和語言品質,那道溝壑都很難填補。主要原因當然在我。自從當了鄉村的叛逃者之後——“叛逃者”這個詞是我最親愛的記者閨密對我們這些鄉村底子、城市身份的人的統稱——我對鄉村想要了解的欲望就越來越淡。記者閨密對此也有深入潛意識的尖刻評價:只要有路,只要有車,只要有盤纏,只要有體力,所有的叛逃者都只想越逃越遠。
對她的評價,我只用沉默應答。
“明兒能回嗎?”那天是個周四,姐姐打電話問我。
“什么事?”我問。姐姐沒事不打電話,只要打電話肯定是有事,而且八成還是錢的事,一般來說還不會太少。其他三個人雖然在縣城,日子卻都只是過得去,不如我寬裕,且又都是兄弟,有媳婦管著,不好貼補她。逢到用錢的事,姐姐也只有向我伸手。前兩年她翻蓋新房,我就貼給她了3萬。
“沒啥事。”
“說吧。你先電話里說說,讓我有個底兒。”P3-4
姐姐對我的感覺,應該也是一樣。一年多來,每次我碰到姐姐,我們之間親熱是親熱,客套是客套,但也橫亙著體積龐大的生疏。我會問她:“黏玉米那么貴為啥不種點兒?”“去磨坊磨面也太羅唆了吧?”她會問我:“聽說你有仨電腦,要恁多干啥?”“整天坐飛機不害怕?多費錢。”我的提問,她的回答認真;她的提問,我的回答敷衍。但我并不覺得虧欠。我很清楚:無論認真還是敷衍,這些問答對我們之間的那道溝壑而言都只是杯水車薪。無論是什么樣的語言材料和語言品質,那道溝壑都很難填補。主要原因當然在我。自從當了鄉村的叛逃者之後——“叛逃者”這個詞是我最親愛的記者閨密對我們這些鄉村底子、城市身份的人的統稱——我對鄉村想要了解的欲望就越來越淡。記者閨密對此也有深入潛意識的尖刻評價:只要有路,只要有車,只要有盤纏,只要有體力,所有的叛逃者都只想越逃越遠。
對她的評價,我只用沉默應答。
“明兒能回嗎?”那天是個周四,姐姐打電話問我。
“什么事?”我問。姐姐沒事不打電話,只要打電話肯定是有事,而且八成還是錢的事,一般來說還不會太少。其他三個人雖然在縣城,日子卻都只是過得去,不如我寬裕,且又都是兄弟,有媳婦管著,不好貼補她。逢到用錢的事,姐姐也只有向我伸手。前兩年她翻蓋新房,我就貼給她了3萬。
“沒啥事。”
“說吧。你先電話里說說,讓我有個底兒。”P3-4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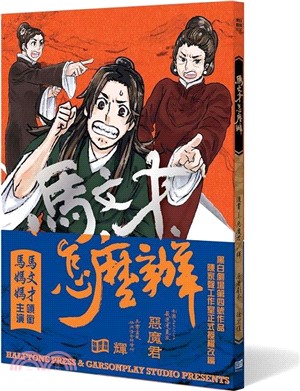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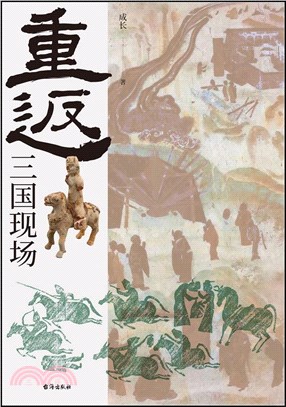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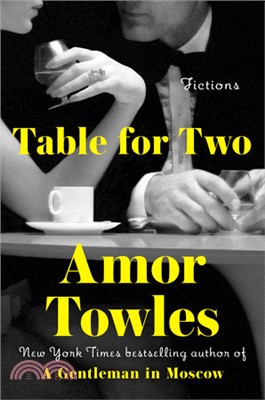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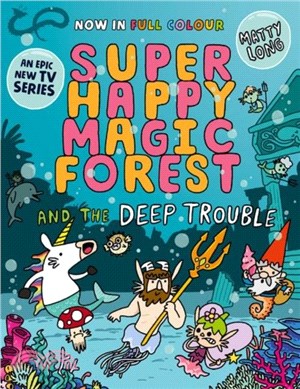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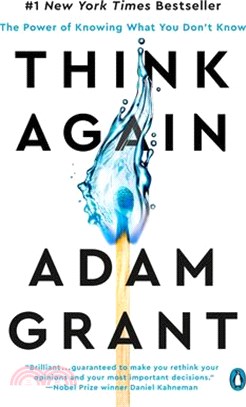
![Wicked [Movie Tie-In]:魔法壞女巫電影原著](https://cdnec.sanmin.com.tw/product_images/006/00628528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