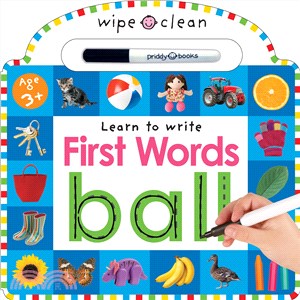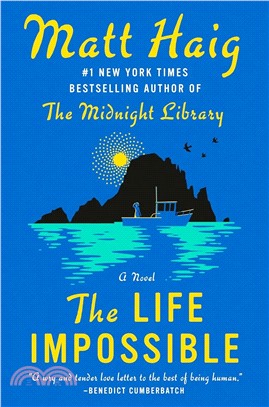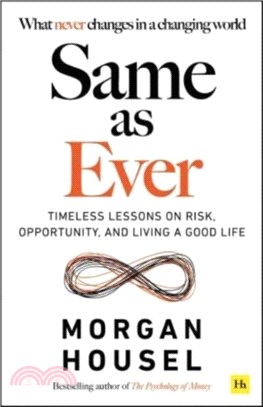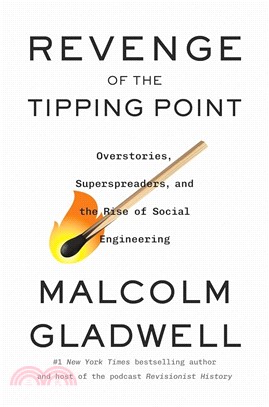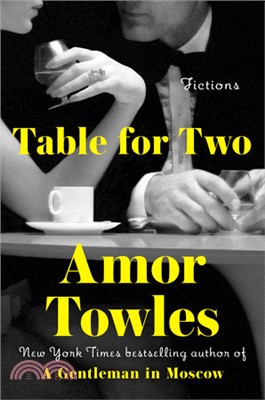商品簡介
來自全球26家頂級博物館的珍貴館藏,為讀者呈現當年八國聯軍在北京城的巷戰、義和團進京、北洋新軍的興起、清末新政、日俄戰爭、各行各業百姓生活圖景……
中國人的悲喜命運,都在這部書的影像以及文字中。它們在哪裡,我們的歷史就在哪裡。尤其在當下,此書猶如一本中國版的《光榮與夢想》,正在述說著我們尚未發現的中國的祕密。
作者簡介
何謙,文史研究工作者。
東亞,文史研究專家。
序
1900~2000 陌生的祖國
一部由影像講述的中國百年史
(代序)
「往回看,才能明白未來」。
任何歷史都是由後人所記錄與創造的,我們看到的那些歷史以及英雄們的表演,以及他們在時間中的定位與背影,都帶着後來者的價值觀與需要,「需要」正在成為歷史書寫中的重要理由與事實。我們無法確認自己正在閱讀的就是那些在時間中曾經存在的。我們真的可以相信,那些只由幾個人編撰的歷史就是一部真實的歷史?史家們對於歷史的看法就是歷史本身才應當有的那些聲音與形象嗎?
曾為中美關係鋪平道路的「中國通」亨利.基辛格認為,中國過去遭受的不公正對待決定了「中國如何參與世界事務、如何界定在其中所要扮演的角色。」對許多中國未來一代來說,「中國有時候不僅僅只是一個值得發現的真相」。
近年風起的漢學家們,大書特書對於中國的發現,以及他們遙遠的對於陌生中國圍觀的歷史,更重要的是他們的世界觀正在影響着新一代青年對於自己祖國的認知。他們自小學開始的閱讀,內地、臺灣省、香港特區歷史課本中的中國以及西方撰寫的中國,這些不同的認知體系正在重新引領着新一代中國人對於祖國的探險。雖然他們同在一個國家,卻在一個久遠的歷史細節中發現不同的答案。親愛的,有着近2000年歷史的中央帝國,我的祖國,有時看上去如同一潭渾水,我們艱難地試圖尋找到其中的那條若隱若現的魚,或者其他的暗藏的礁石。然而,那些不同的個人見解,諸如大陸風行的《百家講壇》,諸如被稱為現代大家的史學者,都無法在這股重新發現中國的潮流中,為我們提供最精確的方向。而這個論壇所創造的許多「傳統國產」的演講家們,講述的歷史多以演繹的方式開始……而現在他們開始拋棄評書式的歷史講座,學會了「用講故事的方式」來打動對於祖國歷史陌生而好奇的一代人了。那些漢學家們,有些甚至從來沒有來過中國。他們對中國的認知,或者來自大陸旁邊的臺灣省、香港特區的報刊,或者來自上世紀初傳教士們在中國的攝影作品。而這些記錄下的祖國,則正在這股重新發現中國的熱潮中悄然佔據上風。
年輕人開始閱讀這些西方人發現的中國歷史,而另外一代人,他們的父輩,對中國有着豐富的了解,具有高超的對於事務的熟知能力,並佔據着重要資源的一代人,則守候在《百家講壇》前,他們渴望了解的是2000年間的中國宮廷鬥爭以及諸代望臣的命運,廟堂的操運倫理。家庭主婦們則從漫長的古裝電視劇中的「後宮嬪妃們的爭鬥中」了解屬於她們的普遍歷史。他們的後代,20歲或者30歲的改革的孩子,則從西方人的撰寫中,關注近百年中國的命運,他們對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亞洲隨之建立的第一個共和國的興趣遠大於對於遙遠的唐宋或者明清的關注。那些廟堂與歷史爭鬥對他們來說,僅只是一種傳說與故事,從這一百年中尋找到中國現代化的腳印,則是他們了解歷史的動力。
這種歷史認知斷層猶如對於「複雜中國」的重新定義,一代人有一代人對於歷史的看法。他們對於歷史的斷代與判別像黃士高原深處那些被埋藏進化萬年形成的煤層或者石油,你不知道在哪一部分會發現,它們在一萬年前是大海,在五千年時則成為了高原。
而歷史隱藏在哪一種表述中呢?
1999年歲末,澳門,這個以賭博勝名的彈丸之地,在被葡萄牙統治了近百年後,回歸了。我作為CCTV直播這一祖國光榮時間的一員,與央視的一些至今仍然著名的主持人們住在拱北海關的一家賓館。
那時候我已快30歲,從軍13年,在那個小城,撲面而來的來自祖國三個不同地區或者西方的報刊、電視臺對於同一事件的報道差異,讓我對自己的判斷開始產生了懷疑。那些報刊幾乎以完全陌生的方式講述着澳門的故事。我知道,澳門回歸是我正在經歷的歷史,這個歷史,北京的電視臺用自己的方式記錄了,而在那一天,我看着BBC、NBC以及香港或者澳門的電視臺,他們也用自己的方式記錄了這個歷史時間。它們的語言是英語、廣東話。入城式的畫面也竟然如此截然不同。這個正在發生的時間顯然對於居住在不同地域,有着不同世界觀的人也是不同的。
而我作為一個曾偏居內地30年的人,也在這種混雜的記錄中,找到了自己對於正在經歷的時間的看法。
歷史是甚麼?
它們開始成為困擾我的一個巨大難題。它們在我們身前的背影顯得那樣模糊不清,每個人在時間中的記憶都帶着自己對於時間的看法,而那些時間對於我們則遙遠得如同命運,我們只看到了一個個結果,或者一個個由結果組成的「歷朝歷代鐵口直斷式」的表達。這些就是我們要面對的歷史?
某個特殊的巧合,我看到了宋美齡女士的圖像展。儘管已近百歲的她當時仍在人世,但那些舊年代的細節,以及她與蔣先生普通的生活圖像,仍然讓我感覺新鮮。我那時候已對文字所描述的世界開始了懷疑,真實的黑白圖像使我堅信,它在某些時間,遠比我所接觸到的教育更為可靠,無論你相信與否,她在美國國會演講時堅強的眼神與她的演講稿,都使我堅信,歷史在某些圖像中出現的時候,它們是真實而且有力的。而且與那些文字記載的歷史有着不一樣的結論。宋的眼神改變了我的歷史態度,至少改變了我對於一部分用文字記載的歷史的態度。我要找到屬於自己研究歷史或者至少接近真實的舊時間的方式與願望。如有神示,我從那些分散在各地的,比如臺灣省國民黨黨史館、「中央社」以及更多的渠道中發現的黑白圖像中,找到了近千張由宋的圖像組成的一部用圖像串聯起來的宋的歷史。2002年,在這位106歲的老人去世前十五天,我出版了《宋美齡畫傳》。這本書因為某種神祕的巧合與唯一性,而使它成為內地了解宋的一個普及性的常識讀本,與一個純屬巧合的熱門話題與暢銷書。而這個無意間的巧合,也使這本圖文結合的,在國內出版史上首創的體例,引領了一個畫傳風潮。從這本書開始,也許有意無意間開始了我對於中國百年間歷史的重新認知與寫作。我開始有意識地尋找這百年間的圖像以及關於這百年的重要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了解。而隨着我了解的越多,卻發現歷史是如此陌生與神祕,在一件基本的常識性的問題上,至少對於我來說,它們幾乎是兩種或者更多種不同的說法,而那些舊像片的出現,更使我發現,我對於歷史的了解如此之少。歷史的寫作方法或者拍攝方法竟然因為國家的不同,或者寫作者身份的不同,會如此變異。圖像表達的是一種歷史,而文字,同樣也是歷史撰寫的一種。
我們更應該相信哪一種?
人類一直在探求自己對於歷史與世界的表達與記錄方式,他們在發明了語言與文字之後,1838年,世界上出現了兩種特殊的語言:影像與聲音的傳播。1839年,法國人路易斯.達蓋爾(Louis Daguerre)發明了攝影。這個世界從此可以在銀鹽紙上展現真實的人像與自然。塞繆爾.摩爾斯(Samuel Morse)則開始首次公開示範電報。當遙遠的歐洲可以替代油畫並用電報與鐵路拉近時間距離的時候,遙遠的「天朝上國」則正處在一個用山水畫來描述的時代。英法帝國商人試圖用鴉片改寫道光年間的年號與史紀順序。19世紀晚期,外國的傳教士則隨着洋槍隊與冒險家們,來到中國向非信徒傳播基督教福音時,用他們手中的攝影機為那個時期的中國歷史留下了另一個「汗國」的影像檔案。西方人是從電報與影像中,突然發現了一個陌生的國家:用精緻的瓷器做成的吸煙工具;男人頭上繫着的奇怪小辮;絲綢織成的長袍;1949年前曾經存在過的北京厚厚的城牆;可以娶一個以上的老婆;巨大的邊疆;瘦小卻狡猾,戴着磨石眼鏡,頭頂着長翎紅頂帽子的清國官員。貧窮但卻不願意與海外那些尋求財富與瓷器、金銀的商人通商的封閉國家。並且他們試圖用長城來表達這種從明朝就開始擁有的願望:閉關鎖國。
英國人則戴着假髮,拍發着電報,在打字機上打印小說書或者發行報紙,用他們的小船開進全世界所有未知的領土,並佔領它們。「殖民」這個詞開始重新製造着兩百年間的世界歷史。許多未來的大國幾乎都是在這兩百年間突然誕生的。
而這百年間,尤其對於一個有着長達千年的古老順序與規制的中央帝國來說,突然被西方幾萬人組成的洋槍隊與鴉片或者宗教,輕而易舉就打敗並發現了。
在16世紀左右的傳教士與正在走向現代化的歐洲人眼裏,這個古老的國家竟然是個「少年中國」,幼稚,不熟悉世界,自大,蜷在一隅,像一個活在夢境裏的與世隔絕者。而叫醒這個被民國譯成「拿波輪」的法國皇帝稱為睡獅的「清國」的,竟然是一群西方的商人。他們僅僅因為利益,因為鴉片,或者宗教。
但對於這個大一統近千年,並如「黃禍」般留在歐洲人記憶中的「汗國」,同樣也成為歐洲發明的報刊的神祕報道。在那些報刊與充滿探險家氣質的記者們「尋找CINA」的時候,更多的攝影師伴隨着這股熱潮帶着他們的好奇心與銀鹽紙進入了中國,蘇格蘭攝影家John Thomson(約翰.湯姆森)是最早來遠東旅行,並用他古舊而時尚的攝影術記錄遠東各地人文風俗和自然景觀的攝影師之一,這個冒險主義者曾在遙遠的1867年移居香港,開始了他攝影生涯中至關重要的幾年。他的紀實主義風格為我們留下了長辮的中國以及北京的轎夫,斬首的場景。這段冒險的經歷為他贏得了在1881年成為維多利亞女王指定御用攝影師的名號。而這些無關政治的圖片無意間在百年後成為我們回憶帝國的重要影像,其後的攝影師們則用他們的鏡頭表達了對於中國的政治以及現實的記錄,他們用自己的方式,記錄了擺拍或者原始的中國現實。比如,那些清朝官員都是端坐着,或者合影,也是一群人木訥地看着1900年以前的鏡頭。在今天的攝影師們的鏡頭裏,我們還可以發現他們當時制定的攝影規則。群像,端坐,目視着2000年的日本照相機鏡頭。事實上,鏡頭中的中國似乎從來沒有改變過。但改變這一切的是甚麼呢?這些一百年間的景物,或者他們隨手拍下來的孤獨的風景,伴隨着相機快門的定格,「John Thomson們眼中的中國都市與破敗鄉村的狀貌,包括了政治、經濟、文化到習俗的諸多信息,不動聲色地留在了歷史的底片上」。
John Thomson「以他在1860年代末至1870年代初對中國的人物和風光的生動寫照,無疑是當時最好的攝影師之一。是衡量19世紀其他在中國活動攝影師的標杆。」
「我的照相機是一件邪惡而神祕的工具,它能助我看穿岩石和山脈,刺穿本地人的靈魂,並用某種妖術製作出謎一般的圖畫,而與此同時被拍攝者身體裏的元氣會失去很大一部分,他的壽命將因此大為折損。」John Thomson在他進入「清國」拍照時,遇到的困境,在現代的中國,仍然有着遙遠的傳統,比如鄉間仍然會流傳照相會吸走人的精血的愚昧說法。同樣的事實也發生在:鐵路會毀壞中國的龍脈,電報可以刺傷中國古老的靈魂。事實上,當這一切在其後的二百年,電報悄然消失,鐵路正在進入高鐵時代,甚至臺式電話也快成為古董,相機即將被喬布斯的蘋果手機取代,成為中國青年記錄自己業餘生活一部分的時候,這個曾經的歷史時間軸正在失去它的功能還是在失去它的靈魂?
事實上,他們手中的相機,真實地刺穿了中國的靈魂,但也保留了中國的元氣,至少,我們看到了一部分我們應當了解的歷史。當「歷史可以觀看」的時候,我們發現圖片遠比文字更加真實,當文字成為一家之言的時候,那些陳舊的圖片的表面至少還保留着1910年我們無法描述並看清楚的小腳,靠在北京的舊城牆邊上發呆的藝人。或者1900年幾個工人站在北京朝陽門正在維修的木柱上,他們木訥的表情曾是那個時代對於外部真實的寫照。那個高高的舊城樓的土建工人與當時美國最高大樓鋼鐵支架上站立着的現代工作,都是當時地球上發生的故事。只是東方的舊城樓上的工人看到的是一條塵土飛揚的舊長安大道,而紐約的工人,則正享受着現代化到來時的不安與興奮—因為他們站得太高了。
事實上,在這個圖像氾濫的時代,圖片正在成為一種通用語言,而變得比世界語英語表達得更加直截了當與簡捷。當我們翻開一本外文版的書刊時,在陌生的語言面前,圖片成為我們迅速了解這本書的窗口。近幾年國內對於畫傳的流行以及更多的人對於圖片的重視與收藏,也開始顯示一種新的可能性:當一部分人在收藏這些舊圖片的時候,其實他們也在無意間保留着日漸陌生的歷史。而這似乎也印證了蘇珊.桑塔格的那句話:「所有的照片,都會由於年代足夠久遠而變得有意味和感人。」
為甚麼要重新寫作這些所謂的耳熟能詳的歷史?
在中國,重新寫作「蓋棺定論」的老歷史是「既複雜又敏感」的事。「尤其是這一百年的中國,它複雜而且充滿許多神祕的運作。對祖國歷史的領悟和學習,不能孤立與封閉自己,更不能視角單一。不僅要同世界歷史相關聯,更需要借用他國的眼光,來反觀自己的歷史。這樣在辨別那些大是大非或大真大偽的歷史問題時,才能更為客觀,結論也更能經得起時間的推敲。」但對於中國的了解,我能找到的渠道是甚麼呢?
John Thomson們的出現,給我們提供了一個現實的難題,我們是相信機器
中的影像還是那些坐在書房裏的史家研究?歷史為甚麼會有許多不同的版本,不同的事件為甚麼會有不同的表述,英語的表述與國語的說法為何如此難以達成一致,哪一些是真實的,哪一些又是虛假的,從《宋美齡畫傳》開始,這些都是困擾我多年的問題。這些問號一直等待我們去拉直,但卻找不到拉直它們的方法。我在尋找這個答案,而這可能就是我無意識間對於中國近百年歷史的探險的開始。
中國的百年時間正在成為東西方文明的分界線,也成為東西方重新發現與製造中國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中國的一百年發生了甚麼?而西方的一百年發生了甚麼,一個巨人倒下的姿勢與用洋槍打開它的國門的姿勢同樣令人迷戀與猶疑,儘管它們一個是屈辱的樣貌,一個是勝利的微笑與倨傲。
在最近波瀾壯闊的百年間,東西方文明正以另一種語言來重新書寫世界。
「從19世紀和20世紀早期的中國,直到今天所理解的『版本』,也許長期以來都與西方通常敍述中的中國格格不入。」似乎是《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稱:「在中國的『屈辱世紀』裏,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緩慢崩塌十分不可思議,簡直像是一個漫畫家編造出來的:一位志向遠大的文職人員沒有通過科舉考試,變得神志不清,以為自己是耶穌基督的弟弟,被派來把中國從清朝的統治下解救出來,他在1850年發起了太平天國運動。兩千萬人死於之後的社會動盪。英、法、德、奧匈、俄、美、意、日組成的八國聯軍輕鬆打敗了義和團成員以及加入他們的清朝士兵,但是在那之前,義和團已經殺死了三萬多名中國基督徒。西方人來中國宣傳基督教的和平和同情精神。他們也在鴉片貿易中輕鬆獲利,並為繼續獲利而發起了一場戰爭。」這場運動在侮辱了中國的同時,也促使了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出現。
百年以來,中國邁向現代國家之途披荊斬棘,一再猶疑,多所反覆,常常倒退,令人難以確知其未來。進三步,退一步,成為中國式的智慧與藉口,我們不知道自己是在前行還是在後退,時間在哪裏?我們在向前進,但我們的方向在哪裏?
我們要到的那個地方在哪裏?
這本書寫的是1900年到2000年間的劇烈變動的中國。研究100年間的中國,不是懷舊,也不是算舊賬,而是如何找到我們從哪裏來,到哪裏去,為甚麼來這兒的原因。這部普及式的常識讀物將只給大家提供一個可以選擇的嚮導。它不是司馬遷的《史紀》,也不是史景遷的外國眼鏡下的演繹。它在這個被互聯網製造出來的扁平時代,所發揮的作用也許只不過是給大家一個維基百科式的基本的中國百年常識或者一個國家的基本面目。
「對祖國歷史的領悟和學習,不能孤立與封閉自己,更不能視角單一。不僅要同世界歷史相關聯,更需要借用他國的眼光,來反觀自己的歷史。這樣在辨別那些大是大非或大真大偽的歷史問題時,才能更為客觀,結論也更能經得起時間的推敲。」歷史事件是無法重複的,只有匯集各種視角的資料,只有擁有各種類型的歷史證據,我們才可能逼近歷史的真實。其實歷史的張力,就存在於這種視角的差異中,我們對這種差異了解得越充分,對自身的把握也就越清晰。
我們可以盲目地熱愛自己的祖國,但不能盲目地歌頌祖國的歷史。對歷史來說,曾經的災難不是巧合,幸運同樣不是從天而降的,這是任何人無法迴避的。當人們不允許從多視角來澄清歷史記憶時,往往意味着謊言和壓制的開始,這時真理和真相便成為被扼殺的對象。
為保持這本書的基本真實以及可能的時間長度,也為了防止我自己對於歷史的偏見而影響這本書的「常識」「向導」價值,我們選擇了一個簡單的體例,即它由圖片與外國人以及中國人的發現共同組成。它沒有「立場」,沒有「特製的意識形態」,沒有知識分子與精英們認同的「普世價值觀」,有的只是那些曾經被拍攝下來的1900年代破敗的不收門票的故宮,或者孫中山先生的背影,或者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的目光。我們試圖尋找到的另類表述,只是想區別於那些「被需要」而寫成或者有着固定價值觀的歷史書。而這些歷史,可能只是那些大歷史中的小細節,但這些陌生的小細節構成了百年中國戲劇。但不正是神祕和未知讓人趨之若鶩?百年後回看,它們如同遙遠的蟻群,在緩慢地行走,而我們正在試圖加入這個蟻群中,我們在歷史中是如此弱小,如此模糊不清,但卻又是這些模糊的背影正在構成以前的歷史。
這套書的基本野心只是提供一個具有世界觀的中國,在二十世紀的時間軸心中的位置與被注視的方式。而對於這本書的讀者來說,我們提供的只是他們眼中陌生的祖國與西方人拍攝的黑白歷史。但願這些歷史可以成為一部簡明的歷史常識,一部西方人發現的中國的歷史,一部陌生化的中國史,一部有圖有真相的歷史……一個了解中國的路徑或者參考消息式的指路牌。或者乾脆就是一本關於中國這一百年的歷史「向導」。
中國人的悲喜命運,都在這部書中的影像以及文字中。它們在哪裏,我們的歷史就在哪裏。而這就是我們要撰寫的關於中國的百年變革史的意義。尤其在當下的「複雜中國」,此書猶如一本中國版的《光榮與夢想》,正在述說着我們尚未發現的中國的祕密。
目次
1900~2000 陌生的祖國(代序)
公元1900年之前 想像中的天朝
1900 交困
1901~1902 凋零
1903~1904 先學中文,再謀中國
1905~1907 激變
1908~1911 崩潰
在清朝
書摘/試閱
公元1900年之前
想像中的天朝
「這條河流如此之長,穿過了如此多的地區和城市,江中來來往往的船隻如此之多,運送的財富和貨物如此之多,實際上比基督教世界所有河流和海洋加在一起還要多!」
最早走進中國這片土地的西方人中,馬可.波羅無疑是影響最大的一位。而當他留下對神奇長江的讚歌時,西方世界也開啟了對東方的想象與探索之旅。
幾個世紀以來,旅行家、傳教士、考古家、商人、政治家、記者、侵略者們各自懷揣不同的訴求、理由、想象還有目光走進中國,各自書寫,也各自記錄。
在馬可.波羅、利瑪竇、湯若望們的記載中,中國是恢宏、壯觀、富裕的東方古國。京師城(杭州)簡直是天城,它的莊嚴和秀麗,是世界其他城市都不可比擬的,城內處處景色秀麗,讓人疑為人間天堂。在元大都可以找到世界上所有最珍奇的東西。中國人用一種「黑色的石頭」作燃料,讓人百思不得其解(因為歐洲人那時還不懂得用煤)。中國人有美不勝收的瓷器、絲綢、茶葉,也喜歡換取一船船西方人的香料、珠寶。外來人士只要穿上中國士大夫的服裝,就能得到官府民眾不約而同的信任。在利瑪竇繪製的世界地圖上,中國被標在最中央的位置,這樣顯而易見能夠博得和迎合中國人的好感與認同。順治皇帝會對湯若望進呈的渾天星球、望遠鏡等西洋玩意兒感興趣。湯若望也獲賜二品頂戴,成了最早在中國宮廷任職的西方人。
「中國」被傳遞到西方,被描畫,被口述,毫無疑問都是溢美的辭藻。哥倫布後來碰巧發現美洲新大陸,其實是帶着西班牙女皇給中國皇帝的信函,在探尋中國的航程中的神遇。
在西方人自己的總結中,通過16、17、18世紀的西方航海家、旅行家,尤其是傳教士的活動,大量關於中國的故事、見聞和理解傳到了歐洲。這其中,耶穌會傳教士的根本作用不是傳教,是在東西方之間架起了一道重要的橋樑。17世紀後期,他們是西方了解中國的最高權威。
西方信仰目光裏的中國
於是,傳教士們來了。
他們攜着西方教義興沖沖地來到古國,如明清之際來華的意大利傳教士衛匡國(原名馬爾蒂諾.馬爾蒂尼)所言,在他們剛剛發現「東域」(Cathay)和「中國」(China)是一回事時,也受到東西方信仰巨大差異的衝擊。他的著作《中國新圖誌》裏,有了關於「天朝上國」(Celestial Empire)的第一次重要描述。
「天朝」在傳教士們的視野裏,有了概念,並且漸次清晰。
耶穌會傳教士從自己的天朝經驗中發現,在中國作謙卑和苦行的表白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在中國人的眼光中,卑賤和寒酸並不意味着品行高潔。傳教士們必須使自己適應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才能在中國生活下去,甚至必須像中國人一樣梳洗打扮自己,不能像其他遠東地區的宗教信徒們一樣死守着他們在歐洲習以為常的禁欲主義原則。
這些渴望在天朝傳遞信仰的西方人,是想給中國人帶來一場思想上的革命。然而,在順從中國習俗的同時,他們恰恰不得不首先學習領悟中國的哲學。
利瑪竇的目光代表了他們早期較為單純而直接的觀察:中國哲學家中最為有名的一位是叫作孔子的人。這位博學的偉人誕生於基督紀元前551年,享年70餘歲,他既以著作和授徒,也以自己的身教激勵他的同胞追求道德。他的自制力和有節制的生活方式使他的同胞斷言,他遠比世界各國過去所有被認為是德高望重的人更為神聖。
在中國人對祖先崇拜風俗的巨大壓力下,一些傳教士試圖把儒教與基督教調合起來。一部分西方人主張允許中國的基督教摻入祖先崇拜的部分精神營養,但不同教派的傳教士卻堅決反對。也正是因此,17世紀和18世紀前期,基督徒們對天朝的「禮儀」(Chinese Rites)的爭議掀起了風暴。
由傳教士開啟的「天朝」的詮釋與想象之旅,在19世紀進入另一個高潮。這期間,不只是傳教士,記者、政治家、商人,更多的人蜂擁而至。他們好奇而來,驚奇而奔走、發現、記錄、傳達,變的是往來的故事和記述方式,而不變的是,「這始終是一個偉大又高貴的民族;他們古老的倫理思想傳承至今;中國人在文化和考試教育方面值得我們學習;他們的文明比我們的文明更具人性;他們在許多方面都領先於我們……」
西方依舊對天朝想像不斷。
「在中國,我遇到了許多我認為是正確,而實際恰好相反的事情」
經過17、18世紀傳教士的鋪墊,西方人對天朝的想像變得更加具體。
倫敦19世紀的雜誌《威斯敏特評論》裏,關於中國的描述已經不再是幾個簡單的溢美詞彙了:這是個有着悠久歷史、遼闊疆土、眾多人口的國家。從東到西和由北向南各長1.4萬英里的國土上生活着由一個君主統治的三億多人民。而且據推測,這些居民始終保持着自己獨特的風俗習慣,保留時間之長遠遠超過了任何一個有文字記載的民族。
儘管中國人不能被稱為長相漂亮的人種,他們的表情還算是顯得聰明和令人喜歡的。即使中國女人的面相和外型與男人特別相似,她們的面部卻毫無表情。中國女人通常被人說得一無是處。她們寬大的腦門、塌塌的鼻子、細長的眼睛被看成是醜陋的特徵。中國女人的體型比歐洲女人小,但是是勻稱的。
人類的歷史進程和中國的發展狀況並沒有呈現出雷同的現象,4000多年來,中國始終保持着國家的統一和獨立,它的管理理論和基本行政機構從未發生過特別重大的變化。
除此,攝影技術發明前的百餘年間,西方人還會通過繪製版畫,向自己國家的讀者介紹當時依舊很神祕的天朝。版畫同時凝聚現場與想象,記載了對於西方人來說頗為細節又陌生的中國。在1873年《倫敦新聞畫報》上,帝京的提籠架鳥就成為令西方人感到新奇的街頭一景。
作為珍貴的史料,這些版畫原始地記錄了西方人對於土生土長北京老百姓生存狀態的觀察與理解,而皇庭歲月,城牆、城門的圖景,同時成為研究老北京歷史和城市格局變化的佐證。然而,並非被記錄的即完全真實的。
神祕有時來自西方式想象的自我虛構。即便當時的西洋畫師隨使團參與正式謁見,也沒有可能現場寫生,很多畫作均為事後默寫。在資料極度缺乏的情況下,某些畫作的信息來源也會包括一些道聽途說的傳聞。至於大場面,則多為畫師頭腦中各種東方元素的無序糅合,在關於中國都城的描繪中,有時甚至出現作為背景的熱帶植物、古羅馬街市和古埃及神廟的影子。
文學藝術也成為這一場想象之旅中的重要一站。
那時候西方人的中國觀,幾乎都是從文化資料的積累中得來的,而西方人自己富有想象力的有關中國題材的文學藝術作品更是直接塑造了很多人對於「天朝」的第一次想象。荷蘭詩人馮戴爾(Vondel)用衞匡國的《韃靼戰紀》中的史料寫出一個名為Zung Chin的劇本。法國作家朱迪斯.戈提爾出版了叫作《龍的帝國》的法文小說。在西方人自己的觀察裏,這是第一部以中國為背景,有「似乎真實」的中國情節和中國人物的法文小說。
在波士頓的報紙上,一個歐洲人寫的在中國的經歷,證明了所有的「似乎真實」是由於西方人的想象方式與講述角度,使得中國故事顯得神奇:
當我向艄公詢問我們停泊的渡口在甚麼方向時,我得到的答案是西北,他說風是東南風。「我們歐洲人就不這麼說。」我想他看出了我的驚訝神情,就向我解釋了羅盤針的用法。
他說:「這根針指向南方。」在中國,我遇到了許多我認為是正確,而實際恰好相反的事情,我同意一個朋友的看法:中國人除了地理上跟我們相對外,其他許多事情也跟我們倒着來。
……這片陌生的非常陌生的土地上的一切真讓我頭暈目眩。
中國人會識別和西方人完全迥異的方向,讓他們頭暈目眩。更重要的是,那時候西方人還不知道,他們想象中的天朝,本來也正走向令人頭暈目眩的方向。
有一種傳說,叫中華帝國
儘管傳教士們記述的中國,在對其性格、哲學和文明成果的處理上有時不準確、持成見、帶偏頗,但依然是西方人的中國觀最重要和最豐富的來源之一。
儘管版畫、文學、戲劇乃至民間傳說描畫的中國,凝聚太多想象和「似乎真實」的部分,它們依然呈現了西方人認識的中華帝國。這個帝國在地理上與世隔絕是它能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它的北面是廣闊的沙漠,西部是崇山峻嶺,南面和東面是波濤洶湧的海洋。另一個原因是它的書面語言的獨特性,這個特徵是維繫一個國家統一的重要紐帶。因為這種文字是表意文字,比表音文字更優越,不受發音的變化和方言的影響。一個山東人也許不懂一個廣東人說的話,但他們卻能用相同的文字表達相同的意思。
已經深入進「天朝」骨子裏的平靜和安和的觀念與中國作為一個偉大民族的進化思想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緩慢地決定着處在與世隔絕中的中國的命運。自17世紀和18世紀耶穌會的傳教士們描繪了中國寧靜、安穩,充滿令人愉悅的畫面以來,西方人總把中國看成是世界上最和平安寧的國家。
對於西方人,第一次中英戰爭(即鴉片戰爭)是中國從已經存在了大約兩千多年的舊事物向西方新思想轉變的出發點。由於這場戰爭,西方與中國開始接近。這一時期,在美國和英國的重要期刊上居然出現了25篇之多以《中國和中國人》為題的報道。更多的西方人,尤其是記者開始到訪這個傳說中的中華帝國。
在寫了名為《中國》的報道集的英國記者柯克(George Wingrove Cooke)看來,隨着時間慢慢推移,這片東亞的土地,將向英國數以千計的商品流通打開門戶,並為它自己的國民開闢數以百萬計的勞動力市場。
從這個時候回望,四千多年來,中華帝國幾乎一直由自己的君主統治着。居民的服裝、道德、風俗習慣和信仰一直保持着統一性,它的古代立法者們制定的富有智慧的制度從來都沒有絲毫的改變。而從此,傳說中的中華帝國要徹底改變了。
1840年前,大多數西方人可能還在接收定型的飽含想象力的觀點,傳教士們誇大了中國的穩固和平靜,他們所描述的那種永恆的平穩在中國從來就沒有存在過,但是全世界卻一直把對中國永恆和平的想象當成不容置疑的真理。顯然,英中之間這一年爆發的衝突使得那些習以為常的認識漸漸瓦解。更多的西方記者們宣稱:中國不再是一個不為人知、裹着祕密和神祕外衣的區域。
傳說被打破的同時,中華帝國的變革正式拉開序幕。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