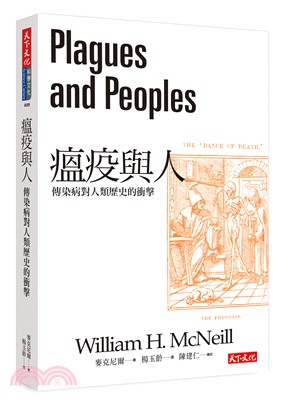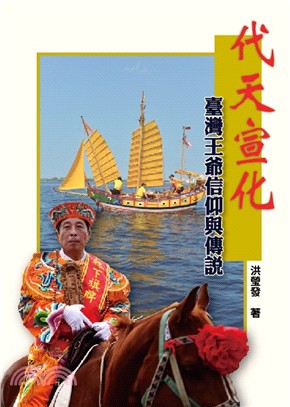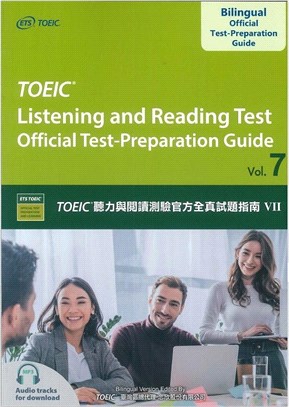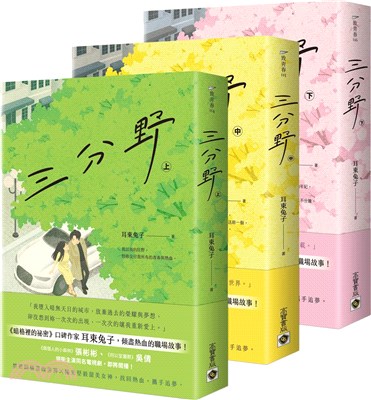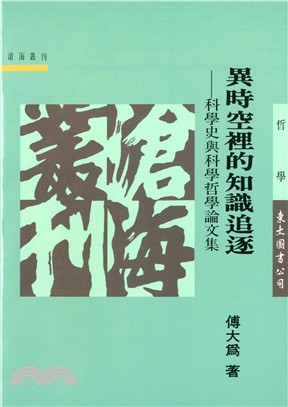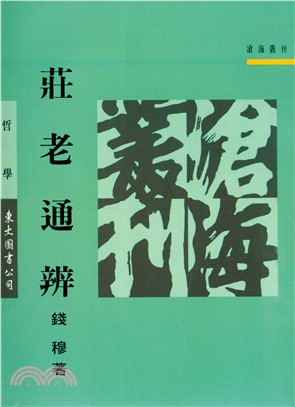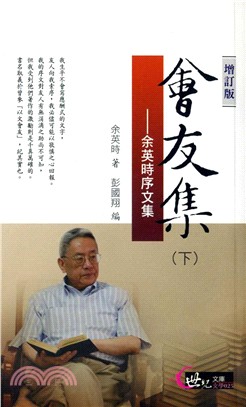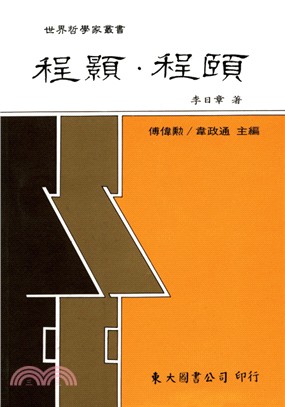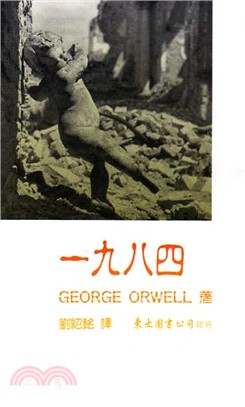瘟疫與人: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衝擊
商品資訊
系列名:科學文化
ISBN13:9789864790784
替代書名:Plagues and Peoples
出版社:天下文化
作者:麥克尼爾
譯者:楊玉齡
出版日:2016/10/21
裝訂/頁數:平裝/336頁
規格:21cm*14.8cm*2cm (高/寬/厚)
版次:3
適性閱讀分級:621【九年級】
定價
:NT$ 400 元優惠價
:90 折 360 元
絕版無法訂購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相關商品
商品簡介
病菌,是塑造人類歷史的推手,
槍砲、鋼鐵也擋不住這股力量!
「瘧疾」的兇暴,使莊嚴的朝聖之旅,化成疫病的溫床;
「霍亂」的版圖,藉交通便利的無國界化,再展新勢力;
「禽流感」的威脅,迫使高密度畜養的經濟方式,面臨挑戰;
生活在樹上的靈長類遠祖,因跳蚤和體蝨而搔癢不已;初踏上地面的人類祖先,由於大草原瀰漫的昏睡症而病懨懨;開始農耕的文明社群,遭血吸蟲症削弱了整體生產力;歐亞間的經濟貿易,致使天花悄悄跟著商旅隊伍進入新地域;蒙古大軍勢如破竹,將鼠疫散布歐亞大陸;西方帝國靠著無心傳染的天花,達成了殖民野心;工業革命帶來的交通躍進,更是讓全球成為疾病大鎔爐。
麥克尼爾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至本世紀前半,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形塑不同文明的特色。《瘟疫與人》為讀者揭示一幕幕條分縷析、鉅細靡遺的傳染病與文明交融史。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是否能靠著現代公共衛生技術,而讓文明不再受傳染病影響呢?《瘟疫與人》一書中有最好的解答!
媒體推薦
讀過《瘟疫與人》,就會從此改變看待世界歷史的觀點。
──《紐約書評》
《瘟疫與人》有著深奧微妙的內容,強而有力的分析。
──《華盛頓星報》
《瘟疫與人》是令人屏息之作。
──《國家觀察者報》
具有原創性的非凡之作……讀完《瘟疫與人》絕對會收穫匪淺,麥克尼爾的苦工沒有白下。
──《華盛頓郵報》
《瘟疫與人》是麥克尼爾繼《西方的興起》之後,又一輝煌的著作。他以恢宏的規模,將生態、人口與政治、文化整合起來,堪稱論點精采且挑戰性高的學術成就。
──《柯克斯評論》(The Kirkus Reviews)
《瘟疫與人》是一本引人入勝的書,作者強調的是一般歷史書裡不常探討的事件。讀者一旦開卷閱讀,將愛不釋手……本書值得立即推薦給大眾。
──《坦帕論壇時報》(Tampa Tribune-Times)
洞見深遠……《瘟疫與人》兼具原創性與刺激性,肯定會激起一陣波瀾。
──《出版人週刊》
《瘟疫與人》是才氣縱衡的一本書。
──《克利夫蘭日報》
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非常有說服力的論證了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巨大衝擊,是非常精采的歷史推論。
──《進步》月刊
作者在本書中展現驚人的學識涵養……《瘟疫與人》的寫作手法純熟……它勢必吸引廣大的群眾。
──《綺色佳日報》
《瘟疫與人》用引人入勝的史例,提出極為出色又具有十足挑戰性的論述。
──《紐約》雜誌
這是兼具重要性與原創性,又精心研究的作品。
──《圖書館雜誌》
《瘟疫與人》這本書令人無可抗拒。
──《波士頓週日先鋒報》
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用大量累積的證據,論述疾病在人類歷史上,扮演常見的關鍵角色。
──《巴頓魯治倡導報》(Baton Rouge Sunday Advocate)
《瘟疫與人》對於世界歷史有著極具吸引力的新解讀。
──《舊金山觀察家報》
麥克尼爾做了一件值得讚賞的事,對於人們忽略的傳染病與流行病,他提供了數量驚人的細節。
──《芝加哥日報》
《瘟疫與人》鉅細靡遺的內容,為我們提供了洞見,看透疾病這種自然災禍,如何在長遠的歷史中大幅消滅世界人口。
──《納奇茲民主報》(Natchez Democrat)
傑出歷史學家的創新研究……對於歷史事件專業的重新解讀,加上科學細節的支持,麥克尼爾提出了非常強力的論點。
──《美國圖書館協會書單》
啟蒙人心……《瘟疫與人》絕對值得推薦閱讀。
──《大湍城日報》(Grand Rapids Press)
麥克尼爾以熟練的學術風格,提出了大量證據,指出疾病在人類活動中扮演中心角色,進而影響了人類歷史的進展。
──《每日新聞》
《瘟疫與人》是首屈一指的重要著作,一部道地的革命性著作。
──《紐約客》
看待歷史的嶄新觀點,我從《瘟疫與人》中受益匪淺。
──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美國作家兼歷史學家,普立茲非小說獎得主。
《瘟疫與人》提出了非常創新,也極具挑戰性的歷史概念,令人閱讀時欲罷不能。這本書企圖引起轟動,而它也的確辦到了!
──哈里森‧梳士巴利(Harrison Salisbury),美國記者,普立茲國際報導獎得主。
得獎紀錄
聯合報讀書人版每週新書金榜推薦
中國時報開卷版一週好書推薦
誠品書店「誠品選書」
槍砲、鋼鐵也擋不住這股力量!
「瘧疾」的兇暴,使莊嚴的朝聖之旅,化成疫病的溫床;
「霍亂」的版圖,藉交通便利的無國界化,再展新勢力;
「禽流感」的威脅,迫使高密度畜養的經濟方式,面臨挑戰;
生活在樹上的靈長類遠祖,因跳蚤和體蝨而搔癢不已;初踏上地面的人類祖先,由於大草原瀰漫的昏睡症而病懨懨;開始農耕的文明社群,遭血吸蟲症削弱了整體生產力;歐亞間的經濟貿易,致使天花悄悄跟著商旅隊伍進入新地域;蒙古大軍勢如破竹,將鼠疫散布歐亞大陸;西方帝國靠著無心傳染的天花,達成了殖民野心;工業革命帶來的交通躍進,更是讓全球成為疾病大鎔爐。
麥克尼爾以編年的手法,從史前時代至本世紀前半,詳實探討傳染病如何肆虐歐洲、亞洲、非洲等文明發源地,而這些疾病又如何形塑不同文明的特色。《瘟疫與人》為讀者揭示一幕幕條分縷析、鉅細靡遺的傳染病與文明交融史。二十一世紀的我們,是否能靠著現代公共衛生技術,而讓文明不再受傳染病影響呢?《瘟疫與人》一書中有最好的解答!
媒體推薦
讀過《瘟疫與人》,就會從此改變看待世界歷史的觀點。
──《紐約書評》
《瘟疫與人》有著深奧微妙的內容,強而有力的分析。
──《華盛頓星報》
《瘟疫與人》是令人屏息之作。
──《國家觀察者報》
具有原創性的非凡之作……讀完《瘟疫與人》絕對會收穫匪淺,麥克尼爾的苦工沒有白下。
──《華盛頓郵報》
《瘟疫與人》是麥克尼爾繼《西方的興起》之後,又一輝煌的著作。他以恢宏的規模,將生態、人口與政治、文化整合起來,堪稱論點精采且挑戰性高的學術成就。
──《柯克斯評論》(The Kirkus Reviews)
《瘟疫與人》是一本引人入勝的書,作者強調的是一般歷史書裡不常探討的事件。讀者一旦開卷閱讀,將愛不釋手……本書值得立即推薦給大眾。
──《坦帕論壇時報》(Tampa Tribune-Times)
洞見深遠……《瘟疫與人》兼具原創性與刺激性,肯定會激起一陣波瀾。
──《出版人週刊》
《瘟疫與人》是才氣縱衡的一本書。
──《克利夫蘭日報》
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非常有說服力的論證了傳染病對人類歷史的巨大衝擊,是非常精采的歷史推論。
──《進步》月刊
作者在本書中展現驚人的學識涵養……《瘟疫與人》的寫作手法純熟……它勢必吸引廣大的群眾。
──《綺色佳日報》
《瘟疫與人》用引人入勝的史例,提出極為出色又具有十足挑戰性的論述。
──《紐約》雜誌
這是兼具重要性與原創性,又精心研究的作品。
──《圖書館雜誌》
《瘟疫與人》這本書令人無可抗拒。
──《波士頓週日先鋒報》
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用大量累積的證據,論述疾病在人類歷史上,扮演常見的關鍵角色。
──《巴頓魯治倡導報》(Baton Rouge Sunday Advocate)
《瘟疫與人》對於世界歷史有著極具吸引力的新解讀。
──《舊金山觀察家報》
麥克尼爾做了一件值得讚賞的事,對於人們忽略的傳染病與流行病,他提供了數量驚人的細節。
──《芝加哥日報》
《瘟疫與人》鉅細靡遺的內容,為我們提供了洞見,看透疾病這種自然災禍,如何在長遠的歷史中大幅消滅世界人口。
──《納奇茲民主報》(Natchez Democrat)
傑出歷史學家的創新研究……對於歷史事件專業的重新解讀,加上科學細節的支持,麥克尼爾提出了非常強力的論點。
──《美國圖書館協會書單》
啟蒙人心……《瘟疫與人》絕對值得推薦閱讀。
──《大湍城日報》(Grand Rapids Press)
麥克尼爾以熟練的學術風格,提出了大量證據,指出疾病在人類活動中扮演中心角色,進而影響了人類歷史的進展。
──《每日新聞》
《瘟疫與人》是首屈一指的重要著作,一部道地的革命性著作。
──《紐約客》
看待歷史的嶄新觀點,我從《瘟疫與人》中受益匪淺。
──威爾‧杜蘭特(Will Durant),美國作家兼歷史學家,普立茲非小說獎得主。
《瘟疫與人》提出了非常創新,也極具挑戰性的歷史概念,令人閱讀時欲罷不能。這本書企圖引起轟動,而它也的確辦到了!
──哈里森‧梳士巴利(Harrison Salisbury),美國記者,普立茲國際報導獎得主。
得獎紀錄
聯合報讀書人版每週新書金榜推薦
中國時報開卷版一週好書推薦
誠品書店「誠品選書」
作者簡介
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著
1947年於康乃爾大學博士畢業後,即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教職生涯長達四十年。麥克尼爾的史學著作產量豐富,目前翻譯成繁體中文的作品有《世界史》、《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歐洲歷史的塑造》、與兒子勞勃・麥克尼爾(Robert McNeill)合著的作品《文明之網》,以及《瘟疫與人》。
麥克尼爾向來擅長以分析眼光,細數宏大歷史長河中的點點滴滴。他的《西方的興起》曾榮獲196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瘟疫與人》是麥克尼爾融合流行病學史與人類文明史的代表作,受這種新史觀影響的著名作品,即有《槍砲、病菌與鋼鐵》。
麥克尼爾於1996年獲頒歐洲重要的獎項──伊拉斯謨獎(Erasmus Prize),以表彰他在世界史上的貢獻;2009年榮獲美國人文獎章。麥克尼爾於2016年7月8日逝世,享壽九十八歲。
陳建仁/審訂
出生於香蕉王國的高雄縣旗山鎮,在家排行老七,個性爽朗、樂觀,喜歡大自然。畢業於台灣大學動物系、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流行病學研究所博士班,專攻人類遺傳及遺傳流行病學。曾任台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流行病學研究所創所所長、公共衛生學院院長、行政院衛生署署長、行政院國科會主委、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現為中華民國第14屆副總統。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教育部國家講座、中央研究院院士、總統科學獎、世界科學院院士、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等。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六百餘篇,著有《流行病學》、《流行病學原理與方法》等書。
1947年於康乃爾大學博士畢業後,即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教職生涯長達四十年。麥克尼爾的史學著作產量豐富,目前翻譯成繁體中文的作品有《世界史》、《威尼斯共和國的故事》、《歐洲歷史的塑造》、與兒子勞勃・麥克尼爾(Robert McNeill)合著的作品《文明之網》,以及《瘟疫與人》。
麥克尼爾向來擅長以分析眼光,細數宏大歷史長河中的點點滴滴。他的《西方的興起》曾榮獲1964年美國國家圖書獎。《瘟疫與人》是麥克尼爾融合流行病學史與人類文明史的代表作,受這種新史觀影響的著名作品,即有《槍砲、病菌與鋼鐵》。
麥克尼爾於1996年獲頒歐洲重要的獎項──伊拉斯謨獎(Erasmus Prize),以表彰他在世界史上的貢獻;2009年榮獲美國人文獎章。麥克尼爾於2016年7月8日逝世,享壽九十八歲。
陳建仁/審訂
出生於香蕉王國的高雄縣旗山鎮,在家排行老七,個性爽朗、樂觀,喜歡大自然。畢業於台灣大學動物系、公共衛生研究所碩士班、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流行病學研究所博士班,專攻人類遺傳及遺傳流行病學。曾任台灣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所長、流行病學研究所創所所長、公共衛生學院院長、行政院衛生署署長、行政院國科會主委、中央研究院副院長。現為中華民國第14屆副總統。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教育部國家講座、中央研究院院士、總統科學獎、世界科學院院士、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等。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六百餘篇,著有《流行病學》、《流行病學原理與方法》等書。
序
【再版導讀】宏觀的疾病文明史 / 李尚仁
長年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加拿大裔歷史學者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於2016年7月8日以九十八歲高齡逝世。他的經典名著《瘟疫與人》中譯本在同一年度再版,可說是台灣對這位重要歷史學者極佳的致敬與紀念。麥克尼爾被視為是目前十分熱門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研究領域的先驅,成名作是出版於1963年的《西方的興起》,該書的主標題或許會讓人以為麥克尼爾談的是「西方」的歷史,其實他討論的是數千年來人類各種文明的互動,以及西方如何於短短五百年間在此過程中興起。麥克尼爾另一本世界史名著是1982年出版的《權力的追求》(The Pursuit of Power),討論軍事與科技如何影響權力關係與人類社會。
《瘟疫與人》的內容更廣泛、企圖心也更大。表面看來該書探討的是疾病史,而此類研究早已有之,畢竟傳染病的暴發常會對歷史有重大影響。例如斑疹傷寒對遠征俄國的拿破崙大軍造成巨大傷害,或是中世紀晚期的瘟疫對歐洲封建制度的衝擊。然而,《瘟疫與人》處理的範圍遠超過個別事件、疫情與疾病,而企圖討論史前時期直到現代疾病如何影響人類的歷史。
簡潔原理看疾病史
儘管涉及的範圍龐大,《瘟疫與人》的基本解釋原理卻相當簡單,它建立於簡單的免疫學與疾病地理學觀念。簡而言之,人群接觸到來自不同環境的新病原時,常會因為缺乏免疫力而導致嚴重疫情與大量死亡。這種接觸可能是因為人群遷徙到新的環境,也可能是外來的人群或病媒將新的病原引入。接觸過微生物而仍存活者,則會產生一定的免疫力,當病原與免疫力達成平衡後,該疾病往往成為當地的風土病,尤其是兒童疾病,其殺傷力大減。
溫暖潮濕的熱帶森林,致病微生物種類多於寒冷乾燥的溫帶地區;擁擠城市的傳染病多於地廣人稀的鄉間;農業耕作和畜牧也會帶來更多的傳染病。除了病菌這類微型寄生物之外,人們還常常面臨榨取其勞動果實的巨型寄生物,像是統治者、征服者與殖民者等等。本書從這些基本原理出發,來探討生態、疾病與人類歷史的關係;從史前時代到現在的人類歷史,就是微型寄生物、巨型寄生物以及被寄生者之間的互動過程與結果。
《瘟疫與人》是生態史與環境史的重要經典,但它不是唯一的先驅。麥克尼爾自承在寫作《西方的興起》時,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為何為數甚少的西班牙冒險家,能夠擊敗印加與阿茲特克等大帝國,進而征服美洲?許多證據顯示,其實是美洲原住民對西班牙人帶來的傳染病缺乏免疫力,遭到疫情嚴重打擊,而讓野心家有機可乘。麥克尼爾並不是頭一個研究此一課題的學者,美國歷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Jr.)稍早在1972年出版的《哥倫布大交換》,就是探討此一主題的生態史名著。
但《瘟疫與人》更進一步,試圖以生態因素解釋許多看似難解的歷史現象,像是玄奧的宗教教義。例如,相對於中國入世的儒教,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之所以教導人棄絕塵世,是由於印度溫暖的環境具有更多的傳染病,致使生產力低的人民在應付國家的稅賦之後,資源所剩無幾,因此發展出貶低物質世界的宗教。他還推測印度種姓制度的產生,是因為北方征服者為避免染上南方部落民族身上的寄生蟲病,所發展出的接觸禁忌。有趣的是,麥克尼爾在書中也否定過去疾病史常有的看法,像是梅毒是哥倫布的船隊從新大陸帶到歐洲的說法。
學界多方檢視
《瘟疫與人》一出版就廣受好評,學界大多讚賞其宏觀視野與大膽綜述所帶來的啟發。然而,如此充滿驚人之論的著作必然會引起批評,尤其是史料的使用與推論必遭到嚴格檢視。具有醫師資格,也專研疾病史與疾病地理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艾克納希特(Erwin Ackerknecht, 1906-1988),就稱《瘟疫與人》為「科幻小說」。英國醫學史學者阿諾(David Arnold)1996年出版的《自然的問題》(The Problem of Nature)一書就宣稱,麥克尼爾對於黑死病與蒙古帝國擴張之間的解釋,具有高度臆測性質。阿諾提出許多的質疑,例如鼠疫真的是起源於中國雲南?會不會在十四世紀時中亞的老鼠就已經帶有鼠疫桿菌了?鼠疫真的是借助蒙古大軍傳播的嗎?會不會是氣候變遷導致帶菌的老鼠從原棲地出走,而使得人類與牠們接觸的機會大為增加?
此外,中國史籍關於疫病的記載大多十分簡略,在1330年代與1340年代大量發生的疫病,真的是鼠疫?還是其他傳染病?這種對於將現代醫學知識套用於過去史料的批評,在1990年代的醫學史學界達到高峰。學者懷疑能否透過史料記載,對過去的疾病進行「回顧診斷」,畢竟古代人對疾病的認知與描述和現代醫學大不相同,而古代醫者所信奉的體液說等醫學理論,也和現代細菌學大異其趣。除非有好的遺體標本,否則今天的學者也沒辦法對古代病人做細菌學檢驗,怎能光憑文字記載就斷定當時的人罹患的是何種疾病,甚至進而做出各種令人嘖嘖稱奇的歷史推論?
歷史經典瑕不掩瑜
不過,正如任教於牛津大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哈里森(Mark Harrison)所指出,學者如果採取這樣徹底的懷疑態度,認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所描述記載的疾病,絕對無法對應到今天的疾病分類,那麼就不可能進行任何長時段、大地理範圍的疾病史研究,更遑論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
換句話說,要不要做回溯診斷以及進行疾病生態史的推論,需要看探討的是何種議題而定。如果學者追問的是社會文化與醫學理論,如何影響對疾病的認識與治療,那當然不需要借助現代醫學來做回溯診斷。但如果要宏觀了解生態、經濟與長時程歷史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透過現代科學知識來揣摩當時的疾病種類,仍舊是無可避免的。在《疾病與現代世界》(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這本書中,哈里森強調執著於這樣的爭論是沒有益處的,疾病史的研究應該要「百花齊放」。
《瘟疫與人》這樣的經典,影響力有時會出現在出乎意料的地方。法國學者拉圖(Bruno Latour)往往被視為是對科學與科技有著激進看法的前衛思想家,他有時也被某些人批評為極端相對主義者。然而,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書中,將微生物與人類帝國比喻為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以吞食消化來比喻族群與文明的征服、消長乃至滅絕,此種看法成為拉圖的《巴斯德的實驗室》一書的靈感來源之一,不只多次加以引用,而且還大為讚賞。
麥克尼爾以同樣的視野看待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正符合拉圖將人類與非人類(微生物、動植物、機械甚至整個地球)都當成網絡中的行動者的理論觀點。強調科學推論的環境決定論與前衛的相對主義建構論,在此出現奇特的交會,這也許就是麥克尼爾的史學想像,展現於《瘟疫與人》的奇特魅力。
家學淵源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麥克尼爾一家祖孫三代都是歷史學者。他的父親約翰・麥克尼爾(John McNeill)是長老會牧師,也是研究基督教史的學者。他的兒子約翰・勞勃・麥克尼爾(John Robert McNeill)是目前仍很活躍的傑出歷史學者,和乃父一樣專攻世界史與環境史,著有《太陽底下的新鮮事》,更和父親合寫了《文明之網》。這兩本書在台灣都已有中譯本出版。勞勃・麥克尼爾在史學上克紹箕裘,甚至在父親成名的疾病環境史研究領域也發光發熱,他在2010年出版的《蚊子帝國》(Mosquito Empires),探討歐洲殖民加勒比海區域以來,黃熱病與瘧疾等病媒蚊傳播的熱帶疾病,以及該區域頻繁發生的戰事,如何塑造此地的歷史。此書出版以來獲得學界極大的好評,讚譽不斷。《蚊子帝國》的卓越成就,或許正說明了《瘟疫與人》所開拓的研究途徑,在更細膩的分析方式下,仍可帶來豐碩的史學成果。(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緣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大約二十年前,為了撰寫《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書,我曾閱讀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這段歷史,以充實相關的知識。眾所周知,當時柯爾特斯(Hernando Cortez)只帶了六百名不到的隨從,就征服了擁有數百萬人的阿茲特克帝國。這麼一小撮人怎麼可能戰勝人口眾多的帝國呢?這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那些常見的解釋似乎都不夠充分。即使蒙提祖馬(Montezuma)和他的夥伴在剛開始時,錯把西班牙人視為天神,但沒多久,他們就從經驗中獲得實情了。或許在第一回合交手時,馬匹和火藥令土著既驚且怕。然而,在武裝衝突後,馬匹的血肉之軀以及西班牙人所舞弄的原始槍炮,自然會暴露出它們的極限。當然,柯爾特斯有辦法號召墨西哥境內多支印地安民族,合力對抗阿茲特克帝國,是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那些印地安盟邦要不是有理由認定柯爾特斯會贏,是不會選擇站在西班牙人這一邊的。
事實上,這則奇特的墨西哥征服記,只是更大謎團中的一部分(隨後不久,在南美洲又發生同樣驚人的歷史:皮薩羅征服印加帝國)。能夠漂洋過海來到新大陸的西班牙人並不多,但是他們卻能成功的把文化傳播給為數極眾的美洲印第安人。然而,單憑歐洲文明固有的魅力,以及西班牙人所精通的科技優勢,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為何印地安人會如此大規模的叛離歷史悠久的傳統生活方式及信仰。
譬如,為何墨西哥及祕魯的古老宗教會消失得這般徹底?村民對於庇蔭他們農田無數年代的神明和祭典,為何不再虔誠了?縱然在西方傳教士的心目中,這是因為基督教的真理是如此明晰,因此根本無需解釋為何能成功轉變數百萬印地安人的信仰;但來自傳教士的宣教以及基督教本身的吸引力,似乎也不足以解釋這一切。
一窺疾病角色
在柯爾特斯征服史的諸多解釋中,有一項不經意的說法(我已記不得它的出處了),為上述問題提供了一則解答。在審慎思考這個答案以及它背後的涵義後,我的新假說變得愈來愈有可能,且愈來愈有分量了。因為,就在阿茲特克人把柯爾特斯及其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傳染病正在城中肆虐、蔓延。那位率隊攻打西班牙人的阿茲特克將領也死於那場「悲傷之夜」(noche trista,這是後來西班牙人對這場疫病的稱呼)。這場致命傳染病釀成的癱瘓效應正足以解釋,為何阿茲特克人當時並未乘勝追擊潰敗的西班牙人,反而讓對手有時間、有機會喘息及重整,進而聯合其他印地安族人來包圍墨西哥城,贏得最後的勝利。
再者,像這樣「只殺死印地安人,而西班牙人卻毫髮無損的傳染病」,在心理方面的暗示也很值得考量。這種差別的遭遇,當時只能用超自然力來解釋,而在這場戰爭中,哪一方受天神的庇護也是無庸置疑的。在西班牙人信奉的神展示了卓越的神力之後,環繞著印地安神祇所建立的宗教、祭師與生活方式,再也無法維持下去。難怪,印地安人會如此溫順的接受基督教,向西班牙人俯首稱臣。上帝顯然偏袒西班牙人,而且此後每一場從歐洲(不久後又加上非洲)引進的傳染病大暴發,都不斷的重複這種教訓。
這類一面倒向侵犯印第安人的傳染病,提供了門路,以理解西班牙人如何在軍事及文化上,輕鬆的征服美洲。然而,這個假說立刻引發了其他問題:西班牙人是何時且如何獲得這種染病經驗,使他們能在新大陸無往不利?為何印第安人不具有能消滅西班牙人的地方疾病?只要試著回答這些問題,很快就會開始發現迄今仍被忽略的史學領域:即人類與傳染病交鋒的歷史,以及每當舊有疾病的疆界被打破,使得新傳染病入侵某個對它缺乏免疫力的民族時,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歷史也提供了許多十六、十七世紀發生在美洲的類似事件紀錄。本書的重點即在描繪這類致命接觸的主軸。我的結論將令讀者大吃一驚,因為在傳統歷史中備受冷落的事件,卻占據我論點中的樞紐地位。主要原因在於,負責篩檢人類在歷史上存活紀錄的學者,對於各種疾病模式可能產生的重大變化,缺乏敏銳的洞察力。
史學家忽略了傳染病
「從未遇過的傳染病襲擊人類族群時,會發生的慘劇」這類重大事件,歐洲歷史確實記錄了幾樁。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可以算是最主要的代表,其次是十九世紀的霍亂大流行,後者破壞性雖然沒有那麼大,但卻是比較近代且記載較完備的案例。然而,歷史學家從來不把這些案例,視作重大傳染病暴發這種大型事件,因為這類與新疾病慘烈交手的早期案例,被深深的埋藏在過去,那時的紀錄殘缺不全,使得事件的規模和意義都輕易的遭到後人忽略。
在評鑑古代典籍時,史學家自然會受限於他們個人對傳染病的體驗。由於現代人已歷經過各種疾病,對於許多熟悉的傳染病,都練就出相當程度的免疫力,因此總能很快的鎮壓住一般的疫病流行;訓練有素的史學家,生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不由得會把疫病造成重大傷亡的所有論點,都當成誇大之辭。
事實上,從前的史學家之所以沒能適度看重這整個主題,基本原因是在於他們不了解「疾病在普遍具有罹病經驗的族群中暴發流行」與「同樣的疾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間的重大差別。史學家若預設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所有傳染病的模式,都和歐洲地區的傳染病模式大同小異,那麼疫病流行自然就沒什麼好提的,因此,史學家也傾向採用隨興的方式,把這類資料輕描淡寫過去,正如我在柯爾特斯的勝利中所閱讀到的一樣。
於是,流行病史成為古文物研究者的領地,他們興致勃勃的抄抄寫寫,記下一堆基本上沒什麼意義的數據,就只因為這些資料剛好就在手邊。不過,還是有黑死病以及其他幾個流行病例,都是在軍營內突然暴發疫病,因而扭轉了軍情,有時甚至決定了戰爭的勝敗。像這類插曲當然不可能遭人遺忘,但是它們所帶有的不可預測性,卻令史學家深感不自在。我們都希望人類歷史的軌跡有理可循,而史學家為了迎合大眾需求,通常也特別強調歷史中可計算、可定義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素。然而,當疫病在戰時(或和平時期)成為決定歷史的關鍵因子時,這份解析歷史的努力恐怕徒勞無功。因此史學家總是低調處理這類重要的疫病事件。
當然,有一些圈外人會扮演提出異議的角色,例如美國細菌學家靳塞(Hans Zinsser),蒐集了一堆足以說明疾病的確舉足輕重的例子。因此,靳塞那本讀來令人津津有味的著作《老鼠、蝨子與歷史》(Rats, Lice and History)中,指出斑疹傷寒大流行,如何經常破壞國王與武士的錦囊妙計。
但這類書籍並未嘗試把疾病史擺進人類歷史中更重大的場景。這類書籍和其他書籍一樣,還是把偶爾暴發的疫病慘案,視為突發且無法預期的事件,這在本質上已超出史學詮釋的範圍,因此無法引起詮釋歷史的專業歷史學者的興趣。
本書藉由揭示各種疾病傳播的模式如何影響遠古與現代人類的歷史,想把流行病史帶入歷史詮釋的領域。我所做的諸多猜測及推論都仍在試探階段。我提出的這些論點,還有待精通各種難懂語言的專家,細心審視經典古籍,來加以確認或是糾正。像這類的學院派研究工作,往往需要寫成論文,做為「箭靶」,看是否經得起考驗。我提出的想法和猜測,應該合乎上述的要求,同時還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使他們關心人類歷史諸多舊觀念之間所存在的重要鴻溝。
除了我必須提出的細節內容外,想必大家都會認同「進一步了解人類社群在自然平衡中不斷變遷的地位」,應該成為我們解析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沒有人能懷疑,傳染病在過去及現在都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寄生」無所不在
在開始說故事之前,有幾項關於寄生、疾病、瘟疫的論點以及相關的觀念,或許有助於避免讓讀者弄混。
對於所有生物而言,疾病和寄生現象都是無所不在的。某生物從另一方生物身上成功取得食物,對後者(宿主來說),等於一場惡性感染或疾病。所有動物都依靠其他生物為食物來源,人類也不例外。覓食問題以及人類社群在覓食上的各種招式,充斥在經濟史中。反倒是「避免成為其他生物的食物」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少見,大體是因為人類早在相當遠古的時代,就已經不畏懼大型掠食者,例如獅子或野狼。話雖如此,我們或許還是可以把大部分人類的生命,視為一場介於「病菌的微寄生」以及「大型天敵的巨寄生」之間的危險平衡;而所謂的大型天敵,主要是其他的人類。
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指的是微小的寄生物(病毒、細菌或是多細胞生物),它們能在人體組織中,找到維生所需的食物來源。有些微寄生物會引發急性疾病,結果不是很快的把宿主殺死,就是在宿主體內引發免疫反應,讓自己被宿主殺死。偶爾這類致病的生物不知怎的,進入特殊宿主的體內,使宿主成為帶原者,有能力感染其他人,自己卻不生病;另外還有一些微寄生物,有辦法和它們的人類宿主,達成比較穩定的平衡關係。這類感染無疑也會吸走宿主體內的部分能量,但是它們的存在並不會妨礙宿主的正常功能。
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也展現出類似的多樣性。有些會立即致命,例如,當獅子、野狼在吃人或是吃其他動物時,勢必會令宿主立即喪命;有些巨寄生物則容許宿主無限期(indefinitely)的存活。
早在遠古時代,從事狩獵的人類,其技巧和威力便已超越了他們的動物天敵。人類於是竄上了食物鏈的頂端,從此不再那麼容易被大型掠食動物吞噬。然而從那之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互相殘殺」幾乎是兩相鄰部落的互動特色。這使得成功的人類狩獵者,真正躍上和獅群、狼群同等級的地位。
接著,當生產食物成為某些人類社群的生活方式後,另一種新版本的巨寄生方式也跟著出現。征服者可以從生產者手中取走食物,供自己消耗,因此對於生產者而言,征服者便成為另一種型態的寄生物了。尤其是在土地富饒的地區,甚至證明了人類社會可以發展出相當穩定的巨寄生模式。
摘自 緣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長年任教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的加拿大裔歷史學者麥克尼爾 (William H. McNeill),於2016年7月8日以九十八歲高齡逝世。他的經典名著《瘟疫與人》中譯本在同一年度再版,可說是台灣對這位重要歷史學者極佳的致敬與紀念。麥克尼爾被視為是目前十分熱門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研究領域的先驅,成名作是出版於1963年的《西方的興起》,該書的主標題或許會讓人以為麥克尼爾談的是「西方」的歷史,其實他討論的是數千年來人類各種文明的互動,以及西方如何於短短五百年間在此過程中興起。麥克尼爾另一本世界史名著是1982年出版的《權力的追求》(The Pursuit of Power),討論軍事與科技如何影響權力關係與人類社會。
《瘟疫與人》的內容更廣泛、企圖心也更大。表面看來該書探討的是疾病史,而此類研究早已有之,畢竟傳染病的暴發常會對歷史有重大影響。例如斑疹傷寒對遠征俄國的拿破崙大軍造成巨大傷害,或是中世紀晚期的瘟疫對歐洲封建制度的衝擊。然而,《瘟疫與人》處理的範圍遠超過個別事件、疫情與疾病,而企圖討論史前時期直到現代疾病如何影響人類的歷史。
簡潔原理看疾病史
儘管涉及的範圍龐大,《瘟疫與人》的基本解釋原理卻相當簡單,它建立於簡單的免疫學與疾病地理學觀念。簡而言之,人群接觸到來自不同環境的新病原時,常會因為缺乏免疫力而導致嚴重疫情與大量死亡。這種接觸可能是因為人群遷徙到新的環境,也可能是外來的人群或病媒將新的病原引入。接觸過微生物而仍存活者,則會產生一定的免疫力,當病原與免疫力達成平衡後,該疾病往往成為當地的風土病,尤其是兒童疾病,其殺傷力大減。
溫暖潮濕的熱帶森林,致病微生物種類多於寒冷乾燥的溫帶地區;擁擠城市的傳染病多於地廣人稀的鄉間;農業耕作和畜牧也會帶來更多的傳染病。除了病菌這類微型寄生物之外,人們還常常面臨榨取其勞動果實的巨型寄生物,像是統治者、征服者與殖民者等等。本書從這些基本原理出發,來探討生態、疾病與人類歷史的關係;從史前時代到現在的人類歷史,就是微型寄生物、巨型寄生物以及被寄生者之間的互動過程與結果。
《瘟疫與人》是生態史與環境史的重要經典,但它不是唯一的先驅。麥克尼爾自承在寫作《西方的興起》時,注意到一個奇特的現象:為何為數甚少的西班牙冒險家,能夠擊敗印加與阿茲特克等大帝國,進而征服美洲?許多證據顯示,其實是美洲原住民對西班牙人帶來的傳染病缺乏免疫力,遭到疫情嚴重打擊,而讓野心家有機可乘。麥克尼爾並不是頭一個研究此一課題的學者,美國歷史學家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 Jr.)稍早在1972年出版的《哥倫布大交換》,就是探討此一主題的生態史名著。
但《瘟疫與人》更進一步,試圖以生態因素解釋許多看似難解的歷史現象,像是玄奧的宗教教義。例如,相對於中國入世的儒教,印度的佛教和印度教之所以教導人棄絕塵世,是由於印度溫暖的環境具有更多的傳染病,致使生產力低的人民在應付國家的稅賦之後,資源所剩無幾,因此發展出貶低物質世界的宗教。他還推測印度種姓制度的產生,是因為北方征服者為避免染上南方部落民族身上的寄生蟲病,所發展出的接觸禁忌。有趣的是,麥克尼爾在書中也否定過去疾病史常有的看法,像是梅毒是哥倫布的船隊從新大陸帶到歐洲的說法。
學界多方檢視
《瘟疫與人》一出版就廣受好評,學界大多讚賞其宏觀視野與大膽綜述所帶來的啟發。然而,如此充滿驚人之論的著作必然會引起批評,尤其是史料的使用與推論必遭到嚴格檢視。具有醫師資格,也專研疾病史與疾病地理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艾克納希特(Erwin Ackerknecht, 1906-1988),就稱《瘟疫與人》為「科幻小說」。英國醫學史學者阿諾(David Arnold)1996年出版的《自然的問題》(The Problem of Nature)一書就宣稱,麥克尼爾對於黑死病與蒙古帝國擴張之間的解釋,具有高度臆測性質。阿諾提出許多的質疑,例如鼠疫真的是起源於中國雲南?會不會在十四世紀時中亞的老鼠就已經帶有鼠疫桿菌了?鼠疫真的是借助蒙古大軍傳播的嗎?會不會是氣候變遷導致帶菌的老鼠從原棲地出走,而使得人類與牠們接觸的機會大為增加?
此外,中國史籍關於疫病的記載大多十分簡略,在1330年代與1340年代大量發生的疫病,真的是鼠疫?還是其他傳染病?這種對於將現代醫學知識套用於過去史料的批評,在1990年代的醫學史學界達到高峰。學者懷疑能否透過史料記載,對過去的疾病進行「回顧診斷」,畢竟古代人對疾病的認知與描述和現代醫學大不相同,而古代醫者所信奉的體液說等醫學理論,也和現代細菌學大異其趣。除非有好的遺體標本,否則今天的學者也沒辦法對古代病人做細菌學檢驗,怎能光憑文字記載就斷定當時的人罹患的是何種疾病,甚至進而做出各種令人嘖嘖稱奇的歷史推論?
歷史經典瑕不掩瑜
不過,正如任教於牛津大學的著名醫學史學者哈里森(Mark Harrison)所指出,學者如果採取這樣徹底的懷疑態度,認為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文化所描述記載的疾病,絕對無法對應到今天的疾病分類,那麼就不可能進行任何長時段、大地理範圍的疾病史研究,更遑論進行跨文化的比較研究。
換句話說,要不要做回溯診斷以及進行疾病生態史的推論,需要看探討的是何種議題而定。如果學者追問的是社會文化與醫學理論,如何影響對疾病的認識與治療,那當然不需要借助現代醫學來做回溯診斷。但如果要宏觀了解生態、經濟與長時程歷史的關係,在某種程度上,透過現代科學知識來揣摩當時的疾病種類,仍舊是無可避免的。在《疾病與現代世界》(Disease and the Modern World)這本書中,哈里森強調執著於這樣的爭論是沒有益處的,疾病史的研究應該要「百花齊放」。
《瘟疫與人》這樣的經典,影響力有時會出現在出乎意料的地方。法國學者拉圖(Bruno Latour)往往被視為是對科學與科技有著激進看法的前衛思想家,他有時也被某些人批評為極端相對主義者。然而,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書中,將微生物與人類帝國比喻為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以吞食消化來比喻族群與文明的征服、消長乃至滅絕,此種看法成為拉圖的《巴斯德的實驗室》一書的靈感來源之一,不只多次加以引用,而且還大為讚賞。
麥克尼爾以同樣的視野看待微型寄生物與巨型寄生物,正符合拉圖將人類與非人類(微生物、動植物、機械甚至整個地球)都當成網絡中的行動者的理論觀點。強調科學推論的環境決定論與前衛的相對主義建構論,在此出現奇特的交會,這也許就是麥克尼爾的史學想像,展現於《瘟疫與人》的奇特魅力。
家學淵源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麥克尼爾一家祖孫三代都是歷史學者。他的父親約翰・麥克尼爾(John McNeill)是長老會牧師,也是研究基督教史的學者。他的兒子約翰・勞勃・麥克尼爾(John Robert McNeill)是目前仍很活躍的傑出歷史學者,和乃父一樣專攻世界史與環境史,著有《太陽底下的新鮮事》,更和父親合寫了《文明之網》。這兩本書在台灣都已有中譯本出版。勞勃・麥克尼爾在史學上克紹箕裘,甚至在父親成名的疾病環境史研究領域也發光發熱,他在2010年出版的《蚊子帝國》(Mosquito Empires),探討歐洲殖民加勒比海區域以來,黃熱病與瘧疾等病媒蚊傳播的熱帶疾病,以及該區域頻繁發生的戰事,如何塑造此地的歷史。此書出版以來獲得學界極大的好評,讚譽不斷。《蚊子帝國》的卓越成就,或許正說明了《瘟疫與人》所開拓的研究途徑,在更細膩的分析方式下,仍可帶來豐碩的史學成果。(本文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緣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大約二十年前,為了撰寫《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一書,我曾閱讀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的這段歷史,以充實相關的知識。眾所周知,當時柯爾特斯(Hernando Cortez)只帶了六百名不到的隨從,就征服了擁有數百萬人的阿茲特克帝國。這麼一小撮人怎麼可能戰勝人口眾多的帝國呢?這究竟是如何發生的?
那些常見的解釋似乎都不夠充分。即使蒙提祖馬(Montezuma)和他的夥伴在剛開始時,錯把西班牙人視為天神,但沒多久,他們就從經驗中獲得實情了。或許在第一回合交手時,馬匹和火藥令土著既驚且怕。然而,在武裝衝突後,馬匹的血肉之軀以及西班牙人所舞弄的原始槍炮,自然會暴露出它們的極限。當然,柯爾特斯有辦法號召墨西哥境內多支印地安民族,合力對抗阿茲特克帝國,是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但那些印地安盟邦要不是有理由認定柯爾特斯會贏,是不會選擇站在西班牙人這一邊的。
事實上,這則奇特的墨西哥征服記,只是更大謎團中的一部分(隨後不久,在南美洲又發生同樣驚人的歷史:皮薩羅征服印加帝國)。能夠漂洋過海來到新大陸的西班牙人並不多,但是他們卻能成功的把文化傳播給為數極眾的美洲印第安人。然而,單憑歐洲文明固有的魅力,以及西班牙人所精通的科技優勢,似乎仍不足以解釋,為何印地安人會如此大規模的叛離歷史悠久的傳統生活方式及信仰。
譬如,為何墨西哥及祕魯的古老宗教會消失得這般徹底?村民對於庇蔭他們農田無數年代的神明和祭典,為何不再虔誠了?縱然在西方傳教士的心目中,這是因為基督教的真理是如此明晰,因此根本無需解釋為何能成功轉變數百萬印地安人的信仰;但來自傳教士的宣教以及基督教本身的吸引力,似乎也不足以解釋這一切。
一窺疾病角色
在柯爾特斯征服史的諸多解釋中,有一項不經意的說法(我已記不得它的出處了),為上述問題提供了一則解答。在審慎思考這個答案以及它背後的涵義後,我的新假說變得愈來愈有可能,且愈來愈有分量了。因為,就在阿茲特克人把柯爾特斯及其手下逐出墨西哥城的那晚,天花傳染病正在城中肆虐、蔓延。那位率隊攻打西班牙人的阿茲特克將領也死於那場「悲傷之夜」(noche trista,這是後來西班牙人對這場疫病的稱呼)。這場致命傳染病釀成的癱瘓效應正足以解釋,為何阿茲特克人當時並未乘勝追擊潰敗的西班牙人,反而讓對手有時間、有機會喘息及重整,進而聯合其他印地安族人來包圍墨西哥城,贏得最後的勝利。
再者,像這樣「只殺死印地安人,而西班牙人卻毫髮無損的傳染病」,在心理方面的暗示也很值得考量。這種差別的遭遇,當時只能用超自然力來解釋,而在這場戰爭中,哪一方受天神的庇護也是無庸置疑的。在西班牙人信奉的神展示了卓越的神力之後,環繞著印地安神祇所建立的宗教、祭師與生活方式,再也無法維持下去。難怪,印地安人會如此溫順的接受基督教,向西班牙人俯首稱臣。上帝顯然偏袒西班牙人,而且此後每一場從歐洲(不久後又加上非洲)引進的傳染病大暴發,都不斷的重複這種教訓。
這類一面倒向侵犯印第安人的傳染病,提供了門路,以理解西班牙人如何在軍事及文化上,輕鬆的征服美洲。然而,這個假說立刻引發了其他問題:西班牙人是何時且如何獲得這種染病經驗,使他們能在新大陸無往不利?為何印第安人不具有能消滅西班牙人的地方疾病?只要試著回答這些問題,很快就會開始發現迄今仍被忽略的史學領域:即人類與傳染病交鋒的歷史,以及每當舊有疾病的疆界被打破,使得新傳染病入侵某個對它缺乏免疫力的民族時,所帶來的深遠影響。
從這個角度來看,人類歷史也提供了許多十六、十七世紀發生在美洲的類似事件紀錄。本書的重點即在描繪這類致命接觸的主軸。我的結論將令讀者大吃一驚,因為在傳統歷史中備受冷落的事件,卻占據我論點中的樞紐地位。主要原因在於,負責篩檢人類在歷史上存活紀錄的學者,對於各種疾病模式可能產生的重大變化,缺乏敏銳的洞察力。
史學家忽略了傳染病
「從未遇過的傳染病襲擊人類族群時,會發生的慘劇」這類重大事件,歐洲歷史確實記錄了幾樁。十四世紀的黑死病可以算是最主要的代表,其次是十九世紀的霍亂大流行,後者破壞性雖然沒有那麼大,但卻是比較近代且記載較完備的案例。然而,歷史學家從來不把這些案例,視作重大傳染病暴發這種大型事件,因為這類與新疾病慘烈交手的早期案例,被深深的埋藏在過去,那時的紀錄殘缺不全,使得事件的規模和意義都輕易的遭到後人忽略。
在評鑑古代典籍時,史學家自然會受限於他們個人對傳染病的體驗。由於現代人已歷經過各種疾病,對於許多熟悉的傳染病,都練就出相當程度的免疫力,因此總能很快的鎮壓住一般的疫病流行;訓練有素的史學家,生活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不由得會把疫病造成重大傷亡的所有論點,都當成誇大之辭。
事實上,從前的史學家之所以沒能適度看重這整個主題,基本原因是在於他們不了解「疾病在普遍具有罹病經驗的族群中暴發流行」與「同樣的疾病在缺乏免疫力的族群中蔓延」間的重大差別。史學家若預設在現代醫學出現之前,所有傳染病的模式,都和歐洲地區的傳染病模式大同小異,那麼疫病流行自然就沒什麼好提的,因此,史學家也傾向採用隨興的方式,把這類資料輕描淡寫過去,正如我在柯爾特斯的勝利中所閱讀到的一樣。
於是,流行病史成為古文物研究者的領地,他們興致勃勃的抄抄寫寫,記下一堆基本上沒什麼意義的數據,就只因為這些資料剛好就在手邊。不過,還是有黑死病以及其他幾個流行病例,都是在軍營內突然暴發疫病,因而扭轉了軍情,有時甚至決定了戰爭的勝敗。像這類插曲當然不可能遭人遺忘,但是它們所帶有的不可預測性,卻令史學家深感不自在。我們都希望人類歷史的軌跡有理可循,而史學家為了迎合大眾需求,通常也特別強調歷史中可計算、可定義而且多半也能控制的因素。然而,當疫病在戰時(或和平時期)成為決定歷史的關鍵因子時,這份解析歷史的努力恐怕徒勞無功。因此史學家總是低調處理這類重要的疫病事件。
當然,有一些圈外人會扮演提出異議的角色,例如美國細菌學家靳塞(Hans Zinsser),蒐集了一堆足以說明疾病的確舉足輕重的例子。因此,靳塞那本讀來令人津津有味的著作《老鼠、蝨子與歷史》(Rats, Lice and History)中,指出斑疹傷寒大流行,如何經常破壞國王與武士的錦囊妙計。
但這類書籍並未嘗試把疾病史擺進人類歷史中更重大的場景。這類書籍和其他書籍一樣,還是把偶爾暴發的疫病慘案,視為突發且無法預期的事件,這在本質上已超出史學詮釋的範圍,因此無法引起詮釋歷史的專業歷史學者的興趣。
本書藉由揭示各種疾病傳播的模式如何影響遠古與現代人類的歷史,想把流行病史帶入歷史詮釋的領域。我所做的諸多猜測及推論都仍在試探階段。我提出的這些論點,還有待精通各種難懂語言的專家,細心審視經典古籍,來加以確認或是糾正。像這類的學院派研究工作,往往需要寫成論文,做為「箭靶」,看是否經得起考驗。我提出的想法和猜測,應該合乎上述的要求,同時還能吸引讀者的注意力,使他們關心人類歷史諸多舊觀念之間所存在的重要鴻溝。
除了我必須提出的細節內容外,想必大家都會認同「進一步了解人類社群在自然平衡中不斷變遷的地位」,應該成為我們解析歷史的一部分,而且也沒有人能懷疑,傳染病在過去及現在都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寄生」無所不在
在開始說故事之前,有幾項關於寄生、疾病、瘟疫的論點以及相關的觀念,或許有助於避免讓讀者弄混。
對於所有生物而言,疾病和寄生現象都是無所不在的。某生物從另一方生物身上成功取得食物,對後者(宿主來說),等於一場惡性感染或疾病。所有動物都依靠其他生物為食物來源,人類也不例外。覓食問題以及人類社群在覓食上的各種招式,充斥在經濟史中。反倒是「避免成為其他生物的食物」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少見,大體是因為人類早在相當遠古的時代,就已經不畏懼大型掠食者,例如獅子或野狼。話雖如此,我們或許還是可以把大部分人類的生命,視為一場介於「病菌的微寄生」以及「大型天敵的巨寄生」之間的危險平衡;而所謂的大型天敵,主要是其他的人類。
微寄生物(microparasite)指的是微小的寄生物(病毒、細菌或是多細胞生物),它們能在人體組織中,找到維生所需的食物來源。有些微寄生物會引發急性疾病,結果不是很快的把宿主殺死,就是在宿主體內引發免疫反應,讓自己被宿主殺死。偶爾這類致病的生物不知怎的,進入特殊宿主的體內,使宿主成為帶原者,有能力感染其他人,自己卻不生病;另外還有一些微寄生物,有辦法和它們的人類宿主,達成比較穩定的平衡關係。這類感染無疑也會吸走宿主體內的部分能量,但是它們的存在並不會妨礙宿主的正常功能。
巨寄生物(macroparasite)也展現出類似的多樣性。有些會立即致命,例如,當獅子、野狼在吃人或是吃其他動物時,勢必會令宿主立即喪命;有些巨寄生物則容許宿主無限期(indefinitely)的存活。
早在遠古時代,從事狩獵的人類,其技巧和威力便已超越了他們的動物天敵。人類於是竄上了食物鏈的頂端,從此不再那麼容易被大型掠食動物吞噬。然而從那之後,有好長一段時間,「互相殘殺」幾乎是兩相鄰部落的互動特色。這使得成功的人類狩獵者,真正躍上和獅群、狼群同等級的地位。
接著,當生產食物成為某些人類社群的生活方式後,另一種新版本的巨寄生方式也跟著出現。征服者可以從生產者手中取走食物,供自己消耗,因此對於生產者而言,征服者便成為另一種型態的寄生物了。尤其是在土地富饒的地區,甚至證明了人類社會可以發展出相當穩定的巨寄生模式。
摘自 緣起〈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目次
再版導讀 宏觀的疾病文明史 李尚仁
導讀 古往今來話傳染病史 陳建仁
緣起 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第1章 狩獵族群的行蹤
第2章 古文明世界的疾苦
第3章 歐亞疾病大鎔爐
第4章 蒙古帝國打通路徑
第5章 闖入美洲新世界
第6章 近代醫學大放異彩
附錄 中國流行病史
作者誌謝
名詞注釋
導讀 古往今來話傳染病史 陳建仁
緣起 史學家的漏網之魚
第1章 狩獵族群的行蹤
第2章 古文明世界的疾苦
第3章 歐亞疾病大鎔爐
第4章 蒙古帝國打通路徑
第5章 闖入美洲新世界
第6章 近代醫學大放異彩
附錄 中國流行病史
作者誌謝
名詞注釋
書摘/試閱
【內文試閱】古籍中少不了瘟神
然而,文字證據還是能清楚的證明,流行性疾病的確曾在古代中東地區出現過。在巴比倫的《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所提及的災難中,曾把河水氾濫描述為「瘟疫之神造訪」,另一本年代相仿的埃及古籍(西元前2000年),也曾把對法老王的敬畏,拿來和某個瘟疫年時對疾病之神的敬畏相提並論。
在中國也一樣,根據最古老的可辨識文字(約西元前十三世紀)中,顯露出當時的人們對傳染性流行病已相當熟悉。古代河南安陽的統治者曾經問道:「今年是否為疾年,又有幾許人喪命?」於是,他的卜卦專家便把這個問題,以現代學者能讀懂的文字型式,記錄在羊的肩胛骨上,以便在祭典時,向神明尋求答案。《聖經》的文字記載,雖然年代要晚了許多,但是其中可能保存了可追溯到差不多同個時期的口傳歷史。因此,在〈出埃及記〉中所描述的埃及疫病,可能真的有歷史根據。其中曾經提到,摩西為埃及招來的疫病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瘡」,不只如此,單單一個晚上,某種致命的災難降臨埃及的長子、長女,使得「無一家不死一個人的」。
我們也可以把上帝懲罰非利士人(Philistines)扣押約櫃、上帝對大衛罪孽的懲罰(若《聖經》所言屬實,即把一百三十萬名以色列、猶太壯丁中的八萬人殺死),又或者耶和華使者造訪,一夜之間「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迫使亞述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自猶太撤軍,沒能拿下耶路撒冷城〕等等事件,視為流行病的造訪。
根據這些章節,這群舊約《聖經》的作者,在西元前1000年到西元前500年間,把這些文章寫成當時的格式時,就已經相當了解突然暴發致命疾病的可能性,而且還把這類流行病解釋為上帝的懲罰。現代譯者都習慣用「plague」這個字來形容大規模的傳染疫病,因為歐洲持續受到這股致命威力的疾病侵擾,直到十八世紀才定出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即黑死病)這個名詞。不過,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假設古代那些流行病,也是淋巴腺鼠疫的大暴發。任何一種熟悉的文明性傳染病,不論是經由呼吸道傳染(如麻疹、天花或感冒),或是經由消化道(如霍亂和痢疾),都可能造成《聖經》裡那種突然暴發的大規模死亡。
因此,我們能推論,在西元前500年之前,古代中東人民相當熟悉這類傳染病,而且傳染病在降低人口密度以及影響戰事方面,必定曾經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這類疾病的蹂躪,顯然還不足以規律的摧毀軍隊,或是讓人口數低於建立帝國所需的標準。否則,亞述及波斯帝國,就不可能在西元前第九到第五世紀期間,如此興盛。接著還能推論,那些吸引《聖經》作者注意的流行疾病,無論在嚴重程度或頻率上,都還不足以徹底摧毀文明社會的架構。
換句話說,從致病生物的觀點來看,當時他們正要和人類宿主達成相互容忍的適應。動物的病媒庫(就像鼠疫的例子),當然也可能在兩次傳染病暴發事件之間,扮演保存致病原的重要角色。但是,古代中東地區的人口,絕對多得足以支撐現代兒童疾病的始祖,成為後續傳染模式的基礎。
在幾個主要的人口及社群中心,擁有建立長期人類感染鏈的良機,其中某些疾病很可能因此而變成常見的兒童疾病,顯現出今日我們所熟悉的模式。於是,流行病暴發主要還是發生在偏遠地區,因為在那些地方,人口密度還不足以長期支持傳染病,但是偶發狀況(通常與軍事活動有關)卻可能突然引爆一場傳染病,強烈的程度,足以對人民生命造成慘重影響,進而引起飽學教士及學者的注意,並在《聖經》中提及這類事件。
假使這些推論正確,在古代中東地區,文明傳染病的興起時間,只比灌溉農業的傳染病與宿主族群取得平衡的時間稍微晚一點。在西元前500年左右,中東這處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中心,而且也是世上最大的人口集中地之一,不啻提供了最適當的時間和機會,讓微寄生以及巨寄生平衡,能在鄉村和城市生活規範的條件下,達到穩定狀態。
更特別的是,由於現存最早提到流行性疾病的文獻,可以回溯到大約西元前2000年,因此從那時到西元前500年,便有足夠長的時間,能讓傳染病在文明化且人口密集的古代中東地區,建立起穩定的模式。
相反的,在較偏遠的次要地區,則顯得較不穩定,這類地區包括三大不同的天然環境:黃河流域沖積平原、恆河流域的季風帶以及地中海沿岸。它們和中東地區比起來,都算是相當近代才支撐起文明社會的架構。因此,在西元前500年,這些地區的生態平衡依舊不安定,而且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地方的疾病模式,也遠不如中東地區來得固定。
想證明生態的不穩定性,首先可以由相對的大量人口成長看出端倪,而在西元前500年前後,上述幾個地區都出現了這種現象。人口成長的證據雖然只是間接的,但是可信度卻一點兒也不差。要是人口數目不曾大規模提升,這些文明所占有的領地,是不可能擴張得如此厲害。再者,上述每個案例中,人口成長還會隨著農耕的精良技術而調適,同時,各個巨寄生政治和文化結構上的適度複雜化,使得各文明在後續歷史中,獲得持久且獨樹一幟的風格。
稅金與地租的雙重寄生
在遠東地區,耕種黃河流域沖積平原的農人,大約是在西元前600年之後,有了真正的進展。這些進展包括,把農業區由早期中國農業大本營的半乾旱黃土區,向外擴張,並且把主要作物由小米改為稻米。要把廣大的沖積平原,轉換成一片片連綿不斷的稻田,而且每塊稻田都必須定期灌溉,勢必得投入大量人力從事築堤、排水、挖渠以及開墾沼澤、濕地等工程。此外,整個農作區域為了預防河水氾濫,還必須築一道規模龐大又巧妙的防氾工事,來控制滾滾騷動的黃河。
這條水域是全世界地質活動最旺盛的河流之一。最近(以地質時間標準而言),它併吞了其他流系的一些重要支流,因此它的主流流經黃土區域時,會沖下大量黃土,逐年將河道愈切愈深。接下來,當飽含黃土的河水來到幾近平坦的沖積平原時,水流變緩,造成黃河上游大量侵蝕土壤,但下游卻大量沉積土壤。結果,黃河在沖積平原上的河床,迅速的節節高升。
當人們開始利用人工築堤,來防範水流時,就碰上麻煩了。當然,堤防可以配合河床沉積的淤泥,每年築高一點兒。但造成的後果是,不久後這條大河就會從高出周邊土地的肥沃沖積平原流出,奔騰入海。要把黃河留在堤防內,需要大量人力才辦得到,因為任何一道小水流只要在堤防上找著出路,假使沒有及時被人發現而加以圍堵的話,不久就會增長為強烈的激流,甚至只要幾小時就足以在堤防上撕裂出大缺口;一旦大缺口出現,整條河流就會從人工河床中溢出,為自個兒尋找一條新的、地勢更低的水道。這條大河曾經多次變遷水道達數百公里之遠,湧流進黃土高原的北部(如同現在的位置)或南部。黃河在地質上的不穩定性愈演愈烈,但這並非人為活動所造成;而黃河需要經過一段地質時間,才能與它的水流取得穩定的調適。
另外一項影響古代中國生態平衡的因素,則比較接近人類的時間尺度。例如在政治層面,因為種植稻田而增廣的食物來源,供養了敵對王侯間的戰事達數百年之久,直到西元前221年,一位征服者平定了整個黃河流域沖積平原,以及黃河南、北兩岸接壤的大塊領域。又經過一陣短暫的內戰後,漢朝於西元前202年取得政權,並且至少在名義上統治了全中國,直到西元221年為止。
帝國統治當局,可能是藉由減低長期戰爭時的農人賦稅,來確保帝國的內部和平。不過,漢朝的和平也意味著,儘管當時人們對種稻(或小米)的農夫有著雙重巨寄生,大體上仍相安無事。因為私有地主所抽的地租,以及上繳王朝的稅金,全都來自同一批農夫,顯然兩者是競爭的。然而,他們同時也充分的相互支援。他們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因為事實上,王朝裡的官僚,通常也是由地主階層徵召而來的。
深植儒家思想
然而,在巨寄生平衡中還有另外一個有力因素,開始出現在古代的中國。就在中國地主聯合起來向農民需索之際,一套截然不同的觀念和行為理念,也同時在地主以及官員階層中生根發芽,也就是「儒家思想」。在王朝官員和私有地主間傳播儒家文化,會在他們心中營造出「禁止濫用或擴張權力」的道德觀。這造成的重要影響是:向農民強索的物資限度必須合乎傳統,也不能超過農民的負擔。
結果,到了漢武帝時代(西元前140年至西元前87年),在中國社會內部,農人和直接寄生在他們身上的兩個社會階層之間,達成相當穩定且長期的平衡。這種平衡一直延續下來,雖然曾經歷某些變革,但是從來沒有真正破壞過結構,直到二十世紀。
整體說來,我們能確定,地主及收租官員的需索,雖然沉重,但仍然能讓中國農民生產並留下自個兒所需的基本糧食,否則中國人口在黃河沖積平原及鄰近地區,就不可能出現緩慢、大規模的成長,並南移到長江流域地區;而中國農民也不可能替傳統中國的壯麗文化和帝國架構,提供不斷擴張的根基(雖說其中也曾經歷數不清的挫折)。
現存文獻無法讓我們精準的追蹤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腳步。然而,中國南方的開發,卻一直遲到漢朝結束之後才開始。換句話說,從真正開始馴服黃河流域沖積平原,到長江谷地也進行類似的開發之間,約相隔了一千年之久。
乍看之下,中國開墾現今南方地區的腳步,可能緩慢的令人驚訝。政治、軍事方面的障礙並不是主要原因。南方地區也很適合農業移墾,因為溫和的氣候有著較長的生長季,而豐沛的雨量,更是排除了在北方時,經常無法灌溉土地的乾旱危機。
再者,長江由西邊山麓流出之際,曾行經許多湖泊,這也意味著不會出現棘手的大量沉積物,來填塞長江流經的低窪處,所以黃河最頭痛的河床淤積問題,長江一點也不用擔心;南方的堤岸以及人工渠道,也不像在北方有著極大壓力。簡單的說,黃河流域在歷史上的那些技術性災難,在此統統不見了。
摘自 第3章〈歐亞疾病大鎔爐〉
然而,文字證據還是能清楚的證明,流行性疾病的確曾在古代中東地區出現過。在巴比倫的《吉爾伽美什史詩》(Epic of Gilgamesh)所提及的災難中,曾把河水氾濫描述為「瘟疫之神造訪」,另一本年代相仿的埃及古籍(西元前2000年),也曾把對法老王的敬畏,拿來和某個瘟疫年時對疾病之神的敬畏相提並論。
在中國也一樣,根據最古老的可辨識文字(約西元前十三世紀)中,顯露出當時的人們對傳染性流行病已相當熟悉。古代河南安陽的統治者曾經問道:「今年是否為疾年,又有幾許人喪命?」於是,他的卜卦專家便把這個問題,以現代學者能讀懂的文字型式,記錄在羊的肩胛骨上,以便在祭典時,向神明尋求答案。《聖經》的文字記載,雖然年代要晚了許多,但是其中可能保存了可追溯到差不多同個時期的口傳歷史。因此,在〈出埃及記〉中所描述的埃及疫病,可能真的有歷史根據。其中曾經提到,摩西為埃及招來的疫病是「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瘡」,不只如此,單單一個晚上,某種致命的災難降臨埃及的長子、長女,使得「無一家不死一個人的」。
我們也可以把上帝懲罰非利士人(Philistines)扣押約櫃、上帝對大衛罪孽的懲罰(若《聖經》所言屬實,即把一百三十萬名以色列、猶太壯丁中的八萬人殺死),又或者耶和華使者造訪,一夜之間「在亞述營中殺了十八萬五千人」〔迫使亞述王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自猶太撤軍,沒能拿下耶路撒冷城〕等等事件,視為流行病的造訪。
根據這些章節,這群舊約《聖經》的作者,在西元前1000年到西元前500年間,把這些文章寫成當時的格式時,就已經相當了解突然暴發致命疾病的可能性,而且還把這類流行病解釋為上帝的懲罰。現代譯者都習慣用「plague」這個字來形容大規模的傳染疫病,因為歐洲持續受到這股致命威力的疾病侵擾,直到十八世紀才定出淋巴腺鼠疫(bubonic plague,即黑死病)這個名詞。不過,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假設古代那些流行病,也是淋巴腺鼠疫的大暴發。任何一種熟悉的文明性傳染病,不論是經由呼吸道傳染(如麻疹、天花或感冒),或是經由消化道(如霍亂和痢疾),都可能造成《聖經》裡那種突然暴發的大規模死亡。
因此,我們能推論,在西元前500年之前,古代中東人民相當熟悉這類傳染病,而且傳染病在降低人口密度以及影響戰事方面,必定曾經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這類疾病的蹂躪,顯然還不足以規律的摧毀軍隊,或是讓人口數低於建立帝國所需的標準。否則,亞述及波斯帝國,就不可能在西元前第九到第五世紀期間,如此興盛。接著還能推論,那些吸引《聖經》作者注意的流行疾病,無論在嚴重程度或頻率上,都還不足以徹底摧毀文明社會的架構。
換句話說,從致病生物的觀點來看,當時他們正要和人類宿主達成相互容忍的適應。動物的病媒庫(就像鼠疫的例子),當然也可能在兩次傳染病暴發事件之間,扮演保存致病原的重要角色。但是,古代中東地區的人口,絕對多得足以支撐現代兒童疾病的始祖,成為後續傳染模式的基礎。
在幾個主要的人口及社群中心,擁有建立長期人類感染鏈的良機,其中某些疾病很可能因此而變成常見的兒童疾病,顯現出今日我們所熟悉的模式。於是,流行病暴發主要還是發生在偏遠地區,因為在那些地方,人口密度還不足以長期支持傳染病,但是偶發狀況(通常與軍事活動有關)卻可能突然引爆一場傳染病,強烈的程度,足以對人民生命造成慘重影響,進而引起飽學教士及學者的注意,並在《聖經》中提及這類事件。
假使這些推論正確,在古代中東地區,文明傳染病的興起時間,只比灌溉農業的傳染病與宿主族群取得平衡的時間稍微晚一點。在西元前500年左右,中東這處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中心,而且也是世上最大的人口集中地之一,不啻提供了最適當的時間和機會,讓微寄生以及巨寄生平衡,能在鄉村和城市生活規範的條件下,達到穩定狀態。
更特別的是,由於現存最早提到流行性疾病的文獻,可以回溯到大約西元前2000年,因此從那時到西元前500年,便有足夠長的時間,能讓傳染病在文明化且人口密集的古代中東地區,建立起穩定的模式。
相反的,在較偏遠的次要地區,則顯得較不穩定,這類地區包括三大不同的天然環境:黃河流域沖積平原、恆河流域的季風帶以及地中海沿岸。它們和中東地區比起來,都算是相當近代才支撐起文明社會的架構。因此,在西元前500年,這些地區的生態平衡依舊不安定,而且我們有理由相信,這些地方的疾病模式,也遠不如中東地區來得固定。
想證明生態的不穩定性,首先可以由相對的大量人口成長看出端倪,而在西元前500年前後,上述幾個地區都出現了這種現象。人口成長的證據雖然只是間接的,但是可信度卻一點兒也不差。要是人口數目不曾大規模提升,這些文明所占有的領地,是不可能擴張得如此厲害。再者,上述每個案例中,人口成長還會隨著農耕的精良技術而調適,同時,各個巨寄生政治和文化結構上的適度複雜化,使得各文明在後續歷史中,獲得持久且獨樹一幟的風格。
稅金與地租的雙重寄生
在遠東地區,耕種黃河流域沖積平原的農人,大約是在西元前600年之後,有了真正的進展。這些進展包括,把農業區由早期中國農業大本營的半乾旱黃土區,向外擴張,並且把主要作物由小米改為稻米。要把廣大的沖積平原,轉換成一片片連綿不斷的稻田,而且每塊稻田都必須定期灌溉,勢必得投入大量人力從事築堤、排水、挖渠以及開墾沼澤、濕地等工程。此外,整個農作區域為了預防河水氾濫,還必須築一道規模龐大又巧妙的防氾工事,來控制滾滾騷動的黃河。
這條水域是全世界地質活動最旺盛的河流之一。最近(以地質時間標準而言),它併吞了其他流系的一些重要支流,因此它的主流流經黃土區域時,會沖下大量黃土,逐年將河道愈切愈深。接下來,當飽含黃土的河水來到幾近平坦的沖積平原時,水流變緩,造成黃河上游大量侵蝕土壤,但下游卻大量沉積土壤。結果,黃河在沖積平原上的河床,迅速的節節高升。
當人們開始利用人工築堤,來防範水流時,就碰上麻煩了。當然,堤防可以配合河床沉積的淤泥,每年築高一點兒。但造成的後果是,不久後這條大河就會從高出周邊土地的肥沃沖積平原流出,奔騰入海。要把黃河留在堤防內,需要大量人力才辦得到,因為任何一道小水流只要在堤防上找著出路,假使沒有及時被人發現而加以圍堵的話,不久就會增長為強烈的激流,甚至只要幾小時就足以在堤防上撕裂出大缺口;一旦大缺口出現,整條河流就會從人工河床中溢出,為自個兒尋找一條新的、地勢更低的水道。這條大河曾經多次變遷水道達數百公里之遠,湧流進黃土高原的北部(如同現在的位置)或南部。黃河在地質上的不穩定性愈演愈烈,但這並非人為活動所造成;而黃河需要經過一段地質時間,才能與它的水流取得穩定的調適。
另外一項影響古代中國生態平衡的因素,則比較接近人類的時間尺度。例如在政治層面,因為種植稻田而增廣的食物來源,供養了敵對王侯間的戰事達數百年之久,直到西元前221年,一位征服者平定了整個黃河流域沖積平原,以及黃河南、北兩岸接壤的大塊領域。又經過一陣短暫的內戰後,漢朝於西元前202年取得政權,並且至少在名義上統治了全中國,直到西元221年為止。
帝國統治當局,可能是藉由減低長期戰爭時的農人賦稅,來確保帝國的內部和平。不過,漢朝的和平也意味著,儘管當時人們對種稻(或小米)的農夫有著雙重巨寄生,大體上仍相安無事。因為私有地主所抽的地租,以及上繳王朝的稅金,全都來自同一批農夫,顯然兩者是競爭的。然而,他們同時也充分的相互支援。他們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因為事實上,王朝裡的官僚,通常也是由地主階層徵召而來的。
深植儒家思想
然而,在巨寄生平衡中還有另外一個有力因素,開始出現在古代的中國。就在中國地主聯合起來向農民需索之際,一套截然不同的觀念和行為理念,也同時在地主以及官員階層中生根發芽,也就是「儒家思想」。在王朝官員和私有地主間傳播儒家文化,會在他們心中營造出「禁止濫用或擴張權力」的道德觀。這造成的重要影響是:向農民強索的物資限度必須合乎傳統,也不能超過農民的負擔。
結果,到了漢武帝時代(西元前140年至西元前87年),在中國社會內部,農人和直接寄生在他們身上的兩個社會階層之間,達成相當穩定且長期的平衡。這種平衡一直延續下來,雖然曾經歷某些變革,但是從來沒有真正破壞過結構,直到二十世紀。
整體說來,我們能確定,地主及收租官員的需索,雖然沉重,但仍然能讓中國農民生產並留下自個兒所需的基本糧食,否則中國人口在黃河沖積平原及鄰近地區,就不可能出現緩慢、大規模的成長,並南移到長江流域地區;而中國農民也不可能替傳統中國的壯麗文化和帝國架構,提供不斷擴張的根基(雖說其中也曾經歷數不清的挫折)。
現存文獻無法讓我們精準的追蹤中國古代文明發展的腳步。然而,中國南方的開發,卻一直遲到漢朝結束之後才開始。換句話說,從真正開始馴服黃河流域沖積平原,到長江谷地也進行類似的開發之間,約相隔了一千年之久。
乍看之下,中國開墾現今南方地區的腳步,可能緩慢的令人驚訝。政治、軍事方面的障礙並不是主要原因。南方地區也很適合農業移墾,因為溫和的氣候有著較長的生長季,而豐沛的雨量,更是排除了在北方時,經常無法灌溉土地的乾旱危機。
再者,長江由西邊山麓流出之際,曾行經許多湖泊,這也意味著不會出現棘手的大量沉積物,來填塞長江流經的低窪處,所以黃河最頭痛的河床淤積問題,長江一點也不用擔心;南方的堤岸以及人工渠道,也不像在北方有著極大壓力。簡單的說,黃河流域在歷史上的那些技術性災難,在此統統不見了。
摘自 第3章〈歐亞疾病大鎔爐〉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