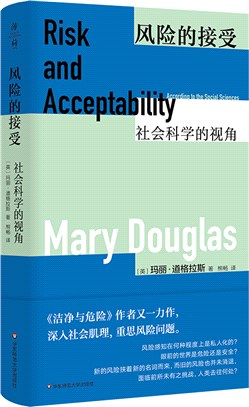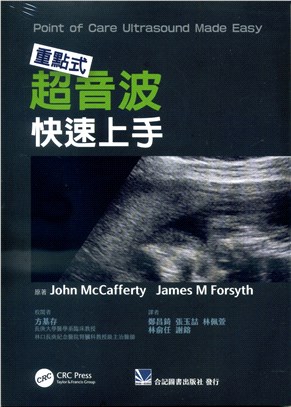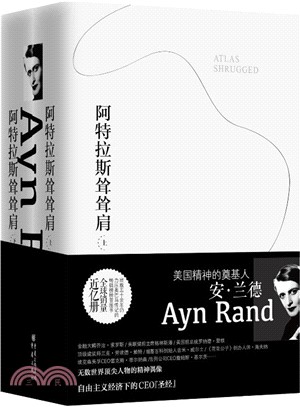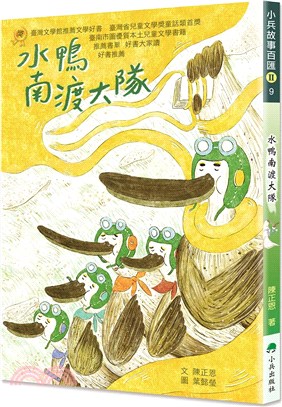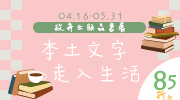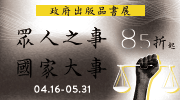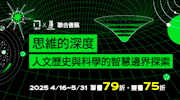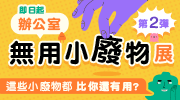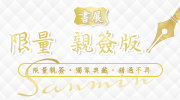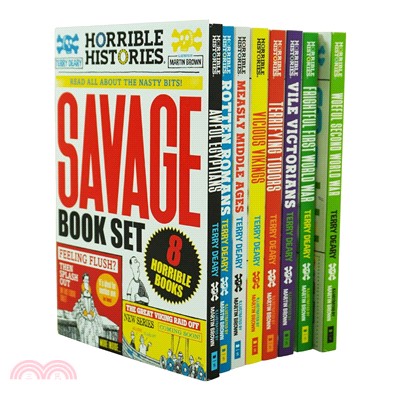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名人/編輯推薦
序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本書基於對司馬遷《史記》的閱讀和思考,作者董成龍在多年潛心閱讀經典的基礎上,整理出一條貫穿三皇五帝至漢朝的立朝與立教線索,根據這條線索,又反觀司馬遷的史家筆法及其背後的心法。
司馬遷繼《春秋》之志而作《史記》,申明周秦之變與秦漢之變,敘事貫穿立朝與立教兩大問題。立教是確立官奉學說、改正朔(年的起始月和月的起始日),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則無法導民以德,延綿政權。漢朝立朝以來,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呂無違高祖確立的漢朝祖制,雖行黃老之術卻不依黃帝(土德)為國朝敲定土德;中經漢文帝劉恒(前203-前157)、漢景帝劉啟(前188-前141)意欲改弦更張,遭遇立朝權臣捍衛祖制,未能成行;終於漢武帝確立代秦而起的漢朝新德(土德)。與此同時,在儒生建議下,漢朝不再沿用秦制顓頊曆,改用太初曆,重啟歷史紀元。改德與太初曆創制(天人之際),加之由黃老之術而獨尊儒術(君臣關係)的官學調整,共同構成立教時刻。
司馬遷繼《春秋》之志而作《史記》,申明周秦之變與秦漢之變,敘事貫穿立朝與立教兩大問題。立教是確立官奉學說、改正朔(年的起始月和月的起始日),要害在立德。立朝而不立教,則無法導民以德,延綿政權。漢朝立朝以來,高祖沿用秦制秦德(水德),惠呂無違高祖確立的漢朝祖制,雖行黃老之術卻不依黃帝(土德)為國朝敲定土德;中經漢文帝劉恒(前203-前157)、漢景帝劉啟(前188-前141)意欲改弦更張,遭遇立朝權臣捍衛祖制,未能成行;終於漢武帝確立代秦而起的漢朝新德(土德)。與此同時,在儒生建議下,漢朝不再沿用秦制顓頊曆,改用太初曆,重啟歷史紀元。改德與太初曆創制(天人之際),加之由黃老之術而獨尊儒術(君臣關係)的官學調整,共同構成立教時刻。
作者簡介
董成龍,法學博士,現為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學院講師、碩士生導師,主攻政治思想史,聚焦中世紀之後的立國與立教。主編“世界史與古典傳統”譯叢,編譯著作《大學與博雅教育》、《德性與權力》。代表作品: 《清民變局中的政治儒生與國運情懷》、《共和與君主》、《梁漱溟的“建國運動”》、《立教時刻的史家筆法》等論文,《排他性共和主義與非君主制共和國》等譯文。
名人/編輯推薦
1.劉小楓寫長篇序言解讀、推薦此書。
2.本書基於對司馬遷《史記》的文本細讀,以“立朝”、“立教”為綱,張開史家“筆法”、“心法”之目。
3. 本書提供了《史記》的另一種閱讀方式和思考路徑。
2.本書基於對司馬遷《史記》的文本細讀,以“立朝”、“立教”為綱,張開史家“筆法”、“心法”之目。
3. 本書提供了《史記》的另一種閱讀方式和思考路徑。
序
後 記
洪邁(1123―1202)指出秦、隋二朝被後世詬病,未必因為它們太過不堪,還有一層原因,是它們緊隨其後的漢朝和唐朝都“享國久長”,相較之下,顯得秦、隋這兩個朝代很糟糕(《容齋隨筆·秦隋之惡》)。長短比較,固然有其道理;但更重要的差異或許在於秦、隋兩朝都是紛繁戰局的終結者,完成了立朝的事業,原本承載了歷史寄託,卻迅速重蹈覆轍,留待它們身後的漢、唐兩朝才完成立教的事業。如饒宗頤先生(1917―2018)所示,正統之“正”(立教)比“統”(立朝)更重要,無奈歷代正統論大多著眼於“統”。
漢朝一改黃老之學與漢初祖制,轉向以法立國、以儒文明的政制安排;唐朝一改以往的進身之制,開創科舉,以制度化的方式將士子身心收入斛中。漢、唐在經學和制度兩方面的事業拓展,為此後直至今日的中國文教事業提供了核心要素,雖然經學及其制度已經被打散,但一些義理已經化作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素。文教事業這三重面向,不可不察。
1936年,毛澤東經過長征到達陝北,創作了《沁園春·雪》,感歎江山多嬌,回望中古君主,“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毛澤東評點了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元太祖五人,指出了他們的缺陷,無疑都指向文教問題。馮至先生(1905―1993)曾詩雲:“我們走過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們的生命”(《我們站立在高高的山巔》)。無怪乎,經歷過漫長中世紀和二十世紀數次大革命的我們,面對文教的故事並不陌生。
猶太人面臨著“保國”、“保種”、“保教”的問題;晚清先進士人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看來在思考國是上,猶太人問題和中國人問題在這三個層面相遇:國、種和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構詞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從這三個層面來講的(“人民”作為一種“教”來自於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中所呈現的解放全人類的教義)。中國近代以來遭遇的這三個層面的問題,延綿至今。這本小書就是在這一思想脈衝下完成的。
數年前,我在業師邱立波先生指導下完成一篇小文,當時落筆總結說全文皆是邱師學思之注腳,今日這本小書當然也沒有逃出邱師為我規範的學人心性和問題意識;原來今日的思考早在數年前邱師為我講解班馬異同時就已埋下伏筆。本書還在擴充時,邱師的《禮法與國體:兩漢政治的歷史與經驗》問世(中央編譯出版社,2018年),不禁感慨師徒學緣殊勝。業師許振洲先生行無為之教正是無違我業已確立的學問品性,時至今日方知當時許師是在潛移默化地讓我習練收束之功,可惜而今才理解這番良苦用心;他早年研究法家,可惜我不通法語,無法閱讀他用法語撰寫的《中國法家的統治藝術》(L’Art de la Politique chez les Légistes Chinois,1995),許師晚近研究共和國史的一身工夫,我也未能吸收一二,否則這本小書可能會有另外的境界。
劉小楓先生讓我見識到成德者如何提攜年輕後學,本書大綱正是在小楓先生的點撥下才得以成型,若沒有小楓先生的鼓勵,這本小書也斷不能成。十七年前,小楓先生曾以述為作,撰文《司馬遷是政治哲學家?》(載《二十一世紀》,2001年2月),十七年過去了,不知道司馬遷研究的路線有沒有受此影響而引發轉變;十七年後的今日,這本小書若能呼應那篇文章則是莫大之幸――畢竟,這本小書的許多觀點背後都是小楓先生的“幽靈”(當然,文責自負)。這些年,若沒有幾位賢師相伴,真不知道該如何度過。
在本書大綱以《立教時刻的史家筆法》刊發(載《天府新論》,2018年第2期)前後,劉訓練先生、任鋒先生和唐文明先生都曾提供無私的幫助,為我最終完成這部小書增添了信心。婁林兄和顧枝鷹兄為本書正標題提供了漂亮的拉丁文和希臘文翻譯。從定稿到問世,若沒有彭文曼編輯的辛勤勞動,本書也無法這麼快問世。謹此一併致謝。
本書力圖以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當代觀察貫通“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的理解,當然也因此始終存在將司馬遷看小的危險和疑慮。全書除引言外,共六章,其中四章都分別有三節篇幅,唯有論黃帝一章僅兩節,論武帝一章則占四節,顯然是武帝一章偷走了黃帝的一節。關於《史記》五部分的篇章安排,本書也提供了某種思考,穿插在書中,留待細心的讀者挖掘。
修改書稿的夜深時分,曾經一度翻讀北島的《時間的玫瑰》,用讀詩的意境來消解讀史的疲乏,其中寫到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8)的一句詩:“我淚水涔涔,卻不是為了個人的不幸。”這不也正是司馬遷下筆時幾度哽咽的獨白嗎?所謂“情深而文明”(《禮記·樂記》,《史記·樂書》)的文教理想,怎能不為之神往?
下筆至此,想到幾年前編譯的一本小冊子,其中一句話令我至今難忘――哈欽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曾經說:“一個沒有經驗又未開化的強國,會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脅……未開化的政治權力是危險的,未開化的閒暇是墮落的,也會是危險的”(《大學與博雅教育》,華夏出版社,2015年)。
本成果受北京外國語大學一流學科建設科研項目資助。這本以專著面貌問世的小書,著實是一篇關於《史記》的讀書報告。
寫作本書,原不在研究計劃之列,可謂迷失了正路。
為了記下閱讀文字、探尋幽暗的摸索過程,前後又花費了近一年時間將心海中的瑣思排列組合,落成文字。2017年夏秋之際,輾轉于貴陽花溪與樂山峨眉山之間,初創草稿;2018年驚蟄書稿始成,又經春分、大暑,往返于京津寧路上,我在行將奔赴長春淨月潭之前成稿。從西南到東北,書中所記,當然可以看到時代的印記,也有個人的顛簸,不免有生疏淺陋之處。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說得恐怕不只是應當注意逝者的喪葬之禮,還在於如何對待故事和傳統及作為它們承載者的古人和古書。走進兩千年前《史記》幽暗昏惑的文字森林,有了這本小書作為紀念。但在研討立國與立教這一問題線索上,許多思考並未因此結束,反倒剛剛開始。
董成龍
2018年8月7日
戊戌年立秋定稿于魏公村
洪邁(1123―1202)指出秦、隋二朝被後世詬病,未必因為它們太過不堪,還有一層原因,是它們緊隨其後的漢朝和唐朝都“享國久長”,相較之下,顯得秦、隋這兩個朝代很糟糕(《容齋隨筆·秦隋之惡》)。長短比較,固然有其道理;但更重要的差異或許在於秦、隋兩朝都是紛繁戰局的終結者,完成了立朝的事業,原本承載了歷史寄託,卻迅速重蹈覆轍,留待它們身後的漢、唐兩朝才完成立教的事業。如饒宗頤先生(1917―2018)所示,正統之“正”(立教)比“統”(立朝)更重要,無奈歷代正統論大多著眼於“統”。
漢朝一改黃老之學與漢初祖制,轉向以法立國、以儒文明的政制安排;唐朝一改以往的進身之制,開創科舉,以制度化的方式將士子身心收入斛中。漢、唐在經學和制度兩方面的事業拓展,為此後直至今日的中國文教事業提供了核心要素,雖然經學及其制度已經被打散,但一些義理已經化作日用而不知的生活要素。文教事業這三重面向,不可不察。
1936年,毛澤東經過長征到達陝北,創作了《沁園春·雪》,感歎江山多嬌,回望中古君主,“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雕”。毛澤東評點了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元太祖五人,指出了他們的缺陷,無疑都指向文教問題。馮至先生(1905―1993)曾詩雲:“我們走過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們的生命”(《我們站立在高高的山巔》)。無怪乎,經歷過漫長中世紀和二十世紀數次大革命的我們,面對文教的故事並不陌生。
猶太人面臨著“保國”、“保種”、“保教”的問題;晚清先進士人面臨前所未有的變局,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看來在思考國是上,猶太人問題和中國人問題在這三個層面相遇:國、種和教。“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構詞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是從這三個層面來講的(“人民”作為一種“教”來自於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中所呈現的解放全人類的教義)。中國近代以來遭遇的這三個層面的問題,延綿至今。這本小書就是在這一思想脈衝下完成的。
數年前,我在業師邱立波先生指導下完成一篇小文,當時落筆總結說全文皆是邱師學思之注腳,今日這本小書當然也沒有逃出邱師為我規範的學人心性和問題意識;原來今日的思考早在數年前邱師為我講解班馬異同時就已埋下伏筆。本書還在擴充時,邱師的《禮法與國體:兩漢政治的歷史與經驗》問世(中央編譯出版社,2018年),不禁感慨師徒學緣殊勝。業師許振洲先生行無為之教正是無違我業已確立的學問品性,時至今日方知當時許師是在潛移默化地讓我習練收束之功,可惜而今才理解這番良苦用心;他早年研究法家,可惜我不通法語,無法閱讀他用法語撰寫的《中國法家的統治藝術》(L’Art de la Politique chez les Légistes Chinois,1995),許師晚近研究共和國史的一身工夫,我也未能吸收一二,否則這本小書可能會有另外的境界。
劉小楓先生讓我見識到成德者如何提攜年輕後學,本書大綱正是在小楓先生的點撥下才得以成型,若沒有小楓先生的鼓勵,這本小書也斷不能成。十七年前,小楓先生曾以述為作,撰文《司馬遷是政治哲學家?》(載《二十一世紀》,2001年2月),十七年過去了,不知道司馬遷研究的路線有沒有受此影響而引發轉變;十七年後的今日,這本小書若能呼應那篇文章則是莫大之幸――畢竟,這本小書的許多觀點背後都是小楓先生的“幽靈”(當然,文責自負)。這些年,若沒有幾位賢師相伴,真不知道該如何度過。
在本書大綱以《立教時刻的史家筆法》刊發(載《天府新論》,2018年第2期)前後,劉訓練先生、任鋒先生和唐文明先生都曾提供無私的幫助,為我最終完成這部小書增添了信心。婁林兄和顧枝鷹兄為本書正標題提供了漂亮的拉丁文和希臘文翻譯。從定稿到問世,若沒有彭文曼編輯的辛勤勞動,本書也無法這麼快問世。謹此一併致謝。
本書力圖以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當代觀察貫通“天人之際”和“古今之變”的理解,當然也因此始終存在將司馬遷看小的危險和疑慮。全書除引言外,共六章,其中四章都分別有三節篇幅,唯有論黃帝一章僅兩節,論武帝一章則占四節,顯然是武帝一章偷走了黃帝的一節。關於《史記》五部分的篇章安排,本書也提供了某種思考,穿插在書中,留待細心的讀者挖掘。
修改書稿的夜深時分,曾經一度翻讀北島的《時間的玫瑰》,用讀詩的意境來消解讀史的疲乏,其中寫到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1821―1878)的一句詩:“我淚水涔涔,卻不是為了個人的不幸。”這不也正是司馬遷下筆時幾度哽咽的獨白嗎?所謂“情深而文明”(《禮記·樂記》,《史記·樂書》)的文教理想,怎能不為之神往?
下筆至此,想到幾年前編譯的一本小冊子,其中一句話令我至今難忘――哈欽斯(Robert Hutchins,1899―1977)曾經說:“一個沒有經驗又未開化的強國,會是世界和平的一大威脅……未開化的政治權力是危險的,未開化的閒暇是墮落的,也會是危險的”(《大學與博雅教育》,華夏出版社,2015年)。
本成果受北京外國語大學一流學科建設科研項目資助。這本以專著面貌問世的小書,著實是一篇關於《史記》的讀書報告。
寫作本書,原不在研究計劃之列,可謂迷失了正路。
為了記下閱讀文字、探尋幽暗的摸索過程,前後又花費了近一年時間將心海中的瑣思排列組合,落成文字。2017年夏秋之際,輾轉于貴陽花溪與樂山峨眉山之間,初創草稿;2018年驚蟄書稿始成,又經春分、大暑,往返于京津寧路上,我在行將奔赴長春淨月潭之前成稿。從西南到東北,書中所記,當然可以看到時代的印記,也有個人的顛簸,不免有生疏淺陋之處。
“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說得恐怕不只是應當注意逝者的喪葬之禮,還在於如何對待故事和傳統及作為它們承載者的古人和古書。走進兩千年前《史記》幽暗昏惑的文字森林,有了這本小書作為紀念。但在研討立國與立教這一問題線索上,許多思考並未因此結束,反倒剛剛開始。
董成龍
2018年8月7日
戊戌年立秋定稿于魏公村
目次
目 錄
何謂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劉小楓)
第一章 引言:閱讀司馬遷
第二章 黃帝為首:紀元與土德
一、五帝之首
二、修德振兵
第三章 秦亡漢興:秦制與黃老
一、周秦之際:文敝峻法
二、漢朝祖制:秦德秦制
三、惠呂順守:黃老之術
第四章 黃老之學:人世與刑名
一、老子的人世論
二、黃老的刑名說
三、陰謀:修德與逆德
第五章 文景之治:無為而有為
一、漢家重定
二、改德變法
三、德位之辯
第六章 武帝立教:“且戰且學仙”
一、文學風教
二、儒生酷吏
三、推恩削藩
四、封禪改德
第七章 史遷之志:立教與古今之變
一、欲與仁義
二、時與世
三、復古更化
主要參考文獻
索引
後記
何謂世界歷史的中國時刻(劉小楓)
第一章 引言:閱讀司馬遷
第二章 黃帝為首:紀元與土德
一、五帝之首
二、修德振兵
第三章 秦亡漢興:秦制與黃老
一、周秦之際:文敝峻法
二、漢朝祖制:秦德秦制
三、惠呂順守:黃老之術
第四章 黃老之學:人世與刑名
一、老子的人世論
二、黃老的刑名說
三、陰謀:修德與逆德
第五章 文景之治:無為而有為
一、漢家重定
二、改德變法
三、德位之辯
第六章 武帝立教:“且戰且學仙”
一、文學風教
二、儒生酷吏
三、推恩削藩
四、封禪改德
第七章 史遷之志:立教與古今之變
一、欲與仁義
二、時與世
三、復古更化
主要參考文獻
索引
後記
書摘/試閱
《史記》的記事,雖然從黃帝開始,歷經夏、商、周三代,最後落腳到漢武帝當朝,然而數千年歷史畢於一冊,一定會有詳略分配,不會無的放矢。司馬遷就講,神農氏以前的人世太久遠了,太久遠就無法詳談,必定要簡略些。既然如此,黃帝是取而代之的新君主,黃帝以後的人世是不是就要詳細寫了?他又說,殷朝以前的故事也很久遠,這樣一來,五帝和夏、殷兩朝的事都沒法詳談,就只能從周朝開始多寫點了。司馬遷寫到周厲王(前904―前828)時,“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之所以停下來感慨萬千,就在於周秦之變正要從周厲王和周幽王(?―前771)算起,而周幽王和周厲王之前的往事太久遠了,那麼周幽王、周厲王之後呢?“厲、幽之後,王室缺,侯伯強國興焉,天子微,弗能正”(《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周厲王出逃後,周公姬旦、召公姬奭執掌朝政,即周召共和(《十二諸侯年表》正是從周召共和寫起,收束於孔子);周幽王被犬戎殺害之後,周朝都城東遷,“秦始列為諸侯”(《史記·宋微子世家》)。
最後,鋪墊了那麼久,司馬遷終於坦白,五帝、三王的事都太久遠了,那重點顯然就是秦、漢兩朝了――既然如此,為什麼還非要寫作五帝、三王之事?對於司馬遷而言,占比不多未必就不重要,五帝、三王的鋪墊提供了一種已經一去不復返的政治規範,如果不記,就意味著忘記了這個規範,沒有規範的政治那還了得?“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孟子·告子上》),既要寫五帝、三王,又要寫秦、漢兩朝,所以要有一個貫通其中的主線,那就是兩大古今之變:周秦之變和秦漢之變。
這兩大古今之變,貫穿著立朝與立教兩條線索。其中,黃帝是五帝之首,即立朝事業之首;繼之而起的第二帝顓頊是黃帝之孫,“治氣以教化”,即立教事業之首。 司馬遷關心立朝,則以黃帝為首,關心立教,則能卒章明志(《太史公自序》一開篇就從顓頊談起)。《史記》中秦漢之際尤其是漢朝立朝以來六十餘年的敘事,皆由立朝與立教貫穿,散見於全書各處,“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周朝末年,王道衰微,“禮廢樂壞”,“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朝政與教化分離。縱然如子夏這般孔門高弟還會“出見紛華盛麗而說(悅)”,何況中人以下的普通人?“漸漬於失教,被服于成俗”(《史記·禮書》)。秦朝終結戰國時代,代周而起,以法術治國,但二世而亡,窮其智與力,竟不能捍衛國朝。周朝末年和秦朝末年頻頻有德性討論,其實是在問立朝之後的立教問題,如果不能提供新的教化,國朝如何真正立得起來?“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
孔子述而不作其實是以述為作,司馬遷的《史記》是效法孔夫子的《春秋》。他曾提及,孔子編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成為了歷史作品的典範,此後的《左氏春秋》、《鐸氏微》、《虞氏春秋》和《呂氏春秋》都從《春秋》出發。荀子、孟子、韓非子都是如此,漢朝的張蒼、董仲舒也是從《春秋》中推演大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既然如此,司馬遷還要效法孔子《春秋》,一方面是接續這種致敬的傳統,另一方面也是在指斥推演《春秋》傳統中普遍存在的問題,要別開生面,另立新說――否則何必再添一部作品?
此外,孔子也講:“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既然司馬遷以《尚書·堯典》為原型,依據改制學說,開創了“八書”的體例,“關鍵在於漢家改制”, 那麼,司馬遷的立教之意可見一斑。司馬遷也講到開創國朝基業的“受命帝王”和穩固壯大國朝的“繼體守文之君”(《史記·外戚世家》),前者就是立朝者,後者是在國朝的有機體內綿延不絕的立教者,“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史記·春申君列傳》)。董仲舒也有類似的考慮,他說道“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也是在說“受命帝王”和“繼體守文”這兩種君主。
立朝是建立新政權,立教則是確立新的社會和新的人,論定是非,立教時刻來臨之前的國朝實際處在是非未定或懸而未決的時刻。論定是非,貌似容易,因為做抉擇似乎並不難,但艱難的是要決策者承擔抉擇之後的後果,所以楊朱行至十字路口竟然哭泣(“楊朱泣于逵路”)!秦朝提供了立朝的原型,漢朝提供了立教的原型。若要討論秦、漢以來的中國歷史,以及由此出發而來的當代中國,可能要回到這兩個原型。漢宣帝劉詢(前91―前49)在位期間,王吉提到當時仍然是“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所以他要移風易俗,讓“六合同風,九州共貫”(《漢書·王吉傳》)。 看來立教並非一勞永逸,而是永遠在路上的事業。
最後,鋪墊了那麼久,司馬遷終於坦白,五帝、三王的事都太久遠了,那重點顯然就是秦、漢兩朝了――既然如此,為什麼還非要寫作五帝、三王之事?對於司馬遷而言,占比不多未必就不重要,五帝、三王的鋪墊提供了一種已經一去不復返的政治規範,如果不記,就意味著忘記了這個規範,沒有規範的政治那還了得?“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孟子·告子上》),既要寫五帝、三王,又要寫秦、漢兩朝,所以要有一個貫通其中的主線,那就是兩大古今之變:周秦之變和秦漢之變。
這兩大古今之變,貫穿著立朝與立教兩條線索。其中,黃帝是五帝之首,即立朝事業之首;繼之而起的第二帝顓頊是黃帝之孫,“治氣以教化”,即立教事業之首。 司馬遷關心立朝,則以黃帝為首,關心立教,則能卒章明志(《太史公自序》一開篇就從顓頊談起)。《史記》中秦漢之際尤其是漢朝立朝以來六十餘年的敘事,皆由立朝與立教貫穿,散見於全書各處,“正名實,不可不察也”(《史記·太史公自序》)。
周朝末年,王道衰微,“禮廢樂壞”,“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朝政與教化分離。縱然如子夏這般孔門高弟還會“出見紛華盛麗而說(悅)”,何況中人以下的普通人?“漸漬於失教,被服于成俗”(《史記·禮書》)。秦朝終結戰國時代,代周而起,以法術治國,但二世而亡,窮其智與力,竟不能捍衛國朝。周朝末年和秦朝末年頻頻有德性討論,其實是在問立朝之後的立教問題,如果不能提供新的教化,國朝如何真正立得起來?“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
孔子述而不作其實是以述為作,司馬遷的《史記》是效法孔夫子的《春秋》。他曾提及,孔子編次《春秋》,“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成為了歷史作品的典範,此後的《左氏春秋》、《鐸氏微》、《虞氏春秋》和《呂氏春秋》都從《春秋》出發。荀子、孟子、韓非子都是如此,漢朝的張蒼、董仲舒也是從《春秋》中推演大義(《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既然如此,司馬遷還要效法孔子《春秋》,一方面是接續這種致敬的傳統,另一方面也是在指斥推演《春秋》傳統中普遍存在的問題,要別開生面,另立新說――否則何必再添一部作品?
此外,孔子也講:“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既然司馬遷以《尚書·堯典》為原型,依據改制學說,開創了“八書”的體例,“關鍵在於漢家改制”, 那麼,司馬遷的立教之意可見一斑。司馬遷也講到開創國朝基業的“受命帝王”和穩固壯大國朝的“繼體守文之君”(《史記·外戚世家》),前者就是立朝者,後者是在國朝的有機體內綿延不絕的立教者,“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史記·春申君列傳》)。董仲舒也有類似的考慮,他說道“王者必受命而後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禮樂,一統天下”(《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也是在說“受命帝王”和“繼體守文”這兩種君主。
立朝是建立新政權,立教則是確立新的社會和新的人,論定是非,立教時刻來臨之前的國朝實際處在是非未定或懸而未決的時刻。論定是非,貌似容易,因為做抉擇似乎並不難,但艱難的是要決策者承擔抉擇之後的後果,所以楊朱行至十字路口竟然哭泣(“楊朱泣于逵路”)!秦朝提供了立朝的原型,漢朝提供了立教的原型。若要討論秦、漢以來的中國歷史,以及由此出發而來的當代中國,可能要回到這兩個原型。漢宣帝劉詢(前91―前49)在位期間,王吉提到當時仍然是“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所以他要移風易俗,讓“六合同風,九州共貫”(《漢書·王吉傳》)。 看來立教並非一勞永逸,而是永遠在路上的事業。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大陸出版品因裝訂品質及貨運條件與台灣出版品落差甚大,除封面破損、內頁脫落等較嚴重的狀態,其餘商品將正常出貨。
特別提醒:部分書籍附贈之內容(如音頻mp3或影片dvd等)已無實體光碟提供,需以QR CODE 連結至當地網站註冊“並通過驗證程序”,方可下載使用。
無現貨庫存之簡體書,將向海外調貨:
海外有庫存之書籍,等候約45個工作天;
海外無庫存之書籍,平均作業時間約6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