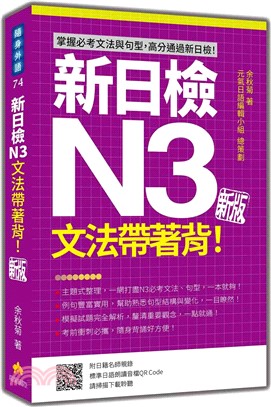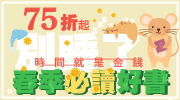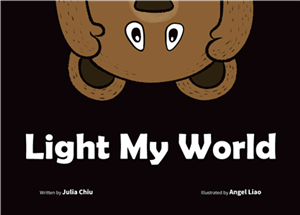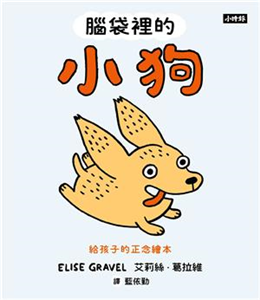博物日本:本草學與江戶日本的自然觀
商品資訊
系列名:Beyond
ISBN13:9786267052365
替代書名:The Knowledge of Nature and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in Early Modern Japan
出版社:衛城
作者:費德里柯‧馬孔
譯者:林潔盈
出版日:2022/06/01
裝訂/頁數:平裝/544頁
規格:21cm*14.8cm*3.2cm (高/寬/厚)
商品簡介
認識近世日本探索未知,建構自然知識的歷程
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只發生在西方?
德川幕府時代,日本也曾嘗試有系統地整理自然知識
江戶時代累積的研究成果,明治維新後融入近代科學,也影響了臺灣
重新認識在亞洲近代化過程中,被遺忘的一頁知識史
★普林斯頓東亞研究專家費德里柯.馬孔顛覆認知、開創視野之作
★深入江戶日本的社會文化,看本草學者如何掌握時勢,盤點自然,開創新知!
★跳脫東西文化大分流的刻板印象,看見從江戶日本到近代科學的連續發展
★科學史、環境史、博物學領域學者共同推薦
在古代日本,未開發的自然被認為是神聖的空間,人類不能輕易跨入。但這樣的自然觀,到了江戶時代卻發生重大轉變。有一群本草學者,開始有系統地研究自然、認識自然。幕府時代的後期,也曾發展出與近代歐洲相近的開發自然、富國思想。明治維新之後,江戶時代累積的本草學研究成果,被吸納進西式的學科分類中,對台灣也曾產生深遠的影響。
過往史家認為,科學革命、啟蒙運動都發生在西方。本書顛覆了這種刻板印象,指出在德川時期(一六○○―一八六八)曾經發生近似的知識革命。
十六世紀末,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從中國傳入日本。日本的學者雖然深受影響,卻也很快發現:來自中國的自然知識在日本無法完全實用。時值戰國時代結束,德川政權穩固,社會經濟開始發展,新知識得到發展的空間。漸漸地,本地學者開始研究日本本草,發展出與中國不同的本草學。
日本第一部原創藥物學百科全書――貝原益軒的《大和本草》,即是在這樣背景下問世。貝原益軒曾表示,他的研究目是提供本國人民具體幫助。到了德川幕府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在位時,更是對日本動植物物種發動了全面性的調查,由本草學者主導,各藩國配合提交「產物帳」。德川吉宗更參考普查所獲得的新知,進行農業改革,並建立國家贊助的藥園。
本書帶領我們進入江戶時代蓬勃發展的本草學,一探其中豐富奇妙的知識史問題:
◎日本為何能發展出與中國截然不同的本草學?――從以中國的《本草綱目》為典範,到注重觀察本地自然、發展本地知識。
◎幕府、藩國怎樣贊助、培養新一代學者?
◎貝原益軒、丹羽正伯等學者如何整理本地自然知識?
◎日本學者為何在十八世紀進行全國的物種普查?
◎幕府將軍,各地如何搜集資訊編纂「產物帳」?
◎本草學問如何影響經濟改革?
◎十九世紀的「薩摩經濟奇蹟」,背後有本草學者運籌帷幄?
◎日本近世自然觀的轉變,與西方近代自然觀有何異同?
◎明治維新之後,本草學與西方科學的關係,是斷裂還是融合?
這是在亞洲近代化過程中,被忽略的一段知識史。馬孔帶著我們,跳脫西方科學發展史的視角,深入日本近代的一場知識革命。除了讓我們更加認識知識生產、典範創造的過程,打開「何謂科學?何謂知識?」的想像,也帶給我們一個重新認識亞洲,認識亞洲近現代化歷程的寬闊視野。
作者簡介
威尼斯大學(Università Ca' Foscari Venezia)東亞語言與文化研究畢業,副修語言哲學。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史博士。博士研究期間曾長期於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進行研究。曾於哈佛大學賴肖爾日本研究所進行博士後研究,後在維吉尼亞大學歷史系擔任助理教授。現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學系副教授,也在歷史系教授日本史。
名人/編輯推薦
★閱讀江戶日本的本草學史,對我們來說並不只是閒情偶寄的異域趣味而已,更重要的是,這也是瞭解傳統知識生產與實踐,以及如何過渡到今日的重要鎖鑰。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張哲嘉
★日本是個盛產博物學家的國度,數位天皇與皇族皆在自然史研究上有頗高的學術造詣。然而,和西方自然史源自於自然神學、欲彰顯神的榮耀之基督教傳統有別,日本自然史傳統係源自於研究山川草木、蟲魚鳥獸的本草學。這本好書以非歐洲中心主義的視角,耙梳大量中、日兩國的關鍵史料,讓我們能夠清楚掌握日本自然史的早期發展脈絡,並且省思如何在保有自身文化傳統的情況下,擁抱現代科學來豐富我們對自然和環境的理解與認識。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助理教授、科普部落客/Gene黃貞祥
★臺灣人飲食日常充滿「藥食同源」,因此「本草學」之於我們,並不是艱澀的字詞。而貫穿本書的正是「本草學」,不論是幕府本草學如何轉變為現代自然史,還是各種地方組織與人物所編織起的各式內涵,從地瓜到鳥獸,將軍到平民都為此著迷。作者將近代日本本草學,放入社會脈動、資本主義、物質社會、日本政治情勢及對外關係變化密切,生動地編織起一張玲瓏的歷史之網。關心東亞歷史與社會、環境史、自然史,抑或是熱愛本草學在亞洲發展流變,都不能錯過本書。
――自然史研究者、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博士/蔡思薇
★馬孔大膽挑戰「唯獨西方發展科學除魅」的過時觀點。日本的本草學學者,就像近代歐洲的科學家一樣,以系統化的方式把自然原先整體的生態系統,改造成可以被分析、操縱、控制的獨立個體。這項引人振奮的研究,將日本獨特的科學發展軌跡,置於商品文化的增長和學者專業化這兩大脈絡之下。
――費正清獎得主、聖母大學歷史系教授/茱莉亞.艾德妮.湯瑪絲(Julia Adeney Thomas)
★對於日本與自然環境之間相處的歷史,本書開啟了一個有趣的視角……本書不僅止於討論日本對自然界中事物的研究,同時也討論自然學者階級的興起與自我認同、相關專業領域的定位、市民大眾熱衷於自然史研究的風潮,以及對自然世界的陳列與鑑賞……這本書無論從近世科學史、自然史,抑或是德川日本文化的角度來看,都是一本必讀佳作。
――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梅隆講座教授(Andrew W. Mellon Chair)/那葭(Carla Nappi)
★書市充斥著太多包含許多偉大思想家的書籍,但卻很少有書可以像本一樣包含著那麼多有價值的思想。這本書是一個既偉大,又博學、細膩的研究;它同時也是一個有關日本近世時期發人深省的工作成果。
――哈佛大學日本史教授/大衛.豪威爾(David L. Howell)
★這是一本既豐富又充滿細節討論的書,它同時也深度討論本草學的方方面面。這本書將會吸引跨學科的眾多讀者,包含日本與東亞史家、科學史家、環境史家等等……它代表著學術新浪潮的一部分,讓我們對東亞科學有更深刻的認識。這本優秀的書也意味著將引發讀者閱讀的興趣,以及作為一本任何東亞科學史課程書單上必讀的書。
――香港城市大學語言與翻譯系教授/孟瀚良(Florin-Stefan Morar)
★本書是英文世界裡第一本關於近世日本時期「自然研究」的專書,企圖在自然的現代性議題上,挑戰傳統的歐洲中心主義觀點。
――《加拿大歷史學報》(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
★義大利的日本史專家費德里柯.馬孔以聰穎的分析與犀利的筆鋒,向西方的讀者首次引進日本近世史時期的自然史研究成果。一六三七年首次在日本出版的《本草綱目》,引發了自然研究的首波革命浪潮,同時也鼓舞了當時的自然學者們去開拓自然史並深化日本科學的發展。這些自然學者是誰?他們如何產生並融入日本社會?他們又做出什麼貢獻?這些問題都巧妙地被羅織並解答在馬孔的敘事當中。
――《自然史檔案》(Archives of Natural History)
★本書對東亞科學史提出了創新的觀點,並以比較的視角重新評估與近代歐洲科學之間的差異。
――《伊西斯》期刊(Isis)
★費德里柯.馬孔所講述的本草學歷史極其豐富,這段故事也幫助我們填補日本近世時期的研究成果。在本草學的科學發展和知識論轉移上,本書同時聚焦於自然知識的演進以及對自然考察的詳細研究上……這是一本有趣又不失嚴謹的著作,本書必將持續成為日本近世時期思想研究的指標讀物。
――《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這本書最主要的貢獻在於,它翔實地考察了在社會和階級脈絡下,德川日本時期如何製造並使用自然知識;而普遍認為日本科學的發展是西化過程的結果,本書對此也提出深刻的反思。本書考察的範圍不僅僅是科學史,還包含環境研究、經濟史、圖鑑的出版史,以及藝術史,這種豐富程度可以最大可能地服務廣泛的讀者群。
――《日本研究學報》(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導讀:赤芍與白芍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張哲嘉
《本草綱目》如今在全世界享有盛名,被譽為中醫藥史上最璀璨的瑰寶。就其書中所收藥物品類之繁多、分類安排之巧思來看,擁有如此崇高的地位似乎是理所當然。然而,事實上《本草綱目》原本在中國國內的遭遇並不順遂。不但將書稿呈獻給朝廷後被冷凍起來,在最初尋求出版的過程也是屢屢碰壁,顯然書商評估市場時並不看好。幸而付梓之後再版了數次,卻因為內容太過龐雜,醫生臨床使用起來並不方便,書中兼容並蓄的內容,反倒較為符合推崇博學多聞的富裕文人需要。只不過李時珍編輯時喜歡任意更動引用原文,在考證學風當道的清代頗受主流學者的訾議,因此在國內的名望難以與《神農本草經》等古代經典相抗衡。到了現代之所以能後來居上,跟它流傳到國外後受到東洋、西洋讀者的重視脫不了關係。閱讀江戶日本的本草學史,對我們來說並不只是閒情偶寄的異域趣味而已,更重要的是,這也是瞭解傳統知識生產與實踐,以及如何過渡到今日的重要鎖鑰。
眾所周知,日本自古就接受中國的官修本草作為國家的藥典,長期以來一直扮演追隨者的角色,似乎引進了先進醫學之後,全國上下就會從此享受康泰的生活,然而現實上並非如此。中國本草書上所記載的藥品,絕大多數在日本必須要依靠進口才能取得。不但價格昂貴,而且買到的舶來品也多難辨真偽。曾經有一次,朝鮮王朝的使節團到京都與當地人筆談,才發現朝鮮國內醫師開處方籤都只要仰賴藥商提供即可,而日本醫師通常都需要自行上山採藥才足以支應所需。因此可以想見,在藥品種類與敘述細節都遠超前代的《本草綱目》一傳入日本,立刻引起廣泛的重視。畢竟辨識藥物跟日本醫師的例行性作業密切相關;而如果無法在國內找到藥草,或者培育堪用的代用品,又會連帶影響到國家的外匯收支,這是攸關民命與荷包的大事。面對同樣的本草,日本人閱讀的心情卻是大不相同。《本草綱目》很快成為日本鑽研本草學的基準,不管是官方還是民間,都對國內的產物調查與培育投注了中國人難相比擬的資源與心力。到了江戶後期,日本的本草學逐漸走出了中國以藥學為核心的窠臼,開展出注重觀察實物的特長。此一表現既體現了傳統學術發展多種可能性的潛能,恰好也與西歐博物學所重視的風格正相接軌,從而更平順地接引到近代轉型為植物學、動物學等新式學科。此為江戶本草學值得我們重視的理由之一。
儘管如此,江戶時代日本人對於中國專家的知識權威還是十分敬畏的。十八世紀末,僻居九州南端的薩摩藩,曾經假借受其控制之琉球王國所具備的朝貢身分,派遣專人攜帶植物種苗渡海,懇請福建的官員、藥房、醫師、船員,乃至於遠至北京同仁堂師傅指點是何品種、有無藥效。最後將所蒐集到的情報編成《質問本草》一書,在鹿兒島出版。從此看來,中國境內不乏能人,只不過我們無從得知這些人物之間平時有無交流,而且,假使沒有日本史料留下記錄,他們的智慧也只能隨草木同朽。雖然清代也有如趙學敏、吳其濬等高手,但除了他們自己的著作本身之外,無從獲悉其知識生產過程與內容,更乏其他史料作為旁證。相對而言,江戶日本的本草專家或愛好者環繞著藩幕體制與私人講學,形成了彼此既串連、又帶有競爭性的多重人際網路。現存還有不少的手稿或出版品,足以讓我們部份重建這些人物的個人活動或相互影響,也可略窺當時作為一位本草學家的學思歷程與挑戰之所在,這一些寶貴的訊息,是中國本草文獻中絕少透露的。此為江戶本草學值得我們重視的理由之二。
自從大航海時代以後,東亞世界與西歐往來更為頻繁,藥學、博物學知識更是彼此都亟欲瞭解、交流的重點之一。跟日本一樣,歐洲人對於滿載大陸深處祕藥訊息的《本草綱目》十分推崇,也想進一步認識日本的物產,與此同時,他們也帶來了採集自全球各處的商品與西洋式的學問,包括林奈式的分類體系。日本人在同時承接中國與西洋兩大知識傳統時,無可避免地面臨了何所適從的爭辯,在磨合的過程中,調和折衷派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發言權,並將《本草綱目》中所用的「綱」、「目」、「屬」、「種」等詞彙作為翻譯西洋知識分類體系的正式學術術語,《本草綱目》的地位得以維持不墜。即使是到了明治維新、西式學科制度確立之後,日本國內仍有振興本草學的呼聲。而成功轉型為新式藥學學者的本草愛好者,仍然將舊有的素養導入新式教育之中。如中國醫藥學院在臺中成立,首先敦聘以開設本草學課程的學者乃是那琦教授,他早年就讀於滿洲醫科大學藥學部,受業於本草學大家岡西為人。他以在課餘全臺走透透調查藥草資源而聞名,在試圖解決海島上藥物資源匱乏的問題而努力之餘,也體現出早年教育所陶冶的江戶本草學家精神。在這個意義上,日本的學風也孳乳了今日臺灣的學術與保健生活,此為江戶本草學值得我們重視的理由之三。
自從我在大學講授傳統醫藥史以來,一直固定加入相當比例的日本史內容。當我開始介紹日本本草時,總是用中藥的赤芍與白芍作為比喻,雖然與中國本草系出同源,卻各有所長。因為臺灣的高等教育缺乏日本醫學史的內容,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始終想盡一份心力。但缺乏適當的中文教材供學生閱讀,常以為憾。本書是在普林斯頓大學之馬孔教授的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而成。當我在二○○八年於哈佛燕京學社訪問之時,我的接待人栗山茂久教授曾特地邀請剛獲得學位的馬孔博士到劍橋演講,並且十分欣喜英文學界終於有一本有關江戶本草史的專論,對於未來學術的推展必有相當助益。如今此書之中文版得以問世,我也體會到栗山教授的心情。尤其希望有更多讀者以本書為契機,開啟對本草學豐富內涵的知識之旅。
序
我在位於東京大學本鄉校區的三条町家民宿度過了二○一三年的夏季。這間民宿在一座名為育德園的花園附近,這座花園建於一六三○年代,當時是前田利常(一五九四―一六五八)在江戶的住宅。前田利常是日本德川時期最富裕的加賀藩藩主(稱為「大名」),位高權重。花園圍繞著一個「心」字形的池塘展開,現在大部分人都將這個心字池稱為「三四郎池」,則是因為夏目漱石小說《三四郎》中主人翁的名字。池塘周圍植被茂盛,讓人不禁有種無序且令人不安的荒野之感。至少,當我沿著池塘周圍狹窄不平的小路散步時,往往會有這種感覺。這裡有各式各樣的鳥類:烏鴉、杜鵑、鶇、啄木鳥、朱鷺、魚狗、日本樹鶯、金背鳩與一群綠色的鸚鵡。有一天晚上,我甚至看到一隻貉(學名Nyctereutesprocyonoides viverrinus的日本亞種),也就是日本人口中的「狸」。日本民間故事常以這種動物為主角,故事中的狸通常具有超自然的力量,是頑皮的搗蛋鬼、偽裝大師,而且常被描繪成擁有巨大睪丸的形象。然而,仔細一看,這座花園看似雜亂無章的繁茂遠非荒野之兆。事實上,許多樹的樹幹上與矮小的草本植物之間,都可以看到標示著植物名稱的塑膠標籤。對於這些豐富的花園植物而言,這些標籤可說是它們的精準編目,並且與花園最初予人的荒野印象形成一種奇特的對比,它們暗示著設計、規劃、人工,以及最重要的,對自然的支配。如果你造訪東京的其他公園,想要為夏季的悶熱尋找幾乎不可得的調劑,你也會有同樣的奇異感受:雖然乍看之下有一種無序的荒野感,不過當你注意到標有樹木與草本植物名稱的標籤時,這種感覺就會消失,而且有 些標籤甚至會寫上拉丁文學名。
自有人類之初,關於自然界的知識就已經存在。對早期智人來說,有關植物營養、療效與毒性的資訊是攸關性命的問題。即使在今天,生物學家也經常運用東南亞、非洲與南美洲狩獵採集者部落的「植物學」知識,對倖存的熱帶雨林裡最偏遠的角落進行探索。然而,像植物學與動物學這類自然科學所產生的知識是截然不同的。它將一個生態系分割成分離的元素,這些元素被隔離、解構、分析、切片、物化為圖像、乾燥或防腐的樣本,用作實驗、操縱、轉化、受版權保護,並經常被大量複製和被用作商業用途。
儘管在過去幾十年間,各種「綠色」思想家與運動都強調人類社會與環境的不可分離性與重疊性,但我們多半還是相信現代的世界觀,認為人類與自然世界完全分離。在人類世的時代,人類普遍否認自身在自然世界的嵌入性。我們認為自己注定要主宰自然。儘管有確鑿的證據顯示出我們對環境造成了災難性的影響,但今日「完全開化的地球散發著災難勝利的光芒。」
科學史家認為這種現代世界的典範起源於文藝復興時期,是社會與知識在漫長複雜的集結進程中的一部分,屬於科學革命的範疇。近世歐洲的自然哲學家愈來愈將物種從其生態系中分離出來,在圖冊與繁殖實驗中將其物化,並把它們當成奢侈食材、藥學、農業、工業與娛樂的資源來進行商品化。根據這樣的經典觀點,隨著歐洲強權在帝國時代的擴張,西方科學被當成其現代化成就的一部分,而這種世界觀也在傳統(意味著「落後」)文化中被全球化了,例如日本與中國都在十九世紀晚期擁抱西方科學。因此,無論是頌揚還是譴責過去兩個世紀科學現代性的革命性影響,世界的「啟蒙」始終是一項無可爭議的西方事業,尤其是歐洲的事業。
本書旨在糾正這種假設。書中試圖論證,遠在現代之前的德川時期(一六○○年至一八六八年),日本已經藉由對自然物進行系統研究的形式,開始了對自然環境的去神話過程。這與歐洲自然史有著驚人的相似性,但卻沒有直接受到歐洲自然史的影響。這個過程是由入侵原始地區的學者進行的,他們調查日本的動植物物種,並將這些動植物歸納成字典與百科全書的獨立條目,或是當作認知、審美或娛樂商品來收藏、分析、交換、展示或消費。這門學科最初被稱為本草學,它是源自中國的研究領域,從屬醫學,專門研究礦物、植物與動物的藥理特性,後來發展成為一個非常兼容並蓄的領域,包含大量的實踐、理論、概念化與目標。我主張,本草學的演變既來自其內部發展,也來自德川社會的深刻轉變,以及那個社會中學者的社會專業軌跡。當明治時期(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一二年)引入西方科學以維持日本的現代化時,本草學的許多實踐、制度與知識並沒有丟失或被放棄,而是經過轉譯、改變,並被納入植物學、動物學與生物學等新學科的語言與形式中。
當位於東京本鄉的前田利常院落被改成公共用地,並交給文部省,用於建造東京醫學校與東京開成學校(後於一八七七年被合併為東京大學)的新硬體設施時,育德園還是一片荒地。它逐漸被縮減成現在的規模,植被的維護則由東京大學植物研究中心與白山的小石川植物園共同輔導。賦予這片荒野樹木與植物一抹馴化感的標籤,很可能就是在那時貼上的。然而,前田家族是德川時期的藩主,家族中也有人是本草學的業餘學者。誰知道他們是否也給心字池周圍的植物貼上了標籤?
目次
赤芍與白芍/張哲嘉 導讀
前言
第一部分 序論
第一章 沒有本質的自然:近世日本自然研究史導論
第二章 《本草綱目》與它所創造的世界
第二部分 名稱的排序:一六〇七年至一七一五年
第三章 轉譯的知識:林羅山與《本草綱目》評注
第四章 寫作自然百科全書
第五章 日本最早的自然百科全書:《大和本草》與《庶物類纂》
第三部分 盤點登錄資源:一七一六年至一七三六年
第六章 德川吉宗與十八世紀日本的自然研究
第七章 盤點自然
第四部分 自然的展示:漫長的十八世紀(一七三〇年代至一八四〇年代)
第八章 自然奇觀:作為消遣的自然史
第九章 文化圈的自然
第十章 展出的自然:平賀源內
第十一章 再現自然:從「真實」到「準確」
第五部分 日本自然的形成:江戶幕府末年
第十二章 幕末本草學:折衷主義的結束?
第十三章 作為累積戰略的自然:佐藤信淵與本草學和經濟學的綜合
後記
致謝
注釋
書摘/試閱
日本本草學從中國模式的分歧(中國清代的本草學與明代本草學專家如李時珍活躍的時期相比,並無太大變化)並不是一夕之間發生的。造成如此變化的原因,不僅有學者的論述、物質上的實踐,以及他們在社會專業身分上的改變,也包含幕府與藩政府以組織物產調查、支持藥草或替代作物種植等方式的參與,再加上新機構的設立,如醫學研究院和幕府、藩政府贊助的植物園等等。
德川幕府建立後的長期政治穩定,導致了深刻的社會變革。尤其是,市場經濟的發展對德川時期的社會秩序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其中最明顯的是統治階層武士菁英的貧困化,以及相應地被削弱實際的權力。經濟的貨幣化、國內與國際商品貿易的增長、愈形倚賴市場來獲得社會再生產的手段,以及農業生產的商業化等,這些都是德川時期日本社會經濟生活的轉變,有利於基於財富而非出身的新型式社會統治的出現。
商人與工匠階層的識字率穩定上升,讓這些人成為文化商品的熱情消費者。這個現象的結果是文化商品市場的多元化,因為這些將時間與資源投資在文化活動中的人,都是來自不同的社會階層。擁有土地的農民(豪農)透過放款,以及將農業剩餘物資投資於紡織、清酒釀造與靛藍染料製造等小規模製造業的方式,變得更加富裕,而出現在這個階級的新興文化消費者們,則讓文化離開了上方與關東地區的主要城市中心,向農村蔓延。
歷史學家曾經認為這是一個長時間的社會停滯流動期,但是到了十八世紀下半葉,德川時期發生了徹頭徹尾的社會變革,打破了既有的社會關係階級制度。一方面,武士菁英自十七世紀以來一直在經歷一個「開化過程」(civilizing process),這個過程往往融入了和平時期社交的新規則。這些規則包括池上英子(Eiko Ikegami)所謂的內化「馴服」(taming),提倡自我克制,而不是中世紀的暴力與武力理想。道德被轉化成一種文雅、禮儀和藝術專長的語言。在這種新的價值體系下,知識博學成為地位的重要標誌。在其他藩主眼中,品味與學識的差異賦予他們地位,增加了他們的政治特權。由於稻米價格持續下跌,有學問的中下階級武士陷入貧困,因而經常藉由在知識與文化領域的就業來改善生活。雖然他們作為學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贊助,但他們在藩政府的就業也有助於改變藩主與家臣之間的關係。文化與知識事務的有償諮詢取代了戰爭中的兵役,這與初代德川幕府將軍開始的武士階層非軍事化與官僚化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在正式社會階梯的底層,富有的平民將他們新獲得的經濟繁榮投資於教育以及藝術和智識訓練,從而提高他們的社會存在。如此一來,他們既遵循也推動了現在普遍存在的理學道德論述的轉變。理學最初讚揚這種道德修身的活動,同時也譴責對金錢的追求。平民積極參與文化圈與私塾學習,為他們提供了與武士菁英成員的間接接觸,以及更罕見的直接接觸。不斷擴大的文化交流網絡,儘管只是偶爾將武士和平民聚集在一起,但由於有共同的想法、興趣與實踐,而且往往由同樣的學者教師來監督不同群體的活動,因而形成了智識的交往。在十八世紀下半葉,來自各個社會階層的成員,從武士到富裕的農民與商人,對文化活動的參與有了爆炸性的增長,產生了德川後期日本生氣勃勃的大眾文化。
本草學只是十八世紀蓬勃發展的諸多藝術與知識活動之一。和其他事業不同的是,本草學因為對國家福利的實際效用,而且與理學「格物致知」的思想相關聯,因而具有道德效益,也因此受到德川政府的青睞。參與一個致力於自然研究的文化圈,在社會與智識上都是有益的。就像十九世紀英格蘭富裕的中產階級,或是中國文人的私人追求一樣,武士菁英與富裕平民之所以受到這類活動吸引,是因為它們有趣、令人振奮,而且得到社會認可。充斥於許多本草學文本的藝術插圖,也符合德川時期菁英和大眾文化對視覺表現的審美品味。此外,藉由公開展示從世界偏遠地區進口的防腐標本與活體動植物,本草學的公共展示與娛樂方面在熱鬧的都會脈絡下蓬勃發展,讓它的從業者能夠創造並利用民眾對自然界日益增長的興趣。
即使本草學這門學科保持了它源自藥學的名稱,但它也正在經歷著深刻的轉變,成為一種被認定為「自然史」的東西。主要的變化在於,愈來愈多學者專注於動植物本身的研究、觀察與描述。儘管大多數人繼續從實際效用與用途的角度來構想他們的研究,他們的知識實踐卻愈來愈著重於製作對動植物物種之形態、生態與行為的準確描述。
在這個過程中,本草學於十八世紀下半葉逐漸變成一個相對更自主的專業領域,在國家資助的學校與研究機構中被教授,而且擁有自己的典籍。它的從業者不再是像林羅山和貝原益軒等人,只是附帶參加其活動的博學家而已,而是可以被視為博物學家,並且能在這種專業知識的基礎上占據愈來愈多職業區位的專業學者,例如田村藍水與小野蘭山。許多人繼續在藩主麾下服務,其他人則在幕府的醫學研究院裡找到工作。少數發展成私人教育家,有自己的學校,如松岡玄達(即松岡恕庵,一六六八―一七四六)。還有一些人透過講座、文化圈與會所來尋求公眾支持,或以園丁、插畫家或外來物種經銷商等身分受到雇用。
在這種更廣泛的意義上,對公眾的依賴意味著本草學專家發現自己必須互相競爭,以滿足新消費者的口味,這是前所未有的現象。他們的處境早已不同於一個半世紀前的林羅山,更不必像林羅山那樣,得在佛教僧侶與傳統宮廷機構之外努力爭取社會對學者的認可。現在,儒者是被社會接受的專業人士。一般民眾也發生了變化。到了十八世紀,日本的大型城鎮數量遠超過許多其他城市化的社會,幕府首都江戶(今東京)的人口達到一百萬。江戶是充滿活力的新城市景觀文化的典範,有劇場、娛樂場所、馬戲團、展覽和街頭表演,同時還充斥著大量出版通俗小說、諷刺小說與旅遊景點指南等繁榮的出版業。隨著富裕地主農民人口的出現,江戶、大阪、名古屋和京都等城市的流行文化,開始共存於日本鄉間城鎮與村莊中一種充滿活力但獨特的文化網絡。本草學實踐在這兩個圈子裡都存在,儘管它的活動在個別脈絡下多少有些不同。
稻生若水的弟子松岡玄達經常在京都公開講課,前去聽課的人很多,光是學生的學費就足以讓他維持生計。松岡玄達的弟子小野蘭山自詡有來自日本各地的一千多名學生在他於京都開設的私塾學習。在鄉間,圈子比城市小,活動也不那麼張揚,但是興趣與實踐方式是類似的。事實上,他們延請的學者教師往往是同一位,教師旅行到各地教授各個團體,並在這樣的過程中,透過思想與文化實踐將不同社會地位的成員連結起來――在當時的社會結構中,不同階級是無法聯繫在一起的。田村藍水與他的弟子平賀源內舉辦了第一次全國性的動植物展覽,將私人收藏的數千件珍稀標本公開向江戶民眾展示,受到民眾前所未有的熱情歡迎,將來自城市中心與鄉村中不同社會地位的業餘愛好者與學者聚集起來。受益於這股本草學風潮的不只有學者。有一小群畫家和插畫家,為藩主、文化圈、出版商和博物學家服務,用極其精緻的動植物圖畫來豐富目錄、文章與論文集的內容。
在德川時期的後半段,自然史享受到一種流行時尚所能得到的所有好處。對動植物專業知識的需求增加,導致專業本草學學者的人數激增。然而,專家人數的增長卻被幕府對知識生產做出更嚴密的控制所抵消,特別是在一七九○年所謂的異學禁令之後。隨著對學術作品的需求增加,學者聲望也隨之提高,但是如果沒有藩特權階級的贊助與支持,謀生仍然非常困難,平賀源內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在德川統治的最後一個世紀,人們對自然史的狂熱達到頂峰,但這並不足以保證其從業者的經濟穩定。就某種意義而言,本草學這門學科的進展可以說比本草學專家的情況要好。一方面,自然史成了一個在所有社會階層都有足夠多追隨者的領域,與十七世紀的本草學者相形之下,這個時期的學者對他們的知識生產方法有著更大程度的控制。另一方面,專家本身的社會同質性在很大程度上維持不變,直到德川時期結束。也就是說,大多數博物學家仍然是來自低階或中階武士階層的醫生,而且往往受僱於幕府與藩政府的行政機構。雖然本草學日益普及的 情況並沒有改變其知識生產者的社會構成,但這確實意味著他們的自然史研究不再只是為了順應統治階級的需求。十九世紀的歐洲也是如此,即使在生物這門學科已經被認定為一個學術領域以後,博物學家往往也不是一個能夠自立謀生的職業。綽號「達爾文的鬥牛犬」的演化生物學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曾抱怨道,「要靠科學過活是不可能的。我一直不願相信,但事實就是如此。」理察.歐文(Richard Owen)可能是他那個時代最著名的比較解剖學家,他的年收入為三百英鎊,「比許多銀行職員的工資還低。」十九世紀的歐洲與德川後期的日本,自然史儘管大受歡迎,但仍然是一種紳士活動,從業者幾乎完全是來自於能夠負擔得起這類活動花費的階級。
【更多有趣內容,請參閱本書】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