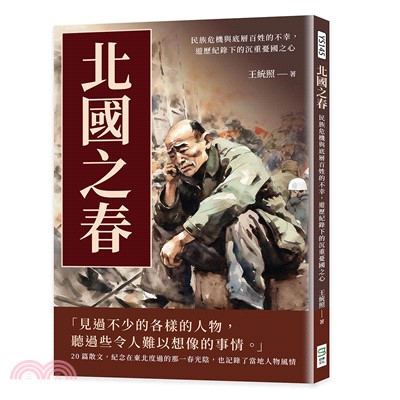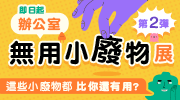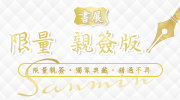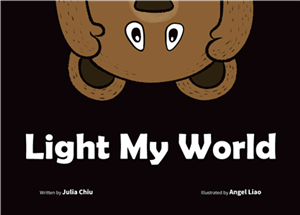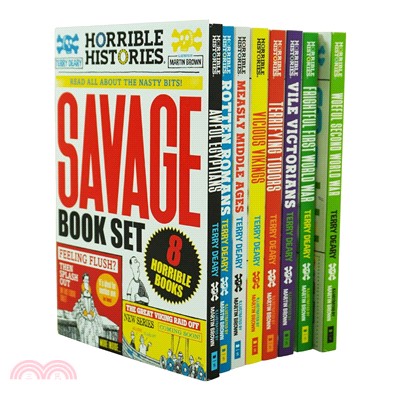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目次
書摘/試閱
商品簡介
「見過不少的各樣的人物,聽過些令人難以想像的事情。」
20篇散文,紀念在東北度過的那一春光陰,也記錄了當地人物風情
▎被檢察的「小學教員」
那位視學與軍人紅了臉收拾起散亂的東西。白衣的茶房也過來幫著用繩子將被褥捆起;十分熟練的手法如那日本紳士的熟練的眼光一樣。
即時同屋子中的中國人都將身子轉過去,沒有一個說話的,都在等待著,等待著!
▎小賣所中的氛圍
這是平常平常不過的事,在這「劫外桃源」的地方是中國人的相當娛樂場所。香菸中的半仙態度,性的糟踐的生活,什麼都不管的心思,這是這地方暫時的主人的教條。好好的自加學習,這桃源中準可允許有你的一個位置,這是我們從一瞬間得來的反省。
▎紅日旗的車中
「國」這個字的造成,第一我是十分佩服我們先哲,──不,我們的先民的聰明。四圍的風雨不透,這才像是一個東西;只是與「囹圄」、「固困」一個意義。他們早知道了這一層玄祕的道理了!不知怎的活潑而像是能打翻一切的現代人,高唱著「全民呀」,「世界呀」,「人類呀」,這種種鑄金的名詞,卻沒有一些兒燕子與蝴蝶的自由,只想著將好好的青年捉到「囹圄」裡,「固」與「困」成了每個講界限疆域的所有物,幾乎每個人都相同的感到這「囹圄」的苦惱。
▎生活的對照
多賣書夾的未必是什麼好地方,但只能講日本話,聽金票行市,我在這分水嶺似的大橋上(四洮南滿鐵道中間有穹式大橋,鐵軌在下面,即以此處分中日管理界),凝望著茫茫的煙塵,黃衣紅肩章的兵士的來往,不知是怎樣聯想的,便覺得這一個小問題(書夾子買不到)像頗為重大似的。中國市街不過是買不到書夾子而已,而鄰人的炮臺卻雄立在大道的旁邊。
▎人道
晚飯後,又得如廁,所有的報紙都用淨了,只有保存著關於某醫院強姦華婦的新聞的那張。為了需要與保護自己起見,究竟帶去鋪在長方孔的上面。同時我悠然地想了,「人道」只可以這樣在足下,在垃圾中踐踏與撕亂?
▎植樹
我看它們沒枝沒葉的孤獨樣兒,令人想到植樹的意義。這在鄉村中,或人家的田邊陌上,不是有根有枝的小樹嗎?但它們現今卻在大大小小青年們的足下,或手中,呻吟著「生之叫喊」的低聲,無疑,這悲慘的風是給它們送葬歌了。
▎贛第德的世界
麻木過度了,還要樂觀,還相信「庸人自有庸福」,若何大的土地,若何多的出產,若何了不得的許多人才,於是我們只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了!我們這兒有英雄,有古董,有線裝書,有小白旗,到處又召集的幾百萬壯丁。還有我們的「墳」,我們的古來的同化的魔力,還有我們的能創新的青年,於是大家可以開口嘻笑了!憂慮與憤激不是將力投在虛空中麼!於是我們有光明的希望,有快樂的可能,有享受與爭奪,更有夢入天國的妄想。
▎白城子中的投影
過去的文化的遺留,能以動人的美感,使人有懷往的幽情,知道古代的生活的片段,不過它的使人眷戀的心情,與捨不掉打不碎的為難狀況,也足以阻礙新機的發展。比如最古的國家,與最老的民族,愈是有其久遠的文化史的,現在怎麼樣還不是被物質的暴力壓榨出他們的保守的血汗?累得抬不起頭,掙扎不起疲弱的手臂,徒發出呻吟的懷舊的怨聲。有何補益?
▎松花江上
兩條名字異常美麗,且富有詩意的江水,偏在東北。我們想起鴨綠就會聯想到日人的耀武,想起松花就有俄人的暗影。風景的幽清,自來是戰血洗滌成的,人類原不容易有真正的愛美的思想,那只是超乎是非利害無關心的一時的興趣的沖發,及至將他們的獸性盡情發散的時候,哪裡還管什麼風景,文化。
本書特色:本書為王統照於東北任教並遊歷時撰寫的報告文學。當時他目睹東北人民在日本侵略下的痛苦生活,深切感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東北將危亡,遂將所見所聞寫成此報告文學集《北國之春》。
20篇散文,紀念在東北度過的那一春光陰,也記錄了當地人物風情
▎被檢察的「小學教員」
那位視學與軍人紅了臉收拾起散亂的東西。白衣的茶房也過來幫著用繩子將被褥捆起;十分熟練的手法如那日本紳士的熟練的眼光一樣。
即時同屋子中的中國人都將身子轉過去,沒有一個說話的,都在等待著,等待著!
▎小賣所中的氛圍
這是平常平常不過的事,在這「劫外桃源」的地方是中國人的相當娛樂場所。香菸中的半仙態度,性的糟踐的生活,什麼都不管的心思,這是這地方暫時的主人的教條。好好的自加學習,這桃源中準可允許有你的一個位置,這是我們從一瞬間得來的反省。
▎紅日旗的車中
「國」這個字的造成,第一我是十分佩服我們先哲,──不,我們的先民的聰明。四圍的風雨不透,這才像是一個東西;只是與「囹圄」、「固困」一個意義。他們早知道了這一層玄祕的道理了!不知怎的活潑而像是能打翻一切的現代人,高唱著「全民呀」,「世界呀」,「人類呀」,這種種鑄金的名詞,卻沒有一些兒燕子與蝴蝶的自由,只想著將好好的青年捉到「囹圄」裡,「固」與「困」成了每個講界限疆域的所有物,幾乎每個人都相同的感到這「囹圄」的苦惱。
▎生活的對照
多賣書夾的未必是什麼好地方,但只能講日本話,聽金票行市,我在這分水嶺似的大橋上(四洮南滿鐵道中間有穹式大橋,鐵軌在下面,即以此處分中日管理界),凝望著茫茫的煙塵,黃衣紅肩章的兵士的來往,不知是怎樣聯想的,便覺得這一個小問題(書夾子買不到)像頗為重大似的。中國市街不過是買不到書夾子而已,而鄰人的炮臺卻雄立在大道的旁邊。
▎人道
晚飯後,又得如廁,所有的報紙都用淨了,只有保存著關於某醫院強姦華婦的新聞的那張。為了需要與保護自己起見,究竟帶去鋪在長方孔的上面。同時我悠然地想了,「人道」只可以這樣在足下,在垃圾中踐踏與撕亂?
▎植樹
我看它們沒枝沒葉的孤獨樣兒,令人想到植樹的意義。這在鄉村中,或人家的田邊陌上,不是有根有枝的小樹嗎?但它們現今卻在大大小小青年們的足下,或手中,呻吟著「生之叫喊」的低聲,無疑,這悲慘的風是給它們送葬歌了。
▎贛第德的世界
麻木過度了,還要樂觀,還相信「庸人自有庸福」,若何大的土地,若何多的出產,若何了不得的許多人才,於是我們只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了!我們這兒有英雄,有古董,有線裝書,有小白旗,到處又召集的幾百萬壯丁。還有我們的「墳」,我們的古來的同化的魔力,還有我們的能創新的青年,於是大家可以開口嘻笑了!憂慮與憤激不是將力投在虛空中麼!於是我們有光明的希望,有快樂的可能,有享受與爭奪,更有夢入天國的妄想。
▎白城子中的投影
過去的文化的遺留,能以動人的美感,使人有懷往的幽情,知道古代的生活的片段,不過它的使人眷戀的心情,與捨不掉打不碎的為難狀況,也足以阻礙新機的發展。比如最古的國家,與最老的民族,愈是有其久遠的文化史的,現在怎麼樣還不是被物質的暴力壓榨出他們的保守的血汗?累得抬不起頭,掙扎不起疲弱的手臂,徒發出呻吟的懷舊的怨聲。有何補益?
▎松花江上
兩條名字異常美麗,且富有詩意的江水,偏在東北。我們想起鴨綠就會聯想到日人的耀武,想起松花就有俄人的暗影。風景的幽清,自來是戰血洗滌成的,人類原不容易有真正的愛美的思想,那只是超乎是非利害無關心的一時的興趣的沖發,及至將他們的獸性盡情發散的時候,哪裡還管什麼風景,文化。
本書特色:本書為王統照於東北任教並遊歷時撰寫的報告文學。當時他目睹東北人民在日本侵略下的痛苦生活,深切感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東北將危亡,遂將所見所聞寫成此報告文學集《北國之春》。
作者簡介
王統照(西元1897~1957年),字劍三,筆名息廬、容廬。現代作家、《文學》月刊主編。1918年辦《曙光》,1921年與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等人發起成立文學研究會。著有短篇小說集《春雨之夜》、《霜痕》、《夜行集》,以及長篇小說《黃昏》、《山雨》等。
目次
被檢察的「小學教員」
小賣所中的氛圍
紅日旗的車中
生活的對照
老人
人道
植樹
單調
風的詛咒
贛第德的世界
詩話
沙城
洮兒河畔
白城子中的投影
夜話
牧馬場
神祕的葛根廟
松花江上
墳園中的殘照
中央大街之夜
小賣所中的氛圍
紅日旗的車中
生活的對照
老人
人道
植樹
單調
風的詛咒
贛第德的世界
詩話
沙城
洮兒河畔
白城子中的投影
夜話
牧馬場
神祕的葛根廟
松花江上
墳園中的殘照
中央大街之夜
書摘/試閱
小賣所中的氛圍
托張君的福,他來回經過這「名所」的次數多,午後四時我們便由旅館中的趙先生導引著走入一個異樣的世界。
趙先生在這裡作事已有十年以上的資格。青布皮衣,紅胖的面孔,腮頰上的肉都似應分往下垂落,兩道粗黑的眉,說話時總有「×他媽」的口語。脫略,直爽的性格,與痛快的言詞,的確是一個登州屬的「老鄉」。一見張君便像十分相知似的,問這個那個,又要求介紹我們這兩位新熟識的客人。──老先生與我──及至張君一提倡走,我就猜到他們的目的地;好在有趙先生的「老大連」,我也覺得一定有別緻的地方,可以展露在我們的面前。
穿過幹路麻布通後,向南走進了一個小巷,右轉,中國式的三層樓入門。拾級而上,二層的門口,第一個特別現象是木櫃檯上有幾十枝各式各種料子作成的鴉片煙槍,很整齊地擺著,不同的色澤在目前閃耀。
我們驟然墮入迷香洞中了,──也可叫做迷雲洞中。
大廳中幾張煙榻一時弄不清楚,煙霧迷濛中只看見有許多穿長袍短裝的人影在煙中擠出擠進。幸而還好,我們五個人居然占了兩個小房間;這一定是雅座了。一間真小,不過縱橫五尺的屋子,門窗明明是油膩得如用過的抹布,卻偏是白色的。木炕上兩個歪枕,兩分褥子,是古式的氣派,這才相稱。於是精工雕刻的明燈與古色鮮豔的槍枝便即刻放在當中。
趙先生的手技高明,小黑條在他那粗壯的手指上捻轉的鋼簽之下,這麼一轉,一挑,向火尖一偏,一抬,那原小的發泡的煙類便已成熟。扣在紫泥的煙斗上,恰相當。於是交換著吸,聽各人的口調不同,有一氣嚥下去的,煙棗在火頭上不會偏缺;有的將竹管中的煙氣一口吞下,吃完後才從鼻孔中如哼將軍的法氣一般地呼出。軍人與我太少訓練了,勉強吸過兩口,總是早早吐了好些,本這用不到從竹管中用力吸,滿屋子中的香氣,那異樣的香,異樣的刺激的味道,一點不漏地向各個人的呼吸器管中投入。沉沉的微醉的感覺似是麻木了神經,一切全是模糊的世界,在這瀰漫的青煙氛圍中,躺在窄小的木炕上便能忘了自我。一杯清茶不過是潤潤微乾的喉嚨,並不能將疲軟的精神振起。
我躺在木炕上正在品嚐這煙之國的氣味,是微辛的甜,是含有澀味的嗆,是含有重星炭氣的醉人的低氣壓;不像雲也不像霧。多少躺在芙蓉花的幻光邊的中國人,當然聽不到門外勁吹的遼東半島的特有的風,當然更聽不到滿街上的「下馱」在拖拖地響。這裡只有來回走在人叢中喊叫賣賤價果品與瓜子的小販呼聲,只有尖淒的北方樂器──胡琴的喧音,還有更難聽的是十二三歲小女孩子的皮簧聲調。
一會,進來了一個紅短衣褲的剪髮女孩,一會又進來了一個青背心胖臉的女孩。她們在門窗前立了幾分鐘後,一個到間壁去,我們都沒的說。趙先生這時將槍枝向炕上一丟,忙忙地到外邊去。回來,拿著一個胡琴,即時他拉起西皮慢板的調子。手指的純熟如轉弄煙燈一樣。半個身子斜欹在炕邊,左手在拂弦的指頭是那樣運用自如,用力的按,往下一抹,雙指微捺弦的一根,同時他的右手中的弓弦高,低,快,慢都有自然的節奏相應。於是尖利而調諧的音便從手指送出。手法真特別,夥計,小販都時時掀開門窗的一邊來看。一段過後,連與他熟悉的張君也大拍掌,不住道地:「好,好!唉!好指音!再來,再來。」
「不容易,難得,不曾聽過這麼好的胡琴。……」老先生也嘖嘖地稱讚。
我呢,這時真覺得多才的趙先生也是個令人驚奇的人物。他是那樣的質樸,爽快,一天又忙著算帳,開條子,還得永恆的堆著笑臉向客人們說話;但在此中他卻是一位特殊的音樂家。
趙先生將厚垂的眼皮閉著,天真的微笑,若在他的十指中創造他的宇宙。忘記了客人也似忘記了這在哪裡,用勁地快樂地拉著一種一種的調子。
磞的一聲,胡琴上的粗弦斷了。他趕急又跑出去,回來將弦纏好,還沒開始拉,便道,「來哇,誰唱誰唱?」
張君向立在間壁門口的軍人說:「有趙先生拉,你來幾嗓子。」
「不行,我喉嚨痛。」
老先生還在炕上燒煙,十分高興道地:「還怕什麼,到這裡來原不是講規矩的。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你還怕羞?幹嘛!」
「還是老先生,痛快,痛快!」趙還沒拉動胡琴,卻向張君問:「可是這老先生以前的貴幹還沒領教。」
「唉,這也是位老風流名士呀!兩年前他還在作科長呢。你別看他有鬍子,一點也不拘板。……」
「是,是!倒是痛快。唱呀!」他將弦調好,向軍人等待著。
軍人終是搖頭不唱。
「大榮,叫大──榮──來啊!」趙先生這時才實行他的政策。一會那方才立在門口的紅衣女孩進來,將一個綢面紙裡油垢的戲目折遞給我。我略一展視,看到許多老生小旦的舊戲名字,便遞與在我身後邊坐著的張君。
「說說,點什麼戲?」
張君看幾分鐘道:「好多,會唱這些,隨便隨便,趙先生,你熟,隨便挑一出不完了。」張君態度頗見興奮。
還是那個女孩子自己說了,「坐宮吧?」
在幾個人一同說「好」字的口音之下,慢板的胡琴與她的十字句的戲詞同時將音波顫動。
她的過度的高音使她不得不將雙肩屢屢聳動,每到一句末後的拖長而激亢的音時,我看她實在吃力。大張開嘴,從小小的喉中發出這樣要夠上弦音的調來。頭上的披髮一動一動的,她那雙美麗的大眼直向灰黑色的牆上注射出急切的光亮。聽到,「我好比淺水──龍,困臥……在沙──灘!」一句,我替她著急;同時心中也有些不自知的感動。覺得我們在這奇異的世界中是在買沙灘中的沒有一點水的小動物的把戲看!……門窗外來回瞧熱鬧的人不少,就是賣果品的小販也時而停留住聽這不甚調諧卻是引人來聽的戲詞。
一曲既終,她背了兩手立在門側休息。大家自然是喝彩了。張君問過她才十四歲,「好啊!以後一定有出息,聽聽調門真不錯!」
本來可以讓她休息了,但趙先生還在調弦,而這清瘦的孩子眼巴巴地仍然希望再唱。這是為什麼呢?我有點明白,但我的淒感卻咽在心頭,沒有話可說。接著又叫了她的妹妹來,一樣是個大眼睛面目聰明的孩子,比她還低一頭。於是汾河灣的生旦戲便由這兩個孩子當作久不會面的夫妻連唱起來。
神采十足的趙先生合了雙目在玩弄他熟練的手法,兩個粗亢與低細的口音不斷地唱,說白,時間不少,約有一刻鐘方才止住。這時我換了十個角子,便趕緊交與那大孩子。張君還爭著要給她,末後終算是我會了鈔。在聽眾的讚許聲中,可憐的女孩歡躍而去。但她一起一落的肩頭遠如影片一般在我的目前。當她用皺皮的疲手來接這十個角子時。我真覺得由我的手上將「侮辱」交給她了!
這是平常平常不過的事,在這「劫外桃源」的地方是中國人的相當娛樂場所。香菸中的半仙態度,性的糟踐的生活,什麼都不管的心思,這是這地方暫時的主人的教條。好好的自加學習,這桃源中準可允許有你的一個位置,這是我們從一瞬間得來的反省。
有點頭暈了,這奇異的世界不能久留,便一同走出在樓門口等待著後行的趙先生,還不來,那位青年人望著門口的銅牌子道:「這樓上還有飯館哩,看這小賣所。」
張君輕藐道地:「方才吸的玩意還不是?這一市中多少掛了這樣牌子的地方,如你願意進去,保吸不錯。真是鄉下人,還有賣飯的在上面哩!」
軍人方有點恍然。
及至我們走到大街上,也沒看見趙先生的影子,都說他又不知在那雲霧中辦什麼交涉了,便決議去逛浪速町的夜市,不再等他。
當我們由日人的百貨商店走回旅館到自己的房間中時,趙先生卻跳了進來道:「好找,好找,我出來連你們的後影也沒瞧見。……」
「我們以為你與那小姑娘打交涉去了。」張君答他。
「可不是,她娘也在那邊的煙炕上吸菸。那孩子因為給了她一塊錢,歡喜的沒法子,拖住我再去吸兩口,我去說幾句話後便出來,遲了。」
原來他與她們都很熟悉。
「應分是一齣戲多少錢?」
「四角小洋。」
「誰養著她們?」我在問。
「一個女老闆弄上幾個小孩子,教得會唱了,便做這宗生意。大一點也可送到窯子中去。」趙先生上樓氣喘,只說到這裡。
一會下面有人喊他,他又笑著招呼我們幾句,匆匆地跑下樓去。
托張君的福,他來回經過這「名所」的次數多,午後四時我們便由旅館中的趙先生導引著走入一個異樣的世界。
趙先生在這裡作事已有十年以上的資格。青布皮衣,紅胖的面孔,腮頰上的肉都似應分往下垂落,兩道粗黑的眉,說話時總有「×他媽」的口語。脫略,直爽的性格,與痛快的言詞,的確是一個登州屬的「老鄉」。一見張君便像十分相知似的,問這個那個,又要求介紹我們這兩位新熟識的客人。──老先生與我──及至張君一提倡走,我就猜到他們的目的地;好在有趙先生的「老大連」,我也覺得一定有別緻的地方,可以展露在我們的面前。
穿過幹路麻布通後,向南走進了一個小巷,右轉,中國式的三層樓入門。拾級而上,二層的門口,第一個特別現象是木櫃檯上有幾十枝各式各種料子作成的鴉片煙槍,很整齊地擺著,不同的色澤在目前閃耀。
我們驟然墮入迷香洞中了,──也可叫做迷雲洞中。
大廳中幾張煙榻一時弄不清楚,煙霧迷濛中只看見有許多穿長袍短裝的人影在煙中擠出擠進。幸而還好,我們五個人居然占了兩個小房間;這一定是雅座了。一間真小,不過縱橫五尺的屋子,門窗明明是油膩得如用過的抹布,卻偏是白色的。木炕上兩個歪枕,兩分褥子,是古式的氣派,這才相稱。於是精工雕刻的明燈與古色鮮豔的槍枝便即刻放在當中。
趙先生的手技高明,小黑條在他那粗壯的手指上捻轉的鋼簽之下,這麼一轉,一挑,向火尖一偏,一抬,那原小的發泡的煙類便已成熟。扣在紫泥的煙斗上,恰相當。於是交換著吸,聽各人的口調不同,有一氣嚥下去的,煙棗在火頭上不會偏缺;有的將竹管中的煙氣一口吞下,吃完後才從鼻孔中如哼將軍的法氣一般地呼出。軍人與我太少訓練了,勉強吸過兩口,總是早早吐了好些,本這用不到從竹管中用力吸,滿屋子中的香氣,那異樣的香,異樣的刺激的味道,一點不漏地向各個人的呼吸器管中投入。沉沉的微醉的感覺似是麻木了神經,一切全是模糊的世界,在這瀰漫的青煙氛圍中,躺在窄小的木炕上便能忘了自我。一杯清茶不過是潤潤微乾的喉嚨,並不能將疲軟的精神振起。
我躺在木炕上正在品嚐這煙之國的氣味,是微辛的甜,是含有澀味的嗆,是含有重星炭氣的醉人的低氣壓;不像雲也不像霧。多少躺在芙蓉花的幻光邊的中國人,當然聽不到門外勁吹的遼東半島的特有的風,當然更聽不到滿街上的「下馱」在拖拖地響。這裡只有來回走在人叢中喊叫賣賤價果品與瓜子的小販呼聲,只有尖淒的北方樂器──胡琴的喧音,還有更難聽的是十二三歲小女孩子的皮簧聲調。
一會,進來了一個紅短衣褲的剪髮女孩,一會又進來了一個青背心胖臉的女孩。她們在門窗前立了幾分鐘後,一個到間壁去,我們都沒的說。趙先生這時將槍枝向炕上一丟,忙忙地到外邊去。回來,拿著一個胡琴,即時他拉起西皮慢板的調子。手指的純熟如轉弄煙燈一樣。半個身子斜欹在炕邊,左手在拂弦的指頭是那樣運用自如,用力的按,往下一抹,雙指微捺弦的一根,同時他的右手中的弓弦高,低,快,慢都有自然的節奏相應。於是尖利而調諧的音便從手指送出。手法真特別,夥計,小販都時時掀開門窗的一邊來看。一段過後,連與他熟悉的張君也大拍掌,不住道地:「好,好!唉!好指音!再來,再來。」
「不容易,難得,不曾聽過這麼好的胡琴。……」老先生也嘖嘖地稱讚。
我呢,這時真覺得多才的趙先生也是個令人驚奇的人物。他是那樣的質樸,爽快,一天又忙著算帳,開條子,還得永恆的堆著笑臉向客人們說話;但在此中他卻是一位特殊的音樂家。
趙先生將厚垂的眼皮閉著,天真的微笑,若在他的十指中創造他的宇宙。忘記了客人也似忘記了這在哪裡,用勁地快樂地拉著一種一種的調子。
磞的一聲,胡琴上的粗弦斷了。他趕急又跑出去,回來將弦纏好,還沒開始拉,便道,「來哇,誰唱誰唱?」
張君向立在間壁門口的軍人說:「有趙先生拉,你來幾嗓子。」
「不行,我喉嚨痛。」
老先生還在炕上燒煙,十分高興道地:「還怕什麼,到這裡來原不是講規矩的。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你還怕羞?幹嘛!」
「還是老先生,痛快,痛快!」趙還沒拉動胡琴,卻向張君問:「可是這老先生以前的貴幹還沒領教。」
「唉,這也是位老風流名士呀!兩年前他還在作科長呢。你別看他有鬍子,一點也不拘板。……」
「是,是!倒是痛快。唱呀!」他將弦調好,向軍人等待著。
軍人終是搖頭不唱。
「大榮,叫大──榮──來啊!」趙先生這時才實行他的政策。一會那方才立在門口的紅衣女孩進來,將一個綢面紙裡油垢的戲目折遞給我。我略一展視,看到許多老生小旦的舊戲名字,便遞與在我身後邊坐著的張君。
「說說,點什麼戲?」
張君看幾分鐘道:「好多,會唱這些,隨便隨便,趙先生,你熟,隨便挑一出不完了。」張君態度頗見興奮。
還是那個女孩子自己說了,「坐宮吧?」
在幾個人一同說「好」字的口音之下,慢板的胡琴與她的十字句的戲詞同時將音波顫動。
她的過度的高音使她不得不將雙肩屢屢聳動,每到一句末後的拖長而激亢的音時,我看她實在吃力。大張開嘴,從小小的喉中發出這樣要夠上弦音的調來。頭上的披髮一動一動的,她那雙美麗的大眼直向灰黑色的牆上注射出急切的光亮。聽到,「我好比淺水──龍,困臥……在沙──灘!」一句,我替她著急;同時心中也有些不自知的感動。覺得我們在這奇異的世界中是在買沙灘中的沒有一點水的小動物的把戲看!……門窗外來回瞧熱鬧的人不少,就是賣果品的小販也時而停留住聽這不甚調諧卻是引人來聽的戲詞。
一曲既終,她背了兩手立在門側休息。大家自然是喝彩了。張君問過她才十四歲,「好啊!以後一定有出息,聽聽調門真不錯!」
本來可以讓她休息了,但趙先生還在調弦,而這清瘦的孩子眼巴巴地仍然希望再唱。這是為什麼呢?我有點明白,但我的淒感卻咽在心頭,沒有話可說。接著又叫了她的妹妹來,一樣是個大眼睛面目聰明的孩子,比她還低一頭。於是汾河灣的生旦戲便由這兩個孩子當作久不會面的夫妻連唱起來。
神采十足的趙先生合了雙目在玩弄他熟練的手法,兩個粗亢與低細的口音不斷地唱,說白,時間不少,約有一刻鐘方才止住。這時我換了十個角子,便趕緊交與那大孩子。張君還爭著要給她,末後終算是我會了鈔。在聽眾的讚許聲中,可憐的女孩歡躍而去。但她一起一落的肩頭遠如影片一般在我的目前。當她用皺皮的疲手來接這十個角子時。我真覺得由我的手上將「侮辱」交給她了!
這是平常平常不過的事,在這「劫外桃源」的地方是中國人的相當娛樂場所。香菸中的半仙態度,性的糟踐的生活,什麼都不管的心思,這是這地方暫時的主人的教條。好好的自加學習,這桃源中準可允許有你的一個位置,這是我們從一瞬間得來的反省。
有點頭暈了,這奇異的世界不能久留,便一同走出在樓門口等待著後行的趙先生,還不來,那位青年人望著門口的銅牌子道:「這樓上還有飯館哩,看這小賣所。」
張君輕藐道地:「方才吸的玩意還不是?這一市中多少掛了這樣牌子的地方,如你願意進去,保吸不錯。真是鄉下人,還有賣飯的在上面哩!」
軍人方有點恍然。
及至我們走到大街上,也沒看見趙先生的影子,都說他又不知在那雲霧中辦什麼交涉了,便決議去逛浪速町的夜市,不再等他。
當我們由日人的百貨商店走回旅館到自己的房間中時,趙先生卻跳了進來道:「好找,好找,我出來連你們的後影也沒瞧見。……」
「我們以為你與那小姑娘打交涉去了。」張君答他。
「可不是,她娘也在那邊的煙炕上吸菸。那孩子因為給了她一塊錢,歡喜的沒法子,拖住我再去吸兩口,我去說幾句話後便出來,遲了。」
原來他與她們都很熟悉。
「應分是一齣戲多少錢?」
「四角小洋。」
「誰養著她們?」我在問。
「一個女老闆弄上幾個小孩子,教得會唱了,便做這宗生意。大一點也可送到窯子中去。」趙先生上樓氣喘,只說到這裡。
一會下面有人喊他,他又笑著招呼我們幾句,匆匆地跑下樓去。
主題書展
更多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