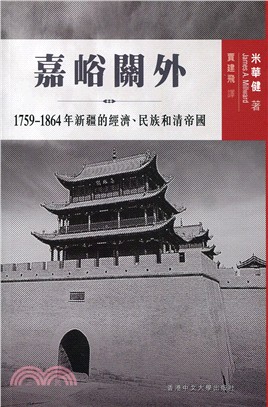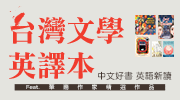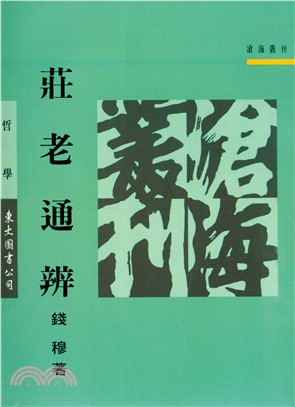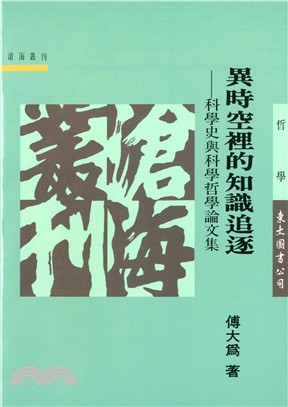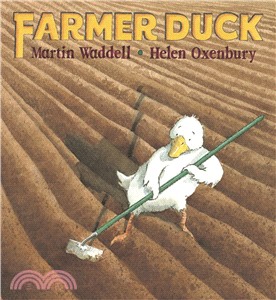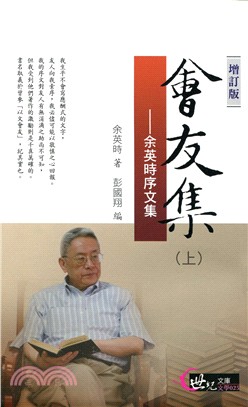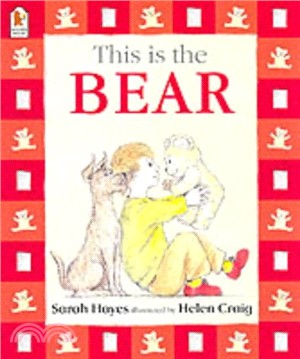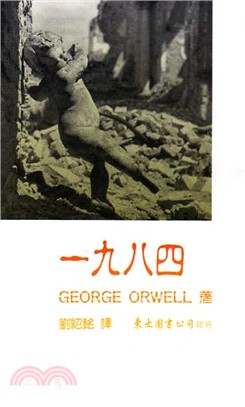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
商品資訊
系列名:邊疆研究系列
ISBN13:9789882370043
出版社: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作者:米華健 (James A. Millward)
出版日:2017/06/16
裝訂/頁數:平裝/448頁
適性閱讀分級:846【高於十二年級】
商品簡介
作者簡介
賈建飛,歷史學博士。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現為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中央歐亞系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近現代新疆歷史,尤其是清代新疆移民史及法制史。已出版《清乾嘉道時期新疆的內地移民社會》及《清代西北史地學研究》等。
名人/編輯推薦
─馬大正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
這是一部關於新疆的傑出研究,它通過族群和經濟的視角,紮實地呈現了清帝國如何在這片新的疆土上建立並維持統治。從沒有哪個王朝能夠像清朝這樣將新疆併入其疆域並進行深度有效的經略,米華健的書則對清朝這一曠古未有的功績作了最全面的展示。我衷心將此書推薦給所有對中國邊疆史感興趣的讀者。
─濮德培(Peter C. Perdue)教授,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
此書在問世之際就允稱美國漢學界對清代新疆歷史長途越度關津的鑿空之作,迄今的流播更彰顯出鐵板銅琵高唱大江東去的健銳。作為這本書寫作的見證者、中譯本的審校者以及相關領域研究的同道,我非常樂見中文版的問世。
─張世明教授,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序
中文版序
賈建飛將拙著《嘉峪關外》譯為中文,對此我甚感欣慰。我也非常榮幸拙著中文版經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後,能夠讓更多的讀者一睹其顏。為了翻譯此書,建飛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尤其是為了術語和引文的精確,他查閱了大量的原始中文文獻和檔案,使得譯文在很多方面都較英文原文有了改進。因此,本書的中文和英文版本是可以相得益彰的。
《嘉峪關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1990年在北京進行的,本書最早的版本是我於1993年提交給斯坦福大學的博士論文。隨後,我對博士論文進行了修正,並由斯坦福大學出版社於1998年出版了英文版本。所以,本書的首次出版距今已將近二十年,距我最早開始寫作此書的時間就更久遠了。那時,在英文世界中幾乎沒有有關清代新疆的著述,在清史研究領域,新疆的地位一直非常邊緣。普林斯頓大學的歷史學家韓書瑞(Susan Naquin)曾經在一次會議上公開向我提出挑戰:「告訴我們清朝征服新疆對蘇州的百姓有何影響?」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劍橋中國史)中傅禮初(Joseph Fletcher)的章節是當時僅有的有關新疆研究的新近作品;這些作品利用了傅禮初當時可以獲得的一些零散的多語種文獻,具有很深的洞察力,在很多方面也可以視為是這個偉大的學者的巔峰之作。但是,由於傅禮初並未有機會接觸到清廷內部的檔案,因此有關清代新疆的很多問題依然無法解答。在英語世界中,我應該是第一個利用北京的清代檔案文獻對新疆進行研究的人,我的結論都是基於這些文獻以及當時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友好和開放。
當然,自那時起,已經出版了一些有關清代新疆的英文著述(漢語的著述自然更多),如今沒有人會再懷疑這個地區在我們對清朝以及清朝作為一個帝國進行運轉的理解中的重要性。金浩東(Ho-dong Kim)的Holy War in China: The Muslim Rebellio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 1864-1877(中國的聖戰)是利用伊斯蘭、中文和其他語言的文獻,對阿古柏伯克政權進行的一部研究。事實上,在我寫作《嘉峪關外》一書的時候,金浩東的Holy War in China已經完成,只不過出版的較晚。吳勞麗(Laura Newby)的The Empire and the Khanat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Qing Relations with Khoqand c. 1760–1860(清帝國與浩罕汗國)利用滿文和漢文檔案,為我們講述了清朝與浩罕汗國的關係史。濮德培(Peter Perdue)的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中國西進)則從比較史的、泛歐亞的角度,論述了康熙、雍正和乾隆時期與準噶爾戰爭中的軍事和政治歷史。近年來,賴恩.薩姆(Rian Thum)的The Sacred Routes of Uyghur History(維吾爾歷史的神聖路線)精辟地闡述了在維吾爾語言tazkirahs中所體現出的歷史傳統,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在漢語和滿語文獻中不曾有過的新疆的歷史景象。另外,金光明(Kwangmin Kim)的Saintly Brokers: Uyghur Muslims, Trade, and the Making of Qing Central Asia, 1696–1814(聖潔的中間人)對於拙著主要聚焦於漢、回商人的問題進行了糾正。金光明揭示了維吾爾精英在與明清的商業關係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強調了貿易對清帝國的形成的重要性。
我很高興這些著作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近代早期新疆的認知,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為這些作者能夠比我使用更多的滿文和維吾爾語的文獻。但是,我也很高興《嘉峪關外》的主要結論在二十年後還依然成立。
第一,商業貿易和商人對於清朝向中亞的擴張和將新疆整合入清王朝非常關鍵。從這個角度來說,很明顯「絲綢之路」一直都沒有終結。相反,遠程的交流已經延伸到了新的歷史時期,並使得中亞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聯繫在了一起。斯科特.列維(Scott Levy)與馬修.羅曼涅羅(Matthew Romaniello)有關中亞和俄羅斯帝國的研究也從帕米爾的另一端對此進行了論證。人們可以認為在今天的中國和中亞、南亞以及西南亞之間擴張的商業和外交聯繫,包括「一帶一路」的提議,都是近代早期受到清朝激發下的全球化進程的延續。
第二,清帝國在新疆的統治十分成功。在整整一個世紀中,這個地區的人口得到了增長,經濟獲得了發展,大體上也保持了和平的局面。儘管在Makhdumzada和卓的派系之間存在本地化的教派衝突,但是並沒有發生反抗清朝的「聖戰運動」(jihad),在伊斯蘭教和北京之間也沒有內在的矛盾。十九世紀初期發生在喀什噶爾附近的變亂從來都沒有威脅到清朝在整個新疆的統治,整個地區一直保持了相當的穩定。由於清朝和伊斯蘭教雙方的靈活性,二者之間在思想和政治制度方面的摩擦也得到了調節,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清朝並沒有要求當地的穆斯林蓄留髮辮。這是清朝統治者經過慎重考慮後的決定,不對具有象徵意義的宗教、服飾和身體外觀等事務進行干預。(清朝政策中的這種文化多元與中國政府在廿一世紀初期禁止維吾爾人蓄留鬍鬚、佩戴面紗或是限制齋月封齋的行為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十九世紀後期清朝喪失了對新疆的控制,這是內地發生的太平天國運動和其他叛亂的結果。這些叛亂使得清政府對新疆的白銀供應遭到中斷,導致了新疆地方官員的貪腐、剝削和暴政。在這種不穩定的氛圍下,陝甘回民叛亂擴展到了新疆,阿古柏伯克也從中亞侵入新疆。但是,在反抗清朝在新疆統治的叛亂中,宗教自身從未成為其中的起因。
第三,清朝在新疆的一個世紀的成功統治,證明瞭它在這個遼闊帝國中,針對民族多樣性所實施政策的明智。清朝統治者並不主張社會的同化,他們的統治理念不僅承認帝國的五個主要文化群體(滿、漢、蒙、藏和「回」)所代表的多元文化差異性,而且還在思想體系和政治上,通過標誌性的象徵和行政制度,主動接受和強調這種差異性。這與歐洲的海外帝國極為不同,也與今天一些人錯誤地認為漢化(sinicization)政策才是歷史的標準截然相反。事實上,乾隆時期對這種非同化理念的多重表述表明清朝的──或許我們可以稱之為──「集權化的多元主義」(centralized pluralism)並不只是統治的權宜之計:相反,正是這種典型的清朝認同的特徵,方才使得清朝能夠獲取這塊文化與民族多樣性的遼闊疆土並維持對其之統治,如今這一領土已經變成了現代的中國。後來,1980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紀由一些中國以外的學者提出了所謂的「新清史」,這在中國也產生了很多的爭論。事實上,在包括《嘉峪關外》在內的那些著作中所持有的很多觀點,已被如今的英語學術圈所接受,當然其中的一些觀點本身也再次得到修正──這些觀點也理應得到修正。無論如何,多數有關清史的英文著作,還有一些漢語作品,都已經或多或少反映出了我們對清代的民族性和帝國的重新構建。我依然記得當我們於1990年代在中國發掘更多有關清代新疆的歷史時,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的老師們和我一起分享從檔案中所浮現出的新的、更為積極的清代形象時的激動的情形。遺憾的是,也有一些人視這種對清史進行重新思考的所謂「新清史」是對中國懷有惡意。和很多歷史觀點發生的變化一樣,今天為人們所知的「新清史」有關族群性和帝國的觀點,都是根據新的文獻和新的關注點而作的重新思考。這種思考並非是一個孤立的行為,而是包括中國史學家、檔案工作者和外國史學家在內的共同努力的結果。事實上,《嘉峪關外》一書的中文簡體譯本最初就是在中國官方資助的國家清史纂修工程的支持下出版的,只是由於和本書自身並不相干的原因,一直都沒有公開發行。
歷史講述的不僅是過去,也是今天。對清帝國的地理、族群和心理的疆界進行新的思索,將其視為一種靈活的文明、多樣的群體和一個現代的國家,對於加深我們對中國的理解大有裨益。新疆、西藏、蒙古、台灣和香港都在通過不同的形式將其與現代的中國民族國家之間的特殊的、有時候又顯尷尬的地位歸因於清帝國的遺產,這些都是偶然的嗎?對清朝歷史的坦誠的、無偏見的、周到的和創造性的考察,如何可以讓中國與那些地方和民族之間的關係變得更為和諧呢?
米華健
2016年1月於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
目次
地圖、圖與表 xi
中文版序 xiii
英文版序 xix
致謝 xxiii
導言 1
邊界與中國近代史 5
走向以清朝為中心的清史 14
清帝國主義 17
從清朝到中國 19
第一章 界標 27
地理分佈 28
歷史上的地形 32
盛清新疆 40
嘉峪關、清朝的擴張和「中國」 44
文人的反對,帝國的回應 46
在國內證明帝國的合法性 49
第二章 為新疆籌措資金 57
哈薩克貿易 58
哈薩克與「朝貢制度」 61
開發邊疆 63
地方財政資源 66
商人借貸和清軍的物資供應 70
新疆的白銀生命線 72
元寶流向印度王公了嗎? 75
兩種金屬,三種貨幣 78
普爾錢-白銀匯率與棉布 87
貨幣問題和改革 89
第三章 西徼之地的官方貿易和商稅 103
新疆的軍事部署 104
茶葉與新疆官方貿易的開端 107
新疆官鋪的形成 110
新疆與內地的官方商業行為 118
南疆的官鋪 120
清王朝與「絲綢之路」 126
發掘新疆的私人商業財富 129
三成的偏激改革計畫 133
那彥成的茶稅計畫 135
國家的財政基金 138
第四章 「雲集」:內地商人向新疆的滲透 149
前往西域的年輕漢人:開關政策 150
新的基礎設施和管理制度 154
路票制度 156
其他的管理措施 157
烏什起義與新疆的隔離政策 160
新疆城市中的內地特徵 162
「滿城」還是「漢城」?正名 188
第五章 商人與貿易物品 205
回子商人 206
朝貢貿易 208
北京的回子 211
新疆的內地商人 213
內地回民商人 222
新疆的茶葉和大黃貿易 228
玉石 233
鴉片 246
第六章 清朝的民族政策與內地商民 259
清朝對新疆居民的印象 260
普天之下的五族:高宗的帝國想像 262
對辮子的一種新曲解 268
異族通婚、異族性行為和強姦 271
內地人在新疆的放債行為 273
內地商人影響不斷增加 276
喀什噶爾的「伊薩克陰謀」 278
喀什噶爾大屠殺 282
葉爾羌與和闐守衛戰 290
清朝民族政策的轉變 291
內地商民和其家人在南疆的團聚 292
結論 趨於歸化的清帝國 311
咸豐時期的財政危機 314
經世致用的思想家和清代新疆 321
清帝國主義的問題 325
附錄 乾隆廷的一個維吾爾穆斯林:香妃的多重意義 337
參考文獻 377
索引 405
書摘/試閱
導言
1805年7月初,被流放的祁韻士正在穿越乾燥且人煙稀少的河西走廊,向著北疆方向前進;去年,他的仕途遭遇到了嚴重挫折。身為京城鑄幣機構寶泉局的監督,祁韻士只負責查閱冊藉,憑賬冊交接,並不盤點鑄幣庫的實際銅庫存。但國家在對銅的供應進行例行審查時,發現了其前任所遺留下的巨大虧空。祁韻士成為代罪羔羊,被流放到了伊犁。
祁韻士對此並不感到特別意外。在乾隆帝駕崩,其寵信的貪官污吏和珅也被處死的那個動蕩年代中,官僚機構中極易樹敵。雖然祁韻士並沒有公開曝光那些掌管糧運系統的官員的違法行為,事態卻未因此而得以改善。這些貪官污吏們的行為越發地變本加厲。
對於前面的旅途,祁韻士並不陌生。在任職寶泉局前,他曾以翰林院編修協助編纂《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傳》,這工作使他已經涉獵於清王朝的內陸亞洲邊疆的歷史和地理。*他的流放日記反映了一個十八世紀的學者客觀的、經驗主義的方法:「西行三十里至火燒溝,土色多赤,然實無溝。」再一天,「西行四十里至赤斤湖,非湖也。」不過,暫不論祁韻士的背景,當他坐著高輪馬車顛簸在充滿沙礫的驛路上時,內地的最後一個城市已經在他身後七十里了。*黃昏時分,矗立於黃土地上的雄偉的嘉峪關防禦工程的暮影越來越近,他的心情也由於即將踏上的征程對他的深刻影響而變得沉重起來。
祁韻士非常清楚嘉峪關被賦予的官方功能:儘管嘉峪關完全位於甘肅省境內,但卻是通往清王朝最西邊的領土新疆的門戶。他的隨從需要在這裏出示路票(人們不能隨意出入這個石頭築就的關門)。祁韻士對此並不關心,而是憶起了一些描寫雲霧繚繞的山崖以及保衛西域邊疆和飽受風沙侵襲的要塞的文字篇章。他或許會想起李白的著名詩句:
明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幾萬里,吹度玉門關。
漢下白登道,胡窺青海灣。由來徵戰地,不見有人還。
這樣的描寫讓他產生了很多想像。當然,祁韻士發現真正的嘉峪關與他的想像截然不同。他在遊記中寫道,周圍的山很遙遠,夜晚「不見崒嵂巍峨之勢」,要塞「亦僅地居高阜,未為險峻」。他還意識到,從內地到嘉峪關外的這段路程將是一個重要的時刻,一旦通過嘉峪關,他就將踏上西域的土地:
關門既出,夐不見人,壯志離情,一時交集。瞻視山形地勢,頓覺改觀。
我們無法瞭解祁韻士當時的真正感悟,儘管他在如下真實的觀察記載中有所暗示:「然古人所稱玉門、陽關,尚在此關之西數百里,為今敦煌縣境,則嘉峪猶未足為遠也。」1
未足為遠──正如祁韻士所言,距離在縮小。嘉峪關並不是那些動情的唐詩中所描述的進入蠻荒之地的險要關口。那些險要關口位於更西的地方。顯然,想像與現實之間的不一致在困擾著祁韻士,而他並不知道該如何對此進行闡釋。事實上,在祁韻士的時代,玉門關和陽關僅僅只是存留於記憶之中,廢墟早已為沙漠掩蓋,他知道他是無須再從玉門關和陽關通過了。然而,實際上他已經越過了這個關口,在這種矛盾的心理產生之時,他就已經進入了西域。
邊疆的概念近來被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視為一種強有力的暗喻和闡釋的工具。根據邊界的劃分,分歧得到明確的表達和談判,決定了該囊括還是排斥,文明的種類也得以劃分。邊界不僅確實區分了兩個實體,它們還限定了這種實體的範圍:沒有野蠻人就沒有文明;沒有無信仰者就沒有真正的宗教;沒有東方就沒有西方;沒有他人就沒有自我。然而,邊界並非固定不變的。邊界更像由各種不同的物質或不同概念的地帶之間相互聯結和滲透而形成的多孔的表面結構。邊界不是靜止的,隨著時間的流逝它們的位置、特徵以及意義都會得到改變。2
在十八和十九世紀,嘉峪關就是一座具有所有這些意義的邊界,兼有自然與象徵雙重層面上的意義。它是一所擁有防禦性長城牆的城堡和門戶,是一處軍事檢查站,一個明確將中國內地十八行省(清代資料中所謂的「內地」)與「關外」版圖相分隔的邊界。(內地與關外這對術語至今仍在使用,關既指嘉峪關,也指山海關,後者位於明長城的另一端。)祁韻士認為,對於朝廷和那些受過教育的大清子民而言,嘉峪關是連接過去和現在的一個點。玉門關和陽關是漢代設在西北的堅固防禦體系的門戶。在那些描寫居住在人跡罕至的邊陲,奉守職責的士兵、受罰的流放者以及嫁給蠻夷頭人的公主們的邊疆文學作品中,它們都是明確的界標。這種流派的詩篇通過對迥然相異的自然環境的描述,強調了他們所看到的將中國內地與長城以外土地割裂開的道德與文化上的隔閡。唐詩或是小說《西遊記》中為人熟知的,以及在漢唐時期的西域地名中所含的祈願中體現出來的這些共鳴,也賦予了後來的嘉峪關。如同漢唐時期的陽關和玉門關,嘉峪關後來也是內地與關外的界標。在明永樂帝統治(1403–1424)後的文化與戰略收縮時期,這個靠近西北長城終點的邊疆要塞在中國人眼中更容易被視為文明與草昧之間的界線。
然而到了大清,嘉峪關在許多方面都已成為名不副實的遺存。它沒有真正的戰略意義。它的另一邊既不存在威脅,也不是排斥非中國人的「關外」;事實上,當時也禁止稱呼新疆的居民為「夷」(外國人,非國民)。3數十年來,往來於新疆的內地漢人*與西部的穆斯林的數量日漸增加,內地人在新疆的聚居區也越發興旺。嘉峪關既不是任何氣候帶的分界線,也不具有自然的疆界特徵:長城和嘉峪關將整個甘肅一分為二,兩邊看起來並無二致。祁韻士是一個拘泥於字面意思的人,他很快就將注意到,理想化的文學想像中對邊疆門戶地形的生動描述與他所看到的嘉峪關存在很大的差異。嘉峪關的建立在地理上將清帝國簡單地分成了兩個部分,然而,若仔細對其加以分析,其目的卻根本並非如此簡單。
邊界與中國近代史
直到最近,都很少有西方的清史學家或中華民國史學家將他們的研究範圍越過嘉峪關,更少有人研究十九世紀六〇年代前嘉峪關外的歷史。4他們忽視了這些事實:與準噶爾的戰役使清朝最終征服了新疆,但康雍乾時期的國庫為此吃緊;清朝創建的兩個主要的機構理藩院和軍機處,都深陷於處理和維護對新疆地區統治的繁雜事務之中;清朝在十九世紀幾次決定重新征服新疆的部分地區或整個新疆地區,儘管多數近代學者認為(當時的許多清朝大臣們也贊同)當時在中國內地的沿海地區有更急迫的問題需要集中財力去解決;毛澤東及其他早期的領導人重申北京早就控制了新疆(新疆自古就是中國的一部分)。為甚麼二十世紀很少有歷史學家肯花精力去研究這個地區及其被征服後所產生的問題呢?為甚麼認為清帝國對內陸亞洲的擴張不重要呢?當人們認為在美國史學中「西部史」或是「邊疆史」佔據著突出的地位時,幾乎完全被忽略的十八世紀中國向西部和北部的擴張就更值得關注。
在西方的近代「中國」歷史編撰中對清代新疆和內陸亞洲的忽略不是偶然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一些在此領域中最具影響力的歷史學家們對近代中國史進行劃界和分期的結果。
需要為此負責的學者之一無過於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當然這很具有諷刺意味,因為拉鐵摩爾是遊牧民族的偉大朋友,他曾穿越滿洲、蒙古和新疆進行遊歷,並留有很多有關這些地區的居民及其與中國關係的遊記和歷史作品。他著名和最具可讀性的著作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中國的內陸亞洲邊疆)闡述了中國人的世界,構建了一個鮮有學者見逾其右的理解內陸亞洲和中國的框架,其獨特的分析以及強調長城的邊界意義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在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中,拉鐵摩爾不是按時間序列來審視中國與內陸亞洲的關係,而是從古代史和邊疆地理中去尋找「基本規律」。因此他的多數歷史分析關注的是從秦朝統一前到公元220年漢朝滅亡期間的中國與遊牧國家的相互影響。拉鐵摩爾在書中還用大量篇幅闡述了內陸亞洲與中國之間的地理、經濟和生態的差異。基於此,拉鐵摩爾得出了一系列的結論:長城是用來劃分中國歷史的「地理領域」;邊界沿線的邊緣地帶形成了一個兼有草原遊牧特性與中國內地特性的社會,遊牧民族在此積蓄力量,並最終前來征服中國;中國與遊牧民族的歷史具有相互影響和彼此關聯的特徵。他把這些現象稱為歷史規律:
因此,從漢初到十九世紀中期約兩千年期間,內陸亞洲和中國相互融合的歷史可按照兩種循環模式來描述:草原部落的分散與統一的循環模式和中國王朝的整合與崩潰的循環模式。這兩種模式截然不同,但隨著歷史推移彼此又相互影響。
書中拉鐵摩爾的時代劃分(至十九世紀中期)很有意義。在其旅途中,除了驚嘆於二十世紀二、三〇年代外國在中國的存在和帝國主義對中國邊疆的入侵外,還驚嘆於近代工業制度在內陸亞洲的影響,尤其是鐵路。他斷言「歐美工業社會秩序對整個亞洲的滲透,是一次新的全面整合,它正在終結長期以來的勢力消長的循環模式。」
拉鐵摩爾認為正是十九世紀中期西方國家在中國的出現,才終結了他所支持認同的內陸亞洲的遊牧部落和中國王朝之間沿長城邊界地區相互影響的歷史模式。因此,他在描述有關清早、中期介入內陸亞洲的內容時草草了之,直接討論清代蒙古、新疆與西藏的內容不超過二十頁;對回民起義前清朝在新疆的統治的描述還不足兩段。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給讀者留下的印象是長城作為邊疆是不容置疑的,長城發揮了長期隔斷歷史上的敵對社會的作用,這些社會以氣候和地形規律所決定的永恆不變的方式相互影響。只有現代性(鐵路、槍炮、西方和日本帝國主義)才能打破那種古老的模式,真正將中國和內陸亞洲整合起來。這種觀點忽略了清早、中期內陸亞洲發生的重大變化,也忽略了包括中國和內陸亞洲在內的清(不是中國)帝國時期的長城邊疆的意義發生的變化。6
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基礎性貢獻同樣也使研究興趣從清代內陸亞洲轉移到了別的方面。費正清詳細闡述了一個相互關聯的思想體系,它形成了二十世紀的對中國以及英語國家的認識。這些觀點包括:傳統與近代二者在中國的應用;西方衝擊─中國回應模式;通過接近中國文化而產生的自發性的中國化的觀念;將「朝貢制度」和「中國的世界秩序」作為中國人與非中國人相互關係的模式。這些觀點在近幾年又受到了廣泛的反思,我在此不再重復這些評論。7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這些觀點關鍵在於導致了一些觀念的形成,致使清朝在中國內地以外地區的活動受到忽略,並掩蓋了清帝國秩序中的那些與中國史中以中國為中心的描述不相符的方面。
這些觀念並非費正清本人的想法。但是,它們已經不同程度地深深扎根於十九世紀早期的有關中國西部的著作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對民族主義的中華帝國史的闡釋之中。費正清具有影響力的教科書和研究教學也使我們在對近代中國的理解過程中發展並確立了這些思想。而且,費正清用這些觀念來解釋通常認為的十九世紀中國沒有能夠對西方適時地做出反應的原因。
也許這些觀念最根本的是傾向於認為「傳統中國」在本質上是不變的,或至少是無法進行有意義的「變革」。柯文(Paul A. Cohen)認為這種想法源於十九世紀工業化中西方沾沾自喜的觀點。然而柯文沒有注意到這種觀點卻很好地支持了費正清的一個主要闡釋模式:朝貢制度。費正清的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中有一章列舉了朝貢制度,並在他與鄧嗣禹共同承擔的三項有關清代行政研究中的一項中進行了更為詳細的論述。後來,費正清又在The Chinese World Order(中國的世界秩序)導言“A Preliminary Framework”(一種初步的構想)中進一步完善了這一論述。這些版本的重點略有不同,但這一理論的基本觀點一樣。8
簡而言之,費正清認為,中國通過與非中國人的「野蠻人」,尤其是北方遊牧部落數個世紀的相互交往獲得了發展。到了明代,一種銘刻了中國對其周邊民族的文化優越感和中國帝王對普天之下具有統治權神話的「外交方式」得以制度化。外交儀式和外交辭令都表達出這樣一種思想,即中國幅員遼闊,人們在從中國內地外遷時,只需在習俗上作不同程度的適應性調節即可。理學家(Neo-confucian)思想中所極為強調的國內政治和社會關係中的等級觀念被擴展到了處於相似等級制度中的外國領土上,而這種等級制度的頂端是中國的天子。「在中國人看來......帝國政府的對外關係僅僅是中國內地行政的向外延伸。」9前來中國尋求發展貿易或其他關係的外來者被中國政府看作是(或者至少記載於宮廷檔案)「皈依教化」。在中國人看來,這些外來者呈獻的朝貢物品和叩頭這樣的禮儀行為,說明了他們對天子無上美德以及對自己在等級上的附屬地位的承認。即使這些外來者只是謀求商業利益,也要遵循這樣的儀式;貿易因此也被視為朝貢。只要把中國的安撫賠款看作「賞賜」,外交和貿易夥伴的軍事利益也可被滿足。正如費正清所說,在中國經典中體現出的這種理想化的帝國宇宙哲學或多或少決定了中國與外來民族的關係模式,而這一模式一直持續到了十九世紀末;朝貢儀式還是這一時期外交關係的先決條件—當然,這可能是由於在與西方往來之前,中國在本質上的不變性(「在傳統範圍內改變」)。費正清還認為,中國中心的世界觀甚至在非漢人統治的王朝中仍然存在。事實確實如此,否則朝貢制度模式就無法解釋十九世紀清王朝在與西方國家外交中的無能。因此,「中國化」的觀念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正如費正清所指,由於中國自發地吸收並從文化上改變了其征服者,因此滿洲人也將朝貢制度中的這種自大情緒內在化了,這就導致他們在歐洲商人和使者到達中國沿海時無法作出適當的反應。
這樣,近代中國史的主要敘述就不可能偏離清王朝的這種世界觀或前代王朝的外交戰略。在這些敘述中,「清」與「中國」並沒有實際區別,所以,清朝向內陸亞洲的擴張(一種完全不同於晚明的方式)對費正清而言是一個略有疑問的問題,因為他起初傾向於將清代內陸亞洲的臣民視為外國人。例如,在“On the Ch’ing Tribute System”(清代的朝貢制度)的文獻注釋中,他和鄧嗣禹寫道:「這種草率的論述顯示出我們在對清朝對外關係的認識上還存在很多的空白:中亞的滿洲當局;十七世紀的中-荷關係;中國與暹羅、老撾和琉球的朝貢關係;整體上對外貿易中的中國方面。」10
而後,在The Chinese World Order的導言中,費正清對清朝在內陸亞洲的地位依然顯得有些模稜兩可。滿洲人、蒙古人、各突厥民族和西藏人都沒有出現在「1818年清朝朝貢國」一覽表中,儘管費正清認為構成朝貢制度的一系列慣例(賜予任命權、官方印信和貴族頭銜、使用清朝曆法、呈交朝貢名錄和地方特產、由官方驛站護送使節、行叩頭禮、接受帝國的回贈以及帝國賜予其在邊界和在京城的貿易特權)既適用於清朝在新疆的回子官員,也適用於外國統治者──確實,甚至漢人官員也遵循這樣的慣例。然而,費正清在兩頁後的「中國外交關係的目標與手段」一表中將內陸亞洲人列入其中,他們被歸入「內陸亞洲帶」──由朝鮮、越南、琉球群島和日本佔據的「中國文化區」之外的地區。這看上去極不合理,那些與清帝國皇族聯姻、敬神和狩獵的內陸亞洲人在文化上比那些只派遣使臣的國家,甚至是日本還要遠離「中心」,而這些地區在十九世紀後半葉前與清朝根本沒有官方聯繫。11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無庫存之港版書籍,將需向海外調貨,平均作業時間約30個工作天,然不保證確定可調到貨,尚請見諒。
為了縮短等待時間,建議您將港書與一般繁體書籍分開下單,以獲得最快的取貨速度。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