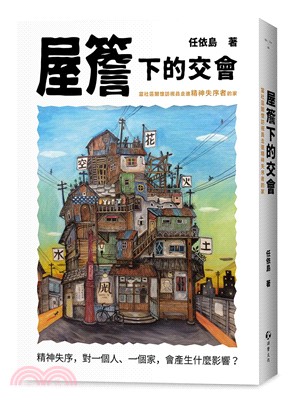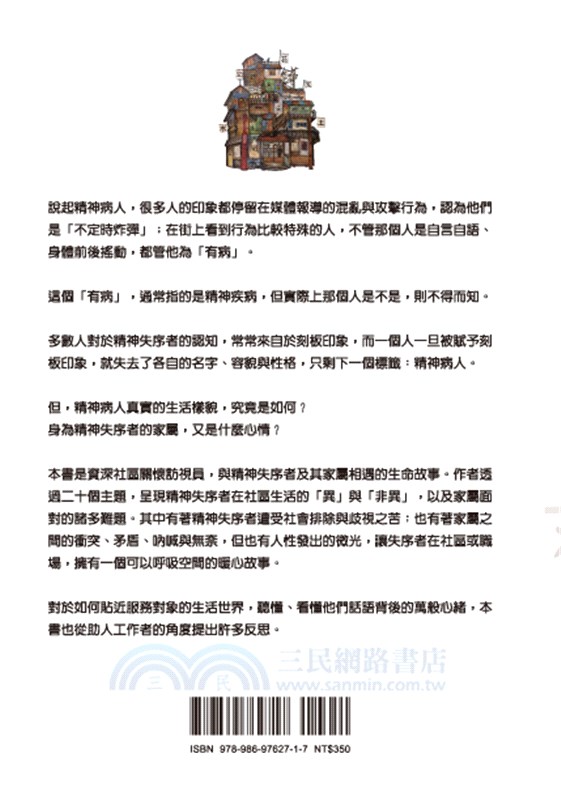屋簷下的交會:當社區關懷訪視員走進精神失序者的家
商品資訊
商品簡介
★入圍2019年Openbook好書獎.年度美好生活書系
精神失序
對一個人、一個家
會產生什麼影響?
說起精神病人,很多人的印象都停留在媒體報導的混亂與攻擊行為,認為他們是「不定時炸彈」;在街上看到行為比較特殊的人,不管那個人是自言自語、身體前後搖動,都管他為「有病」。
這個「有病」,通常指的就是精神疾病,但實際上那個人是不是,不得而知。
多數人對於精神失序者的認知,常常來自於刻板印象,而一個人一旦被賦予刻板印象,就失去了各自的名字、容貌與性格,只剩下一個標籤:精神病人。
但,精神病人真實的生活樣貌,究竟是如何?
身為精神失序者的家屬,又是什麼心情?
本書是資深社區關懷訪視員,與精神失序者及其家屬相遇的生命故事。
工作期間,他走進社區,凝視失序者的日常生活,聆聽家屬受苦的經驗。
作者將他訪視的所見所聞,透過二十個主題,呈現精神失序者在社區生活的「異」與「非異」,以及家屬面對的諸多難題。
其中有著精神失序者遭社會排除與歧視之苦;也有著家屬之間的衝突、矛盾、吶喊與無奈;但也有人性發出的微光,讓失序者在社區或職場,擁有一個可以呼吸空間的暖心故事。
對於如何靠近服務對象的生活世界,作者也從助人工作者的角度提出許多反思。尤其討論了如何以「互為主體性」、同而為「人」的姿態,貼近對方的世界。
全書分為三篇:第一篇為精神失序者的日常生活;第二篇描繪的是精神失序者家屬的陪病生活;第三篇寫社關員是誰,工作性質,以及對制度的省思與批判,也寫作者和精神失序者及家屬相遇的經驗。
透過這些故事,希望大眾對於精神失序者有更立體的認識,撕下標籤與刻版印象,看見他們身而為人的模樣,在病人這個身分之外,他們更是某人的阿嬤、媽媽、父親、姊姊、丈夫、孩子、鄰居與朋友。
※本書作者版稅將捐贈25%給台灣民間社區精神復健機構、25%給「家連家精神健康教育協會」
【什麼是社區關懷訪視員?】
台、澎、金、馬各縣市衛生局依「精神病社區關懷訪視計畫」直聘或委外醫院聘僱的第一線工作人員,須具備護理、職能治療、心理、社工等背景才能從事。社區關懷訪視員的任務除掌握社區精神病人病情穩定程度,並提供必要的醫療協助外,也幫忙多重困境的服務對象與家庭連結資源。踏入社區與入家服務是他們主要的工作模式。部分社區關懷訪視員須兼自殺通報個案關懷業務,從業人數若將精神病與自殺通報兩計畫分開估算,全台大約100位。
【一致推薦】按筆畫排列
余安邦(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專
作者簡介
就讀北投(Pataw,凱達格蘭語女祭師之意)復興高中時,從國文老師手中拾獲平埔族群謎樣身世的一塊碎片。大學甄試想讀文學院繼續追尋,卻被拒於門外,不明就裡讀了商學院,但也莫名奇妙被二一,只好深思熟慮地航向心理學領域。曾經擔任身心障礙機構教保員、自殺通報關懷訪視員,現任社區關懷訪視員。對人類廣袤與深邃如海洋的心理好奇,也對藍色星球上的萬物感興趣。持續以傾聽、健行、爬山、旅行及書寫,練習跟人類及土地連結。
希望小島台灣能活出她美麗多姿的樣子。
名人/編輯推薦
推薦序
開展一段互為主體的疾病書寫
吳易澄(精神科醫師、英國杜倫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段無法逆轉的航行,通過一條漫長的隧道;我無法看見出口,但我知道一定有一個出口存在。我無法回頭,只有持續向前進,一步接著一步,直到終點。
—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寶拉》
這段強忍著無助卻又不放棄希望的自白,是古巴裔美國人類學家露思.貝哈(Ruth Behar)在她書中《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引用智利作家阿言德書寫她罹患紫質症而長期昏迷女兒的一段話。藉由書寫者對自我脆弱性的理解,反而能將自我反身性帶入民族誌的書寫當中。本書作者任依島的精神疾病書寫,便是這般揉雜著凝視他者之痛苦,卻又不吝承認自己微弱的誠實之作。身為「社區關懷訪視員」的作者,由於「位處精神醫療與公共衛生最偏遠的角落」,歷經被漠視的制度性歧視,反而摸索出他實踐在社區精神照護場域中,足以具備的洞見。
近年來,台灣接連出現的社會事件,使得精神疾病的議題逐漸受到大眾重視。公共電視在二○一九年春天,播出《我們與惡的距離》社會寫實劇,刻劃思覺失調症病人的生活面貌,及其周遭家屬人等的道德世界,引起熱議。精神醫學界也罕見地打鐵趁熱,發表大眾書寫,期待國人能進一步正確認識精神疾病。電視劇的腳本,其實都發想於這幾年來台灣的真實事件,包括二○一六年內湖的隨機殺人事件,由於受害女童年僅四歲,事發後,舉國譁然,三日後,台北市政府則將一名時常出沒於政治大學的精神障礙者強制送醫。隨後,二○一七年底,曾收容精神病患的高雄龍發堂,爆發阿米巴痢疾的群聚感染,也招致其非人道收容的質疑。這一連串事件開啟了國人對精神疾病的重視。
事實上,與精神疾病相關的社會事件,並非近年才有。早在一九八四年三月三十日,螢橋國小遭疑似精神病患闖入,對學童潑灑硫酸,造成嚴重的傷害事件,也驚動全國。該事件促使政府啟動精神疾病防治計畫,積極研擬《精神衛生法》;該法於一九九○年公告實施。在這之後,《精神衛生法》也因應保障病患人權的要求,在二○○七年修正,以審查會的制度,來確保強制住院流程的細膩與公正。細數這些事件,是想闡明,精神疾病並非單純的器官變化與行為異常,在治療端也不只有藥到病除那樣單純。精神疾病所捲動的是一個家庭、一個社區的集體勞動,也考驗著一個國家在資源與制度面上能夠支持病患與家屬的能耐。
《屋簷下的交會》一書,透過一個個精神障礙者的個案訪查,帶出了一段段生命沉思。從這些故事裡,讀者能夠藉由深度的凝視,理解一個人在罹患精神疾病後,如何經歷生命軸線的斷裂。書中的每一段故事,讀來都不輕鬆。作者一開始,仍然不乏說教式的諄諄訴說,提醒讀者精神病人並不可怕,也不如大眾媒體渲染的那樣暴力。精神病人所期待的,不只是一帖治病良方,在病人的周遭生態世界中,不但需要緊密的、能夠互相信任的依存關係,同時,更需要縝密的社會安全網絡與照護體系。
當然,疾病不盡然只是單向式進行的災難,作者在社區訪視過程中,走進每一個經歷疾病的家庭,感受疾病對生活、工作、乃至於親屬關係的衝擊;但這也絕非意味著罹病必然招致人生的崩塌。本書難能可貴之處,在於捕捉病者或病家,乃至於一個社區或部落,在面對疾病時所展現出的韌性(resilience)與能動性(agency)。即使在每一個故事中,我們感受到病人面對症狀的痛苦,以及制度上的歧視,但也看到病者己身與周遭人等,如何發揮支持的能耐。例如書中提到的,部落裡發揮照顧的老闆娘,或是移工因著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而經驗了文化照顧的力量。甚至,曾經身為被照顧者的病人,有一天也成為經驗豐富的照顧者。透過這些觀察,作者實際經驗了賦權(empowerment),而保有持續作為的能量。同時,他也對社區照顧提出方案,指出照顧體系必須「考量多元族群的文化差異,參照原住民文化照顧的概念與實作,並鼓勵民間創立多元、創新的中繼站」。
我很喜歡作者「抵家」的說法,他以中文書寫來仿擬台語「在這裡(佇這,tī tsia)」的發音,然後也帶出對「家」的想像。所謂「佇這」,便是「此地」與「此刻」(here and now)。事實上,對於遭逢生命意義突然斷裂而無所適從的病患來說,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個能夠接納自己的地方。在實作上,我們往往躊躇在是否強制送醫、住院,或是回歸社區的掙扎,然而若是緊扣「抵家」的概念,我們就會知道許多作法並不抵觸。我們能做的,必然是在此地此刻的條件下,尋找最多的資源與最多的包容。
本書的書寫策略,採取的是將一個助人者的反身性思考辯證,灌注在他所關切的每一個生命環節之中。作者身為社區關懷員,其實是政府公部門的代言者,然而也因為對病人主體性的關切,他所代言的,同時也是病人對於加諸於其身的精神治理的各種抵抗與反思。這樣的書寫,我想與作者本身的生命與學思經歷有關。我與作者相識於中央研究院舉辦的人類學營,共同走過歷經災難的部落,也有一些心理專業領域的省思對話。我們皆深知,即使擁抱己身助人專業的角色,若不了解服務對象的文化脈絡,那麼再如何高舉善意的人道工作,都有可能招致另一場災難。
醫療人類學家安瑪麗.摩爾(Annmarrie Mol)曾在《照護的邏輯》一書中,提出她理想中的照護概念。她認為好的照護不應該只是給出更多「選擇」給病患而已;更重要的是,醫病之間持續合作,並且針對生病的身體與複雜的生命經驗,持續地調和知識與技術。作者因為自身社關員的身分,從其專業分工上的不確定性,反而能繞過資源掌握者由上而下的介入,從而思索病者或病家所需,這與摩爾所謂「照護的邏輯」,可說不謀而合。
在本書中,作者也以簡短精要的歷史,考察日治時期到今日,相關政策的演變,道出社區關懷員這類「非典型專業工作者」的歷史由來與職業特色。或許不光是作者自述「邊界混種雜生」的身分,而是這類帶有殖民性格,向國家靠攏的社區照護,讓作者感受到相當程度的不自在。然而也因為如此,使得作者得以成為一介「易受傷的觀察者」,在以圍繞「受苦」為主題的場域中,開展出與案主互為主體的書寫,成為本書的特殊風格,從而能帶領讀者以更貼近主體經驗的角度來認識精神疾病。
序
開展一段互為主體的疾病書寫
吳易澄(精神科醫師、英國杜倫大學人類學系博士候選人)
一段無法逆轉的航行,通過一條漫長的隧道;我無法看見出口,但我知道一定有一個出口存在。我無法回頭,只有持續向前進,一步接著一步,直到終點。
—伊莎貝.阿言德(Isabel Allende),《寶拉》
這段強忍著無助卻又不放棄希望的自白,是古巴裔美國人類學家露思.貝哈(Ruth Behar)在她書中《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引用智利作家阿言德書寫她罹患紫質症而長期昏迷女兒的一段話。藉由書寫者對自我脆弱性的理解,反而能將自我反身性帶入民族誌的書寫當中。本書作者任依島的精神疾病書寫,便是這般揉雜著凝視他者之痛苦,卻又不吝承認自己微弱的誠實之作。身為「社區關懷訪視員」的作者,由於「位處精神醫療與公共衛生最偏遠的角落」,歷經被漠視的制度性歧視,反而摸索出他實踐在社區精神照護場域中,足以具備的洞見。
近年來,台灣接連出現的社會事件,使得精神疾病的議題逐漸受到大眾重視。公共電視在二○一九年春天,播出《我們與惡的距離》社會寫實劇,刻劃思覺失調症病人的生活面貌,及其周遭家屬人等的道德世界,引起熱議。精神醫學界也罕見地打鐵趁熱,發表大眾書寫,期待國人能進一步正確認識精神疾病。電視劇的腳本,其實都發想於這幾年來台灣的真實事件,包括二○一六年內湖的隨機殺人事件,由於受害女童年僅四歲,事發後,舉國譁然,三日後,台北市政府則將一名時常出沒於政治大學的精神障礙者強制送醫。隨後,二○一七年底,曾收容精神病患的高雄龍發堂,爆發阿米巴痢疾的群聚感染,也招致其非人道收容的質疑。這一連串事件開啟了國人對精神疾病的重視。
事實上,與精神疾病相關的社會事件,並非近年才有。早在一九八四年三月三十日,螢橋國小遭疑似精神病患闖入,對學童潑灑硫酸,造成嚴重的傷害事件,也驚動全國。該事件促使政府啟動精神疾病防治計畫,積極研擬《精神衛生法》;該法於一九九○年公告實施。在這之後,《精神衛生法》也因應保障病患人權的要求,在二○○七年修正,以審查會的制度,來確保強制住院流程的細膩與公正。細數這些事件,是想闡明,精神疾病並非單純的器官變化與行為異常,在治療端也不只有藥到病除那樣單純。精神疾病所捲動的是一個家庭、一個社區的集體勞動,也考驗著一個國家在資源與制度面上能夠支持病患與家屬的能耐。
《屋簷下的交會》一書,透過一個個精神障礙者的個案訪查,帶出了一段段生命沉思。從這些故事裡,讀者能夠藉由深度的凝視,理解一個人在罹患精神疾病後,如何經歷生命軸線的斷裂。書中的每一段故事,讀來都不輕鬆。作者一開始,仍然不乏說教式的諄諄訴說,提醒讀者精神病人並不可怕,也不如大眾媒體渲染的那樣暴力。精神病人所期待的,不只是一帖治病良方,在病人的周遭生態世界中,不但需要緊密的、能夠互相信任的依存關係,同時,更需要縝密的社會安全網絡與照護體系。
當然,疾病不盡然只是單向式進行的災難,作者在社區訪視過程中,走進每一個經歷疾病的家庭,感受疾病對生活、工作、乃至於親屬關係的衝擊;但這也絕非意味著罹病必然招致人生的崩塌。本書難能可貴之處,在於捕捉病者或病家,乃至於一個社區或部落,在面對疾病時所展現出的韌性(resilience)與能動性(agency)。即使在每一個故事中,我們感受到病人面對症狀的痛苦,以及制度上的歧視,但也看到病者己身與周遭人等,如何發揮支持的能耐。例如書中提到的,部落裡發揮照顧的老闆娘,或是移工因著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而經驗了文化照顧的力量。甚至,曾經身為被照顧者的病人,有一天也成為經驗豐富的照顧者。透過這些觀察,作者實際經驗了賦權(empowerment),而保有持續作為的能量。同時,他也對社區照顧提出方案,指出照顧體系必須「考量多元族群的文化差異,參照原住民文化照顧的概念與實作,並鼓勵民間創立多元、創新的中繼站」。
我很喜歡作者「抵家」的說法,他以中文書寫來仿擬台語「在這裡(佇這,tī tsia)」的發音,然後也帶出對「家」的想像。所謂「佇這」,便是「此地」與「此刻」(here and now)。事實上,對於遭逢生命意義突然斷裂而無所適從的病患來說,最重要的是找到一個能夠接納自己的地方。在實作上,我們往往躊躇在是否強制送醫、住院,或是回歸社區的掙扎,然而若是緊扣「抵家」的概念,我們就會知道許多作法並不抵觸。我們能做的,必然是在此地此刻的條件下,尋找最多的資源與最多的包容。
本書的書寫策略,採取的是將一個助人者的反身性思考辯證,灌注在他所關切的每一個生命環節之中。作者身為社區關懷員,其實是政府公部門的代言者,然而也因為對病人主體性的關切,他所代言的,同時也是病人對於加諸於其身的精神治理的各種抵抗與反思。這樣的書寫,我想與作者本身的生命與學思經歷有關。我與作者相識於中央研究院舉辦的人類學營,共同走過歷經災難的部落,也有一些心理專業領域的省思對話。我們皆深知,即使擁抱己身助人專業的角色,若不了解服務對象的文化脈絡,那麼再如何高舉善意的人道工作,都有可能招致另一場災難。
醫療人類學家安瑪麗.摩爾(Annmarrie Mol)曾在《照護的邏輯》一書中,提出她理想中的照護概念。她認為好的照護不應該只是給出更多「選擇」給病患而已;更重要的是,醫病之間持續合作,並且針對生病的身體與複雜的生命經驗,持續地調和知識與技術。作者因為自身社關員的身分,從其專業分工上的不確定性,反而能繞過資源掌握者由上而下的介入,從而思索病者或病家所需,這與摩爾所謂「照護的邏輯」,可說不謀而合。
在本書中,作者也以簡短精要的歷史,考察日治時期到今日,相關政策的演變,道出社區關懷員這類「非典型專業工作者」的歷史由來與職業特色。或許不光是作者自述「邊界混種雜生」的身分,而是這類帶有殖民性格,向國家靠攏的社區照護,讓作者感受到相當程度的不自在。然而也因為如此,使得作者得以成為一介「易受傷的觀察者」,在以圍繞「受苦」為主題的場域中,開展出與案主互為主體的書寫,成為本書的特殊風格,從而能帶領讀者以更貼近主體經驗的角度來認識精神疾病。
目次
感同身受病人及家屬的痛/邱爸
推薦序/潘正德
推薦序/萬育維
作者序
生命的意外之旅--拓印一段助人工作的足跡
第一篇 精神失序者的日常
流行音樂、廟宇供桌上的准考證、孩子的操場
一家之主
以少成音?以缺合奏
家鎖與「開」「關」
好手好腳
失速男(人)生
第二篇 家屬的陪病生活
未完(成)的問號
家的模樣
欲走無路
護送就醫×強制住院邊緣記事
複數家庭
抵家
你的心情,我的天氣
第三篇 社關員與他們,還有自己
幻化為光
詐騙集團
33908
可以當朋友嗎?
邊界混生
關懷之始
迷惘天平
附錄 台灣的社區精神復健資源
書摘/試閱
貧困的生活,將若竹壓得無法呼吸,每當擔憂、焦燥到爆裂頂點,她最常做的就是吞下一把藥,讓自己在最短的時間,不省人事,暫時忘卻現實的愁煩。醒來時不是在醫院急診室,就是已經由醫院返家,每當看到手上殘留的膠帶黏痕,才覺知又與死神搏鬥過一回。
「妳在吞藥前,通常在想些什麼?」有一次若竹主動提起自己前幾天吞藥,我順勢問了她。
「還不是錢,煩惱錢啊!月底看到那堆帳單就很煩,還有房租要繳,我從來沒欠過房租,一次都沒有喔,孩子學校三不五時也有一堆費用要繳。」若竹講話的神情與口氣,彷彿重現她吞藥前的情緒。但是當她不願坐困愁城到底,仍會起身向前夫親人商借周轉。
遠方的娘家親人十分擔心,幾乎每晚跟她視訊,但不論科技如何地幻構沒有距離,仍不敵相隔千里的真實距離。
這年農曆年前,若竹說好幾年沒回娘家了,她父母也一直叫她回去修養。她覺得前面兩個孩子也都滿大了,可以照顧自己,她只需要帶最小的兒子回去。她跟我說可能會回去至少兩個月,叫我下次不用來。
下一次再見到若竹,真的是兩個月以後的事了。當話題從回家開始聊起,她的眼睛立刻張亮了起來,語調也隨之上揚:「回家真的好輕鬆喔,什麼事都不用擔心,也不用煩惱,晚上睡覺也不用安眠藥,一顆都不用喔。」
「但是……」她托著臉頰,眼神瞬時關暗,聲調跟著下滑:「一回到台灣,不知為什麼……就覺得煩,很煩,不曉得在煩什麼?也不一定全都是錢,大女兒很乖巧,她讀高中綜合班,下班後還去超商打工,每月領的薪水幾乎都給我,當然對家裡經濟的幫助很大,但還是很吃緊。回到台灣的第一天,又不能睡了,又恢復吃安眠藥的日子了。」
她的么兒在一旁,玩著手機遊戲,開心地笑著,純白地反射媽媽的黑色憂愁。
「其實我不是真的想死,我都會想到如果我真的走了,三個孩子要怎麼辦?我吞藥就只是想好好休息,讓時間暫停。有時我吞藥後,還會走到樓下水果行,請老闆幫我叫救護車,我好像也曾打給你,不過大部分都是老大跟老二幫忙處理。我覺得好愧對他們,好像我這個媽媽不盡責,沒有盡到照顧好他們的責任,又常給他們添麻煩。」
若竹在先生失能後,承接了主要照顧者的角色,但除了原本的母職角色,現在又需要擔憂家庭的經濟,可是肉身被無端憂慮、莫名恐慌,以及生理疾病所囿限,無法透過工作削減這個重擔,於是更加被母子關係綑綁,自怨自責於沒能好好照顧子女,反而還要被孩子照顧。
身為人母所承受的家庭負擔如此沉重,不難理解為何她回到娘家後,整個人輕鬆許多,因為回到原生家庭,她就返回女兒的角色;回到原生家庭,她就暫時卸下照顧者的重任,只要享受父母的照顧就好。
相隔千里的家庭照顧壓力,在這兩個月暫時隔絕,如同吞藥也是為了暫時隔絕身心苦痛,只是一個是在意識清楚的狀態下,身體重新找回放鬆的感覺,一個是在失去意識的狀態下,身體暫時失去感知能力。
***
精神失序者同時為照顧者,除了有夫妻間的照顧,親子間的照顧,其實還有隔代間的照顧。
瑞霞阿嬤時常接到孫女學校老師與社工打來的電話,說冠婷又曠課好幾天了,希望阿嬤能勸勸她,除此之外,她還要看顧次孫冠睿。
阿嬤說:「最近細漢ㄟ(sè hàn,幼小),就是冠睿學校老師在聯絡簿都寫了很多字,可惜我不會寫字,要不然就可以回給老師。他那個撿角老北(lāu pē,失敗老爸)常不在家,要不然他應該加減可以看小孩的功課。不過,就算在家也沒用啦,都在玩網路賭博。」
阿嬤停頓了一下,接著怒氣沖沖地說:「講到他們的老北,就歸腹火(kui-pak-hué,一肚子火),從穩定的7-11送貨司機,到現在做臨時工,都是喝酒跟賭博害的。兩個孩子都不管,放給我這老ㄟ顧。」
若非長時間訪視與陪伴瑞霞阿嬤,可能很難貼近一個年近八十歲,從年少到年老,為了家庭無盡付出,且帶著精神失序症狀,卻仍舊在為這個家擔心、受苦的心理歷程。
某一天,阿嬤請我帶她去醫院,說次子剛被診斷出恐慌症,她想去醫院現場掛號,請醫師安排他住院。於是結束上一個訪視後,我趕到阿嬤家,帶她去醫院。
路上閒聊時,她突然請我幫忙尋覓租屋處,原來是長子抱怨房貸壓力大,次子表示地下錢莊討債追得緊,兩人有意將房屋售出,減輕金錢壓力,所以瑞霞阿嬤必須搬離原本住的地方。
沒想到下次訪視,阿嬤就叫我去她的租屋處,剛好這天她出嫁的女兒,跟孫子女的媽媽也都來到新家走訪,本來想跟她有多一點互動,只見她拿著名片大小的咖啡色電話簿,打了好幾通電話,等告一段落後,她跟我說:「歹勢,剛剛都在跟冠婷學校老師聯絡事情,還是一樣,老師跟社工說她一個禮拜沒去學校了,就叫袂振動(bē tín-tāng,叫不動)啊,我都有叫她去,她就不去。煩惱這兩個孫子都煩惱不完。」
話鋒轉到賣房子的事,瑞霞阿嬤難掩心中失落:「講起這個房子,我實在就毋甘耶(m̄ kam,不甘心),住了三十多年。我先生以前骨力食貧惰做(kut-la̍t tsia̍h pîn-tuānn tsok,好吃懶做),又愛賭博,沒有存到錢買房子,後來生病早早就過世了。我一直希望能有自己的房子,之前的房子是我辛苦工作付頭期款買的,我生病後沒辦法工作,大兒子工作比較穩定,就幫我繳貸款,不過他自己在外租房子,老二不要跟我拿錢就不錯了,不敢肖想(妄想)他會幫忙出。」
因為知道阿嬤總是牽掛這個家,既憂且慮,且煩又悶的症狀表象,僅能作為整體受苦處境的一個註解,所以家訪時,總會從關心阿嬤的近況開始,而她總說:「差不多啦,差不多煩啦,煩惱東、煩惱西,上次有個什麼協會的志工叫我唸佛、唸心經,說唸了就不會煩了。哪有那麼簡單?我跟他說心不清,唸經也不會靜。」
阿嬤的操煩,不只是寫在臉上的情緒,以及無力處理孫子女的學校事務而已,從她那本電話簿也可見一斑。
有一次我向她詢問某位社工的電話,她拿出電話簿,翻到其中兩頁,寫滿了所有網絡工作人員的電話,區公所社會課承辦人員、社福中心社工、家暴社工、家防官、學校老師與社工、還有數個民間社福單位社工的電話。此外,我還曾在區公所遇過她,正要將數斤重的白米、麵條等物資拖上公車帶回家。
精神失序且為主要照顧者的苦,似乎連「苦」這個字都只能緊緊咬在唇間。瑞霞阿嬤雖然症狀大致穩定,且三個月才須返診一次,但偶爾還是會出現緊急狀況,像是有一次跟孫女發生口角後,孫女大力推她一把而撞到頭部,出現瘀血。事後,阿嬤氣血攻心,差點跳樓輕生。
身為一個關懷阿嬤的工作者,每次見到她為這個家,讓自己起伏不已的身心遊走在失控邊緣,都相當不捨。好想跟她說:「妳可以不要管兒子跟孫子的事了嗎?那不是妳的責任,照顧孫子女不是他們爸爸的事情嗎?妳自己的狀況也不好,操煩那麼多,只會讓自己更不好。」
但我知道說這些話,效用不大,只好暫放心裡,而我現場的話語撫慰也只能舒緩片刻,因此每當她壓力漸增,便鼓勵她住院,即便是暫離那個煩心的情境也好。
不過阿嬤都會回我:「我不是沒想過要住院,上次醫生也建議我住院,但我要是去住院,他們放學回來,誰煮飯給他們吃?」
阿嬤也非堅決不住院,她都是忍著,忍到家裡的事情處理到一個段落,才會安心地去住院,因此她的住院頻率不高,一、兩年至多一次。
瑞霞阿嬤之所以必須扛起照顧孫子女、張羅家庭經濟之責,顯然是本來在這個位置上的兒子缺席了。兒子不是消失無蹤,也不是毫無收入,而是就算去賺錢,他的收入也沒有挹注到家裡,回到家還會對母親惡言相向,甚至偷拿她手邊僅有的一、兩千元去賭博。
面對失去父職功能的兒子,身為阿嬤的瑞霞,看到孫子這麼黏她,確實難以放著不管,對於總是惹事生非的孫女,也很難完全不理,於是就形成了多方責怪她溺愛孫子女的情況。
冠婷學校的輔導老師就曾打電話跟我討論,能否請阿嬤不要每天拿錢給冠婷,以免她把錢拿去買毒品。還有那天他們媽媽來到阿嬤家,說阿嬤都把孩子寵壞了,像冠睿穿褲子都還要人幫忙才會穿。
但大家或許不懂阿嬤的為難。
「我也都只是給一百塊而已,總是怕她會餓,要給多,我也沒辦法。」
得獎作品
★榮獲2020年台北國際書展書展大獎非小說類首獎
★入圍2019年Openbook好書獎.年度美好生活書系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