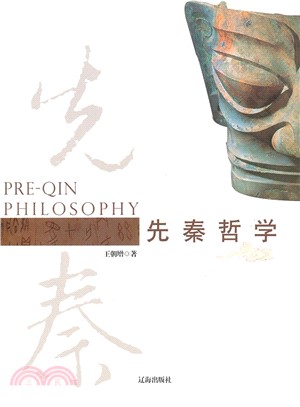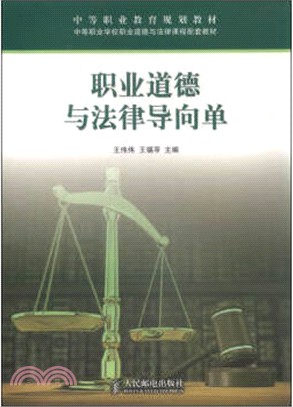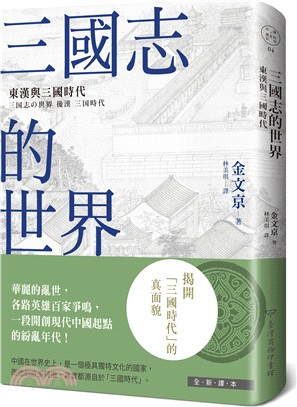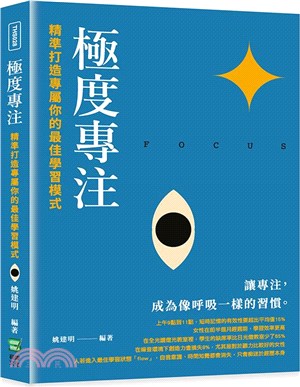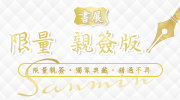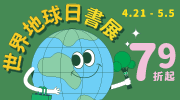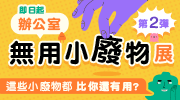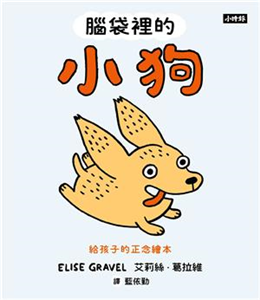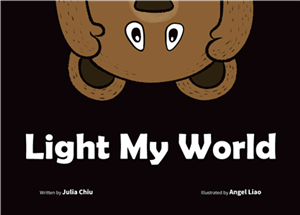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電子書)
商品資訊
ISBN:9787208163898
出版社: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作者:王明珂
出版日:2020/06/01
裝訂:電子書
檔案格式:EPUB
商品碼:2222221840465
商品簡介
《華夏邊緣》是著名學者王明珂討論中華民族族群認同與歷史發展的重磅研究,為回答“什麼是中國人”提供了全新路徑。王明珂認為,“當我們在一張紙上畫一個圓形時,事實上是它的‘邊緣’讓它看起來像個圓形。”他視“華夏”為長程歷史中的人類生態,而“華夏邊緣”不僅是時間上的邊緣、地理上的邊緣,也是認同上的邊緣。在特定的資源競爭與環境分配中,在集體性的記憶塑造與失憶選擇中,華夏邊緣的形成、變遷、維持,亦可說明華夏族群及認同的形成與變遷。
《華夏邊緣》是具有理論範式意義的經典著作,出版多年暢行不衰。書中第一部分主要陳述了全書的理論框架和分析方法;第二部分利用考古材料,說明了華夏族群邊界形成的人類生態背景;第三部分闡述了華夏族群的重要形成基礎,即周人的族源傳說與歷史記載,並通過荊楚吳等例子,說明了邊緣族群華夏化與非華夏化的往復遊移;第四部分著眼於近代華夏邊緣的再造,通過40年代民族調查過程中的微觀事例,分析了個人、族群與社會在認同建立過程中的張力。王明珂運用社會人類學理論、考古發掘報告、歷史文獻史料等各學科理論與資料,結合個人在羌族的田野考察經歷,深入探討了資源環境與族群邊緣關係,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的相互滋長,個體與集體記憶和認同的差異,等等問題,以期為當下的民族與族群認同問題提供更多反思和新知。
作者簡介
王明珂
著名歷史人類學家,1952年出生於南臺灣黃埔軍校旁的眷村,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1983),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博士(1992),臺灣“中研院”第30屆人文社會科學組院士,曾任“中研院”史語所所長。長期從事於結合華夏與華夏邊緣,以及結合人類學田野與歷史文獻的中國民族研究,其多點、移動的田野考察遍及青藏高原東緣羌、藏、彝族地區。主要著作有《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遊牧者的抉擇》《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以及《尋羌》《父親那場永不止息的戰爭》等田野雜記及隨筆集。
名人/編輯推薦
著名學者王明珂成名作,從另類視角解讀中國與中國人
人文社科必讀經典,暢銷二十年
·什麼是中國人?華夏認同如何發軔演變?
《華夏邊緣》試圖以“華夏”或“中國人”為例,建立解釋族群現象的一般性理論。以深入考察族群自我認知的“邊緣研究”,取代描述性概括族群特征的“民族溯源”,即從回答“我們是誰”,到響應“我們為什麼要宣稱我們是誰”。
·以邊緣視角理解族群,在歷史記憶中反思認同
《華夏邊緣》突破性地采取從族群邊緣看整體的研究思路,創造了族群問題研究的全新範式。王明珂提出,應從長程歷史觀察民族問題。以人類生態為基礎,通過歷史的記憶與失憶,人群建構集體想象、凝聚情感、確立邊界,鞏固和擴張群體資源以供內部分享,這是族群問題的歷史本相。
·人文社科研究必讀書目,經典再版
《華夏邊緣》甫一出版就曾引起兩岸三地學界的強烈反響,出版二十餘年,至今暢銷不衰,仍是理解中國民族形成與認同的關鍵性著作,也是歷史學、人類學、考古學等多個領域的必讀書目。此次再版新增代序《如何觀看與了解邊疆》一篇,是王明珂近年來對“華夏邊緣”問題的研究反思和方法提煉。
序
如何觀看與了解邊疆
邊疆是個矛盾的地方。在人們心目中,它既危險又神聖,既匱乏而又潛藏著無窮財富與希望,它經常被忽略但有時又被深切關注,它既遙遠又切近。這是因為,邊疆是一政治、文化與地理空間體(國家)的邊緣地帶,經常也是兩個或多個國家的邊緣、邊界交錯之處。因遠離政治、文化與相關社會秩序核心,邊疆人群較有能力擺脫各種核心典範的約束,或能在兩個或多個政治文化體之典範間作抉擇,因此從一政治文化體的核心觀點來看,邊疆社會是失序、野蠻、混雜與危險的。然而邊疆也是國家的資源邊界地帶,因此在國與國之間的資源競爭中,邊疆又變得十分神聖,值得人們拋頭顱、灑熱血去維護它。邊疆的“邊緣性”主要來自資源競爭或資源匱乏。它或因政治強權間的資源競爭與分界而成為邊疆,更常因資源匱乏而成為邊疆。然而對於核心地區的窮人、失敗者、不滿現實者來說,邊疆也是充滿無主財富與無限希望的真實或想象樂土。
邊疆不僅因其自然資源、地理空間、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邊緣地位而成為邊疆,且因被來自核心的人們觀看、描述而強化其邊緣、邊疆性。過去,在中原之人的一種特殊觀看、觀察與描述角度下,邊疆物產為“奇花異卉”“珍禽異獸”,其風俗習慣為“奇風異俗”或“蠻風陋習”,其服飾“五彩斑斕”,其飲食則好生食“昆蟲、蚱蜢、蝸蜒之類”,其宗教信仰為“淫祀”,其人所相信的歷史則是“神話”與“鄉野傳說”。近代以來又出現兩種背離前者並彼此矛盾的邊疆話語:一為美好自然環境、獨特民族傳統、多元文化、原生態生活、綠色食品、樸實民風,一為教育、開發、團結、維穩與現代化。這些對“邊疆”的觀看與描述,以及過去與現在之間的差距與矛盾,呈現的是人們對於“邊疆”不足、錯誤且有偏見的理解。另一方面,這些得自邊疆的知識信息,強化了我們所熟悉的知識體系,說明什麼是合宜的服飾、正常的飲食、進步的宗教、可信的歷史,以及高尚的道德倫常與政治社會秩序。同時,我們也被禁錮在這些知識所造成的世界中,而難以察覺周邊事物的本相。
近代學術有一“覺醒”運動,即後現代主義學風,對一切知識理性之建構保持懷疑,更直接揭露其(知識)被建構的過程。邊疆以及與之相關的邊緣、邊界,在此學風下成為新的研究重心與知識解構焦點。譬如,近代世界許多地方皆經歷國族國家之建構過程,此過程也包括與國族邊緣及國家疆界有關的歷史與民族知識建構﹔在後現代主義風潮下,這些歷史與民族知識被解構,邊疆因此或常卷入相鄰之國間的疆界糾紛,或有統一及分離主義的衝突與對立。看來,近代典範的歷史與民族知識固然造成邊疆的邊緣性,但後現代主義知識也未必能使邊疆之地與人過得更好。主要問題在於,所謂後現代之“覺醒”經常是將他者“喚醒”,而非對自我身份認同與認知偏見的覺醒﹔“解構”常流於兩個政治文化主體相互解構,而邊疆依然為邊緣。
以上這些評論,似乎都可用來批判我對中國邊疆的“華夏邊緣”研究。或因書名如此,《華夏邊緣》常被一些學者認為仍是由“華夏中心觀點”來分析居於“邊緣”的少數民族。我所建構的歷史與民族知識,對於典範的民族史與民族學知識而言的確是一種解構﹔我的一些研究又深受後現代學術影響,因此我有時也被認為是後現代主義學者。然而,我難以接受典範的華夏中心主義史觀之邊疆書寫,我也不同意後現代主義史學對當代中國民族史與民族現實的解構邏輯。以下,我嘗試說明自己在“華夏邊緣系列”——《華夏邊緣》《羌在漢藏之間》《英雄祖先與弟兄民族》《遊牧者的抉擇》等——著作中對中國“邊疆”的看法,也借此表示一種對“邊疆”的觀看與解讀角度。
一、華夏與華夏邊緣的形成
我稱這些著作為“華夏邊緣系列”,其意義有三。首先,我不認為今日中國漢族與55 個少數民族之國族結構為一“近現代”現象,而是將之視為長程歷史中“華夏”與其“邊緣”共生、互動,並經過近代變遷而造成的結果。其次,由人類生態角度,我承認“華夏”(地域與人群)為一政治、經濟與文化核心,其周邊地域及人群居於“華夏邊緣”地位﹔這是歷史事實,也是人類生態現實。最後,認識了以上兩點之後,我們可以思考歷史上華夏及其邊緣之出現,各歷史階段(包括近代)兩者間的互動,以及因此造成的雙方內涵與本質變遷,並由此了解當代中國民族現況之人類生態意義。
在當代國族主義與國族國家研究中有一種“近代主義者觀點”,將當代所有民族國家及其內部之民族、少數民族、民族文化等皆視為近代建構。此說認為,近代西方之民族主義、民族概念、民主思潮等,隨著歐美帝國主義國家之資源競奪及勢力擴張而席卷全球,在世界各地激起當地的國族主義及民族國家建構運動。因此,當代民族國家被稱作近代出現之“想象的共同體”,而民族文化也被視為在近代“被創造的傳統”。近代中國之民族國家及其內的56個民族,也在此種詮釋模式下得到一種新穎的歷史與文化解釋。這種解釋看來十分合理﹔近代中國,相關民族歷史及文化之建構過程皆歷歷可考。
我們不得不承認,近代有一個民族國家、少數民族及相關歷史與文化知識的建構過程。然而這並不新穎。人類一直在創造“文化”,編造“歷史”,以符合或修正當代人群的政治社會組織與群體認同。我不同意民族國家近代建構論的理由便在此﹕所謂“民族國家”(民族與國家的結合)並不是什麼新玩意,這是人類族群認同與政治社會組織結合的舊瓶新酒。簡單地說,一人類群體常集體想象、記憶及相信大家有共同的“血緣”關係,以此根基情感來凝聚群體(族群、民族或國族),其目的在於宣稱、鞏固或擴張該群體的資源,界定可分享此資源的人群邊界。然而無論是族群、民族或國族,它們都是一個個的空殼子,它們需要借“實質的”政治社會組織才能遂行其維護、擴張共同資源的目的。在古今中外歷史上,無論是部落、部落聯盟、帝國,其內部都蘊含以共祖記憶來凝聚的“族群”(帝王家族、統治階層或貴族),它們都是“族群”與“政治組織”的結合。因此,“民族國家近代建構論”忽略了近代變遷的古代基礎,更忽略了這長程歷史中的人類生態變化。
以下我便先從人類生態之長程歷史變化來說明“華夏”與其“邊緣”如何同時形成,在歷史上兩者如何共生並相互激蕩而產生變遷,並以此來認識當代中國的國族國家,以及其內部之漢族與邊疆少數民族。
關於華夏認同與華夏邊緣的出現,我在本書中提及一個關鍵因素,那便是距今約4000 年前後的氣候變遷對華北地區人類生態的影響。在此氣候幹冷化之影響下,內蒙古中南部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絕大多數新石器晚期農業聚落都被人們放棄,而後在春秋戰國時再占居此地的是遊牧或半遊牧社會人群。在青海河湟地區,距今約3700 年的本地辛店、卡約文化人群,放棄過去齊家文化人群那種長期定居、養豬、行農業的經濟生活,開始多養馬、牛、羊而經常遷徙。在西遼河流域,距今約3500 年之後各地農業聚落與人類活動都減少,距今2900 年左右出現以畜牧為主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混合經濟人群。顯然在這些原來便是新石器時代農業的邊緣地區,突來的劣化氣候趕走了本地住民,或使他們成為相當依賴草食動物且定居程度低的農牧混合經濟人群。
對此我們還可作些補充。考古學者蘇秉琦先生曾提出,新石器時代晚期古文明在中國各地“滿天星斗”式地出現,以此主張中國文明起源的“多中心起源說”。這一點毫無疑問,且值得我們深切關注。然而,另一考古學者俞偉超先生曾注意到,在距今約4000年前後,許多中原之外新石器晚期及銅石並用時期的古文化都有突然夭折的現象。他認為,氣候變遷可能是造成此普遍性考古文化面貌變遷或中斷的原因之一。這些在距今4000 年前後經歷消亡或重大變遷的中原之外的考古文化約有﹕長江下遊的良渚文化(距今約5300 至4000 年),中遊的石家河文化(距今約4600 至4000 年),長江中上遊的寶墩文化(距今約4500 至4000 年),黃河上遊的齊家文化(距今約4200 至3700 年),遼河流域夏家店下層(距今約4000 至3500 年)。然而相對於此的是,黃河中下遊的中原地區在同一時間,由二裡頭、二裡崗等考古文化所呈現的人類生態變化顯然是,人群間的衝突增加,防衛性建筑出現,人群間財富與權力分配愈來愈不均,政治結構愈來愈龐大,終於在距今3600 年左右出現了中央化的商王朝。簡言之,這是一個由“滿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過程。
我們再看看中原北方的人類生態變化。約在西周至戰國時期,陜、晉、冀三省北方山岳地帶農牧混合經濟人群南移,爭奪農牧資源,如此造成南方東周諸國貴族以“華夏”認同來彼此凝聚,華夏(實指其政治體之統治上層)成為一個強力維護共同資源的族群,同時將較依賴畜牧的人群視為非我族類(戎狄)﹔此即最早的“華夏”與“華夏邊緣”之出現。如我在前面所提及的,族群只是一認同群體,它需要具體的政治社會組織來實踐其意圖。華夏也不例外。秦與漢代的統一帝國,便是實踐華夏意志—對外保護及擴張其資源領域,對內執行資源階序分配—的政治社會體。秦漢帝國建立後,被排除於帝國之外或被羈縻於帝國周邊的四方邦國、部落與村落人群,其政治、經濟邊緣性進一步被強化,且因各地人類生態有異,與中原帝國之互動模式不同,而成為許多性質不同的“華夏邊緣”。
“月明星稀”這比喻,對於居於核心之“月”並無歌頌褒揚之意﹔由人類生態角度看,我們對於文明有一種反思—文明是集中化政體、階序化社會產物,它靠著燃燒被剝削者的脂膏而發出光芒。“月明星稀”更重要的意義在於,“星”並沒有消失,而是被月光掩蓋。探索“華夏”及“華夏邊緣”之各個區域性人類生態體系,以及它們因互動而共構的人類生態體系,可以使我們更深入了解整體中國歷史發展之動態因素。
二、人類生態與華夏邊緣
我必須對前面多次提及的人類生態作些說明。人類生態是指,一人群所居環境、所行經濟生業及其社會結群(社會組織與群體認同),這三方面共構的生物社會體系。環境包括自然環境與人們對其之修飾、改造與邊界建構。經濟生業是指人們利用環境以獲得生存資源的種種生計手段,如漁獵、農、牧、貿易等。社會結群則是,人們為了在特定環境中行其經濟生業,以及為保護、分配、競爭領域和生存資源,而在群體中建構的種種社會組織(如家庭、部落、國家)以及相關的人群認同與區分(如性別、年齡、貴賤、聖俗群體,以及由家庭到民族的“族群”等)。
華夏帝國與華夏邊緣出現後,華夏帝國(更恰當的稱法應為“中原帝國”)本身便為一人類生態體系。秦漢長城成為一具體、實質的華夏邊緣,華夏以此隔阻北方畜牧化、武裝化人群南下爭奪生存資源。此情況導致長城以北各人群的全面遊牧化,並因此形成數個地域性人類生態體系﹔它們與華夏帝國間的互動,則形成華夏帝國與華夏邊緣共構的人類生態體系。在《遊牧者的抉擇》一書中,我以漢帝國北方三種遊牧人群,鮮卑、匈奴與西羌為例,說明他們各自的環境、遊牧經濟與社會政治組織特色,以及他們與漢帝國之間的互動。他們或嘗試突破漢帝國的長城封鎖線,或設法抵擋漢帝國的擴土。由於自然環境、遊牧經濟與輔助性生計(如狩獵、農業、貿易)等差異,北方草原遊牧的匈奴組成“國家”,東北森林草原遊牧與混合經濟的鮮卑組成“部落聯盟”,而在西北的甘青高原河谷遊牧的西羌則為許多大小“部落”,平日彼此爭奪可行農牧的美好河谷,只在應付戰爭時短暫結盟。
匈奴帝國以武力對漢帝國施壓以獲得資源,但因此也使得鄰近長城的部族漸依賴漢帝國的資源,造成草原帝國分裂(南、北匈奴)。國家組織的集中化與遊牧的分散化原則相矛盾,這是遊牧帝國的內在困境。烏桓、鮮卑的部落聯盟,在吸收各部族及適應新環境上極具彈性,因此能侵入草原、穿越長城,後來建立統領漢地與部分草原的前燕、西秦、南涼、北魏等政權。西羌分散的大小部落,各小單位人群皆能自作行動抉擇,此反而令漢帝國窮於應付﹔將他們遷於塞內之舉,更使帝國西北陷入長期軍事衝突與社會動蕩之中。
這些漢代的北方遊牧、半遊牧與混合經濟人群的經濟生業與社會組織,以及他們借此與漢帝國的互動模式,後來都在某種程度上被延續下來。如在歷史上,西北方,青藏高原東部被華夏稱為“羌”或“番”的高原遊牧人群,經常在部落分散的情況下彼此爭奪草場、河谷。正北方,蒙古草原上一個個的遊牧帝國相繼興起,嘗試以武力突破長城,但也因此造成近長城的部族與其北方、西方部族間的分裂(如匈奴之後又有東西突厥的分裂)。東北方的森林遊牧、漁獵與混合經濟部族(女真、契丹等),則常組成部落聯盟南下或西進,吸收各種經濟生業之部族而不斷變化其族群內涵與政治社會組織(如建立國家),此使得他們經常能成功地突破長城,建立兼統草原與中原的帝國。
從人類生態來看,今日內蒙古為中國的一部分而蒙古為一獨立共和國,此與漢代南北匈奴分立之人類生態意義十分相似。而曾為高句麗、渤海國、契丹、女真之域的東北今日成為中國邊疆,顯然並非由於中原帝國對這地區的征服,而是相反的,從烏桓、鮮卑以來一波波本地部落聯盟對中原的征服及滲入所造成的人類生態。今日新疆移民“兵團”與本地農、牧多族共處所呈現的人類生態,亦與漢帝國在西域屯田所形成的人類生態類似—由人類生態來看,新疆並非清帝國的“新”邊疆。這些例子皆顯示,“國族國家近代建構論”不足以解釋今日中國及其邊疆之情況。
我們再舉南方之華夏邊緣為例。湖南南部、西部,至少由東漢以來便成為一特殊之華夏邊緣。由於近在帝力所及之域,以及資源匱乏,本地村寨居民自古以來便為帝國郡縣之賦稅所苦。在漢歷史文獻與本地社會記憶中,皆經常可見此一華夏邊緣人群之特殊“邊緣性”。如漢晉史籍中的“白虎復夷”故事,據稱該種夷人因其先祖為秦除虎害有功,而得免賦役。又如隋唐史籍中的“莫傜”,也自稱祖上對朝廷有功而得免賦役。盤瓠故事,神犬盤瓠因功娶了帝王之女,他們的後代因而世世免於傜役稅賦的故事,更由漢晉時期的漢文典籍流傳到近代南方非漢族群之口傳歷史中﹔苗、瑤、畬族的許多地方族群皆自稱“盤瓠後裔”,借此訴說本地人應免於賦役。史籍中稱本地人“愁苦賦役,困罹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指的便是此種華夏邊緣人類生態下“蠻夷之亂”的普遍模式。
清代為了防堵抗賦稅的地方變亂,在湘西實施軍屯制度,征地租、征屯租以養兵。到了民國時期,此屯防制度更成為地方官府、軍閥斂財及擴張勢力的工具。1933—1935年湘西連年遭到天然災害,人民無糧可繳屯租,負責征繳屯租者以殘酷手段催逼,於是暴發湘西革屯運動,後來發展為全面武裝革屯。1936—1938 年湘西革屯運動可說是長程歷史中一個“華夏邊緣”之近代延續與變遷。延續的是本地人對官府賦役的抵抗,如歷史上無數次的蠻夷之亂與苗亂﹔變遷的則是發起此運動的地方領袖們以“民族平等”“全國人民應臻平等”為訴求,“七七事變”發生後他們更將革屯武裝部隊改稱為“革屯抗日軍”。這些都顯示,許多近代中國邊疆的情況有其基於人類生態的歷史延續性,亦有新時代變遷。
目次
代序 如何觀看與了解邊疆
1997年版序言 什麼是中國人?
2013年版序言 “什麼是中國人”再思考
2013年版增訂說明
第一部分 邊緣與內涵
第一章 當代社會人類學族群理論
第二章 記憶、歷史與族群本質
第三章 民族史研究的邊緣理論
第二部分 華夏生態邊界的形成
第四章 青海河湟地區遊牧社會的形成
第五章 鄂爾多斯及其鄰近地區遊牧社會的形成
第六章 西遼河地區遊牧社會的形成
第三部分 華夏族群邊緣的形成與擴張
第七章 華夏邊緣的形成:周人族源傳說
第八章 華夏對西周的記憶與失憶
第九章 邊緣人群華夏化歷程:吳太伯的故事
第十章 華夏邊緣的漂移:誰是羌人
第十一章 漢人的形成:漢代華夏對四方異族的多元意象
第四部分 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
第十二章 近代華夏邊緣再造
第十三章 近代華夏邊緣再造的微觀過程
第十四章 一個華夏邊緣的延續與變遷
結語 資源競爭、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
參考書目
書摘/試閱
民族史的邊緣研究
我所謂的“民族史邊緣研究”,主要是建立在一種對“族群”的定義上:“族群”被視為一個人群主觀的認同範疇,而非一個特定語言、文化與體質特征的綜合體。人群的主觀認同(族群範圍),由界定及維持族群邊界來完成,而族群邊界是多重的、可變的、可被利
用的。在多層次的族群認同中,民族是最一般性、最大範圍的“族群”。這個主觀族群或民族範疇的形成,是在特定的政治經濟環境中,在掌握知識與權力的知識精英之導引及推動下,人們以共同稱號、族源歷史,並以某些體質、語言、宗教或文化特征,來強調內部的一體性、階序性,並對外設定族群邊界以排除他人。然而隨著內外政治、經濟環境的改變,資源分配、分享關係也隨之變化,因此造成個人或整個族群或民族的認同變遷。在這過程中可能被觀察到的現象是,原來的共同祖源被淡忘,新的共同祖源被強調;創造新的族稱,或重新定義原有族稱的人群指涉範疇;強調新的文化特征以排除“外人”,或對內重新調整人群的核心與邊緣。基於這種對民族本質的理解,民族史研究的重點自然將由民族內涵轉移到民族邊緣。
邊緣研究
關於邊緣研究,最簡單的理解方式就是:當我們在一張白紙上畫一個圓時,最方便而有效的方法,便是畫出一個圓的邊緣線條。在這圓圈之內,無論如何塗鴉,都不會改變這是一個圓圈的事實。相同的,在族群關係之中,一旦以某種主觀範準界定了族群邊緣,族群內部的人不用經常強調自己的文化內涵,反而是在族群邊緣,人們需要強調自身的族群特征。因此,邊緣成為觀察、理解族群現象的最佳位置。
族群邊緣的研究,並不是將族群視為一個有固定疆界的人群。相反的,族群邊緣研究的前提便是,族群邊緣是多重的、模糊的、易變的。以這樣的觀點來看,族群邊緣研究類似於一些考古學者所謂的“邊疆與邊界研究”(frontier and boundary studies)。這種邊疆與邊界研究的主旨是:(1)它認為一個社會體系是開放的體系;(2)為了解這樣的開放體系,一個辦法就是研究它的邊疆或邊界變化。族群邊緣研究也與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y)者所稱的“邊界研究”(border study)有相似之處—都著意於觀察、分析,在各種文化典範與政治權威所建立的“邊界”下,人們企圖跨越邊界的情感與作為。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民族溯源研究著重於構成一個社會體系的“內涵”。因此,溯源研究的方法學基礎,便是在多項事物中找尋、比較其內涵相似性以建立這些事物間之關係的“類推法”(analogy)。譬如,民族溯源研究者常分析歸納考古、語言、體質以及歷史等資料,而得到某一民族的客觀特征。然而這種客觀特征,事實上是學者強調它們間的相似性,並忽略一些“異例”(anomaly)所得的結果。在這樣的理智活動中,我們很容易受自己主觀偏見的影響。考古學者古爾德(R. A. Gould)曾檢討,以“類推”與找尋“相似性”來建立規律法則,這樣的研究法在增進我們的知識上有很大的限制。他指出,不規則的現象或“異例”才應是我們研究的焦點。同樣的,在族群邊緣研究中,我認為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邊緣的、不規則的、變化的族群現象。因為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探討人類的族群本質,以及詮釋由此衍生的族群現象。
一些核心問題
由於對民族或族群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族群邊緣研究所提出的核心問題,與溯源研究所欲解決的問題也大不相同。如前所言,族群邊緣研究兼采並融合工具論與根基論觀點。因此,首先,站在族群研究之工具論立場,造成族群邊界出現或改變的人類資源分配與競爭背景,必然是一個值得探索的問題。譬如,關於華夏民族,我所關心的不是考古學上某種“典型器物”在時間、空間的分布所反映的夏、商、周民族起源。而是,在什麼樣的環境與社會經濟背景中,華夏因其族群邊緣出現(界定可分享資源的人群範圍)而形成,以及,在什麼樣的環境與社會經濟背景中,華夏邊緣人群進入或脫離華夏。本書中所謂邊緣人群,或指新石器時代晚期黃土農業邊緣的人群,或指商末周初的周人與姜姓,西周晚期的戎與秦人。或是,在某一時代由非華夏成為華夏,或由華夏成為非華夏,或處於華夏族群邊緣的人群;如春秋時的吳人、越人與楚人,以及魏晉南北朝時部分的“五胡”,近現代的臺灣人與華僑等。
其次,以歷史記憶為基礎的根基論觀點,華夏如何以歷史記憶來強化或修正其族群邊緣,邊緣人群如何假借華夏歷史記憶以進入華夏,如何排拒、修飾華夏歷史記憶以維持其非華夏的本土族群認同,或如何采納多元歷史記憶以便遊移於華夏邊緣,這是另一組研究焦點問題。
再次,在一個族群之中,各個次群體對於本族群之本質常有不同的詮釋,對於“歷史記憶”也因此有許多爭論。這是核心與邊緣之爭。也就是說,各群體都希望自己是本族群的核心。因此,邊緣研究的另一個核心問題便是:族群認同與歷史記憶如何形成?它主要是誰主張的認同,誰強調的邊界,誰的歷史記憶?經由什麼樣的過程而成為人群的集體認同、邊界與歷史記憶?
邊緣研究中的考古學重心
不僅問題取向不同,邊緣研究對於考古材料與歷史材料的偏重與解讀,也有異於溯源研究所為。在考古學方面,民族溯源研究的考古學基礎,主要是建立在“器物學”上;而族群邊緣研究的考古學基礎,則主要建立在“生態考古學”上。
因為,如前所言,“族群”這樣的人類結群是人們為了維護共同資源,以主觀的血緣關係(歷史記憶)彼此聯系並排除外人的人群組合。因此,研究族群邊界的形成,首先我們要注意邊緣地區的環境與人類生態變遷問題。譬如,以華夏的形成為例,青海河湟谷地及內蒙古鄂爾多斯等黃土農業的邊緣地區,由新石器時代晚期到戰國時期,都曾經歷由龍山式農業經濟而趨向遊牧化的過程。在這過程中,由於資源競爭以及需要保護和擴張共同資源,華的北方、西方族群邊界逐漸形成,並向西擴張(請參看本書第四、五、六、九各章)。在這樣的研究中,我們較依賴主要基於動植物標本分析所建立的環境與人類生態考古知識。因此,邊緣研究與溯源研究在考古學基礎上的差異,也就是考古學者所戲稱的“ 骨頭、種子考古學家”(bones and seeds archaeologists) 與“罐子考古學家”(pots archaeologists)的歧異所在。中國考古學界的研究重心顯然是偏於後者;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溯源研究取向所造成的結果。
在考古器物遺存(artifacts)方面,也由於人類生態取向,邊緣研究較注重器物的功能分析。在民族溯源研究中,器物風格的同異變化常被用來推論一個族群的時空分布範圍與遷移路線;對於這一點我相當存疑。基本上,我認為留下那些器物的古人,是一些有偏好、欲求、憂懼的人,這些主觀情感影響他們制作、保存某些特定風格的器物。因此,器物風格並不能表現一個古代族群的範圍以及他們的族源。舉個簡單的例子,學者可能以戰國秦人器物的風格,來推論秦人屬於“東夷民族”,是由東方遷移到西方的族群。但是,我們無法否認,秦人也可能原為本土的“西戎”,因心慕東方文化所以刻意模仿東方的器物風格,或刻意用他們認為珍貴的、有東方風格的器物隨葬。因此,考古上器物風格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變化,本身並不代表族群的分布範圍及遷徙路線。雖然如此,它仍不失為一種重要指標,顯示某種影響人群認同的文化接觸或生態環境變遷正在進行之中。
20 世紀80 年代以來,研究“集體記憶”的學者們關注的一個焦點是:社會人群如何以某種媒介(文字、歌舞、定期儀式、口述或文物)來傳遞集體記憶。許多學者都注意到文物(artifacts)或圖像與集體記憶間的關係。個人經常將知識與經驗圖像化,以便於回憶;社會也常以文物或圖像來強化集體記憶。譬如:一張畢業紀念照,一塊紀念碑,一個家族徽記,都可能保存一些人群的集體記憶。由此來看,傳統上我們將“歷史文物”(無論是傳世或是發掘品)當作完全客觀的證據,以文物的“相似性”來證明人群間的親緣關係,或人群的遷移,應該可作部分修正。考古發掘所得,尤其是出於墓葬與窖藏的文物,從某種觀點來看,可說是有意被制造、收集及保存下來的文物。這些器物上所包含的文字銘刻、紋飾圖案,常刻意表達某種社會價值,或強調某些集體記憶。一塊刻著家族譜系的隋唐石碑,碑上的族譜不能被認為是毫無疑問的歷史事實,它應被認為是制造者有意要別人相信的譜系。相同的,一個刻著族徽及銘文的殷周青銅器,其徽記與銘文內容的重要性不在於它們所呈現的“史實”,更重要的是,為何器物主人要刻意保存這些記憶。也就是說,我們希望經由這些遺存來探索留下此記憶者的“意圖”,這種意圖經常表現其個人或社會的價值觀或心理傾向。
邊緣研究中的歷史文獻
在文獻資料方面,歷史文獻所記載的有關一個民族的文化特征、族名、族源傳說、史事等,都有助於探索民族邊界的形成與變遷。但是,我們對這些資料的解讀方式,或與民族溯源研究者的看法有異。最根本的差異在於,由邊緣研究的角度,我認為歷史文獻並不是一些真偽史事集結而成的“史實庫”,而是一種“社會記憶”。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時代,許多不同的人群,都在組織、記錄當代或歷史上的重要事件與人物,以符合或詮釋一個時代或一個人群的本質。這便是一個時代的社會記憶。在一個社會中,有些人所記錄的過去,被認為更有權威或更真實;這種社會記憶,被社會制度化地推廣、保存,如此形成我們今日所見的“歷史文獻”。因為它們是一種社會記憶,所以我們從中希望得到的信息是,當時的人為何要選擇這些記憶?為何要保存這些記憶?在什麼樣的社會情境中,這些記憶對他們有意義?當文獻記載的史事有明顯錯誤,或者兩項資料相左時,我們的工作不只是“去蕪存菁”以追求史實;更重要的是,探求為何古人對同一事件有不同的記錄與詮釋,其中反映了哪些族群、階級、性別或時代社會的差異與變遷?
譬如,根據戰國文獻記載,中國北方與西北的戎狄是周人的主要敵人。這種敵對關係,可以追溯到周人建國之前。因此史家常說,戎狄之禍與西周相始終。但是,在西周彝器銘文中,周人的主要敵人卻來自南方與東方,如東夷、東國、荊蠻、楚荊、南國等。如果戰國文獻與西周金文都是“史實庫”,那麼歷史學者只需探索究竟西周時周人的主要敵人來自何方。但是,如果我們將之都當作歷史記憶,那麼西周彝器銘文所載,顯然是西周時人認為重要的記憶;而戰國文獻所載的西周,則是戰國時人在一個新的社會架構之下對西周的集體回憶。如此,兩者之間的差異便形成了前面曾提到的“異例”。配合其他資料對於這個異例的詮釋,可能使我們進一步了解由“周人”到“華夏”之間的族群邊緣變化(參見本書第七、八章)。
以下我將從歷史記憶的觀點,來說明在邊緣研究中,我如何看待歷史文獻記載中的族群文化、族稱與族源歷史。
族群文化 在前面我們曾提到,客觀性文化特征不能確切地定義一個族群的範圍,但這並不表示客觀文化特征不重要。雖然不是在每一個人身上都可觀察到表現族群身份的文化特征,但的確有些人,在某些時候,會以某種文化特征來強調其族群身份。因此問題在於:什麼人需要表現這些文化特征?在什麼情形下一個人需要奉行這些文化特征?為什麼選擇某些特定的文化特征來強調族群身份?譬如,我們都知道中國人有一些文化特征,如中國人的服飾衣冠、舉止言談,中國人的飲食習慣、風俗習尚,以及中國人的價值觀與道德觀。但不是每一個中國人都需要奉行這些文化特征來強調自己的族群身份。需要強調族群身份的人,經常是處於族群邊緣而有認同危機的人。這時,強調族群特征等於是宣稱一種族群認同。
因此,漢文典籍中對“我族”的描述,都可以從社會或個人的認同危機或認同變遷等角度來理解。
相反的,漢文典籍中對於“他族”文化特征的描述,有時能為我們提供關於該人群的一些客觀資料(如果這些描述是正確的話)。但更重要的是,這些史料也反映記載者的自我意象與對“非我族類”的意象。從這個觀點來看,漢文典籍中關於異族風俗習尚的記載,可比擬於一種古典的民族志。我們知道,功能學派人類學家的主要貢獻之一,便是以一系列方法論上的問題使人類學民族志工作有了核心。在此之前的早期人類學家,尤其是被戲稱為“躺椅上的人類學家”(armchair anthropologists),對於異文化的描述基本上是有選擇性的—他們描述他們認為有趣的主題,而這些有趣的主題,經常是對觀察者而言的“奇風異俗”。這種心理不難理解:我們習於自己所熟知的風俗習尚與價值觀,而以強調異族的“奇風異俗”來肯定“我們”間的相似性。這種心理,也反映在漢文典籍裡類似民族志的資料中。也就是說,漢文典籍對四裔民族的記載,透露出當時華夏主觀上詮釋“為什麼他們不是我們之一”諸如此類的信息。因此,可將之視為華夏主觀的、文化上的族群邊界。譬如,在《後漢書• 西羌傳》中,我們看到漢晉時人對於西羌的生活習俗有如此記載:
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谷,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十二世後相與婚姻。父沒則妻後母,兄亡則納嫠嫂……不立君臣,無相長一。
由這個記載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華夏對於自身與非華夏之間族群邊界的定義是:相對於華夏的規律與秩序,羌人的異族本質在於他們的“不規律性”。他們沒有一定的居所,沒有一定的親族體系,沒有一定的政治秩序。1 因此,比較各時代漢文典籍對這些“異族”的文化習俗記載,或比較個別作者對於“異族”的描述,我們或可探討華夏族群邊界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人群中的界定與變遷。
族稱 前面我們曾提及,一個族群的自稱與對他族的稱謂,兩者在反映同類與異己上各有其重要性。由民族溯源研究的角度來看,所謂華夏、漢人、唐人、華人、中國人,都是一個民族連續體在不同時代、不同場合的自稱族號。但由民族邊緣研究的角度,我認為,當一個人或一族群使用多種不同自稱時,每一種稱謂所涵括與排除的人群範圍都可能有所不同,其所反映的族群現象值得留意。
個人或群體宣稱多種族稱,可能有以下幾種不同的情形。第一種情形是,不同族稱所涵括的人群大致相同,但所排除的人群不同。第二種情形是,多種族稱所涵括與排除的人群不同,但兩者並不矛盾。如一位臺灣客家人,可能自稱客家人、臺灣人或中國人;每一種稱號,都使他與不同範疇的人群結合在一起。這是由於族群認同經常呈由內向外、由親至疏的多重結構體系,這種族群認同體系也反映在族稱上。第三種情形是,兩種族稱所涵括與排除的人群不同,且彼此矛盾。譬如一個人在某種情況下自稱滿人,在另一種情況下他又自稱漢人。還有第四種狀況。比如,部分住在岷江上遊的人群以母語自稱“爾瑪”,以漢語自稱“羌族”;兩種稱號代表兩種族群分類體系,以及兩種相互交錯的族群知識與歷史內存系。在不同世代之羌族間,這兩種族稱所涵括與排除的人群不盡相同。老年人或認為,“爾瑪”只是指一條山溝中各村寨的人;當他們認識並接受當前羌族概念及本民族分布情況後,他們才將“爾瑪”等同於羌族。以上四種情形都顯示,人們常視狀況而使用不同的稱號,這就是所謂的“視狀況而定的族群認同”(situational ethnicity)。但是,以上四種情況所顯示的族群現象有相當大的不同。在第一種與第二種情況下,各稱號間並無矛盾,使用這些稱號的人在認同上也無矛盾。在第三種情況下,當宣稱一種族群身份時,當事人需要隱瞞另一種族群身份。第四種情況經常發生在當前世界各地之少數民族與原住民身上。如岷江上遊的羌族,一方面他們是當地族群分類中的“爾瑪”,另一方面又是國家認可之民族分類中的“羌族”;這可說是一種雙重族群認同。然而隨著時代變化,老年人心目中狹隘的“爾瑪”概念多因老成凋謝而漸成為過去。在當今大多數羌族心目中,爾瑪與羌族已合而為一。
因此,在民族史邊緣研究中,我們不但須分辨史料中的自稱族名與他稱族名,還要探究一群人在不同狀況下,所使用的族群稱號中所表達的涵括與排他的族群認同體系(ethnic system)。譬如,在漢代初年,一個青海河湟地區土著的族群認同體系可能是,牧團→次部落→部落。在與漢代中原之人密切交往之後,他們的族群體系成為,牧團→次部落→部落→羌。到了魏晉時,部分羌人居於關中。他們的認同體系中,華夏式的姓氏與地望逐漸取代了各級部落,同時也有了羌與華夏兩種矛盾的認同;如南安姚姓羌人,自稱是羌人名族“燒當羌”之後,也自稱“有虞氏”(舜帝)之後。總之,自稱族名在民族邊緣研究中有更積極的意義;它不只是民族範圍的代號,各層次的族群自稱也表現族群體系結構以及認同變遷。同一族稱在不同時代,不同地區,甚至不同的個人中,都可能有不同的詮釋。這正如一位人類學家所言,族群本質(ethnicity)是在每一代、通過每一個人而不斷地重新詮釋而成。
漢文典籍中的他稱族名,尤其是有強烈“非人”含義的族稱,如戎、狄、蠻、夷、羌等,常直接表現華夏的異族意象,因此可視為華夏族群邊界的指標。譬如,“羌”有西方異族人的含義,指“那些在西方不是華夏的人”,因此它可被視為華夏的西部族群邊界。由商代到漢代,華夏民族不斷地向西方擴張(包括移民與同化西方的非華夏),使得原來的“羌”成了華夏。於是華夏心目中的“羌”也不斷往西方推移,以反映新的華夏族群邊界。這就是為什麼在漢文典籍中,由商代到漢代,“羌”所對應的地理與人群內涵不斷向西方推移。如果我們忽略了族群邊緣的本質以及同一族稱在不同時代的內涵變化,並忽略我們自己的族群本位偏見(ethnocentralism),那麼就很容易依賴這些歷史材料建構出一部“羌族遷移史”。事實上,許多聯系商代之羌與現代藏、羌族的“羌族史”,便是如此被民族溯源研究者建構出來的。從邊緣研究的觀點看,我認為一部由商代到漢代的“羌族史”所反映的不是某一“異族”的歷史,而是華夏西部族群邊界形成與變遷的歷史。關於這一部分,我將在本書第八章中詳細說明。由這個例子,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邊緣研究與溯源研究的不同旨趣。溯源研究者假設民族是有共同或相似血統、語言、文化的人群;人們能夠觀察到這些客觀的人群區分,因此古人所稱的胡、戎、羌與今人所稱的漢藏、苗傜、氐羌等都是客觀存在的“民族”。但站在邊緣研究的角度,我認為脫離了主觀認同,就沒有所謂的客觀存在的民族。因此所謂藏緬民族、苗傜民族或氐羌民族,事實上並非建立在其成員主觀認同上的族體;或者,只有在接受優勢群體或國家之族群分類概念,並長期生活在此概念所造成的社會現實中,這些人群範疇才可能成為人們主觀認同上的族群。
族源史料 許多歷史學家認為,史料中關於一個民族的族源記載,為追溯該民族的起源、遷徙及其與他族群間的關係,提供了直接的證據。這種研究典型的例子,見於錢穆對周人族源的研究。但是,由人類學與口述歷史的研究中我們知道,當個人或一群人通過族譜、歷史或傳說,來敘述與他或他們的祖先源流有關之“過去”時,其中經常所反映的並非完全是歷史事實。因此人類學家以所謂的“虛構性譜系”(fictive genealogy)來形容虛構的親屬關係譜系,以“結構性失憶”(structural amnesia)來解釋被遺忘的祖先。許多口述歷史學者,也采用社會記憶觀點(而非史實觀點),來處理采訪所得資料。
為何無論是在口述或文獻記載中,“族源”都常有如此的虛構性質?這是因為,“起源”對於許多社會人群的凝聚都太重要了。炎帝與黃帝是自稱炎黃子孫的中國人之共同起源。當然,我們知道炎黃確是虛實難以捉摸的神話人物。但是在凝聚人群上,這些起源是不是“史實”並不重要;宣稱自己是炎黃子孫的人,從來不用擔心炎帝或黃帝是否存在的問題。而且,為了適應現實環境的變遷,“起源”經常被遺忘、修正或重新詮釋,以改變個人或一個群體的認同,或重新界定當前的族群關係。因此,許多文獻中的族源資料,其中所包含的史實便相當有限了。雖然如此,在民族史邊緣研究中,族源資料是理解一個族群的本質,或觀察族群認同變遷最好的指標。以下我舉三個例子來說明。
首先,宣稱一個共同的起源—如商人稱“玄鳥降而生商”,大部分的藏族自稱獼猴之後,許多突厥民族中有祖先狼生傳說——等於是宣稱一種族群認同。這種族源傳說,反映一個民族的虛擬起源記憶。由這種起源記憶,我們能探索歷史上某地區人群的族群認同及其認同變遷。譬如,漢代部分河湟西羌自稱無弋爰劍之後,魏晉時期的黨項羌自稱獼猴種,南安羌人姚氏自稱是有虞氏及燒當羌之後;這些自我宣稱的族源,都表示不同的族群認同本質。因此,無論有多少考古、體質或歷史文獻上的證據,都無法證明河湟西羌、黨項羌與關中羌人是同一民族。因為造成一個族群的,並不是文化或血緣關係等“歷史事實”,而是對某一真實或虛構之族群起源的“集體記憶”。一旦宣稱新的祖源,即表示他們與原族群間的結構性失憶產生,新的集體起源記憶將他們與一些共有這些記憶的人群聯系起來。族群的結合與分裂,即在不斷凝結的新集體記憶與結構性失憶中產生。
其次,有些族源歷史透露族群認同的邊界。譬如,在《史記•周本紀》所記載的周人族源故事中,周人宣稱他們的始祖為後稷(農神),他們輾轉流徙於戎狄之間,曾嘗試行農業、定居,但遭到挫折。最後他們終於遷到周原,從此過著農業定居生活。這整個族源傳說所傳遞的信息是:雖然他們經常生活在戎狄之間,甚至有戎狄之俗,但他們強調祖先是行農業與定居的,他們也一直努力這麼做。因此這族源傳說反映,在當時渭水流域的族群關係中,部分人群以“農業”與“定居”來設定族群邊界,以排除另一些比較不務農而遷移較多的人群(戎狄)。無論這族源記載是否為有“史實”根據的記憶,這都是選擇性記憶,書寫或述說者以此強調該族群的邊界與特質。
最後,有些族源傳說也反映當時的族群關係。譬如,《後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記載巴郡南郡蠻的族源: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樊、瞫、相、鄭氏,皆出於武落鐘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為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眾皆嘆。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服者當以為君。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為廩君……四姓皆臣之。
這種族源傳說,一方面將五姓人群以共同起源聯系在一起,另一方面解釋巴氏在該族群中領袖地位的由來。它所透露的不是過去曾發生的事實,而是當時(漢晉時期)巴郡中部分人群間的族群關係。
人群以共同族源來凝聚認同,而認同變遷又由改變族源來完成。因此,強調、修正或虛構一個族源歷史,對於任何人群都非常重要。以此而言,每一個民族史的溯源研究,無論是對本民族或他民族溯源,本身即成為一個族群“起源記憶”的修正版,因此也成為我們探討族群認同與變遷的材料。由這個觀點來說,世世代代如司馬遷與傅斯年等中國歷史學者,他們的研究不斷強調選擇性的華夏歷史記憶,重新詮釋“過去”以符合本身與當代社會族群生活經驗,“華夏認同”也由此不斷得到新的本質、內涵與邊緣。因此,這些歷史著作皆可作為探討各時代、各地域人群華夏意象的“史料”。
另一方面,華夏歷史學家對於華夏邊緣各人群的溯源研究著作,所反映的也經常是他們在當代華夏意識下對華夏邊緣的塑造與重塑。因此,我們可以借著這些著作來探索華夏邊緣的變化(也就是華夏自我意識的變化)。譬如,近代歷史學者常建構一部部的羌族史或藏族史,將他們的源頭追溯到商代的羌。但川西北到西藏間許多人群,他們有自己的族群稱謂與歷史傳說。如此,這些少數民族的認同,便常徘徊在兩種版本的歷史記憶與族群稱謂之中。許多歷史學家認為,雖然少數民族不知道自己的來源,但仔細考察中國文獻記載,輔以語言、考古、體質等資料,這些少數民族的族源可以被重建。但在民族史邊緣研究的觀點看來,以藏族族源為例,獼猴說(此說出於古吐蕃文獻)與西羌說(此說出於漢歷史文獻),並沒有孰是孰非的問題。對藏族知識分子而言,接受哪一種“歷史”,表現的是他們如何定義“我族”以及他們如何理解“我族”與中華民族之關係。對於漢族來說,這則是如何建立一個異質但友好的華夏邊緣的問題。
主題書展
更多書展今日66折
您曾經瀏覽過的商品
購物須知
為了保護您的權益,「三民網路書店」提供會員七日商品鑑賞期(收到商品為起始日)。
若要辦理退貨,請在商品鑑賞期內寄回,且商品必須是全新狀態與完整包裝(商品、附件、發票、隨貨贈品等)否則恕不接受退貨。